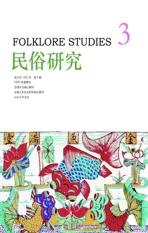共谋与协力:节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源化实践
——以恩施土家女儿会为例
2021-11-25桂胜谌骁
桂 胜 谌 骁
恩施土家女儿会发源于恩施石灰窑、大山顶一带,是月半期间(1)在恩施地区,月半是指农历七月十二。另外,石灰窑、大山顶皆存在女儿会的节俗,但两处时间不一致。石灰窑女儿会是在农历七月十二,处于月半期间;大山顶女儿会是在农历五月初三,在端午节前两天。1995年,女儿会从农村搬到城市,但是恩施政府、旅游局等官方主体主要以石灰窑女儿会为基准,在农历七月十二前后组织开展与女儿会相关的文化展演活动,因而本文选取石灰窑女儿会习俗进行分析。以赶场相亲、对歌传情为主的婚恋民俗(2)参见湖北省恩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北省恩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编印:《恩施土家女儿会·恩施文史·第十六辑》,恩施州新闻出版局印刷厂,2005年,第20-21页。,于2009年被列入湖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民俗类保护项目。有学者认为女儿会产生于改土归流之后,是土家先民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产物,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3)参见曹毅:《城乡视角下的民俗节庆之争——对湖北恩施“女儿会”民俗移植的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但清代以来的地方性文献、碑刻中却鲜有女儿会的记载,直到1983年恩施建州之后,文献中才出现相关的内容。(4)参见《鄂西土家族简史》编写组编:《鄂西土家族简史(初稿)》,1983年,第110页。目前,作为恩施土家族节日类非遗项目的女儿会,俨然成为恩施市一年一度的民族盛会,每年农历七月十二前后,政府组织举办女儿会开幕式,企业商家、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小摊商贩等纷纷涌入,活动现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学术界对于节日类非遗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对保护主体的讨论与分析,如李玉臻关注到政府在节日实践中的主导性地位(5)参见李玉臻:《从边缘到中心:旅游背景下民族传统节日转型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学术论坛》2009年第2期。; 李靖注意到地方宗教人士参与节庆空间的表述(6)参见李靖:《印象“泼水节”:交织于国家、地方、民间仪式中的少数民族节庆旅游》,《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邵媛媛等人指出民众的族群关系影响节日文化秩序递演(7)参见邵媛媛、彭虹:《从“族群界别”到“传统风俗”:沧源勐角乡泼水节节日秩序的涵义演变》,《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薛洁等人则强调家庭对于节日文化传统保护的价值。(8)参见薛洁、韩慧萍:《家庭教育传承对于“非遗”保护的价值和意义——以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为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而对于恩施土家女儿会的研究也存在相关著述,如杨洪林指出政府的社会命名才使女儿会得以重回公共文化领域(9)参见杨洪林:《非物质文化的历史境遇与公共文化重塑——以恩施土家女儿会为考察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高卫华等人认为媒体将女儿会打造为民族文化符号从而推动其发展。(10)参见高卫华、杨兰:《大众传媒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符号化结构功能——以〈恩施日报〉报道“恩施女儿会”为例》,《当代传播》2012年第5期。以上研究有助于认识和理解节日类非遗保护中不同主体的文化实践,但总体而言,大多数的讨论都是从比较单一的主体出发进行分析,缺乏对于保护主体多元性的关注。而节日类非遗保护实践往往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各种参与力量都是一种主体性存在,是文化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不利于其整体性保护,从而影响文化的存续与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多元化保护主体的角度展开论述。
文化资源化理论内涵了文化价值的多元性,指出文化保护有赖于多方参与主体的热情和付出。(11)参见李向振:《文化资源化: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理念转换及其价值实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0期。引入文化资源化理论,有利于保护主体多元性的分析和讨论,因为不同参与主体在实践中赋予了非遗文化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共同构成了非遗保护的多元价值,而这些价值本身又决定了所有参与者都具有主体性。通过引入文化资源化理论对恩施女儿会进行历时性分析,有助于更加直观地呈现各方参与力量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共谋与协力,从而赋予该非遗项目多元性文化价值,使其保护实践更具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本文将立足田野作业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女儿会最初如何被“发现”?其二,政府、企业、民众等主体如何参与当下女儿会的文化实践?其三,女儿会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多元文化价值的表达?其中,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女儿会作为节日类非遗项目,其文化资源化实践中各参与主体的关系。
一、恩施土家女儿会的“发现”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年轻的自治州。自古以来,恩施便是多民族汇集之地,其中土家族数量尤为众多。在长达四百多年的土司制度时期,恩施形成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局面,产生了诸多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改土归流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但恩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仍然保留着浓郁的土家风情,过月半、赶场、唱山歌是恩施地区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沿袭至今。女儿会将“过月半”“赶场”“唱山歌”三种民俗文化要素有机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土家婚恋民俗。月半期间,未婚少男少女身着盛装,佩戴最好看的首饰前来赶会。少女们将提前准备好的山货摆在地上,等待有缘人前来选购。而小伙子们佯装闲逛,漫不经心地与“摆摊”姑娘搭讪。如果双方交流顺畅、互相中意,就会另择稍微隐蔽之地对唱山歌,互表心意,甚至约定终身。(12)参见湖北省恩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恩施土家女儿会》,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9-12页。女儿会最初主要在恩施偏远山区石灰窑等地流行,如今节会在市区举办,日益吸引了来自政府、企业、民众等社会各界的关注。源自山区的女儿会从被外界“发现”到最终成为恩施州的地域代表性节日,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一)借势首次“亮相”
1983年12月1日,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13)1993年,“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石灰窑人李辉轩当选为该州的第一任州长。1984年农历七月十二,红土乡人民政府在石灰窑集镇举办恩施建州后的第一次女儿会庆典,相关部门不仅动员、组织了恩施市各商家、厂家来女儿会举办商品展销会(14)参见《女儿会的社会价值》(2020年3月20日),载土家族文化网。网址http://www.tujiazu.com.cn/Archives/IndexArchives/index/a_id/6042.html。访问时间:2020年10月6日。,还邀请了州长等其他州市机关干部前来“赶会”。州长的到来吸引了诸多周边的乡民,不少城市居民也前往石灰窑参加女儿会。此外,还有诸多媒体记者、学术研究者来到石灰窑,通过后期撰写新闻稿、学术论文的方式揭开了女儿会的“面纱”,使外界“发现”了女儿会。刘铁梁曾对民俗文化价值进行了“内外”的界定,指出“内价值是指民俗文化在其存在的社会与历史的时空中所发生的作用,也就是局内的民众所认可和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价值。外价值是指作为局外人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化产业人士等附加给这些文化的观念、评论,或者商品化包装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等价值”(15)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就此而言,传统石灰窑女儿会满足未婚青年男女社交需求是其内在价值的体现,而1984年政府主导举办女儿会,推广地方文化,发展地方经济,更多地是对其外在价值的发掘与利用。当地红土乡政府邀请州长李辉轩回到故乡参加女儿会,借势宣传女儿会,以此推动地方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力图将女儿会转化为地方性文化资源,凸显地域特色,提升地方知名度,同时女儿会也转化为潜在的政治文化资源,是地方政府政绩的彰显。而女儿会上举办展销会则是将其转化为经济文化资源,强调经济效益的发挥。除此以外,据李辉轩回忆,当地民众在女儿会上进行物资交易的场面非常热闹。(16)参见李辉轩:《恩施州首任州长李辉轩——关于建州后首次女儿会的回顾与联想》,载女儿会故乡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I53ZcGAua015Z3yc8lzhwA。访问时间:2020年10月6日。剩余农产品、家庭手工艺品等市场交易活动一直是我国农村家庭重要的生计来源,由此可见,政府主导下的石灰窑女儿会同样具有地方民众日常谋生的功能,彰显了其内在的生活性价值。
(二)走向城市“舞台”
1995年,为推进中国民俗风情旅游年活动,湖北省将女儿会的举办地点迁至恩施市区,女儿会第一次“进城”,并且被选择为“土家族的传统节日”。“进城”后的女儿会逐渐成为集文化、商贸、旅游为一体的民族盛会,极大地推动了恩施文旅经济的发展。2000年4月5日,恩施州第一次全州旅游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明确要将恩施打造成“生态旅游州、民族风情园”(17)参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恩施州志(1983-2003)》,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7页。,文化旅游成为恩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民俗文化在旅游事业发展中的驱动性作用引起了高度重视。于是,政府将女儿会引入梭布垭石林景区,尝试将文化习俗与自然风光相结合。活动当日(农历七月十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20多家媒体争相报道采访,进一步提升了女儿会的对外影响力。(18)参见刘绍敏、刘清华:《恩施土家女儿会演变揭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同年,女儿会与州庆节、牛王节、摆手节一同被恩施州人民政府视为“全州四大民族节日”。由此,女儿会一步一步“走出”大山,其文化习俗范围、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成为恩施州民俗节庆。不难发现,女儿会的“城市化”进程始终充斥着经济文化资源属性的挖掘与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模式。以女儿会文化为核心发展旅游经济,不仅具有优化城市文化生态环境、推动产业升级等溢出效应,而且女儿会本身也获得了文化生命力,成为地方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在民族属性、传承范围等方面得到了官方的充分关注。
(三)从恩施民族民俗文化“名片”到湖北“非遗”项目
2006年底,恩施市党政主要领导换届,新的领导班子通过召开会议等形成了一个总体性发展构想,创造性地提出了“12345”跨越式发展的工作思路。(19)参见《资料:恩施之变哲学透视(1):从“12345”到仙居恩施》(2011年04月22日),载央视网。网址http://news.cntv.cn/china/20110422/112341.shtml。访问时间:2020年10月6日。在该思路的指导下,为充分挖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恩施市决定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打造恩施土家女儿会等“三张名片”(20)参见伍功勋:《让“女儿会”成为恩施走向世界的名片》,《恩施日报》2009年8月29日。。女儿会由此成为展示恩施城市形象、推动恩施经济发展的重要民族民俗文化名片。虽然将女儿会打造为恩施“三张名片”之一,是对女儿会潜在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肯定,但结合“三张名片”的确定背景来看,女儿会则是被纳入到新任领导的政治思路、构想之中,作为一种政治资源服务于官方权威的建构。
2006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恩施却没有任何民俗事象被纳入其中,这引起了相关部门对于非遗申报工作的重视。恩施市的具体相关事务由市文体局负责,预备申报女儿会、灯戏、傩戏、社节4个项目,其中女儿会是恩施市的首选项目。女儿会申遗小组首先整理了相关材料并制作了申遗项目书,其次前往大山顶、石灰窑拍摄了相关视频资料,并成立了女儿会传承保护协会。2009年5月27日,女儿会被列入湖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类保护项目。从中可见,女儿会的申遗工作遵循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路,是为了填补恩施非遗空白而进行的一项文化工程。此时,女儿会主要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资源、政治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为恩施争取象征资本,而这种象征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地方社会发展的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
自被外界“发现”起,女儿会便脱离了“自在自为”状态,踏上了文化资源化的发展之路。从首次“亮相”到“搬进”城市再到被确立为恩施“三张名片”之一,并被列入湖北省“非遗”名录,女儿会彰显出了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等多重文化资源属性。虽然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女儿会所承载的核心资源属性因时而异,但就女儿会节俗文化本身而言,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生态,它往往同时满足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多种需求,其具体的资源属性也是相互交织难以区分的。回顾女儿会的“发现”历程,政府的介入是其实现资源转化最直接的驱动性力量,政府通过引入市场资本等要素使女儿会更具创新性和发展活力。
二、女儿会的多方参与实践
1995年,女儿会从农村迁往城市,其文化资源性转化实践在时空环境中得以加持。交通运输方面,沪蓉、沪渝高速的完工与宜万铁路的建成大大缩短了恩施到武汉、宜昌、重庆、成都等城市的“距离”,推动了恩施旅游业的发展,讲好恩施故事、彰显恩施特色成为文化旅游经济的关键。女儿会作为综合性的民俗文化空间,成为擦亮恩施旅游特色的文化名片。近年来,电视、微博、微信等新旧媒体交相辉映的融媒体格局加速了女儿会文化传播与推广,推动女儿会进一步融入民俗文化与旅游产业相交织、非遗保护与经济开发相呼应的文化旅游市场。此外,女儿会的发展也得到了相关学者的关注,如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曾带领其研究团队前往恩施调研女儿会。(21)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项目“武汉大学非遗扶贫工作思路”研究团队。可见,女儿会资源化进程的加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其中,其价值内涵也日趋多元化。鉴于此,对女儿会文化资源性转化的认知可结合2019年的展演情况,在其实践场域中讨论政府、企业、民众如何参与女儿会及其背后的逻辑。
(一)综合性价值的挖掘:政府的引导与策划
2019年恩施土家女儿会由恩施市委、恩施市人民政府主办,恩施市委宣传部、文旅局、广播电视台承办,共青团恩施市委统一组织。(22)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党、团、事业单位与政府存在一定的区别,但与一般性民间组织相比,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因此本文将之宽泛地统称为政府。整个活动中,政府始终扮演主导性角色。首先是前期宣传,2019年7月1日起政府开始着手宣传推广,包括海报张贴、出租车电子屏幕广告以及微博、微信推文等方式。从文案来看,政府前期宣传除了扩大女儿会活动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以“招募”为导向:一是招募单身男女参加女儿会相亲活动;二是招商引资,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标。其次是组织与展演,本次女儿会开辟了龙马小镇、梭布垭石林、恩施市区风雨桥、红土石灰窑等多个会场,其中龙马会场最为隆重,也是政府组织前期招募人员参加相亲活动的主会场。在龙马女儿会中,开幕式是场面最热闹、观众最多的环节,主要以歌舞表演的形式展示女儿会的文化内涵,着重凸显与赶场相亲相关的文化元素,如开场山歌对唱《郎在施州府》、舞蹈《赶场忙》、歌舞《土家女儿会》《东方情人节》,皆为恩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以赶场相亲为故事原型改编而成。此外,还进行了茶艺表演,介绍了恩施茶产业的发展历史。最后是领导发言,表达对女儿会推动恩施文化旅游发展的期许。开幕式之后,相关部门组织相亲人员参加娱乐节目式的互动游戏。而风雨桥会场以举办晚会为主,晚会中组织男女相亲嘉宾开展互动游戏。梭布垭会场则举办了音乐节、山地自行车比赛、篝火晚会、拦门定亲仪式等活动。
各分会场风格迥异的展演形式使女儿会呈现出丰富的活动面貌,政府作为官方策划者与组织者直接推动了女儿会的文化资源性转化,在不同层面发挥其价值与功能:其一,招商引资、推介茶产业是政府“以文促经”的具体举措。近年来,以恩施玉露为代表的茶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以女儿会为契机,提升恩施茶叶的知名度,彰显了女儿会促进地方产业发展的经济价值;其二,政府组织单身青年参加相亲活动,实现了女儿会满足单身青年社交需求的社会价值;其三,开幕式中的歌舞表演节目不仅表达了女儿会的文化内涵,其歌舞本身亦为展示民族风情的文化符号,体现了女儿会对于凸显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价值;其四,在会场选址方面,龙马会场所在的龙马风情小镇位于国家综合扶贫改革试点龙凤镇龙马片区,是国家综合扶贫改革试点重点项目。成为女儿会的主会场,不仅有利于提升龙马风情小镇的知名度,促进其旅游业发展,而且大量游客的前往也推动了当地餐饮、小吃等地方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商家及部分周边居民的经济收入,发挥了女儿会助力脱贫攻坚的时代价值。
(二)经济性价值的追求:企业的投资与加盟
女儿会以“赶场相亲”为主要特征,“赶场”是相亲的外在形式和有效契机,而“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经济场域,也是商户、摊贩的经贸活动聚集地。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背景下,企业以更加多元化的形式参与女儿会。其一,直接参展。这是最为传统、直接的参与方式,参展企业大多借助女儿会节庆的噱头,推出五花八门的特价促销、优惠套餐、节俗定制产品等活动,吸引顾客。如恩施洞藏老酒“化米洞”推出了“土家女儿会定情酒”,并且在女儿会期间签单全款八折优惠,订单定金交200元抵300元,还可以获赠洞藏老酒一提。其二,物资赞助。这是最为显眼的参与方式,主要是通过赞助将企业符号投射到女儿会活动物资上,如会场布置的装饰品、游戏活动的嘉宾奖品等后勤所需物资,运用企业识别系统中的视觉识别策略,提高企业logo的出镜率,以此提升企业知名度。其三,内容互动。这是最为巧妙的参与方式,具体表现为将企业产品性能、特征等宣传穿插进节俗活动之中,如女儿会展演中有一项游戏环节,其内容是以吉利汽车配置为比赛文本,参赛嘉宾念得越快越准则得分越高,获胜几率越大,使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广告,甚至在参与或者观摩活动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了解企业产品性能或者内容,成为企业潜在的消费者。
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费者社会”(23)[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6页。,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超出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的阶段,商品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表示着生活质量的物质和文化的复合物。(24)参见张卫良:《20世纪西方社会关于“消费社会”的讨论》,《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物的消费”转向“符号消费”,人们将消费视为自我凸显的“符号”,甚至将其看作一种“交流体系”,一种“语言的同等物”,以此传递和实现自身的表达。(25)参见[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页。企业以参展或者赞助的形式介入女儿会,不仅以广告的方式扩大其知名度,而且试图借助女儿会浪漫的婚恋文化提升其产品所象征或者代表的意义、美感、档次和情调,以此迎合市场关于产品符号和意义的消费。可见,女儿会转化为经济资源也暗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细胞,它们也是女儿会活动中最为活跃、积极的行为主体,为女儿会活动筹划、组织注入了极具创新性的活力,如由企业赞助的扫描微信二维码摇一摇的红包活动,吸引了诸多观众,使现场活动氛围热闹非凡,有助于女儿会文化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传承与发展。但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皆为利润的最大化,参与女儿会同样是市场经济逻辑支配下而产生的商业性逐利行为,其关注的重点亦为女儿会所蕴藏的经济文化价值。
(三)社会性价值的认同:民众的参加与叙事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提出:“每一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所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的价值或意义评判。”(26)巴莫曲布嫫、张玲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就恩施土家女儿会而言,其文化持有者——民众大多是在政府的引导与资本的推动下,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从而赋予女儿会内在的社会文化价值。首先是作为“相亲者”参加女儿会,单身男女大多先在公众号上报名,加入共青团市委所组织的相亲方阵,再由工作人员统一组织参加相关活动;市区的风雨桥会场,也有不少民众通过现场报名参加互动游戏或者张贴个人信息到相亲榜等形式参与相亲活动。其中参与者大多都是与同事、朋友一同前往,将女儿会视为周末出游的契机;也有不少人表示参加活动是为了感受女儿会文化。事实上,参与者大多都非常渴望能够遇到一个心仪的有缘人,“想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27)在微信公众号报名后,工作人员将报名对象拉进一个联谊交友群,联谊群中的成员表达了该想法。,但又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正如周某所言,“就是看看自己运气好不好,能不能遇到合适的另一半”(28)访谈对象:周某;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19年8月15日;微信访谈。。而钟某谈及参与感受时,告诉笔者“遇到了一个女孩,有了点不一样的感觉”(29)访谈对象:钟某;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19年12月20日;微信访谈。。其次是女儿会活动的观看者,既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也有看“热闹”的周边居民,他们将女儿会视为休闲娱乐的场域。此外,还有风雨桥会场相亲榜前三三两两的人群,以大爷大妈为主体,大多是替晚辈们寻觅良缘。最后是女儿会“原生态山民歌赛”中的表演者,他们都是来自恩施市各乡镇的代表队成员,大多是“山民歌”爱好者,未受过专业和系统的训练,所表演的节目多为自学自编自演,普遍将该活动视为自我展示的平台和与亲朋好友共同出游的契机。
文化具有一定的共享性,恩施土家女儿会作为地方性民族文化节庆活动,理应为广大民众所共同参与、共同享受,从而彰显其内在社会性价值。其一,作为以婚恋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节日,女儿会为单身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社交平台。在职业分工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日常社区生活中的公共空间被不断“抽离”(30)黄剑:《日常实践的分化与回归:生活文化嬗变的机理分析》,《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的背景下,参与活动相遇或者长辈物色而得之良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单身人士的幸福生活需求;其二,传统民俗文化中,诸多民俗节日根据农事节律而设置,以调试民众日常艰辛的劳作生活。而如今的女儿会活动,被大部分参与者视为与亲人、朋友共同出行的契机。事实上,虽然技术的发展减轻了民众身体上的劳累,但现代社会中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往往使人内心感觉疲惫,以女儿会为契机安排一场或远或近的旅行,不仅使日常生活中积攒的压力得到调适和宣泄,而且也是民众进行社会资本积累、家庭关系建构的绝佳时机。因此,历年女儿会开幕式大多安排在周六,这正是基于民众休闲娱乐需求的考量。其三,女儿会中有一批小摊贩,他们自发到会场售卖手工艺品、炸土豆、凉面凉皮等。对于他们而言,女儿会只是短暂性的机遇,交易的绝对数额不会太大。但是对于某些年迈的老人而言,却是赚取零用钱的绝佳机会,因为他们出售的是手工布鞋、鞋垫等,平日里很难卖出去,却能在女儿会上吸引部分外地游客,卖上好价格,很可能成为老年人积蓄的主要来源。
从不同主体的角度入手探析女儿会当下发展态势,可以发现其资源性转化仍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其政治、文化及社会效益。政府具有社会治理的职能,作为女儿会的总体规划师,力图挖掘整合其促进文旅经济发展、增进地方人民福祉等综合性文化价值。而企业资本在民俗文化发展中越来越活跃和主动,他们能动性的发挥使得女儿会在经济文化资源的转化层面更为突出、明显。内在文化价值的享用者——民众很难为女儿会的发展直接建言献策,但这不代表民众完全无法享用其文化成果。事实上,企业在女儿会上开展商业性活动正是为了吸引民众,并将其吸纳为潜在的消费者,所以民众也能在活动中感受参与的乐趣。只是这种乐趣主要是在市场经济逻辑的支配下而产生,与日常生活中所充斥的消费主义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诸多看似“快乐”的参与者也可能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新鲜、有趣、充满人情味的风俗文化。
三、女儿会的多元文化价值表达
从2019年恩施土家女儿会实践中,可见各参与主体都在不同层面推动着女儿会的文化资源化发展。通过不同参与主体的话语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呈现女儿会的多元文化价值,从而凸显其文化保护实践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政府在女儿会文化资源转化实践中担任着主导性的角色,决定着女儿会发展的方向与格局。2019年女儿会风雨桥会场立了一块“温馨提示”牌,大体内容是告知周边居民风雨桥女儿会的举办时间,提醒居民可能带来的生活不便,落款是“中共恩施市委、恩施市人民政府”。提示内容的开头“为进一步擦亮女儿会文化名片,提升恩施文明旅游城市形象”则言简意赅地阐释了政府对于女儿会活动的总体性定位。龙马风情小镇女儿会会场开幕式中的领导致辞则更直观地反映了政府对于女儿会的态度。
从1995年开始,恩施女儿会由自发的民间节日开始变成了政府主办的民族盛会……实现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倾力打造恩施大峡谷、土家女儿会、恩施玉露茶“三张名片”,全力开展脱贫攻坚“三大行动”,借助龙凤综合扶贫改革试点、东西部协作等外力,全市干部群众砥砺奋进,勠力前行。(31)2019年恩施土家女儿会龙马会场开幕式中某领导致辞。参见《直播回顾|情定女儿会·爱在恩施行,土家女儿会开幕!》(2019年8月9日),载云上恩施APP。网址https://live.xinhuaapp.com/xcy/reportlist.html?liveId=1565315160902129。访问时间:2020年3月1日。
以上领导致辞的部分内容表明政府在关注女儿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注重其社会价值的呈现。事实上,政府行为总体上以实现社会治理为目标,利用丰富资源维持社会秩序,维护民众整体利益,推动社会更加民主公正。(32)向德平、苏海:《“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具体到女儿会活动,以民俗文化推动社会治理,以经济为切入点无疑是效果最为明显的,任何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无法忽视经济建设,而且经济发展与其它方面的发展相比是最易量化、统计的。此外,经济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如在致辞中提及的“文化繁荣”“扶贫改革”等。
企业本质上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其行为皆以经济利润为导向。就某种程度而言,企业与政府在女儿会经济效益的追求上,存在一种合谋关系。政府关注女儿会对于地区经济的效益,而企业则为地区经济的微观实体,因而政府谋划的地区经济发展实则囊括了企业的发展,企业谋求自身经济发展也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女儿会龙马小镇分会场联投公司职员费某说道:“作为一个新开发的风情小镇,龙马坚持文旅融合的发展理念,希望能够通过女儿会这样的民俗节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龙马,打出龙马的知名度。今年的龙马是女儿会的主会场,去年女儿会也是以龙马为主会场。”(33)访谈对象:联投公司职员费某;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19年8月13日;微信访谈。以文旅融合为经营理念,企业越来越注重文化在经营活动中的价值,而女儿会作为地方代表性节庆文化,更是诸多企业争相追逐的文化资源。以女儿会为契机吸引消费者,实现了女儿会的经济文化价值表达。但是在具体实践层面,企业与政府活动理念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某市场部职员鲁某认为:“女儿会相亲大会完全没有相亲气氛,相亲成员的活动参与度不高,缺乏面对面的交流。泼水节活动完全没有调动起来,没有音乐,不够嗨,很多都是小孩子在那里玩。像之前的泼水节,请了几个比基尼美女游街,就把人吸引到活动现场。泼水的过程中,现场放着DJ背景音乐,气氛很嗨,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参与进去了。”(34)访谈对象:某市场部职员鲁某;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19年8月13日;微信访谈。可见,企业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政府则在地方经济建设之外,还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引导活动规范、促进文化传承等责任。因此,尽管政府举办的活动规范有序,但对企业而言无法真正刺激、吸引民众。而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显然不可能如企业这般为吸引人气而“无所不用其极”。因而,企业看起来似乎比政府更关注民众的感受与体验。在市场经济逻辑支配下,企业经营大体上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并迎合其消费偏好,以此在市场竞争中攫取优势地位。参与女儿会的企业要想通过女儿会节俗文化吸引消费者的眼球,离不开女儿会对消费者不同层次需求的满足,因而眼光长远的企业也会关注女儿会内在文化价值,注重女儿会中的民众参与。
民众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是其价值和意义的评判者。而对于恩施女儿会,地方民众的认知存在差异性:民众对它的历史记忆大都极其模糊,部分民众将女儿会等同于政府或者其他组织举办的一场表演活动,他们只是作为台下观众参与其中;也有民众积极参与到当地女儿会相关的活动中,加入女儿会传承协会,不仅积极挖掘和整理女儿会文化习俗,还热情地投身于女儿会展演活动,对其相关的发展历史、非遗认定等情况了解甚多。
事实上,就一般民众而言,大多是出于实用主义原则参与其中,不管是台下观众还是活动积极分子,民众更多关注的是当下的女儿会。尽管历史记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但石灰窑民众大多以女儿会发源地为荣,正如史某所言“女儿会毕竟是发源于石灰窑,提起女儿会我心里还是很激动、自豪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是希望能为女儿会做点事情,比如做个志愿者之类的”(35)访谈对象:史某;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20年3月1日;微信访谈。。在女儿会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推文中总能看到类似于“为家乡文化点赞”的留言。无论女儿会是作为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只要有政府关注、活动场面热闹,地方民众就会引以为豪,产生文化自信心理。还有民众认为石灰窑作为女儿会的发源地,应该受到政府更大力度的建设和发展,视女儿会为帮助家乡争取资源的象征资本。当然大部分人还是更关注活动体验,即女儿会的“有用性”(36)桂胜、孙仲勇、李向振:《文化空间再造与少数民族“非遗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鄂西恩施市的田野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不少单身人士表达了对活动的期待:
如果真的能够像原始的女儿会一样,待嫁闺中的土家姑娘,早早起床,精心打扮以后,去镇上逛逛街买买东西,其实不是去买东西的,而是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对象,就更让人向往了。(37)访谈对象:史某;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20年3月1日;微信访谈。
平时工作很久不碰面的朋友,可以借机一起嗨一下,聊聊天之类的,还是很不错的。当然女儿会相亲会也可能有相亲成功了的,不过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节目的形式,单身男女青年参加一下可以认识一些朋友,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也有可能遇到爱情。(38)访谈对象:张某;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0日;微信访谈。
其实吧,我参加女儿会,更多的心态是凑热闹。当然除了凑热闹,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小期待的。特别是现在感觉自己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39)访谈对象:赖某;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19年12月20日;微信访谈。
虽然现代社会社交方式日趋多元化,性别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婚恋早已实现自由,但还是有不少民众期待在女儿会节俗文化空间中找寻幸福,这表明女儿会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语境并未完全消失,它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青年男女进行社会交往、邂逅浪漫爱情的情感需求。除了婚恋以外,民众也关注其他社会生活层面的价值,正如原生态民歌大赛的参与者朱家二儿媳所言:“只要一家人能够出来玩玩,大家开心就可以了。”(40)访谈对象:朱家二儿媳;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19年8月12日;访谈地点:清和园广场。女儿会在民众的参与实践中实现了社会文化价值的表达,包括社会交往中社会资本的建构、休闲娱乐中身心愉悦的慰藉等多维度的效应。其中民众着眼于女儿会微观个体需求的满足,并不会过多关注政府、企业等外在主体的目的及动机。虽然也有民众指出,“现在的女儿会已经不像原始的那样了,已经被商业化了。之前去女儿城看过他们在女儿会期间搞的现场相亲活动,感觉不怎么样,像翻版的非诚勿扰,还是比较乱的那种”(41)访谈对象:史某;访谈人:谌骁;访谈时间:2020年3月1日;微信访谈。。但此类评论依然是立足于自身的参与感受,女儿会活动使其产生了不良观感,他将其归因于女儿会的商业化运作,换而言之,如果商业化的女儿会活动创新、有序,使其感受到趣味性,他将不会对此存在质疑。事实上,不少民众乐于参加女儿会相关的活动,龙马女儿会开幕式当天不少附近的男女老少一大早提前赶往会场占座,开幕式后半部分时间阳光比较强烈,很多乡民带着草帽、打着遮阳伞甚至以跟着阴凉跑的方式坚持到开幕式结束。会场还有不少市民携带家人前去观赏,在张灯结彩的风雨桥前拍照、玩耍等,晚会期间更是人山人海,舞台下围满了密密麻麻的观众。为调动民众积极性,晚会安排了由企业赞助的“摇一摇得红包”活动,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可见民众的真正关注点在于是否能够在活动参与中获得愉悦、惊喜、轻松等体验。
总之,女儿会资源性转化实践的参与主体因其立场、目标的不同而形成了差异性的价值诉求: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关注女儿会文化的综合性价值,力图以此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组织,更偏向于发挥女儿会的经济效益,从中谋取经营利润;而民众作为普通参与者,更注重活动参与的感受、体验以及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等社会性价值,将其视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而差异性的背后也存在着互为主体,即“主体间性”的交往过程(42)参见岳永逸:《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03-241页。,如政府与企业皆为女儿会经济文化价值的拥趸;企业吸引消费者需关注民众参与活动的体验感受,而政府以女儿会为契机进行文化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人民谋福祉。只是现实经验层面,各主体受制于总体性目标的考量,其实际行为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冲突。以上不同参与主体价值诉求的满足,使女儿会的多元文化价值得以表达和实现。
四、结论与思考
如前所述,女儿会的文化资源化实践是多方共同参与、协力推动下促成的文化共谋:政府利用文化政策、融媒体资源整合地方特色民族文化,企业、民众等主体也基于自身诉求积极参与其中,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利用、博弈与妥协,使女儿会的周期性展演成为可能。由此可以看出,节日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是一项系统性的文化工程,是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协力促成的文化实践,过于强调或偏袒任何一方都是不合理的。如过于强调企业,节日文化实践就会沦为商业性展演而背离文化初衷;而过分强调民众,则会导致缺乏媒体宣传、资金支持等外在动力而丧失文化吸引力。各方参与力量不断平衡与协调,在实践中赋予其多元文化价值和意义,使节日类非遗文化得以更好地延续和发展。
民俗文化很难停滞在某一时空而不受外界文化的干扰,非遗也不是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能拯救人类心灵与社会问题的“文化法宝”(43)田素庆:《“原生态”的幻象——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剑川石宝山歌会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相反,诸多非遗项目在人类文化长河中一直传承与发展,正是由于它们能转化为经济、文化、政治等不同领域的资源,所以看似“来历不明”的女儿会才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化资源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本真性”“原生态”等评判标准,更多关注女儿会当下的多元文化价值。因而,非遗实践中的民俗或传统文化再生产现象不应被视为文化保护的众矢之的,而是囊括了民俗文化多元价值表达与实现的社会事实。厘清社会事实背后的生成逻辑,关注各参与主体的行为诉求,有利于节日类非遗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节日类非遗保护的文化资源化实践。
民俗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流动的概念(44)参见徐赣丽、黄洁:《资源化与遗产化: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趋势》,《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非遗也不是静态化的民俗事象。文化资源化理论对多元参与主体的关注,有助于认识节日类非遗在动态化实践中不同维度的价值表达,有利于平等地对待各主体力量的期待与诉求,摒弃简单化倾向的价值判断,从而客观中立地评价不同参与主体的实践意义,使“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