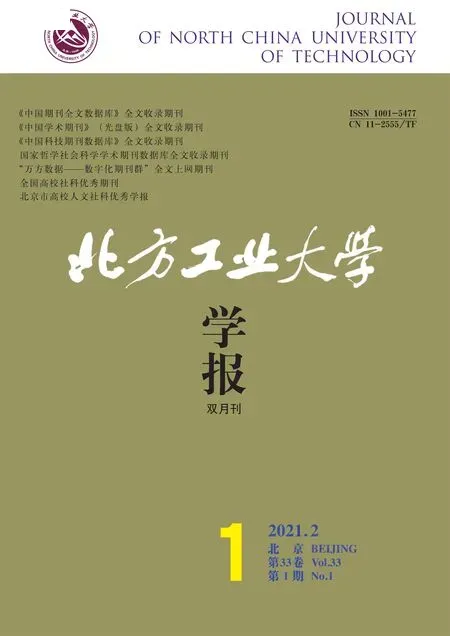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生成*
——《文心雕龙》与早期文献中的文学观
2021-11-23蔡宗齐李卫华
[美]蔡宗齐 李卫华 译
(1.伊利诺伊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61820,厄巴纳-香槟市; 2.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050024,石家庄)
刘勰的《文心雕龙》①通常被誉为前现代中国最系统的文学批评作品,其范围之广、见解之丰富都是无与伦比的。对刘勰批评体系建构的探讨,是《文心雕龙》研究中最富有成效的学术领域之一。②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内在连贯性或系统性出发,探讨这一系统性著作的研究却明显匮乏。在这里,我打算用这种大视野来集中审视《文心雕龙》的文学观。我将首先讨论从远古到汉代发展起来的三个主要的文学观念,然后我会思考刘勰是怎样综合了前人的关切,形成自己的综合文学观的。③为了证明这四种文学观的相关性,我将识别并讨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通过这种相关性,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系统。
1 《尚书》中的宗教文学观
最早的文学观一般可以追溯到“诗言志”,这一说法出自传说中的皇帝舜与他的乐官夔的谈话,记载于儒家的六经之一《尚书》的第一章《尧典》。④尽管很少有人相信这一说法真的出自传说中的皇帝之口,但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它传递了已知最早的文学观念。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⑤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
这些话虽然简短,但涵盖了艺术过程的三个主要阶段:起源于人的内心、外在表现形式、对外界的影响。诗歌被视为旨在协调内部和外部过程的表演的最初部分。在这场表演中,表演者试图通过诗意的话语、吟咏、歌唱、奏乐和舞蹈来传达“志”,或者说是心灵的运动。⑥这种表演的一个理想结果是达到内心的平衡,一种被认为有利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心理状态。通过观看或参与这样一个表演过程,年轻人可以获得一个平衡、和谐的性格。然而,这种演出的更重要的目的是使人与神相一致。通过一系列强化的有节奏的身体动作,在百兽的舞蹈中达到高潮,表演者寻求取悦于神并与之和谐相处。夔下令的百兽舞蹈通常被认为是穿着动物皮毛的图腾舞蹈的一种形式⑦。然而,像孔颖达这样的学者更喜欢对“百兽率舞”作字面的理解。在孔颖达看来,这种动物被感动到一起跳舞的描述,是为了表现“神人以和”的神奇效果。他写道:“人神易感,鸟兽难感。百兽相率而舞则神人和可知也。”[2]
这种舞蹈,不管是不是图腾舞,都标志着整个表演的中心和高潮,它对实现人与神的和谐是最有帮助的,尽管这一点是由夔而不是由舜自己明确提到的。在追溯“志”的“外化”序列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言语到吟咏,再到奏乐,再到舞蹈的高潮。这标志着有节奏的身体运动的稳步加强,这种渐强表现出很大程度上基于身体表现力的价值尺度。诗歌中身体最不活跃,被放在底部。而舞蹈中身体最具活力,构成了整个表演的高潮。
这种对身体运动速度的强调通常被认为是大多数原始传统宗教表演的一个显著特征。有人将其归因于原始人的愿望,即模仿、回应甚至“控制自然界和生命中无处不在的神秘力量,这些力量潜在地活跃于人间事务中”。[3]在中国远古时代,舞蹈一定在宗教表演中扮演了如此关键的角色,意在唤起和利用神力。⑧然而,如果我们翻阅所有关于远古时代的主要文本,包括《尧典》,我们就会注意到,对古代宗教舞蹈的叙述,无论是在纯粹数量上还是在被赋予的重要性上,都远不及对音乐的叙述。这是否表明,在上古时期,舞蹈并不像“诗言志”所说的那么重要?或者,这仅仅反映了周代晚期对音乐的重视,而大部分关于远古时代的记录都是在这时记载于各种编年史和宗教文献中的?
对许多学者来说,后一种假设更为合理。为了肯定舞蹈在古代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些学者试图重新解释古代诗歌,尤其是《诗经》中的“颂”,主要是作为宗教舞蹈的记录或剧本。王逸在《楚辞·九歌序》中写道:“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4]后来,阮元在解释《诗经》最古老的部分“颂”的含义时,写道“颂字即容字也”,又说“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作也。”[5]通过这一解释,阮氏显然意在强调诗歌完全融合于、甚至从属于那些古老的宗教圣歌中的舞蹈。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中国学者接受并进一步发展了阮元的“颂”与舞蹈的关系的观点。梁启超主张“颂是舞乐或剧本。”[6]周策纵将“颂”追溯到一种特殊的宗教性的瓮舞。[7]最近,叶舒宪大胆地(或许过于富有想象力地)将“颂”等同于各种原始舞蹈,包括与生育、埋葬甚至狩猎有关的舞蹈。[8]在讨论中国诗歌和戏剧的起源时,章炳麟、陈梦家、王国维和刘师培也强调了宗教舞蹈对这两种文学形式诞生的重要意义。⑨
总之,《尧典》中的“诗言志”表述了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学观。它的特点是诗歌从属于舞蹈,承认诗歌在唤起神灵方面的辅助作用,以及对“神人以和”的压倒性关注。虽然以舞蹈为中心的宗教表演的重要性在后来消失了,但正如朱自清所说,“诗言志”这种说法仍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山纲领”。[9]它将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它阐述了一个核心信念:文学是一个过程,它产生于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内心反应,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并反过来协调天地人之间的各种过程。⑩这一核心信念为此后千年理解文学提供了基本的观念模型。
2 《左传》和《国语》中的人文文学观
后来的批评家在将“诗言志”的论断发展为自己的文学观时,倾向于将文学重新定义为一个过程,重新确定“志”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的优先顺序,并根据文学对不同外在现象的影响来重新评价文学的功能。这一漫长的、持续不断的重新使用“诗言志”的过程,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这一说法在《左传》和《国语》中多次出现。然而,东周的编年史家们通过重复这句话,试图表达与《尧典》中的宗教文学观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学观。他们开始重新定义诗歌,把它作为宫廷仪式中以音乐为中心的表演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音乐融歌、诗于一体,已取代舞蹈成为“志”的主要表现形式。朱自清指出,此时的人们“乐以言志、歌以言志、诗以言志……以乐歌相语,该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10]考虑到音乐的这种支配地位,难怪“乐语”成为一门非常重要的教育科目。在《周礼》中提到的六类乐语(兴、道、讽、诵、言、语)中[11],朱自清解释说,第一个和第二个似乎是合奏,第三个和第四个是独奏,第五个和第六个是在日常生活中引用歌词。[12]
音乐的主导与诗歌的从属,也反映在当时的两大诗歌类型中:献诗(或采诗)和赋诗。这两种诗歌都是在宫廷场合高声和乐咏唱的。第一类诗歌起初是由平民百姓创作和演唱的,后来由乐官收集并谱曲,上呈统治者。第二类诗歌,主要是《诗经》中的诗歌,由封建领主或官员在外交场合配乐咏唱,以表达个人志向和州国宏图。
《左传》和《国语》中以音乐为中心的宫廷表演,其主要目的是协调社会政治或自然过程,而不是像《尧典》那样取悦于神灵。在这方面,这两个文本讨论了三个具体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使统治者能够判断民众的情绪和治理的状况。在《左传》中,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对《诗经》中所有主要诗群的音乐表现进行了评论,将它们的审美品质与治理状况、当地的民情以及产生的时代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郑风所表现出的乐诗过度的特点,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和社会政治的混乱。反之,中庸的品格则预示着人民的伦理美德和统治者的正确治理。它表现在各种不过分的美德上:“忧而不困”、“思而不惧”、“直而不倨”等等。季札认为周颂体现了“制中”的理想,并列举了这些颂诗中多达13种不同的保持中庸的美德。除了评论这些诗,他还观察到音乐(“五声”)和伦理社会政治现实(“八风”)之间的一般关联。
第二个功能是帮助塑造统治阶级成员的道德品质。如果说《尧典》这一段涉及到音乐和诗歌的熏陶作用,晏子则对《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音乐转变人的力量进行了解说。和季札一样,他也在进行相关的论证。他认为音乐的元素来源于无数种类的事物,自然而然地成为它们的象征关联物。他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13]他认为,音乐与事物固有的秩序是如此复杂地联系在一起,音乐可以发挥各种对立的作用,并在演奏过程中协调它们。而且,这种和谐的音乐表演能在听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心理平衡,使他成为一个品德高尚、身心和谐的人。他继续说:“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14]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春秋时期的人们来说,人类事务的协调往往只是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而这些更广泛的努力是为了实现与自然过程和力量的最重要的和谐,这些自然过程和力量对人类的生存和福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国语·周语》中,伶(乐官)州鸠在公元前522年对音乐、歌曲和诗歌如何带来这种和谐进行了精彩的阐述。为了劝说周景王不要违反乐器制作的规则,州鸠向他解释了音乐与自然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州鸠也继续探讨了一个相关的论点。他先是重申了治理与音乐的共同原则——和谐与和平:“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15]为了证明音乐与自然过程之间的关联,他率先展示了和谐的音乐是如何调节“八风”的。多亏了这样的音乐,他说,“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16]州鸠认为,通过和谐的音乐,人可以实现与自然过程和超自然神灵的和谐。他总结道:“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17]
综上所述,《左传》和《国语》中对“诗言志”的重新表述,催生了一种新的人文文学观。在提升音乐的地位和重新思考音乐和诗歌的功能时,此二文本中的说话人始终表现出对社会政治和自然过程的压倒性关注,这些过程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条件。这些人文关怀与早期对神灵的压倒性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诚然,春秋时期的人们一直在讨论神人和谐。但正如州鸠论乐时所说,这种和谐并不是通过强有力的节奏性的舞蹈、吟咏、歌唱向神灵进行巫术祈祷的直接结果。相反,它是通过仪式和音乐协调自然和社会政治过程而产生的间接后果。鉴于人文关怀高于宗教关怀,用“人文”一词来描述《左传》和《国语》所表达的新文学观似乎是恰当的。
3 《诗大序》中的教化文学观
“诗言志”的论述在汉代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改写,在《毛诗大序》中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教化文学观念。正如宇文所安所说,《诗大序》是“中国传统上关于诗的性质和功能的最权威的陈述”。[18]它与早期的诗歌讨论的区别在于它把诗歌的语言置于音乐和歌曲之上,并以纯粹的教化术语重新评估诗歌的功能。
首先,让我们看看《诗大序》中诗歌是如何在与音乐、歌曲的关系中被重新定义的。在对“诗言志”的论述中,作者不遗余力地强调了“言”,或词语的中心地位。“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他显然认为,心中的东西,无论叫“志”或“情”,主要表现在诗的言词上。为了支持他对词语的地位的提升,他简单引用了《乐记》中的一段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9]在《乐记》中,这段话出现在结尾[20],让我们觉得只是一个不重要的事后补充;但在这里,它构成了作者主张诗歌语言高于音乐和舞蹈的论点的基石。
将这一段与《尧典》和《周语》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它是如何有效地逆转诗在传统上的辅助角色的。在《尧典》一文中,诗歌被置于其他仪式活动的首位:吟咏、唱歌和跳舞。这种布局给人一种错觉,即诗歌引发了这些活动,因此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经过仔细研究,很明显,诗歌只是让读者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言语只是原材料,它将被以吟咏、歌唱、音乐演奏、舞蹈等方式依次转化。因此,这些活动的连续性表明身体运动的强化过程——从说话时的正常呼气,到吟唱中的长时间呼气,再到舞蹈中的全身运动。这个过程似乎意味着,随着生理运动的加强,其重要性也在成比例地上升。诗歌——或者说是诗歌的语言——处于这个等级的最底层,因为它需要最少的生理活动,离高潮点最远。
《周语》一文主要论述音乐,而不讨论舞蹈。然而,它采用了一种相似的价值尺度,把音乐表演置于语言之上,认为诗歌吟咏仅仅是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诗大序》中,诗也放在吟咏、唱歌和跳舞之前。然而,这一相同的顺序表明了重要性的下降。现在,这些活动的中心是在生理上最不突出的诗歌,所有其他活动都是作为诗歌语言的补充。只有当诗歌的语言不能充分表达情感时,吟咏、唱歌和跳舞才以渐进的方式变得有必要。这种音乐和舞蹈的边缘化在《诗大序》中显然贯穿始终。舞蹈只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提到过。而音乐也不会因其自身而被讨论。事实上,即使作者引用了《乐记》中关于“声”和“音”的另一段话,他似乎也只提到了诗歌语言的情感音调。“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21]在《乐记》中,这些评论后面紧接着是关于音乐与伦理—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的长篇讨论。相比之下,在这里,它们导向了对诗歌与音乐完全分离的转变力量的赞美。很明显,“声”和“音”这两个词现在被用来指代诗歌语言的音调,而不是实际的乐音和音符。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作者首次确立了诗歌的词语比舞蹈、音乐和歌曲更重要的地位。
在我看来,文学被重新定义,被视为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社会交往形式,这产生于战国和汉代发生的两次深刻变化:诗歌与音乐的逐渐分离,以及人类压倒一切的焦点逐渐从自然过程转向人际关系。到了春秋末期,这两种变化已经开始了。例如,在《论语》中孔子对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诗经》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两种变化的大量证据。在《论语》中,孔子总共19次提到了《诗经》。[22]除了两次以外,他都是把《诗经》与音乐分开讨论的。他不仅认识到诗歌相对于音乐的独立性,并对诗本身进行考察;而且还将诗与音乐放在同等的位置。他宣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3]他将压倒一切的关注转向人际关系,这也是非常突出的。在讨论《诗经》时,他完全不考虑它对自然力的影响,只关注它的伦理、社会和政治功能。例如,在他的总结性陈述中,他解释了《诗经》如何以中庸的精神帮助调节人际关系,并为平等者之间、父子之间、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人际交往提供规范。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24]
在后来的战国时期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变化的延续。以《孟子》与《战国策》为例,对《诗经》的讨论不再以《诗经》的音乐表现为直接背景来展开,也不涉及任何对音乐的认真思考。与《左传》和《周语》中对天人关系的前景化处理不同,这两种文本中最主要关注是《论语》传统中的人际关系。到公元1世纪《诗大序》问世时,诗歌已独立于音乐,儒家学说已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诗大序》的作者很自然地将诗歌重新定义为以语言为中心的社会交往形式,并强调其伦理、社会和政治功能。
《诗大序》全面考察了诗歌的四种不同的调和功能。第一种功能是协调个人的内在和外在生活。通过将情感转化为语言,作者认为一个人可以恢复内在的平衡,保持外在的道德礼仪。在这一点上,他写道,诗“发乎情,止乎礼义”。[25]
第二种功能是促进特定国家中人民之间的和谐。作者认为,一个人的情感话语与其他人的情感话语产生共鸣,因此发出了“治世之音”或“乱世之音”来表示国家治理的状况。由于这种道德共鸣,一个人的话就代表了整个国家的风气(“风”)。
第三种功能是实现臣民与统治者的和谐。在作者看来,“风”是统治者与臣民沟通交流的一种特别理想的方式,因为它们“主文而谲谏”。[26]通过高度暗示性的“风”,“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27]这种微妙的沟通方式在不损害将上层和下层分开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和谐。
诗歌的第四种功能是对大众施加道德影响。通过用“风”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统治者可以向他的人民举例说明什么是好政府和坏政府,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作者相信,通过这四种功能,诗歌不仅可以矫正伦理—社会—政治的进程,而且还可以实现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因此,他宣称:“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28]
《诗大序》的作者也谈到了诗歌的起源。他认为诗性的语言表达是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回应,体现了外在世界的秩序或混乱。基于这一信念,他将《诗经》中已知的四种体裁——风、大雅、小雅、颂与不同的伦理—社会—政治现实相对应。据他所说,“风”产生于个人对于其国家状况所作出的反应,“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29]“雅”则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30]“颂”是对统治者的伟大美德和成就的回应的产物,它的作用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31]除了这四种体裁之外,他还提到了“变风”和“变雅”是对社会政治混乱和道德沦丧时代的回应。
通过将诗歌提升到音乐之上,将其与伦理—社会—政治过程重新整合,并重新认识诗歌在这些过程中的协调功能,作者将“诗言志”的表述转化为一个完备的教化文学观。在我看来,这种教化观念的兴起,与上文提到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有多大关系,就与《诗经》研究的语境变化有多大关系。在《左传》和《周语》中,对《诗经》的谈论大多是由诸侯及其随从在评论当时的宫廷典礼仪式时发表的。在这样的语境中,说话人和受话人就在对方面前,二者都不会呈现一个独立的教化立场。因此,他们对诗歌的谈论往往让我们觉得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说话人试图通过相关推理来理解音乐和诗歌对社会政治和自然过程的影响。相比之下,《诗大序》的作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形的隐含演讲者的角色,面向从平民到君主的广大听众。作者内在的超然使他能够超越当时的宫廷仪式的限制,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对《诗经》的运用中,重新审视《诗经》并将其定义为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社会交往形式。此外,这种超脱使他能够站在儒家道德的制高点,规定统治者和臣民如何使用《诗经》。由于这种教化思想渗透并统一了他的整个论证,所以把他的文学观定性为教化式的似乎是恰当的。
4 《文心雕龙》的综合文学观
如果说《诗大序》的作者把“诗言志”的表述发展成了一个完备的教化文学观,那么刘勰就把这一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山纲领”转化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学观念。他的巨著《文心雕龙》通常不属于我们今天所知的“诗言志”传统的谱系。这可能是因为它缺乏强有力的教化观念,而“诗言志”传统在汉代之后就以其教化性而为人所知。在这里,我把《文心雕龙》与“诗言志”的传统联系起来,并不是要把它与后者的教化性联系起来,而是要说明刘勰是如何从后者那里继承了把文学理解为一个和谐过程的基本模式。正如我们现在将看到的,通过这种模式,刘勰重新认识了文学的所有主要方面:它的性质、起源、思想和语言的形成以及它的功能。
刘勰把文学重新定义为一个过程,正如《诗大序》的作者一样,刘勰以诗歌高于音乐为出发点。《诗大序》暗地里扭转了音乐对诗歌的支配地位,而刘勰则公开地把诗置于音乐之上,并明确地阐述了他提升诗歌地位的理据。“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故知季札观辞,不直听声而已。”(《文心雕龙索引》 7/99-101,107-108)在这里,刘勰以一种相当巧妙的方式将诗的重要性置于音乐之上。他接受传统的对音乐的赞美,但补充说,音乐的神奇力量来自于它的语言,而不是它的声音。这种看似无足轻重的限定条件,无异于对传统音乐观的否定。由于声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音乐的本质,他将声音比作肉体意味着音乐本身被贬为次要地位。此外,他把诗歌称为音乐之心,巧妙地将传统对音乐的赞颂转给了诗歌。为了强调诗歌高于音乐,他把有文学头脑的君子与从事乐器工作的文盲盲人音乐家进行了比较。此外,他还重新诠释了季札观周乐的故事,认为季札更关心的是词,而不是歌曲和音乐的声音。
然而,与《诗大序》的作者不同,刘勰认为诗歌优于音乐,并非因为它的语言具有矫正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关系的功效。在他看来,诗歌,或者广义地说,文学,其主要特征是书面的“文”,其次是语言化的“音”。文学之所以优于音乐,是因为它的文字具有视觉冲击力,而不是语言化的听觉效果,这种听觉效果与音乐没有什么不同。在第48章《知音》中,刘勰试图通过将书面语与音乐声音进行比较来确立文字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写道:“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索引》48/97,100-101)。对刘勰来说,文字,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口头语言或音乐的声音,使我们能够洞察古代作家的心灵。此外,写作有能力揭示隐藏在大自然中的东西。他接着说,“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文心雕龙索引》48/104-107)在写作和阅读的动态过程中,刘勰认为,一个人能够透过创造性的文字书写模式看到基本原理。
在这种将文学从根本上视为书面文字模式的观念指引下,刘勰以一种早期批评家所不知道的方法重新审视了文学的起源。早期的批评家把文学的起源追溯到“志”,或者说是心灵对特定的外在过程的回应,而刘勰则把文学的诞生归结于“道”的自然显现(终极过程),以及有意识的人类努力将一种内在的体验转化为书面文字的“模式”。刘勰在《文心雕龙》第一章《原道》的开篇就阐述了这种文学的双重起源观。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索引》1/1-21)
如果说文学的起源在早期的文本中只是略加讨论的话,刘勰则在《文心雕龙》前三篇中把这个问题作为唯一的焦点。他认为,文学与天地同源于道,是终极过程,因此是一个与天地平行的自主过程。这一论断是基于他对文学图像形式的如下确认:文学图像与天地之间的空间形象类似,都是“道”的模式(文)。他认为,天、地、人都是通过适合自己的空间形式来显现“道”的——对于天来说,是通过日、月和其他天体图像;对于地来说,是通过山、河和其他地理形状;对于人类,则是文字的图形模式。在这三种相似形式中,他认为最后一种形式比其他两种形式更有效。它提供了“道”最微妙的秘密,因为它是人类的智慧结晶,而人是五行之秀,是天地之心。
刘勰显然意识到,这些说法可能存在矛盾。如果说文学的模式与天地的模式是相同的,那就意味着它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说它是因为人类的参与而变得更加精致,这是在假设它不是无意识地形成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刘勰巧妙地运用了关于文字起源的传统神话。通过对这些神话的叙述,刘勰指出了文字的双重来源:龟龙向人类呈现的“河图”和“洛书”上的标记,以及古代先贤们发明和阐释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第一个源头是文学的终极的非人类的起源——太极。“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文心雕龙索引》1/42-43,52-57)通过声称“河图”和“洛书”产生了八卦和九畴,刘勰明确了后者是对前者的人类阐释,二者都应视为“道”的自然显现,正如天地的外部形态一样。第二种来源揭示了在古代圣人所绘制的宇宙图景中人类书写的第二个起源。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龙索引》1/44-51)
在刘勰看来,《周易》的卦像优于“河图”,因为它们所做的远不止提供宇宙力量的粗略草图。它们揭示“道”的最深处的秘密,建立宇宙的经纬,完善人类世界的法则(《文心雕龙索引》 1/96-109)。在此基础上,刘勰主张这种“人文”优于天地之文(《文心雕龙索引》 1/14-41)。
刘勰从这一角度阐释文学的终极的与次之的起源,从而避免了他认为“人文”与天地之文既相似又优越的潜在矛盾。刘勰在探索文字的起源时,力图展示道与人世、卦与后世文字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古代的圣人被赋予了丰富的智慧,所以他们能够在其著作中理解并揭示“道”的运作方式。同理,后世的著作之所以能够继续彰显“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来源于古代圣贤的光辉著作。为了阐明圣人的著作在“道”的表现和传播中的关键作用,刘勰写道: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心雕龙索引》1/110-117)
刘勰投入了第一篇《原道》和第二篇《征圣》的大部分内容,以及第三篇《宗经》的全部内容,致力于追溯“道”从《周易》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各种不同文体中的传播过程。首先,他在儒家经典中建立了一个序列,从《周易》到《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文心雕龙索引》1/74-95;3/12-25)。接着,他阐述了这五部经典作品中独特的观察和表达方式(《文心雕龙索引》2/42-59;2/64-67;3/35-74)以及由此产生的文体特征(《文心雕龙索引》3/103-110)。根据其文体特征,他将五部经典中的每一部都作为特定体裁的来源(《文心雕龙索引》3/85-102)。以这种方式,他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文学流派谱系,从五经开始,到他那个时代大量的文学和非文学文体。
刘勰的文学创作观与汉代及之前批评家的文学创作观完全不同。如果文学对之前的批评家来说是以舞蹈、音乐或口头表达为中心的公开的、富于表情的表演过程的一部分,那么对刘勰来说,文学意味着一个创作书面的文学作品的过程,这一过程基本上是私人的,沉思的和创造性的。在讨论这个表现性和表演性的过程时,早期的批评家倾向于关注这一过程与某一给定领域——神的、自然的或人类的领域的相互作用。而当刘勰在研究这个沉思性—创造性的过程时,仔细分析了在不同的创作阶段,这一过程与外在过程在多个层面的互动关系。
刘勰在第26章“神思”和第46章“物色”中专门考察了整个创作过程。第46章开篇的段落描写了文学创作之初情感的激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文心雕龙索引》46/1-4,11-12)刘勰认为,作家在一个同样简单的、心理的层面上,回应了大自然的不间断的发展变化。季节的轮回,随着许多事物形态的不断变化,在作家心中产生了喜悦、沉思、忧郁或悲伤。这些反应唤醒了作家的欲望,使他想要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刘勰写道:“是以诗人感悟,联类无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文心雕龙索引》46/29-32)
在第26章“神思”中,刘勰首先考察了这样一种“联类”如何导致诗人的精神在下一阶段的飞扬。现在,作者不再回应具体的物理的事物。相反,他静静地沉思,内心深处的灵魂游荡在外,去迎接超越时空限制的事物。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这种神游体外的状态通常被认为是“神思”的唯一含义。然而,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紧接着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它只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的最初部分。“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文心雕龙索引》26/11-15)紧接着上一段穿越万里的飞行,如果你愿意,在这里我们追踪到了远方的事物向着眼睛和耳朵的返航。这种相对运动在神思的过程中是互补的。鉴于此,我们应该走下一条线,“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索引》26/16-17),意思是一个人的精神离开自身与外在世界交融,并最终带着外在世界返回自身。刘勰指出,“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文心雕龙索引》26/18-19),即神游于外是由心理—道德过程(“志”)和生理—道德过程(“气”)所控制的,从而再次确定了神思是一种往返旅行。然后他指出,感知过程(听觉的和视觉的)和智力过程(语言的有意识使用)对于调解远处事物的涌入至关重要。“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文心雕龙索引》26/20-21)对刘勰来说,神思的成功取决于影响这一往返旅行的所有这些过程的协调运作。“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文心雕龙索引》26/22-25)刘勰认为,神思的最终结果是内在(神,情)与外在(物,象)共同转化为“意象”,并将这种“意象”完美地体现在“言”这种媒介中。
刘勰认为,要想达到神思的理想效果,一个作家必须培养自己具备一些重要的品质,以便顺利地运作这些过程。作家必须学会获得“虚静”的状态,这是神游于外的必备条件。刘勰写道:“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文心雕龙索引》26/26-27)为了确保他的精神顺畅 的通道,作家必须“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文心雕龙索引》26/28-29)。换言之,他必须建立自己的生命能量和道德品质。为了提高他的智力,他必须“积学以储宝”(《文心雕龙索引》26/30)和“酌理以富才”(《文心雕龙索引》26/31)为了加强他的感知能力,他必须“研阅以穷照”(《文心雕龙索引》26/32)。最后,为了能够用语言表达他的意象,他必须“驯致以怿词”(《文心雕龙索引》26/33)刘勰相信,当一个作家培养了所有这些品质之后,他就能够有效地在直觉、生理、道德、心理和智力层面参与外部过程。从神思的这种协调得很好的运作中将会产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刘勰的文学功能观也与早期批评家的文学功能观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对文学功能的探讨是汉代及以前的批评文本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它恰恰是刘勰文学观中最不重要的部分。《文心雕龙》的五十章中没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而有很多章节都仅仅是为了探讨文学的起源和创作。与《诗大序》的作者不同的是,刘勰没有阐述文学如何能够而且应该用来矫正人际关系,协调自然的力量和过程,使人神相谐。相反,他仅仅承认“顺美匡恶,其来久矣”(《文心雕龙索引》6/32-33),并且在许多章节中敷衍地提到了这两种教化功能。在理论层面上,刘勰认为文学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价值的判断不是看它如何协调某些社会政治过程,而是看它如何在“文”或“美的形态”中体现“道”,从而“经纬区宇,弥纶彝宪”(《文心雕龙索引》1/106-107)。
不论以哪种标准来看,刘勰的文学观都是非常全面的。在构想它的过程中,刘勰巧妙地吸收和改造了早期文学批评中对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过程的关切。我们先来看看他对于外部过程的处理。在终极宇宙过程的层面上,我们观察到他将早期宗教对超自然的神灵的痴迷,转变为既在心灵内部、也在外部世界与神的艺术约会和对“道”的神秘运作。在自然过程的层面上,我们发现他对文学与阴阳、五行、具体自然过程的关系有着敏锐的观察,就像《左传》和《国语》中不同的说话人一样。然而,他希望探索这些自然过程对艺术创作的关联性,而不是文学在调节这些自然过程以求发展和繁荣方面的有用性。在伦理—社会—政治过程的层面上,我们注意到他的注意力从“诗大序”对实际的教化作用的关注转移到一个“形而上学”的任务: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体现理想的道德和社会秩序。
再来看内在过程。我们会注意到,在超感官经验的层面上,刘勰用沉思的直觉代替了宗教的召唤,作为与终极实在接触的手段。在生理经验层面,我们观察到他将仪式化的身体动作升华成一种为了文学创作而培养和锻炼“气”的努力。在心理体验层面,我们看到他把兴趣从《诗大序》的中心关注点“志”的表达上转移到了“情文”。在道德经验层面,刘勰将道德劝诫和道德教化降至次要位置,但他继续强调作家道德品质与文学创作的关联性。
刘勰使读者能够从一个复杂的内部和外部过程的多层次互动中感知文学的不同方面。大多数现代批评家都认为刘勰的宏伟计划是以“道”为中心的,但他们对“道”的本质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现代批评家们以各种方式识别刘勰的“道”,把它视为《论语》中的人之道、老庄的自然之道、佛教之道,以及《易传》中儒家与道家之道的综合。根据这些观点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盛行的观点,我认为,《文心雕龙》的核心之道,与《易传》中的“道”,尤其是《系辞传》中的“道”是相同的。在《系辞传》中,我们被告知“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32]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以这一包罗万象的“道”为参照中心,在生理、心理、道德、直觉和智力五个层面上,建立了一个人类与各种各样的外部过程互动的有机体系。
通过将文学观置于这样一个有机体系,刘勰真诚地努力仿效孔子及更早的先贤建立的非文学之文,旨在确立文学之文的规范原则。在整本书的结语《序志》(第50章)中,刘勰写道,成为这样一个文学的“系统化者”,是他实现童年“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梦想的必由之路(《文心雕龙索引》 50/34-35)。他感到遗憾的是,自从马融、郑玄等儒家学者已经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透彻的阐释之后(“马郑诸儒,宏之已精”,《文心雕龙索引》 50/44-45),他再也无法成为一个伟大的儒家训诂学家了。但由于早期文学批评家的不足,他看到了通过编纂文学原则实现不朽的机会。对他来说,没有严格的系统性是他前人最大的不足。他发现他们的作品“不周”、“疏略”、“碎乱”或“寡要”。因此,刘勰要超越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最系统的方式确立文学原则。为此,他以《周易》中关于“大衍之数”五十的符号命理学,作为模型来“位理定名”(《文心雕龙索引》 50/129-132)。在《周易》中,这种符号命理学服务于意指宇宙的有机整体性:太极,天地、日月、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或以太。[33]刘勰采用这一命理学,无疑希望构建一个包含所有文学经验的系统:从其终极宇宙起源到最细致入微的修辞细节,从整个文学传统到个人才能,从非文学到文学文类和亚文类,从创作到接受过程,从作者性格到读者素质,等等。我们可以认为,刘勰的综合文学观及其批评体系,总的来说,是从他一贯的、自觉的文学思想中,通过《易经》的范式而产生的。
5 四种文学观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体系
刘勰对早期关键问题的综合,证明了其文学批评的敏锐性,以及四种文学观之间的内在的亲和力。最后,让我考察这些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
如果说这四种文学观有一个公分母,我想应该是它们有一个核心信念:文学是一个过程,它协调了在天、地、人的领域中正在进行的各种过程。根据中国早期批评家的说法,当一个作曲家或作家在生理、心理、道德、直觉或智力水平上对各种外部过程作出反应时,这个过程就产生于他的内心。当他通过跳舞、演奏音乐、唱歌、说话或写作来表达自己的反应时,这一过程从内心走向外部,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简单地说,文学由三个主要阶段组成:它对世界的回应,它在人的心灵和语言中的形成,以及它协调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功能。
比较这四种文学观,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的区别。首先,文学作为一个过程的定义是非常不同的。在《尧典》中,它是以舞蹈为中心的宗教表演的一个辅助部分。在《左传》和《周易》中,文学是一个相对重要的、但却是以音乐为中心的宫廷仪式的辅助部分。在《诗大序》中,它是言语化的社会交际的核心部分。最后,在《文心雕龙》中,这是一种很大程度上自主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美学追求。
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文学的起源、形成和功能是从与不同过程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的。在阐释文学起源时,早期批评家将其追溯到作家对外部过程的内在反应,这一外部过程在《尧典》中是超自然的“神”,在《左传》和《周易》中是自然力,在《诗大序》中是伦理—社会—政治过程,而在《文心雕龙》中是“道”的多重过程。在考察文学形成的过程中,这些批评家在人类经验的不同层面强调了这些互动:在《尧典》、《左传》和《周语》中是生理和心理层面,在《诗大序》中是心理和道德层面,而在《文心雕龙》中则涉及各个层面。在文学功能的描述上,他们强调与超自然神灵的和谐、与自然力的调和、对人际关系的矫正,以及“道”在各个领域的神秘启示。
这四种文学观之间的联系揭示了一个复杂的批评体系。当然,这样一个体系,驳斥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中国传统批评没有一个连贯的体系的错误观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因其印象式、随意性和无序性令人震惊,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试图在基于西方批判思维的“以真理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范式的分析框架内理解它。然而,当我们在“基于过程”的范式中重新审视它时,我们可以看到压倒性的证据,证明了前面讨论中所勾勒的系统一致性。
这样的批评体系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后期批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连贯性。显然,刘勰之后中国批评的发展表现出与早期中国批评核心相同的基本原则。后来的中国批评家同样珍藏这样的信念:文学是一个和谐化的过程。他们倾向于通过以“道”为核心的一些信条来表达这一信念,例如“诗以明道”、“诗以载道”、“诗以贯道”,以及更古老的信条,如“诗言志”、“诗缘情”、“原道”等。他们还试图重新定义文学作为一个过程的本质,经常颠倒音乐和口头语言、或音乐与书面写作的相对重要性。第三,他们还交替地把文化或自然作为讨论文学起源、形成和功能的终极参照。
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创作、文体分类、文学流派谱系等特定批评主题讨论的内在一致性。例如,我们可以根据文学创作和欣赏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的外部过程在生理、心理、直觉、道德或智力等水平上的复杂互动模式来探讨传统上被认为是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在一个基于过程的范式中,我们甚至可以尝试重建许多因难以捉摸、逻辑上没有联系而饱受诟病的中国文学批评术语的命名法。例如,我们可以在内部和外部过程的交互方案中重建与“气”相关的术语的命名法。
几十年来,在中国传统批评中识别出一个批评体系,这一目标一直让我们感到兴奋和困惑。在考察这四种文学观时,我发现了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而揭示了中国早期批评的系统连贯性。由于可清楚地看到其他时期的批评写作具有相似的系统连贯性,我们可以从整体上设想中国传统批评的以过程为基础的系统性。进一步发展这一系统论的思想及其对理解中国传统批评的实用性,将是一项令人兴奋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 本文引用的《文心雕龙》原文,均出自朱迎平.文心雕龙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为避免重复标注,此类引文一律在原文后直接注明索引条目。
② 对这一领域广泛学术成果的总结,请参阅《文心雕龙学综览》。
③ 刘勰也将其他的文学观念吸收进他的有机结构中。
④ 《尧典》分为两章——《尧典》和《舜典》,“诗言志”这一命题出自其中的《舜典》。《舜典》以及其他章节的年代,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顾颉刚在《古史辨》的《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中,将其追溯到由西周到东周的过渡时期。顾颉刚所确定的年代被朱自清的《诗言志辨》,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卷一所接受。然而,屈万里在《尚书不可尽信的材料》中,将《舜典》的年代定于战国时期。
⑤ “志”一词被理雅各在《书经:历史文献汇编》中译为“earnest thought”,而被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译为“the heart’s intent”。
⑥ 这一系列的活动似乎与米哈伊尔·斯巴洛苏(Mihail Spariosu)所说的古希腊“诗歌朗诵、音乐制作、舞蹈以及仪式和戏剧表演的古代神话统一体”相吻合。
⑦ 参见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卷)[C]。
⑧ 关于中国古代舞蹈的宗教功能,见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⑨ 参见章炳麟《文始》,陈梦家《商代神话与巫术》,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等论著。
⑩ 文学是一个过程的观点,一直被中国诗学界的许多学者所注意到。例如,宇文所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预兆》认为,在中国传统诗学中,“从世界或时代的条件,通过诗人,进入诗歌,最后到达读者,这一运动不被看作一系列的因果关系,而被设想为一个有机的表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