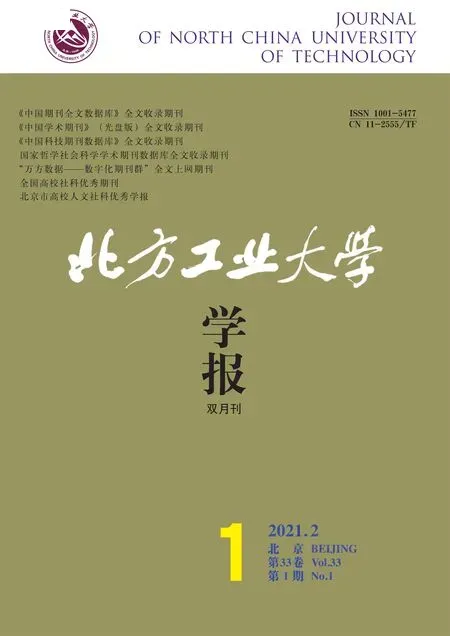罗赞诺夫的赫尔岑观探析*
2021-11-23纪薇
纪 薇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300387,天津)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赞诺夫①(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иевич Розанов,1856—1919)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家、宗教哲学家、批评家、作家。在赫尔岑100周年诞辰之际,列宁写了《纪念赫尔岑》(1912)一文。此后,但凡涉及赫尔岑人们就必从中引用高度肯定的赞誉。其实,1912年3月赫尔岑100周年诞辰之际,罗赞诺夫也写了回忆录《赫尔岑与六十年代》,但《新时代》报没有发表,当时苏沃林认为它不符合“主导思想”,时至今日也无法找到这篇文章。罗赞诺夫的《赫尔岑》一文写于1911年,罗赞诺夫因科特良列夫斯基教授所写关于赫尔岑的精彩随笔《六十年代的舆论倾向》引发对赫尔岑的评论。1911年的《赫尔岑》与1912年的《赫尔岑与六十年代》这两篇时隔不久的文章中包含的主要观点想必应该出入不大。现在我们能够解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被封杀的文章,可见当代文坛更加开放、民主、公平,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
罗赞诺夫首先肯定科特良列夫斯基教授的这篇随笔,指出这篇随笔对确定赫尔岑在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政治运动中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他赞同科特良列夫斯基教授对赫尔岑的主要观点:赫尔岑活跃于1840年代,在1850—1860年代他已经过时了。并且罗赞诺夫在这篇文章中深入论述了这一结论的两个原因。一方面,赫尔岑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有待开掘的庞然大物”——极端保守分子。他远离祖国,脱离人民,不是生活中的人,不具有从事政治宣传的能力;另一方面赫尔岑被罗赞诺夫称为“肤浅之人”。在1960年代赫尔岑的创作是没有内涵的纯粹文学,没有核心,令人生厌,他的《警钟》犹如毁弃的黄钟,发出瓦釜雷鸣般生锈的腔调。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单一思维看待赫尔岑的生平与创作、文学观、哲学观、政治观、社会历史观,而经典的意义正在于常读常新,在俄国思想史上赫尔岑并不是一位能被简单界说的人物,其人其文其思有无数的宝藏可供挖掘。由罗赞诺夫的《赫尔岑》以及其他相关文章,笔者归纳出罗赞诺夫对赫尔岑赞成与反对的悖论变奏评价,并分析了罗赞诺夫对赫尔岑双重评价的原因,最后对罗赞诺夫关于赫尔岑的评论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罗赞诺夫对赫尔岑离经叛道的评论观点为我们重新全方位审视赫尔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展现了一个非单质的、丰满的赫尔岑形象,对赫尔岑研究起到有益的启发、批判和丰富作用。
1 罗赞诺夫的赫尔岑观
1.1 创作评价:赫尔岑既是非凡的文学家,同时也是脱离生活的老爷
一方面,罗赞诺夫将赫尔岑列为仅次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二流文学大师,与其并肩的还有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冯维辛、格里鲍耶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斯科夫、别林斯基,高于康杰米尔、杰尔查文、巴丘什科夫、杜勃罗留波夫这些罗赞诺夫所认为的三流作家。罗赞诺夫认为,赫尔岑在出国前和出国后的最初时期还能创作美好的文学,写出了《一个青年人的札记》(1840—1841)、《谁之罪》(1841—1846)、《克鲁波夫医生》(1847)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等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优秀作品,在群星闪耀的19世纪俄国文坛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833年,赫尔岑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以莫须有的种种罪名屡遭迫害,先后在彼尔姆、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等地被流放近十年。1842年重返莫斯科,基于流放期间的丰富生活积累,赫尔岑创作出大量哲学、政治、文学作品,尤其在文学讲坛上发出自己心灵的呼唤。但另一方面,罗赞诺夫指出,在各种运动蓬勃发展的1960年代,赫尔岑并不善于文学创作。“赫尔岑却不善于从事任何一种活动,甚至不善于从事文学方面的活动。手握笔杆的赫尔岑无法使自己适合其中任何一种活动。”[1]在罗赞诺夫看来,这是因为作家不能离开故土,这样的创作方式对赫尔岑的命运产生了悲剧性影响。从1947年赫尔岑开始长达二十余年的侨民生涯,先后游历法国巴黎和尼斯、英国伦敦、瑞士日内瓦。赫尔岑长时间侨居国外与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远离祖国、脱离人民,使他并不能亲身感受到俄国人民的疾苦,无法创作出时代所需的先进作品。在《赫尔岑》一文中,罗赞诺夫指出:“他是一位令人惊叹不已的、了不起的文学家,无人能与之媲美。但他却不是一个生活中的人。”[2]“他甚至使自己摆脱了在苦涩真理中的‘人’的概念,没有亲自用自己的双手耕过一垄地。”[3]赫尔岑从未在土地上辛勤地劳作,没有考察过伦敦的监狱,没有深入民巷,自始自终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老爷。“令人厌恶的老爷这一语词毕竟还是可以应用到他身上的。即使他曾经呼唤人们拿起斧头,他也依然是和音乐在一起的小少爷。他的音乐非常迷人:但音乐仍然受这样一种意识折磨,是小少爷的音乐,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者的音乐。”[4]而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做得比赫尔岑好得多。托尔斯泰贵为公爵,身为庄园主,却经常亲自下田耕种务农。罗赞诺夫认为自己也是劳动者,而赫尔岑却是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我家的餐桌旁坐着十个人,还要加仆人。人人都靠我的劳动吃饭,人人都在我的辛苦边找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赫尔岑可是‘悠哉游哉’……”[5]
1.2 思想评价:赫尔岑既是尼古拉时代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亚历山大时代的空谈家
一方面,罗赞诺夫认为,赫尔岑为1960年代社会思潮的高涨做了准备。赫尔岑是19世纪前半叶后期最大的革命家,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创作于1940年代的美好文学向落后的农奴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在流亡期间,赫尔岑于伦敦创建“自由俄国印刷所”,创办辑刊《北极星》,又与挚友奥加辽夫发行周报《警钟》(1857—1867),这一切都对俄国革命运动发挥了一定的催生作用。因此,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称赞道:“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6]而另一方面,罗赞诺夫强调,“在赫尔岑身上,俄国革命产生了也死掉了。”[7]因为赫尔岑是1940年代的人,在尼古拉统治时期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但他仍不失为尼古拉统治时期的人,但到了1950—1960年代,他已明显过时、老朽了,落后于1960年代的新人。按罗赞诺夫的定义,赫尔岑是语言领域里语言自足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赫尔岑对自己的政论十分满意,然而在解放农奴、地方自治和实行新的法庭制度的时代,他已然是个极端保守分子,“所有这些是已经老朽不堪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胡说八道。让这些都见鬼去吧!……太枯燥乏味了这些言论……没有一点水分、也没有一点湿气、没有沼泽、没有草墩”。[8]简直是思想荒芜的惊世喟叹。罗赞诺夫主要指责的是,赫尔岑滔滔不绝地说漂亮话却不干实事。在1860年代,俄国各种活动蓬勃发展起来,赫尔岑却把整整一条空话组成的河流引入俄国,空话如银河般向俄国倾泻,他以为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历史。“赫尔岑是政治空话连篇的奠基人,开政治空话的先河者。”[9]罗赞诺夫还写道:“只是在尼古拉时代荒芜的苍穹上赫尔岑才能那样辉煌壮丽。在这个时代人们写过许多诗,但是也有过很多宪兵,没有任何散文,没有任何思想。就在这个时候,伴随着他那些好像泉水般喷出的理念和非常睿智的散文赫尔岑翱翔在天空中。”[10]但这只是思想的市场,却没有一个刻骨铭心、抓得住人的深刻思想。“他绝对没有‘亲手触摸’任何东西,而一切都出于他的杜撰!!”[11]“在这些话里没有具体的内容、没有明显的物质上可以触摸的东西……是没有内容的纯粹文学,没有任何内涵 ……这是夜莺在闭着眼睛歌唱,勉强以‘轻盈的手指’触碰主题。”[12]罗赞诺夫还指出,在赫尔岑的文章中没有一个实例,“一切都是图解,一切都是思想,到处都是激情,到处都是钟声。这样一种音乐归根结底使人厌恶。赫尔岑令人叹服赞美,但是这种赞美的特质只有一个星期。一年之后他变得令人无法忍受”。[13]同时,罗赞诺夫把赫尔岑比作是一把向木桩射击的手枪,他到处开枪,对什么都不欣赏,并不具有从事政治宣传的能力,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斗士,也不是一位政治人物,而是没有核心支点的,大杂烩式的肤浅之人,基于此,在1940年代获得短暂成功之后,他便从最初的成功者沦落为最终的多余人。罗赞诺夫就赫尔岑写了几行文字,后来收入《落叶》中。“一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市场,这就是赫然岑。由此写了好多东西,但是没有读者对赫尔岑任何一页深思冥想(他写得肤浅),姑娘不会哭。不会哭、不会留下深刻印象、不会叹息,很贫乏,赫尔岑既是富人也是穷人,没有丰富广阔的思想。”[14]
1.3 个人评价:赫尔岑既是物质上的富翁,同时也是精神上的穷人
一方面,罗赞诺夫认同赫尔岑很有教养、有才华、有天赋、活跃、机敏、天资秀出。赫尔岑出身于莫斯科的豪门望族,虽然是私生子,却并为此而遭受冷落。他接受了正规的贵族教育,受过系统的欧式教育,深入研究过黑格尔哲学,具有欧洲头脑,父亲死后又为其留下了一份可观的遗产,也就从来没有挨过饿。“赫尔岑没有工作过,只是个富有的、有才华的人。”[15]罗赞诺夫如是说。另一方面,罗赞诺夫认为,赫尔岑虽然物质上富有,有极大的天赋,但因缺乏爱心、恻隐之心,实际上赫尔岑又是一个精神上的穷人,缺乏真正的、永恒的才华。罗赞诺夫说道:“在你(赫尔岑)身上没有永恒之物。爱是永恒的,但你没有。”[16]在法国尼斯期间,赫尔岑家庭出现了第三者,赫尔岑的妻子娜塔丽雅·亚历山大罗夫娜与德国流亡革命家海尔维格有染,关系十分暧昧,以致引发了极大的家庭情感危机。与此同时,赫尔岑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赫尔岑的母亲带着他的儿子从巴黎走海路去尼斯途中,轮船与另一艘客轮相撞,祖孙俩落海遇难。罗赞诺夫因为崇拜家庭,所以不可能接受赫尔岑这个人,他痛骂赫尔岑道:“母亲和儿子淹死了,心里一点也不悲伤。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是会发疯的,心情简直糟糕透顶。赫尔岑只不过是给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浦鲁东写了一封‘悲惨的信’。”[17]此外,在《隐居》一书中,赫尔岑不帮助经济上拮据的朋友也使罗赞诺夫颇有微词。罗赞诺夫写道:“我读了格·乌斯宾斯基痛苦的、恐怖的生活,1 700卢布的债务让他喘不过气来。放高利贷的女人紧随其后,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彼得堡都不让他安宁。格·乌斯宾斯基曾是涅克拉索夫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朋友。他们显然不只是尊重,而且喜欢他(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信中说过)。但是当时为什么他们不帮助乌斯宾斯基呢?有一个很难猜的原因吗?就像百万富翁赫尔岑不帮助别林斯基一样。”[18]相较于杜勃罗留波夫而言,赫尔岑也是略逊一筹的,因为他没有对于亲爱的一切,按照亲人的方式做出反应。虽然作为评论家的杜勃罗留波夫只写过一首诗,但这首诗表达了对祖国的忠贞与敬爱,整个俄罗斯都出现在这首诗中,整个俄罗斯都在杜勃罗留波夫的面前,而在赫尔岑全集中,就连那样的八行诗都没有。杜勃罗留波夫和基列耶夫斯基比赫尔岑贫乏,但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对祖国土地的爱,对乡村歌曲、乡村大门的爱,他们又无可比拟地比赫尔岑更有才华,他们都是与人民血脉相通的。同时,罗赞诺夫强烈谴责赫尔岑的不谦虚。对罗赞诺夫而言,判断作家的个性特点永远具有决定意义。“说实话,在文学中我最敌视的正是在人身上我最反感的自满自足。我就像上校斯卡罗祖勃一样,在同等程度上反对自满自大的赫尔岑。”[19]正因如此,罗赞诺夫推崇基列耶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他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给整个俄罗斯社会输入了钢铁般的硬度,而赫尔岑只是软铁。在罗赞诺夫心里,“沉默使太阳发光,沉默孕育果实,沉默供养根基……越沉默成绩就会越多”。[20]所以,他欣赏的是像基列耶夫斯基这样的俄罗斯孤独的思想家,而不是像赫尔岑那样极尽释放自己,如暴风雨般夸夸其谈,吹吹嘘嘘,他甚至主张把赫尔岑从文学中驱逐出去。“把赫尔岑从文学中驱赶出去,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吹牛、自恋、罪孽。”[21]“你就在日内瓦过你的好日子吧,俄罗斯没你的位置,俄罗斯根本不需要你。”[22]
2 罗赞诺夫对赫尔岑的双重评价探因
钱中文先生指出,罗赞诺夫“自青年时代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取向:追求内在的自由,反对公认的权威和行政当局,不问外界事变而专注自己的内心。在研究写作中,他善于接受不同的传统和影响,把矛盾对立的东西融合一起,避免极端而求兼收中和。因此,在当时常难为人理解,被斥为缺乏原则。”[23]对罗赞诺夫研究颇深的西尼亚夫斯基也指出:“罗赞诺夫的个性和思想极为宽广和多样,他的言论互相排斥和稀奇古怪,不能把他看作哲学体系的创建者。”[24]正如上述两位中俄学者所说,这种矛盾的特质一直伴随着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罗赞诺夫一生的崇拜对象,这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亦此亦彼的非体系性与悖谬性恰恰师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此同时,他却在《落叶》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作是“醉醺醺的神经质的村妇”。一方面,罗赞诺夫盛赞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心理分析和艺术描写非同一般;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让安娜卧轨自杀是托尔斯泰的错误构思。罗赞诺夫一直宣扬自己对上帝的爱与崇敬,但对《马太福音》中上帝“爱仇敌、祝福憎恨之人”的教导,却因为自己牙龈化脓而办不到。在《隐居》中,罗赞诺夫对自己的理解也是摇摆不定的。他先说自己是“傻瓜”“骗子”,然后又说自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奇的人”,最后又把自己简直是“一个神奇的人”这一评价,写在无人能看得到的鞋底上。罗赞诺夫在心理上是亲犹者,而在政治上却是反犹者,所以他不是“耍两面手腕的人”,而是“两种个性的人”。罗赞诺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苏沃林担任主编的《新时代》报供职,却在彼得堡保守的《新时代》报和莫斯科自由主义的《俄罗斯言论》报上以瓦尔瓦林为笔名(1906—1911)同时发表言论相反的文章,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尝试用所有倾向写作。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对罗赞诺夫深有了解,她说过,罗赞诺夫善于“用两只手写作”,他的两只手永远都在真诚地写作,这是因为他的整个心灵是双料的、极端的。
如上所述,罗赞诺夫没有坚定不移的“是”和完全确定的“非” 这种体系作为纲领。他有自己的罗赞诺夫式的对观念的理解,在这种观念中,“是”与“非”,“右”与“左”同存,更准确地说,“是”不永远是“是”,而“非”未必一定是“非”。[25]稍有一点重大意义的批评家都有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纲领,也都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但罗赞诺夫却是一个特例,因为罗赞诺夫的世界观是多质的。罗赞诺夫非常与众不同,喜欢和别人唱反调,同时又极其嬗变,他一分钟前所说的话与一分钟后所说的话可以完全矛盾,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罗赞诺夫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以探索式的、多元的态度对待俄罗斯文学的过去,以非传统的观点看待文化现象。“尝试从相反的方面看待任何现象与事件,这是颇有名气的‘罗赞诺夫式的二律背反’”。[26]他的这种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使思想处于动态,拒绝思想的平庸,在悖谬的思想交锋中体现思想张力,值得后人传承,对当今仍有启示意义。罗赞诺夫“留给后人的主要是他的思维过程本身——不平静、松散、曲折、跳跃,其外部图景充满矛盾,但其内心专注完整。”[27]摇摆不定是罗赞诺夫生活中首要的唯一坚定不移的原则,他认为“因摇摆不定一切才会繁盛,一切才会生机勃勃。假如一旦稳定性来了,整个世界就会被石化、被冻结、变得僵硬了。”[28]“只有通过二律背反,通过发狂的不正常思想以及非传统的视角才能够走近真理,走近在实证主义对问题平淡无味的解决过程中你不能看到和无法明白的,理解与意识的辩证法就在于此。”[29]罗赞诺夫想用矛盾的话语共存来表现观点的两极性,但这未必意味着立场的“再定位”,只是又一种视角,又一种思想而已。类似的这种“多面性”是罗赞诺夫永远的特征,他的世界观永远不是“单质的”,因而他独有的批评观也是多质的。正如我国学者张冰在评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主观批评时所说:“你可以否认某一评价的正确性,但你却无法否认这样一种批评方法的艺术性。”[30]著名的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论罗赞诺夫》一文中对作家言语的矛盾性困惑不解。他认为罗赞诺夫不可能引导任何人,因为一个人的身体不可能同时既向左又向右。但是,罗赞诺夫一生恰恰专注于学习“同时既向左又向右”。这是罗赞诺夫式的作为哲学的语言魅力,罗赞诺夫多元复杂的思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他就像两面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既是先知分子,也是保守分子,既有先锋性,也有滞后性。这也正是爱他的人与恨他的人都会对他有同样挚烈情感的原因。
3 结语
罗赞诺夫“是”与“非”的二律背反式评价,激发了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文学中的许多亮点,他对赫尔岑的矛盾态度,对赫尔岑进行多维度的思考,为我们重新全方位审视赫尔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罗赞诺夫为我们呈现出“两幅面孔”的赫尔岑:在创作评价方面,赫尔岑既是非凡的文学家,同时也是脱离生活的老爷;在思想评价方面,赫尔岑既是尼古拉时代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亚历山大时代的空谈家;在个人评价方面,赫尔岑既是物质上的富翁,同时也是精神上的穷人。这种悖论评价揭示了人们长期忽视的一面,揭去枯燥的概念化的标签,也前所未有地完成了对赫尔岑的去神圣化、脱冕、降格、揶揄以及重估,凸显了赫尔岑形象的复杂性,对赫尔岑研究起到十分有益的启示作用。罗赞诺夫在认同赫尔岑的同时,也表现了大胆的平视态度,不顾禁忌地道出自己想说的任何观点,敢于批判这位神圣化、理想化之人的精神可贵、可敬,可以说是一种狂欢化的批评态度。与此同时,还应认识到,在评论赫尔岑时,罗赞诺夫也存在着一定的主观倾向以及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误区,例如,因受同时代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主观批评以及现代派批评的颠覆与反拨总体倾向的影响,罗赞诺夫对赫尔岑的评论过于严厉,有些揶揄评论也是不完全公平的、不十分客观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地吸纳其中的合理性成分,立足当下,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注释:
① 在中国В.В.Розанов的名字有多种翻译形式:洛扎诺夫、罗赞诺夫、罗萨诺夫、罗札诺夫、罗森诺夫、梁赞诺夫等,在引用时保留上述译名,本论文通篇采用罗赞诺夫这一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