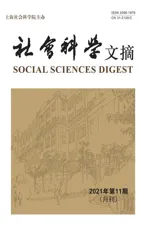卢曼系统论视角下大众传播媒体如何影响社会?
2021-11-15秦明瑞
文/秦明瑞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5期;原题为《大众传播媒体是如何影响社会的?——卢曼系统论视角下的分析》)
问题的提出
如果将大众传播媒体简单地定义为原则上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信息传播场域,那么自从有了这种场域——早期为印刷品,后来增加了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今天则有了如电脑、手机等为载体的互联网新媒体——人们关于社会、历史和自然世界的信息和知识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这种媒体。一方面,人们依赖大众媒体传播各种信息和知识,以便了解社会和世界;另一方面,人们持续怀疑大众媒体传播的态度及其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很多人来说,大众媒体背后似乎有一些隐蔽的幕后操纵者在控制和利用它们以实现某种目的。
卢曼创建的社会系统理论旨在启蒙社会。运用这一理论,他分析过大众媒体这一特别庞大和复杂、表面上看并不那么“系统”的系统。他试图回答的根本问题是:大众媒体是如何影响社会的?而这个问题又被分解为以下问题:大众媒体的“本值”或“自身行为”是什么?在认识了这种“本值”以后,使媒体显得神秘的某种“秘密”是否还存在?他的基本论点是:媒体是现代社会功能分化产生的一种效果或后果,其既可以被认识又可以在理论层面被反思;其背后并无操纵者或者秘密。像所有其他系统一样,媒体按照自身逻辑运行,即在自身密码“信息/非信息”和纲领(节目、栏目)的基础上生产和传播信息。
大众媒体的定义及其建构的世界真实
卢曼认为,大众媒体应被理解为“社会中利用复制技术手段传播沟通的所有机构”。在此,卢曼的理解显然与一般大众媒体理论有别:他不是将大众媒体理解为信息传播的机构,而是将其理解为传播“沟通”的机构。正如下文将介绍和分析的那样,卢曼认为,大众媒体在以独特的方式生产出信息后将其传播给大众,旨在引起受众在日常世界中的沟通以及与媒体的沟通,从而影响社会。
卢曼区分了三种大众媒体。第一种是印刷品,包括图书、杂志、报纸等;第二种是运用照相和电子复制技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这类产品的受众是不确定的;第三种是基于无线电的沟通传播,但这种沟通指的不是单个参与者之间的电话通话,而是面向大众的沟通,如广播、电视等。在此,卢曼提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只有在作为沟通载体的某种产品(如电视剧)被机器生产时,大众媒体这一特殊系统才得以分化出来。
卢曼提出这一观点,进而将大众媒体当作一个类似于经济、法律、政治等系统的功能系统来分析。他认为,对大众媒体这一系统来说,传播技术是一种媒介,它使大众媒体系统得以分化出来,就像货币这一媒介引发了经济系统的分化一样。在卢曼的理论中,媒介是构成形式的底物,而系统中形式的生产是由沟通的操作来完成的。通过这些沟通,系统的分化和闭合成为可能。
每一个系统的操作方式都受一些结构性框架条件的限制。首先,在大众媒体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不发生在场者之间的互动。他们之间的沟通凭借媒体的传播技术得以进行。传播者可以与单个受众互动,但他不可能与所有受众互动。媒体沟通中这种直接接触的中断有两种作用:一是沟通的自由度得以保持在较高水平,沟通的可能性得以大幅度增加或出现剩余。这种剩余只能在系统内部通过自组织和自身的真实建构得以控制和加工。二是沟通的可能性又受两种选择机制的限制,即媒体的传播意愿和受众的接受兴趣。两种机制都无法由某个机构集中调控。大众媒体中用于生产沟通的组织机构能够对受众认可和接受的内容做出评估。在此基础上,它们将自己的节目标准化和区别化,即发展出一些针对不同群体的节目(如电视台下午四点播放家庭主妇喜爱的烹饪节目)。当然,这些节目不可能满足所有个体的喜好,但节目的多样性可以使每个个体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或对自己重要的内容来接收。
传播技术虽然是大众媒体的基础,其工作方式使大众沟通得以结构化,但在卢曼看来,这种沟通属于传播技术领域的工作——印刷过程、电子设备的操作等,并不属于大众媒体系统的操作。大众媒体系统的构成性要素主要是作用于这些机器设备工作的沟通过程并贯穿其中。卢曼称技术性的机器设备为“沟通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这些设备传播的信息所引起的沟通,也就是这些信息被接收,才属于大众媒体系统的沟通。
要理解卢曼的这种区分,就需要简单认识一下他对沟通概念的定义。他认为,沟通是由三种要素构成的完整过程,即信息、传递和理解(或误解)。信息是区分的操作结果;传递行动是将这一信息告知他者的行动;理解或误解是接受者对这一信息的接受过程,它可以是理解也可以是误解。当这三种要素都出现时,就形成了沟通。
从这一定义出发,卢曼进一步揭示了大众媒体的特征。在传递环节,大众媒体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难以确定正在参与沟通的人群即受众圈,而只能假定这一人群。在一次沟通完成之后,在大众媒体系统内部和外部参与相关沟通的圈子就更难确定了。这种能力限制对大众媒体来说反而是一种优势。正是基于这种不确定性,大众媒体往往将其援引性的沟通范围设计得很宽泛,并且在沟通失败或遇到反对时不放弃沟通,而是尝试寻找潜在的受众,挖掘更多的沟通可能性。
如前文所述,人们今天对世界的了解基本上来自大众媒体。但是大众媒体所呈现的真实并非现实的真实,而是康德所说的“先验的幻想”。卢曼引入观察概念解释了这一现象。观察指的是做出区分后,再标示出这一区分的行动。要理解大众媒体的操作,我们则必须以观察者的视角,即二阶观察的视角来观察大众媒体。
对其观察的结果是:在这一系统中出现的是“对真实的二重化”,其所呈现给受众的真实不是原本的世界真实,而是其观察的结果;如果说世界真实是由一阶观察的活动或演化构成的,那么,大众媒体所反映的真实则是二阶观察的结果,是其建构出的真实或关于真实的沟通结果。这种真实既可以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也可以是关于大众媒体系统自身的真实(如大众媒体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无论是在古典真理问题的讨论中,还是在人们对真理或真实的日常理解中,人们都会问媒体报道的内容真实吗?卢曼认为,对一些被报道的对象(系统)来说,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因为他们了解原初的真实情况;而对广大受众来说,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媒体报道的就是真实情况。
基于这一实际状况,卢曼认为,以上问题可以排除在对大众媒体系统的研究之外。要认识和研究大众媒体,重要的是认识它的运作方式,即它是如何生产或建构真实的?
卢曼的基本观点是,包括媒体在内的所有社会系统都通过自身的操作建构真实;对它们来说,原初的真实不是存在于“外部的世界”,而是存在于认知操作中。在此意义上,卢曼称其所主张的认识论为“操作的建构主义”。其核心内涵是:对操作的系统来说,世界是作为真实而存在的,并且是作为环境而存在的;但这个环境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视域,对系统来说是不可及的,系统只能通过自身的操作来建构真实、认识环境中的一部分真实或者通过对建构真实的观察者的观察来建构自身的真实。
要建构自身的真实,每个系统都要满足一些条件。大众媒体要满足的条件为区分自我指涉和他者指涉、生产自身的密码等。卢曼认为,要认识大众媒体,就要将关于大众媒体的理论置于关于现代社会的一般理论中。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它是由诸多发挥着自身功能的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法律系统等构成的。这些系统的绩效能力能够不断提升,是因为它们自身在细分,并且具有操作性闭合和自我生产的自治性等特征。
大众媒体作为功能系统的自我指涉和他者指涉
在卢曼关于一般系统的描写中,区分和差异是两个互相关联的关键概念。当一个区分被做出时,比如当树上的一只鸟被与其周边的他物区分开来时,就出现了差异,即被区分物(如鸟与周边他物)之间的差异。这种区分被卢曼称为“操作”。而当被区分出的某物(如鸟)之外的万物被忽视而此物(如鸟)被标示出时,就出现了观察。观察是由认识的系统(人和社会的系统如政治系统、法律系统、经济系统、大众媒体系统等)做出的。被观察物之外的万物变成了环境。在此物的某一部分(如鸟的羽毛)与其他部分区分开时,该部分以外的其他构成部分则隐退到背景中去了,变成了环境,但这个环境是鸟的观察这一系统内部的环境。系统是在第一次观察后出现连续的观察时产生的,可以被称为操作(区分)和观察的连续统。当操作和观察只关涉系统内部的事物(如鸟的构成、习性等)时,它们是自我指涉的。当它们关涉系统外的事物(如人类的生产活动)时,其指涉是他者指涉。在系统的操作中,每一次操作都是对上一次区分的“再进入”。再进入是跨越边界的操作,它通过区分走出了上一次区分所形成的系统与环境的边界,同时划出了一种新的系统与环境的边界。在操作只关涉系统内部的事物,即自我指涉时,这种边界是系统内部的系统/环境边界;而当操作他者指涉时,则出现了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边界。
系统的操作是对世界的观察操作,在进行这种操作时,它不能同时观察自身。系统对世界的观察被卢曼称为一阶观察,而对作为观察者的系统之观察则被称为二阶观察,如传媒学对大众媒体系统的观察就是二阶观察。在一个区分做出后,下一个操作是什么,这是不确定的。由于“我”的观察总是在忽略他物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这一系统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确认客观真相”的系统。这一系统的稳定性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即被观察之物和被忽略之物(只有忽略他物才能观察某物),因而具有“双基稳定”的特征。在观察的系统出现后,系统即生成了自己的时间,并且通过自身操作的序列消耗这一时间。每一次区分的操作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都被后续的操作所分解。而通过这些操作,系统实现很多目标、完成很多事情。在此,系统在利用时间进行操作并且期待每一次操作都会引起后续操作。对大众媒体来说,这意味着它总是在假设自身的沟通会引起后续沟通、每一次传播节目会引起下一次节目的出现。因此,对大众媒体来说,重要的不是呈现目前的世界状态,而是自身操作的可持续性,也就是吸引受众的能力。
与所有其他社会系统一样,大众媒体系统也是一个闭合的系统。这种闭合性是由系统自身的操作所决定的,因为这些操作只发生在系统内部,是按照系统自身的逻辑进行的。同时,系统又是开放的,因为系统的操作往往需要从其外部环境中采集材料。对大众媒体系统来说,用于沟通的主题往往来自其寓于社会内部的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领域)。在此意义上,主题代表着他者指涉。对大众媒体系统来说,主题具有以下意义和功能。
第一,主题将媒体采用的作品(稿件、影音作品等)捆束成多种分类单位,由此组织着媒体系统的记忆。在此基础上,在正在进行的沟通中,辨别应保留和继续报道哪个主题、应放弃哪个主题。在主题层面,大众媒体系统自身在沟通中持续发生着自我指涉和他者指涉之间的表决。
第二,主题是大众媒体与其环境即其他社会领域进行结构性耦合的媒介。在选择主题时,大众媒体具有比其他系统(如政治系统、法律系统、经济系统等)大得多的弹性和灵活性;它可以通过主题选择而进入所有社会领域,而其他社会系统却难以将一些主题提供给媒体并使其得到客观的报道。
第三,作为沟通媒介,主题既可以拓展社会的沟通,又可以加速这种沟通。卢曼认为,已经被媒体报道的主题具有与货币这一经济系统媒介相同的功能。在一种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被社会接受后,不同的个体可以用它实现自己的各种交换目的(如购房、买菜、换外汇等)。同样,在一个主题被报道后,人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普遍熟知的资讯用于实现不同的沟通目的。
第四,媒体总是在区分用于沟通的主题与媒体自身的沟通功能。在功能优先的原则下,主题被选择甚至被虚构。媒体的功能首先是传播沟通、吸引受众。媒体的一些固定节目,如天气预报、晚间新闻等,在被证明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后,必须有持续的新闻填充进来。此时,为了满足这一功能,媒体可能放弃一些新闻,也可能制造一些虚假新闻。
大众媒体系统的密码、纲领和信息生产
像所有其他功能系统一样,大众媒体要持续辨识自身操作的衔接性、生产和再生产系统/环境差异,还必须引入一种机制,即密码。这一密码是对信息和非信息的区分。对该系统来说,信息是正值,是其用于标示自身操作可能性的设计值。同时,要具有将某事物确定为“信息”的自由,它又必须具有将其他事物视为无信息价值的自由。无信息价值的事物可以被称为反涉值,它对大众媒体系统的运行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这种反值,系统将陷入被信息淹没的状态,无法将自身与环境区分开来,从而无法减少复杂性、提高自身的绩效即加工信息的能力。
为了避免反值的复归,媒体做了另一种区分,即对编码和编程(制定操作纲领的过程)的区分。编程的结果是作为规则的纲领得出的。这种纲领(如新闻、娱乐节目)可以分解非信息的信息性悖论,有助于系统决定哪些事物可以作为信息来加工。因此,卢曼将密码和纲领称为双重选择机制。通过密码,大量的信息流入系统;而通过纲领,这些信息被分类和分流处理。
讨论
作为普通社会成员,我们已经能感觉到媒体无处不在的影响以及媒体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却难以把握媒体的特质。卢曼运用其社会系统理论对媒体的分析无疑为我们认识媒体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重要的资讯。作为可以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法律系统等相提并论的一个现代社会的主要功能系统,媒体按照自身的操作逻辑即信息/非信息之密码和纲领(栏目分类)运行,生产和传播信息。因此,媒体的传播内容既来自外部世界又不同于外部世界。媒体生产的信息在持续刺激社会,使社会保持清醒,也在推动社会反省和改变自身。但是,这种刺激可能是脱离环境现实的,可能引起对其他系统的过度干扰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震荡。而在后发展国家,由于功能系统(比如法律系统)本身尚处于演化和完善的过程中,各系统的建设可能并不同步,媒体的影响可能偏强,即超出其他系统的信息加工能力;也可能偏弱,即对它们的刺激不够。在第一种情况下,媒体可能会过度干扰其他系统的运行,引起这些系统内部乃至全社会的混乱,即引起结构摩擦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下,媒体可能发挥不了应有的推动社会自我反省的作用而使社会倾向于故步自封、陷入僵化。如何避免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出现,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协调各系统间的关系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