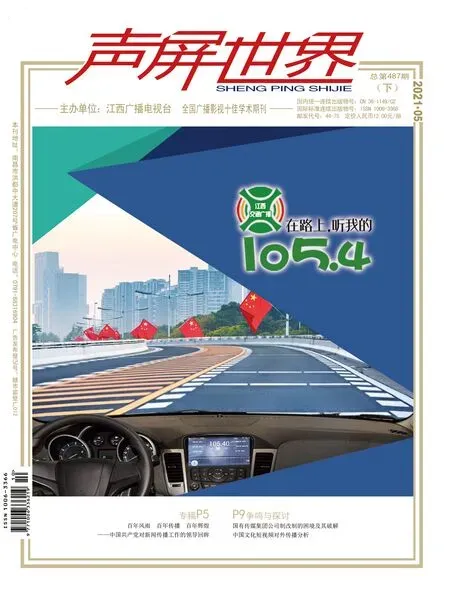从《南京之殇》看中国故事如何实现国际表达
2021-11-14赫金芳
□ 赫金芳
2017年12月13日,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与美国A+E电视网合作拍摄的两版《南京之殇》分别于美国历史频道与历史频道亚洲区主频道首播,在海外引发广泛关注,并被译配十几种语言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2021年2月23日,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公布2020年度优秀海外传播作品,《南京之殇》成功入选。一个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南京的民族创伤故事,如何引起当代国外受众的广泛关注?美国剧情版《南京之殇》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创作思路。
转变叙事视角,建立身份认同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未能及时在世界范围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连续深入的报道,加之日本右翼分子多次歪曲历史真相,南京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与认同远低于犹太人屠杀。自1982年第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南京大屠杀》面世以来,经过近30年的媒介书写,南京大屠杀早已由幸存者的个人记忆上升为中华民族的创伤记忆。但国内以往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大多以资料汇编与口述历史这两种主要形式,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讲述幸存者的创伤经历,在价值取向、主题诉求、审美理念等方面与西方主流纪录片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实现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跨文化传播。
剧情版《南京之殇》由美国A+E电视网络负责具体制作,讲述了四位西方民主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建立国际安全区、拍摄罪行影像等英勇事迹。与以往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不同,《南京之殇》将外国民主人士由见证屠杀灾难的证据符号转变为故事讲述的主角,以真正的他者视角讲述了更靠近西方受众的英雄故事。剧情版《南京之殇》在项目策划之初就确定了受众对象主要是美国受众,四位主要角色——罗伯特·威尔逊、乔治·费奇、约翰·马吉与明妮·魏特琳均为美国国籍。片中的约翰·马吉是一名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他不仅参与建立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公民免遭日本人杀害,还冒着生命危险拍摄难民营内外的惨况,留下宝贵的第一手影像资料。影片不仅再现了约翰·马吉在拍摄现场的危险气氛,还通过亚历克西斯·杜登、杨大庆等美国历史学家的采访补充他的身份背景,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而片中的四位主角在面对日军挑衅时表现出的勇敢与恐惧,面对日军暴行时的无奈与愧疚,尤其是诸如日军扯倒美国国旗,用枪指着威尔逊医生这样的情节再现,更能强烈激起美国受众的愤怒情绪。相比遥远国度八十年前的民族创伤,同胞在异国他乡的正义坚守更能引发美国受众的关注与认同。在这个过程中,观众能相对自然地完成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理解与认同,南京大屠杀话题不再只是中国话题,上升为战争对人性的扭曲、理性、道德与救赎等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深层话题,进入西方受众的文化记忆当中。
坚守真实底线,创新影像表达
真实不仅是纪录片的生命线,还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必须谨慎处理的严肃问题,所有的创作符合史实成为贯穿《南京之殇》项目全程的基本原则。在项目的前期资料搜集阶段,项目主创就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等文博档案机构查阅美国亲历者的文献资料,确保历史真实与立场的客观性;组建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权威机构的专家构成的顾问团,全程把控片子的价值导向、历史观等。“在此基础之上,撰稿创作的文稿保证每一个场景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场景中出现的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是见证事件的人物,旁白中引用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些亲历者真实书信或日记中的语言,没有任何篡改、臆想编造和夸张夸大。”由于美国A+E电视网采用“情景再现”的拍摄手法,导演组在开拍前做足准备工作,查阅大量历史照片,确保道具、服装、场景布置等细节方面的选择符合时代特征。
情景再现,“是指纪录片的一种创作技法,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扮演或搬演的方式,通过声音与画面的设计,表现客观世界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已经发生的事件或人物心理的一种电视创作技法。”由于题材的特殊性,直到2015年国内的创作者才开始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纪录片当中使用这种虚构手法。《南京之殇》以严谨的态度使用情景再现手法,不仅尊重西方民主人士的文字记忆,还考证大量文献资料确保每个再现场景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如影片开头再现美国记者阿奇拜德·斯蒂尔与提尔曼·德丁逃离南京过程中,目睹日军在江边集体屠杀中国军民的亲身经历。这一场景源自德丁登载于《纽约时报》的报道原文,由于报道原文使用的词语是“In front ofthe wall”,美方创作团队便将集体屠杀场景设置在一堵墙面前。中方顾问团根据历史记载、南京当时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等考证出场景为江岸与水面之间的一块滩涂区域,并经过与美方团队的多次沟通协调,主导了这个场景的修改。除此之外,《南京之殇》采用的情景再现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并且创造性地通过后期调色、相似构图转场等影像处理,将虚构的情景再现与第一手影像资料结合起来,观众既清晰分辨历史真实与虚构场景又提升影片的画面质感。片中还让专业演员以直面镜头的方式完成替代性口述,在打破第四面墙的过程中,演员或悲伤或气愤或愧疚的细腻表情与接近历史真实的再现场景结合在一起,能够最大限度地将人物蕴含在文字当中的情绪、情感还原并传达给观众,有利于受众沉浸其中。
再现记忆细节,引发情感共鸣
“以往纪录片创作者们在处理南京大屠杀题材时,多采用全知视角,聚焦历史事件本身,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剧情版《南京之殇》则以四位美国民主人士的日记、书信以及自传等文字记载作为基础,通过展现他们的个人遭遇再现南京大屠杀的黑暗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记忆中选择哪些场景进行展现,能够侧面体现出创作者的主观意图。“纪录片文本通过‘创伤’叙事将受难者的创伤经历、身体和情感伤痛等个体创伤,经由视听媒介‘符号化’并传达给观众,从而在集体范围内形成对创伤的认同和创伤记忆”。四位主要角色在片中都遭遇了不可磨灭的心灵创伤,如因制止日军侵犯医院护士而被枪指着的威尔逊医生,不止一次目睹美国国旗被日军粗暴扯下的乔治·费奇等,同胞的个体经历经由剧情化的再现场景直观呈现在当代美国观众面前,能够最大限度地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及身份认同。而片中重点塑造的明妮·魏特琳这一形象,更是将这种情感共鸣推向极致。
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明妮·魏特琳在金陵女子学院庇护中国妇女和女孩免遭日军侵害,不止一次面对日军的挑衅,甚至威胁要强奸她。在那样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明妮不可能庇护每一个弱者,目睹太多暴行却无法施以援手,使得明妮陷入深深的愧疚当中无法自拔,她不止一次在日记当中表达自己有错,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后,她仍然无法走出抑郁状态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南京之殇》在塑造明妮·魏特琳这个悲剧英雄形象时,将明妮日记中的记忆细节加以形象再现,并以主观镜头等艺术化处理将明妮饱受折磨的内心展现出来。如影片以情景再现的形式将1937年12月17日晚这个明妮记忆中无法忘记的黑暗时刻呈现在观众面前:被乌云遮蔽的月亮,满地干枯的银杏叶沙沙作响,被抓起头发的中国女人,持枪的日本士兵与明妮匆忙赶来的脚步特写,坚毅站立的守护身姿共同建构起一个力量对比悬殊的悲剧场景。与此同时,演员声情并茂的替代性口述交叉出现在再现场景中,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明妮的恐惧与绝望,一声声“救命”宛如在观众耳侧,极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结语
纪录片以其跨越语言差异的视听影像、真实动人的审美特质,成为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传播媒介。但在具体的影像制作过程中,国内的纪录创作者很难摆脱审美定式,在叙事视角、内容架构及影像等方面与国际主流的纪录片风格存在较大差距。只有真正的他者视角和国际表达,才更有可能将更多中国故事传播到世界范围内。《南京之殇》在中方投资确保整体价值导向的基础上,将影片的制作交给美方团队,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现阶段值得借鉴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