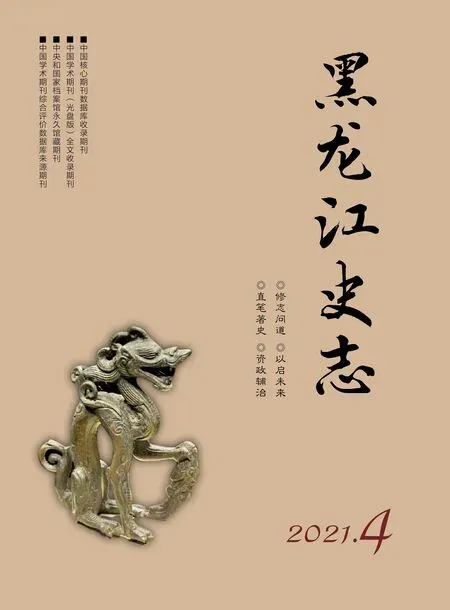民国方志中地方认同的构建
2021-11-13申津宁
申津宁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方志作为中国特有的产物,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方志首先是在于地方,而地方这个概念是相对中央而言,但是每个地方都是独特的,地方的认同有赖于这种独特性。受近代思潮的影响,作为基于传统文化的方志,在当时世风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形态。民国时期地方自治思潮盛行,相较于以往,地方的重要性极大地提高,而这种地方意识的崛起在方志中也有体现。方志本身就是当地的“共同体的符号构建”,方志是当地的认同体现。民国修志数量较多,林林总总千余种,其中著名者如余绍宋所修《龙游县志》,叶楚伧、柳诒徵所修《首都志》,傅振伦所修《新河县志》,地理学家张其昀编纂的《夏河县志》《遵义县志》,黎锦熙所修《城固县志》(已散佚)、《同官县志》《黄陵县志》《洛川县志》《宜川县志》,以及修于西南后方重庆的《北碚志》等。方志本就立足于地方,其有凝聚地方之功用,而对方志如何构建地方认同的研究尚未深入,通过研究方志如何构建地方认同对理解方志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时间的事件——近代方志中的“地方”时间叙述
在中国的历史叙事当中,历史基于时间。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已经清楚阐明了,时间是人类权力关系中能量的一部分。时间在日历,在工作日程,在日常活动中具体化为客观存在;在官方的宗教、哲学、历史和学术流派的权威人士所讲述的故事中,时间化为争夺统治和支配权的工具和舞台。就如同朝贡体系中的朝鲜、琉球、安南等国,通过沿用中国的年号,从而进入中国构建的秩序之中。虽然对近代方志的性质近来多有讨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方志作为对过去的构建,涵盖了时间与空间。
记载时间的方式多种多样,近代方志中记载时间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干支纪年法,天干加地支,如《洛川县志》就有记载“周武王十三年乙卯”,这种时间同宇宙时间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少受到政治时间的干预。60年一个甲子,甲子年开始,癸亥年结束,但是这种纪年方法并非线性的,而是周期的,并且他们并没有标志彼此的不同,故无法将其置于历史时间之中。通常认为时间是线性的,时间一去不复返,但是这种以周期为中心的记录方式在中国古代较为盛行,如阴阳家所提出的五德始终说,这种记录是建基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古代人使用周期来描述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中某种不断再现的模式,如果历史不能以周期表现,那么历史经验便毫无用处。
但是中国并非没有线性时间概念,方志中第二种时间便是块状的政治时间,即以一个朝代中的君王的统治计算,以政治时间加上天干地支纪年,从而使政治时间历史化。在对某些主要的政治或社会时间加以解释时,某些年份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也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性,如《洛川县志》中记载:“周幽王二年辛酉(民前二六九一,西前七八零)”,由此可见民国成立与耶稣诞生就成为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不同的时间记录方式表达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朝贡体系下的中国,一个君主的年号不仅仅是对于中国,更是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像朝鲜、琉球等国皆使用中国的年号,表明了中国时间的世界性。而在民国的方志计时中,“西前七八零”这种记录时间的方式表现为民国后期政治时间的西化的影响。虽然有西方的影响,但是民国的时间记录仍然以民国为主体,民国的时间记录仍然占据当时方志中的主体地位。方志中时间的记录体现了地方对所属政权的归属与认同,也体现了政权对地方的掌控。从民国前期《新河县志》到民国后期《洛川县志》中的时间皆以民国记,属于的民国政治时间中,《洛川县志》中序言多题于民国三十二年,民国方志的时间记录都以民国纪年为基准。而这种时间的记录方式象征了政权对于地方的掌控。地方使用年号标志着它接受了政权所主宰的计时体系,并进入了政权的辖区,因而接受了以政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时空体系。
记录时间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方志中第三种时间记录方式则是属于地方的事件时间叙述。在人们的观念中,时间是无法以刻度精准形成的,即对时间的测量不是根据其在时间线上标尺的位置,而是根据社会上富有意义的事件,或者说是根据这些事件之间的间隔。这点在于地方上特别明显,普通的民众只知晨钟暮鼓,春夏秋冬,其判断时间流逝的方式依赖于日出日落,气温的变化以及打更人的提醒,在没有准确计时工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形成精确的时间概念,他们也无须精确安排时间,他们只要一年年往复循环这些重要日子。而这些日子因为文化地理不同而异,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便具有了地方性。对于地方的时间的叙述,方志往往会使用地方的重大事件来构建属于地方的时间,虽然前面会有带有政权属性的年号时间,但是这种年号仅仅是一种政治意义与宇宙时间计时。而这种作为时间的地方事件往往极具地方特色,《洛川县志》记载了疆域沿革,重修县志经过,匪患、剿匪、政权成立等地方事件;《新河县志》沿革记载了地方历史沿革,如区划设立,地域调整等事件。这些被记录的事件是地方记忆的组成部分,地方的人们根据这些事件界定出属于地方的时间,在地方的人们借此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为了创建共同的认同意识,构建属于自身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集体的身份认同隐藏在集体的记忆之中,方志通过地方事件构建出了属于自身的地方事件时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分享共同记忆的人都是地方的参与者,而不同的地方记忆又会构成不同的地方文化,地方时间是具有文化内涵的。《黄陵县志》中通过对黄帝的书写及庆典的构造试图弥合“现在”与“过去”在时间上的鸿沟,从而构建出黄帝的政统继承,而这点足以让黄陵县之人感到骄傲并产生认同与归属。黄陵县的人们以及前来参拜者通过对于先祖建立功业的伟大事迹的时间线的追溯来表达对于先祖及血脉的骄傲。而这种与整体不同的地方时间构建出一个地方的共同记忆和文化世界,并表达出当地的荣光,使当地之人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
对地方的时间构建不同于国家统一的历法,地方的时间是以事件为主体,加上政治事件与宇宙时间,从而构建出属于地方的时间。而地方是相对于政权中央而言,没有中央政权就无所谓地方,政治时间与宇宙时间使地方的时间不会游离。而作为构成地方时间的事件,是对于地方的历史叙述,是集体记忆的象征,也有了文化的内涵。而集体的身份认同隐藏在集体的记忆之中,在地方群众的参与和对往昔荣光的回忆中构建出地方的认同。
二、“记忆之场”到“文化之场”
记忆之场”是引自皮埃尔·诺拉,由场所和记忆两部分组成,记忆是需要载体的,亦是有范围的,而这个范围和载体就是记忆的场所,这里借用这个术语是因为其与方志相性契合,场所撑开了历史的空间,而历史的时间必须借助场域才会变得立体。方志中的地方认同建基于其地方性,而每个地方就是一个场域,认同则依赖于共同的记忆。
方志中人是记忆的主体,而在方志中这样的群体表现为官,绅,民。官员修志一是为了解当地情况,以其资政,二是作为政绩,名垂地方。而乡绅参与则表达地方或者家族的自豪,通过修志则可以将士绅私人记忆转化为文本,从而再转化县域的公共记忆,再加之方志的官修性,被记录者的事迹获得官方认可,再于志书中“被立言”,从而达到不朽。至于普通民众,虽然方志无法记载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方志中(人口志、氏族志)找到自己的存在,其中忠孝、节烈等还会有专门记载,与明清方志不同的地方是近代方志更加注重对普通人的书写,方志的关注方向下沉,开始由“官”转向“民”。作为地方志中记忆主体的人,其生活范围都在方志所记述的地方之内,记忆也在这个场域之内,从而这个场域从地理概念转变为观念概念,而这种转换就会体现在方志的书写当中。
回忆也植根于被唤醒的空间。方志中,地方是回忆的空间,当它们不在场时,便会被当作故乡在记忆中扎根。方志中所记载的建筑、古迹等是记忆的媒介,亦承载了当地大众的公共记忆,在衙署象征着对于城的掌控,象征着官方权力对于城市空间的大一统政治控制的同时,而祠祀,寺观等公共场所则扮演了公共角色,维持了统治的权威及构建大众社区两方面,从而使官绅民连接起来,可以说方志本身就是当地的“共同体的符号构建”。但是记忆是鲜活的,它是需要载体来对它进行承载的。博物馆、档案馆、墓地和收藏品、节日、周年纪念、契约、会议记录、古迹、庙宇、联想:所有这些就是别的时代和永恒幻觉的见证者。通过这些途径,方志中构造了一个共同的经验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了连接与约束的作用,如地方家族与乡约,从而构建了人与人的联系与信任。在人们被地方的公共事务包围的时候,当地的人们会对其形成诸如纪念性、美观性的认识,并将自身也投入进去。每个群体都会将自己特有的记忆落实到某个地点加以纪念。
并非所有地方的公共记忆都会成为文化,有一些公共记忆会在时间中消亡,被传承下来的就会成为地方的文化记忆。而经过筛选过的方志中的人以及方志中所记载的地点与事物,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其最终都会成为地方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地方文化记忆在地方的群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决定了该群体的认同及其对自身的认识。不同的地方自身的文化记忆是不同的,如《黄陵县志》中亦多提及黄帝,《黄陵志》一卷尤为浩大,几乎为余者之半。黄陵县原为中部县,因黄帝陵寝所在,遂更名为黄陵县,志书中借黄帝阐发民族独立思想较为浓厚。两本志书中都提到了对祭祀与节日,《黄陵县志》中就大量记载了对于黄帝陵寝的祭祀,而这些文化的形成与节日和仪式密不可分。节日与仪式的定期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仪式性的重复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保证了群体的聚合性。不仅仅如此,方志中的风俗志、方言谣谚志都是这种文化记忆的体现,尤其是风俗志,近代方志中的风俗志详细记载了当地的庆典,节日与礼仪;方言谣谚亦是这种文化记忆的体现。对于记忆来说,遗忘是远远多于回忆的,如何阐释回忆才是方志研究的重点。地方的文化回忆引导着当地人们的生活,从而有了被记载传播的意义。方志构建出一个场域,这个场域里有自然的空间如地理疆域,也有客观的事实,像历史沿革,而文化记忆则是在这个自然空间里加入了文化符号,使整个自然场景都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从而使方志从单纯的“记忆之场”向“文化之场”转变。由此形成的地方认同其实是社会构建的产物,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认同。
方志承接过去,保留了大量过去的资料,是一个地方的记忆的文字记录,同时又连接现在,无论官员,乡绅还是每一个最普通的人都可以在方志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共同记忆与地方符号共同构建这样一个地方的共同体。方志是一个地方集体记忆的载体。分享了某一集体的集体记忆的人,就可以凭借此事实证明自己归属于这一群体,所以集体记忆不仅在空间与时间上是具体的,而且我们认为,它在认同上也是具体的,这即是说,集体记忆完全是站在一个真实、活生生的群体的立场上的。集体记忆的时空概念与相应群体的各种社会交往模式处于一种充盈着情感与价值的共生关系中,时空观念在其中表现为故乡与生活史。由此方志的修纂形成了一种基于地方共同体上的地方认同。
三、书写与被书写——曾经的“失语群体”
在传统的方志中,掌握书写权力的是士绅,其他阶级都是被书写、被言说的。明清官修志书大多为官督绅办,官督学办的产物。通志以督巡抚领衔,知府、绅士、学者执笔;府州县志由知府、知州、知县领衔,绅士学者执笔。艾伯华于《征服与统治者》一书中指出,官员实际上来自于地主集团,所以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只存在一个阶级,即士绅。在他的观念之中,中国的士绅社会有三个特点。(一)士绅阶级在经济上依赖土地资本……(二)士绅是由地主、学者、官员所组成,在士绅家庭中家人多半同时参与这三种职业。(三)……从艾氏的观点来看修志人员的组成,无论是督抚、知府、知县等官员,抑或是绅士,学者,其都出于同一阶级即士绅。这种单一的修志群体就导致了方志叙事角度的单一,也造成了传统中国士农工商中其他三个阶级的失语。在传统方志中,其他的阶级一直是被书写的,而这种书写却充满了忽视与想象。如章学诚所编《乾隆永清县志》,其中毫无农工商三者的痕迹,谢氏《广西通志》中亦只有二录:宦迹、谪宦;六列传: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释、诸蛮对人进行记录,其着墨仍重于官宦。而其对于普通人物的书写亦多为执笔者自己的加工与想象。
一个地方中必然有不同的机构、行政区划、思想团体、政党、压力集团、商业团体以及各种宗教,他们都会以各自的方式影响地方的认同。在传统的方志中,有些声音被忽视了。但是在近代的方志中这种现象发生了改变,黎锦熙所修《洛川县志》等志便极具有这一特色,《人口志》有对当地所有人口的调查与统计,《工商志》则记录了工业与商业发展情况及团体,《社会志》则包含了各种人民团体,社会救助机构,《氏族志》虽然前代方志就有,但是民国方志中的《氏族志》运用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当地的姓氏进行了普遍统计与渊源考察。从这些近代志书中可以看到往昔方志中失语群体的存在。
这种曾经“失语群体”的发声首先依赖于民国思潮的改变,“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君史之敝,极于今日。”史学如此,志学亦如是,方志从关注作为精英集团的士绅到关注普通的民众。其次方志的功用也发生了改变,清朝方志独重人文,有关社会方面的内容“不外官吏政绩、士绅行为、寡妇贞操以及地方学者之著述或吟咏。”而近代方志更加注重资政之功用,陈正祥认为:“方志有点像欧美国家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y)”,毛一波于《方志新论》中亦提出此种观点,此点尤其以张其昀《遵义新志》与黎氏所修志书为甚。方志的资政属性会使方志形态发生改变,要求方志运用和吸收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无论是民国的民主思潮还是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会将曾经的“失语阶级”纳入到方志修纂的轨道中去。黎氏所修志书,皆拟定《陕西省第三区各县续修方志工作准则》及《陕西省第三区各县续修方志预拟篇目及采访须知》,并参照城固县志委员会所印之调查表式,共制定挨户调查表式三十种,挨保调查表式十一种。乡镇调查表式二十二种,其他调查表式五十种。这种调查表使人口数量最大的民众参与到方志的调查编修中来,虽然这种参与并非是主动的,但是相较于以往只能被书写的状态,其参与度大大提高,而且其掌握了主动发声的权力。工商业也是如此,工商业参与编修的主动性更高,黎氏所修《同官县志》主要编写人邑人和文身份就是同官县煤矿业同业公会主席,采编亦有煤矿经理的参与。由此可知在近代的方志编写中,由于方志的形态改变,作为曾经的“失语阶级”的农工商在近代方志中完成了由被书写到主动书写的转变,而这种书写群体的扩大会加深地方的认同。
集体的认同是参与到集体之中的个人来进行身份认同的问题,它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而是取决于个体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它。它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它的集体成员的意识中的活跃程度以及它如何促成集体成员的思考和行为。其实地方认同也是通过互动来构建和再生产的。近代方志书写群体的扩大使得地方群体的参与活跃度提高,而具有区域研究性质的近代方志也会使当地的读者去思考地方。在编修方志过程的互动中,通过共同的语言、思考和知识的回忆会形成一个地方的文化意义,即共同的价值、经验、思考、理解制造了地方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共同拥有的文化意义会促生一种集体共识,使每一个分享了这种文化意义的人形成了一种集体高于个人的观感。这种对于享有共同文化群体的认同及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地方,从而形成了方志中地方认同。
结语
当提及方志的时候,总是会首先想到地方。而近代方志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其书写群体范围大大增加。地方是相对于中央的一个概念,但是每个地方都是独特的,首先专属于地方的时间是特别的,而作为构成地方时间的事件,是对于地方的历史叙述,是集体记忆的象征,也有了文化的内涵。从地方这个词就可以看出地方的空间属性,方志空间中的文化符号使得方志的自然空间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书写群体的扩大使得互动与参与增加,在地方这么一个文化记忆的媒介中,分享了共同的文化的群体会对集体产生认同,而这个集体与共同的文化又存于地方之中,从而构建出了方志中的地方认同。
注释:
1.来新夏主编.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A].中国地方志综览[C].合肥:黄山书社,1988.
2. [美]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从明到清的时间重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4.
3. [美]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从明到清的时间重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58.
4.6.申津宁.新旧之间——民国修志思想的转移[J].黑龙江史志,2020,(11).
5.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1.
7. [法]皮埃尔·诺拉著,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8.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2.
9.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2.
10.刘纬毅等著.中国方志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232-233.
11.黄克武.反思现代:中国近代历史书写的重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75.
12.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N].时务报,1897-7.
13.李泰棻.方志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81.
14.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上册)[M].台北:南天书局出版社,1995:41.
15.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