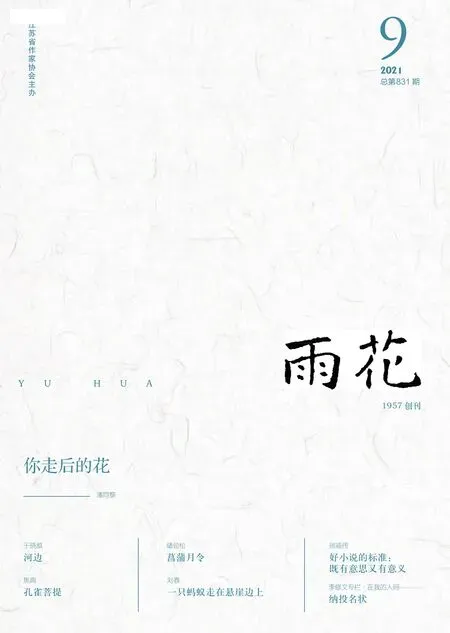残年
2021-11-13江少宾
江少宾
是你啊,回来过清明吧?我有些疑惑,眼又看不大清……
几个月不见,玉大娘又老去了一轮,她坐在门边,手搭凉棚,直到我摘下口罩,快步走到她面前,她才扶着门框,欢天喜地地站起来,皱纹密布的小脸浮起笑容。她是真的欢喜,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垂暮光阴里,她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每一个主动走近她的人。出门的人是不敢轻易盼望的,他们是一群不知疲倦的候鸟,春节短暂的居留过后,又陆陆续续飞往大江南北,那里有他们含辛茹苦、经年累月垒就的新巢。这些年,举家外迁的牌楼人不胜枚举,有些人连户口都移走了,多年杳无音讯,牌楼成了他们成功逃离的“老家”。定旺、从龙、文革、和贵、志高……曾几何时,这些打着赤脚一路“啪嗒啪嗒”的庄稼汉子,从田埂上不声不响地消失了。熟悉的田畴一季季更迭,稻子弯了腰,棉花白了头,绿油油的麦浪无拘无束地翻滚,一波波涌来,又一波波散去……在异乡,他们过得还好吗?我不知道。
“采芹呢?”我问玉大娘,玉大娘抓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地直接把我摁在凳子上。她的手太干枯了,一层皱巴巴的老皮,包着几根生硬的瘦骨头。“采芹啊?做礼拜去了!我跟你讲咯,拦都拦不住,怎么劝都不听,天没亮就出门,也不打个手电筒,十二里路哎,高低要步行,也不怕刮大风,也不管下大雨,也不顾大日头,魔怔……”玉大娘越说越激动,四肢微微颤抖,泪水涟涟。我有些意外,做礼拜只能去扫帚沟老街,采芹怎么就肯步行十二里,风雨无阻地坚持做礼拜呢?玉大娘抓着我的手,一直在絮叨,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安慰说:“又不是做什么坏事啊!你别管了,把你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玉大娘的失望溢于言表,小脸皱起来,声音矮下去:“不是坏事?难不成还是什么好事啊?”
玉大娘八十七岁了,是牌楼还健在的最年长的老人,每次回来,我都要去看看她,听她天南海北地扯闲篇——几个月不见,她憋了一肚子话,急于说给我听——东头那个谁谁谁得了绝症,没法子医了,只能躺在床上等死,看着真寒心;西头那个谁谁谁家进贼了,两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刀,那个谁谁谁大气都不敢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搬家一样扛着电视机,拎着煤气罐……我羞愧地听着,内心涌动着一阵阵风暴。“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玉大娘知道我在新闻单位工作,但从业二十多年来,我既没有给她写过一篇报道,也没有给她拍过一个镜头,换句话说,玉大娘的病痛、畏惧、悲欢,从未真正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她的存在,同时也是她的消失,她是亲历者,同时也是见证人。
玉大娘老伴过世早,我对他的印象已经很淡了,只记得他个子不高,抽旱烟,头发稀疏,而且很早就白了;两个儿子都是瓦工,常年不着家,两个孙子三个孙女都是牌楼人,如今户口都迁到了外地;留在玉大娘身边的,只有小女儿采芹。玉大娘罹患类风湿(牌楼很多妇女都有类风湿),久治不愈,左腿很早就瘸了。瘸腿之后的玉大娘并不格外懊恼,她以为自己的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谁能想到呢,又病恹恹地活了十几年,活得她自己都有些不耐烦了。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人前抱怨,人后也抱怨:“腿走不动,眼又看不清,废人一个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她翻来覆去说了十几年,大家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她自知无趣,便对摇头摆尾的畜生说,对墙上笑眯眯的老伴说,甚至会在农历七月半这天,对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说。
农历七月半,中元节,牌楼人俗称“鬼节”,这是老一辈牌楼人不敢怠慢的大日子,重要性不亚于清明和冬至。老一辈牌楼人笃信,七月半这天,亡魂会从另一个世界回到人间。这一天,大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脚抬起来,不能踩门槛!脚抬起来,不能踩门槛!为什么不能踩门槛呢?问大人,大人都答不上来,只虎着脸,佯装生气。天一擦黑,年幼的孩子便被妈妈搂在怀里,从一个房间抱到另一个房间,生怕被人抢了去。这种日子,谁敢出来作恶呢?实则是,小孩子“火焰低”,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何谓“火焰”?我解释不清楚,玄而又玄。玉大娘经常提起青苔的离奇经历,说他小时候不止一次“看见”自己早逝的老爹爹,坐在老奶奶旁边,光秃秃的脑袋埋在蓝边碗里,狼吞虎咽,几天没有吃饭的样子。还有一次,青苔“看见”老爹爹盘在篾片散落的破藤椅上,手里捏着半个白面馒头,两眼空空的,像两个黑洞……青苔“咯咯咯”地笑,说,那个秃头又来了……童言无忌。苦了老奶奶,老泪纵横,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你不要吓孩子,你不要吓孩子……”青苔“咯咯咯”地笑,他自幼胆大,奶奶稍不留神,他便泥鳅一样溜出门去。
青苔成年之后沦为一个远近闻名的赌棍,赌到倾家荡产,过着在刀口上舔血的日子。他三十二岁就从牌楼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留下一座被丛丛蒿草围起来的老房子。
七月半这天是不宜出门的,老人们约好了似的,一大早就起来了,粗衣,素食,洗锅刷碗,洒扫庭院,忙而不乱地准备着一场约定俗成的神圣仪式。日落时分,炊烟袅袅,仪式在脉脉余晖中开始了。家家户户大门外,供桌已经提前摆好了,桌子上供着三碗饭、三碗菜、三双筷子、三盏小酒杯。也有供五碗饭五碗菜的,以三碗的居多,无论是五碗还是三碗,其中必有一碗山芋粉丝——牌楼人自己做的山芋粉丝很好吃,也很有名。腊月里,经常有外地人开着车子,挨家挨户上门收购。三和五都是单数,为什么不能是四碗、六碗,又为什么必有一碗山芋粉丝呢?我不知道。等主妇把一切都准备妥了,主事的男人(牌楼人谓之“孝子”)再恭恭敬敬地请出祖宗牌位,用事先拧好的潮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一年了,牌位上积满灰尘,脸盆里的水很快就黑了,至少得换两盆水才能擦干净。平时为什么不擦呢?我问过我妈,我妈瞪了我一眼,神情严肃,再无下文。旧时的乡村,凡是与祭祀有关的事情,孩子的好奇心是很难得到满足的,清规戒律太多了,有些事甚至不能开口问,问,也是一件犯忌的事情。如今看来,那些清规戒律大多莫须有,但正是那些莫须有的清规戒律,让寻常的祭祀活动有了一种神秘感和仪式感,也让我们自幼便对天地万物存了一份敬畏心。
擦拭过后的祖宗牌位忽然有了重量,黑黢黢的颜体字看上去墨汁未干,仿佛祖宗们又活了过来,我对漫漶的字迹很不满意,自己忍不住又描了一遍。神圣的时刻终于到了,孝子将牌位轻轻放在供桌上(坐南朝北),然后蹲下来,擦亮火柴,窝着一只手,慢慢引燃铺在地上的一堆大裱纸。火苗很快就蹿出来了,越蹿越高,成了灼热的火焰,呼呼呼,像一个人躺在地上吹着嘶哑的口哨。一家人围着火焰,神情肃穆,取暖似的站在四周,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抽烟。事实上是不能抽烟,也不能放鞭炮。七月半是唯一一个不放鞭炮的祭日。玉大娘解释说,鞭炮声太吵了,归来的亡魂会受其惊扰。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也无法自圆其说,但玉大娘不许我质疑,她是信其有的,老一辈人一直信其有。或许,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构建了乡村社会原始而朴素的宗教。
磕头是最后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火焰渐小渐熄时,就能磕头了,孝子先磕,然后是主妇,再然后是孩子,长幼有序。不能随便坏了规矩。磕头也有讲究,要么磕三个,要么磕九个——风烛残年的老奶奶和有孕在身的新媳妇喜欢磕九个——不能是双数,要一面磕一面在心里默数。若是不小心磕了双数,得站起来,重新磕。
祖宗牌位祭完之后,还得原样放回去,再取,又是新的一年了。牌楼人家的祖宗牌位一般都搁在大门楼上,没有大门楼的人家,会在堂屋墙上开一个小神龛。玉大娘是个例外。她家既有大门楼,也有小神龛,门楼上摆着祖宗牌位,神龛里供着观音菩萨。井水不犯河水。
祭祖是仪式的第一项,第二项是路祭,要找一个岔路口,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烧几刀大裱纸。孩子和妇女是不宜路祭的。妇女怎么也不宜呢?牌楼有些妇女胆子大着呢,敢一个人走很长很长的夜路,一个人黑灯瞎火地摸上山偷柴……你不是去烧过纸吗?那一回我问玉大娘,玉大娘的小脸浮起一片阴云,好半天之后才自言自语似的说:“我不去,谁去呢?采芹不信这个的,回回都要和我吵,吵不赢就是了!那些孤魂野鬼,我有的还认得,总要烧几刀纸吧……”我没有想到这一层,一时间竟然愣住了。那些暮色四合、众鸟归巢的黄昏,玉大娘孤零零地蹲在路口,一面慢条斯理地烧纸,一面自言自语:“腿走不动,眼又看不清,废人一个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路祭结束急急回家的人心有戚戚,却不方便停下来劝她。也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劝她,她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像个巫婆,翻来覆去地尽是些车轱辘话。实则是,这个巫婆一样的老人已经被漫长的岁月榨干了。当骨头缝里的疼痛一阵阵袭来,她只能咬紧空荡荡的牙床,皱着小脸,靠在门框上,眼巴巴地望着空荡荡的机耕路,长时间自言自语。她不止一次在锥心蚀骨的疼痛中生出这样的幻觉:老伴站在远处,面目模糊,一面招手一面说,来啊,来啊……大半天之后,她从一身虚汗里慢慢缓过来,瞅一眼墙上的老伴,怅然若失。机耕路依旧空荡荡,绿树掩映,光影斑驳,一眼望不到尽头。她确信自己还活着,幽幽地长吁一口气。
她颤巍巍地踏进八十岁的门槛,八十岁,多少个日日夜夜啊,牌楼没几个人活到这个岁数。她知足了,也早已看淡了生死,什么都能放下了,唯独放不下采芹。她还记得那个四月的响晴天,四十二岁的她一个人把采芹生在芹菜地里,那么多的血,菜地染红了一大片。当婆婆踮着小脚急慌慌赶来,她怀里那个血迹斑斑的女婴把婆婆吓傻了——看上去就是几根骨头裹着一层皮,活像一个刚刚破壳的外星人,不超过四斤——好半天之后婆婆才回过神来,憋出一句话:“这伢恐怕养不活啊。”玉大娘躺在血泊里,只觉得心慌,口渴,天旋地转。
吊在玉大娘干瘪的乳房上,采芹挣扎着活了下来,转眼长到十八岁,大姑娘了,圆润的苹果脸,泛着近乎透明的光泽。媒人不分白天黑夜地上门,走马灯似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玉大娘喜滋滋地,左看右看,最后相中了一个在牌楼干活的小木匠,这人不抽烟,能喝几杯酒,娃娃脸,大眼睛,面善。那时候手艺人吃香,不问资历,不管年龄,都是师傅,都得好烟好酒地伺候着。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下午茶”——猪油下面条,碧绿的菜叶,焦黄的荷包蛋,闻起来香喷喷的,馋——这是手艺人的福利,猪油下面条和荷包蛋都是奢侈品,除了过年,平时我们是吃不到的。
女大不由娘,采芹悄悄相中了一个“兵哥哥”,国字脸,小平头,喜欢扎马步,稳稳当当,像一根树桩。他脱下军装之后进了轧花厂,负责过磅,不知道是正式工还是合同工,是工人还是干部,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泥腿子”,而是一个不用赤脚就能挣钱的“公家人”。
手艺人吃百家饭,但农忙时还是要赤脚下田,面朝黄土背朝天,公家人多体面啊,国家每个月按时发钱,太阳晒不到,雨也淋不着。玉大娘自然也是愿意的,只是舍不得采芹,媒人把日子都掐好了,她竟死皮赖脸地单方面毁约,还毁了两次。采芹不答应了,坐在房里生闷气,当真是女大不中留,玉大娘无可奈何,只好两眼含泪,看着采芹穿着红绣鞋,小鹿似的,欢快地奔向村口的机耕路……
采芹命好,嫁过去就过上了少奶奶一样的幸福生活,牌楼待嫁的姑娘眼热了,毫不掩饰自己的嫉妒与羡慕。谁能想到呢?采芹的幸福生活没能维持多久,她婚后迟迟不开怀,吃尽各种偏方,始终没有效果。那年腊月,采芹好说歹说,总算把将信将疑的丈夫哄进了医院,一查,丈夫整个人就蔫了,抱着头,蹲在地上,闷声闷气地抽烟。那个闭塞的年代,乡下人不孕不育尚是不治之症,他绝望地甩开采芹,醉汉一样歪歪倒倒,一头撞上一辆疾驶而来的严重超载的农班车。那是采芹挥之不去的噩梦,她目睹丈夫在巨大的撞击下腾空而起,像一片轻盈的枯叶,在空中翻卷着,又碌碡一样,跌了下来。她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幕吓傻了,浑身筛糠一样瑟瑟发抖,一个人居然能够变得那么轻,那是她身强力壮的丈夫吗?她不相信!
她奔过去,冰冷的马路上蜿蜒着一大摊血。啊啊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黄昏摇摇欲坠。炮仗声此起彼伏,就要过年了。
七七四十九天,她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醒着的夜里,她幽灵一样在卧室和客厅间徘徊,头发掉了一万根。家里空荡荡的,像一座专门储存时间的冷库。
一百天过去了。一周年过去了。三周年过去了。她收拾好自己的衣物,朝婆婆跪了下来,说,我要回牌楼。婆婆摸摸她的脸,干枯的眼里渗出几滴泪。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牌楼人一致同意接纳采芹,采芹成了第一个离开牌楼之后又申请迁回牌楼的人。
重新回到牌楼的采芹仿佛变了一个人,苹果脸成了鸭蛋脸,腌过似的,不复旧时光泽。你这不算事哦!遇到合适的,迟早还是要再嫁啊……老人们劝她,她坚定地摇头,泪水决堤一样漫出来,漫的次数多了,老人们也不好再劝,私下里各种猜测。她也真是命硬哦!那么好的一个男人,说没就没了……她影子一样来来回回,路上遇到人,条件反射似的垂下头,像被人活捉的小偷。玉大娘心疼女儿,每每出面维护,她慌不迭地冲过去,推推搡搡着,将采芹一路扯回家。
她守着玉大娘,独自打理五亩多田,起早贪黑地,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长工。稻子一颗颗黄了,麦苗一垄垄青了,棉花一片片白了……她在一季季收成里慢慢活了过来,脸上又有了久违的笑容。
她活了过来,玉大娘也跟着活了过来。农闲时,母女俩时常结伴上街,慢腾腾的,有说有笑,像是遇到了什么开心事。有几次,她甚至把扭扭捏捏的玉大娘牵进老杜茶馆,泡一壶茶,老少爷们一样坐在凳子上,大大方方地撕油条,吃春卷。妇女进茶馆,那时还是稀罕事,老少爷们窃窃私语,“呵呵呵”地傻笑。
媒人又开始登门。她们以为,采芹公开抛头露面是释放信号,她已经治愈了内心的创伤,拂去了内心的阴影,开始为下半生打算了。采芹也一改往日的冷脸,大大方方地给媒人泡茶,续水,递扇子。玉大娘仿佛年轻了十岁,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喜色,谢天谢地,菩萨终于显灵了!
“想通了就好,哪有一生守寡的人呢?总不能守着一个死人过一辈子啊!”
“伢啦,你也算对得起他了!趁早,寻个人过自己的日子。”
……
媒人领来一个,她见一个,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年纪大的,年纪轻的……玉大娘惶惑了,伢啦,这个看不中,那个不如意,你到底想找什么人啊?
她捂着脸,哽咽道:“这几天,一到晚上,我就看到他,躺在血里,望着我,抽搐……我以为,已经忘了,哪晓得,还是,忘不掉……”
玉大娘兀自一惊,颤巍巍地盯着她,仿佛蓦然间撞见女婿的鬼魂。
再无媒人上门。
玉大娘的脸越皱越小,腿完全瘸了,随手拄一根用松木削成的拐棍。
漠漠平田新雨后。布谷声声,牛背鹭结伴飞来,又结伴飞走。她又成了长工,埋着头,没日没夜地,自虐似的劳动。那时候,牌楼还有四个人种田,只有她一个人坚持到了最后。她是在牌楼之外见过世面的人,不吵,不闹,只是据理力争,争到后来,大家都不高兴了,牌楼哪有你说话的份哦?同意你回来,已经算不错的了,怎么还能这样不知深浅呢……她哑口无言,转身去找种粮大户。
种粮大户姓仇,五十岁左右,黑白相间的运动鞋,牛仔裤,蓝格子衬衫。她在心里笑了,这一看就不是种田的人,种田的人,怎么可能穿运动鞋、牛仔裤呢?
仇老板,我没地了,也没事做,你可缺人手啊?
仇老板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紧了紧裤腰带,说,缺是缺,我开不起工资啊……
我不要工资,我只要自己种的小麦、棉花、稻子。
仇老板笑了,你怎么不出去打工啊?种田,挣不到钱的。
她不言语了,转身,失魂落魄一般在田畈里转悠。她不能闲着,也闲不住,一个人在山坳里开荒,栽了几十棵桃树。桃树活了,成了桃林,她又在桃林四周扎起竹篱笆,养鸡。那片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山坳,渐渐成了她的私人农场,她在其间劳作,手里拎着把锄头,腰间别着把砍刀。次第开放的桃花真美啊,红的红,白的白,像一片片云霞挂在枝丫间。
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她不止一次劝自己,采芹啊,丢手吧,出去打工!总不能在牌楼老死啊,好讲也不好听啦……东方既白,又是新的一天。她一如往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全无离开牌楼的打算。
玉大娘愁死了,平白无故找她茬,拿她撒气,变着各种法子撵她,她心知肚明,只顾埋头干活,不搭腔。
母女俩几乎成了仇人。每次说到采芹,玉大娘总要恶狠狠地捶打自己的瘸腿,一面捶一面咒自己:“我真巴不得死啊!早一天死,早一天不烦她的神!”有一次玉大娘梦见老伴了,下雨天,老伴戴着斗笠,挽着裤腿,脚上都是烂泥。奇怪的是,她看不见老伴的脸,破旧的斗笠下面空荡荡的,像一只透明的碗。
2016年,七十六岁的满升大爷在睡梦中走了,孤零零地,身边没有一个人。
2017年,朱家二嫂得了糖尿病,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两个月瘦了三十斤。
2018年,大强不小心跌了一跤,前额磕出一个血窟窿,他从锅洞里掏了一撮柴火灰,摁在额头上止血。大强的四个孩子都在外地,他谁也没告诉,硬扛着没去医院,结果,血是止住了,他说话却不利索了,舌头仿佛短了一截。
2019年,风平浪静,牌楼没有大事发生。
2020年,新冠疫情过后,定旺忽然回来了,黑且瘦,颧骨耸立,峭壁似的,薄薄的嘴唇包不住参差不齐的牙齿。我至少二十年没见过定旺,他常年在外做生意,家里的老屋已经塌掉一半。这次回来,他雇了几个人,在老屋基上重新盖起三层小楼。那是牌楼迄今为止最气派的房子,一水的钢化玻璃,一水的琉璃瓦,高大的门楼前立着两根水桶粗的罗马柱,左边的柱子上盘着一条龙,右边的柱子上雕着一只凤,栩栩如生。谁能想到呢,房子还没盖好定旺就走了,雇了一个远房亲戚负责后面的装修、水电与里里外外的地坪。老人们面面相觑,都不敢相信,新房落成这样的大事,定旺自己怎么能不在场,怎么能不放鞭炮,又怎么能不请大家吃顿饭呢?更令大家吃惊的是,新房落成后的第一个春节,定旺竟然没回来过年,他怎么敢哦!大年三十,新房子黑灯瞎火的,这多犯忌啊,牌楼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个定旺,坏了规矩!
坏规矩的还有采芹,她突然就信了主,置玉大娘的责难、老人们的劝阻于不顾。年轻的一代牌楼人已经被外面的世界改变了,他们更加自我,有着与老一辈牌楼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经不存在了,农耕文明的退场和乡村伦理的瓦解,或许是乡村振兴最大的瓶颈。
那天进山途中,意外遇到礼拜归来的采芹,我脱口而出:“做礼拜啊?”她含糊地应了一声。“没多少人做礼拜吧?”她停了下来,清澈如水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牌楼就我,桃园、杏庄那边多些,统共也不超过二十个。有些人,做做也就不来了,家里人拦着……”
“地方远了,来回都不方便。”
话音刚落,她便步履匆匆地走了,圆润的脸上闪过昙花一现的笑容。我茫然地僵在原地,这个比我小十个月、和我结伴上过四年小学的女人当真要在牌楼终老吗?如果她离开牌楼,又将在何处安放余生呢?
山峦肃穆。淡蓝色的烟岚在山坳间浮游,树冠上的日光瀑布一样迸射,仿佛不是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