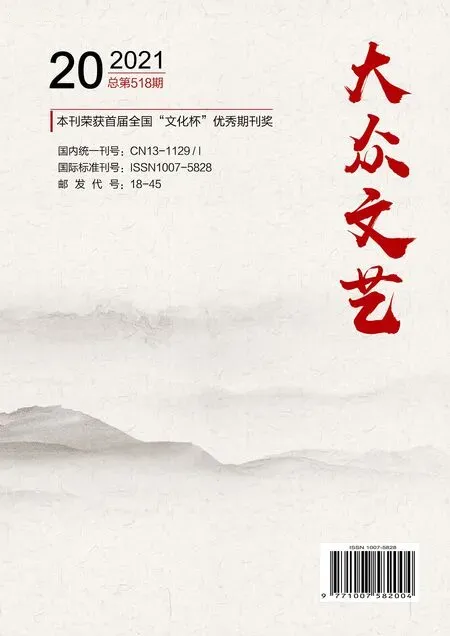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台北人》中的人物悲剧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解析
2021-11-12曹睿洁
曹睿洁
(西北大学,陕西西安 710127)
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十四篇小说的写作背景集中在国民党政权转移至台湾后的十几年里,一边是急需继续的现实生活,而另一边是仍跳动在过去的心。人们心中的零落之感不仅是家国兴衰、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外在物质条件的巨大滑落,更是内心伤痛的形成或激发,而这终将众多流落者引入悲剧的命运走向。精神分析学代表学者弗洛伊德、荣格认为心理对于行为具有巨大作用,个人的人生遭遇固然建立在宏大时代背景之下,但个人命运也是自身细碎选择最后引向的结果,因此内部原因不应被忽略。本文尝试以精神分析的视角对《台北人》中的人物悲剧进行文学赏析,探究众多男女陷进不可抗苦楚境地的缘由,寻求也许存在的可能路径以逃离这宿命般的寂凉深境。
一、情结——个人难逃悲剧的核心
《台北人》中众多零落男女处于历史变化的背景下,要在各自的变故中再次生活。但这样的他和她,在被漫长时间淘洗之后,与人相交似乎仍会任由自己不受控制地滑入同样的悲哀境地;抑或是缠绵追随一事,寻而不得却愈复苦求,导致性灵的窒息、生命被戕害。这种心灵悲剧引发的痛苦结局是个人无意识层面的情结发挥消极影响的结果。这如同着魔般地痛苦复刻,缘于初次创伤分裂出的情结被刺激回归,席卷了整个自我。过往岁月里的起伏消逝但凝成情结,存留在他们无意识中,像是一套行为模式,总是不时跳出来,让人再次遭遇。
虽然情结是正常的心理现象,但“情结是心理不安的真正焦点。”恐惧中别无选择的人们将心理能量全部灌注其中,陷入一次次的荒芜。“情结是内心经验的对象,人们的幸福和悲伤都依赖于它。”因此尝试回溯整个情结形成到发生影响的过程,能更深入地理解人物悲剧遭际的个体内在原因。
(一)情结的形成是个人漫长悲剧的伏笔
在《台北人》的诸多故事中,对主人公来说情结多起源于一次悲剧遭遇。在各种悲惨状况中,人物发生“明显不能完整地保持自己本性”的冲突。外在残酷事实与内心取向的剧烈碰撞,让人发觉到自己内在本质的不能得以保持,为此引发的强烈情感激荡留下重大情结。而情结“是想象的群集,是自主性的结果”,是极具偏见和个体性的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其形成及情感色彩需结合不同主体的特殊经历来进行观照。
“以情感为基础的情结,这是特定的心理情境的意象”。它是一种细小的心理片段,是由于某些严重创伤、冲击裂析出的具有较高独立性的心理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类比为一个较小的二级头脑”,不为意识所知地进行相反于意识的运行。
零落的男女虽都处在悲凉况味之中,但各自占有自己的命运,也就造就着不同的情结,经由曲折殊途被收进悲剧的故事群像里。
有失落于爱造成情结,被爱辜负的男女。爱而不得的波折里,他们追求爱而完整的自我存在受到了冲击,就此郁结了不同情结,让他们失去对爱的信心可仍旧燃着对爱的渴望,而灵肉的分裂冲突而来的种种悲剧也就就此埋下了伏笔。
即使是泼辣圆滑游走夜巴黎舞厅头牌金大班,曾经也做过一次有傻念头的年轻女郎,心想替官家的学生爱人生个孩子,守着他哪怕讨饭也就度过一辈子。只是月如被自己的大官父亲带走之后,她才明白她与自己的爱人今生今世也难再见了。这爱的撕裂带来的痛苦和无奈,分离了情结,让她从此对于这种不顾一切的爱与奉献充满了恐惧和反感。
而《一把青》中,朱青在少女时期于南京与年轻飞行员郭轸恋爱。可完婚不久,国共内战爆发,郭轸随部队被调离南京执行任务。作为新婚妻子的朱青等来的是空难的噩耗。从学生时代遇到郭轸完婚到爱人飞机失事不过短短几年,这由喜入哀倏忽间的转换,让她的心在颠沛中也失去了真正幸福的可能,只能怀念,留下情结的空洞。
《花桥荣记》中,卢先生在世间最挂念的人是桂林家乡青梅竹马的罗家小妹,最真切的希望是和她结成美满的家庭。即使分隔两岸,他还依靠着这个美好期盼继续做着小学老师而生活。可是当他发觉被表哥欺骗,表哥并没有联络上小妹,丢失了积蓄,更丧失了精神支柱的他彻底颓丧。这个爱的情结空洞将长久存在,他无意再去开展美满的生活,只是为现实欲望随意和洗衣服阿春结婚了。
有被时代淘洗而落魄受伤成情结的贵妇人。《秋思》里华夫人已然失势,只是还维持着表面的虚荣浮华,流连于各位太太的舞会。而对她来说真正跌落幻灭的瞬间是丈夫病重离去的时刻,那时她的平静心情被分裂成了细小的情结片段。那几天她守在病榻旁看医生用橡皮管如何抽走他喉头癌变处的脓水,而床头几案胆瓶里的菊花也已经散发出腐烂的腥臭了。现在身在另一个地域,又再一次嗅到冷风中白菊的腥味,在她的心里,生活早已在那个白菊腐烂的秋天停滞。
有求功名不得,志向失落成情结的下层知识分子。《冬夜》中,生活在台北潮湿小巷里的余嵚磊已然不是曾经在北大励志社和同学一起参加五四学潮的壮志青年了,豪气颓败。没能成为有出息的学者,他只是一直守住讲台上当着老师,而志趣相投从青春走来的妻子也因病先离开了。他接受了受现在太太照顾和管制的生活,继续不咸不淡地做着教学的事,但心里一直有出国学习工作的渴望,那意味着另一种自我的模样。
其中爱情的失落是最为典型的。恋爱中的心理状态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强迫性情结。因为这种特殊形式的性欲情结是最普遍的、广为人知的强迫性情结的形式。故事中主要角色大多始于爱的破灭而造成的情结,由此埋下了悲剧性命运的伏笔。
(二)情结的强大力量呼唤悲剧的重演
情结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它始终维持在一个“情结—易感”的状态,最典型的即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情结通过人们的联想和想象,保存着自己,随时预备再次袭来。而当人们再次遭遇或是回忆起曾经形成情结的强烈情感产生的场合,很可能会陷入被控制的恐惧。被刺激重新跳动起来的情结会将个体置于一种强迫的状态,从思想蔓延出去造成强迫的行为,干扰自我的理性发展。因为心理能量已经尽数倾注在情结上,这造成其他心理活动的停摆。
因此故事中的主人公在现在的时空中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境很可能会重蹈覆辙。也许会有一种对曾经情感冲击留下失落的补偿,或就此预估到即将发生的等待事实的到来。由于缺乏理性支撑,被无意识的情结支配,采取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就可能导致悲剧的再次发生。
《那一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王雄原在湖南乡下种田,抗日时被抓壮丁入伍,从此远离家乡,与母亲和定亲的童养媳小妹仔分离。退伍后在叙述者舅妈家当家丁。而他之所以来到丽儿家工作,是因为此时在他眼中年幼可人丽儿的形象与那个家乡的十岁的小妹仔的影子合二为一了。他那对于丽儿的痴恋正是为了捕捉过去,离别的巨大失落分裂出的心理片段企图在此处得到补偿。被迫与小爱人分隔的痛苦形成的情结空洞又再一次通过他的联想复苏,控制了他的行为状态,于是他呈现出抛却成年人尊严极力讨好小女孩丽儿的状态:给她当马骑、为她种杜鹃花、装饰三轮车接送她上下学等等。而上中学后的丽儿脱离曾经小妹仔的形象,也逐渐疏离王雄最终舍弃了他。此时的王雄不仅失去了继续补偿情结的空洞的可能,更是遭受了另一次背叛的冲击。他感到幻灭,就此坠入沉默和暴戾的深渊,对喜妹的肉体施暴后,投海自杀。
而《一把青》中朱青在来台湾后,又不可抑制地喜欢上了年轻的空军学员小顾,好像是要满足爱的情结。当小顾也遇到空难去世时,她不再像是曾经那般倾轧灵魂的哀怮,而是笑着吃着,打着麻将。麻木不仁地、平静地接受或者是等待着和过去一样的悲剧收尾。
情结的易感性和强大力量还体现在即使是间接牵动、影射到个人深处情结的无心之言、他人之事,也会立即触发愤怒和痛楚。金大班即是如此。当发觉悉心培养的爱徒舞场新秀朱凤,被香港来的学生客引诱怀孕后,她立刻暴怒命令朱凤打掉孩子。她想起了自己曾经痴情的梦,企图孕育孩子成立家庭的梦。最后扔下戒指嘱咐朱凤换钱去生下孩子,责令她不要再想回到这个行当赚钱。
而情结为了使自己无意识的巨大威力得到彰显,甚至会出现行为置换以满足情结的需要。对很多人来说,由于性欲情结受到社会道德等的限制,不能被自然地用行动表现出来,情结就选择其他的复杂方式在伪装中展现自己。“对男人来说,如果不能直接把性兴趣付诸行动,性兴趣常常转换成一个狂热的职业活动或对危险运动的激情等,或转换成有学问的爱好,如一个收集癖好。”《冬夜》中余嵚磊似乎就是如此。由于琴瑟相和妻子雅馨的病逝,他爱的欲望落空。而在困窘现实之中,他放下尊严恳求老友吴柱国想要获得的出国机会,甚至是想将儿子也送出国读书的不合时宜的执念,只是一种行为置换,本质是他希望复还到青春岁月,那个时刻他壮志满怀,充满生命的活力,而性与爱合一的对象也在身边。有时行为置换长期进行,逐渐变得稳固,甚至在表面上毫无破绽地替换了原本的性格。朱青即是一改曾经羞涩清纯的女学生形象,成了在台上演唱流行歌曲的空军康乐队的时髦浪荡女郎。她沉浸于追捧中纵情歌唱的演艺生命也许只是不可能再被满足的爱欲执念的行为置换。她用这个来代替自己对再也不得相见相亲的爱人的思恋。而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文中一直从未提道小顾和朱青更深入的交往和为何她并不太为小顾之死而伤怀,因为也许她失落爱欲情结的弥合并不完全依赖于小顾的存在,而是转换到了不同方面。
(三)稳固的自我抵抗情结引发的悲剧
从某种程度上说,情结是造成心理不安的关键缘由。情结的开始作用,是自我自由的停滞,它取而代之成为心理动力指挥行动实施。强烈的情结带来恐怖的感受,经常扰乱和扭曲思想和行为。此种力量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得到阐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情结一定是负面性的,而人也不是屈服于强烈情结的提线木偶。
“情结是内心经验的对象,个人生活的幸福和悲伤都依赖于它们。”它们就是个人人生经历在心理上留下的印迹。情结实质上是一种心理的表征,而并不是病症,作为一种正常现象,构建着无意识的世界。而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的自我实际即是由身体感应到从而聚集并就此稳固于此的一系列联动想象的情结。
“对情结的恐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是对任何令人不舒服的东西都有一种迷信式的恐惧,而我们自大的启蒙还没有触及这种恐惧。只要对情结进行研究,这种恐惧都会引发强烈的反抗,要克服它,需要有极强的意志力。”而如何理解并缓解情结导向的可怖的一面则需要稳固的自我作为基础:“情感基调是伴有躯体神经支配的一种情感状态,自我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所有身体感觉组合物的心理表达,因此,我们的人格是最坚固的和最强的情结,而且(若健康允许)人格可以度过所有的心理风暴。”
而《台北人》故事中实际存在类似人格稳定的角色,为逃离情结困境提供了可能的例证。她们平静面对已有的悲剧现状,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出自理性地接受,由此也就抵挡了情结激发所带来的心理风暴,没有最终落入悲剧的圈套,继续着归于平和的生活。这些人物多为作为中间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与主人公形成对比。《一把青》中朱青的师娘,同样是空军太太,死了丈夫,同样从南京迁往台北。相比于朱青前后判若两人,又遇惨剧,她始终是那个善良温暖、有人情味的平凡女人,即使岁月已经为她黑发洒上了霜。她早知道和丈夫这样空军结婚将要承担的分别的风险,“并学会以打麻将、织毛衣等方式来自卫”。她清晰地对自己有着定位,规划着生活轨迹,并且一步步坚强着自我,丈夫病故后她很快就理性地忙碌于台湾的新生活。她有着稳定的个体人格,“所以能够不受大伤地接受命运的打击”。“花桥荣记”的老板,行伍出身的丈夫在战役中丧生,她被作为眷属撤离到台湾。为了维持生计,她开始在台北开起了桂林家乡菜馆,一开就是十来年。虽然通过她最后搜刮卢先生遗物的行为可以发现她已然是一个市井的庸俗女人了,但不能忽略支撑坚持她过好自己生活的稳定内在自我。
由此可见强健的自我,稳固平和的感情基调是面对情结袭击的防御系统。坚定的人格足以让我们能发挥出理性的自主,而不再是被情结裹挟再次复现往日的打击。
二、原型与集体悲剧
《台北人》中人物悲剧具有普遍性,每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悲剧,每个角色都有着悲惨遭遇。故事中人物的普遍性的悲剧旋律从内在原因上看实际上是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注入行为而导致的。无意识的表层是各异的,即构成心理生活的个人面向的个体无意识,主要内容是具有不同情感色彩的情结。但是“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个层次”,代际传递的,非私人独有的共同的心理基础——集体无意识,其所指向的行事方式普遍地存在于不同时空的所有人身上,而它的内容则是原型。
荣格认为个体的心理状态是处于演进的动态中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力量不止息地竞争。一方面,两者在冲突对峙中,意识总是将不符合现实要求的心意向无意识领域压抑。另一方面,心理总倾向于调和意识和无意识的矛盾,存在将无意识的部分纳入意识的融合过程,而这被荣格称为“与原型相识”。
与原型相识的过程,将集体无意识个体化的过程,也是人深入对自己认识的心灵成长过程。个体化的不同阶段中,人都与不同类型的原型相遇,将其投射于外在的人或物,将它们纳入精神。但之后,如果落入了泥沼,与原型遭遇,但未将自己与它有效分界,人就会成为这种古老形式的附庸,将自己等同于原型,与它的形式保持一致,失去了理性意志控制自身行为的自由人性,而此时人物悲剧也就发生了。
而随着情节发展的过程,《台北人》故事中的主人公都经历着与原型相识的过程,也正是原型个体化的失败导致了他们被集体无意识控制,心理和行为都倒向悲苦的处境,摆脱不了其强大力量让生命成了它的木偶。
原型个体化的“第一阶段——来自社会生活的考验、文明的考验,在这个阶段会与人格原型(面具)相遇。”在消极结果中,主体会被动接受自己的社会身份,机械地、无力地屈从于围绕他/她的社会给予的规章和限制,将自己的个人等同于自己的外在社会功能,而不是认为人格角色只是自己发展过程中的必由状态。而那些《台北人》中一味慨叹、沉溺于光辉回忆的军官将领角色便是因此陷入悲寂的人生后半。在时运急剧变化之际,丢失了往日社会地位的他们急于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将现阶段的自己承担的社会功能和责任当成了全部的自我,而不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失去了继续创造发挥能力的可能,就此屈服于一个低微的位置,只剩下感怀去往岁月地度日。
个人心灵内部的冲突带来下一个阶段:对自我认知的考验,即和影子原型的相遇。阴影原型象征着精神中被压抑替代的部分,这些内容由于道德约规约、文化禁忌和其他原因被压抑到无意识的层面中,它并不意味着邪恶,只是不合。此时的负面状态下,人会被这一存在的与自己有关的阴暗面所震慑,以为这是个体心理的全部,自己的存在得到了整体的否定,恐惧袭来和痛苦的道德限制一道压制这个形式的个体化。《台北人》故事中很多角色都有昏暗过往,低矮现实让人向善的面向成了阴影。蓝田玉渴望爱情,而她孤寂的姨太太身份限制了她得到爱情的可能,她对于郑参谋的感情在道德上有了不合理性,美好的爱情愿望成了不伦阴暗之物。而表现出阴影原型的角色则为抢走郑参谋的钱夫人妹妹。感受到钱夫人妹妹的压力冲突的时刻,她醉酒哑了嗓,甚至在多年的台北聚会上仍旧感觉到阴影的力量,又在想象中经历了一次被夺爱又失声的遭遇。
“第三阶段——与阿尼玛或阿尼姆斯相识”,人间男女都会爱人和被爱,在一生中无数次落入爱情的尘网。阿尼玛原型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因素,影响男性对于女性的想象。而阿尼姆斯则是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因素,影响着女性心中的男性形象。面对爱情的进展,人们在昏沉状态下,服从于原型,依照幻想进行爱情抉择,被无意识拖拽建立爱情关系而不知。《台北人》中很多执念导致的爱情悲剧都是如此,金大班在最后一夜搂住的稚气男学生,卢先生眷恋的当年的清清白白青梅少女,朱青反复追逐的年轻飞行员……这些苦恋的迷途都是个体化失败后爱的原型在作祟。
原型的个体化未完成,或者说“与原型相识”的失败,意味着完整的自觉的自我并未形成,总是受到原型摆布,陷入悲剧,甚至一次又一次反复。而这也就是《台北人》中人物悲剧的普遍性内因。作者描绘多个角色迥异却又基调相似的人生体验,他将带有戏剧性却几近真实存在的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试图唤醒读者思考自己如何抵抗近乎残忍的命运的方法。而如果从上文基于原型理论的分析来看,脱离这种困境需要直面原型的存在,并且企图尽可能地推进原型个体化的完成,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对自己的导引,觉察到自己行为模式中诡异而强大的非理性力量,而这即是曾经在无意识领域实施控制的原型,而意识到的时刻已经意味着这个原型已经被纳入意识层面,实现了个体化。
白先勇在《台北人》中书写了将要从记忆中和现实中消逝而一去不复返的人物、故事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此一部有相当真实性心灵史中的悲剧牵动着读者的怜悯和恐惧之情。对其人物悲剧发生的内在原因进行讨论,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到在历史苍凉背景下个人的苦痛体验和作者的写作用意,在理解中让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以上通过尝试分析《台北人》人物悲剧的内在成因,发现无意识因素对人物悲剧走向的巨大影响。如果人们在阅读体会《台北人》宿命般悲剧的过程中能向内反思,思考悲剧发生的内在原因,从而自觉地挣脱无意识的负面牵扯,避免历史中的个人悲剧落在现实的个体上重演,而这也许即这部作品文学叙述的另一种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