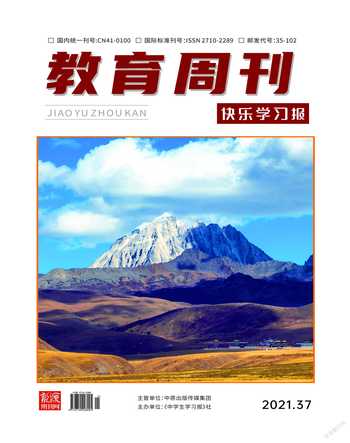细嚼文本明情达意
2021-10-20赵芬
赵芬
《项脊轩志》作为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代表作,可挖掘解读的东西很多。今天笔者想借助文本、作者生平,细嚼品鉴,一窥作者“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中的人生悲喜。
一、可喜
文章一开始,作者就交代了“项脊轩”的全貌——“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日过午已昏”。总之,这是一间又旧又破的老阁子。然而,在归有光的修葺下,旧阁子焕然一新——“室始洞然”、“书满架”、“桂影斑驳”。也是在这小天地里,作者畅游书海和自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所以,作者说“余居于此,多可喜”。
再看作者补记写与妻子魏氏的一段。妻子来归,问的是古事,学的是写字,而对于自幼好读书的归有光来说,得妻如此,夫复何求?而等到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闻姊家有阁子,且何为阁子也。”想一想,小妹妹怎么会问阁子的事情?无疑是姐姐经常在小妹面前提起。那么光提阁子?想必阁子中的人,以及阁子中的一些生活情趣也是不能不提的。寥寥几笔,虽未提及夫妻间其他的相处之事,但是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夫妻二人情投意合,相敬如宾。
细嚼文本,我们想象得到一千多前,在项脊轩里,归有光也曾有过一段明亮盎然的时光,那是关于年少的怡然自得,是关于夫妻恩爱两相知。
二、可悲
生活本有悲欢离合,正如文本所写:“然余居于此,亦多可悲。”而这份“可悲”,在笔者看来,包括三个个方面:一家道中落;二亲人离世;三有负所望。
(一)家道中落
原先归家的庭院是“通南北为一”,而如今是“往往而是”的门墙,又“东犬西吠”、“鸡栖于厅”,可见家中凌乱不堪,每况愈下。而作者在《归氏世谱后》中,写到祖父高祖归度训诫子孙:
吾家自高曾以来,累世未尝分异。传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遗言,切切不能忘也。为吾子孙,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为不孝,不可以列于归氏。
归有光祖先留下遗训,提出分家者不准列入其家谱。然而现实却是叔伯分家愈演愈烈——“庭中始为篱,已为墙”。面对此情此景,归有光怎不痛心疾首,怎不感慨万千?所以即便写下这段文字的归有光才十八岁,即便这段文中没有表达悲痛伤感的明确字眼,但其中暗含的对家世衰败离析的痛心又岂能被忽视?
(二)亲人离世
人生有三大悲事“早年失怙,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仅仅是而立之年的归有光却已承受了两大不幸,何其悲哉!而作者也将这种人生的致痛“每以一二细事见之”。
作者八岁时,母亲去世,因此作者对母亲的回忆并不多,文中只引用了老妪的两句话:一句写母亲生前常常站在某地——“某所,而母立于兹”;一句写母亲隔门询问老妇“儿寒乎?欲食乎?”。两句话存在一定的跳跃性,却能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当年,母亲站在这里沉思什么?母亲询问时的声音是焦急还是轻柔……十年之后的归有光,就在扣扉问食,嘘寒问暖这个细节中,完成对记忆当中那个温婉慈爱的母亲的追忆。
如果说母亲的早逝让年少的归有光少有母爱的滋润,那么,祖母的疼爱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一种弥补。“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这是祖母对孙儿的调侃。接着,年事已高的祖母,将象征家族荣耀的象笏捧来给他,“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在家世衰败离析之际,在久失母爱的少年时期,祖母的期望与肯定,对于此时的归有光来说,是如此珍贵。所以,“瞻顾遗迹”,“令人长号不自禁”。这是怎样一种伤痛,才会让“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归有光嚎啕大哭。
再看补写与妻子魏氏的一段。年少时,归有光是有兴致的“稍为修葺”,而到“吾妻死,室坏不修”“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我们可以猜测这难道不是作者害怕睹物思人而选择逃离?而文章最后“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更有一种物是人非、沧海难为水的无奈与伤痛。
周国平曾写:世界还在,我还在,而你已不在。对于归有光来说,何尝不是这样——母亲以手轻叩的门扉仍在,而母亲已不在;祖母所赠的象笏还在,而祖母已不在;妻子亲手种植的枇杷树还在,而妻子已不在……人生的悲歌,不过如此!
(三)有负所望
查阅归有关的生平,可知他从小聪慧,九岁能成文,十岁时写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对于这种自小聪慧的孩子,于自身而言,是他日当扬名立万,留名青史的自信;于家人而言,是沿袭门风、光耀门楣的骄傲。然而他的才智并沒有让他“春风得意马蹄疾”,相反地,那种功名未就、有负所望的痛楚成为他毕生的煎熬。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十八岁时,归有光以蜀清、孔明当年“昧昧于一隅”比拟自己“区区处败屋中”,然又“扬眉瞬目”,可见少年归有光的自信与抱负。同时,在写完《项脊轩志》正文后第二年,他考中秀才、补苏州府学生员。但造化弄人,之后五次乡试不中,直到第六次才考中举人,此时归有光已经三十五岁。十数年间,家族衰败离析,亲人相继离去,自己屡试不第。于是,曾经“扬眉瞬目”的自信少年不再“余泣”、不再“长号”。魏氏离世后,他写“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我想,这份情感不外泄的沉默貌似悄无波澜,实则暗涌积蓄。所谓悲伤至极,大抵如此。
钱穆先生曾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以载道”观念做过一个颇富启发意义的阐述——在文学里表现出人生。细品归有关的《项脊轩志》,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篇简短而平淡的散文里,暗含了作者追忆时光、感念亲人、有负所望的人生悲喜,可谓是做到了“文以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