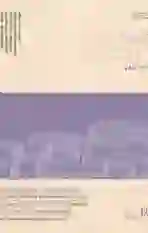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角下《瓦尔登湖》汉译研究
2021-10-14赵瑞芳
摘 要:散文是一种最具审美价值的文学体裁,传递原作品的美感和意义是散文翻译的重要任务。散文翻译研究和接受美学有着密切联系,将接受美学中的重要概念和理论引入散文翻译研究,即将散文翻译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读者和意义阐释方向上来,可以为英语散文汉译研究提供新思路。本文从接受美学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瓦尔登湖》第十二章“禽兽为邻”夏济安先生译本,发现夏济安译本在填补文本视域和读者期待视域视的域差、通过意义阐释发挥译者再创造两方面达到视域融合,阐释出梭罗《瓦尔登湖》丰富的语言和文化意义,再现其深远的意境和回归自然的主题,展现出汉语的美感。
关键词:散文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瓦尔登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3-0055-03
作为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的文学体裁,散文意境深远,形散神聚,需要展开充分的联想以达到美学境界。作者在行文中流露出了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通过意境烘托,使读者对散文产生共鸣。在散文翻译中,传递散文美感是散文翻译工作的核心。刘荣跃曾说自己“最大的毛病是忽略了散文翻译的特殊要求——文采”[1]。此处的文采指通过优美语言展现出来的让目的语读者赏心悦目的写作风格,即翻译出的散文要考虑目的语散文的写作特色以及目的语读者对散文的审美。
梭罗是世界散文创作的名家,散文《瓦尔登湖》是梭罗融入大自然、过简单纯朴生活的名篇,向读者展示出了一幅优美纯净的山水图画,极具审美价值。《瓦尔登湖》描述的一切对象,倾注着棱罗全部情感。本研究赏析的翻译片段来自梭罗《瓦尔登湖》第十二章“禽兽为邻”,所选汉译片段为夏济安先生译本。本研究从接受美学视角出发,分析夏济安先生所译《瓦尔登湖》第十二章“与兽为邻”片段,分析译本体现的视域融合,为今后散文翻译研究提供新思路。
一、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散文翻译
在翻译研究中,接受美学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接受美学是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理论,核心是将读者放到文学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是再创造的过程。在阅读过程中,作者通过文本与读者对话,使文本的潜在意义在读者的建构中表现出来,因而“接受美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理解和阐释问题”[2]。在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中,读者具有定向思维模式、历史视域以及个人视域(包括心理、个性、知识水平,人生体验,美学素养等),对于文本有自己的主观理解。然而,读者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完全主观,接受活动必须在文本领域内进行,实现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流。加达默尔认为,读者从特定角度观察接受事物,得到的一切结论都是“视域”。读者的审美能力和接受能力是读者的“期待视域”,期待视域是不断变化的。散文读者走入文学作者的内心,揣摩感情,理解作品的“文本视域”。在理解文学著作过程中,两种视域同时超越当前视域走向更高境界,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在差异基础上产生。
散文译本中,视域融合是散文美感再现的重要一环。翻译从本质上说首先是一种阅读,是具有一定文化艺术素质、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的读者的解读[3]。在接受美学指导下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亦是译作的作者。译者对于原著的接受可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在阅读中,根据经验理解原文,使原文具体化;第二个过程是在翻译中对原文的再创造。文学翻译的精髓在于通过意义阐释达到美学再创造的目的,这和译者在接受过程中的阐释活动不谋而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经历两次视域融合:一次是在理解原文過程中,作为读者的“期待视域”和原文“文本视域”产生的视域融合;第二次是在前一次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和读者的“期待视域”进行融合,产生新视域。经过这两次视域融合,译者填补解释了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探索原文本的意义,在欣赏原作的同时展示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经过这个过程,原文作者传递的意义不再是文本的全部意义,而是期待视域、文本视域交流和融合后产生的新意义。
二、《瓦尔登湖》 汉译片段的视域融合
散文翻译的最终目标是使读者理解并接受文本,感受原文独特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要达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实现视域融合。即不管是在对原文不确定信息的理解阶段还是译文再现填补空白的阶段,译者都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4]。根据前述,实现视域融合需要译者充分理解原文并使原文具体化,即填补文本视域与期待视域的“视域差”;通过对原文意义阐释进行再创造。读者所看到的目标文本是译者再创造后的产物,译者根据两种语言之间差异所用的翻译技巧和方式都会影响视域融合。下面将从填补“视域差”和译者再创造分析夏济安《瓦尔登湖》“与兽为邻”汉译片段中体现的视域融合。
(一)填补“视域差”
在接受美学看来,原文的意义不全面,中间隐藏着许多空白(blankness),期待读者运用想象力阐释。译者在其中就要发挥能动性,填补读者和原文的视域差。如此,读者的期待视域才能与原文的文本视域逐渐融合。
例1:Sometimes I had a companion in my fishing, who came through the village to my hous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town, and the catching of the dinner was as much a social exercise as the eating of it.
【夏济安译】有时,我钓鱼有人作伴,此人从城的那一头,穿过了村子到我的家里来。两人共同进餐固然是社交,而两人一起垂钓,捕了鱼来佐餐,未尝不是一种社交活动[5]。
例2:I have water from the spring, and a loaf of brown bread on the shelf.
【夏济安译】我汲泉而饮,架上一块棕色面包供我果腹[5]。
例3:His white breast, the stillness of the air, and the smoothness of the water were all against him.
【夏济安译】它那雪白的胸毛,静寂的空气,平静的湖水,把它无所遁形地映显出来——这一切本来都对它不利的[5]。
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由于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客观上是不可能消除的,文本视域与译者视域之间会存在“视域差”。如例1中“and the catching of the dinner was as much a social exercise as the eating of it.”,“the catching of the dinner”指什么,“the eating of it”又指什么?如果尝试译作“我们一同捕鱼好比请客吃饭,同样是一种社交活动”,没有将这种视域差表达出来。反观夏济安先生的译文“两人共同进餐固然是社交,而两人一起垂钓,捕了鱼来佐餐,未尝不是一件社交活动”,把何为“catching of the dinner”“the eating of it”讲明白,译者通过对原句在上下文的考察,理顺原句的逻辑关系,“捕了鱼来佐餐”和“两人共同进餐”都是社交活动,填补了原文与作者之间的视域差,达到视域融合。例2“I have water from the spring, and a loaf of brown bread on the shelf”,可译作“我从泉水中汲水,架上有块棕色面包”,“架上有块棕色面包”与“我从泉水中汲水”有什么关系?夏先生译作“我汲泉而饮,架上一块棕色面包供我果腹”,在脱离世俗的田园生活中,食与饮缺一不可。译文深刻理解原文传递的意义和情境,达到与原文的视域融合。例3中“His white breast, the stillness of the air, and the smoothness of the water were all against him”的介词“against”是理解难点,如果译者没有将视域差填补出来,读者则会费解。这里夏先生将其译作“它雪白的胸毛,静寂的空气,平静的湖水,把它无所遁形地映显出来——这一切本来都是对它不利的”,这样就把“against”的深层意思表达出来:为何湖水、空气、胸毛对它不利?因为这些都把潜水鸟“无所遁形地映显出来”。
(二)译者再创造
在翻译中,视域的融合也体现在译者对原文语言的创造性阐释上。翻译的过程也是一种意义阐释的过程[6]。文本是存在各种潜在元素的框架或结构,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实现具体化。加达默尔认为人类的理解是广泛的、历史的、具有创造性的。其作用在于能激发读者的想象,赋予其权利寻找文本意义,弥补意义空白[7]。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空白应尽可能被填满。
例4:It was surprising how quickly he made up his mind and put his resolve into execution.
【夏济安译】它运筹决策,费时极短,而予以实施,又绝不三心二意[5]。
例5:I found that it was as well for me to rest on my oars and wait his reappearing as to endeavor to calculate where he would rise.
【夏濟安译】我觉得与其估计它下次出现的地点,不如停下桨来,等它自行放水[5]。
例4“It was surprising how quickly he made up his mind and put his resolve into execution”,夏先生译成“它运筹决策,费时极短,而予以实施,又绝不三心二意”,巧妙地将“put his resolve on execution”译成“予以实施,又绝不三心二意”,将潜水鸟那种似人的“坚定决断”表现出来,与原文在视域上达到恰如其分的融合,连用“予以实施”和“三心二意”两个四字结构,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例5中,I found that it was as well for me to rest on my oars and wait his reappearing as to endeavor to calculate where he would rise,仅依靠原文字面意思,难以推测出蕴含的深层含义。“as well…as”本是“和…一样,不但…而且…”,译者根据当时的语境判断和选择达到最贴近文本的意义。夏先生译作“我觉得与其估计它下次出现的地点,不如停下桨来,等它自行放水”,夏先生将其处理成“与其…不如…”的逻辑关系,把原文作者在潜水鸟的“戏弄”下怎么也寻不到它的踪迹后,想出的应对之策表达出来了,原文意义由译者创造性进行阐释。
三、结语
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思维方式的文学理论,接受美学提倡多元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即不仅包括作者,还包括读者在内对于文本解释的权利。
接受美学指导下的文学翻译中,原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基于译者和读者对于文本的阐释。具有双重身份的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也是译作的作者。译者在经历过两次视域融合后,通过填补视域差和文本的空白,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处理,使之达到新的美学境界。这种文本与读者的对话产生新的意义张力,为以后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另一方面,如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成为助力中华文化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思想。汉语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将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不仅需要优秀的汉语译者能够体会原文的内涵,更需要译者将接受美学中的主张应用到翻译过程中,凸显汉语的魅力和美感。从这一角度看,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汉译研究颇具现实意义。
《瓦尔登湖》是梭罗远离尘嚣,在自然的安谧中寻找一种本真的生存状态,寻求一种更诗意生活的散文集。作品内容丰厚,语言生动,意境深邃。
本文通过对梭罗《瓦尔登湖》夏济安译本进行研究,发现译者夏济安的译文通过填补“视域差”,对原文出神入化的再创造后,原文的艺术特点更加鲜活,读者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散文作品。夏先生深刻把握中英文语言差异,运用恰当中文句式和结构,还原原文句式美感,进一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读者也能体会到汉语的美感,进一步扩大了汉语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刘荣跃. 见闻札记:美国文学之父眼中的19世纪欧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 朱健平. 翻译研究·诠釋学和接受美学·翻译研究的诠释学派[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8(02):78-92.
[3] 杨松芳.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148-150.
[4] 尹鸿涛,曹微微. 接受美学视阈下的《墨子》英译研究[J]. 上海翻译,2021(02):56-60.
[5] 夏济安. 美国名家散文选读[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6] 赵勇. “深度翻译”与意义阐释:以梭罗《瓦尔登湖》的典故翻译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02):77-81.
[7] 宋海栗,杨东英.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以《柳林风声》两个汉译本为例[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2019(03):118-122.
(荐稿人:孙晓青,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基金项目: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中国故事的时空传播研究”(项目编号:HGKY2019036)。
作者简介:赵瑞芳(1992—),女,硕士,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跨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