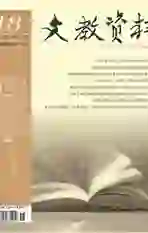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思想
2021-09-23罗雅文
罗雅文
摘 要: 海德格尔跳出“主客体二分”的陷阱,用存在主义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原伦理学依据。生态伦理思想包括生态存在论、异化统治论和诗意栖居论,对后期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海德格尔 生态伦理 存在主义 存在 存在者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人类对自然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令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大自然向人类发出了警示和报复。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道德关怀从社会领域延伸到自然领域,试图赋予“保护生态”的要求道德依据,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出发解释了“存在”与“此在”的关系,从原始伦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存在即自然”,对生态伦理学的建设发展及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生态伦理学讨论的中心话题是人和自然能否构成伦理道德关系,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分裂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置于宇宙中心,认为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如古希腊智者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文艺复兴后的“人作为小宇宙可以反映大宇宙”观点。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人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义务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包括动物权利论、生态女性主义、深生态学等流派,主张“回到丛林时代”,反对一切工业社會的产物,这显然是非理性的并且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
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可以看出,二者都掉入了“主客体二分”的陷阱,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置于彼此的对立面,呈现“非此即彼”的零和状态,前者以牺牲生态环境满足人类发展需要,后者以牺牲社会发展维持生态稳定,不论是哪种观点都不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和理念。海德格尔跳出“主客体二分”的思维盲区,用存在主义刷新了人们看待人与自然的视角,让人重新审视“存在”,回答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包括生态存在论、异化统治论、诗意栖居论等内容。
一、生态存在论
对“存在”的思考贯穿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始终。从哲学论证之初,海德格尔就重提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希望回归“存在”的本义,扭转自柏拉图发端的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错误理解。在他早期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开篇就提道:“我们的时代虽把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当作自己的进步,但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已久被遗忘了……它曾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之思殚力竭。当然,从那以后,它作为实际探索的专门课题,就无人问津了。”[1](3)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把作为世界本源的“存在”假设为某种先验存在,将其表述为“是……”从而用对“存在者”的追问取代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遮蔽了真正的存在,造就了“无根的本体论”,因此必须唤醒对“存在”本身意义的重新领悟[1](2)。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作为最普遍的概念是不能被定义的,“存在”作为最高的概念不可能从更高的概念中导出,也不能简单地由存在者聚合表现。不过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虽不能被定义,但它是一种自明的概念,“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会中”[1](6),“存在”可以被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所意会,“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性”[1](17),这种特殊的“存在者”(此在)既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又能意识到其他存在者的存在,这便是“人”。海德格尔早期分析了“此在”的各种现状,如“共在”“常在”“烦”,并指出这些状况是“此在”被遮蔽后呈现的日常,是“此在”在日常中呈现的非本真状态,会令人逐渐沉沦。要摆脱非本真状态,回到本真世界中可以通过“畏”“死亡”“良知”“决断”。然而通过“此在”逼问“存在”的意义又陷入了传统形而上学突显主体性的圈套,于是海德格尔后期将关注点由“此在”转向了“存在之真理”。
在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中,“自然”和“存在”几乎表达一个意思,这里的“自然”不是指现象界自然之物的总和。海德格尔从希腊文中寻找“自然”的本义,发现“自然”最初指生长,“乃是出现和涌现,是自行开启,它有所出现同时又回到出现过程中,并因此在一向赋予某个在场者以在场的那个东西中自行锁闭”[2](334-335)。这里的“自然”代表时隐时显的运作存在,是支撑存在者存在的依据。“存在即是自然”,然而在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禁锢中的人们总是曲解“自然(存在)”的本义,将“自然(存在)”等同于自然物,把人自身看做存在者的主宰,存在的真理在人们的误解中隐退,人忘记生存之根本和与其他存在物平等的地位。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蕴含朴素的伦理学思想,在探讨作为世界本源的“存在”的呈现方式背后是在探讨人的生存方式,启示人们时刻牢记人作为特殊的存在者,应该成为“存在”的守护者,为“存在”解蔽,与周围的存在者和睦共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否则人将迷失自我,失去生存的根基。
二、异化统治论
海德格尔认为十七世纪是人类信仰剧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开始推翻封建阶级,自然科学发展起来并逐渐应用于生产生活,人的自我意识快速觉醒,人的信仰慢慢由对上帝的崇拜转向对人自身和对技术的崇拜。然而在人类试图征服地球的号角下,在人类欲望无限膨胀的过程中,人不再思考存在之根本问题,存在者被对象化,只有当存在者处于“表象(Vor-stellen)”状态才被当做存在,人的表象活动把世界把握为“图像”(“世界图像”指存在者整体,即人们所理解的“世界观”),“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了”[3](88),存在的真理在技术对人的遮蔽中渐渐隐去。为了拯救被遗忘的“存在”和迷失的人类,海德格尔反思和追问技术。
海德格尔从考察词源出发,认为技术不只是生产的工具,应是为知识提供一种“公开”,是一种让真理显露的“去蔽”之术,但是支配现代技术去蔽是向自然发起挑战。在人支配自然的过程中,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框架”,“框架是属于处置的聚集,处置强迫人,把人推到这个位置,在此,人不得不以勒令的方式,把现实揭示为‘定位—储备”[4](133)。简单来讲,“定位—储备”意味着技术要求所有事物都处在随时随地可供使用的备用状态,一切自然物成为技术的持存物,正是现代技术的危险之处:技术勒令人类处置(stell)自然、支配自然,处置空气生产氮气、处置土地生产矿石、处置矿石生产铀,处置铀生产原子能。海德格尔担忧地表示:“这种能量释放出来,既可以为着毁灭,又可以为着和平。”[4](128)在技术的驱使下,人骄傲地把自己当作地球的主人,将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给生态环境带来破坏,动摇人类生存的物质根基,离揭示真理的道路愈发遥远。
技术带来的危险远不止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危机,还有人本身的异化——人想操控技术反被技术所操控。人在促逼自然者的过程中拥有了世界主宰的角色代入感,殊不知人成为“定位—储备”,成为一种资源(人力资源)被技术调遣和使用。海德格尔举出林务员的例子论证此观点:林务员表面上子继父业每天计算着被砍木头的数目,实质上为生计而受制于制木业,他的价值隶属于植物纤维的可用性。在技术的“框架”中,人们陷入非本真的世界,连同自然物一起沦陷为一种资源,以致人无法听到本源真理的召唤,“今天,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跟他自己亦即不能跟他的本质相遇了”[4](136)。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分析了现代技术的本质及技术带来的种种弊端,并不是否定技术本身,也不是只是单纯地展现人类沉沦而不自觉的不幸和生态被破坏后的灾难场景,而是提醒人们向技术的本质敞开,重新回到自然守护者的位置,因为守护自然就是守护存在的真理,既守护了人生存的物质根基又守护了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保护自然不应是出于某种道德義务,而是一种内生需要——守护自然即守护人类自己。
三、诗意栖居论
现代人面临本质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状态,那么应该以什么方式让人重新把握“存在之真理”,进入真理的澄明之境呢?对于这一问题,海德格尔提出要通过“诗”(或“艺术”)。海德格尔后期借用诗人荷尔德林一首诗歌的内容表达对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憧憬,诗歌的原话是“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栖居”不是指人占用某个住宿地,它的基本特征是保护,“栖居,即带来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保护在其本质之中”[5](1192)。栖居意味着存在者的本质得以保护,是人在大地上赖以存在的方式。“大地”代表存在者被遮蔽的一面,与之相对应的“世界”代表存在者澄明的一面,真理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逐渐显露。人要在大地上真正地栖居,必须通过诗,“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2](468)。
人应该栖居在大地上,那么栖居又怎样实现呢?海德格尔继而对天、地、神、人四方进行解释,他认为世界是天、地、神、人一体的映射游戏,大地承受筑造,滋养果实,蕴藏水流和岩石,庇护植物和动物;天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是周而复始的季节,是昼之光明和隐晦、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日的温寒,是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诸神是神性之暗示着的使者,从对神性隐而不现的运作中,神显现而成其本质;人是终有一死者,因为人有能力承担作为死亡的死亡[5](1178-1179)。这四者是高度统一的,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映射自身和其余三方,进入它在四方纯一性(也称为四重整体)内的本己之中。人通过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护送终有一死者保护四重整体的本质实现栖居。
从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栖居”思想中可以看出对人本质的思考:首先,人不是地球的主人,只是存在者之一,但又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担负着保护存在之真理的天然使命,这一点既否认了人类中心主义征服地球的观点,又否认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将保卫地球视作人的道德义务的观点。其次,人和其他的存在者应该和谐共处。具体到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时,人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应该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物的本质,这里蕴含的自然观与中国古代“天地万物并生”“天人合一”的思想类似。再次,人不应该片面地执着于表象世界,被技术的框架控制和驱使,要通过审慎的思(或诗)净化心灵,追问和反思世界本源,以达到真理的澄明之境,获得根基的持存性,实现诗意的栖居。
四、影响
尽管海德格尔的思想颇具神秘主义色彩,一些语言晦涩难懂,但是他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所说:“他的思激发了关于人应对环境承担责任的思想。”[6](115)
生态存在论是海德格尔生态伦理思想的起点和理论根基,该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原伦理思考建基于他关于“存在”的本体论思考,其存在主义是对世界本源进行的深刻反思和追问,重塑了巴门尼德“最抽象最一般的存在”的思路,引发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根本转变,“诚如哥尼斯堡的康德老人的时钟般的生活背后,潜伏着近代哲学的‘哥白尼式转向”[2](2)。存在主义也融于其他科学和领域,如教育学、建筑学、美学和文学评论、德里达引领的“解构主义”运动等,发挥着哲学指导具体科学与实践的作用。
海德格尔生态伦理思想中的“存在即自然”“技术的本质是框架”“诗意地栖居”“天地神人四方”等思想深刻地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弥补了笛卡尔“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单一视角,从存在主义出发论证了“人与自然一体”,论证了人应当保护自然、保护自然不是出于道德义务而是关照人类自己,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原始的伦理学依据,从根本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启示后人以更包容开放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为解决生态危机、整治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来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思想养分。他在反思现代文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后,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对人类前途发展的思索,这一思想启示人们反思伦理与科技,影响了后面的生态伦理家,如约纳斯将责任原理运用于生物学、医学领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实则是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方式和未来命运走向的本质思考,表现出他守卫地球、守护人类的理想和追求。
参考文献:
[1]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
[2]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马丁·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5]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6]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海德格尔[M].张祥龙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