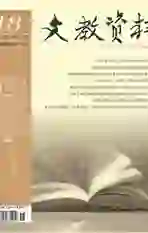彼得·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2021-09-23龚奕佳
龚奕佳
摘 要: 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出版的第一本日记体著作《来自走廊的呐喊》。继而,是他自我批判而再版的《学校生活》。这是一个过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厌倦了后现代左派温和改革主义政治的麦克拉伦,在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实践观的影响下,提出了将阶级斗争和政治带回教育核心、将个人发展与集体相联系的革命性批判教育学。
关键词: 麦克拉伦 批判教育学 马克思主义转向 革命性批判教育学
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1948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教育理论家、教育社会学家。其先锋性的教育学术研究及激进的政治倾向是大众所熟知的,还是北美地区研究弗莱雷(Paulo Freire)的领衔人之一。在美国,他因最经典的作品《学校生活》而闻名。这本书是基于麦克拉伦于内城学校任职期的日记而写的,他任职的学校位于多伦多的简-芬奇走廊地区(Jane-Finch Corridor area),这是加拿大向原住居民提供的最大的公共住房规划区。他的第一本日记《来自走廊的呐喊》(Cries from the Corridor)于1980年出版,并很快成为加拿大的畅销书。在《学校生活》中(现已修订至第四版),麦克拉伦批判了他在《来自走廊的呐喊》中所采取的立场,并且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领域——批判教育学——的领军人物。
一、麦克拉伦批判教育思想的缘起
麦克拉伦在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士学位后,便开始了教学生涯。他选择教授的地点为多伦多的简-芬奇走廊地区(Jane-Finch Corridor area)[1](62-67)。这是一个被功利主义的公共住房所困扰,毫无生态合理性可言的多种族、多语言的工人阶级郊区。此种高密度的住房现况,证实了资本主义是如何集中不均衡的经济及如何进行城市发展的(市场的力量、投机性贪婪及分区法律)。麦克拉伦对此并没有抱怨,而是用叙述写作揭露建立在加拿大学校系统中的那些“残酷的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所揭露的,正是那些拥有特权和发展不平衡的世界所“看不见”的事件。麦克拉伦以此为素材的《来自走廊的呐喊》成为加拿大的畅销书籍,他也以此为契机大声反对学校例行的对贫困儿童实施暴力的制度。与此同时,麦克拉伦重写了《来自走廊的呐喊》,为早期的新闻文献带来了一个理论视角。在Mike Pozo(2003)于“抗议者之声”的采访中,麦克拉伦说道:我最终变得不喜欢这本书了——也许用厌恶来形容更恰当——但是感觉它在美国出版又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自我批判的扩展。原书的问题在于,整本书都是对我经验的描述而很少有分析在里面,以至于以前或现在读都会觉得,是在谴责学生和他们的家人受到的暴力侵害了他们校内和校外的生活。当我将这本书以《学校生活》再版时,加了很多左派分析的观点,使这本书在政治上更加激进,并且每个版本都在理论上产生了细微的差别(到目前为止已有四本)。
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拉伦的开创性著作《学校生活》还曾被莫斯科社会与政治学院国际专家小组评选为外国作者在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领域撰写的12本最重要的书之一。其他提名的作者有: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可以说,《来自走廊的呐喊》一书的出版,不仅将麦克拉伦推向了眾人的视野,还让他开始走向自我批判与形成批判教育学思想之路。从他后来以此为基础改编的《学校生活》,以及多次再版可以看出。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麦克拉伦的影响
麦克拉伦的自我批判并不少见,并且他把重心放在激进主义与学术著作相结合的位置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麦克拉伦表现得更像一位左派的教育理论家,他陷入了所谓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信时尚”的魔咒中,这些理论是美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术“左派”圈子中的重要论述。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McLaren的大部分同僚都通过“后某主义”的福音出书写文章时,McLaren的工作却戏剧性地转向了马克思人文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麦克拉伦“始终反对滥用资本主义”和“支持解放的政治”。麦克拉伦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对社会主义的总体看法,因为他对后现代左派进行了认真的批判性介入,还对差异和代表政治有关的问题很感兴趣[2](165-182)。麦克拉伦后来意识到左翼后现代主义的私有化领域代表着一个社会死胡同,于是逐步沉浸在洛杉矶激进的政治文化中[3](10-15),并开始读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例如Hill Cole Group的著作,此间他还结识了拉雅·杜纳夫斯卡娅(Raya Dunaevskaya),这在他的最后一版的《学校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生活》的第四版。麦克拉伦以马克思的人性化的唯物主义为“实践哲学”的起点,将理论、传记和历史相结合,在这一交汇处,学生/教师在学校内主观地构建自己,以提供真实又不乏想象的“希望教育学”(Freire的话),或者宝拉·奥尔曼(Paula Allman)[4](325-330)所说的“革命性批判教育学”。麦克拉伦通过向读者解释概念(阶级、意识形态和剥削)和经验工具实现这一点。通过将这种批判(以革命性为核心的批判教育学)置于自己的空间而不是社会的场所,麦克拉伦将资本主义知识产业的意识形态永久地置于防御性之上。麦克拉伦和法拉曼德布尔(Farahmandpur)的观点,要求学生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主体,“控制他们的智力和体力劳动”,其中包括找出“将理论从学术界中撬开,并将其纳入教育实践”。这对于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本质上很重要,不仅涉及自由主义的“赋权”概念,还针对“废除阶级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选择”的集体行动和“权力”[5](169)。
当然,在《切·格瓦拉、保罗·弗莱雷和革命教育学》(2000)(Che Guevara, Paulo Freire, and the Pedagogy of Revolution)中,麦克拉伦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的离开是暂时的[6](91-102)。他用格瓦拉和弗莱雷的历史教学法,探讨了如何将阶级意识的自发潜力转化为实际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认为,此时此刻,关键是阶级意识的发展,这种阶级意识在有关必须进行革命斗争的物质条件和极限的知识方面既要协调又要有原则。虽然在每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组织需要面对不同的战术问题,不但应低估嵌入各种自发元素的集体能力积累的政治知识。
这里不应该忘记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无形的思想,而是“感官意识和感官需求两者”的主体[7]。马克思强调“去迷信的(思想)理论类别”,认为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是从“直接的感性环境”或物质中独立出来的,使个人成为人类的条件。这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念的核心,因为感官存在者“可以对这些感官采取行动”(个体地和集体地)改变世界[7]。在现实世界受害人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思想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方式”及来自个人现有信仰体系之外的理论和思想的广泛质疑之上的。此外,在紧紧压制整个战争与恐怖主宰的紧迫压制关头,这种意识层面的对立思想是时代极限的表现。
三、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批判教育学
在过去的20年中,麦克拉伦一直担任着反对资本主义教育的导游。弗莱雷的不朽和麦克拉伦的复兴,实际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麦克拉伦的观点,批判教育学有许多不同的方面(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解放主义者),他所倡导的革命性批判教育学是在常规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对社会主义斗争的最新唯物主义干预[8]。正如麦克拉伦所证明的那样,革命批判教育学的最先形式揭示了它源于对批判教育学的幻想破灭,这种批判教育学却陷入了自由主义/解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方法的流沙中[9](1-9)。即使在今天,麦克拉伦仍然提醒我们:
“批判教育学”的概念已被广泛地使用。换句话说,它已被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者遣返,并受到中庸、市政厅会议创业和礼拜学校传教的影响。可以将其多元文化教育与多元政治联系起来。其中包括通过庆祝“民族”假期,诸如“黑人历史月”和“五月五日纪念日”等主题的“宽容差异”。如果将“批判教育学”这个术语放到当前教育辩论的舞台上,我们必须得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许多早期支持者(例如巴西的保罗·弗莱雷)强烈地驯化了[11]。
(一)阶级斗争与政治
如前所述,麦克拉伦的工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变化。他厌倦了后现代左派的温和改革主义政治,对马克思主义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重新产生兴趣,深受其影响。他与大学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激进主义者建立了新的关系,开始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政治带回到教育的核心。麦克拉伦认为,摆脱制度支持和资本社会束缚的束缚,革命性地批判教育学“将非主观化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基础设定为目标”[10](203-211)。麦克拉伦详细阐述了里科夫斯基(Rikowski.G.)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工作,他说:“阶级斗争既是主体间的又是集体的,是社会整体内部的矛盾力量和驱动力的冲突。”[8]为了阐明这一点,麦克拉伦还在作品中引用了里科夫斯基的话:
阶级关系贯穿于我们的人格。它是我们内部的;我们既是劳动,也是资本。同时我们还是具有对立的社会动力和力量的社会人。这一事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发了矛盾,而解决之道只能来自于我们自身作为资本和劳动力的瓦解以及我们作为一种新的,没有资本化的生命形式的出现[11]。
正如里科夫斯基所言,我们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使我们个体化和集体化”,他认为,我们需要克服我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抵制我们在货币和国家的外来和敌对力量下,以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本的“特殊”形式的自我還原[10](203-211)。正如里科夫斯基所言,我们需要一种人类抵抗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抵制将我们的人减少为劳动力(人力资本),抵制人类的资本化。这种政治也有一个真正的消极面:消灭了使我们陷入僵局并压抑我们的矛盾。然而,只有集体才能消除这些构成人格的矛盾(和社会:没有个人/社会二元性)。它们的终结有赖于消灭产生它们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社会现象中制约它们发展的社会力量,包括“人”(资本)和资本的社会宇宙(价值)的实体的解体。一个集体的、人类反抗的政治工程是必要的,与共产主义政治、一个积极的社会政治和人类重建是密切相关的[11]。
(二)个人发展与集体参与
有鉴于此,一种革命性的批判性教育学将个人的发展(主体的内在生活)与旨在社会转型的集体参与形式联系起来,旨在抵制主体性的“资本化”[8]。所能做的是勾勒出麦克拉伦关于这门学科的最一般的理论,但是由于涉及教育学和那些陷入绝望和希望的生活中的人,值得详细引用他的观点:
革命批判教育学不仅要对那些已经远离异议的人,还要对那些像伊卡洛斯一样生活在上升和下降道路上,但对意志的乐观仍然是力量源泉的任性公民说,他们在政治决策的漩涡中寻找镇流器,但是害怕失去他们的批判能力,他们渴望改变社会政治的地形,却缺乏系统的社会分析语言,他们以坚定的决心超越绝望,但渴望更多的机会围绕一个连贯的实践哲学来构建联盟。拒绝在某个不可命名的空间、某个肥沃的空虚或崇高的形而上学的隐退中避难,在那里,可替代的顿悟代替了改造生产社会关系的具体斗争,他们拒绝接受国家全权代表的官方建议,而赞成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历史经验,他们拒绝把讨论室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反思区,安然地背离了人类生存的荒谬和现代资本与资本斗争的泥泞和不平静的海洋,它避免了宗教胜利主义的陷阱,却渴望生活中的内在启示,与同心同德的公民共同确认公共环境[8]。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者,例如麦克拉伦和他的同事们,正是通过列宁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路线”延伸到各种社会运动中,为革命的可能性奠定了现实基础。“政治曝光”,这些政治曝光集中在资产阶级“可耻暴行”的“活生生的例子”上,组织起来是为了质疑资本主义的“内部运作”[10](203-211)。在列宁的政治小册子里该怎么办?他认为,这种形式的“全方位政治鼓动”构成了“一种全面的政治教育”,应侧重于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各种各样领域的社会问题和世界事件。他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觉悟不可能是真正的阶级觉悟,除非工人们从具体的,尤其从时事政治事实和事件中学习,观察每一个其他社会阶级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的一切表现;除非工人们学会在实践中运用唯物主义理解所有阶级、阶层和人群的生活和活动的各个方面[12](175-183)。
这里重要的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将取决于无产阶级“对一切暴政、压迫、暴力和虐待事件作出反应”的自觉能力。
无论是通过教学、研讨会、在线杂志、传单、报纸或小册子,麦克拉伦相信,这些“生动的揭露”所产生的反思和批判,打破了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结构,将对今天在这一领域活动的不同阶级力量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为革命思想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教育条件,并创造一整套能够使人们有意识地反对这种压迫制度的实践(“支持每一次爆发”)。革命批判教育学是乌托邦式的吗?只是,正如麦克拉伦提醒我们的那样,如果我们盲目或愤世嫉俗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及其对剥削关系的专制,那么这种关系将系统地剥夺人类充分发挥创造的能力和潜力。
四、结语
麦克拉伦,可以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并不是从进入学术界那一刻开始的。他个人的理论重点,以及立足点的变迁,所呈现给大众的,是一位跨学科、不断进行自我否定的学者的形象[13]。作为批判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拓展和发展,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当今,美国公立学校深受危机(如私有化、军事化、公司化)的折磨。麦克拉伦的思想和著作,不仅在对此种危机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方面,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还超越了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的激进功能主义方法(radical-functionalist approach)。麦克拉伦的思想和著作,标志着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复兴。
参考文献:
[1]李宝庆,樊亚峤.麦克拉伦的多元文化教育观及其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2,34(05).
[2]Hill C D. Games of Despair and Rhetorics of Resistance: Postmodernism, Education and Reaction[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5,16(2).
[3]Pruyn M, Huerta-charles L. Teaching Peter McLaren: Paths of Dissent[M]. Peter Lang Inc.,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4]Hyslop-Margison E J. Revolutionary Social Transformation: Democratic Hopes,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and Critical Education[J]. Interchange, 2001,32(3).
[5]Mclaren P. Teaching Against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A Critical Pedagog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2005(27).
[6]Mclaren P. Che Guevara, Paulo Freire, and the Pedagogy of Revolution[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7]Marx K, Engels F.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The Communist Manifesto[M]. Prometheus Books, 1988.
[8]Mclaren P. Life in Schools: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M]. 2015.
[9]Martin G. You Cant Be Neutral on a Moving Bus: Critical Pedagogy as Community Praxis[J]. Journal for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2005,3(2).
[10]Rizvi, Mashhood, and Peter Mclaren. Interview 9: Educating for Social Justice and Liberation[J]. Counterpoints, 2006(295).
[11]Rikowski G. The Battle in Seattle: Its Significance for Education[M]. 2001.
[12]Prins G. 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Part B Medical Anthropology, 1981,15(3).
[13]王雁.美國批判教育学者麦克拉伦的学术生命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