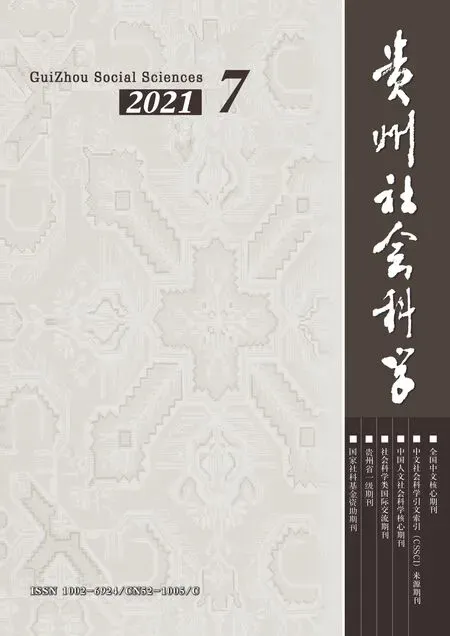琴与嵇康文学形象的生成
2021-09-11熊明
熊 明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嵇康,字叔夜。《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附其传,《晋书》卷四九亦有传。《三国志》卷二一《嵇康传》裴松之案引《嵇氏谱》言及嵇康父、兄:“康父昭,字子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晋扬州刺史、宗正。”[1]605裴注又引虞预《晋书》言及缘何为嵇姓,提供了两种说法:“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嵇’字之上,加‘山’以为姓,盖以志其本也。一曰铚有嵇山,家于其侧,遂氏焉。”[1]605王隐《晋书》云:“嵇本姓溪,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谯国铚县。以出自会稽,取国一支,音同本奚焉。”[2]285《晋书·嵇康传》则取王隐与虞预第二种说法,云:“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3]1369魏晋重视门第,故于出生爵里追溯细致。
嵇康是魏晋名士的代表,其人生经历与被杀的悲剧结局,引来当时和后世无数的论议,也成为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言动的零星记录到传记的撰写、小说的虚构,数量众多的嵇康遗闻逸事、传记和小说故事,呈现出丰富而多面的嵇康形象,而在嵇康文学形象的生成过程中,琴、弹琴与琴曲《广陵散》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事项。
一、琴与嵇康的日常生活
嵇康善琴,已为其同时代人所熟知。其兄嵇喜为其所作传《嵇康传》言:“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4]856这是对嵇康特长和日常生活的说明。嵇康通晓音律,精通琴艺。在嵇康的日常生活中,琴是不可或缺之物,弹琴是嵇康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晋书·嵇康传》亦云“弹琴咏诗,自足于怀”[3]369。
嵇康的这种日常生活,与其人生趣尚密不可分。嵇康好老、庄,在其诗文中曾反复言及,如《幽愤诗》云:“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全真。”[5]13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5]36。嵇喜《嵇康传》云:“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4]856嵇康一生服膺老、庄,以老、庄哲学为其人生哲学,并将其贯之于现实生活,追求一种“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的人生境界[5]83,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把弹琴作为达成这一人生境界的重要手段,他在《养生论》中就说:“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5]49言养生,怎样才能“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绥以五弦”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义。
在时人眼中,嵇康与琴就已密不可分。嵇康出游或访友,常携琴以往,《世说新语·简傲》第4条刘注引《晋百官名》记阮籍遭丧,嵇康往吊,就是挟琴而往:“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6]769
另外,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二“琴价与武库争先”引《金徽变化篇》记嵇康访山涛,亦抱琴而往,且所携之琴是价值连城的极品。其云:“嵇康抱琴访山涛,涛醉欲剖琴。康曰:‘吾卖东阳旧业以得琴,乞尚书令何轮佩玉,截为徽,货所衣玉帘中单买缩丝为囊,论其价,与武库争先。汝欲剖之,吾从死矣。’”[7]14
嵇康身不离琴,在其被杀时体现得最为典型,行将就戮,却念念不忘要最后弹一次琴。《世说新语·雅量》第2条记云:“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6]344《世说新语》所记简略,《文士传》对此描写较细致:“于是录康闭狱,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4]1442《世说新语》简述嵇康临刑索琴弹之,《文士传》则通过一个场景来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世说新语》中,嵇康之兄嵇喜常常作为嵇康的对比性人物出现,嵇康为超迈名士,嵇喜为凡俗之人。不过,就《文士传》观之,还是作为兄长的嵇喜最了解嵇康,居然在嵇康临刑告别之时,也不忘记携琴前往。而嵇康临刑,也要先弹琴一曲而后就戮的做法,不仅是嵇康留给世人的最后形象,同时,也强化了嵇康与琴的联系,这也成为后世嵇康文学形象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事项。
二、嵇康诗文中的琴与自我形象

《琴赋》虽重在赋琴,不过,其间的琴人形象值得注意,嵇康将琴人的品性概括为旷远、渊静、放达、至精,而具体呈现出来的,是“遁世之士,荣期、绮季之畴”的形象,他有着一颗亲近自然、热爱自然之心,可以“越幽壑,援琼枝,陟峻崿”,不畏艰险,探寻幽秘之境。且能发现、欣赏这样的自然之境,是自然的知音:“周旋永望,邈若凌飞,邪睨昆仑,俯阚海湄。指苍梧之迢递,临回江之威夷。悟时俗之多累,仰箕山之余辉。羡斯岳之弘敞,心慷慨以忘归。情舒放而远览,接轩辕之遗音。”《琴赋》中反复呈现的琴人形象,是一种亲近自然、在自然中如鱼得水的潇洒形象,如赋中所歌一段琴曲:“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响以赴会,何弦歌之绸缪。”[5]30-36琴曲中邀列子同游的琴人,齐万物、超自得,委性命、任去留,品高性洁,出于尘表。当他们徜徉在自然之中,那种潇洒闲雅,有如神仙:
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嘉鱼龙之逸豫,乐百卉之荣滋。理重华之遗操,慨远慕而长思。[5]34
这种“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弹琴而歌的形象,和《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中所呈现的“朝游高原、夕宿兰渚”“优游容与”形象是一致的,如第十首所描绘,和《琴赋》“三春之初”几无分别:“携我好仇。载我轻车。南凌长阜。北厉清渠。仰落惊鸿。俯引渊鱼。盘于游田。其乐只且。”此形象在嵇康的诗歌中反复出现。如《五言诗三首答二郭》其二:“岂若翔区外,沧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5]23《五言诗》其三:“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何为秽浊间,动摇增垢尘?慷慨之远游,整驾俟良辰。轻举翔区外,濯翼扶桑津。徘徊戏灵岳,弹琴咏泰真。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恒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一纵发开阳,俯视当路人。哀哉世间人,何足久托身。”[5]28-29且这些形象都具有某种共性,大多在仙境般的自然境界中翱游,弹琴咏歌,逍遥自在。
嵇康《赠兄秀才入军》中也多次提到琴,如第十二首“习习谷风,吹我素琴”;第十五首“鸣琴在御。谁与鼓弹”;第十六首“弹琴咏诗。聊以忘忧”;第十七首“琴诗自乐。远游可珍”;行军携琴,诗中这样的形象和《琴赋》中琴人的形象相似,徜徉自然之中,与自然谐和,怡然自得。这一形象在第十四首中得到完美呈现: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5]10
显然,这种携琴遨游、沉醉自然的形象,恐怕不是其入军的兄秀才,或者其他人,而是嵇康自己,或者说是超脱了现实羁绊的理想的自我形象的写照。
处魏晋之际的嵇康虽有着曹魏宗室之婿的身份,但无论是曹魏集团还是司马氏集团,两大集团在相互倾轧中表现出的人性之恶、让嵇康厌倦,而其中隐含的凶险,也令嵇康不愿委身流俗。《五言诗一首与阮德如》云:“泽雉穷野草,灵龟乐泥蟠。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颜氏希有虞,隰子慕黄轩。涓彭独何人,唯在志所安。”[5]23世俗世界荣名多秽,高位多患。嵇康的选择就是“捐外累”、独自“养浩然”。其实,嵇康在诗中也反复说:“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岂若翔区外”,“轻举翔区外”,“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徘徊戏灵岳”,“游心太玄”,超脱尘俗,轻举高蹈,心游太玄,自由自在,便是这种追求的体现。
嵇康的这种心态,造成了其诗文多表达出尘之想,而无论是自抒怀抱,还是写赠友人、亲人,呈现或凸现出来的,无不是绝弃当下秽浊的俗世,或者翱翔区外,或者集戏灵岳,超然物外神仙般的形象。哪怕是正身处欢乐的酒会,嵇康表达的仍然是“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5]25,希望坐中是东野子一类的人物。嵇康诗文中的这些形象,都是嵇康自我的表达或化身,是其想要成为的自我,或者理想的自我。包括其《圣贤高士传赞》为历代“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作传,也是他自己生命理念的投射。这一点,刘勰以降、论者已多有共识,《文心雕龙》所谓“嵇康师心以遣论”[8]700,陈绎曾所谓“嵇康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9]628正是对嵇康诗文表达自我、投射自我的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形象中,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存在。包括在《酒会诗》这样描写现实生活中自我具体日常生活场景的作品,也两次出现琴:
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5]25-26
这是一次酒会场景,作者与友朋高会,诗中第一次写到琴,“素琴挥雅操”,这是酒会上真实的琴的弹奏,是助酒兴。第二次写到琴,“但当体七弦”,是在写心言志,以琴和琴音表达对知己、对同道中人的希求和渴慕。一首诗中两次言及琴,一实一虚。特别是从以琴写心言志的虚写处可以看出,嵇康在诗文中表达自我心志之时,琴也是重要符号。
三、琴与嵇康名士形象的生成
在时人眼中,嵇康是名士的代表,受到时人的称赏和追捧。这源自于嵇康俊美的仪容与潇洒的风神。两汉实行的察举制度,必然要对人物进行评价。至东汉末年,随着士人与宦官斗争的尖锐化,党锢之祸发生,人物品题成为宣扬节行、制造舆论的手段,由此逐渐形成风气。到魏晋时期,人物品评除了对人物的个性、才能等进行品题外,对人物外貌、精神的品鉴也是重要方面,并逐渐形成了魏晋时期人们对外貌形体、仪容风度之美的特别关注和欣赏。
按照时人形神之赏的标准,嵇康的形貌与风仪,可以说是名士标准的完美体现。《嵇康别传》描写其形神之美:“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4]854据嵇绍《赵至叙》,少年赵至就被嵇康的容仪风度深深吸引:
(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遂随车问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问我?”至曰:“观君风器非常,故问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炙身体十数处。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致邺,沛国史仲和是魏领军史涣孙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阳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经年。[4]1186-1188
同时,嵇康也是当时的玄学大家,著有《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论难文章,参与当时玄学重大问题的论争,为玄学重要一派。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造诣高深。文学、琴学自不待言,他的书法特别是草书也颇负盛名,张怀瓘《书议》曰:“草书:伯英第一,叔夜第二,子敬第三,处仲第四,世将第五,仲将第六,士季第七,逸少第八。”[10]154张怀瓘《书断》中曰:“妙品九十八人,列有嵇康;草书二十二人,嵇康列第三。”[10]252张彦远《论名价品第》曰:“以晋、宋为中古,则明帝、荀渤、卫协、王扁、顾恺之、谢稚、稽康、戴速(原注:已上八人晋);陆探微、顾宝光、袁倩、顾景秀之流是也(原注:己上四人宋)。”[11]将嵇康列为晋宋书画的代表人物。
不仅如此,嵇康还多才多艺,锻铁就是嵇康特殊技艺之一。《世说新语·简傲》锺会拜访嵇康,正逢其锻铁:“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儁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6]766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也有记载:“锺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会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6]767《文士传》亦载嵇康锻铁之事:“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虽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噉,清言而已。”[4]1440-1441
嵇康的容仪、风神、才情,呈露出来,在时人眼中,就是完美的名士,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叹赏。嵇康的名士风流逸事,传于众口,为时人所叹赏。魏晋间裴啟 “撰汉魏以来讫于同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12],著为《语林》,应多载嵇康名士言行,今存《语林》佚文,就存有三条[13]14。至刘宋时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对嵇康言动也多有收集和载录。《世说新语》正文及刘孝标注,涉及嵇康者就多达20余条。如《世说新语·容止》第5条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在当时,就与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被题目为“竹林七贤”[6]727。嵇康死后多年,他的风神依然让人记忆犹新。《世说新语·容止》第11条就记载,多年后,嵇康之子嵇绍长成,人们见其卓然不群,“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6]610” 听完旁人称赏嵇绍,王戎脱口而出,赞叹嵇康的风采。说明虽已过去多年,王戎对嵇康的记忆依然鲜活生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经黄公酒垆下过,每每想起与嵇康等人的竹林之游,遂有“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之叹,“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6]636向秀《思旧赋·序》中对嵇康风神简练而形象的描述和感伤情绪,也是渊源于此:“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3]1375王戎、向秀的嵇康记忆,源自于他们与嵇康的交往,是实实在在的闻见,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嵇康被杀后,嵇康传记随之不断出现。特别是各种名士类传,纷纷将嵇康纳入其中加以传录,如谢万《八贤论》、袁宏《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嵇康均在其中,突出的便是嵇康的名士形象。
谢万《八贤论》,《世说新语·文学》第91条:“谢万作《八贤论》……”刘注引《中兴书》曰:“万善属文,能谈论。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文多不载。”[6]270《晋书·谢万传》(卷七九)亦云:“万字万石,才器儁秀,虽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时誉。工言论,善属文,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稽康四隠四显为《八贤论》。”
袁宏《名士传》,《世说新语·文学》第94条:“袁彦伯作《名士传》成……” 刘孝标于此条下注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6]272《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有《正始名士传》三卷,题“袁敬仲撰”,袁敬仲当是袁宏之误。《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袁宏《名士传》三卷。可知,袁宏《名士传》分三卷、三个部分,分别传录了三个时期的名士,即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嵇康在竹林名士中。
戴逵《竹林七贤论》,《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竹林七贤论》二卷,并注云“晋太子中庶子戴逵撰”;《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均著录《竹林七贤论》二卷,题戴逵撰。在诸书征引中,也有称作“竹林七贤传”者。
谢万《八贤论》今已全部散佚,袁宏《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尚存部分文字。从《名士传》《竹林七贤论》所存文字看,均载录每一位名士生平而重在其言语动止、气度风神等方面,即个性化的言动,来表现人物品性精神,突出其名士身份。袁宏《名士传·嵇康》所存一节文字,叙嵇康随王烈服食养性事,其云:“烈服食养性,嵇康甚敬信之,随入山。烈尝得石髓,柔滑如饴,即自服半,余半取以与康,皆凝而为石。”[4]1475戴逵《竹林七贤论·嵇康》存三节,叙嵇康任心而行、叛逆迕世与潇洒就戮事:“嵇康,字叔夜。与东平吕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嵇康非汤武,薄周孔,所以迕世。”“嵇康临刑,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不与,《广陵散》于是绝矣。’”[4]1494
谢万《八贤论》等之外,东晋张隐《文士传》亦为嵇康作传。张隐,东晋庐江太守张夔之子,曾为陶侃参军。今存《文士传》嵇康传佚文较多,共四节,分别为嵇康从孙登游事、能锻铁事、拒绝山涛举荐自代事、为吕安事牵连被杀事[4]1440-1443。《文士传》为嵇康传,着眼在其文士身份,虽不如袁宏《名士传》专著,但亦不离嵇康的名士风采,如载嵇康能锻铁一事。
不仅各种名士题目如“八贤”“竹林七贤”“五君”等列入嵇康,各种名士传记如谢万《八贤论》、袁宏《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及张隐《文士传》等纳入嵇康,为嵇康所作别传也纷纷杂出。已知就有嵇喜《嵇康传》,孙绰《嵇中散传》,佚名《嵇康别传》,又有顾恺之《嵇康赞》等等[1]853-858。这些嵇康传记虽多散佚,就遗存文字观之,亦多以存录嵇康的名士风采为旨归。如《嵇康别传》云:“康长七尺八寸,美音气,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浚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 《嵇中散传》云:“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毫不吝惜赞美之辞,爱慕、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如嵇喜所作《嵇康传》,文字简省平实,但也抑制不住对嵇康潇洒风神的称美:“家世儒学,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4]853-858
可见,嵇康名士形象的文学生成,经历了由亲闻亲见到传之众口、最后形诸文字的过程。如果说《语林》《世说新语》等还是零星收集、记录其名士遗闻逸事,那么,各种名士传记及别传,则是定位清晰、目的明确的传录。这一过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基本完成。至唐初修《晋书》,《晋书·嵇康传》对嵇康的书写,基本承袭了两晋以来各种名士传、嵇康别传所形成的名士形象。《晋书·嵇康传》所述嵇康生平行事,便是利用各种名士传、别传,对其名士风流的方方面面加以总结。比如开篇一段叙述,明显抄录佚名《嵇康别传》、嵇喜《嵇康传》之文。
在嵇康名士形象的文学生成过程中,琴并没有缺席,而是作为重要事项,被纳入其中。嵇喜《嵇康传》中的“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的表述,是嵇康与琴相联系最普遍的意象,《晋书·嵇康传》也加以继承。至于嵇康临刑而索琴弹《广陵散》之事,经过佚名《嵇康别传》、张隐《文士传》以及向秀《思旧赋·序》、刘义庆《世说新语》等的反复呈现,凝结为“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的典型意象,更是成为经典和故实,被后世诗文反复迻录和化用,《晋书·嵇康传》即据而抄录。
在嵇康名士形象的后世传播中,琴始终是嵇康形象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据五代蜀何光远《鉴诫录》载,南蛮长和国布燮(宰相)段义宗作歌言嵇康,即拣出“鼓琴饮酒”二事:
南蛮所都之地号曰长和国,呼宰相为布燮。王蜀后主乾德中,南蛮选布燮段义宗,判官赞卫、姚岑等为使入蜀。义宗不欲朝拜,遂秃削为僧,号曰大长和国左街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既而届蜀,群臣议奏:“僧有胡法,宜令礼拜。”义宗于是失节焉。至于谈论,敷奏道理,一歌一咏,捷应如流……又《题判官赞卫有听歌妓洞云歌》略云:“嵇叔夜,嵇叔夜。鼓琴饮酒无闲暇。若使当时闻此歌,抛掷广陵浑不藉。刘伯伦,刘伯伦,虚生浪死过青春。一饮一硕独自醉,无人为尔下梁尘。”[14]1035册901上-下
其实,琴与嵇康名士形象的联系,在嵇康在世时就已确立,嵇康好友郭遐周赠嵇康诗云:“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徉。通气自相求,虎啸谷风凉。惟予与嵇生,未面分好章。……援筝执名琴,携手游空房。”[2]19诗中所谓“援筝执名琴,携手游空房”,说明在其朋友眼中,嵇康与琴,就已是一体,密不可分。
这也在当时的绘画艺术中体现出来。1961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刘宋大墓中,出土了一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砖印壁画,其中所画嵇康,就是一个抚琴的形象,微微扬头举眉,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诗意。自此以降,历代有关嵇康的绘画,多有琴相伴,如唐代就有《嵇康〈广陵散〉》,据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引《米氏画史》:“雒阳张状元师德家多名画,其侄孙南都悴兟字茂宗处,见唐画《嵇康〈广陵散〉》,松石远岸奇古,所书故事空民字世未见,同品画真佳作也”。[15]817册204上明代仇英乃至当代傅抱石等所画《竹林七贤图》中的嵇康,都是或抱琴、或抚琴的形象。
四、琴与嵇康故事的编造及新形象的生成
嵇康与琴,在临刑顾日影而索琴弹《广陵散》之后,便更加密不可分,后世嵇康小说故事的编造,多由此生发。
流传最广的是嵇康习得《广陵散》的故事,此故事《晋书·嵇康传》亦载其梗概:“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16]1374此显系无稽之谈,《晋书》采之入史,正如刘知幾对《晋书》的批评:“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16]116-117不过却说明此故事流传十分广泛,家喻户晓,以致史家也将其视为事实并载入正史中。此故事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心理,应该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才艺天授观念。嵇康善琴,而且能弹奏秘而不传的《广陵散》,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得之于鬼魂传授的故事。
寻讨此故事渊源,当出东晋志怪小说《灵鬼志》。《灵鬼志》,《世说新语》见引四条,其“外国道人”言“太元十二年”,其当出东晋无疑。《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灵鬼志》三卷,荀氏撰。《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同。荀氏,不详其名。《太平御览》及《太平广记》《事类赋注》有引《灵鬼志》故事,《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亦有荀氏《灵鬼志》,则其书至北宋初犹存。《灵鬼志》嵇康故事,《太平御览》卷五七九《乐部十七·琴下》、《事类赋注》卷一一《乐部·琴》“或受自华阳”、《太平广记》卷三一七《鬼二》引,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辑《灵鬼志》佚文,此节文字,参校诸书所引,颇善:
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嵇中散神情高迈,任心游憩;尝行西南游,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于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弹众曲,亦不出常,唯《广陵散》声调绝伦。中散才从受之。半夕悉得。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又不得言其姓。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能不怅然!”[13]147-148
故事敷演嵇康《广陵散》得之于鬼魂,委屈细致,十分精彩。其中的嵇康,名士风采依旧,“神情高迈,任心游憩”;且不惧鬼魅,遇鬼于灯下,敢“熟视之”,鬼喜听其抚琴,即“复为抚琴”,并邀请鬼魂现身:“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当然,不怕鬼胆识的赋予,实际上是为鬼魂传《广陵散》作铺垫。故事中,嵇康善琴的一面被强调,常常“灯下弹琴”,“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把能欣赏其琴音的鬼魂当作朋友、知音,“与共论音声之趣”。故事在层层铺垫之后,自然引出鬼魂传授《广陵散》,并生出鬼魂“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又不得言其姓”的情节,为嵇康靳固《广陵散》、不传他人编造出合理的逻辑前因。
南北朝刘宋时刘敬叔《异苑》卷七又载一故事,亦云嵇康《广陵散》得之鬼魂传授,而与《灵鬼志》不同:
嵇康字叔夜,谯国人也。少尝昼寝,梦人身长丈余,自称黄帝伶人,骸骨在公舍东三里林中,为人发露。乞为葬埋,当厚相报。康至其处,果有白骨胫长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复梦长人来,授以《广陵散》曲。及觉,抚琴而作,其声正妙,都不遗忘。高贵乡公时,康为中散大夫,后为锺会所谗,司马文王诛之。[17]68
《灵鬼志》为嵇康夜弹琴而鬼闻琴音而来,共论音声之趣后,授《广陵散》;《异苑》则是昼寝而梦鬼求葬骸骨,葬后致谢,以授《广陵散》。至于鬼魂身份,《灵鬼志》仅云“身是故人”,《异苑》则云“自称黄帝伶人”。《灵鬼志》与《异苑》之外,《语林》又载一故事,言是蔡邕为鬼,亦曾来指点嵇康琴艺。然今存佚文未言及授《广陵散》。其云:“嵇中散夜弹琴,忽有一鬼著械来,叹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调。’中散与琴调之,声更清婉。问其名,不对。疑是蔡伯喈,伯喈将亡,亦被桎梏。”[13]14
《灵鬼志》与《异苑》所造鬼魂传授嵇康《广陵散》故事,在流传中又有变化,且在传播中走向混一。元代道士赵道一所著仙道传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四中的嵇康故事,主体沿袭《灵鬼志》鬼魂授曲的基本框架,细节变化甚多,部分即源自《异苑》故事,授曲地点变为会稽山王伯通家的新馆,鬼魂也由一人变为八人,且鬼魂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由善琴而客死异乡的“故人”变为“舜时掌乐官,兄弟八人,号曰伶伦”。此既源自《异苑》而又不全同。八伶伦之死也冤屈,“舜受佞臣之言,枉杀我兄弟,在此处埋”。八鬼魂的出现和传授《广陵散》,也并非是赏嵇康琴音之美,而是“愿先生与主人说,取我等骸骨,迁别处埋葬”。此亦承袭了《异苑》故事。故事结局则与《灵鬼志》《异苑》皆不同,嵇康被杀,实尸解而升仙:
康闻知大悦,遂以琴与鬼。鬼弹一遍,康即能弹。弹至夜深,伯通向宅中忽闻琴声美丽,乃披衣起坐,听琴音,探怪之,乃问康。康答曰:主人馆中杀人鬼,我今见之矣。伯通曰:何以见之?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见八具骸骨。遂别造棺,就高洁处迁埋。后晋文帝时,伯通果为太守,康为中散大夫。帝令康北面受诏,教宫人曲,康不肯教。帝后听佞臣之言,杀康於市中,康遂抱琴而死。葬后开棺,空不见尸。[18]
在《广陵散》鬼授故事中,鬼魂身份,由《灵鬼志》的“故人”,到《异苑》的“黄帝伶人”,再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舜时掌乐官,兄弟八人,号曰伶伦”,逐渐清晰。不过,在赵道一撰作《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之前的唐宋时期,鬼魂的伶伦身份应已确立。《太平广记》卷二三 “王中散”,注出《耳目记》,云王敬傲北游邺城,与李山甫、李处士会于道观,言及自己所操琴曲时,云:“唯嵇中散所受伶伦之曲,人皆谓绝于洛阳东市,而不知有传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广陵散》也。”[19]1514可见,唐宋人即以为嵇康《广陵散》得之伶伦。
赵道一,号全阳子。为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感儒家有《资治通鉴》,佛家有《释化通鉴》,因著《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五十三卷、《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篇》五卷、《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六卷,收录道教人物九百余人故事。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续编、后集,后收入明《正统道藏》的洞真部。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三四《声乐二·总乐器·琴》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嵇康故事,注出《真仙通鉴》,即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葬后开棺,空不见尸”,暗示嵇康已升仙。其后又引《记纂渊海》云有“叔夜虽示终,而实尸解也”之语,证其被杀实是尸解升仙。《记纂渊海》所引当源自顾恺之所作《嵇康赞》。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载嵇康得曲故事,当在唐宋间流传甚广,以致民间出现了八仙冢,且言之凿凿,具体地点在会稽县东白塔。宋施宿等撰《会稽志》卷一八《拾遗》云:“白塔在会稽县东,俗号八仙冢,华氏《考古》云嵇叔夜过越,宿传舍,遇古伶官之魄,得《广陵散》。曲终自指其葬处,穴今犹在。”[20]宋张淏《会稽续志》卷七《拾遗》亦云:“八仙冢在会稽县五云门外东四十五里,地名白塔。嵇叔夜过越,宿传舍,遇古伶官之魄,而得《广陵散》。其声商,丝缓似宫,臣偪君、晋谋魏之象也。其名《广陵散》,离散播越,永嘉南迁之兆也。曲终指其葬处,至今窟穴犹在。”[21]《浙江通志》卷四五《古迹七·绍兴府下》“八仙家”、卷二三八《陵墓四·绍兴府·山阴县》“晋八仙冢”亦承此说。“八仙冢”“古伶官之魄”,显然与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载同出一源。
在《灵鬼志》嵇康故事中,嵇康的名士身份和形象依然十分鲜明,如不怕鬼、邀鬼现身赏琴、与鬼共论音声之趣,潇洒风流。而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嵇康故事中,“见有八鬼从后馆出。康惧之,微祝乾元亨利贞三遍”,对鬼魂有了敬畏,而被杀之后,“葬后开棺,空不见尸”的成仙结局,也使嵇康在文学中的形象最终由名士转变为神仙。
当然,嵇康之仙化,很早就已开始,顾恺之《嵇康赞》今存佚文,主要是鲍靓夜会嵇康故事:“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静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宁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靓曰:‘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4]858故事中鲍靓所言“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即言嵇康已通过尸解变成了神仙。不过,在后来自葛洪《神仙传》以降的两晋至唐宋的神仙传记,均没有纳入嵇康,直到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嵇康才进入神仙谱系。
也就是说,嵇康的仙化,直到最终被列入神仙谱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嵇康成仙应在民间有着广泛的传播,形成了坚实的俗信基础。宋代佚名《灯下闲谈》所载《坠井得道》,其中有李老善鼓琴而为嵇康后身故事,其云:
青社李老,世业医术,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咸通十五年……秋七月十八日,早自城北别业宿,行草莽间,误堕大枯井中,向五丈余。及醒定意,思尹祈立筮卦,强攀萝而陟丈余,忽扪落一片石,乃见一石窍,可通身而入。遂伛偻而前,来百步,窍广身舒……约二十余里,出洞口,回视,洞门题云大唐玄都洞……瞻视阁内,见一道士,雪髯丹脸,凭几搘颐,旁又有捧琴执簿者。李君乃稽首拜折而坐。因顾侍者,度琴而弹之。李君乃奏《广陵散》曲。道士曰:“尔之制也。”李曰:“晋嵇叔夜感鬼神所传。”道士曰:“感鬼神非也,此自构神思也。尔以业障,不暇忆故事,叔夜即尔亡来之身。”[22]205下-207下
《灯下闲谈》为传奇小说集,《坠井得道》为其中一篇,叙李老误坠枯井,至玄都仙境而遇仙、成仙故事。故事中玄都洞中仙人揭示李老前身为嵇康的情节,是《坠井得道》中的关键情节之一,意在揭示李老身份,有仙缘且合成仙。这个情节实际上也包含了嵇康仙化的背景。这也说明,成仙始终是嵇康文学形象生成中的重要内容。此情节亦颇流传,《类说》卷五二摘录《灯下闲谈》二则,其第二条“白丸子方”即主要是此情节。
嵇康文学形象的仙化,与其本身好服食养生、与神仙交往有关。作为魏晋名士,嵇康精通玄学,好老、庄,热衷养生服食,《晋书·嵇康传》载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尝采药游山泽”,“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3]1369,乃著《养生论》《答难养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文,阐释自己的养生服食观念。嵇康又曾从游高士孙登,《世说新语·棲逸》第2条刘注引王隐《晋书》曰:“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礼而师焉。”[16]649而孙登在东晋葛洪所作《神仙传》中就已被仙化,名列神仙。《神仙传》叙孙登仙事,重要事件就是嵇康从游事。故而在嵇康故事的演化中,嵇康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神仙。同时,嵇康“风姿特秀”,在时人眼中,已是望之如神仙。颜延之《五君咏·嵇康》已云:“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23]另外,此故事中又包含了鬼魂预知生人前途命运的命定观念,“愿先生与主人说,取我等骸骨迁别处埋葬。期半年,主人封为本郡太守”,“后晋文帝时,伯通果为太守,康为中散大夫”[18]。
荀氏《灵鬼志》、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有嵇康得《广陵散》于鬼魂故事。南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所撰志怪小说《幽明录》,又编造出嵇康死后为鬼、传《广陵散》于贺思令的故事。其云: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24]743
此故事亦传播甚广,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二四《鬼九》选录,题“贺思令”。宋吴淑撰《事类赋注》卷一一《乐部·琴》“传古法于嵇康”注亦引,而云出《世说》,当误。已为鬼魂的嵇康,“形器甚伟”,保留了嵇康生前“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的仪表风度;而“著械,有惨色”,则是嵇康作为囚犯被杀戮史实的形象化表达。刘义庆《幽明录》嵇康鬼魂的这一形象,似亦有渊源,前引《太平御览》卷六四四《刑法部十·械》引《语林》蔡邕为鬼著械来为嵇康调一弦的故事中的蔡邕鬼魂形象,与此嵇康形象相似,而《语林》云蔡邕死时被桎梏,故鬼魂著械。则嵇康鬼魂“著械,有惨色”,原因亦当在此,与传统鬼魂观念有关。
《幽明录》故事中嵇康虽为鬼魂,依然悦琴好音,贺思令月中抚琴,便闻声而来,指点贺思令弹琴,并授《广陵散》。生前不传《广陵散》,死后为鬼传之。这一以鬼魂面貌出现的嵇康形象,也值得注意。又,《广异记》“李元恭”中胡郎所引一善弹琴之胡生自云:“亦善《广陵散》。比屡见嵇中散,不使授人。[19]3672”(《太平广记》卷四四九《狐三》引,注出《广异记》)狐、鬼相通,其言“屡见嵇康”,当是见嵇康鬼魂。而嵇康授《广陵散》于胡生,亦要求胡生不得教授他人。也就是说,嵇康的文学形象,由名士最终成为神仙,其间应该还有鬼魂形象的过渡。
五、结语
在时人及后世人眼中,嵇康是魏晋名士的代表。其作为名士的风流逸事,在时人中就已广泛流传,成为人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嵇康被杀之后,随着各种著述如裴啟《语林》、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对嵇康遗闻逸事的载录,特别是如谢万《八贤论》、袁宏《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等名士类传的传录,嵇喜《嵇康传》、孙绰《嵇中散传》、佚名《嵇康别传》、顾恺之《嵇康赞》等个人专传的传录,嵇康的名士形象迅速在文学中得以生成。寻其轨迹,大致经历了由亲闻亲见到传之众口、最后形诸文字的过程,且经历了从零星言动的记录到系统传记撰作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琴、弹琴、《广陵散》往往作为重要事项而存在,特别是在《嵇康别传》等中所呈现出来的临刑顾日影而索琴弹《广陵散》的典型意象,更是成为嵇康名士形象最经典的表达。
各种传记之外,相继出现的新造嵇康故事,与嵇康传记相似,也多与琴及琴曲《广陵散》有关,且多围绕《广陵散》的传授新造故事。综观之,这些新造小说故事,按照出现时间的先后,从荀氏《灵鬼志》到刘义庆《幽明录》、到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凸现出来的嵇康新形象,也有名士、鬼魂、神仙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发现,琴、弹琴、《广陵散》越来越成为代表嵇康身份的特殊符号和作为嵇康显著标志的存在。同时,历史上真实的嵇康,也逐渐成为故事背景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这些小说故事中的嵇康,已逐渐脱离真实的历史人物本身,而成为新的独立的艺术形象。就如《灯下闲谈》卷二《坠井得道》中的李老,为嵇康后身,虽是嵇康,但却是一个新的个体。而这也正是文学创造的魅力所在。当然,嵇康文学形象的生成,无论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嵇康传记,还是逐渐远离历史真实的新造嵇康小说故事,都与历史现实生活中的嵇康与嵇康诗文中的自我投射和写照密切相关,历史现实中的嵇康与嵇康诗文中的自我写照是嵇康文学形象生成的基础和依据。
嵇康留给世人的记忆是深刻而长久的,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七引《童子通神录》云:“房琯少时,曾至洲渚上,团沙捏成睡嵇康,甚有标态,见者多爱之。”[7]51唐代的房琯能团沙成嵇康睡像,足见其对嵇康的熟悉,而这种熟悉,必然得自对嵇康生平行事、嵇康诗文以及嵇康传闻故事的普遍了解和持续的长久兴趣。房琯距嵇康被杀已近500年的时间,尚能如此,也足见历代人们对嵇康的持续热情,这也是嵇康不断出现在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