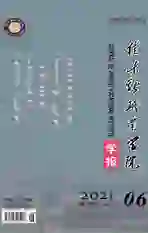弥尔顿与邓恩悼亡诗比较研究
2021-09-10吴雅丽
摘 要: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约翰·弥尔顿与约翰·邓恩都曾为悼念亡妻创作过十四行诗。弥尔顿在《梦亡妻》中通过奇幻的梦境再现了圣徒般纯洁的妻,而邓恩的《第十七首神圣十四行诗》则倾诉了他对亡妻无限的思念与渴求。本文通过介绍这两首诗歌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分析并比较了其中的宗教特色与思想情感,深入探讨了弥尔顿与邓恩两位诗人的悼亡思想。
关键词:悼亡诗;弥尔顿;邓恩
中图分类号:I106.2;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6-00-02
悼亡诗,指的是生者悼念逝者的诗词。被悼念的逝者从广义上讲可以是某个体、某群体甚至整个人类。在西方,人们用来哀吟亡魂的诗歌品类称为挽歌。挽歌源于古希腊丧葬、祭奠亲友时吟唱的歌曲,属于西方抒情诗的一种。它原指悼亡诗,后凡悼亡逝者、悲叹生死与人世无常的诗作都从属于挽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弥尔顿与邓恩两位大诗人都曾创作过悼念亡妻的十四行诗。1656年,弥尔顿在双目失明的状况下创作出诗歌《梦亡妻》。同时期的邓恩也写下《第十七首神圣十四行诗》以悼念逝去的爱妻安·莫尔。本文通过介绍这两首诗歌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分析并比较了其中的宗教特色与思想情感,深入探讨了弥尔顿与邓恩两位诗人的悼亡思想。
一、弥尔顿与凯瑟琳:梦中之喜,梦醒之悲
弥尔顿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斗士。为支持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他不惜以双眼为代价,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民主革命斗争。1658年,“护国公”克伦威尔逝世,弥尔顿政治梦想面临破灭。也正是现实的黑暗之中,诗人梦见了两年前殒于产床上的凯瑟琳,他惊喜于爱妻梦中圣洁的形象并以此为契机,创作出了这首英国诗歌历史上经典的悼亡诗《梦亡妻》。凯瑟琳是弥尔顿的第二任妻子,她温柔贤淑,是弥尔顿心中理想的爱人。不幸的是,1657年凯瑟琳产下一女后因产褥热永远离开了人世,刚出生的女儿也不久夭折。这无疑给弥尔顿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弥尔顿在梦境中遇见了心爱的亡妻,醒来便创作了这首悼亡诗[1]。
从内容上看,诗歌首句便直入主题“我仿佛看到了婚后不久便进入天堂的妻,回到了我身边(胡家峦译)”。在这里,诗人告诉读者他终于再次看到了朝思暮想的妻子,尽管她既苍白又无力。根据他的描述,妻子的再现就像阿尔塞斯蒂从坟墓中回到丈夫怀中一样,让他感到幸福无比。在接下来的诗行中,弥尔顿引用了《旧约》摩西律法中的“净身礼”,婉转地介绍了妻子的死因并描写了她的外貌。受洗后的爱妻一身洁白,脱离了凡世的苦痛,爱、善良、温柔在她身上闪耀,但这一切也只能在幻想中呈现。如果说前十二行诗描写的是诗人与爱妻重逢的温馨梦境,那么最后两行双偶句则道出了梦境破碎后苍凉的现实,“但是,唉,正当她俯身要和我拥抱,我醒了,她逃了,白昼带回我的黑夜。”在诗人的梦境里,当爱妻逐渐走近并俯身拥抱“我”时,梦境却戛然而止,美好的一切皆化为灰烬。此时,苏醒后的诗人立即意识到梦中的妻子只是一个幻象,可望不可即。于是巨大的孤独与无力感瞬间将他吞噬,醒后残酷的现实也变得让人难以承受[2]。
二、邓恩与安·莫尔:超越信仰的爱情
邓恩是玄学派诗歌的开创性和代表性人物。他熟读神学、法律、医学和文学等书籍,所著诗歌逻辑缜密、诗风独特,充满着无数的奇思妙喻。他写跳蚤吸血有孕、写圆规琴瑟和鸣,大胆、丰富的想象力及独特的人生视角奠定了他在整个英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邓恩的爱情观是矛盾的。他一方否定爱情,抱怨女人的善变,另一方面却又赞美爱情的永恒。特别是在献给爱妻的诗歌中,邓恩化作痴情的丈夫,肯定爱情的价值、歌颂它的甜蜜。1617年,年仅33岁的爱妻安先他而去,邓恩悲痛不已,写下《第十七首神圣十四行诗》以寄托哀思。
邓恩与安的婚姻掺杂着许多现实的因素。妻子安出生名门,可邓恩当时只是一个“浪子”。他们的结合自然惹怒了安的父亲,邓恩因此也断送了前途。可即使这场叛逆的婚姻使得夫妻二人吃尽苦头,他们依然选择相依相守。《第十七首神圣十四行诗》虽然是一首悼亡诗,但诗人并未沉浸在丧妻的痛苦之中,而是豁达看待,为爱妻摆脱尘世表示欣慰。诗人在句首写道:“既然我所爱的她,已经把她最后的债务偿还给造化;对她对我都有好处,死了;她的灵魂也早早地被劫夺,(傅浩,2006)”邓恩认为,爱妻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在偿还她所欠债务,由于自己事业上的不得志,他无法给予妻子应有的物质与庇护,使得安成了无辜的受害者[3]。因此,她的死去是债务还完的标志,这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在失去安这一精神支柱后,邓恩也曾急切地寻求上帝,想与安在天国重聚,可生死的界限让他清醒。诗人在后面提到,尽管他找到了上帝也于事无补,盲目地追寻并不能消解渴意,逝去的日子永不会返还,尘世中的爱恋又怎能返回?在诗歌的末尾,诗人将自己的爱恋与信仰相比较,他写道:“您不仅担心,我会放纵听任我的爱移向圣徒和天使、圣物之类货色而且,心怀着您温和的嫉妒之意”在这里,邓恩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对妻子安的爱已经超过了对上帝的爱,这无疑引起了上帝“温和的嫉妒”[4]。上帝担心他听任圣徒和天使的摆布,从而不能保持对主完全的信仰与忠心。于是夺走了他的爱人,留他一人继续在尘世中受难。
三、诗歌比较:现实中的梦境与清醒
两首诗歌都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弥尔顿在诗歌第六行中提到:“我的妻,如同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 拯救的女子,洗净了产褥上的血污,”这里诗人引用了《旧约》摩西律法中的“净身礼”,婉转地介绍了亡妻的死因。根据律法,妇女生子至少要经过33天的洁净礼,否则由于体液血污,身体是不洁的。凯瑟琳死于生育后的产褥热,必须接受洗礼才能保持洁净。诗人希望爱妻能够干净、快乐地生活在天堂之中,因此净身礼不仅是诗歌中宗教色彩的体现,也包含了诗人的美好祝愿,只有洗净产褥上的血污,亡妻才能如此洁净地站在他面前。
基督教的生死观认为,个体的生命虽然短暂又有限,但亡者的灵魂会在天堂中永生,尘世的苦难能够在此消解,這一观念在两位诗人的作品中都均有体现。弥尔顿能够看见远离苦痛的凯瑟琳,邓恩也能视爱妻的离去作为一种解脱。曾几何时,邓恩也曾苦苦追寻上帝,祈求痛苦能够消解,但他很快意识到盲目的追寻只是徒然。在诗歌的最后几行,他提到上帝担心“我”的爱会移向圣徒之类的货色,于是怀着“温和的嫉妒”疑虑众生。这是诗人将自己的尘世之爱与对上帝的信仰之爱进行了比较。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上帝的地位本不可动摇,但诗人与安的爱恋竟然引起了上帝的“嫉妒”,由此可见邓恩对安深厚的情感。总的来说,邓恩的悼亡诗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他把自己的深情与宗教混成一体,坦白曾经因更看重尘世的爱恋而引起上帝的嫉妒。这样精妙的比较手法不仅从侧面表达了诗人对亡妻安哀悼与思念,也在宗教层面上永恒地定义了他们的爱情[5]。
但是,由于诗人的人生经历、体验不同,两首诗歌在某些内容与情感表达方面均各有特点。在内容上,《梦亡妻》创作于一场梦境之后,诗人能够引梦入诗、以诗写梦,形式十分新颖。弗洛伊德认为,梦是冲突愿望的伪装满足,它可以分为隐梦、梦的工作和显梦[1]。弥尔顿在梦中与妻子相遇的情景就是显梦,它是以视象和体验表现了意识的幻想,满足或正在满足主体的欲望。梦中的凯瑟琳是弥尔顿幻想的人物,她的纯洁与幸福不仅代表着诗人美好的祝愿,也是诗人逃避现实的体现。此外,相比于邓恩的诗歌,弥尔顿在《梦亡妻》中使用了丰富的典故和大量的修辞手法。例如,在诗歌第二、三行中,诗人运用了阿尔萨斯蒂的故事来表现再见爱妻的欣喜之情。在希腊神话中,阿尔萨斯蒂与阿德莫托斯这对新婚夫妇忘记向月亮女神献祭。于是女神决定赐死丈夫,阿尔萨斯蒂知道后,选择牺牲自己救下丈夫。最终被朱庇特的儿子从坟墓中救下。在这个典故中,弥尔顿自比阿德莫托斯,通过典故巧妙地还原了再见亡妻时欣喜的情景。在诗歌的结尾,诗人还运用的修辞手法充分表现了内心的悲苦与遗憾。他提到梦醒后的“白昼带回我的黑夜”,看似矛盾却另有深意。由于双目失明,常人的白昼对于弥尔顿来说如同黑夜昏暗无比,可到了夜晚梦境来袭,他可以暂时忘记痛苦与爱妻在天堂里相视相遇,这自然中的黑夜由此成为他心中的“白昼”。在情感表达方面,邓恩对爱妻逝去的释然与现实的清醒也十分引人注目。面对爱妻死亡的现实,他并未过度悲伤,而是接受现实并替她高兴。同样清醒的认识还体现在他另一首哀歌《梦》里。诗人也曾试图在旧爱的幻想中麻痹“失去”的痛苦,但他知道虚幻的梦境终将醒来,爱的“消逝”无可避免。如今的离别虽是生死,但过度沉沦只会使人日渐憔悴。
四、结语
弥尔顿和邓恩在面对丧妻的痛苦时,他们都选择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寄托自己的哀思。双目失明的弥尔顿在《梦亡妻》中再见了爱妻。她脱去染血的产服,如同纯洁的天使一般,将他的黑夜变为“白昼”。在《第十七首神圣十四行诗》中,邓恩则讲述了另一场生离死别。他并未过度悲痛于爱妻的离去,而是为她偿完债务感到欣喜。两首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情感表达上都各有特点,是文艺复兴时期悼亡诗的典例之作。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北京:中國华侨出版社,2013.
[2]李正栓.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3]孙美萍.弥尔顿《悼亡妻》中的悼亡思想试析[J].语言文学研究,2004(8):18-19.
[4]王秋生.西方悼亡诗史综述[J].语文学刊,2010(8):41-43+57.
[5]杨周翰.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6):8.
(责任编辑:张咏梅)
收稿日期:2021-03-01 修改日期:2021-04-10
作者简介:吴雅丽(1996—),女,四川攀枝花人,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