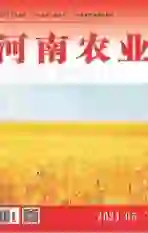《做新闻》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分析
2021-06-28马慧萍
马慧萍
关键词:《做新闻》;建构主义;框架理论
长久以来,大众包括媒体工作者自身都认为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是记者编辑们秉持着真实性、客观性、自由性等原则向大众传播的事实信息。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定义有了不同的声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对媒介组织的性质和工作流程、对媒介的效果和内容研究以后,社会上产生了一波针对“生产新闻”的研究浪潮,盖伊·塔奇曼的《做新闻》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高峰,他引导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我们对“新闻”的说法,为我们重新理解新闻专业主义打开了另一扇窗。
《做新闻》出版于1978年,是塔奇曼深入到新闻行业内部,通过自己的观察、与记者编辑的交流、收集大量数据资料以及依托各种理论共同完成的。严格地说,《做新闻》并非探讨新闻操作技能的书,它的研究重点显然在于理论层面的探讨——从解释社会学的视角揭示框架如何制约新闻生产,新闻生产如何建构现实,并使现实合法化合理化。
一、全书概况
全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主要向读者展示了日常发生的事情如何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第二部分则是后面三章,主要从理论依据上深入阐述产生新闻的根源。在整本书中,作者最为鲜明的观点就是把新闻看作是一种框架。这句话看上去有些抽象,但实际深剖来看又揭示了新闻的重要属性。所以,框架是什么?如何理解框架?我们不妨先从新闻工作者日常工作的方式上试想一下,在这方面,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每天的新闻看上去犹如万花筒,可内里,早已形成自己固定模式和做法,记者们可以娴熟地根据新闻样式或者新闻内容,很快就可以确定去哪里找信息源,从什么角度报道。事实虽然是新的,但是技巧是不变的。”这句话真实地向大家展示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含义。每一件事情落在单个的个体身上也许是从未发生过的“第一次”,但是当纵向来看,把它放进人类共同体这个大库里面搜寻,每一件事情都找得到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也使得新闻工作者们的报道模式有了逻辑参考,可以驾轻就熟,快速反应,按图索骥,有章可循。同时,也正是这些许许多多现实案例的积累沉淀,才为后人探索发现新闻产生的规律提供了大量的实际基础。
按塔奇曼自己的分类来讲,本书大概可以分为“前窗”和“后窗”两部分,前面的一至七章着重从多个方面讲述日常发生的事情是怎样被变成了新闻这种具有现实时空的报道;八至十章揭示新闻生产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同时也交代了自己研究及其结论的理论依据。
对于“框架”在学术上的完整定义和表达,本书中这样写道:“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惯常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常规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由此,这一些框架就成为大众媒介文本编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了的部分,而且可能在受众解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全书中,作者通过考察这个框架是如何建构的,在建构的过程中记者、编辑、信源和新闻机构等等是如何有机结合在一起。最终在书的末尾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知识,是被建构的事实。
二、研究方法
也许是研究方法上的共通性或是相似性,又或是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得社会学和新闻学在调查研究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的作者赫伯特·甘斯一样,盖伊·塔奇曼同样是研究社会学出身的。如果说《什么在决定新闻》是一本新闻业包罗万象的书,那么《做新闻》就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它覆盖的范围不大,并非是对整个新闻行业大方面进行研究,而是着重于具体场景、特定时空甚至个体的行为,描述的也是社会生活和实践的某片段,强调了新闻从无到有整个过程其实受到了各种力量的干预,是被建构而不是事件的直观反映。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质化研究,也就是定性研究,這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和方法之一,是研究者用来定义问题或处理问题的一种途径。塔奇曼通过最直接最贴近实际的田野调查,深入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中,精心选取了一群具有代表性的小规模样本——市政厅记者团,以市政厅记者室以及地下备用记者室为主要观察场所,对9名记者每周一次的工作方式和特征观察、访问、参与式体验获得处于自然工作状态时记者的工作情况,并将一个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被信源、记者、编辑等有目的地建构改造、审核把关,最终变成报纸、电视或网络上新闻的全过程记录下来,从中发现一定的规律和特质。比如,记者与信源的关系和保护信源的方法,分管不同区域新闻的记者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处理交叉地带的新闻,如何与同事或是竞争对手互通信息有无,如何将新闻进行类型化区分,在报道新闻传递消息的过程,中文字和摄像一般通过哪些方法使新闻报道看起来更中立客观等等。这一类的实际问题只有在作者接触这个行业的日常实践、累积相关的经验、规则等才会碰到并记录下来。除了在市政厅记者团等场所进行实际观察与交谈收集到的资料以外,作者还综合运用前人的理论、历史文献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数据作为支撑,再加上研究者的经验、对问题的敏感性和相关的技术,全面洞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最终解释了为什么自己认为“新闻是建构出来的”这一理论。
功能主义、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一发展过程也体现了媒介社会学研究者注意力的转移和不断的探索、拓展,建构主义强调人是具有理解力和创造性的主体,而不是被外在社会结构体系所决定和驱使的角色,他们认为世界不是一个对象,只有在行动和建构中才能达及。《做新闻》也是建构主义的一个代表。塔奇曼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新闻工作者和组织机构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在充分发挥着能动性,在专业与灵活之间,在规范与个性之间切换,勾勒社会的面貌。在塔奇曼的研究过程中,他将研究工作与实际相结合,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打破了学术研究高高在上的地位,也为普通人提供了研究方式和途径。除此之外,塔奇曼的质化研究并没有囿于传播学常用的量化研究方法,也突破了逻辑演绎和归纳法,更多的使用访谈、田野调查等方式,在与研究环境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能体验工作者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既保证了收集资料和调查的客观性,又在研究的过程中添了更多互动性和与生活的相关性,是有益的尝试和研究。
三、研究内容
全书的主线来自于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他认为框架就是人们把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个片段,归整成自己经验知识的规则。在这本书的开篇,作者就提到“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通过这个窗框,我们美国人了解自己,也了解他人,了解美国的制度……跟任何用以描绘世界的框架一样,新闻这个框架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窗口展示的视野取决于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这个视野还取决于视点的位置。”依赖于这样的框架,人们经验到的生活世界,便有了条理和秩序,也是这些被整合条理化了的经验知识,又成为人们下一次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新闻本身也是一种框架,媒体不仅传播着人们想知道、需要知道和应该知道的事情,而且也在议程设置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通过采写编等不同环节的干预,最终构建出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身上自然也带着每一步加工过程给它自身留下的烙印。所以,“做新闻”不是指记者凭空捏造新闻,而是更强调新闻产出过程动态化,“做”即“建构”,强调中间环节发挥的作用。
在“前窗”中,作者涵盖了做新闻的多个方面:在新闻的采集上,每个记者都会保护好自己的信息源,互相不打听信息源也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之一。由于对社会资源掌控的多寡不同,记者对中心场所提供的更集中的信息有依赖性。于是从空间上来看,新闻是以中心机构为定位重心铺开的网状结构,信息采集人组成了这个机构中的等级体系,也为进入机构采访提供了合法性。在新闻的内容上,可以根据类型化分为硬新闻、软新闻、突发性新闻、发展性新闻和连续性新闻,新闻工作者可以将新闻工作专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并根据不同新闻种类的特点合理分配资源,做出规划和预期,控制工作进度。
在“后窗”中,塔奇曼表示新闻的生产带有一定的意志性,顺从了世界原有的价值观,是对社会秩序、价值和现状合法性的不断确认,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社会帮助了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人们在共享社会世界里有意识的积极活动,又共同建构了社会现象,于是读者就可以从字里行间感知所传达的事实和意义。
此外,作者还引入了民族方法学者描述的“自反性”和“指称性”,这两个术语在黄丹导读里面有提到,但是在倒数第二章作者才细致分析了这两个概念。他认为自反性和指称性构成了新闻的公共性特征。对它们的理解应放在不同的社會语境下。通过观察和描述人们如何理解新闻报道的话语、记者如何理解事件以及人们如何从特殊的细节中推断出生活世界的特征,从而表明新闻生产深层次的原因和相应的理论支持,用塔奇曼的话说则是“叙述被嵌入自身刻画、记录、构成的现实中”。
塔奇曼的《做新闻》对新闻生产过程的重点介绍,让我们重新去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对它的真实性、客观性、自由性有了新的认识。那么除了研究方法的突破,在我们最终了解为什么新闻是被建构出来的原因以后,我们对待被建构出来的每一条新闻时,又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呢?这大概也是本书留给我们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