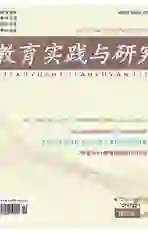抗战时期沦陷区日伪奴化教育述评
2021-06-22吴洪成高亚倩
吴洪成 高亚倩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奴化中国人民,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利用伪政权在中国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一方面摧毁沦陷区原有的学校,阻碍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建立学校和社会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日伪在沦陷区所推行的奴化教育,使中国沦陷区的教育事业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也对学校学生及社会民众心理、思想和感情产生了重大的伤害。
关键词:抗战时期;沦陷区;奴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21)12-0059-06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扶持下的汉奸政权在中国沦陷区兴办教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实施殖民教育的一个特例。其办学活动之复杂、手段之多样、设施之齐全、用心之险恶,为史所仅见,从而形成了一种中国教育史上极为独特的形态,史学界将其界定为奴化教育。
日伪控制中国沦陷区以后,所设置的教育机构殖民地色彩和奴化性质非常浓厚。日伪沦陷区
所设置的教育,其目的是通过奴役毒害青少年,以磨灭学生民族情感;控制民众,进而使他们变成日本的二等臣民,最终实现占领、统治中国的侵略战争目的。这种奴化教育是殖民教育的典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期所实施的较之军事侵略更为深层的文化渗透策略。
一、沦陷区教育文化的整体衰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抵御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拉开帷幕。日本在占领地,对中国原有教育资源加以破坏,强迫实施日伪所需要的战时奴化教育,倒行逆施,使沦陷区所积聚的教育元气大伤,文化倒退。
(一)高等院校的浩劫
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之下,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损失惨重,而高等学校最为严重。如1937年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同日,河北女师、河北工学院亦遭荼毒。8~10月,暨南、复旦、同济、中央、中山各大学也相继遭日军袭击,造成大批校舍被毁,人员伤亡严重。1938年“八一三”事变后,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于8月15日遭到日军摧残,图书馆和实验中学被毁。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9年4月编制的《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统计,截止到制表时为止,日本侵华战争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造成的损失为:国立各校死伤50人,财产损失36527231元,其中包括北京大学1628515元,清华大学6050000元,浙江大学1560000元等。私立各校死伤50人,共损失财产达22662712元,其中包括金陵大学2316310元,复旦大学544975元,南开大学3000000元等。到1939年4月,日本侵华战争已经给我国92所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造成重大损失,覆盖面达90%以上的大专院校,因此日军侵华战争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打击是空前绝后的,把中国教育事业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
(二)教师生活困苦不堪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教师的生活虽然难称殷实富足,但仍能维持全家人的温饱及支出。抗战以后,沦陷区教师的生活境况急转直下,尤其是小学教师最为严重。1943~1944年,华北沦陷区小学教师的工资收入微薄,而物价却比战前迅猛上涨,教师难以靠自己的薪金供养家庭。1944年5月7日,《华北日报》刊文《救救教师》,其内容为:由于生活的穷困潦倒,教师们只好自谋出路,“兼差的兼差,改业的改业,环境逼着他们垂头丧气,苦度艰辛的哲学和献身教育的理想,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的”;教师由“清高神圣的职业变成高等乞丐”。高等学校的教授也同样苦于生计问题。燕京大学的教授们靠吃难以下咽的“混合面”维持生活,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有的教师为了生活,甚至卖掉自己心爱的书籍。在日伪的残暴统治下,教师的温饱都成了难题,还何谈做好教学工作,开展教育研究,并积极推动教育更好地发展呢?
(三)教育管理权沦落敌手
在沦陷区,日伪政权纷纷设立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作为其推行奴化教育的场所。如在1937年12月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下设教育部,管理伪临时政府地区的教育行政事宜,伪教育部下设教育、总务、文化三局。日伪当局除了设立伪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外,还成立了一些协助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教育团体,如“中华民国教育会”“乡村教育促进会”“教育研究所”等。日伪的教育组织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行奴化教育。
(四)爱国师生及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日本侵华期间,日伪对沦陷区爱国师生和知识分子的身心加以摧残,致使很多师生惨遭迫害。如日军侵占太原后,对学生严加监视,学生对学校稍有不满或者谈论国事就会受到处分;教职员也经常受到宪兵的检查,无故被带走。为了有效地监视学校师生,沦陷区学校里大都派有日籍教师,许多日籍教师名义上在校任教或从事其他工作,实则担负监视全校师生之责,一旦发现有爱国或抗日言论,就报告给上级,由日军军部或伪警察局出面管压。为向中國青年灌输奴化思想,敌寇不仅强制学生学习封建古书和风花雪月诗文,还监视青少年的思想行为,经常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思想检查”,一旦发现“不合格者”就会被特务机关管制与迫害。不少优秀青年在敌寇强加的“思想不良”的名义下,受到警告、威胁甚至逮捕。此外,还实行“勤劳奉仕”的压迫方法,强迫学生做农活、杂活等。为消灭学生的民族意识,敌寇除要求学生每周上日语课和军训课外,还要上修身课2小时,并规定每月8、9两日为“祭忠魂碑日”,强迫学生向战死的日军祭奠。
汪伪政权对学校的思想统治尤为明显,对教师队伍的控制也十分严密。教师和学生没有任何言论自由,若发现有抗日意识或者“妨碍邦交”的言论及活动,即停职惩办,一旦被抓走就面临被拷问迫害的风险。江苏省无锡市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因作文中有抗日文字,汪伪教育部作为“大案查处”,汪精卫亲自批示指责该校校长及阅卷教师“公然违背政纲,阻碍和运,殊属胆大妄为,罪无可恕,自应严行究办,以遏乱萌!”结果校长和那位教师被羁押警察局,“分令各县永不任用”。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摧残,还表现在强迫或收买知识分子参加敌伪工作,初中学历的给予伪乡长职位,高中学历的给予伪股长或伪科长职位,如果不愿意就职,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威胁。
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军事占领和殖民掠夺,中国所遭受的不仅是在物质经济上的损失,还反映在教育文化的悲惨遭际。日伪在沦陷区的强制办学,目的是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一刀切断,并在中国建立符合侵略者利益的奴化教育制度。奴化教育制度是在亵渎中华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并且借助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加以推行,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
二、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侵略性实质
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从整体上而言,属于日本文部省所设计的“教育一体化”“文化战争”的核心部分,是侵略、统治中国的“柔化”政策在教育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奴化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了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被日本同化,使教育服务于日军对华经济掠夺、治安稳固、军备筹集等方面殖民统治。
伴随着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的殖民统治、军事上的侵略征服、经济上的搜刮掠夺,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其实质在于奴化沦陷区的人民,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和做亡国奴。奴化教育在理论上高谈“新民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大东亚共荣”的侵略思想相结合,使沦陷区民众的思想“更新”,培养所谓的“新民”。日本右翼学者佐藤三郎指出“新民”的含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中的“亲民”即是“新民”。日本侵略者故意将奴化教育融入到儒家文化中,其用意在于使沦陷区人民都能知“仁”、懂“礼”,甘于接受日伪的统治与奴役。奴化教育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宣扬孔孟之道,祭孔尊儒。一时间,各地在学校内则极为重视经学学习,社会上大肆举行各种活动,“以端教化”。此外,日伪政权还大肆渲染日本的“大和文化”,推行日语教育,打着“中日亲善”的幌子,对中国青少年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奴役。对于日寇的险恶用心,周作人之流的汉奸文人非但不知自省,反而助纣为虐。1941年2月14日晚,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往外交大楼作题为《关于华北教育》的广播讲演,由伪中央广播电台放送,讲演中其极力吹捧日伪统治下的华北教育:事变之后,前临时政府于二十六年冬成立伊始,首设教育部,因鉴于前国民政府教育设施不良,往往利用青年学子之爱国赤忱,专事挑拨民族感情,并受共产邪说之麻醉,殊有根本改正之必要,乃于次年四月间规定新教育之推进方针及其实施上切应办理之事项,并同时修正中小学及师范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先后命令公布,通饰各省市遵循在案。迄今三载对于教育上之进步,因各省市治安之恢复,先后不齐及教育经费之筹多寡不一,虽无特殊成绩可言,但肃正思想,使一般青年弟子有深切之觉悟,逐渐纳于正轨,差堪告慰,嗣后又得友邦之协助,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而共同迈进,当为各界人士所共见共闻。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一贯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因此其所输出的教育必然是服务于日本在华利益,而具有侵略扩张的性质。为培养中国国民的“親日”思想,日本成立了“兴亚院”来处理日中之间外交事务,并根据《对支宣传策略纲要》制定了对华教育基本方针:“消灭民族意识,毁灭中华民族文化,排除一切抗日思想。”1940年8月,汪伪政权控制下的伪南京市教育局颁布了《南京市中小学训育防针》,小学部分规定:“养成儿童有和平亲善敦睦友爱之精神;养成儿童有手脑并用生产就业之技能;养成儿童有忠恕诚实礼义廉耻之美德。”中学部分规定:“训练学生确切认识国际环境与中国地位,以和平反共为建国之基本信念。”可见其教育活动之核心即为“亲日思想”之培植。
日本侵华时期在沦陷区推行的教育是紧密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而实行的思想占领、精神征服的手段,妄图以此达到永远占领被侵略国之目的。在占领中国领土初期,首先是破坏——摧毁原有国家的民族教育体系,占领后则开始建立配合侵略战争、巩固沦陷区的教育系统。
办教育需要有足够的物力,当时沦陷区财政大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在奴化教育方面,侵略者不惜花费大量资金,以奴化中国人民。以日伪统治时期的河南省为例, 1940年至1941年暑假,开封市及豫东的商丘、豫北的新乡、安阳等市,许多省立、市立、私立中小学都纷纷建立起来。特别是开封各县自1942年春以来,“对各乡私塾之取缔极为严厉,派遣伪教育人士四处调查,如某村设有私塾,处罚其保甲长”,并“携带大批糖果及各种反动宣传漫画赴各乡村散发,以笼络无知民众”。从表面上看侵略者统治下的河南教育出现了的短暂“恢复”,实则更加深了日本奴化教育的程度。
在有些落后的边疆地区,日伪出于实施其殖民统治的需要,推行奴化教育,个别地区在某个局部时间学校数量或学生数增多了,其实质是为了诱惑中国人民而采取的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一种举措。他们建立学校之目的是为其侵略战争提供方便。这样的学校愈多,证明日本侵华愈深,中国人民遭受灾难愈重。
三、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复杂影响
日伪在沦陷区实施的奴化教育,给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带来了更加深刻的灾难性影响。
(一)开办各类学校,造就沦陷区殖民统治的力量
日伪为了对中国实施奴化的教育侵略,在各地的伪政权建立之始,立即对教育进行整顿,开办学校,并用胁迫手段,招收青少年入学。据伪华北教育总署于1941年对所辖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青岛七省市的中等、初等教育的情况统计,七省市共有初等学校31467所,学生1586162人;中等学校218所,学生59319人。此外,苏北共有初等学校198所,学生19632人;中等学校10所,学生991人。
日本占领青岛后,开办了各类学校,包括日本女子中学、日本男子中学、日本小学、中文学校、商业学校和幼儿园。不仅是为了解决日本宗主国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实施殖民主义统治所需要的御用人才。为此,学校把武士道精神、军事训练和汉语列为主要课程。这里所有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样,要接受法西斯军事训练和日本“忠君爱国”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武士道精神和等级观念,随时准备“为大东亚圣战献身”。殖民当局还设立5所日语学校,专门招收日本学生,共有354人。日本侵略者第二次侵占青岛后,仿照在北京设立的“国立新民学院”,设立了“新民塾”,开办“青年训练所”,培养为日本效忠的伪职人员。另外,私立东文书院,旨在教授中日语言,“以融洽两国青年之感情为宗旨”。这些学校都意在教学日语,实施奴化教育。
为了培养伪军人员,日伪建立了一些专门教育机构。汪伪政权建立后,在南京建立了伪中央陆军学校,汪精卫亲任校长。1935年8月,日伪还成立了军士教导团,随后,华北伪政权开办了宪兵学校及各种其他班队,如译务训练班毕业学生200多人,军需训练班毕业约100人,军医训练班毕业约100人,注射训练班毕业约100人,为新建伪军训练管理干部及技术人员。
(二)破坏近代中国教育体系,迫使学校内迁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我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建立的教育体系遭受严重破坏。无论是当时的学校,还是图书馆、博物館和其他民众教育机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为应付危急的时势,并适应民族抗战的实际需要,国民政府被迫将一批高等院校迁往内地。内迁高校集中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内迁高校的广大师生在这片贫瘠而封闭地区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使得战时高等教育得以维持和局部发展。与此同时,大批文化界精英涌入内地,极大地提高了内迁高校的办学质量和师资水平。
日本侵华战争致使中国东部及内陆许多地区沦陷,学校教育、文化及科技的有关机构或部门被迫内迁,造成现代史上教育文化区域空间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艰苦环境中的爱国师生备尝辛酸,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办学。以下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办学历程为例加以说明。1937年10月,敌机轰炸无锡,11月14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连同俞庆棠所主持的江苏教育学院师生开始内迁,经南京、溯江而上至武昌,转往长沙。这两所合并而成的学校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11月,日寇侵占武汉,又分兵南下,长沙大火,桂林震动,学校转向广西北流县的山围和萝村,借用民房和祠堂复课。1939年秋,分别在南宁、梧州招生,录取新生100余名。物资缺乏,因陋就简,师生的生活极为艰难,然而,依然教学钻研不辍。1944年8月,日本侵略军攻陷衡阳、桂林,为保护师生安全,校方作紧急疏散。师生们不得不忍痛撤离呕心沥血营建的临时校园,进行更为艰辛的迁移。由平乐至蒙山,借用民居为临时校舍。不久,日寇逼近蒙山,部分师生又西去瑶山金秀,经费困顿,一切勉强维持,直到抗战胜利。
高校内迁汇聚了我国科技文化的精英力量,更重要的是保存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财富。这就在一种程度上保证了我国战时经济的开发,以及为以后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储备了人才。
内迁高校促进了西北、西南地区的教育与经济发展。高校内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播迁”。如西北联大坚持“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并行”的原则,在陕、甘、宁、青、绥、豫六省建立中等教育辅导区。他们利用暑假举办体育、语文、英语、算术等各科教师讲习班、讨论会,帮助当地中学教师提高业务水平;而当时教材、教法中的问题,又成为该校教师科研的课题。1939年,南迁至广西的浙大农学院师生,向当地群众公开展览并推广科学养蚕及缫丝技术;到达贵州后,又曾先后推广马铃薯、蕃茄种植,黔北病虫害防治,蔬菜种子的挑选,西瓜的种植和胡桃的育种技术,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学校向内地和西部的转移,为偏远地区带来了教育的薪火,也为少数民族带来了文明进步的希望。各类学校在战乱中坚持办学并谋求进步,为广大的青少年提供难得的求学机会,为战后重建储备了力量。
文化教育的水平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战时中国大后方文化教育出现短暂繁荣,或许是一种畸形发展。文化教育界爱国进步人士面对日本的教育侵略不得已采取了教育应对措施,将学校教育融入民族抗战的热浪洪流之中,这是大无畏的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精神。此举在绵延国家教育文化的同时,也在进行广泛抗战宣传及多层次人才培养活动,从而构成了战时文化教育发展的亮丽景观,在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历史上写下独特篇章。
(三)引发西方教会办学的震荡
西方教会在华办学历史悠久,构成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独特类型,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教会学校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及中国民族主义风暴的冲击而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调整,办学处于平缓态势,但到抗战时期却受到更为剧烈冲击。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原先在华活动,属于同盟国一些国家的传教士纷纷回国。1941年底,沦陷区一批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迁徙到大后方的传教士不足1000人。与战前相比,基督教传教士减少了大约5000人。许多教会中小学被迫解散或关闭,继续办学学校艰难维持,教学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四、关于沦陷区奴化教育之若干认识
抗战时期沦陷区奴化教育以宗主国利益需求为转移,围绕着培养奴性顺民及供其驱使专业技术者而展开。奴化教育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以宗主国的语言为重,它不仅成为官方的法定语言,而且成为教学的主要媒介。军事征服与精神奴化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两种伎俩,因为殖民者明白单凭军事力量只能占领一个民族的疆土,而思想文化上的征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其心,亡其国。因此,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目的都是灭亡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小学教育是日伪灌输奴化思想的主要阶段,因为小学生年少无知,思想容易受影响。所以,日伪采用各种方法对小学生们施以心理同化,使沦陷区的儿童生活在“顺民”的氛围中。日伪为培养供其驱使的御用技术人才,在各地创设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农业专科学校,开办职业学校服务于战争所需的经济掠夺,把许多中等学校的学生召集到日伪开办的社会教育团体新民青少年团进行训练。沦陷区的社会教育恰如一张无形的网,使沦陷区的广大民众难以摆脱日本侵略者的精神控制。
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持下的伪政权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大力兴办各级实施奴化教育的学校机构,其用心当然在于奴化中国的青少年,及其社会民众。但使他们始料不及的是,沦陷区学校并没有甘于被动地接受这种奴化教育。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感情深厚的大国,再加上中华民族传统教育的长久熏陶,使得奴化教育并不尽如日伪之意,无法达到日伪预期的目标。沦陷区爱国师生员工广泛开展对殖民奴化教育的揭露与批判,和日本军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涌现出一批反日抗日人才,他们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或是在今后的建设中,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及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只有把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化教育史同其殖民过程中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联系起来,才能认清其奴化教育的侵略本质。鉴于国际形势的风云际变,尤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国内抬头,更应把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奴化教育史同当前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相联系,才能发挥教育史研究的价值与功能。这就需要研究者加强以事实、史实说理,反击日本右翼势力。为了使日本侵略历史,包括奴化教育历史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还应继续加强反殖民、反奴化教育的思想及活动探讨。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1988.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吴洪成.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奴化教育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7.
[4]张菊杰.周作人年谱[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5]南开大学.中国现代史稿(下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6]经盛鸿.南京沦陷八年史(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日军祸豫资料选编:河南史志资料选编之四[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
[8]齐红深.日本对华教育侵略——对日本侵华教育的研究与批判[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9]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浙江大学校史稿[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2.
[1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