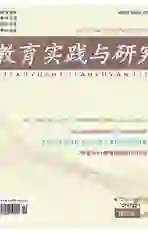学校纪律实践的“合理性”审辨
2021-06-22马甜
马甜
摘 要:学校纪律实践是学校所进行的纪律活动和行为的总称,它以社群性的应然规范问题为起点、以组织性的制度组合内容为过程、以协调性的人际互动关系为落脚。其合理性的内容关涉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大层面,前者诉诸对“成本——效用”的权衡与“程序——规则”的匹配,后者体认对自由的保障与尊严的关照。然而学校纪律实践中存在着工具合理性“膨胀化”与价值合理性“消解化”的矛盾,体现为“机械式”与“独霸式”的实践形态。因此,要实现学校纪律实践中工具与价值的双重合理性,关键在于手段有序高效与个体能动自由的平衡维持,以及程序正义恰当与个体尊严价值的相互根植。
关键词:学校纪律实践;社会行为;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
学校纪律实践以特定的群体对象、利益指向、组织规章和作用方式为必要条件,具体存在于与人、与学校纪律(制定、执行、修改等)相关的一切有意识的活动和行为之中。人们期望学校活动井然有序、学生遵守纪律,可学校场域中依然会出现“缺乏自由”“缺乏纪律”的现象。因此,回答这一问题的实质还需回归到对学校纪律活动“是否应该如此”的考量上,即对学校纪律实践这一行为本身的“合理性”进行审辨。
一、学校纪律实践:一种社会行为
韦伯在对“行为”和“社会行为”进行区分时指出“并非任何方式的人与人接触都具有社会的性质,而是只有自己的举止在意向上以别人的举止为取向时才具有社会的性质。”学校纪律实践是建立在特定组织范围内以及群体中人与人的一种“规则性”交往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规则”定义着组织内个体的角色身份以及边界,因此,学校纪律实践中人的交际行为不是在“纯粹”的“影响”下的举止,而是根据行为人“意向”的“取向”相互调节的活动。
从学校纪律实践的完整性来看,学校纪律实践的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
(一)学校纪律实践的起点:诉诸于社群性的应然规范问题
学校是一个社会关系的汇合点,学校纪律是调节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群体规范,既含有教育规范的意蕴,也体现社会规范的层面。需要注意的是,规范有两种必须严格区分的含义:一种是规定特定行为的应然规范,另一种是描述物与事件之间现实存在的一般关系的实然规范。学校纪律实践置于学校这一通过一定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相对稳定的群体之中,所蕴藏的规范性意识形态不是针对行为“真”或“假”的判断,而是产生于“善”与“恶”判断的特殊层面,转化为具体的内容则是:除包括社会所通行的一般准则外,还包括一种为本组织或群体所规定的特定的行为方式。这种学校组织中的应然规范成为了群体中的个体及其行为的“规”和“尺”。
(二)学校纪律实践的过程:围绕于组织性的制度组合内容
一种社会行为,特别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以参加者的一种合法制度存在的观念为取向的,这种有关制度的“适用”,其含义超过了仅仅受利害关系所制约的社会行为的“规律性”。学校本身是一种组织化了的社会单位,一般学校层面上的纪律实践的过程包括:纪律由哪些校内机关或机关委托的个人及群体按照何种规章制定与认可,在处理有关纪律问题时应遵从何种程序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规则”的集合被称之为制度的内容,用以界定人们交往中的行为边界,从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准则。
(三)学校纪律实践的落脚:具体于协调性的人际互动关系
作為群体性产物的学校纪律,功能在于维护学校组织内人际互动交往关系的稳定性。“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他是总体的一部分。他不可能在不与他的本性相矛盾的情况下,试图逾越强加于各个方面的限制”,这是涂尔干对人的“有限性”的论述。可见,纪律的独特价值使人性在纪律的“约束”中成为人性。一种集体的人际关系的协调表现在两大方面,其一,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场域内主体间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其二,是在组织内化解矛盾、排解纠纷的“非对抗关系”。学校纪律就是调节学校内人际关系的规则,由调节个体行为以及个体之间互动行为明确或隐含的标准、规章和预期所构成。因此,学校场域中的纪律实践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用于约束和协调个体的行为,并在这个过程中生成个体的社会化。
二、社会行为视角下学校纪律实践的“合理性”内容
从社会行为的微观层面考察分析学校纪律实践的“合理性”内容,需要把合理性概念引入社会学。当韦伯在论及具体的社会行为的合理性时,他将社会行为的意义细分为最基础的两种,一种是“目的合乎理性的”;另一种是“价值合乎理性的”。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倾向被称之为: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及其作用作为考量的重心的“工具合理性”,与把行为本身的价值和追求作为关注焦点的“价值合理性”。
(一)学校纪律实践的“工具合理性”
1.成本——效用权衡的计算性考量。对成本与效用的权衡体现出重视纪律实施技术上可能的计算以及技术能真正应用的程度。学校纪律实践成本的考量主要包括:首先,时间成本。强调对于违纪行为处理的及时性,保证手段实现和效果转换的快捷性,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最直接的效果。其次,运作成本。即在实行纪律处分的过程中,强调精简纪律序次,严格控制无效益的成本,或者避免在使用一种纪律手段时产生其他额外成本。最后,机会成本。即选择一种纪律手段,将损失最小化。另外,除实施过程中的时间、运作和机会成本外,还有对纪律实施结果的风险成本的考量,即对手段造成的危害预估显于既得效益,是对得不偿失的预防。这一层面的纪律实践过程集中于对成本的核算和管理结果的有效性考量。
2.程序——规则匹配的预测性输出。在对不合规范的行为施予否定性的制裁时,学校一方往往诉诸于纪律实践中一套“程序化”方法论的操作,即与纪律规章设定下所匹配的“裁判——定性——决策——处分”程序过程。通常对违规、违纪的学生,会视其性质和过错严重程度的不同,做出谴责、告诫、记录过错等纪律处分决定。这体现出程序操作的两大比例原则,一类是拟给予的处分与学生所犯过错的严重程度成比例的实质性比例原则;另一类是学生拟受处分的程序与其过错程度、所受处分的严重程度相适应的程序性比例原则。这两类比例原则体现了在程序具体、定性明确的规则先行前提下,保证对于处分违纪行为的确定性,以及个体对自身行为能给予的衡量预估。
(二)学校纪律实践的“价值合理性”
价值合理性立足于信仰、信念、理想的合理性基础之上,关注的是行为本身价值和意义的创设。“行为的意向不在于行为之外是否能有所成就,而在于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本身。”具体表现为以精神维度支撑为导向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合理性行为。
1.价值判断:自由的保障。学校纪律实践的行动逻辑是为了建立稳定的秩序,以保障个体的自由。合理的纪律实践在应然的价值层面上必须是既能满足人们对秩序的需求,同时又能满足人们对自由的需求。因为纪律的构建来源于群体的契约认同,最终走向个体对规范的自觉转换。这其中的过程必然依赖于纪律运作中对自由的理解,一方面,避免学生成为无关紧要的习惯和礼仪的奴役;另一方面,用规范来约束人们完全的自由意志,从而使他人的自由意志与个体自身的自由意志相互协调,互不侵犯。所以说,学校纪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既是目的,也是结果,前者在于其本身丰富人的自由,后者在于它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2.价值选择:尊严的关照。尊严常与人格挂钩,指向人的自尊心和自爱心,每个正直、品质端正的人,都有他的自尊心和自爱心,不允许别人侮辱和诽谤。在纪律实践的运作中,尊严价值应被理解为:主体间的平等和过程中的透明,即表现在任何纪律当事人的行为和关系都是诉诸于共同层面的,以及意味着尊重一方纪律当事人的意见,不片面认定事实,剥夺当事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力。
价值合理性偏重对行为本身的意义判断,学校纪律实践这一社会行为的应然价值层面在于尊重人格自由发展与维护人性尊严的追求与价值取向,反映在个体本身,即纪律承受方对于纪律实践拥有不受胁迫的选择能力和不去妥协的自主判断。
三、单向度的合理:学校纪律实践“合理性”的矛盾与分裂
学校纪律实践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处于形形色色的不同关系中。然而,从工具合理性的立场出发,“价值合理性总是非理性的存在,而且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它就越是非理性的,因为对它来说,越是无条件地仅仅考虑行为的固有价值(纯粹的思想意识、美、绝对的善),它就越不顾后果。”但是,绝对的工具合理性也仅仅是一种假设出来的边缘情况。也就是说,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有一股巨大的张力,一方是行为者和行为本身对意义和价值的要求,另一方是对普遍客观性的推崇。这种矛盾与分裂在学校纪律实践追求合理化的进程中,很容易走向工具合理性支配和价值合理性消解的单向合理过程。
(一)工具合理性的膨胀转化为暴力的控制
1.标准掩盖事实——“机械式”的合理化。第一,工具合理性膨胀过于追求效用至上原则,使得个体把功利目的和实用效果当作衡量学校纪律实践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这种取向在某一社会行为中独占鳌头,往往容易走向以效果最大化为唯一原则,因此,有计划地统筹、分配和运用“资源”,趋向经过成本核算与有效管理才能取得最大回报。一旦学校纪律实践将对纪律规则和纪律规范的宣传与说教视为最合理的手段之一,并大力致力于此,其本身就失去了真实的意义。第二,工具合理性膨胀着重充斥理性计算原则,使得学校纪律实践从人与人的角色互动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等价交换关系。赋予职能的角色必须抑制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主观意志,以适应不停运转的学校纪律的程序机器和指令,这个过程必须精密细致。纪律实践的每一阶段都渗透着理性的计算,“通过理性计算,每个人成为这架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都关心的是自己能否成为一个较大的齿轮。”人终究被造就为驯服的“秩序人”。
2.手段取缔目的——“独霸式”的合理化。第一,诉诸于权力的运作,视人对人的压迫为合乎权力意志本质的行为。由于学生与学校之间并无紧密的经济联系,且教师对学生并无有效的物质刺激手段,因而,当教师采用规范的约束手段来说服学生服从和参与而未能收到应有效果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辅之以乃至完全转而采用训斥等强制的手段。这时,纪律规范的约束对于学生的强制性,通过教师行为从潜在形态转变为显在形态,带来的是一种建立在塑造与被塑造、支配、隶属和屈服之上的压抑的秩序,其实就是把学校纪律变为对受教育者的改造和钳制。这样的“纪律虚伪”实际上都是教育暴力存在的证明。第二,倾向于命令的强制,被一种显在的强化控制的意识形态所指引。这是一种从“自主——反思”式的参与到“权威——服从”式的参与,走向一种“限制越多、控制越好”的思维循环。一方面体现在学校纪律实践中的法制思维,即按照明文规定与照章办事,遵循的是一种“有张可循、违章必究、执行必严”的逻辑,但是学校纪律实践的强制性,不是法律的强制性,因为纪律的形成是在某种结构和一般规则之下学校场域内的个体互动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纪律实践中的惩罚偏好,即为防范学校权威被违规行为所侵蚀而依赖于惩罚,将违纪行为直接与惩罚挂钩,以使学生个体产生思维定势,因为他们害怕被惩罚。如果学校的纪律活动只停留在命令集中控制之下,那么纪律的建立也只能停留在最基本的层次——他律的层次,而很难进入到自律的境界。
对于学校来说,有效率的手段设置是必要的,但是這种效率本身不是一个目标,它与秩序是两回事。另外,最容易达到目的也并非最适合学生的手段,往往容易走向一种只关注结果的“动机论”。
(二)价值合理性的消解演变为生存的失落
缺乏爱和关怀的关联,人与人之间便不会存在任何内在联系,只能凭借外在的契约而生存在一起,这是一种走向疏离的单子式存在,把自我视为一种实体。意义和价值的消解,表现在人对于学校纪律实践是极为纯粹的人,看似“自足”,实则是“无我”存在。这种状态下的人都是孤立的,往往衍生出学校纪律实践中的恐惧与冷漠。
1.意义遮蔽:纪律实践中的恐惧。学校纪律实践向工具价值取向的过分偏离,容易放大纪律的原始约束和控制属性。教师在秩序化和程序化的维稳追求中,会不经意就自封为压迫性的权威化身,打着“爱”的名义,掩饰没有“爱”的内涵,麻痹人的判断能力。学生不敢质疑、不敢反抗,所谓的有纪律的个体要始终接受规范和原则的指导,如若不然,个体就会面临着被惩罚的危险,这是恐惧在支配着个体的行为,而不是其自身对纪律的自觉体认导引着个体的行为。
2.情感排挤:纪律实践中的冷漠。纪律冷漠是一种特定的畸变的纪律心理和纪律行为。主要体现在两类主体上,一类是教师个体的冷漠,即教师对受纪律处分对象及其行为的关怀道义冷淡,另一类是学生个体的冷漠,即学生的纪律感和遵守纪律现象与行为的麻木存在。前者是行为者践行纪律实践时精神和意义的遮蔽,后者是纪律实践站在个体生命发展的对立面,未能成为个体内心自觉自愿去追求的事物。
四、学校纪律实践中工具与价值双重“合理性”的实现
“合理性”本身既包含社会行为对价值与信仰的要求,又包含各种具体目标的达成与实现,以及对实现目标之手段的效用最大化的可计算性考量。价值合理性指向“应然”状态的意义关系,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工具合理性指向“实然”状态的现存事实,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而作为人类认识活动之一的学校纪律实践离不开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综合考量,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双重实现,这不是否定一方,单纯强调另一方。
拥有工具合理未必有价值合理,因为仅有工具合理是不够的,但是工具的合理也应建立在价值的合理性基础上。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制度应该符合双重要求,即在价值合理的终极原则下,制定出合理的手段与程序,以发挥纪律实践的价值功能。
(一)手段有序高效与个体能动自由的平衡维持
手段的有序高效是学校纪律实践的基本要求。这首先是因为手段的有序高效是维持纪律存在的依托。纪律作为一种规范存在,如果没有一定的效度作支撑,很难保持自身的稳定性,从而受到质疑,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和谐冲突。其次,手段的有序高效可以满足个体对纪律实践中的行为选择和事件发生的可预期性考量。在稳定、有序的前提下,人们对于自己在某种特定场合应如何行动以及他人将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何种反应可以有一定的预期。
个体的能动自由是学校纪律实践的又一基本要求。这首先是因为人的自由本性。正因为人是自由的,人具有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人才具有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能力。但是实现自由的能力和条件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对另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妨碍都会使人的自由名存实亡。
然而,实然层面的矛盾在于纪律实践对手段的有序高效的过分追求,反向则会造成个体能动自由的丧失。维持手段的有序高效与个体能动自由的平衡在于:如何在学校纪律实践中实现二者的统一。
第一,学校纪律必须具有自身改进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在纪律具有适应学校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弹性,其规范的内容能够根据个体认识的不断深化及时作出回应。因为工具合理与价值合理的终极诉求在于判断是否有利于人类的最根本利益的实现。
第二,学校纪律实践的运行维持要为人所认识,受人所坚守,即从外在维持走向内在维持。外在维持是指根据学校所提供的判断个体行为的善恶标准行事;内在维持是指个体将规范内化于自身意识中,自觉地遵守规范行事。一旦实现内在维持,那么学校纪律实践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都会被觉悟,形成体认,个体不再感觉学校纪律是不可违抗的权威的体现,而是其真实地反映了自身的需求。
(二)程序正义恰当与个体尊严价值的相互根植
一方面,评价程序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使人的尊严获得维护的程度,另一方面,尊严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只有它能够保证程序的正当性。将程序正义与深厚的尊严思想连结起来,能为学校纪律实践的工具合理和价值合理的双重统一提供坚实的基础。
程序本身的价值标准要包括平等、透明、理性和参与等观念。在此,我们所关心的关键问题是:在学校纪律裁决的制定过程中使人的尊严是受到尊重还是损害。这种体现于程序本身之中的价值,是以个体普遍的人性为基础而提出的,这些价值能否在实施中得到实现,也取决于裁决制定活动采用什么样的形式。(下转第38页)(上接第34页)此外,包括参与、平等、理性等在内的程序价值的正当性,从不同的角度维护了当事人作为人的尊严,使他们成为主动影响裁决结果的程序主体,而不是消极等待“官方处理”的程序客体。
可以说,程序是用来实现学校纪律规范的工具,程序本身的“善”要取决于它在准确发现事实真相后和正确适用规范方面的能力。因此,程序正当的理由在于对有关规范加以正确适用。其核心就是强调在学校纪律实践的纪律程序设计和运作中应使哪些受利益直接影响的人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从而具有个体的尊严。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吴洪伟. 当代中国中小学纪律实践价值取向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3][法]爱弥儿·涂尔干.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美] 詹姆斯·马奇.规则的动态演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蘇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6]李仁燕. 高校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论[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
[7]王彩云,郑 超.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及其方法论意义——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二分法[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02).
[8]成 然.纪律与现代性——从韦伯与迪尔凯姆的观点看[J].浙江学刊,2005,(04).
[9]金生鈜.论教育权力[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02).
[10]刘海波.”规则与秩序”和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EB/OL].www.sinoliberal.netconstitu.
[11]鲁 洁.关系中的人:当代道德教育的一种人学探寻[J].教育研究,2002,(01).
[12]麻美英.规范、秩序与自由[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6).
[13]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J].中国法学,20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