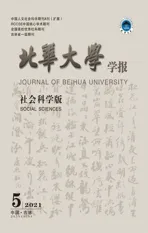日军参谋本部对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的研究
2021-06-21耿铁华
耿铁华
1883年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间谍酒匂景信从中国带回一部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开始组织人员进行研究。由于双勾加墨本是由131张纸组成,需要将其逐一连缀起来,识读文字,考释碑文所涉及的历史与日本的关系。这一过程,出现了很多错误。根据档案和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弄清日本陆军取得双勾加墨本碑文的情况、研究的目的与相关问题是必要的。
一、参谋本部的建立与派往中国军事人员的间谍活动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国家军事实力的增强,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为了实现吞并亚洲的预想,不断增进军事建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对外协调和作战能力。1878年(明治十一年)11月,废除陆军参谋局设立参谋本部。由原任陆军卿山县有朋中将担任参谋部长,大山岩中将担任次长。下设管东局、管西局和总务课,分管各方军事事务。[1]参谋本部直属于日本天皇,可直接参与天皇对于内外战争的决策,在国家军事行动方面具有极大的权力。其中管西局不仅管理本国中西部监军部及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四镇地区军管所军事、地理、政情事务,还要兼管朝鲜乃至中国沿海及陆地的政情。[2]因此不断派出间谍到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地区调查清军布防、当地政务,绘制地形图,以备未来军事行动之用。据记载,参谋本部成立第二年(1879),日本以派驻武官和汉语留学生的名义向中国派出十多名将校军人,开始在中国进行军事调查为主的间谍活动。[3]当时牛庄就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设在东北的一个重要据点。
牛庄是一座知名的古镇,属辽宁省海城市管辖,东距海城20千米,北隔太子河与鞍山相望,西面是盘锦,南面接近营口。明清之际是辽宁南部的水旱码头,商贾往来的繁华之地。
《牛庄镇志》对于牛庄的来历、建置沿革记载得很详细。牛庄城始建于明初,属辽东都司海州卫,当时筑有土城。清代牛庄属奉天府海城县,皇太极重修牛庄城,用青砖砌墙,东西北三面设置城门,驻兵防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1858年5月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通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4]依照中英《天津条约》,1861年4月3日牛庄正式开埠,英国在此设立领事馆,各国商人陆续前来经营,一些传教士也前来传教,牛庄逐渐成为一座国际商港。(1)关于牛庄城、牛庄港、牛庄口岸地理位置的变化及其不同说法的出现与辨证,张士尊先生在《也谈“营口代牛庄开埠”》一文中已经论述得十分清楚,可供参考。
1880年前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已经派人到达牛庄,并以此为据点调查搜集当地军事、商业、地理情报,测绘地图。
证据之一,日本宫崎县综合博物馆收藏着陆军省派遣酒匂景信前往中国的一纸公文(图1)上面的文字是:“陆军炮兵少尉酒匂景信,御用有之清国へ被差遣候事,明治十三年九月三日。陆军省。”[2]217明治十三年九月三日是1880年9月3日,也就是说,酒匂景信于1880年9月3日被派往中国。

图1 陆军省公文
证据之二,佐伯有清记载,酒匂景信是明治十三年九月接受差遣奉命去中国,十月六日同玉井胧虎少尉渡海到达上海,再到北京向北,先后在北京和牛庄生活4年。接续島弘毅、伊集院兼雄等人的“满洲”调查任务,担任东北及“满洲”地区军事要地资料的搜集与调查工作。[2]211
证据之三,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收藏的酒匂景信在牛庄写给参谋本部长官大山岩的亲笔信件。陈述其在牛庄所承担秘密任务完成的相关情况,信上写的时间是明治十六年八月八日。(图2)[5]270-271明治十六年八月八日是1883年8月8日。

图2 酒匂景信签名信件
从炮兵少尉酒匂景信受命到达牛庄一带活动的情况,可以证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中国
沿海地区进行军事调查等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资料档案涉及军事机密,难以看到更具体、更详细的内容。
酒匂景信,日本都城藏马场(都城市藏原町)人,1850年出生。一些档案资料和登记表格中曾记为酒勾景明、酒勾景信、酒匂景明、酒匂景信等。经过中塚明、佐伯有清等学者的辨证,加上资料档案中的公文、书信签名证实,酒匂景信是正确的,酒勾景明、酒勾景信、酒匂景明等则为误写或误记。[2]4-5[3]
根据李进熙和佐伯有清等学者的记载,现将酒匂景信经历的简略列表如下(见表1):
酒匂景信的经历中有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一件是1880—1883年,在北京、牛庄等地搜集了一批军事情报,包括辽东沿海地区清朝的军事防御力量和军事要塞及其相关的地图,为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持,并因此获得嘉奖。另一件是1883年末取道盛京、平壤回国途中获得了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上交参谋本部进行研究,从中寻找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历史依据。两件事虽不相同,却又有密切联系。本文所讨论的则是酒匂景信获得双勾加墨本与参谋本部组织的研究。

表3 酒匂景信经历简介(2) 此表综合李进熙《广开土王陵碑研究》(日本吉川弘文馆1974年增订版第146-147页表格),佐伯有清《好太王碑与参谋本部》(日本吉川弘文馆1976年版第213-215页表格)进行删节整理。
二、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的获得
1883年8月8日,在牛庄完成秘密侦查任务的酒匂景信,向参谋本部长官大山岩发出了秘密报告书,准备返回日本。9月3日,酒匂景信向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步兵大佐桂太郎提交了到中国盛京和朝鲜旅行的申请。实际上,是借机到中朝边界鸭绿江一带进行军事侦察,了解当地军事防御情况。10月接到命令,取道盛京,渡过鸭绿江到达朝鲜,然后归国。如果10月接到归国命令之后,酒匂景信从牛庄出发,经过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义州,很可能在此期间得到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从日本参谋本部最早的研究论文中可以得到证实。
资料一:1884年7月,海军省军事部第五课任御用挂的青江秀接受命令,对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进行研究,写成《东夫余永乐太王碑铭之解》。在附言中写道:
近来,某报称:满洲盛京省与朝鲜交界处之鸭绿江上游,自古即在水底埋有一大石碑。最近从盛京将军处得知,以大量人工,终于将该碑掘出。当刷洗石面之际,日本人某恰在该地,拓出之后乃持而归之,藏于参谋本部。该碑高凡三丈,宽一丈五六尺,字体为绝好隶书。只因年代久远,几经磨损,文字不能卒读者有之。又当该碑掘出之际,另得一高八寸宽四五寸许之奇形瓦一枚。瓦之右侧面刻有“大王之墓安如山固如岳”十一字云云。[5]4
资料二:1889年《会余录》刊登《高句丽碑出土记》,记载如下:
碑在清国盛京省怀仁县,其地曰洞沟,在鸭绿江之北,距其上流九连城八百余里。(清国里法,以下仿之)地势平坦,广三四里,长十二三里。中央有旧土城,周围五里余,内置怀仁县分县,即古之令安城也。距此城东约四里许,离江边三里许,山下有一小溪,则碑所在也。据土人云:此碑旧埋没土中,三百余年前,始渐渐显出。前年有人由天津雇工人四名来此,掘出洗刷,费二年之功,稍至可读。然久为溪流所激,欠损处甚多。初掘至四尺许,阅其文,始知其为高句丽碑。于是四面搭架,令工毡拓。然碑面凸凹不平,不能用大幅一时施工。不得已,用尺余之纸,次第拓取。故费工多而成功少,至今仅得二幅云。日本人某适游此地,因求得其一赉还。碑已掘出者,其高一丈八尺,前后广五尺六七寸,两侧四尺四五寸,埋没土中者,尚不知有几尺。面南而背北,四面皆刻有字,南十一行,西十行,北十三行,东九行,通计四十三行,每行四十一字,大略一千七百五十九字。字长短不齐,长者五寸,短或三寸,刻深至五六寸。其残欠者凡一百九十七字。碑之旁有一大坟,宛然丘陵,而其形倾欹,势如被压,盖高句丽盛时,葬永乐太王之处。某闻其中有古砖,悬金募购,得数枚而还,今藏其家。(3)《会余录》是日本亚细亚协会主办的刊物,1889年第5集1-3页刊登的《高句丽碑出土记》一文无署名。有人认为是酒匂景信的讲述,由橫井忠直记录,内容与橫井忠直手写的《高句丽古碑本之由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大体相同。
资料三:1889年的《会余录》上还刊载了橫井忠直撰写的《高句丽古碑考》,文中对碑文内容进行了说明,没涉及双勾加墨本来源,原稿后有“明治廿一年十月,橫井忠直识”:
— 碑文,前无款题,后无年月,据文考之,则颂第十七世好太王功德,且铭记守墓人烟户者,而其王殂之三年甲寅所建也。
— 碑文,凡分三大段,起首至以永后世焉为第一大段,提立碑纲领。自始祖说起,自其言曰,至村一千四百为第二大段,历叙好太王武功。自守墓人烟户至终,为第三大段,规定守墓人烟户,揭好太王遗训为法。
资料四:后来在“无穷会”发现了橫井忠直撰写的《高丽古碑考》汉字稿本,原稿后有“明治廿一年十月,橫井忠直识”,开头记载了双勾加墨本的来源:
— 高句丽古碑拓本者,僚友酒勾大尉清国漫游中所获也,事有可资考证,字亦浑朴可爱,乃缩写其文,略附鄙考,颁诸同好。
— 碑在清国盛京省奉天府怀仁县洞沟,洞沟在鸭绿江上流,距九连城凡我一百余里,陵谷变迁,埋没地中,既而为溪流所涤,三百年来,稍露头角,渐次现出,数年前,盛京将军某奇之,命工夫数十名掘之,凡二阅年,始见全身,而尚未及其基址云。
— 碑石,长凡一丈八尺,幅员、前后凡五尺六七寸,左右各四尺四五寸,面南而背北,刻字四旁,南十一行,西十行,北十三行,东九行,通计四十三行,每行四十一字,亡虑一千七百五十九字,字大小不齐,大者长至五寸,短者仅三寸,刻深五六寸云,其残欠者,凡一百九十七字。
— 碑文,前无款题,后无年月,据文考之,则颂第十七世好太王功德,且铭记守墓人烟户者,而其王殂之三年甲寅所建也。
资料五:另外在“京都大学”还发现了橫井忠直撰写的另一种《高丽古碑考》汉字稿本,原稿后有“明治廿一年十月,橫井忠直识”,开头记载了双勾加墨本的来源:
— 高句丽古碑拓本,僚友某清国漫游中所获也,碑在盛京省奉天府怀仁县洞沟,洞沟在鸭绿江上流距九连城,凡我一百余里,陵谷变迁,埋没地中,既而为溪流所涤,三百年来,稍露头角,渐次现出,数年前盛京将军某奇之,命工夫数十名掘之,凡二阅年始见全身,而尚未及其基址云。
— 碑石,长凡一丈八尺,幅员前后凡五尺六七寸,左右各四尺四五寸,面南而背北,刻字四旁,南十一行西十行北十三行东九行,通计四十三行,每行四十一字,亡虑一千七百六十一字,字大小不齐,大者长至五寸,短者仅三寸,刻深五六寸云,其残欠者,凡一百九十七字。
— 碑文,前无款题,后无年月,据文考之,则颂第十七世好太王功德,且铭记守墓人烟户者,而其王殂之三年甲寅所建也。
资料六: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橫井忠直手写本《高句丽古碑本之由来》:
是古碑本、明治十七年、陆军炮兵大尉酒匂某、在‘支那’旅行途中、购得并带回者、古碑所在地名曰洞沟、洞沟在鸭绿江上流、距九连城八百余里[2]61
以上资料一、二均记载为“日本人某”在当地获得拓本。资料三无碑文获得记载。资料四明确“高句丽古碑拓本者,僚友酒勾大尉清国漫游中所获也”。资料五则隐去人名,记为“高句丽古碑拓本者,僚友某清国漫游中所获也”。资料六为“陆军炮兵大尉酒匂某,在支那旅行中获得”。也就是说,以上原始记录中明确了参谋本部的双勾加墨本是日本人酒勾或酒匂大尉在中国获得。
1898年,日本学者三宅米吉记载:获得双勾加墨本的“为一陆军炮兵大尉酒勾某。”[6]
1918年,日本陆军上将押上森藏在历史地理学会讲演时说道,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是陆军炮兵大尉酒勾景明得到并带回日本。[7]
1966年,朝鲜朴时亨教授的著作中采用此说法。[8]
1972年,李进熙在书中记载:“日本参谋本部的酒勾景信1884年(明治十七年)带回的广开土王陵碑‘拓本’。”第六章则多处记作“酒匂景信”。[9]
据佐伯有清记载:“明治十六年(1883,光绪九年)秋,参谋本部员清国派遣军人酒匂景信在现地获得拓本(双勾本)一本将其带回日本,从此成为好太王碑文研究的开端。”[5]4时间与酒匂景信到兴京、义州一带旅行相吻合。也就是说,他得到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是在1883年10月前后。
可以肯定,是日本间谍酒匂景信在中国得到的双勾加墨本,并将其带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那么,酒匂景信是否到过好太王碑所在地通沟呢?
资料一、二 记录“日本人某恰在该地”“日本人某适游此地”,即是在好太王碑所在地得到了好太王碑。资料三无记双勾加墨本的来源。资料四、五 则记载“僚友酒勾大尉清国漫游中所获也”“僚友某清国漫游中所获也”,只说是在“清国漫游中所获”,并没有具体地点。
后来的记录与研究,都是根据资料一、二或四、五、六得出的结论。资料一出自青江秀,1884年7月撰写,时间最早,其根据应该是酒匂景信的介绍。资料二公布的稍晚,却与资料一最为接近,虽然没有署名,有人以为是酒匂景信的记录。无论是青江秀、还是橫井忠直,他们的身份都是军人,接受参谋本部的命令对双勾加墨本进行研究。他们都是酒匂景信的同僚,关于双勾加墨本的由来以及碑石所在地的状况,都应该是酒匂景信介绍的记录。资料记载中的差异,一方面是由几次介绍的不同或听者记录的差异所造成,另一方面则是在《会余录》发表时处于保密而只说“日本人某”而不提酒匂景信之名姓。也许酒匂景信向青江秀和橫井忠直讲了他是在好太王碑所在地得到的双勾加墨本。但是从《会余录》公开发表的碑石状况看,是颇令人怀疑的。[10]
其一,碑石所在地是通沟而不是洞沟 。《高句丽碑出土记》记载,好太王碑在怀仁县境内,在鸭绿江之北,大体是准确的。“其地曰洞沟”则是错误的。怀仁建县当年,在通沟设巡检。《奉天通志·崇实传》《东华录》光绪二年二月丙子,王志修《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中都有“通沟巡检”的记载。
其二,《高句丽碑出土记》有关“距其上流九连城八百余里”的记载更是错的离谱。九连城在安东(今丹东)附近,属于鸭绿江下游,根本不在通沟的上游(上流)。通沟与九连城的距离八百余里相差太多。清代通沟至九连城的陆路距离约为565里左右,水路约为484里。若亲自到过通沟,驿站会告知准确距离的。
其三,《高句丽碑出土记》记载:“中央有旧土城,周围五里余,内置怀仁县分县,即古之令安城也。”此即高句丽国内城,衙门前有“怀仁县通沟巡检”的牌子,从未有“怀仁县分县”之记载。《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三国史记》都有“国内城的记载”。“古之令安城”,或与《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安市城、安地城相混淆,而安市城、安地城距离通沟何止千里。
酒匂景信得到双勾加墨本,应该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件大事,如果是在通沟得到,不仅没必要隐瞒,而且还要大肆宣扬一番。可在呈献拓本的公文上却只字未提拓本是从何得来,各种记录也没有明确记载。酒匂景信在向管西局局长提出旅游申请时,也只提到盛京、义州,说明当时他主要行经地点是盛京和义州,并非怀仁和通沟。作为一名驻外间谍,遵守上峰指令,严格按经费规定路线行走是必须的,不可任意改变行程。
其四,对于好太王碑的现状记录更是错的离谱。《高句丽碑出土记》记载:“据土人云,此碑旧埋没土中,三百余年前,始渐渐显出。前年有人由天津雇工人四名来此,掘出洗刷,费二年之功,稍至可读。”如果到过碑前,从拓碑人手中买到拓本,绝不会相信这些传言。碑石巨大,一直立在原地,从未埋没土中,更未移动,一眼便可看清。只有那些从未到过通沟碑前的人才会道听途说、漏洞百出。此外,如果到过碑前,就会发现碑文第三面的文字是十四行,而不是十三行,刻字深度是否达到四五寸更是一看便知,不会有如此明显差错。还有墓砖上的文字很好认“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与“瓦上”文字“大王之墓安如山固如岳”差距也很大,且砖瓦不分。可以证明错误在于传闻,而非亲眼所见。
其五,如果酒匂景信亲自到通沟购得拓本,在好太王碑现场会将若干小张拓片的顺序核对清楚,编号记录,防止带回后弄错拓片顺序而造成错误,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事实证明,他对拓片编号顺序并不清楚,致使多处错位,造成语句不通的情况。酒匂景信本人也毫无办法,说明他对碑石及其文字根本不了解,一些情况只是传闻而已。
酒匂景信是一位精通汉语,又经过多年特殊训练、有经验的军事间谍,到盛京等地考察,取道朝鲜义州返回日本。出于职业的本能,对于所到的地方,所见的古建筑、古文物遗迹和附近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自然方位、距离远近、重要标志及其文化特点,都会极为敏感,都会留下准确的记忆或记录。如果他到达通沟,懂得汉语的军人绝不会忽略中朝边境战略地位明显的通沟巡检地,绝不会把“通沟”误记成“洞沟”。历尽艰辛,好不容易见到好太王碑,一定会留下照片、绘图和详细测量结果。而且会将这些重要情报资料连同好太王碑拓本一起带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然而,这些最为简单易行的工作都没有见诸记录,也可以说是根本没做。不要说一位资深的军事间谍,就是一位普通游客,见到好太王碑这样高大的碑刻也会有明确的记忆和记录。因此,酒匂景信没能提供通沟及好太王碑真实的资料记录,绝不符合经过特殊训练的军事情报人员的性格特点与技术本能。依此推断,他很可能是在盛京、义州的途中买到双勾加墨本,带回日本,同时带回了一些错得离谱的传闻。
三、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的研究
参谋本部得到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之后,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人进行研究。首当其选的是青江秀和橫井忠直。青江秀出生在德岛县农村,专门攻读过汉学,曾在海军省军务局负责编写日本海军历史,被认为是懂历史有学问的军人。因此,调入参谋本部研究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橫井忠直是小苍县人,出生在儒医世家,担任过中学教师,汉文功底深厚。1880年进入参谋本部任编纂课员、陆军大学教授。奉命与青江秀一起进行研究。由于参谋本部研究的政治企图和他们对于高句丽历史、文物、碑刻相对陌生,致使碑文的识读、解释与研究出现许多错误,给后来的研究造成误导和不良影响,需要严肃认真地进行批评。
第一,碑文识读的混乱。好太王碑高6.39米,幅宽1.34—2.00米不等。四面环刻汉字隶书碑文,原有文字1 775个,少部分文字因长期磨损与火焚除苔的裂痕伤损,尚有1 600字左右可以识读。酒匂景信带回去的双勾加墨本是好太王碑发现后不久流行的拓本。其方法先将小块纸敷在碑上,轻轻捶拓,现出文字影像,再用墨勾出边缘,然后用墨将字外涂黑,白字黑地,清晰可辨。由于拓者以意描画,容易造成讹误。参谋本部的双勾加墨本应该是最早的拓本之一。共有131张纸:第一面30张,第二面28张,第三面40张,第四面33张,酒匂景信带回去的双勾加墨本,原本是有编号的,按照顺序排列,便可以进行识读了。当地的拓碑人初天富不识字,他做的编号只是一种标记,如“一元”“〡一”“〢一”“三〢”等,标号模糊,青江秀与橫井忠直又不熟悉好太王碑,尽管知道碑文有四面,在编排时,还是出现不少错误。特别是碑文第二面和第四面,错乱较多。第1—9行,下面第29—41字,有大小7张纸,原本应该是排在上面第1—13字的位置上。这样上下颠倒,整面文字全都错了位置,不仅联不成句子,也与原来的碑文大相径庭。第四面第1—4行,排在下面第38—41字,一张纸,本应该是第2—5行第1—4字,这样一串,使得碑文第1—5行的文字都出现错乱。[5]10-13
1889年《会余录》第五集刊印了一幅重新排列的碑文局部拓片,左下角的“後”字,根本不是这一段的文字,不知是从何处移过来的(见图3)。这就说明,至少在1889年,参谋本部在得到双勾加墨本5年之内,都没能将碑文的顺序排列准确。因此,其释文的混乱和错误就可想而知了。
1893年参谋本部又得到了一种好太王碑拓本,被称作小松宫拓本加以介绍。对于酒匂景信带回的双勾加墨本,也被粘接成4大幅,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11]学术界一般称之为“酒匂景信双勾加墨本”或“酒匂双勾加墨本”“酒匂本”(见图4)。

图3 《会余录》第五集

图4 酒匂景信双勾加墨本保存现状
第二,碑刻年代的误判。碑文是用中国古代传统干支纪年的,如“甲寅年九月”“永乐五年岁在乙未”“六年丙申”“九年己亥”“十年庚子”“十四年甲辰”“十七年丁未”,等等。最初的研究中,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也有一些错误。
通过“甲寅年九月”,青江秀推断,把广开土王之死推定在东晋义熙九年癸丑,甲寅则为义熙十年。认为立碑在义熙十年(414)应该是正确的,然而,广开土王的死亡定在义熙九年(413)则是错误的。另外,他把“辛卯年”推定在东晋咸和六年(331)则又提前了60年。[5]15-17
橫井忠直却将立碑年代“甲寅年九月”下推了一个甲子,成为公元474年,[5]16这就大错特错了。不仅如此,更是导致以下的诸多干支纪年都后推了60年。对于这些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错乱。与中国正史《高句丽传》难以对应,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也完全不同。类似的错误不胜枚举。
第三,碑文所涉及历史的错误解释。青江秀、橫井忠直等人,对于双勾加墨本的制作与编号所知有限,加上酒匂景信缺乏对碑石、碑文状况的起码了解,难以提供更多的依据,致使拓片连缀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第二面和第四面,上下小拓片颠倒串位,导致文字差错不通畅,解释起来错误更多。比如第一面的“辛卯年”纪事,第二面的“九年己亥”纪事,“归王请命”条,“十年庚子”纪事,第三面“十四年甲辰”纪事等,不仅是年代方面的错误,还有一些历史记录的错误。他们依据《日本书纪》《新撰姓氏录》《古事记》等日本文献中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记录,否认朝鲜史书的记载,随意解说4—5世纪东亚诸国的关系,颠倒历史,宣扬“皇国史观”“侵略史观”。违背了尊重历史事实进行研究的基本原则,遭到了日本一些正直学者的批评 。
那珂通世、三宅米吉、阿部弘藏、吉田东野、落合直澄等人,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引用好太王碑碑文内容与干支纪年,证明日本古史纪年的错误,并展开了关于历史纪年的争论。日本军国主义的当权者和军人史家,罗织罪名,打压正确意见,并给他们加上“无视国体”的罪名,扼杀正义史学家的言论和著述,使好太王碑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持在军国主义者手中,为侵略战争服务。
第四,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的研究,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成立,就是为了加强对外侵略的军事指挥权。不断向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派出间谍,刺探军事情报,勘测绘制地图,搜集各地政治经济发展资料,目的在于做好军事侵略的准备,努力寻找借口和历史依据。
参谋本部在1882年就完成了《任那考》,摘录《日本书纪》《朝鲜史略》《大日本史》等书籍中有关神功皇后远征新罗的传说,认为在4世纪后期,日本曾在朝鲜半岛南部设立统治机构——任那日本府。随时准备恢复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1884年初,得到了酒匂景信带回的双勾加墨本。碑文中不仅有“倭以辛卯年来”的记载,还有“急追至任那加罗”等文字。一时间以为找到了侵略的依据和借口,于是才命令青江秀、橫井忠直等人进行研究。
关于“倭以辛卯年来”的一段文字,见于碑文第一面第8行第34字至第9行第24字。多年来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论,被东亚各国学术界称之为“辛卯年”条或“辛卯年句”。关于文字的识读主要有以下几种:
由于学者们的释文不同,断句不同,解释也有很大不同。学者们从历史研究出发,存在分歧是正常的。而参谋本部是从寻找侵略别国历史依据出发,认为好太王碑所记录的历史,是证明4世纪以后日本势力已经进入朝鲜半岛的真实史料。认为“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一段碑文中的“倭”就是“大和民族军队”“日本军队”,就是日本曾经占领朝鲜半岛的历史依据。“任那加罗”就是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这种对外侵略的历史观,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朝鲜半岛发动侵略战争,对邻国犯下了累累罪行,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痛苦和灾难。日本参谋本部对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的研究完全是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二战以后,各国历史学家不断揭露和批判参谋本部研究的内幕,才使得好太王碑及其拓本研究回归正常历史研究领域。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需要深刻认识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