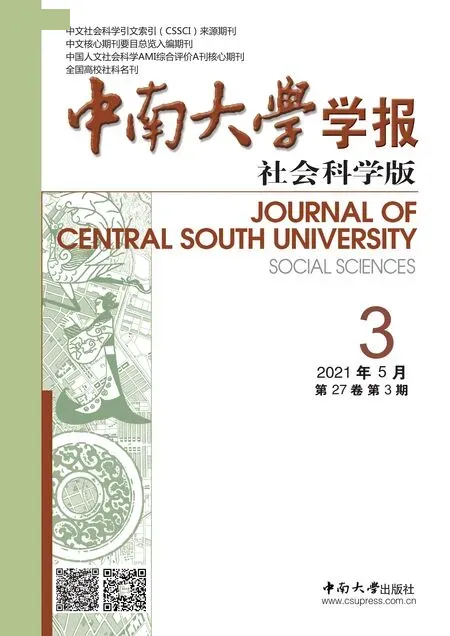《汉书·五行志》“傅《春秋》”的逻辑结构与灾异家谱系构建
2021-06-17王尔
王尔
《汉书·五行志》“傅《春秋》”的逻辑结构与灾异家谱系构建
王尔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傅《春秋》”是《汉书·五行志》叙述的一大特征。除了“经曰、传曰、说曰”体式因袭刘向之《洪范五行传论》外,班固在“说曰”以下的“例说”部分精心重组了“春秋”和“汉”的史事,呈现二者对应的结构关系,旨在表明《春秋》咎征解读可挪用于汉世。班固对汉儒文辞的引用可分为“灾异著作”和“历史言论”两种形式,各有不同的史源及含义。前者凸显董仲舒、刘向父子及京房的灾异学说通古今之变的权威性,后者则表现具体政治情境下士人的廷谏及君主态度,与《汉书》各章史事形成关联,呈现出汉代士人引《春秋》义理汲汲进谏而皇帝不以为然的历史景象。借这两种形式,《五行志》建构起汉代典范灾异家的谱系,暗示汉君对灾异家言论的虚心接纳或置之不理的态度将会影响朝廷的命运,希冀对东汉王朝起到政治上的警示作用。
《汉书·五行志》;“例说”;《春秋》;灾异家;班固
一、引言
班固在《叙传》自述《汉书》体例:“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1](4235)关于“《春秋》考纪”,颜师古注:“谓帝纪也。而俗之学者不详此文,乃云汉书一名《春秋考纪》,盖失之矣。”《后汉书·班固传》章怀注引《汉书音义》:“《春秋》考纪谓帝纪也。言考核时事,具四时以立言,如《春秋》之经。”[2](1335)若此说有据,则班固有将帝纪类比作《春秋》的意图。除了“考核时事,以四时立言”即以编年叙事外,《汉书》帝纪与《春秋》鲁公之数同为十二,这使“比附《春秋》”有了形式的可能。比起始于五帝、迄于孝武,以贯通古今为跨度,以王朝更替为体的《史记·本纪》,始终记录“汉史”的《汉书》帝纪与“鲁史”《春秋》形式上更相似。宋代学者刘子翚在《〈汉书〉杂论》称“班固作《汉书》,惟《纪》最为严密。事皆详载于《传》,而撮其要书于《纪》,固自名之曰‘春秋考纪’,其言有深意焉”,并举例论证班固从《纪》到《传》皆运用了“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史事中①。
这种比附远不止于帝纪。作为《汉书》最长的一篇,卷二七《五行志》展示了一种“傅《春秋》”的体例。这种“傅”不仅如学者所说是一种汉代史学对《春秋》经学之附庸[3](29),更多的是体现了作者班固的精细构思和价值追求。考察《五行志》这一书写结构和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春秋》在何种层面上影响了班固、《汉书》在何种意义上与《春秋》相契合、班固这一比附有何意图等问题。
学界对《汉书·五行志》已有很丰富的研究成果②。其内容与体例,目前较普遍的看法是袭用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体例及部分内容,并杂糅了董仲舒《灾异之记》、京房《易传》、刘歆《洪范五行传论》、许商《五行传记》等西汉灾异学文本③。《五行志》因这种袭用和糅合而混乱了体例④,且这种紊乱影响到《汉书》的整体性。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侧重于梳理《五行志》的内在逻辑线索,以辨识班固的建树所在;关注《五行志》“傅《春秋》”体例及由其展现的“灾异家”群体,追究班固创作此志的意图——不只是对董仲舒、刘向父子诸人著作的因袭杂烩,更是建构一段比附春秋时代的西汉史,及与整部《汉书》相关的、以《春秋》谏政的“灾异家”典范。《五行志》尽管在咎征解释和排比上存在一些舛误,但总体而言,内部逻辑结构严谨,并与《汉书》他篇叙述形成照应。其背后有班固对西汉衰亡原因的总体性思考,以供东汉资鉴[4]。从某种意义上说,《五行志》是一部立足东汉、总结西汉的“史学”作品,充满对前汉与后汉王朝的关怀及期待,这也使之与董、刘诸人之“经学灾异学”区别开来。
《五行志》开篇便标榜“傅《春秋》”。在总论《洪范》和《周易》所承载的“天人之道” 后⑤,班固转入一段学术史叙述,作为书写此志的背景: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1](1317)
班固列举了三位《春秋》学者作为汉朝“承秦灭学”后的灾异家代表:董仲舒以《公羊》论灾异有首创之功;刘向治《穀梁》并以《洪范》解之,承袭仲舒思路;刘歆治《左氏》,其学独树一帜。通过将三人举为《春秋》三《传》的代表人物,班固设立了“汉《春秋》灾异学”的基本谱系。选择这三位学者,应与他们的学术贡献——“以汉事傅《春秋》”有关⑥。班固又明确指出,本志引用董仲舒至李寻诸人之学说及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含有总结历史的语气。颜师古注:“傅读曰附,谓比附其事。”既然是“傅《春秋》”,则“汉十二世”与“春秋十二世”不能说毫无关联。如记录春秋鲁国末世昭、定、哀公时期和汉成帝、哀帝、平帝时期的灾异尤多,将二者相对比的笔法很 常见:“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 三。”[1](1500,1506)尽管这些学者并非专治《春秋》,班固仍采用他们的言论。说明在他看来,“比附《春秋》”并非“春秋学家”的专利,也不仅仅是《春秋》三《传》之学的问题。
《汉书·叙传》提及《五行志》的编纂意图:“《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1](4243)《五行志上》记汉武帝建元六年六月辽东高庙起火,引董仲舒之言:“《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1](1331−1332)两者皆提到《春秋》对本篇的意义。班固以《春秋》之道在“告往知来”“举往以明来”,而《五行志》的目的应是通过解读“《春秋》之占”,“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以《春秋》取义之法推知古今“天地之变”(即灾异)与“王事”“国家之事”的联系。
二、《五行志》“傅《春秋》”的逻辑结构
据游自勇统计,《五行志》引《春秋》家言高达307次,占所有引言的64.6%。他指出:“《汉书·五行志》的思想内核里,《春秋》居于核心地位。”[5]《五行志》“傅《春秋》”不仅表现在引用《春秋》家言次数上,更重要的是在结构体例上。此篇总体结构如下:“经(《尚书·洪范》)曰”为一级主题,“传(伏生《洪范五行传》)曰”为解释经文的二级主题,“说曰”为解释传文的三级主题⑦。在“说曰”以下,也是占据全文最大篇幅的,是作者集合西汉各家之文辞,附以具体历史事例,对经、传、说作出的解释。本文将这部分内容称为“例说”。“经曰”“传曰”和“说曰”三部分根据《洪范》及《洪范五行传》的逻辑展开,综论“五行”“五事”等条目的义理,相当于“纲目”。“说曰”以下记录具体灾异现象的“例说”,细论灾异与人世变迁的对应关系以佐证“纲目”,相当于“骨肉”。“纲目”和“骨肉”组成《五行志》有述有论的体系。“纲目”主要承袭《洪范》《洪范五行传》及西汉“洪范学”学者说辞。与之不同,“骨肉”部分由班固整合各位学者的灾异著作以及春秋、西汉的史事,编排、归纳而纂成,是作者所言“傅《春秋》”的具体内容。
全篇从“经曰”“传曰”“说曰”到“例说”四部分的大结构承袭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从“五行”“五事”到“皇极”共十一章,与《洪范五行传论》“凡十一章”相一致[1](1705,1950)。不少学者认为“例说”也主要采自董仲舒、刘向父子之书⑧。实际上,这部分有班固精心的整合与编排。尽管董、刘诸人已做了将“汉”比附“春秋”的工作,班固仍有诸多创建,他以东汉史臣的立场俯视西汉一代,将各家灾异著作及史事整合成段,重新置于“春秋”与“汉”二维叙述框架 下⑨。“例说”中的很多内容仍应属于班固的 独创⑩。
春秋事与汉事的对举不仅为“经曰”到“说曰”的“纲目”提供例证,还呈现为意义彼此呼应的“傅《春秋》”结构,从中可见班固“以春秋隐喻汉代”的编纂深意。以“五行·火”为例,春秋、汉两段记录多有对火灾咎征的相近解读,如“废杀太子”、“女祸”、“纵骄臣”。虽上下文并非毗邻,但“春秋事”和“汉事”的对应颇为明显。从以下例子可看出这一逻辑结构的展开:
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诛季氏,又用其邪说,淫于女乐,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显而奢僭者。……(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董仲舒、刘向以为亡国之社,所以为戒也。天戒若曰,国将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灾,屡于定、哀之间,不用圣人而纵骄臣,将以亡国,不明甚也。[1] (1329−1330)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按《春秋》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孰,而孔子之圣方盛。夫以盛圣而易孰恶,季孙虽重,鲁君虽轻,其势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两观灾。两观,僭礼之物。天灾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以去。已见罪征,而后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灾。二者同事,所为一也,若曰燔贵而去不义云尔。哀公未能见,故四年六月亳社灾。两观、桓、釐庙、亳社,四者皆不当立,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见灾者,鲁未有贤圣臣,虽欲去季孙,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见之,其时可也。不时不见,天之道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 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 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也。”[1] (1331−1332)
两段叙事均以“火灾”意象为逻辑起点。春秋部分,针对“奢僭过度”的季氏,天以庙灾警戒鲁公,鲁公不听天戒、“纵骄臣”,以致被季氏驱逐。汉部分借董仲舒言论,以季氏专政为例推知汉事,表明春秋“火灾”在当代仍有警戒效力。修辞上与春秋事部分相呼应,如“天戒若曰,去高显而奢僭者”与“天灾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以去”;“不用圣人而纵骄臣”与“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最终,以田蚡叛逆之言、淮南衡山二王谋反的结局肯定了仲舒对武帝庙灾的解读。这段叙述的逻辑顺序如下:首先,从春秋之灾异出发,引用董仲舒、刘向学说的解释,说明灾异与咎征的关联。其次,列举汉代与之相同的灾异,以“通伦类以贯其理”的原则,推导出与其对应的汉事。最后,说明对春秋时代灾异的解释在汉代也能行得通,《春秋》灾异学具有“举往以明来”、贯通古今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事和汉事两部分引用董仲舒的方式不同,前者用“以为”,后者用“对曰”,二者史源不同,分别来自仲舒《灾异之记》与其廷议记录(下文详析)。之后,汉事又列举“武帝太初元年柏梁台灾——夏侯始昌言灾——巫蛊之乱”“昭帝元凤元年燕城南门灾——刘向解灾——燕王作乱伏辜”“元帝永光四年宣帝杜陵园东阙南方灾——刘向解灾——石显谮毁周堪、张猛”等情节,均显示了同一逻辑:汉灾异家解读春秋“火灾”,能为汉世揭示此类天戒的现实指向。
又如“五行·金”一节有将春秋昭公八年与汉成帝鸿嘉三年所发生的两次“石言、石鸣”事件毗邻对举[1](1340−1341)。先举昭公八年晋平公“筑虒祁之宫”一事,师旷“对曰”进谏;后举成帝鸿嘉年间“起昌陵”一事,“虒祁离宫去绛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野”。二者有内在的对应关系。两次“石鸣”在昭示“宫室奢侈”“民力凋尽”及“轻百姓”诸现象上意义一致,且先后两次提及师旷这一贤人。作为春秋与汉事之间的纽带,反映“君子”对春秋灾异的解读适用于汉朝,汉人领悟昭公八年师旷和叔向的警告之语,便可掌握“石言”意象所指,以正汉事。
“五事·言”载春秋鲁文、成公时“鸲鹆”与元帝时“井水溢”两条童谣,在昭公和成帝时各有应验,最终分别发生“阴盛而灭阳”之结果:昭公被季氏所逐,成帝封侯王莽,为篡汉埋下伏笔[1](1394)。关于“鸲鹆之谣”,《五行志》“五事·视”载:“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鸲鹆来巢’。……刘向以为有蜚有蜮不言来者,气所生,所谓眚也;鸲鹆言来者,气所致,所谓祥也。鸲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1](1414)“鸲鹆”之异象征“阴居阳位”。元帝时有“井水溢”之童谣,成帝建始二年应验“井水溢”。班固称此事“象春秋时先有鸲鹆之谣,而后有来巢之验”,将刘向以“鸲鹆之谣”对应“阴居阳位”“去宫室而居外野”的解读移用至此,“象阴盛而灭阳,窃有宫室之应”,形成如下意义:“鸲鹆之谣”预示季氏的出现,建始谣言则与生于元帝、封侯于成帝、最终篡汉的王莽有关,皆应验“以下犯上”。《五行志》通过将刘向对昭公童谣的解读挪至元、成之事,顺理成章地指向王莽篡汉,用“季氏逐昭公”隐喻汉代的终结。
“星陨”一节以春秋庄公七年与汉成帝永始二年两次“星陨”紧邻对举[1](1508,1510−1511)。《天文志》载:“《春秋》‘星陨如雨’为王者失势诸侯起伯之异也。其后王莽遂颛国柄。王氏之兴萌于成帝时,是以有星陨之变。后莽遂篡国。”[1](1311)谷永以“《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严 (庄)以来,至今再见”警告成帝,呼应春秋 庄公七年的星陨异象。谷永的原理是“星辰附离于天,犹庶民附离王者也”,与“春秋事”部分董、刘“诸侯微”和“民失其所”的解读再度形成对应。
对春秋、汉两段不甚有关联的事例,班固也能强行比附:
《左传》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刘向以为近鼓妖也。丧,凶事;声如牛,怒象也。将有急怒之谋,以生兵革之祸。是时,秦穆公遣兵袭郑而不假道,还,晋大夫先轸谓襄公曰,秦师过不假涂,请击之。遂要崤阨,以败秦师,匹马觭轮无反者,操之急矣。晋不惟旧,而听虐 谋,结怨强国,四被秦寇,祸流数世,凶恶之效也。[1](1428)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曰:“《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八月,博、玄坐为奸谋,博自杀,玄减死论。[1](1429)
春秋晋文公葬礼上有“鼓妖”之声,音大如牛而有怒象,象征“急怒之谋”(先轸之谋)和“兵革之祸”(秦晋之战)。哀帝时朱博、赵玄在丞相和御史大夫就职礼上有“鼓妖”之声,预示“其人自蒙其咎”,朱博最终自杀,其罪实为勾结傅太后[1](3407−3408)。从灾异释读和咎征上看,两件事的比附显得牵强。班固称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恐有凶恶亟疾之怒”,比附晋襄公听取先轸的“急怒之谋”,这个解释挺勉强。引李寻对“鼓妖”的解读,也与《洪范五行传》有较大差距。“鼓妖”属“五事·听”,“说曰”载“‘听之不聪,是谓不谋’,言上偏听不聪,下情隔塞,则不能谋虑利害,失在严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杀物,政促迫,故其罚常寒也。……君严猛而闭下,臣战栗而塞耳,则妄闻之气发于音声,故有鼓妖。”[1](1421)君严急、臣战栗的情况不见于哀帝、朱博之例。汉“鼓妖”事仅此一件,大概因为班固举不出更多例子与此类春秋事 对应。
再如春秋哀公十三年、成帝元延元年各自“有星孛于东方”的例子: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乱气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终。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东方者,轸、角、亢也。轸,楚;角、亢,陈、郑也。或曰角、亢大国象,为齐、晋也。其后楚灭陈,田氏篡齐,六卿分晋,此其效也。[1](1515−1516)
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晨出东方。……谷永对曰:“上古以来,大乱之极,所希有也。察其驰骋骤步,芒炎或长或短,所历奸犯,内为后宫女妾之害,外为诸夏叛逆之祸。”刘向亦曰:“三代之亡,摄提易方;秦、项之灭,星孛大角。”是岁,赵昭仪害两皇子。后五年,成帝崩,昭仪自杀。哀帝即位,赵氏皆免官爵,徙辽西。哀帝亡嗣。平帝即位,王莽用事,追废成帝赵皇后、哀帝傅皇后。……平帝亡嗣,莽遂篡国。[1](1518)
《春秋》记载最后一位君主鲁哀公时发生“有星孛于东方”。有意思的是,董、刘只认为这是“乱气蔽君明”,并没说和国家命运有关。而班固有意将此与“《春秋》事终”联系,暗示这是《春秋》所载鲁国的结束。班固接着提到这样一种说法(“一曰”):日在氐宿,东方是轸、角、亢三宿,分别对应楚国、陈国、郑国,其征验是楚国灭郑国;还提到另一说法(“或曰”):角、亢对应齐国、晋国,征验是田氏篡齐、六卿分晋,春秋时代终结。可见班固刻意将哀公时“有星孛于东方”跟亡国相联系,对应于汉事部分的论述。成帝时也发生“有星孛于东井”,班固先引谷永,认为昭示“后宫女妾”和“诸夏叛逆”,举赵昭仪之乱为证。最终“王莽篡国”被视为灾异之结果,班固借此将“汉家之终”与“春秋之终”并列对比。然而成帝元延元年距离“莽遂篡国”尚有十余年之久,当时恐难预知莽祸。将元延元年星孛与哀公十三年对应、定西汉亡国的征兆于成帝,应是后人追述,最终由班固敲定记下。《五行志》多次讨论王莽篡汉,并认为其祸根在成帝,蕴含班固对西汉衰微历程的思考。这种“成帝中衰”之论与上引“石言”例(鸿嘉三年)、“童谣”例(永始二年)、“星陨”例(永始二年)相一致,符合《成帝纪》赞所谓“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的总结性叙述[1](330)。
《五行志》平行记录春秋与汉事、呈现对应性结构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春秋四国同日灾,汉七国同日众山溃,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1](1457)。“当春秋时,侯王率多缩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考之汉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终亡二日仄慝者……”[1](1506)还频繁出现如“天戒若曰”和“王不寤(不改)”的修辞,通用于春秋和汉两部分叙事。班固的观念隐寓其中:春秋天戒发生于汉世仍具警告效力;汉主不悟天戒,将如鲁君一般遭天惩罚;借助君子的提醒,把握《春秋》灾异,能在汉世应对相似天戒。《五行志》春秋、汉二维对应叙述结构的暗示逻辑如图1所示。
这一逻辑环节表明,一旦不听取灾异学者警告,君主便无法获悉及应对灾异,从而无从更正引发灾异的错误行为;长期下去将使汉朝逐渐“不合天意”,最终遭致天命抛弃。此因果链条显示了“灾异家”沟通天、君的关键作用。综上所述,班固编织素材,挑选与春秋咎征对应的西

图1 《五行志》春秋、汉二维对应叙述结构的暗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