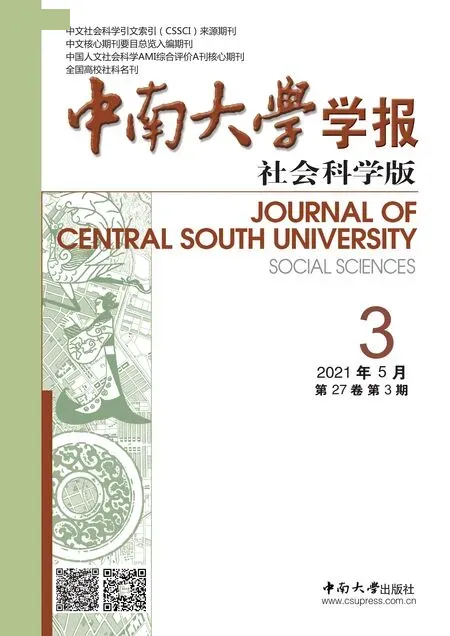生命主体化及其乌托邦:论《别让我走》的生命政治
2021-06-17支运波
支运波
生命主体化及其乌托邦:论《别让我走》的生命政治
支运波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上海,200040)
《别让我走》将读者置入由制造生命和自然生命同构的生命政治图景,去直面一个女性克隆人凯茜的短暂生命历程,并让读者与其一起体验和反思生命被外在因素介入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在于:小说客观冷静地书写了政治权力和生物医学的管治技术,以及由这种管治技术引发的复杂的生命感性问题;小说细致地叙述了生命在权力、技术等外部因素介入后面临的诸多不适,以及由此造成的生命自身的“问题化”,让读者在一种不对称的体验张力中思考人类应如何面对自己制造的生命客体;小说呈现了生命在适应与抵抗外部因素时激发出的主体化努力,以及最终的乌托邦结局。作为一部书写生命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为生命政治批评提供了一个范本。
《别让我走》;生命政治;主体化;乌托邦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籍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长篇小说《别让我走》()出版,并接连斩获多项文学大奖,登上英美多家重要媒体的年度最佳图书榜。学者们随即从多个角度对该小说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认为,《别让我走》最重要的当代意义在于:一是《别让我走》延续了由《失乐园》《鲁滨逊漂流记》《科学巨人》《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裸体午餐》《V.》《死者年鉴》《幻影书》《米娜哈克的来信》《雪人》等作品所开拓的生命政治书写[1];二是《别让我走》正好处于由《一九八四》[2]与《美丽新世界》[3]所共同界定的可怖的未来世界的生命政治景象的核心点上[4](3);三是《别让我走》把生命政治问题与生命政治批评置于显眼位置。作为一部书写生命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为生命政治批评提供了一个 范本。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生命政治概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生命政治业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管治范式。它在哲学、美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学,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和人类科学领域,开始被学者们大量使用,并作为他们理论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112)。毫不夸张地说,生命政治已从福柯思想中的一个概念,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6](73)与思想武器。我们有理由相信:沿着由生命政治前沿理论开启的批评路径,或许可以廓清当代文学书写中生命概念在生命政治理论中所存在的某种疏离或超越的吊诡关系[6](90)。
一、生命政治管治与生命感性
《别让我走》是一部有关制造生命、看护生命和思考生命的生命小说。小说书写的克隆人,是人类为了提升自身的生命质量借助生物技术制造出来的生命。也就是说,这是一群由生物技术与生命政治制造的人造生命。小说以凯茜、汤米和露丝三个年轻人为中心,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英格兰的一群克隆人从生到死的生命故事。小说从青春期以前就生活在黑尔舍姆(Hailsham)寄宿学校的克隆人说起,展示了她们辗转各种生命看护机构,直到为人类做完四次器官捐献旋即生命终结的悲惨历程。作者冷静地道出了克隆人的身世秘密和未来命运,并把人类置于一个可被审视与反思的客观立场,以此呼应当代生命政治的管治机制及其造成的生命境遇。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别让我走》“堪称生物工程时代的《一九八四》”[7]。
石黑一雄以第一人称的敞开性视角叙述了克隆人所生活的场所——黑尔舍姆,及黏附于权力之上的一切关系和“规训机制”。一方面,小说极力铺陈黑尔舍姆的规训与惩戒,例如,高高的栅栏、遍布各处的“天线和卫星接收器”等监控设施、每周一次的严格身体检查、形影不离的监护人、各种各样的“晨会”“谈心”“训诫”“警告”“秘密护卫队”,以及克隆人内部之间无时不在的监视与偷听,乃至“关禁闭”“体罚”“剥脱权利”,等等。这些克隆生命成为权力的直接对象和物质目标的装置过程。另一方面,与这些直接作用于克隆人身体上的惩戒权力相比,那些由权力和技术引发的潜在危险对克隆人的压制,则更为恐怖。比如,通过散布树林里闹鬼的恐怖故事、强化克隆人不能生育的生理缺陷、凸显裂开伤口的纯物质性叙述的诸多恐惧情绪,实现对克隆人的心理规训。
作者细致地呈现了生命中那些不可名状的恐惧。小说多处出现“被告知却又没有真的被告知”[8](82)的心理暗示,把莫名的恐惧推到极致。显然,这些有形和无形的东西成为权力管治生命过程中“煽动、强化、控制、监督、抬高和组织它手下的各种力量的作用的一个部件。它是一个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促使它们增大、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阻碍它们、征服它们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并且,这种惩罚性、恐怖性的权力“部件”,又同时“成了对一种积极地管理、抬高、增加、具体控制和整体调节生命的权力的补 充”[9](88)。克隆人的生物生命(zoē)完全沦为生命政治化的生命。
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权力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从君主政治的君权元首权力过渡到法官、律师、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那里。也就是说,权力位移(向下、发散)之后,实施权力的主体变得多元、模糊和匿名了。《别让我走》正凸显了那些不具名的、潜在的、散布于各个方面的权力实施者的威慑性。由于这些掌权者往往没有具体的形象和来源,所以更令人感到恐惧。比如,小说告知“看护员”和“夫人”是管治黑尔舍姆的掌权者,却没有说明他们为谁服务,受谁指使。这种权力的“无首化”使得克隆人生活在由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生物危险、权力危险和疾病危险构成的恐惧之中。此外,小说似乎还故意将克隆人呈现为关乎人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政治。这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认识到:克隆人的状况也是我们自己的状况[10](60)。这种故意模糊人类与克隆人的种属界限、物人之分的做法,其用意是让二者自动进入生命政治生与死的矩阵中,进而让人类与克隆人对视。此外,作者还有一个明显的叙述策略,即一旦涉及生命医学问题,就立刻呈现欲言又止的模糊叙述。读者也无时无刻不处在担忧之中。或许,作者正是用这种复杂的生命感性预设了生命政治的可能场景:生与死的模糊边界与例外状态,彰显的是死亡政治尖锐的临界性。
人类借助生物技术给予克隆人生命,可是在克隆人步入死亡的过程中,人类又故意改变了古典权力一次性收回生命的形式,而采用借助器官捐献这种多次收回生命的生命政治方式。作者以此诠释在遭受权力与生物技术规制的过程中,生命的敏感与脆弱,进而彰显生命被政治化所造成的残酷的生命感性状态。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孩子们在一个与其他同伴隔绝的环境中被克隆和养大。一旦她们到了成年,就成为‘捐赠人’,她们的器官在一系列的操作中被收割和被用 来治理人类的疾病。在捐献四次以后,便走向 死亡。”[11]
在小说结尾部分,夫人道出了克隆人的生命真相:凯茜等人是一群因担忧人类生命的风险(或为了增强人类生命的质量),由权力、商业、医学等机构支持而进行的生物学实验产生的,是被“创造”“规划”和“安排”的,来自技术而非来自自然生殖的实验生命。那些维系克隆人生命的一系列看护行为、教育行为、健康检查和监控行为等,既不把克隆人视为生命存在,也不把克隆人视为生命的一种自然需求,而是完全出于某种外部的政治目的和生物医学需要。因此,克隆人与其说是“人”(生命),不如说是一种“物”(或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像凯茜这样的克隆人不断受到各种各样、无处不在、或隐或现的外部因素(力量)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生命问题和不可言说的健康问题、情感问题。《别让我走》用凄婉的故事,生动地注解了生命政治理论家们关于生命是与政治(权力)、医学(制度)、知识体系密不可分的关系物的论述,让人们看到了政治权力、医学技术、知识与经济等外部因素“介入人类存在的生命特征而进行的尝试”[12](64)时所显现的生命权力(biopower)场景。
凯茜等人的生的机会和死的意义都聚焦在“给正常人类提供生育优异的智商、优异的体质,诸如此类高素质孩子的可能性”[8](264)。此刻,生命权力体现的“不是以对政治对手的胜利为目的,而是以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并以与此消灭相联系巩固人种或种族为目的”[13](195)。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逻辑在小说中被转换为一种较隐秘的方式——器官克隆,并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社会中成为合法性存在。不管是把克隆人视为延续人类生命而献祭的牲人(homo sacer),还是把其视为可任意处置的生物器官,她们都处于一种例外空间和悬置状态,即这些克隆人可以随意被处置而不受任何处罚,因为她们是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是“处在生命与死亡、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一个界限性地带”和无区分性地带的赤裸生命(bare life)[14](213)。克隆人因“政治”而“生”(zoē)为生命客体(对象性存在),却没有任何生命的权利和价值。对此,凯茜等人的处境可以说明:她们创作的大多数艺术品都被视为没有创造性和艺术价值的垃圾,少量艺术品则被无偿拿走;不仅用爱情欺骗本来不存在的延迟捐献,而且还在寻找生命原型上无情地斩断她们自我认同形成的可能;只有看护员才可以“行进在那一度唯有至高权力才可以进入的无主之地中”[14](214)。
生命政治主要还是显现为“生”的政治,即治理的松动和提升生命的质量。《别让我走》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黑尔舍姆的监控实在谈不上有多么坚固,如同《一九八四》里的“电幕”一样。比如,监护栅栏没有电气化、克隆人可以私下里评价看护员,生活在这里竟然让克隆人感到“真正轻松自在,甚至是恬静宜人”[8](237)。黑尔舍姆也并不被视为监视场所,而是被称为学校或者生命保护场所。小说安排凯茜等人从黑尔舍姆到村社和其他康复中心,生活环境由封闭场所变为更宽松自由的平展空间。不管作者是否在暗示某种管治权力的松动,可克隆人十分怀念黑尔舍姆,这是确信无疑的。所以,与其说是对克隆人的严格监控,不如说是用一种较为温和的知识渗透和情感培育的方式引导她们顺利进入器官捐献或尽量适应未来生命的一种预演。此外,交换艺术品则旨在训诫克隆人的无偿奉献意识,“代币之争”是在暗示她们对于自身价值的认知,拥有友谊、爱情和寻找生命原型意在强化其身份认同和生命主权。
黑尔舍姆给克隆人提供了优良的健康保护,提供了如同家人一般的生命关怀,让她们安然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快乐时光。虽然是克隆人,其实她们和正常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比如,看护员需要对看护工作全情付出,否则这将是一份常人难以胜任的艰巨工作;捐献者也需要富有情感才可以延续捐献次数,否则同样痛苦不堪,甚至情绪(情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疾病本身。故事叙述者凯茜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她是克隆人的看护者和幸存者,是三个主要人物中最温柔、天真和友爱的人。她非常满意看护工作,对寄宿学校生活与日常交往的回忆和常人一样。同样是做器官捐献,她却不会“情绪波动”。因此,技术制造了人,也制造了人性。克隆人在看护与被看护的过程中也在逐渐塑造着自我,只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时不时表现出的“神秘与风险”,时刻提醒她们(包括读者)不要忘了克隆人与人类的 不同。
二、非对称的生命政治与主体塑造
根据福柯的看法,生命政治指的是发生在18世纪末期由“‘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向“‘让’人活或‘不让’人死”[9](80)的现代权力的转变,以及管治技术模式的更迭。同时,它也意指以个体肉体为中心进行规训(les disciplines)的身体解剖政治(anatomopolitique)向以整体性人口为中心进行介入和调控的生命政治(biopolique)的过渡机制,以及在主体那里造成的多重效应。它以群体人口为治理对象,以管理生命、增强生命、看护和理顺生命为旨趣,进而实现治理的合理化。但是它也造成了生命“不确定状况或不明确的部分”[15](51)、生命统计学化和生命的问题化,以及抵抗臣服化的主体性之路的乌托邦化等诸多关键性难题。福柯发展了尼采的权力思想,主张管治并非指某种纯粹的统治关系,也不是迫使他人的手段,而是一种具有引导性的美学手段和主体间的技艺,一种“使人能够利用人们的自我,利用人们的自我指导”的技艺[16](102)。也就是说,生命纳入权力治理 在制造了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和否定性的死亡政治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实施着自我塑造的主体化。
石黑一雄用一个由生物技术制造的实验生命——克隆人的生命故事,展现了在“生殖成为生命政治的核心”[17](281)语境中的种种难题和非对称性。凯茜、汤米、露丝等克隆人虽然是正常人类器官经由生物技术批量生产诞生的,而不是经由有性生殖诞生的“同一性的人”,但是她们却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脾气。也就是说,她们和常人无异。这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不可复制的、唯一的《别让我走》磁带与独一无二的克隆生命之间可能构成的强烈的生命隐喻:她们来到世上是为了给人类捐献器官,她们活的意义却又偏偏在于“死”的行为。她们要完成捐献(即死),却又反讽地必须保持健康、活得愉快、充满友爱,并受到严格看护、监控和教育等一系列生命照料。这很好地注解了“赐生”“让死”和死亡 政治(thanatopolitique)作为生命政治反面的辩证、模糊与不对称性。凯茜在听到《别让我走》的 歌曲时热泪盈眶,对生充满无限留恋,对生育充满无限期待,可她们的母体原型却又偏偏是不珍惜生命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罪 犯等[8](166)。
处于身体规训和人口调节两条轴线交叉点的性却吊诡地发生了错位。其一,人类像害怕蜘蛛一样对待克隆人,克隆人像没有灵魂的生物垃圾一样被随意处置,这表征了人类遭遇的后人类政治烦恼[18](33)。基于提升生命质量的目的,结果却制造了一个冷漠的社会,人类一手制造的克隆人在追寻与弃置的错位中暗示了生命伦理在生命政治中的严重缺位。其二,人类似乎以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出现:她们对自己的器官不满,同时又作为器官身体疏离参与塑造的人;她们追求生命健康却在本质上隐含必然的不健康;对克隆人照料备至却有“捐献四次”的限制。生物技术与生命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预设了对生命存在的本质的关怀与尊重之外,还隐含人类反思自身的意味。
石黑一雄用“学生”替代克隆人的生物医学称呼,又通过淡化克隆人的特殊性,让读者觉得她们就是自己身边熟悉的人,以此强化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思考。人们通常认为“医学所希望的只能是阻止反常现象,重建自然生命规范和支撑它的身体规范”[12](20),从而把生命挽回到正常的生物学轨道。然而,小说中克隆人很好地适应了不同的环境,虽然她们自身的疾病时时伴随着她们,但是事实上她们并没有出现危及生命的症状或者器官衰竭等严重问题。这就导致对生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就像福柯的老师康吉莱姆所认为的那样:生命不是物理和科学问题,而是政治与伦理问题;生命病理不是来自结构性失衡,而是来自生命的变化或变异,或者知识的制度化。也就是说,作家在小说中把生命体认带到了另一个政治空间。
这就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究竟人类有没有必要对自身器官进行克隆?为了增强生命是否应将克隆人弃之不顾?正常人类的自然生命模式还要不要继续?克隆技术和延长生命技术是否能够制造与维持一段高质量的生命?克隆人的生命算不算生命,或者说,算不算某种有价值的生命?是否需要担忧可能造成的生命风险?等等。小说暗示生命政治反而导致了某种无用性。克隆人不管是创作艺术品,还是培育友谊或爱情,本以为能提升自我价值,可结果并非如此。反而需以监护人的认可来证明克隆人的精神存在,借此为克隆技术(这一项目,或政治行为)获得支持提供证据。与此类似,生命政治着眼群体治理反而导致了对个人价值和生命情怀的忽视,使个人成为献祭者。
生命政治强调关注集体人口健康的同时应该关注个体的生命质量,在被动接受生命政治福利时,生命也主动参与了自我塑造。所以,“生命政治分析也必须考虑到主体化的形式”[19](120)。评论界对克隆人为何不逃离黑尔舍姆一直争论不休,这恰好印证了评论家所关注的乃是生命政治中主体塑造这个核心问题。对此,生命政治理论家奈格里指出,生命政治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生产了社会关系。《别让我走》看似平淡的叙述其用意就在于彰显克隆人的生命存在:凯茜这么一个平常的克隆人在寄宿学校度过了快乐童年,在创造和阅读艺术作品中自由成长,尽心尽责地做看护工作。她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的好恶、嫉妒、忧伤、报复心以及其他小情绪,她可以思考,能够憧憬,她认为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停下来思考和回忆”,尝试去弄明白她们作为克隆人未来的生命问题[8](37)。
小说用零度叙事的方式将正常人类置于克隆人的他者地位,又采取否认克隆人对等性和同一性的方式,让人类与克隆人在生命政治场域中互相省视。再以感伤的基调叙述克隆人的生活、情感、心理,从而展现克隆人细腻的内心情感世界。石黑一雄试图以把实验生命与自然生命并置于同一空间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将人类带入到生命政治语境中重新体认:“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完全不是由于物质性设计。而正是人类所独有的全部情感,让人产生了生存意义、目标、方向、渴望、需求、欲望、恐惧、厌恶等意识,因此,这些才是人类价值的来源。”[20](169)
以克隆人的视角反观人类,可以发现:人类追求生命改良的意愿难以规避生命在本质上不健康的必然,即还是克服不了生命的自然逻辑;克隆人之间的友好情谊反衬出人类的冷漠无情;克隆人不具人性(无苦痛感)的设定,隐喻的是人类理性的无情;克隆人面对的未来同样是人类要面对的未来。以生命政治来审视人类自身的生存,才是该小说的主旨。“别让我离开”是说克隆人也是生命,与人类一样需要增强、提升、关怀。这不是人类伦理、权力规训对人类的指责,而应该从生命政治视角去重新理解。《别让我走》中克隆人对生命的渴望与祈求在不对称性的设置中出现了反转与深化。
如果说克隆人存在的价值在于捐献器官,维持健康是其唯一重要的事情,那么维持人的生命健康也是现代生命政治唯一重要的事情。因为,维持人口的健康是维持人类生存以及继续生产的基本条件。克隆人对生命的期盼在于留恋生命、享受生命、珍爱生命,与人类延续生命的生产、政治、知识等多重目的及无情的理性主义相比,更符合生命的本质。因此,《别让我走》在凸显生命政治冲突、彰显生命难题时,也让读者“体验强大的张力与压抑的力量”[21]。这也是作者对生命政治管治中对个体生存塑造缺少价值关怀的批判。
三、生命关怀与生命政治的乌托邦
《别让我走》的意义还在于:在生命成为政治算计的明确核心和生物技术的直接生成物之后,它预示了由生物技术制造的新生命主体性的涌现,预示了克隆人拥有的智力、情感、认知、艺术创造等诸多有关人性的部分是不可被规训、被管辖的[22](205)。相反,需要在生命政治之外做自我与他者的审美关怀[10](8)。进而言之,《别让我走》提出了在生命政治背景下,生命如何改变对象的客体性地位去主动参与自身塑造,以及其中的关怀问题。
《别让我走》的人物和情节异常简单、平易。显然,这不是为了说明人类如何利用生物技术去制造一个异于自身的客体,或者克隆人对于人类的有用性。它更为关心的是克隆人“控制、管理、制造、重塑、调节作为活生生的生物的人类具有的生存能力的能力”[12](3),即由生物技术制造出来的克隆生命如何进行自身的社会关系生产及构筑新自我、新主体的问题。就像奈格里说 的,“生命政治生产的最终核心不是为了主体 去生产客体,而是主体性自身的生产”[22](4)。人类并不是用生物技术去制造一个有别于自己的他者,而是要克隆人与人类自身达成同一。
权力是一种相互关系。权力关系中的主体塑造,或者对权力关系中主体的关怀,自然离不开主体对权力的抵抗。福柯就主张:如果没有抵抗就不会有权力关系,而且抵抗是首要的和优先的。《别让我走》的抵抗书写是借助凯茜对生命的顺从与自我塑造的方式实现的。作为克隆人,凯茜在捐献过程中承受着生物照料和身体规训。同时,也在器官复生和器官捐献之间作为一个“新的活着的死人,即一种新的神圣人”[14](178)而存在着。但小说的巨大张力恰恰在于凯茜等人摆脱生物技术和惩戒技术进行自我塑造的主体性,以及对生命的关怀。凯茜已经习惯了身体监控、卫生检查、人文教育和情感引导,但是她的观念(认知)却没有被权力规约成具体模式。凯茜等人的具体经验[23](13)表明了被制造生命的“身体与自身(self)黏附在一起”,以及“这一黏附性是我们无法逃离的”[24](204)的残酷命运。
凯茜热爱自己的看护工作,对结束看护工作也真心接受,因为她认为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思考生命;她热爱黑尔舍姆,无限怀念在那里度过的快乐时光;她对寻找原型兴趣强烈,可在知道原型母体和可能的未来后也能坦然接受;她对生育无限向往,在得知不能生育后,倍感忧伤;她对延长捐献全力以赴,可在知道无法突破四次捐献后,依然能平静面对。她已经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自然生命成长的必然历程。凯茜有爱、有创造性、有灵魂、有情感,她以满腔热情去抵抗生命政治机制。四次捐献之后生命就将终结揭示了生命自然属性的真相,也对人类试图生产出理想生命种属(克隆人)的政治意图给出了乌托邦式的答案。
乌托邦通常是指对于某种制度、规范或状态近乎完美的想象性建构,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之外的向往[24](49)。乌托邦具象为我们所期望的美好生命,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前缀bio在古希腊就意指一种美好生命。可见,生命政治与乌托邦之间存在本质的关联。但这种关联性却是借助治理术来实现的。各种机制、程序、分析以及反馈形式,以及针对人口的计算和统计学策略、权力形式、政治经济学知识、生物医学或卫生知识,所有这些都指向安全装置和治理性的乌托邦。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生命政治干预和管理的重要后果是他们不仅成了国家乌托邦实现顺从或不知情的参与者,而且他们(及其身体)也成了国家机构和国家话语的管治者”[25](4)。生命关怀是生命政治治理乌托邦的必然结果。
凯茜自述了她从“黄金年代”陡然坠入阴暗时刻的生命历程,就如同“白昼陡然变成了夜晚”一般。这些克隆人被教育、被规训,被要求从事艺术,相互之间友爱,“和任何正常的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以确保有“大笔的基金”[8](262)和众多的支持者来继续这项生命实验计划。可导致这项计划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莫宁·戴尔事件——违反法律的增强生命计划破产了。这说明了克隆生命与生命政治直接相关。黑尔舍姆、桑德斯信托所、格伦摩根大楼……每一处都是生命实验场地。克隆一种完美生命(永远健康)表面上看是生物医学的乌托邦,实质上是隐喻提升生命质量的生命政治治理的乌托邦。
“乌托邦和生命政治都已与科学构成了一个整体。”[26](193)在《别让我走》中,一方面,人类想尽办法训诫这些克隆生命,使之成为人类希望的理性客体,让她们变得情绪稳定、没有喜怒哀乐。另一方面,克隆生命源于像“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及“犯罪分子”等卑贱者的器官。小说还详细地描述了人类对克隆人进行的人文教育,可克隆人创造的作品却几乎没有艺术价值;培养克隆人“适当的性”的结果是她们任意的性和无法生育的事实;凯茜满心期待地用真心去爱,期望延迟捐献,得到的结果却是最多捐献四次,在凯茜和汤米问夫人延迟捐献的最终结果时,却发现是个谎言。这一切都有强烈的乌托邦意味:生命无可挽回地消逝,她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她们生命的工具性。克隆生命难以匹配技术、权力的“适当性”要求,自身也存在种种问题。这都说明了生命的不可复制,及其生命政治的乌托邦宿命。
总而言之,有关《别让我走》的诸多生命政治批评,基本都集中于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路径:或着眼于黑尔舍姆的权力规训,或专注于克隆人的“赤裸生命”(bare life)。要么从国家管治的视角去谈权力监视,要么从献祭的视角去谈个体生命的极端时刻。事实上,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是一种国家福利与人口健康的政治,阿甘本所谓的生命政治则意在呈现极权政治中生命的尖锐时刻,二者都不能很好地概括《别让我走》对克隆人个体生命在生命政治中的风险的书写,以及克隆人的主体性塑造这个核心问题。
其实,《别让我走》的深刻寓意或许是:在生物科技时代,生命政治须直面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国家的政治利益,也不是个体生命游走在献祭边缘的状态及由权力、经济等因素导致的道 德缺失,而是基于个体生命在生命自身的政治化问题中的主体性问题。生命政治中主体的问题(生命主体化及生命关怀、生命价值等)取代了生命质量的提升(物的方面),成为权力的新逻辑。凯茜等人对复制生命的母体的追寻、对看护工作的专注、对生育的向往、对友谊及爱情的认知,对生命过程的思考等,这一系列塑造主体的 强烈意识与难逃工具宿命的结局,让人深思。于是,“在复制人的世界中,生命与生命权出现脱钩,请求保护甚或请求生存的声音成为具体的诉求”[27]。
四、结语
《别让我走》书写了一群克隆人对爱、人性和童年的向往,其关切点并不在创造克隆人的生物技术,不在科幻色彩,而在于这些克隆人的情、爱、性,以及对生命自身的追寻、确认和思考,从而呼应了文学与生命、政治之间的现代议题。此外,《别让我走》呈现了克隆生命在遭遇生命政治时的敏感与脆弱,呈现了克隆人生命过程中的种种“不对称性”和“无可逃离”,呈现了克隆生命的主体化策略及乌托邦结局。这不得不让人反思:面对生命政治新世界,人类应如何看待生命、处理生命、审视生命,如何安置自身的人性与情感?
当代文学既是对人类丢失姿态(gesture)的一种记录[28],也“隐存着一种生存方式、生命模式”[29](213)。文学本来是在生命内部书写生命,可突然之间把生命视为一个纯粹对象来观照时,便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别让我走》结尾处给出了夫人在看到凯茜抱着枕头跟着歌曲《别让我走》跳舞时热泪盈眶的原因:“我看到了一个别样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迅速来临。更科学,更有效。”[8](272)这或许也给出了文学批评将要面对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政治后人类世界的新场景、新时刻。
[1] BREU C. Insistence of the materi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M]. Minneapol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2] 支运波. 生命政治与《一九八四》[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106-112. ZHI Yunbo. Biopolitics and 1984[J].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4): 106-112.
[3] BÜLENT DIKEN. Huxley’s brave new world - and ours[J].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2011(2): 153-172.
[4] FUKUYAMA F.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5] LEMM V, VATTER M. The government of life: Foucault, biopolitics, and neoliberalism[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NILSSON J, SVEN-OLOV. Foucault, biopolitics, and governmentality[M]. Huddinge: Södertörm University, 2013.
[7] 谷伟. 沤浮泡影: 略论《千万别弃我而去》中“黑尔舍姆”的体制悖论[J]. 外国文学, 2010(5): 14-20. GU Wei. On the paradox of Hailsham system in[J]. Foreign Literature, 2010(5): 14-20.
[8] KAZUO ISHIGURO. Never Let Me Go[M]. New York: Vintage, 2006.
[9]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佘碧平,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 Trans. SHE Bip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10] ARNE DE BOEVER. Narrative care: Biopolitics and the novel[M].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USA, 2014.
[11] WHITEHEAD A. Writing with care: Kazuo Ishiguro’s[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11(1): 54-83.
[12] 尼古拉斯•罗斯. 生命本身的政治: 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M]. 尹晶,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ROSE N. The politics of life l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Trans. YIN J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13]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FOUCAULT M.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M]. Trans. QIAN Han. Shang 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0.
[14] 吉奥乔•阿甘本.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 吴冠军,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AGANMBEN G.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M]. Trans. WU Guanju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6.
[15] 阿兰•布罗萨. 福柯: 危险哲学家[M]. 罗慧珍,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 BROSSAT A. Michel Foucault: Un philosophe dangereux[M]. Trans. LUO Huizhen. Guilin: Lijing Press, 2014.
[16] 米歇尔•福柯. 自我解释学的起源: 福柯1980年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演讲[M]. 潘培庆, 译.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FOUCAULT M.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 Lectures at Dartmouth College, 1980[M]. Trans. PAN Peiqing. Chongqing: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8.
[17] PROZOROV S, RENTEA 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biopolitics[M]. London: Routledge, 2017.
[18] JHOHNSTON J. OMAR. The prosthetic novel and posthuman bodies: Biotechnology and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D].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ndison, 2012.
[19] LEMKE T.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M]. Trans. Eric Frederick Trump.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 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黄立志,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FUKUYAMA F.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M]. Trans. HUANG Lizh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21] PUCHNER M. When we were clones[J]. Raritan, 2008(4): 34-51.
[22]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大同世界[M]. 王行坤,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HARDT M, NEGRI A. Commonwealth[M]. Trans. WANG Xingku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 JARRÍN A. The biopolitics of beauty: Cosmetic citizenship and affective capital in brazil[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24] SUVIND. Metamorphosi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M]. Berlin: Peter Lang, 2016.
[25] STAPLETON P, BYERS A. Biopolitics and utopia: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M]. New York: Martin’s Press LLC, 2015.
[26] LEVITAS R. The concept of utopia[M].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7] 陈重仁.《别让我走》与生命政治的美丽新世界[J]. 中外文学, 2012(2): 15-54. CHEN Chongren. The brave new world ofbiopolitics in[J].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2012(2): 15-54.
[28] 支运波. 姿态的诗学: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评[J]. 文艺理论研究, 2018(2): 59-68. ZHI Yunbo. Poetics of gesture: Agamben’s biopolitical criticism[J].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018(2): 59-68.
[29] CHARLES J. Stivale.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M]. Itha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Life subjectification and its utopia: On the biopolitics of
ZHI Yunbo
(Department of Drama Literature,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Shanghai 200040, China)
The novelplants the reader into a biopolitical field co-formed by man-made life and natural life, to face a clone girl’s short-lived life, and to invite the reader to experience and rethink together over various problems popping up whenever outside factors intervene into life. These matters mainly lie in that the novel has impersonally written political power and biomedical government technique, and some complex life sensibility problems caused by this technique in life, that the novel has narrated in detail much of discomfort problem when life is intervened by outside elements such as power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life itself, so as to let reader ponder over how mankind, in experiencing a kind of asymmetric tension, should face a life object made by itself, and that the novel has presented life’s subjectifying efforts in adapting to and resisting against the outside factors as well as the ultimate utopian ending. As a science fiction of writing life,offers a sample text to carry out biopolitical criticism.
; biopolitics; subjectification; utopia
2019-10-15;
2021-04-23
上海市曙光学者项目“生命政治理论美学的批判性研究”(17SG4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明互鉴视域下欧陆左翼前沿文艺理论研究”(2018BWY00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艺术理论的生命政治影响与建构研究”(19FYSB005)
支运波,安徽怀远人,文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美学、生命政治理论,联系邮箱:muziyuexia@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1.03.015
I106.4
A
1672-3104(2021)03-160-09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