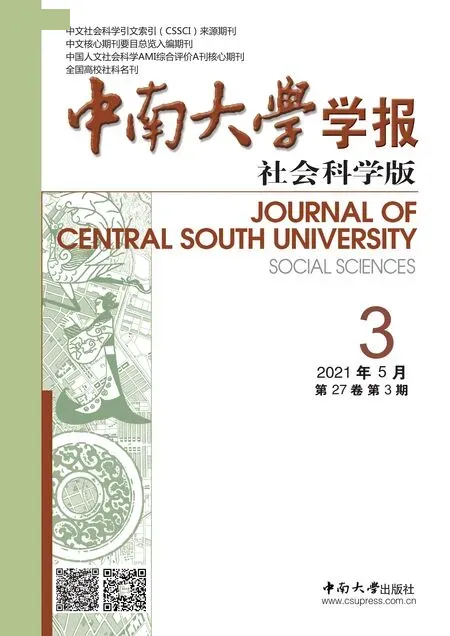从《湘行散记》《湘西》看沈从文的多重面相
2021-06-17唐小祥
唐小祥
从《湘行散记》《湘西》看沈从文的多重面相
唐小祥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
从《湘行散记》和《湘西》这两部返乡散文集中,可以看到沈从文观察和书写湘西时现代文明和乡土文明兼而有之的双重视角和眼光、深切的地方性与“照我思索”的方法论;可以感受到他对文学重造社会、国家、民族和新人的顽强信念,对传统乡土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碰撞的思考,以及对启蒙之困境和人类知识、理性之有限性的清醒洞察。由此,能够发现沈从文及其作品的多重面相。1980年代以来的沈从文从纯文学知识谱系中浮出历史地表,逐渐被文学史经典化。这种看似回归文学本位的阅读方法,实际上是对作家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稀释与简化。在文学经典化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如何对待及进行文学的经典化,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沈从文;《湘行散记》;《湘西》;地方性;寂寞
一、引言:从“沈从文的寂寞”谈起
早在1936年,沈从文就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在读者那里的“失败”,因为“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够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所以“提到这一点,我感觉异常孤独”。这是因小说不能被准确理解而带来的寂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在给戴乃迭翻译的《散文选译》作序时,沈从文又谈到了自己的散文在读者那里的“失败”,沈从文写道:《湘行散记》“乍一看来,给人印象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琐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它“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它“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1](388-390)。而普通读者关注更多的是它们作为游记散文本身的思想和艺术特征,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复杂问题”、所包含的“感慨和寓意”,以及那些“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则往往被忽略了。
过去讨论沈从文的寂寞,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寂寞,“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于被当时现实所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2](222);二是沈从文人生理想的寂寞,“沈从文的‘人的重造’思想虽然与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现代性发展有某种契合,但它与打破阶级枷锁、争取‘人的解放’的主流政治方案设计及其实践却产生了严重的错位,理想虽美却无现实性,因而只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空想”[3](11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沈从文既遭遇了文学的困境,也遭遇了个人的困境。一方面,“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新兴的革命文学,另一方面,他个人也不能认同新时代对文学的“事功”要求[4](78)。
笔者认为,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这两种寂寞产生的特殊背景如今都不存在,唯有另一给作者带来“寂寞”的重要因素,即作品被偏解,至今仍然无法消除。在文学史的盖棺论定之中和之外,到底谁是沈从文?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沈从文?这样一位始终以“乡下人”自居的作家对今天的读者、作家意义何在?他那些“感慨和寓意”,那些“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今天有没有得到解决?他那些关于重造新人和民族品德的思想,在今天有没有被接续上并得到新的拓展?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以为从沈从文的散文入手是最好的途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迄今为止的沈从文研究中,散文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和冷清,更因为与小说相比,散文“最容易表现人生”[5](73),也最容易“知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6](36)沈从文最好的散文作品自然是《湘行散记》和《湘西》,下面将对这两部作品展开讨论,尝试发现沈从文的“多重面相”。
二、观察和书写湘西的两种眼光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从印刷工人赵奎五那里偶然看到《新潮》《改造》等报刊[7](15),发现“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反复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刚接触时,他心里还“发生不少反感”,但时间一长就“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了[8](362)。对于沈从文的人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转机”,促使他想要走出湘西,摆脱“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的厄运。而对于沈从文的文学生涯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性时刻。他在报刊上所发现的“对于目前社会作反复检讨与批判”,“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以及“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皆构成他日后文学观念和实践的主体内容。《边城》《长河》等小说,《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集以及他主编的《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都是对这个发现的模仿和展开。并且由于他“乡下人”性情的执拗,他始终没有放弃和调整这个“发现”,一直在按照这个“发现”的方向规范着自己的写和不写。从写作的发生学来看,正是“五四”运动把那个青年士兵沈岳焕重造为作家沈从文。
郁达夫在谈到现代散文的特点时有一个深刻的判断,他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9](445)。沈从文的北上就正是这种发现个人的产物。他在秘密地想了四天之后,终于决定“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沈从文在人生态度与人生哲学上,从听天由命变为自我支配,这正是运用自己的理智启蒙的结果。经由这种理智的运用,他还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8](362)。日后他热心提携后进文艺青年,为湘西的团结进步出谋划策,不顾个人安危发声营救丁玲,在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中坚持捍卫作家的创作自由等行为,都是这种“为别人设想”“为未来设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年的文章里,他将“五四精神”概括为一种天真和勇敢的精神。这种不同于民主、科学的表述,无疑是沈从文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某种夫子自道。他后来的文学写作、社会活动和人生选择,也的确称得上天真和勇敢。正如他 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回忆的那样,当初他到北京时,“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都已 经过了高潮转入沉寂阶段,“除少数人对于社会种种还抱着一种顽强憎恶的态度,以为可用文学作品来慢慢动摇它、推翻它、扫荡它,除旧布 新,有个崭新的明天会来”,很多人早已“失去了‘五四’时代的兴奋热情”。反而是他这个“新从内地小城市来的乡下人”,还“呆头呆脑地 把‘文学革命’看得死板板的,相信它在将来 一定会起良好作用”,认为“这个社会必须重 新安排,年青人明天才会活得庄严一些,合理 一些”[1](373)。
离开湘西11年之后,沈从文带着自己的“五四”眼光重回故地,把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给妻子张兆和看,于是就有了《湘行散记》。又过了4年,沈从文因故在家乡沅陵住了三个多月,接触了许多地方上的人和事,深感外界对湘西的误会不利于湘西的团结,于是又写了《湘西》来“辟缪理惑”。由于散文不必像小说那样“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是一种更宜于直抒胸臆的文体,因此他在这两部散文集里就径直发了些议论。研究者也就围绕这些议论来“辩证”地评价它们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
在《湘行散记》的12篇散文和《湘西》的8篇散文里,沈从文经常提到两个词,即历史与命运;经常提到两种感受,即无言的哀戚与神圣的感动;经常提到两种对照,即读书人和乡下人的对照、过去和现在的对照。从知识社会学的视域来看,一种解释或知识,只能从某种特定社会地位的视角或眼光来阐述。密布在《湘行散记》《湘西》文本中的对照,其实反映了沈从文观察湘西的两种视角和眼光,一种是外面现代的“五四”眼光,一种是传统的乡土中国地方视角。由于“五四”思想启蒙的某种不彻底性和先天缺陷,也由于沈从文对现代启蒙了解的广度和深度都相当有限,使得他无法用“五四”视角来解释湘西的全部现象和问题,往往会碰到“说不通”的尴尬。而反过来用传统的地方视角来审视外部社会时也往往只能提供道德化、情绪化的批评,并不能切中现代文明弊病的肯綮。沈从文对湘西及其百姓的偏爱其实是对曾经养育过他的土地的深情眷恋,对外部世界的调侃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解嘲,并不是在理性的层面上对比二者的是非、优劣和美丑。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就会误以为沈从文在虚构一个怀旧的乌托邦来抵抗庞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工程,认为他缺乏基本的历史理性和现代精神。很多对他的批评正是抓住这一点做文章。沈从文虽然在现代都市生活了十几年,但并没有也不能像徐志摩和胡适那样真正融入摩登都市的内部肌理,平和从容地享受现代文明提供的便利和舒适。他在不同场合反复申说自己的“乡下人”身份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毕竟接受过“五四”启蒙思想的洗礼,见识过现代文明的轮廓,在理性上无法不与之建立认同(比如《凤凰》里对放蛊、落洞、游侠精神的现代心理学分析)。因此再回到湘西时就无法继续视原来滋养过自己的那些乡土文明为天经地义的存在,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消逝只是时间问题。面对故土的文明和人群,就像面对日薄西山的母亲,因其伟大的生养之情而在心里涌起一股“神圣的感动”,又因其日薄西山 毫无回旋余地而不得不感到一种“无言的 哀戚”。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里的一段话,颇能代表沈从文观察湘西时现代文明和乡土文明兼而有之的双重视角和眼光: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的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鹭鸶,向下游缓缓划去。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 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 哀戚。[10](253)
以乡土文明的眼光来看,“历史”确实与湘西的这些儿女们毫无关系,他们生活在靠经验累积的乡土社会,不用作什么计划,也不必吸取什么教训。因为在自然的时间进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传统的生活方案”,每个人都“依着欲望去活动”,而且那欲望往往可 以作为行为的指导,最终“印合于生存的条 件”[11](109)。而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知识即是权力,“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也是权力的象征。湘西的儿女们在历史中就像渔船上那些“黑色沉默的鹭鸶”一样没有自己的声音和位置,属于不能表述的无权人群。想到这些,沈从文心里自然会涌起“无言的哀戚”。
这种惆怅和无奈之情在《箱子岩》里表现得更加强烈:
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10](281)
既然人与自然相契合,“对历史毫无担负”,为何要给他们的心灵里制造一种“惶恐”的感受呢?为什么要转移他们狂热的方向和对象呢?因为现代文明正在步步逼近,“若不想法改变,却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说起它时使人痛苦,因为明白人类在某种方式下生存,受时代陶冶,会发生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10](376)。更何况那些“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人们仍然在把湘西神秘化,对“地方的真正好处不会欣赏,坏处不能明白”[10](355),只是在日益加重湘西儿女的苦难。
沈从文因此忍不住发出了愤怒的质问:
这应当是谁的责任?瞻望河边的风景,以及那一群肮脏瘦弱的负煤人,两相对照,总令人不免想得很远很远。过去的,已成为过去了。来在这地面上,驾驭钢铁,征服自然,使人人精力不完全浪费到这种简陋可怜生活上,使多数人活得稍象活人一点,这责任应当归谁?是不是到明日就有一群结实精悍的青年,心怀雄心与大愿,来担当这个艰苦伟大的工作?是不是到明日,还不免一切依然如旧?[1](379)
由此可见,沈从文决不想让湘西维持其原始落后的面貌,好给都市里烦闷无聊的现代人提供一个休闲的胜地,或是给怀旧的知识分子存留一个宜发思古之幽情的古迹。恰恰相反,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自己细腻的描写和叙述来激发外人对湘西应有的理解和同情,来唤醒湘西青年上进的意志和心劲,一面克服负气和自弃的性情,一面培养自尊心,让湘西青年意识到自己对湘西对历史的责任远比个人的得失荣辱来得重要,以实现湘西的重造。至于对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曾芹轩、辰河船上的水手和妓女、虎雏以及从容跃井的煤矿工人的赞美,不过是出于对现代教育所造成的“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的不满,对现代文明规训下人的生命活力日渐萎缩的忧虑。而不是在拿湘西社会与外部世界对比并褒前贬后,更不是要刻意美化湘西的人和事、掩盖其间真实的苦和痛。在沈从文看来,湘西儿女固然在人事上有缺点,需要知识和理性的补救,才不至于在新一轮竞争中又被历史淘汰;然而那些经受过启蒙思想和现代文明洗礼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却是一团糟,有的甚至荒诞不经,而且个人的灵魂和情感在这种知识和理性的主宰下失去了安放的空间,淳朴忠厚的道德也在唯实唯利的风气下荡然无存,许多青年“成了颓废不振萎琐庸俗的人物”[1](312),各自在自私地打着自己的算盘。沈从文自己作为“五四”之子,面对启蒙的困境,不知如何去调适和解释,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知识的僭妄”。
这种不满和忧虑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用“爱和美的宗教”而不是用知识和主义来重造新人的思想。《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里那位姓印的近视眼朋友在北伐军一进入湖南就立即参加了党务学校,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和训练,对革命和政治的热情达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还俨然以黄袍加身的“伟人”自诩和自居,可是等到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却摇身一变当了地方的百货捐局长,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完全把革命和政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连与沈从文这个可能跟共产党有牵连的老朋友会面都不敢。从当代文学中新人的曲折重造史来看,不得不承认沈从文的立人思想确实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具有某种深刻的预见性。因为,“那种理性凝聚的伦理命令使所建造的‘新人’极不牢靠,经常在这所谓的‘绝对律令’崩毁之后便成为一片废墟;由激进的‘新人’到颓废的浪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有‘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的情感的陶冶塑造,才有真正的心灵成长,才是真实的人性出路”[12](129)。
三、深切的地方性与“照我思索”的方法论
《湘行散记》《湘西》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其真实可感的地方性。它既体现在沈从文对湘西的地理、方言、风俗、人情、心理的准确把握上,也体现在他对湘西地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全面了解上。《鸭窠围的夜》里杨氏托水手“大老”给自己儿子顺顺捎的话,《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水手牛保跟河街妇人情意缱绻的对话,都写出了湘西人那种活泼泼的生命和心灵。《常德的船》细致描绘了沅河两岸的大小船只,从名称、桅杆、结构到材质、功能、数量,无一不交代得清清楚楚,可读起来却引人入胜,并不觉得枯燥。因为沈从文的态度不像社会学的田野调查那样客观中立,而是饱含着对故乡的感情、对船只和水手的善意去观察和下笔的,使人和船结合在一起,船的形制代表了人的个性。沈从文看似是在写常德的“船”,实际上是在写地方上那些可爱的驾船水手,以及船浮泊在其中且养育了地方儿女的河流。雨果在给《克伦威尔》作的序里说,“准确的地方性是真实性的一个首要的因素”。他还以戏剧为例说明了这个艺术规律,“一出戏中,并不是只靠有台词、有动作的人物把事实的忠实印象铭刻在观众的脑海里。发生变故的地点也是事件的不可少的严格的见证人;如果没有这一不说话的人物,那么,戏剧中最伟大的历史场面也要为之减色”[13](49)。正是因为沈从文在散文中对地方性的准确描写,才使读者信任并爱上了他笔下的湘西,反过来也使读者只要一提起湘西就会想起沈从文,并且使现代散文也具备了“传奇的魅力”[14](118)。
在新时期以前,沈从文是因为其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与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成规存在区别,也因为其对于人生和社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故常常被视为是一位缺乏社会性和思想性、离被压迫的人民较远的“空虚的作者”[15](187)。在今天普遍的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社会接受语境中,他又被想象成一位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兴趣不大,一心守护着自己文学理想的“纯文学”作家。二者的批评标准不同,结论却十分相似。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有很多,在一般读者那里主要是因为对沈从文作品的阅读量不够,仍停留在《边城》留下的印象中,脑子里只记得茶峒的秀丽风光、乡村少女翠翠和两个少年令人忧伤的爱情;在很多专业读者那里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京派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的误导,还没有阅读完作家的作品,就概念化地认为既然沈从文是京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与朱光潜、徐志摩、胡适等自由主义人士过从甚密,那么肯定不会像鲁迅那样写渗透着“血和泪”的作品。而事实上,《湘行散记》《湘西》,特别是《湘西》,的的确确是包裹着湘西苗族儿女在漫长的黑夜中所倾流的“血和泪”的,也写出了沈从文对湘西儿女的深厚悲悯、对未来湘西的深刻忧患。这是由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个人性情、审美理想和语言方式所决定的。对于这种误解,沈从文自己似乎早有预见,在回答凌宇关于作品批评的提问时,他说,“凡是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16];在遗作《抽象的抒情》里他又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1](527)。批评可以有“前理解”,但不能有既定的“观点”和先入之见,不然就只能理解自己愿意理解的,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而“碰不到问题”,没有说服力。理解沈从文,也只能用沈从文的方式去理解他,正如他在《辰溪的煤》里所说的,读书人要想明白湘西儿女生命的庄严与光辉,就必须在调查和同情以外看到湘西人长期在无知和穷困的包围中所形成的生命态度的必然性,也就是要从“当地人的观点出发”,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他者”。
20世纪中国加速前进,个体从出生到死 亡横跨了两个时期以上,这种福泽谕吉所说的“一生而历两世”,即历史奔跑着逃离人类的现象,导致人的“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17](33)。很多人在人生的一个时期不得不怀疑和否定另一个时期,在一种场合的言行不得不怀疑和否定另一种场合的言行。沈从文也身处这个动荡而“断裂”的世纪,不过由于他始终“守住一个‘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绝不依傍任何特殊权势 企图侥幸成功,也从不以个人工作一时得失在意”[1](388),所以他不至于出现个人“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的情形,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在《湘行散记》《湘西》里所担忧的地方问题,比如“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来开发,来教育。统治者不以‘征服者’自居,不以‘被征服者’对待苗民”[10](410)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湘西儿女的生活也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日益改善。沈从文彼时身处现代与传统夹缝 中的文化境遇,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普遍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仍有其现实迫切性,乡关何处仍是萦绕在每一个现代人心头的精神难题;沈从文对“五四”思想启蒙的困境和知识、理性有限性 的洞察,对于生活在技术主义罗网中的人们,也不失为一种警示。所有这些问题的开放性、有效性,均构成了我们(“我们”已不能视为一个不言自明的集合词)今天去“重读”沈从文的理由。
四、余论
自1980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在1984—2012年的1 763篇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里,有28篇以沈从文为研究对象,仅次于鲁迅研究[18];在中国知网以“沈从文”为主题可检索到8 353条文献,远高于除鲁迅之外的其他现代作家。从这些大数据可以看出,沈从文在“文学性、审美性和新时期文学策略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已被经典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部分[19]。
由于沈从文独特的成长经历、文学观念和审美旨趣,也由于《文学者的态度》《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等文章所引发的争论,沈从文研究在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里一度是个无人问津的禁区,甚至在“文革”快结束时一些青年作家都仍然不知道他的存在[20](45)。在1980年代,“纯文学”“回到文学本身”“人道主义”“主体性”等话语谱系占据主导地位,沈从文也正是在这种知识范型中被重新阐释的;原来的那个“反动作家”“桃红色作家”变成一个在动荡历史中始终坚守自己审美趣味的文学朝圣者。这正是今天伍尔芙意义上的“普通读者”对沈从文的认知。此种看似回归文学本位的阅读方法,实际上是对作家的压缩和简化,因为“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品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所提供的有关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蕴含”,实在让人眼花缭乱[21](390),远非一个纯文学作家的标签所能概括。
南非作家库切在谈到巴赫的经典化历程时认为,巴赫之所以成为巴赫,“不是由于音乐品质纯净而明快的缘故,至少在其音乐加以适当的包装然后推出之前不是如此。巴赫的名字和巴赫的音乐必须成为一项事业的一部分,而这项事业就是因反抗拿破仑而兴起的德国民族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清教复兴。巴赫的形象成了宣传德国民族主义和清教主义的工具之一;与此同时,以德国和清教主义的名义,巴赫被推为经典”[22](14)。1980年代以来,沈从文其实也成了“一项事业的一部分”,那就是摆脱过去那种文学从属于、依附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命运,转而追求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洽性,建立一种自由书写人性和自我的文学哲学。这项事业以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为中介,直接启发了先锋派的写作。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自我不仅在作家那里变成普遍的哲学”,而且成为“文学创作的唯一篇章结构和叙述方式”[23]。沈从文也在这种书写人性和自我的文学认知装置中,被视为仅次于鲁迅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24]。沈从文研究著作中最常见的切入点和关键词也是“人性”[25]。今天的普通读者和文学青年对沈从文的认知与评价,仍然处在这种人性和自我书写的思想脉络之中,并将之视为自身对沈从文作品的真实阅读感受,而没有察觉到那种感受其实受制于文学史的塑造。对于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文学史家来说,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最缺少的就是“面对苦难、荒诞时坚持自我的勇气,就是‘纯文学’的执着和那种极其浪漫、理想的爱情传奇”[26]。而这些正是文学家沈从文的强项和特质,沈从文就这样作为文学与思想“资源”被回收和投放到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生成机制之中,其作家形象和文学史位置也被重新规划和厘定。正如美国学者阿诺德•克拉普特所说,“经典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更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秩序化”[27](57)。沈从文自1980年代以来被确认为“文学史经典”和“文学经典”,也是为了“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个人脱离“大我”、谋求“小我”成功的观念取得了自身的合法性,自我主体性的发挥也无时无刻不受到资本逻辑的召唤。而那种文学“完全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存在模式,恰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它的物质性运作需要的主体性意识形态模式”[28](9),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那些迷信自我神话、人性神话的文艺青年,还有那些迷信资本神话、成功神话的中产阶层,都如此青睐沈从文这类作家的原因。
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化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如何对待及进行文学的经典化,值得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1]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16卷[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SHEN Congwen.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Vol 16[M].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2.
[2]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QIAN Liqun, WEN Rumin, WU Fuhui.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Revised Edition)[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罗宗宇. 沈从文思想研究[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 LUO Zongyu. Research on Shen Congwen's thought[M]. Changsha: Hun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张新颖. 双重见证[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ZHANG Xinying. Double witness[M].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5.
[5] 钱穆. 中国文学论丛[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QIAN Mu. Chinese literature review[M]. Beijing: Life·Reading·Knowledge Bookstore, 2002.
[6] 梁实秋. 论散文[C]// 俞元桂.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LIANG Shiqiu. On prose[C]// Yu Yuangui. Chinese modern prose theory. Nanning: Guangxi People's Press, 1984.
[7] 吴世勇. 沈从文年谱[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WU Shiyong. Chronicle of Shen Congwen[M]. Tianjing: Tianjin People’s Press, 2006.
[8]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13卷[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SHEN Congwen.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M].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2.
[9] 郁达夫.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C]// 俞元桂.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YU Dafu. Department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Prose II’ introduction[C]// Yu Yuangui. Chinese modern prose theory. Nanning: Guangxi People's Press, 1984.
[10]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11卷[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SHEN Congwen.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M].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2.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FEI Xiaotong. Native China[M].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15.
[12] 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LI Zehou. On historical ontology [M]. Beijing: Life·Reading·Knowledge of bookstore, 2002.
[13] 维克多·雨果. 雨果论文学[M]. 柳鸣九,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HUGO V. On literature by Victor Hugo[M]. Trans. Liu Mingji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2011.
[14] 王尧. 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WANG Yao. Where is the township: The cultural spirit of Chinese prose in the 20th century[M]. Beijing: Oriental Press, 1996.
[15]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C]// 邵华强. 沈从文研究资料: 上.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SHI Heng. An inane author: Comment on Mr. Shen Congwen and his works [C]//Shao Huaqiang. Research materials of Shen Congwen: I.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ss, 2011.
[16] 凌宇. 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对一些有关问题的回答[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0(4): 315-320. LING Yu. Shen Congwen talks about his own creation: Answers to some related questions[J].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agzine, 1980(4): 315-320.
[17] 米兰·昆德拉. 相遇[M]. 尉迟秀,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KUNDERA M. Meet[M]. Trans. YUCHI xi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2010.
[18] 洪亮. 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3(7): 128-137. HONG Liang. Analysis on topic selection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84 to 2012 year[J].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agzine, 2013(7): 128-137.
[19] 任南南. 转型语境和人性话语: 新时期初期的沈从文重评[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93-100. REN Nannan. Transformational context and human discourse: Reconsideration of Shen Congw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period[J]. 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5): 93-100.
[20] 汪曾祺. 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C]// 朱光潜, 荒芜.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WANG Zengqi. Shen Congwen's loneliness: Talking about His Prose[C]// Zhu Guangqian, Huang Hu. Essay in my Opinion of Shen Congwen. Changsha: Yuelu Press, 1986.
[21]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Dialogue between Jia Pingwa and Xie Youshun[M]. Suzhou: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 库切. 异乡人的国度[M]. 汪洪章,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 COETZEE J M. Country of strangers[M]. Trans. Wang Hongzhang.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10.
[23] 程光炜. “史诗”和“故事”: 在自我的历史能量耗尽后[J].上海文学, 2019(1): 127-136. CHENG Guangwei. "Epic" and "story": After the ego’s historical energy is exhausted[J]. Shanghai Literature, 2019(1): 127-136.
[24] 王一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M].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4. WANG Yichuan. Library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s about novel[M]. Haikou: Hainan Press, 1994.
[25] 吴立昌.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WU Lichang. "Humanity therapist"——Biography of Shen Congwen[M].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3.
[26] 程光炜. 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J]. 文艺争鸣, 2007(2): 47-49. CHENG Guangwei. Many problems impli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entury literature[J]. Literary Contention Magzine, 2007(2): 47-49.
[27] 阿诺德·克拉普特. 美国本土文学与经典[C]// 乐黛云. 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KRAPT A.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lassics[C]// Yue Daiyun. Selected works of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for ten years.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1996.
[28] 特里·伊格尔顿. 审美意识形态[M]. 王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EAGLETON T. Aesthetic ideology[M]. Trans. Wang Jie.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Shen Congwen's multifaces seen fromand
TANG Xiaox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ner Mongolian University, Hohhot 010070, China)
From the two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home-coming,and, we can see the author's dual perspectives and visions combining both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local color in observing and writing his west Hunan, his deep concern about locality and his methodology of reflecting on thinking. We can also feel the author’s tenacious belief that literature can reconstruct a society, a country and a new man, his pondering over the colli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rural civilization and modern urban civilization, and his clear insights into the dilemma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finitenes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rationality. Hence, we can discover multiple facets in both Shen Congwen and his works. Since the 1980s, Shen Congwen has emerged to the surface of history from the pure literary knowledge pedigree, and has gradually been canonized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is kind of reading method that seems to return to the literary ontology is actually a dilu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writer. Behind the canonization of literature, there tend to exist complicated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And how to treat and carry out the canonization of literature is worthy of more in-depth thinking.
Shen Congwen;;; locality; lonesome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1.03.016
I266
A
1672-3104(2021)03-0169-09
2019-08-10;
2021-04-07
唐小祥,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联系邮箱:shaoyangtang@126.com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