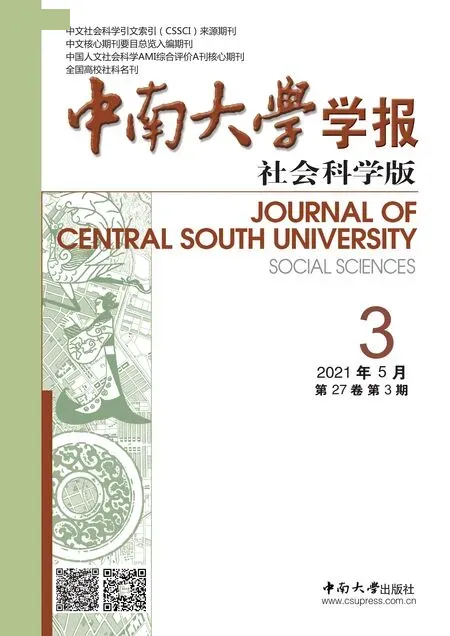大数据竞争行为对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挑战与应对
2021-06-17叶明张洁
叶明,张洁
大数据竞争行为对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挑战与应对
叶明,张洁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401120)
在数字经济时代,围绕数据的获取、使用、分析等展开的大数据竞争行为逐渐涌现。虽然大数据竞争行为具有激发市场竞争活力的积极效果,但也可能诱发垄断风险,因而引起反垄断关切。鉴于大数据竞争行为的主体具有企业与市场的二重性,手段依附于数据与算法的运用,后果较为复杂,其反垄断执法原则、执法工具、执法方式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具言之,在执法原则方面,矫正适用包容审慎原则,秉持积极的规制态度;在执法工具方面,围绕非价格竞争维度健全执法工具,并引入技术监管,培育“以技术规制技术”的意识与工具;在执法方式方面,注重运用以反垄断约谈为代表的柔性执法方式。
大数据竞争行为;反垄断执法;包容审慎;非价格竞争;反垄断约谈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目前人类已经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1]。在我国,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核心的增长级之一。例如,从2005年到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由2.6万亿元扩大至35.8万亿元,数字经济在GDP中的比重逐年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并进一步凸显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价值。因此,在我国政府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同时[2],市场经营者之间围绕数据资源展开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尽管围绕数据的获取、使用、分析等展开的大数据竞争行为具有激发市场竞争活力的积极效果,但也可能诱发垄断风险,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成为阻碍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不良因素”。在实践中,顺丰与菜鸟物流的数据争夺战[3]、腾讯与华为的数据之争[4]等即为印证。因此,我国社会各界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垄断风险均投以高度关注,并呼吁反垄断执法机构及时回应。在此背景下,我国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垄断指南》)中均吸收了数据与算法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反垄断关切。但一方面,鉴于相关规定的模糊性、原则性,其实践效果如何尚待进一步检验,将依赖实践经验予以反向补足;另一方面,这一回应相较于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规制需求而言仍然不够,比如没有关注经营者不当采集和使用数据等剥削性滥用行为。故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规制大数据竞争行为时,仍面临较多难题。对比当下域外竞争执法机构已经开始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执法进行探索,对部分行为展开调查①甚至作出处罚,典型如“德国脸书案”等②,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回应态度稍显低沉。为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并助力我国在全球市场中抢抓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机遇,引领和参与制定国际竞争规则,有必要积极探索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执法问题。
互联网领域非法外之地,大数据竞争行为也不应因其新颖性与特殊性而当然地排除适用反垄断法。在面对大数据竞争行为时,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应否对其进行规制,而是应秉持何种执法原则。在确定基本的执法原则之后,需进一步思考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特殊性对反垄断执法提出了何种挑战,并寻求因应对策。目前,虽然我国学者已经围绕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规制问题展开了一些研究,但多集中于大数据竞争行为关涉的具体反垄断规制问题,较少关注执法原则、执法方式等前提性、基础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对大数据竞争行为进行反垄断法有效规制的重要议题。故本文将从宏观的、系统性的视角研究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执法问题。首先,依循反垄断法规制垄断行为的一般思路,指出大数据竞争行为在主体、手段、效果上的特点及其影响,以勾勒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真实样貌。这是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执法如何作出改变的前提与基础。其次,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思维路径,分析当下的反垄断执法原则、执法工具、执法方式因应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特点作出何种改变,以明晰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执法思路。
二、执法对象的考察: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真实样貌
因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与变化,有效回应反垄断执法需求的前提是正确认知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真实样貌。就行为类型而言,在反垄断法规制视阈,大数据竞争行为可能牵涉的仍主要是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等三种垄断行为。本文主要依循反垄断法规制垄断行为的一般思路,从行为主体、行为手段、行为后果三方面来阐明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特点。
(一) 行为主体:主要是互联网平台企业
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系实施大数据竞争行为的重要主体,是反垄断执法的主要关注对象。这一方面与反垄断法重点关注市场支配力的行使与市场结构的变更有关,而互联网平台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能力与可能性,同时也是企业并购的重要实施主体。另一方面,则因为当下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基于自身庞大的用户数量,容易在数据方面形成竞争优势,从而更容易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中小企业则更可能成为相关垄断行为的受害者。
不同于市场以价格机制决定资源配置,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5]。源于此,传统行业的市场经营者通常被认为仅扮演企业这一角色,仅发挥企业的功能。但是,互联网平台企业除了作为企业存在以外,往往借由其平台为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交易场所,发挥着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表现出企业与市场的二重性。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企业以主营业务为核心,在不同的相关市场与其他经营者展开竞争,此时其内部的资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在此意义上,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企业的性质。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企业又不局限于像传统企业一样直接生产或销售商品,更多是把供给和需求有效匹配起来,让销售者和消费者找到最适合的彼此[6]。就此而言,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市场管理权力。
行为主体融合企业与市场双重功能的特点,首先决定了不能单纯从企业角色这一维度判断互联网平台企业实施的大数据竞争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平台所具有的免费定价、双边市场、数据驱动的网络效应③等特点必须被考虑在内。其次,提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规制大数据竞争行为时,应当关注平台自治与市场竞争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如上所述,互联网平台企业扮演的“市场角色”赋予了互联网平台企业一定的市场管理权力。这种管理权力的行使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7],但同时也容易异化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实施垄断行为的手段,能够帮助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杠杆效应实施垄断行为。从发展趋势来看,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典型如目前备受关注的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因此,如何界分正当的平台自治行为与不正当的大数据竞争行为,厘清正当的平台自治行为与垄断行为之边界,值得反垄断执法机构思考。
(二) 行为手段:依托数据与算法
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是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核心特点。其中关涉两项基本要素:一是(大)数据④,二是算法。前者构成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基础原料,后者则提供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基本技术。在实践中,二者总是相辅相成。经营者主要借助(大)数据与算法实施大数据竞争行为,因此,相关垄断争议多围绕数据与算法这两项基本要素展开。如何正确衡量数据与算法的角色、地位等成为适用反垄断法规制大数据竞争行为的新命题。
当今,算法已取代电话、邮件、会议等传统方式成为市场经营者实现共谋的新方式。经营者可以利用由数据驱动的算法实时监测竞争对手的行为与反应,并据此调整己方的经营策略与行动。如2015年美国司法部首次针对算法共谋行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亚马逊网站上某电商主管Topkins伙同其他共谋方采用特定的定价算法,固定特定海报产品的价格⑤。在某些情况下,如通过预测类算法、自主类算法的使用,甚至可以仅借助算法而不依赖经营者的沟通交流或意思联络达成默示共谋[8]。就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而言,数据既可能作为投入要素成为影响经营者市场支配力的新型重要因素,也可能作为价值产品本身成为决定经营者市场支配力的新型关键因素⑥。围绕数据采集、数据使用、数据分析等展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可能性日益增长。前述“德国脸书案”、顺丰与菜鸟物流的数据争夺战等均凸显了此种垄断隐忧。数据更可能直接构成推动经营者集中的主要因素,增强数据拥有量、强化数据控制力成为部分经营者集中行为的目标。如在微软收购领英案中,获取领英后台完整详实的客户数据被认为是微软实施并购行为的重要驱动力[9]。欧盟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也重点关注了二者整合用户数据的行为是否会对在线广告服务等相关市场带来竞争损害⑦。
(三) 行为效果:具有复杂性
不可否认,大数据竞争行为存在垄断风险,这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其投以反垄断关注的前提。但这仅仅构成大数据竞争行为效果的一个方面,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行为后果实际上更加 复杂。
其一,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行为后果具有双重性。在可能招致垄断后果的同时,大数据竞争行为也可能带来促进竞争、提高消费者福利、提升效率的正面效应[10]。
其二,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垄断危害具有不易识别性或隐蔽性。这既指因为数据、算法的运用,大数据竞争行为变得更为技术化、智能化,人们有时难以察觉垄断行为的发生;又指因为“数据黑箱”“算法黑箱”的存在,数据垄断的形成机理趋于复杂化,人们不容易辨别相关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否属于反垄断法规制范围内的竞争损 害[11]。例如,合法使用定价算法提高效率与非法使用定价算法限制竞争的分水岭难以界定[12]。
其三,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垄断后果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体现在对数据、算法的认知不足或不一致,导致人们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垄断风险存在不同判断。比如,能够形成市场支配力的究竟是经营者对数据控制的本身还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13]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风险判断。也有观点认为,数字经济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复杂性、界定数据相关产品和地域市场存在的固有困难,导致规制机构无法辨别相关行为是损害竞争还是促进竞争[14]。另一方面,体现在对部分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垄断危害可能存在场景预设的问题。例如,自主学习类共谋尚未有实际案例,未来能否真正实现也尚未可知。德国著名反垄断经济学家Schwalbe亦指出,自主学习类共谋主要是学者们的一种想象,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重要问 题[15]。就实践情况来看,“虽然有诸多迹象显示数字市场的运行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目前算法共谋对市场的损害尚未被证成”[16]。就此而言,当下对部分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反垄断关注属于超前担忧。
三、执法原则的确立:包容审慎原则的矫正适用
对大数据竞争行为采取何种反垄断执法原则,直接反映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基本态度,也会影响反垄断执法工具、执法方式的选取,对匡正反垄断执法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反垄断执法本质上属于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故选取何种执法原则的根本因素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众所周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当下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在确立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执法原则时,必须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政府只能适度干预。鉴于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行为主体兼具企业与市场的双重功能,当下对数据、算法技术的认知尚不成熟,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行为效果又较为复杂,反垄断执法失误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为实现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适度规制,宜继续秉持我国政府针对新经济业态确立的包容审慎原 则⑧。不过,回顾过去12年内我国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情况,包容审慎原则似乎并未达到实效,有关包容审慎原则的质疑甚嚣尘上。因此,面对大数据竞争行为,我们有必要反思包容审慎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
(一) 互联网领域包容审慎原则的实践与 质疑
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执法秉持包容审慎原则的旨趣,在于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积极效用,释放互联网经济红利,最大程度避免不恰当的反垄断执法错误干预市场发展,造成不可挽回、不可弥补的损害。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当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政府对于市场力量的尊重[17]。其中蕴含的具体逻辑则可以分解为一个基本前提与基本假设(或确信):反垄断执法存在失误(基本前提)与市场本身相较于执法机构更具错误修复能力(基本假设)。
众所周知,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规制垄断行为时既可能产生假阳性失误(或积极失误)的后果,也可能产生假阴性失误(或消极失误)的后果。前者指有效的竞争性行为被反垄断执法机构误认为是反竞争行为而禁止;后者指反竞争行为被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为正常的商业行为[18]。二者均会带来一定成本。由于不可能完全避免反垄断执法中假阳性失误或者假阴性失误的发生,故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判断二者的相对成本高低,从而在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之间做出选择,以最小化社会总成本。选择依据主要是对市场与执法机构纠错能力的认知。如果认为市场本身较之于执法机构更具纠错能力,假阴性失误可被市场矫正而假阳性失误很难被矫正,则更为关注假阳性失误的问题,倾向于放松规制;反之,则更为关注假阴性失误的问题,倾向于加强规制。我国采取包容审慎原则的依据即在于确信市场本身较之于执法机构更具纠错能力这一基本假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力不足,执法经验欠缺,对其是否具备有效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存疑,另一方面则应当是受在反垄断法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芝加哥学派之影响——该学派的基本理念是市场可以通过市场进入实现自我矫正,因此假阴性错误能够得到纠正,而假阳性错误很难纠正[19]。
在这样一种原则指导下,“除非非常明确,否则不予干预”成为我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基本态度。这无疑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空间——“我国所推行的包容、审慎之路为数字经济产业在短期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提供了有力的机制保障”[20]。多年来,尽管我国学界一直强调反垄断执法的包容审慎不等于投鼠忌器、消极放纵,可过去12年内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案件数量为零的不争事实,也招致了“将包容审慎等同于无为而治”的质疑[21],“反垄断法作为行为禁止法的谦抑性面临拷问”[22]。亦有学者指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执法过于谦抑导致执法回应不足[23-24],并围绕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25]、数字内容平台版权集中[26]、网约车经营者集中[27]等具体主题展开分析。对比同一时间境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情况,如欧盟数次对谷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罚款⑨、美国司法部近期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28]等,此种质疑更凸显其必然性,值得关注。
(二) 包容审慎原则的新要求
从我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既往情况来看,尽管反垄断执法机构秉持的是包容审慎原则,但就其落实该原则的方式与结果而言,更像是走入了规制观望的误区,未能在需要干预的时机恰当介入市场,事实上偏离了包容审慎原则的基本要求,从而招致社会各界的争议与批评。借鉴以往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执法经验,针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执法需要格外关注如何正确践行包容审慎原则的核心问题,区分包容审慎与行政不作为的界限,避免包容审慎滑向行政不作为的误区。对此,我们认为除了在微观层面提升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增强执法透明度外,还应从以下两方面调整适用包容审慎原则。
一是应当对“市场本身相较于执法机构更具错误修复能力”这一基本假设持审慎态度。如前所述,市场较执法机构更具纠错能力这一基本假设是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互联网领域保持克制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就某一行为或某一领域的反垄断法规制而言,要判断“相较于行政机构的积极执法,市场本身是否具有更强的纠错能力”往往需要结合实证研究,产生一个综合的“经验判断”。实证材料的积累、支撑是得出妥善结论的前提之一[29]。因此,就某一行为或某一领域的反垄断法规制而言,事实上很难抛开现实情况(包括具体国情、市场本身发展状况等)而从理论层面单独讨论市场与政府在纠正垄断行为中的作用。例如,芝加哥学派秉持“市场本身相较于执法机构更具纠错能力”这一观点的基础在于其认为假阴性失误能够通过市场进入得到纠正(即市场的自我矫正),而假阳性失误很难得到纠正。但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市场进入并不一定如想象中的快速、简单,更何况尚需考虑市场自我矫正的频率、速度、程度⑩。如我国有学者指出,就数字内容平台的版权集中行为而言,版权集中赋予的垄断力量不能自毁,版权集中缔造的壁垒导致假阴性失误不能通过长期动态竞争实现自愈[26]。现实情况也证明,很多互联网企业的支配地位虽然不是永久的,但通常持续很长时间。市场自我矫正的力量得到一些质疑,因此,面对大数据竞争行为,应当对“市场本身较执法机构更具错误修复能力”这一基本假设持审慎态度。同时,无论是从近12年我国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情况及其反馈、互联网领域频现的垄断争议等,还是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提升上来看,在缺乏市场实证研究的情况下,默认市场本身相较于执法机构更具纠错能力这一前见,也不见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二是应当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秉持积极的规制态度。就大数据竞争行为规制而言,对“市场本身相较于执法机构更具错误修复能力”这一基本假设持审慎态度,意味着假阳性成本与假阴性成本的判断更为困难,反垄断执法机构因此更难判断正确干预大数据竞争行为的时间、限度等。在无从得知假阳性成本抑或假阴性成本更高的情况下,转换规制观望的态度,主动积累实证经验,对于解决问题可能更有意义。毕竟反垄断执法中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始终难以避免,但执法机构若以此为由完全居于幕后状态,则可能导致执法不力,也可能因为实践经验的缺乏反而限制问题的解决。我国互联网领域频现的垄断争议与国内外反垄断实践的对比情况即为例证。
如此做法也有助于避免先包容后审慎的实践操作导致包容与审慎之间的生硬割裂。目前我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迎来所谓的“强监管时代”。对比此前该领域较少的反垄断执法情况,此种“先包容后审慎”的实践操作难免有割裂包容与审慎之疑。其不良效果较为明显:反垄断执法干预稍显迟钝,不少垄断纠纷引发社会各界争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与可信赖性遭受一定损害。对大数据竞争行为持积极规制态度,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持续关注、主动研判相关问题,能够避免割裂实施包容审慎原则的不良 后果。
有必要指出的是,主张对大数据竞争行为持积极规制态度不等于抛弃包容审慎的基本要义,不是要求执法机构在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基本样态、竞争效果等尚不清晰时贸然干预,也不同于单纯强调“让子弹多飞一会儿”而执法机构扮演局外人角色,而是强调执法机构应当切实结合现实背景主动探索,在执法应当有所回应时积极回应,避免一味地踌躇不前。
四、执法工具的革新:传统执法工具箱的局限与改进
明确对大数据竞争行为采取何种执法原则之后,需解决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认定问题,即怎样认定某一大数据竞争行为构成垄断行为。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评估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竞争效果。反垄断法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围绕这一问题形成独有的分析框架与工具。虽然针对不同类型的垄断行为,分析框架有所不同,但就分析工具而言,并无本质差异。对于传统工业时代的竞争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任务主要在于正确运用手中的分析工具,判断争议行为是否符合反垄断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要件。如果符合构成要件,则认定相关行为构成垄断。但是,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特殊性对传统执法工具提出了挑战,执法机构面临的难题是现有的反垄断执法工具难以认定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竞争效果。如果因循守旧,可能错误评估大数据竞争行为的损害,导致名为保障竞争实为不当放纵垄断行为的不良后果,将包容审慎原则的实践推入无所作为的误区。
(一) 传统执法工具箱的局限性
1.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执法工具应对乏力
在传统工业经济中,市场竞争主要围绕价格展开,反垄断法规制体系也因此形成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规制逻辑。无论是在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还是在竞争效果分析等方面,价格一直是反垄断审查的核心要素。但是,面对大数据竞争行为,传统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执法工具暴露出局限性。其表现是:一方面,延续互联网领域固有的反垄断执法难题,互联网平台企业所具有的价格免费、双边市场等特点对于以价格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传统执法工具提出挑战,包括基于价格上涨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法(SSNIP)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的无力,单一市场份额标准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上的不足,营业额申报标准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局限等。另一方面,无论是互联网平台基于数据“反馈循环”形成的网络效应,抑或数据、算法技术的广泛使用,均要求在反垄断审查中考量数据和算法技术扮演的角色、地位,传统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执法工具显然对此毫无准备。
究其根本,传统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执法工具之所以应对乏力,原因在于围绕数据获取、使用、分析展开的竞争本质上是市场经营者在非价格维度展开的竞争,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价格竞争已经逐渐被非价格竞争取代。这不仅表现在延续互联网时代的基本特点,数字经济时代的诸多产品、服务往往“免费”或“零价格”,更表现为在此基础上,隐私、创新等成为新的竞争维度。如在微软收购LinkedIn案中,隐私问题就被作为反垄断审查的一部分⑦。这意味着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垄断危害或许不必然是价格居高不下,而是产品质量、研发创新和用户隐私安全等方面的损害[30]。鉴于此,传统立足于价格竞争基础上的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反垄断分析范式表现出不适用性。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评估某些数据驱动型案件时,目前的分析工具往好了说表现平庸,往差了说毫无价值[19](13)。
2.技术性规制工具欠缺
除了传统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执法工具表现不佳以外,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既有执法工具难以充分回应规制大数据竞争行为时关涉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如上所述,大数据竞争行为以数据、算法的广泛应用为基本特点。这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要实现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有效规制,必须对数据、算法技术在大数据竞争行为中的应用原理、运作机理等基本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正确认知。大数据竞争行为在危害后果上表现出的不易识别性与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也归因于当下对于数据、算法技术的认知不足和认知不一。而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而言,数据如何运用、算法如何运作等技术性问题往往属于知识盲区。另一方面,数据、算法的结合运用可能会突破反垄断“人类中心主义”的规制框架[16],传统以“人类行为”为中心设计的规制工具可能失效。例如,就算法共谋而言,无论是行为的发现、调查抑或取证,对传统行政规制工具在时效、证据发现、证据固定等多方面均提出挑战。在单纯的法律监管维度之外引入技术监管,能够帮助反垄断执法机构客观地、准确地认识与判断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行为效果,并减少大数据竞争行为规制中不必要的争议。
(二) 反垄断执法工具箱的完善
1.关注非价格竞争
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反垄断执法工具明显难以满足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规制需求,因此,非常直观的解决之道在于关注非价格竞争,围绕非价格竞争形成新的测度工具[22,31]。对此,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已经有所关注,并在《反垄断指南》中给予了适当回应。但是,尚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其一,从《反垄断指南》的内容来看,目前我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更多地关注数据作为投入要素、算法作为技术工具所带来的规制问题,在传统反垄断法规制框架下吸收了数据、算法这些新要素,包括利用数据、算法达成共谋,考量数据、算法在赋予经营者市场势力中的作用等,对于单独的数据产品或服务给反垄断法规制提出的挑战并未作出回应。考虑到当下单独的数据产品或服务逐渐涌现,也存在针对纯粹的数据市场进行单独的市场界定(或跳过市场界定步骤)、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等可能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还需持续关注如何围绕“数据市场”这一更具特殊性的市场形成一套比较体系化的分析理论。
其二,在《反垄断指南》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表达了对非价格竞争的分析、测度主要采取定性分析方法的倾向,对于定量分析方法的革新并未回应。当然,在定性分析的结果足够明确时,确无必要进行定量分析。这也契合当下的需求,毕竟要求针对非价格竞争进行精准的量化测试短期内可能并不现实。以学界广泛认可具有代表性贡献的“奇虎360诉腾讯QQ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为例,在该案中,针对产品差异化明显且质量、服务等非价格竞争成为重要竞争形式的互联网即时通讯领域,最高法院虽然采用SSNIP测试法的替代方法SSNDQ测试法(基于质量下降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法)进行了简单分析,但也仅针对少数情况,且主要是适用SSNDQ测试法的基本逻辑进行定性分析,而非定量分析。但是,这种定性分析方法能否切实解决大数据竞争行为规制中面临的问题存疑,定性分析方法的主观性、不确定性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长久来看,仍旧有必要探寻非价格竞争的量化分析工具。对此,我们认为可以考虑SSNIC测试法(基于成本上涨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法)的适用,借助数据定价实现非价格竞争的量化。这一方面是因为质量指标具有消费者异质性、消费者敏感度弱的特点[19](137147),对质量指标进行客观测度的难度较大,因此SSNDQ测试法具有一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契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个人数据的授权使用事实上成为消费者的主要投入成本,伴随着数据价值化进程的推进,和数据确权、数据交易的发展,实现数据定价并非完全不可能。通过数据定价事实上可以解决SSNIC测试法所需要的成本测算问题,包括基准成本的选取、成本上涨幅度的确定等。
2. 引入技术监管
数据、算法的广泛应用,使得在法律维度之外增加技术监管成为必然选择。针对大数据竞争行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确立并培育“以技术规制技术”的意识,学会充分利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其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充分借助技术专家力量、平台力量等补足自身在技术知识方面的欠缺,为进行有效的反垄断法规制打下基础,包括深入研究数据、算法涉及的技术问题,在具体行政执法过程中吸收专家力量,听取专家建议等。其二,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可充分利用市场力量,鼓励市场主体研发反制技术。例如,“消费者算法”被认为可以帮助消费者识别价格、识别合谋[32],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垄断行为的发生频率,也能够帮助消费者识别垄断行为的发生,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提供线索。因此,鼓励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研发反制技术,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垄断行为的发生,也能够借助市场力量为反垄断执法提供证据,降低反垄断执法难度。其三,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有意识地发展、引入必要的监管技术,以应对大数据竞争行为规制中面临的取证等难题。例如,针对基于算法协调价格的违法行为,可引入商品价格跟踪与回溯技术,以提升电子取证和存证效率[16]。
有必要指出的是,解决大数据竞争行为规制中涉及的技术性问题,除了依靠反垄断执法机构树立技术规制意识、培育技术规制能力以外,也需要依靠其他配套制度的建设,其他配套制度建设的完善至少可以帮助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解决技术性问题时事半功倍。例如,算法合谋规制中的一个技术性难题为算法黑箱。假设通过设置数据活动顾问实现对算法的陪同规制[33],则可以克服技术鸿沟。这无疑会为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反垄断执法提供便利。就此而言,解决大数据竞争行为规制中涉及的技术性问题,事实上还依赖于我国围绕数据、算法技术构建的整体制度。
五、执法方式的调适:柔性执法方式的适用与限制
(一) 单一刚性威慑方式的不足
在执法方式上,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一直以来主要采取的是单一的刚性威慑方式,即以行政处罚方式为主,通过事后对行为人课以法律责任来实现规制目的。必须承认,刚性威慑方式对于预防、制止垄断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采取单一刚性威慑方式的不足已经逐渐暴露出来。面对大数据竞争行为时,这种不足暴露得更加明显。
其一,受制于各种前置性难题,刚性威慑方式存在无法适用的可能性,并可能因此导致执法回应不足。事后规制、进行行政处罚的模式,以行为明确违法为前提。但由上文可知,大数据竞争行为的特点导致传统反垄断执法工具难以完全适用,受制于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等前置性难题,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可能很难完成对一些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其结果是在反垄断执法规则、执法工具不作相应调整的情况下,行政处罚方式可能被束之高阁。纵观我国12年来的反垄断执法历程,鲜有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执法案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当然,行为明确违法方能进行处罚的方式,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能够避免反垄断执法过度干预市场竞争。但在上述情形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并不是因为确认涉案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而作出不处罚决定,而是因为无从判断涉案行为是否违法进而无法确定能否进行处罚。这很可能导致执法回应不足的问题。从《反垄断指南》来看,无论是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积极对数据、算法这些新型要素作出回应,抑或明确引入必需设施理论等,其目的都在于解决上述前置性难题,为行政处罚方式的适用扫清前置障碍。但是,这些规则的抽象性与法律规则固有的滞后性,意味着当下的反垄断执法规则能否有效应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规制需求仍需打个问号。在这种情形下,刚性威慑方式的适用空间必然受限。
其二,面对大数据竞争行为,仅倚重刚性威慑方式难以有效实现反垄断法规制目的。一方面,仅依靠单一刚性威慑方式规制垄断行为的实践效果欠佳。目前我国反垄断法上的行政法律责任主要是罚款。就互联网领域而言,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出现一起行政处罚案例,因而无从判别刚性威慑方式的实际效果,但从国外实践情况来看,仅依靠刚性威慑方式很难有效实现反垄断法预防、制止垄断行为的目的。如在2017—2019年,欧盟委员会三次对谷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罚款,罚款总额高达82.4亿欧元(约合90亿美元)。从这一罚款频率与2019年后谷歌依旧多次被控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知,通过罚款制止垄断行为的实际效用并不突出,即使不断增加罚款数额,其结果也并不理想[34]。当下“适用结构性救济方式”的观点频现,实际上也是在回应刚性威慑方式效果不佳的问题。但是,结构性救济因其过分干预市场竞争,能否广泛适用、适用空间如何、适用限度如何等均有待进一步探索。同时,结构性救济方式作为事后救济方式,同样可能面临无法适用的问题,实践效果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前展规制逻辑、引入保护性预防规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22],从预防风险的角度来讲,确有必要在单一刚性威慑方式之外发展其他执法方式。如前所述,大数据竞争行为在行为效果上具有不确定性,这给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合适的干预时间、干预限度等均带来挑战。但同时,大数据竞争行为对于市场竞争秩序的损害通常不可逆,这又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必须及时回应规制需求。如果仅依靠行政处罚这一单一刚性威慑方式,等到事态非常明确、清晰之时再进行干预,可能导致一些确实危害市场竞争秩序的大数据竞争行为得以逃脱法律规制,无法及时回应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时代要求。尤其是考虑到此前我国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情况与后果,可见单一刚性威慑方式遵循的事后规制理念已经暴露出其局限性。
综上所述,欲有效规制大数据竞争行为,有必要在单一刚性威慑方式之外探索其他执法方式。当然,这并不是单纯否弃刚性威慑方式,而是强调应同时适用其他执法方式,即制裁与执法行动尽管不能带来最适威慑,却是反垄断法最适威慑实现的必要条件[35]。在遵循适度规制理念、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为避免对于市场竞争的过度干预,尤其是考虑到对于大数据竞争行为规制中关涉的一些独特问题,社会各界的认知尚不清晰,我们建议在单一刚性威慑方式之外注重运用柔性执法方式。
(二) 柔性执法方式的运用:以反垄断约谈为例
为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规制需求,已有学者建议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学习域外经验、采取“市场研究”这一柔性执法方式[36]。“市场研究”方式强调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相关竞争行为的效果尚不清晰时,通过对相关市场展开调查,以更好地理解、认知相关竞争行为,并为后期反垄断执法做好铺垫,从而避免执法回应不足的问题。在规制大数据竞争行为时,引入“市场研究”方式同样具有积极作用。但限于篇幅,同时考虑到实践中的应用趋势,本文在此着重探讨更具中国特色的柔性执法方式——反垄断约谈,在大数据竞争行为规制中的适用问题。
1.反垄断约谈的积极效用
事实上,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互联网领域执法时,已经逐渐在行政处罚方式外探索适用反垄断约谈。面对互联网领域可能造成竞争损害的涉嫌垄断行为,在面临诸多规制难题、相关行为是否真正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答案尚不清晰时,为回应社会各界呼吁,更具软性、弹性的约谈成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采取的一种主要应对方式。例如,针对各方反映强烈的平台“二选一”行为,我国市场监管部门多次约谈电商企业,要求平台公平竞争,不得限制、排斥其他经营者开展促销活动,并表明会适时展开反垄断调查[37]。
通过约谈解决垄断争议,契合垄断风险的不确定性特点[38],能够回避反垄断法规制面临的一些难题,为后期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提供一定的经验,也能够以平等协商、磋商对话等工作方式疏解监管压力、减少社会矛盾[39],且具有节约执法资源与成本的优势。此外,约谈本身具有的柔性特点,意味着反垄断约谈一般不会对市场造成过度干预,能够在及时回应社会需求与避免过度干预市场之间实现平衡,符合包容审慎的要求。如上所述,大数据竞争行为主体的特殊性、行为手段的独特性,对垄断行为分析步骤包括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行为认定等提出一定挑战,大数据竞争行为的效果也比较复杂,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不明晰。受制于这些前置性的规制难题,以及部分大数据竞争行为可能存在垄断危害而有待及时回应,反垄断约谈在数字经济时代确实存在一定适用空间。不过,采取约谈这一柔性执法方式并非毫无弊端,在适用反垄断约谈时应当予以关注。
2. 适用反垄断约谈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其一,采取约谈方式解决垄断争议,虽然可以回避反垄断法规制的一些具体认定难题,及时回应反垄断法规制需求,但因始终不能正面回应反垄断法规制面临的具体问题,难以深入研判、解决相关问题,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可资借鉴的实证样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难题。因此,长久之计仍在于着力解决大数据竞争行为规制中的具体难题,解决反垄断执法面临的前置障碍。
其二,采取约谈方式解决垄断争议,因不需要进行严格的反垄断调查,可能会因过度干预而扭曲原本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尤其是当下社会监督在推动反垄断执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反垄断法规制措施的采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众意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未必正确。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风险的认知更倾向于‘体验-情感模式’,对风险的判断更多立足于感官刺激,对新兴风险的认知更加缺乏理性判断”[40]。过度的媒体话语渗透,借助“风险框架的社会放大”效 应,很容易使执法工作失去应有的冷静和理性,进而沦为“冲突-回应”的被动过程[41]。就此而言,应当明确反垄断约谈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具体程序等基本内容,避免以约谈之名行干预之实。
其三,需要警惕异化约谈的风险,典型如“以谈代罚”。约谈的作用空间并非完全没有限度。一般认为,约谈范围应当以潜在的或是轻微的违法行为为主[42]。一旦超出这一适用范围,便可能产生“以谈代罚”的现象。其结果是一方面招致社会公众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作为的质疑,另一方面不利于发挥反垄断法本应发挥的威慑作用。因此,既需要明确反垄断约谈与行政处罚的关系、衔接方式、衔接条件等,避免反垄断约谈成为垄断主体逃避规制的避风港,也应关注程序公开、公正,使社会公众更充分地了解反垄断约谈的原因、内容、结果等,增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公信力,减少社会公众的认知偏差。
六、结语
在以往的反垄断执法中,因为有相对明确的科学依据和经验事实作为支撑,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任务主要在于预防或制止相对确定的危害结果出现,反垄断执法面临的难题多集中于具体技术层面。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数据、算法技术的使用,大数据竞争行为的出现对既有反垄断执法原则、执法工具、执法方式或多或少提出一定挑战。要促进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有效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必须对既有执法原则、执法工具、执法方式进行调适与革新。我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2021年2月7日公布的《反垄断指南》对上述问题作出了一定回应,将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执法提供有益指引,但相关规定如何落实、具体实效如何尚待进一步观察。同时,如前文所述,该指南对部分问题尚未作出回应。对此,反垄断执法机构仍需承担化解规范供给与规制需求不匹配之矛盾的重要任务。此外,尚有一个老生常谈却仍未解决的问题,即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人力资源问题。就现状来看,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人员编制很难有效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执法需求,从而使其整体执法能力更加低下。为实现对大数据竞争行为的有效规制,我国还须关注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人力资源问题。总而言之,在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执法不复以往的直观、简单,更具不确定性、复杂性与风险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对此有所认识,并有所作为。
① 如欧盟委员会在2019年7月就已经对亚马逊利用第三方零售商数据的行为是否违反欧盟竞争法规展开正式调查。See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 into possible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of Amazon, (July 17, 2019),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4291. 202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又对亚马逊利用第三方零售商数据的行为发出异议声明,并对亚马逊的商业模式展开第二次正式调查。See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mazon for the use of non-public independent seller data and opens second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commerce business practices (Nov 10,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077.
② 在该案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认定Facebook未经用 户同意通过第三方应用程序收集用户个人数据的行为,构成剥削性滥用行为,并作出处罚决定。See Bundeskartellamt, Facebook Inc. i.a.—The use of abusive business terms pursuant to Section 19 (1) GWB, (June 2, 2019),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 Entscheidung/EN/Entscheidungen/Missbrauchsaufsicht/2019/B6-22-16.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5.
③ 网络效应(或称网络外部性)是互联网平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指一种产品对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产品或可兼容产品的用户增多而增大。参见叶明:《互联网行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困境及其破解路径》,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1期,第31页。在数据、算法技术未得以广泛应用之前,互联网平台的网络效应主要基于用户数量的“反馈循环”形成,而在数据、算法技术逐渐广泛应用之际,互联网平台的网络效应则更突出地表现为基于数据的“反馈循环”形成,数据的重要作用得以凸显。参见贾晓燕,封延会:《网络平台行为的垄断性研究——基于大数据的使用展开》,载《科技与法律》2018年第4期,第26-27页。
④ 就反垄断分析而言,大数据与数据这两个概念并无实质差别,故本文对二者不作区分使用。
⑤ 该案以Topkins签署认罪协议结案。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lea agreement: U.S. v. David Topkins, (Apri 30, 2015), https://www.justice.gov/atr/case-document/file/ 628891/download.
⑥ “大数据的应用有两种形式,一是大数据作为产品或服务的输入要素,二是作为单独的数据产品或服务。”在两种不同情形下,数据对于市场支配力的影响不同。参见殷继国:《大数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4期,第76页。
⑦ 该案以附条件批准结案。See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approves acquisition of LinkedIn by Microsoft, subject to conditions, (Dec 6, 2016), https:// 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6_4284.
⑧ 在我国多种法律规范文件中均可见包容审慎监管的思想,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
⑨ 如2017年,因优待自家对比购物服务,谷歌遭欧盟委员会处罚24.2亿欧元,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2.42 billion for abusing dominance as search engine by giving illegal advantage to ow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June 27, 2017),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7_1784;2018年,因预装谷歌搜索和Chrome浏览器,谷歌遭欧盟委员会处罚43.3亿欧元,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4.34 billion for illegal practices regarding android mobile devices to strengthen dominance of Google's search engine, (July 18, 2018),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IP_18_4581;2019年,因限制第三方网站展示竞争对手广告,谷歌遭欧盟委员会处罚14.9亿欧元,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1.49 billion for abusive practices in online advertising, (March 20, 2019),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1770.
⑩ 从“市场能够自我矫正”得出执法不足的错误会得到“自我校正”的结论,需要依赖一个未说明的前提,即“该等市场进入普遍被证明能够在反垄断法最为关切的寡头语境中防范市场势力——至少被证明能够以足够的频率、在足够的程度并以足够快的速度防范市场势力,使得假阳错误的成本系统性地低于假阴错误”。Jonathan B. Baker. Taking the error out of “error cost” analysis: What’s wrong with antitrust’s right, Antitrust Law Journal, 2015(1): p.9.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 [EB/OL]. (2020-07-22) [2021-01-02]. http://www. caict.ac.cn/kxyj/qwfb/bps/202007/t20200702_285535.htm. CAIC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2020)[EB/OL]. (2020-07-22) [2021-01-02]. http://www.caict.ac. cn/kxyj/qwfb/bps/202007/t20200702_285535.htm.
[2] 新华社. (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EB/OL]. (2020-04-09) [2021-01-02]. 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zywj/2020-04/09/c_1125834458.htm. Xinhua. (Authorized to issue) Opin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building a more complete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EB/OL]. (2020-04-09) [2021-01-02]. http://www.xinh uanet.com/politics/zywj/2020-04/09/c_1125834458.htm.
[3] 北京晚报. 国家邮政局深夜协调顺丰菜鸟全面恢复数据传输[EB/OL]. (2017-06-03) [2021-01-02]. http://www. xinhuanet.com//fortune/2017-06/03/c_1121081262.htm. Beijing Evening News. After the State Post Bureau coordinated, SF and Cainiao fully resumed data transmission [EB/OL]. (2017-06-03) [2021-01-02]. http:// 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06/03/c_1121081262.htm.
[4] 新京报. 腾讯华为“数据之争”授权是尚方剑?[EB/OL]. (2017-08-11) [2021-01-02]. http://www.xinhuanet.com/ tech/2017-08/11/c_1121465577.htm. BJNEWS. Data dispute between Tencet and Huawei [EB/OL]. (2017-08-11) [2021-01-02]. http://www. xinhuanet. com/tech/2017-08/11/c_1121465577.htm.
[5]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 1937(16): 386-405.
[6] 陈永伟. 平台反垄断问题再思考: “企业-市场二重性”视角的分析[J]. 竞争政策研究, 2018(5): 25-34. CHEN Yongwei. Rethinking platform antitrust: A firm-market duality perspective [J].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2018(5): 25-34.
[7] 刘权. 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J]. 法学研究, 2020(2): 42-56. LIU Quan. Public nature of internet platform and its realization [J]. Chinese Journal of Law, 2020(2): 42-56.
[8] 时建中. 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拓展适用于算法默示共谋研究[J]. 中国法学, 2020(2): 89-107. SHI Jianzhong.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llective dominance institution to the tacit algorithmic collusion [J].China Legal Science, 2020(2): 89-107.
[9] Matt Hunter. Why the Microsoft / LinkedIn Marriage? It’s All About Enterprise [EB/OL]. CNBC, June 2016: 13. Available at: https://www.cnbc.com/2016/06/13/why- the- microsoftlinkedin-marriage-its-all-about-enterprise. html?&qsearchterm=microsoft%20acquire%20linkedin (accessed 01/02/2021).
[10] 方燕. 论经济学分析视域下的大数据竞争[J]. 竞争政策研究, 2020(2): 33-59. FANG Yan. Research on big data competition from economics analysis perspective[J].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2020(2): 33-59.
[11] 殷继国. 大数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J]. 法商研究, 2020(4): 73-87. YIN Jiguo. Legal regulation of abuse of market dominance by big data operator[J]. Studies in Law and Business, 2020(4): 73-87.
[12] 阿里尔·扎拉奇, 莫里斯·E·斯图克. 算法的陷阱: 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M]. 余潇,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75. ARIEL EZRACHI, MAURICE E. STUCKE. Virtual competiti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algorithm- driven economy[M]. Trans. YU Xiao. Beijing: Citic Press, 2018: 75.
[13] 孟雁北. 论大数据竞争带给法律制度的挑战[J]. 竞争政策研究, 2020(2): 5-17. MENG Yanbei. Research on challenges of legal system from big data competition[J]. Competition Policy Research, 2020(2): 5-17.
[14] JOSHUA D. WRIGHT. Abandoning antitrust’s Chicago obsession: The case for evidence-based antitrust[J]. Antitrust Law Journal, 2012(1): 241-271.
[15] ULRICH SCHWALBE. Algorithms, machine learning, and collusion[J].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2018(4): 568-607.
[16] 周围. 算法共谋的反垄断法规制[J]. 法学, 2020(1): 40-59. ZHOU Wei. Antitrust regulation to algorithm collusion [J]. Law Science, 2020(1): 40-59.
[17] 刘大洪. 论经济法上的市场优先原则: 内涵与适用[J].法商研究, 2017(2): 82-90. LIU Dahong. On the principle of market priority in economic law: Intension and application[J]. Studies in Law and Business, 2017(2): 82-90.
[18] FRANK H. EASTERBROOK. The limits of antitrust[J]. Texas Law Review, 1984(1): 1-40.
[19] 莫里斯·E·斯图克, 艾伦·P·格鲁内斯. 大数据与竞争政策[M]. 兰磊,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9: 267. MAURICE E. STUCKE, ALLEN P. GRUNES.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M]. Trans. LAN Lei. Beijing: Law Press, 2019: 267.
[20] 陈兵. 法治视阈下数字经济发展与规制系统创新[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100-115. CHEN Bing. Digita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ulatory system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le of law[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4): 100-115.
[21] 孙瑜晨. 互联网共享经济监管模式的转型:迈向竞争导向型监管[J]. 河北法学, 2018(10): 21-27. SUN Yuchen. Regulato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n China: To competition-oriented regulation model[J]. Hebei Law Science, 2018(10): 21-27.
[22] 陈兵. 因应超级平台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挑战[J]. 法学, 2020(2): 103-128. CHEN Bing.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super- platforms to antitrust regulations[J]. Law Science, 2020(2): 103-128.
[23] 谭晨. 互联网平台经济下最惠国条款的反垄断法规制[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2): 138-152. TAN Chen. Antitrust regulation against MFN clauses in the internet platform economy[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0(2): 138-152.
[24] 郜庆. 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背景下支配地位认定条款之重塑[J]. 行政法学研究, 2020(5): 77-90. GAO Qing. The reshaping of dominant position clause in the context of optimizing business environment[J].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20(5): 77-90.
[25] 龙俊. 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竞争风险及其规制方法[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83-94. LONG Jun. Competition risks of digital music copyright exclusive authorization and its solutions[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2): 83-94.
[26] 王伟. 数字内容平台版权集中的法律规制研究[J]. 政治与法律, 2020(10): 134-147. WANG Wei. O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copyrights concentration by digital content platforms[J].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020(10): 134-147.
[27] 刘乃梁. 包容审慎原则的竞争要义——以网约车监管为例[J]. 法学评论, 2019(5): 122-132. LIU Nailiang. Competitive essentials of principle of inclusive prudence: Taking regulation of online car hailing as an example[J]. Law Review, 2019(5): 122-132.
[2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Sues Monopolist Google for Violating Antitrust Laws [EB/OL]. Justice News. Official website of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ctober 2020: 20. Available at: https://www. 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sues-monopolist-google-violating-antitrust-laws (accessed 01/02/2021).
[29] 李剑.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体系冲突与化解[J]. 中国法学, 2014(6): 138-153. LI Jian. System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antimonopoly law[J]. China Legal Science, 2014(6): 138-153.
[30] RUBINFELD D L, GAL M S. Access barriers to big data[J]. Arizona Law Review, 2017(57): 339-385.
[31] 杨东. 论反垄断法的重构: 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J]. 中国法学, 2020(3): 206-222. YANG Do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ti-monopoly law: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digital economy[J]. China Legal Science, 2020(3): 206-222.
[32] Michal S. Gal. Algorithmic-facilitated Coordination: Market and Legal Solutions [EB/OL]. Antitrust Chronicle. CPI, May 2017: 15. Available at: https://www. 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CPI-GAL.pdf (accessed 01/02/2021).
[33] 林洹民. 自动决策算法的法律规制: 以数据活动顾问为核心的二元监管路径[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9(3): 43-53. LIN Huanmin. Legal regulation of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lgorithms: Dual regulatory path with data activity consultant as the core[J]. Science of Law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019(3): 43-53.
[34] 方翔. 竞争合规的理论阐释与中国方案[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4): 48-59. FANG Xiang.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ompetition compliance and China’s program[J].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Hum & Soc. Sci.), 2020(4): 48-59.
[35] 喻玲. 从威慑到合规指引: 反垄断法实施的新趋势[J].中外法学, 2013(6): 1199-1218. YU Ling. From deterrence to compliance guidelines: New trends in antitrust enforcement[J]. 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 2013(6): 1199-1218.
[36] 唐要家, 尹钰锋. 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及工具创新研究[J]. 产经评论, 2020(2): 5-16. TANG Yaojia, YIN Yufeng. Antitrust regulation and tools innovation on algorithmic collusion[J]. Industrial Economic Review, 2020(2): 5-16.
[37] 新华社.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平台企业将对“二选一”行为依法开展反垄断调查[EB/OL]. (2019-11-05) [2021-01-02]. 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5/ content_5449039.htm. Xinhua.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interviews platform companies to conduct anti-monopoly investigations against “either-or choice” behavior [EB/OL]. (2019-11-05) [2021-01-02]. http://www.gov.cn/ xinwen/2019-11/05/content_5449039.htm.
[38] 王虎. 风险社会中的行政约谈制度: 因应、反思与完善[J]. 法商研究, 2018(1): 22-29. WANG Hu. Administrative interview system in risk society: Response, reflection and perfection[J]. Studies in Law and Business, 2018(1): 22-29.
[39] 周泽中. 行政约谈的规制功能及其法治约束[J]. 学习论坛, 2019(12): 86-96. ZHOU Zezhong.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interview and its legal constraints[J]. Tribune of Study, 2019(12): 86-96.
[40] 郭传凯. 人工智能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J]. 法学论坛, 2019(6): 107-117. GUO Chuankai. Difficulties and outlets on AI risk regulation[J]. Legal Forum, 2019(6): 107-117.
[41] 吴元元. 信息能力与压力型立法[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1): 147-159, 224. WU Yuanyuan. Informational power and pressure- induced legisla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0(1): 147-159, 224.
[42] 朱新力, 李芹. 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建构[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4): 91-97, 150. ZHU Xinli, LI Qin.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administrative interview[J].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2018(4): 91-97, 150.
Challenges of and response to big data competition to China'santitrust enforcement
YE Ming, ZHANG Jie
(School of Economic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big data competition around data acquisition, use, analysis, etc. is emerging. Although big data competition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market competition, it can also induce monopoly risk and cause antitrust concern. In view that the subject of big data competition holds its duplicity in both the enterprise and the market, that its method depends on the use of big data and algorithm, and that its consequences are fairly complicated, its anti-monopoly law-enforcement principles, tools and ways need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To be more specific, in terms of law-enforcement principles, rectification should be tolerant, prudent and actively disciplined; in law-enforcement tools, we should revolve around non-price competition to maintain its perfection, introduce technology supervision and cultivate awareness and tools of regulating technology with technology; in law enforcement ways, we should focus on flexible ones represented by antimonopoly interview.
big data competition; antimonopoly enforcement; tolerance and prudence; non-price competition; antimonopoly interview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1.03.003
D922.294
A
1672-3104(2021)03-0026-14
2020-12-01;
2021-03-0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经济的法治保障研究”(18ZDA150);贵州省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贵州大数据支撑公共卫生智慧应急管理的法律问题研究”(20GZQN05)
叶明,四川绵阳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数据法学;张洁,山西运城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数据法学,联系邮箱:412856281@qq.com
[编辑: 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