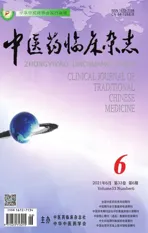张国梁审证求机分期论治慢性乙型肝炎经验
2021-04-17刘丽丽周灏侯勇李艳施美张国梁
刘丽丽,周灏,侯勇,李艳,施美,张国梁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合肥 230031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是目前人类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据WHO报道,全球约有2.57亿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HBV感染所致的肝衰竭、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1]。目前西医在治疗上多采用抗病毒、护肝等,但是会出现临床耐药、诸多不良反应、费用高等不可规避问题。而中药治疗能改善患者胁痛、乏力、厌油等临床症状,具有护肝、抗肝纤维化、抗病毒作用,对于患者提高HBsAg阴转率,较之西医有独特的优势[2]。
笔者导师为张国梁教授,江淮名医,安徽省首届名中医,师从国医大师徐经世。张师擅长治疗肝胆疾病,在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上有着独到的见解,现将张师审证求机论治慢性乙型肝炎的经验总结如下。
病因病机
慢性乙型肝炎属于胁痛范畴。张师从事中医药诊治慢性肝炎长达三十余年,在慢性乙型肝炎的诊治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认为因肝主疏泄,性喜条达而恶抑郁,肝脏受病,多表现为肝经气郁不舒。另外,肝位于胁下,其经脉循行于两胁之间;因此胁痛是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对于其病因病机多认为主要由于情志不舒或外感湿热疫毒之邪或饮食不节、劳倦内伤或久病他脏之病累及于肝等导致肝失疏泄,肝经气滞、血行不畅而致血瘀、湿热疫毒等邪郁结于肝使肝体络脉失养。张师认为久病正气亏虚常常贯穿于胁痛发病的始终,这也是其迁延不愈的重要原因。
因此,胁痛病位虽主要在肝,但病久又可与脾、胃、肾等脏腑相关。其病机演变常为感受湿热疫毒之邪,肝失疏泄从而可出现气滞、血瘀等病理变化,病久毒损肝体同时肝病及脾,气血生化无源则会出现正虚邪恋,本虚标实之势。
临证经验
以证候为基础,探寻其内在证候要素,并分析各要素间变化机理,即审证求机,突破了传统审证求因或审症求因,把握疾病病机的特点及疾病发展演变转归的趋势,及早对疾病的发展和转归作出判断,可为提高临床准确辨证、准确论治提供经验[3]。张师认为慢性乙型肝炎的演变过程主要为“病初在肝,继而传脾,久病及肾”,病初病位较浅,邪在气在经,病久邪气入络入血,故临床辨证应分清气、血、虚、实,治疗当分期论治,辨证时应全面分析,辨明主次。
1 湿热疫毒,肝失疏泄
张师认为肝属木,主少阳春升之气,其性升发;肝主疏泄,性喜条达;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肝为藏血之脏,血液运行不仅有赖于心气、肺气的推动还有赖于肝气的疏泄调畅。慢性乙型肝炎初期,机体感受湿热疫毒之邪,郁蒸中焦,侵及肝胆,肝郁气滞,气行不畅则可致血瘀为痛,血瘀又可加重气机运行障碍,气血瘀阻,瘀毒内结,致肝络受损。初期邪在气在经,常表现为气滞、湿热、瘀毒而致的胁痛,多实证,病位较浅。早期治疗应清热解毒,调达木郁。
2 肝郁脾虚,瘀血阻络
疾病中期,肝病及脾或肝脾同病,肝逆脾遏,土壅木郁,气机不宣为主要病机,肝经气郁日久,脾失健运,临床常表现为肝区胀痛或隐痛或刺痛,性情急躁易怒,睡眠不稳;食欲减退,纳谷不馨;胃脘痞满胀痛,大便不爽,神疲乏力,脉多见弦,本证即叶天士“肝木乘脾土”。气滞日久常可导致血瘀凝结;瘀毒或湿热日久,又可兼有气滞。张师认为中期既有气滞、瘀毒而致的实证胁痛,亦有脾土亏虚而致的虚证表现,为虚实夹杂之证候。中期治疗应肝脾同调,除邪务尽。
3 中州失调,肝肾亏虚
晚期肝阴不足进而延及脾肾可见脾肾亏虚等虚证的表现。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肝主疏泄,肾主封藏,肝肾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精血同源、藏泄互用以及阴阳互滋互用等方面,精血皆由水谷之精化生和充养,且能相互资生。清·张璐《张氏医通》说“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血”即是说肾精化为肝血,肾精与肝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病理上肝血不足与肾精亏损多可相互影响。另外,肝气疏泄可促使肾气封藏有度,肾气闭藏可防止肝气疏泄太过。肝病日久不仅可以出现肝血肾精的化源不足,还可因肝失疏泄导致肾失封藏,而出现肾精亏损的临床表现。症见胁痛隐隐,爪甲不荣,面色黧黑,腰膝酸软等肝肾亏损的临床表现。张师认为晚期常因湿热或热毒伤阴或久病误治还可出现肝阴不足、正气亏损的的虚实夹杂证候。晚期治疗当扶正祛邪,活血通络。
辨治特点
张师从事中医肝病临床三十余年,总结了疏肝、解毒、清热、泻肝、扶正、健脾、醒脾、理气、活血、凉血、补肾、补肝、填精、活血等多种治肝方法,根据疾病进展采用不同治法,但需注意不可拘泥于一法一方及病程分期,审证求机因人而异,灵活运用。以下仅从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病程阶段,简要介绍一二,以供临床参考。
1 早期:调达木郁,清热解毒
临床常用柴胡疏肝散、四逆散等加减,对病程短、病位浅者确有解郁止痛之效,若肝郁日久,必致肝络瘀阻,其疼痛明显者则常需佐以活血通络之品,如延胡索、郁金、桃仁、莪术、归尾等药。
宜柔而不宜伐。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理气药物大多辛温香燥而不利于肝体,如久用或用量不当往往易耗损阴血使病情加重。
注重肝之生理特性,用药不可偏颇。若气滞轻浅,症见精神抑郁、脘胁不适,纳谷不馨者一般选用陈皮、砂仁、枳壳、苏梗等芳香疏郁之品;若气滞较重,症见胸胁胀满、气滞胃痛以及积滞、痞块者,则宜选用青皮、柴胡、木香、延胡索、郁金、川芎等辛宣破结之品;如气滞日久兼见阴血不足者,在疏肝解郁的同时常常伍用柔肝养阴之品,以防耗伤阴血,常选枸杞子、白芍、山茱萸、北沙参、酸枣仁、当归等。
注重解毒,给邪以出路。目前国内外医家在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尤其是热毒稽留、湿热蕴结不解、谷丙转氨酶增高的患者,常用清热解毒法[4-8],取用垂盆草、半枝莲、蛇舌草等药[9]。但张师认为滥用苦寒清热解毒之品非但无效,反致邪毒深伏。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升降正常方能受纳、腐熟、运化水谷、传糟粕于体外。肝胆为气机出入的枢纽,如果其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则一身之气皆有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善治病者重视调气,善调气者重视调畅肝胆脾胃之气。肝病治疗大法应以恢复肝胆脾胃升降出入之能,苦寒之药虽可清热解毒,但用之过度就会郁遏肝脏的升发之气,致其升发无权,疏泄无力,同时又可影响脾胃阳气,使之纳化呆滞,运化失常。临证应在疏肝理气等治法基础上配合清热解毒,稍佐一二味给邪以出路。
2 中期:肝脾同调,除邪务尽
首先,疏肝解郁,健脾行气,方宜选用逍遥丸、四逆散、柴胡疏肝散等方加减。疏肝气宜用柴胡、香附、合欢花、川楝子、川芎等辛香理气之品。若胃脘胀满不舒者宜随证加入枳壳、陈皮、砂仁、厚朴等行气之品;若纳谷不馨者宜加木香、砂仁等醒脾行气药;若脾气虚弱者则多用白术、山药、茯苓、白扁豆、党参、炙甘草、薏苡仁等健脾药;若湿困脾阳者常常选用薏苡仁、白术、茯苓、白扁豆等健脾利湿药。
其次,调理脾胃,特别要注重脾胃升降之枢,方选四逆散合异功散,方中柴胡疏肝气、升清阳,枳实泄浊阴、散气滞;与党参、白术同用,消补兼行,以助脾运,此即“肝病治脾”之训。若气滞甚而纳谷不馨,食后脘胀较甚者加木香以醒脾行气,增强运脾之力。
再次,肝病日久如疏肝不应,则宜兼用活血止痛之法。正如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所言“经主气,络主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因此临证常常选用丹皮、川芎、赤芍、桃仁、丹参等药,若疼痛较甚则加用延胡索、郁金等行气活血止痛药;如合并有黄疸者则重用赤芍,认为黄疸为瘀热胶结在里,赤芍不仅能散邪,且能行血中瘀滞,现代医学也证明赤芍能利胆退黄、改善肝脏及全身微循环作用[10-13]。
3 后期:扶正祛邪,补肾养肝
首先,扶正调中。《黄帝内经》在论厥阴病治法时提出“调其中气,使之平和”,意即厥阴病久治不愈应当求治于阳明,与“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相对应,说明厥阴肝经病证既可从脾治疗,也可从胃论治。国内医家认为慢性乙型肝炎病位在肝胆,但病变在脾胃,其基本病机是脾失健运、肝失疏泄而致胁痛[14-15]。而张师认为胁痛病起于肝而延及于脾,肝气郁结久则克脾犯胃,水湿不得运行,则致肝郁更甚,血行受阻,终致气滞、湿热、瘀毒等留滞不去。另外,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腹中真气所主之地,肝病日久正气不支,则病邪留恋不去。因此,慢性乙型肝炎病至后期治疗宜扶正调中,中州健运,则正气渐旺而能抗邪于外。
其次,补肾养肝也是慢性乙型肝炎后期的一大治法[16-20]。清·张璐《张氏医通》:“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血”,认为肝病日久不仅可以出现肝血肾精的化源不足,还可因肝失疏泄导致肾失封藏,而出现肾精亏损。张师认为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肝主疏泄,肾主封藏,肝肾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精血同源、藏泄互用以及阴阳互滋互用等方面,精血皆由水谷之精化生和充养,且能相互资生。临床常见胁痛隐隐,爪甲不荣,面色黧黑,腰膝酸软等,补肾宜用黄精、女贞子、墨旱莲、菟丝子等,养肝体宜选用枸杞子、白芍、山茱萸、北沙参、酸枣仁、当归等药。
病案举隅
张某,男,31岁。2018年4月10日初诊。自诉反复右胁不适10年余,一直未治疗。刻下:情绪焦虑抑郁,右胁肋部疼痛,腹胀,神疲乏力,纳差,大便溏结不调,2~3次/日,便前腹痛,泻后痛缓,无粘冻及脓血,无畏寒发热,小便正常,夜寐尚可。肝功能示 ALT 110U/L,AST9 3U/L;乙肝五项 HBsAg+,抗 HBe+,抗 HBc+;HBV DNA 3.53×105copies/ml;肝胆胰脾彩超示肝脏回声增粗。中医诊断:胁痛病,辨证属肝郁脾虚,正虚邪恋;西医诊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治法:疏肝健脾,扶正祛邪。处方:生黄芪30g,北柴胡15g,川芎10g,赤芍12g,白芍12g,炒白术15g,炒枳壳10g,陈皮12g,太子参12g,垂盆草30g,香附12g,生甘草6g。14剂,1日1剂,早晚分服。
二诊:2018年5月27日,患者腹胀、乏力症状稍减轻,纳谷不馨,稍多食则脘腹胀满,复查肝功能示:ALT 45U/L,AST 67U/L,。舌淡红,苔薄白稍腻,脉弦弱。处方:上方加炒谷芽15g,炒麦芽15g,木香12g。14剂,1日1剂,早晚分服。
三诊:2018年6月23日,患者自觉体力有增,纳食渐馨,大便逐渐恢复正常;唯仍有右胁肋部隐痛不适,睡眠欠稳,复查肝功能恢复正常。舌淡红,苔薄白润,脉弦。处方:生黄芪30g,北柴胡15g,川芎10g,白芍12g,炒白术12g,太子参12g,枸杞12g,女贞子12g,墨旱莲12g,生甘草6g。14剂,1日1剂,早晚分服。
四诊:2019年1月13日,患者前方加减间断服用半年余,刻下肝功能恢复正常,饮食睡眠可,乏力,胁肋部隐痛等不适症状基本消失。
按:慢性肝炎起于肝而延及于脾,肝气郁结久则克脾犯胃,水湿不得运行,则致肝郁更甚,血行受阻,终致气滞、湿热、瘀毒等留滞不去。另外,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腹中真气所主之地,肝病日久正气不支,则病邪留恋不去。针对此型病证,张师常疏肝健脾,配合扶正祛邪之药,但同时也强调,肝病日久及肾,疏肝不应,宜滋肾柔肝补养肝体,故减理气疏肝之品,以防肝气疏泄太过,加入滋肾柔肝的枸杞、女贞子、墨旱莲而获效。
结语
是故审证求机决定治法与方药,张师认为该病病机为情志不疏或外感湿热疫毒之邪等导致肝失疏泄,肝经气滞而致血瘀、湿热疫毒等邪郁结于肝,肝体络脉失养。病初病位较浅,邪在气在经,病久邪气入络入血,其治疗应分期论治,总结出疏肝、解毒、清热、泻肝、扶正、健脾、醒脾、理气、活血、凉血、补肾、补肝、填精、活血等多种方法,临证虽需根据疾病进展采用不同治法,但需注意不可拘泥于一法一方及病程分期,应审证求机,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