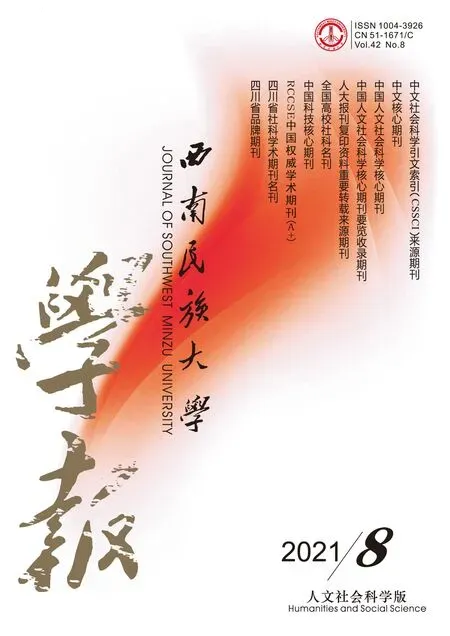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与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2021-04-17裴萱
裴 萱
[提要]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密切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通过“第三空间”“另类空间”等概念一方面建构出空间符号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则发掘符号形式内蕴的身份、阶级、文化等深层话语价值。与此同时,文学理论知识需要采取“建构论”的生产模式和“价值论”的意义生成途径。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文学理论提供了崭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理论资源。首先,空间生产论与文学活动论能够相互契合,并在“美的规律”本质论、精神实践创作论等方面提供崭新视角;其二,空间符号论与文学文本论不仅建构出文学的空间审美形式,更是在文学形象、文学意象、审美意识形态方面实现文本“深层结构”的意义释放;其三,空间批判论与后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大生产”景观相互渗透,并通过另类空间文化反思、流动空间的审美自由以及公共空间的符号共鸣等发掘文学理论的介入性、实践性与人文性价值。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当代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学资源与研究视角。
空间与时间构成主体生存实践的双重要素,空间理论和空间转向构成知识现代性工程中的重要维度,并且调整了传统“历史——时间”的线性知识思维模式,呈现出“共时——空间”的言说方式。马克思与恩格斯立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殖民扩张、城市建立等现代性事件,将空间视为主体生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静止的“物质载体”,而是具有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价值的独特存在。空间被赋予了实践性、生产性、主体性和意识形态性等新的色彩,并开始介入进现代哲学与文化领域。20世纪60年代的空间转向思潮则进一步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社会学阐释模式,将空间视为主体物质生产和文化批判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当代文学理论也面临新一轮的知识建构,需要在“大理论”与“小理论”、“文学性”与“知识互涉性”、“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众多知识形态中找到突破,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文学理论提供了崭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建构起“空间——社会——符号形式”的三元辩证法,并能够有效介入到文学批评与分析中。空间生产与文学活动的相互结合、空间符号与意识形态的“询唤”机制以及空间正义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凸显等等,这些一方面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的知识内涵,另一方面也给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文本论、创作论、意识形态论、价值论等提供了理论资源。
一、知识主体:空间生产与文学理论“实践论”的主体建构
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密切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空间不仅是事物存在的三维立体结构形式,更是主体进行实践的对象和“本质力量对象化”观审的结果,内蕴了主体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精神生产的过程,也凸显了主体的审美意识与文学创作动力。可见,现代空间不再仅仅具有静谧、自然的物质形态属性,而是与主体形成相互建构、渗透共存的关系。一方面,主体对空间的社会化改造行为,包含了面向空间的精神实践,营造出具有“主体性”特质的文学艺术景观;另一方面,空间承载着主体的审美意识,并与感性、身体、社会、阶级、意识形态等问题产生关联,塑造了文学理论知识话语的新面貌。
(一)空间生产与文学活动“美的规律”相互推动
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视为主体实践的对象与结果,并与主体的社会存在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文学艺术的生产也是源自主体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并通过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审美愉悦和“美的规律”的创造来实现。由此,空间生产不仅表征出主体的物质实践能力,更是成为劳动创造美的重要“中介”。“人首先在一定的空间持存和展开,并通过生产和交往塑造着社会空间形态。”[1](P.68)主体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反观到社会分工、阶级差异、空间区隔、日常生活等问题,还以精神实践的方式认知到空间也具有诗性体验的意味,凸显出主体的审美愉悦与反思。由此,空间生产和文学艺术“美的规律”具有相互推动的关系。从空间生产的角度而言,空间自身已经被注入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性含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市场拓展的过程也正是全球的空间整合过程,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化”空间持续向“另类空间”侵蚀的行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P.31)与此同时,资本的流动与市场的拓展又带来新一轮的空间不平衡关系,比如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对立、城市内部商业区与贫民区的空间区隔、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空间差异等等,这些都表征出现代社会新的生产关系与主体生存状况。“但是我毕竟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曼彻斯特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的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3](P.328)空间区隔带来了城市空间的景观断裂,资产阶级享有豪华的商业区与居住地,而工人却只能居住在条件较为恶劣的贫民窟中,呈现出空间异化的场景。恩格斯以微观纪实的方法对工人的居住空间进行描绘。“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3](P.306-307)工人的居住空间状况是资本主义空间失衡场景的缩影,并表征出深层的生产关系与权力话语,显示出恩格斯对工人主体的人道主义关怀。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不仅将主体纳入物质实践与社会革命的宏大视域中,更是将空间视为活生生的、主体感性活动之承载,这也正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的重要论题。“人化自然”的过程也正是“人化空间”的拓展过程,二者在“人学”维度上得以契合。“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4](P.75)主体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正是“人化空间”的关系,空间也就蕴含了人道主义与感性解放的意味。从“美的规律”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建构出主体实践与生活活动的诗意关联,美学意义由此产生。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人学视角出发,将“现实”“对象”与“感性”等要素纳入进时间与空间、现象与本质、存在与实践的辩证体系内部。主体的感性活动并非仅仅局限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视域中,更是成为主体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是最深刻的‘美学家’,他相信人类的感觉力量和能力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目的,不需要功利性的论证。”[5](P.194)马克思将主体的感性审美活动视为主体社会实践的前提,同时也是“自由自在”生存的目的。主体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建构出主体与自然空间之间的诗意情感关系,体现出精神实践的完整性与能动性。“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4](P.51)此种精神实践的过程也完成了“自然的人化”与“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愉悦,通过视觉、听觉等丰富的感性活动完成社会主体的塑造。与此同时,美的规律与审美实践也蕴藏于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的差异性不仅表征出阶级与社会关系,更是凸显出文艺层面的话语表达。空间成为“人化自然”的载体,推动主体审美实践的完成。哈克奈斯是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女作家,其作品《城市姑娘》《曼彻斯特的衬衣工人》等多以英国城市空间为基础,展开现实主义的故事文本与人物塑造。尤其是《城市姑娘》的城市空间区隔构建出“相对典型”的故事环境。工人多是聚集在伦敦东部的贫民区,而以格兰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以及教会、“救世军”等集中在伦敦西部区域,两种城市空间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别。由此,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论述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适当肯定了《城市姑娘》城市空间描写的合理性。“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做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6](P.590)城市空间不仅是主体物质实践的结果,更是通过“美的规律”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环境。
将空间生产与审美实践进行结合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不仅把空间视为主体实践的结果,更是认为空间自身成为某种感性符号与审美象征。此种“人化空间”的建构过程也是主体进行审美实践与“美的规律”生成的过程。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将主体的空间实践划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维度。表征空间是在第一层次的空间物质实践、第二层次的空间概念基础上形成的符号化空间,该空间包含了艺术家诗意的真实与想象,是一种被边缘化了的精神空间,并充满了对审美自由的向往。“表征空间是具有生命力的:它会说话。它拥有一个富有感情的核心:自我、床、卧室、寓所、房屋;或者是广场与教堂。……它本质上是灵活的、能动的。”[7](P.42)可见,空间生产构成主体的审美实践和文学艺术生产的重要承载;文学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也包括了对空间的审美实践与“美的规律”生产的过程。空间绝非主体进行物质生产的被动存在,更是延展出审美意义与文化景观,彰显了文学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主体实践关系,成为文学活动论、艺术生产论等理论视域的重要知识学资源。
(二)空间生产与文学创作“精神实践”密切契合
从文学创作论的视角而言,空间成为激发主体文学创作动机、进行艺术发现并且进行文学构思的关键元素。在当代文论知识框架中,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实践表述成为文学创作论的主导内容。一般而言,创作主体需要经过“信息储备”“艺术发现”“审美构思”“语词提炼”“文本技巧”等若干步骤推动文学生产。“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8](P.25)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创作是主体特殊的、独立的精神生产,是辩证联系了创作客体与创作主体的历史发展进程。“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9](P.861)在文学创作的进程中,空间元素成为主体生活经验积累、生存场景怀旧、激发审美意识以及文化批判反思的承载。从“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10](P.661)的空间感怀,到“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11](P.234)的空间思念;从鲁迅在日本教室中的空间反思,到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的另类空间表达,这些都表征出创作主体面对特定空间场景的诗意咀嚼与审美共鸣。
马克思主义主体空间精神实践的第一个层面是身体感性体验,这也契合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的论证。主体处在诸如城市等特定空间内部,以身体视觉、听觉等“视知觉”感知的方式来接触空间,从而构建出依赖于生存和体验维度的空间实践模式。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空间生产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了“生存——实践论”空间观念,强调审美主体的直观性空间体验。由此,主体审美经验在空间中得到激活与延展,并建构起“生存——体验论”空间话语。本雅明立足于现代城市空间内部的差异性,创设出美学领域的“闲逛者”形象,以此来完成空间维度的审美现代性对抗。“闲逛者”自由行走在城市的拱廊街、公园、咖啡馆、艺术区、贫民区等另类空间中,没有特定的行走目的,只是以艺术家的视角来感受、体验都市空间景观。“移情乃是闲逛者投身人群时的那种陶醉的本质。”[12](P.123)这正如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塑造的“异邦人”“浪荡子”形象,他们对城市的空间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对倦于人生斗争的灵魂,海港乃是一处有魅力的盘桓之地。天空的广阔,云的移动建筑,海的变化的色彩,灯塔的闪闪发光,形成一面棱镜,非常适宜于愉悦眼目,使人久看不厌。”[13](P.478)本雅明高扬了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并将“异邦人”的空间体验转化成为具有都市政治美学的“闲逛者”形象。“闲逛者”属于普通人群的一员,又能够以“看”与“被看”的方式与空间保持若即若离的现代性审美距离。城市空间已经成为一种审美符号,它隐匿在城市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中,并生成了属于艺术家自我的空间美学,这也构成文学创作论中艺术发现、艺术构思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主体空间精神实践的第二个层面是空间审美释放。如果说本雅明的身体感性体验构成主体对现代性空间的反思,并以强烈的批判姿态进行“异化”对抗的话;那么后现代空间压缩景观则带来新一轮的空间紧张,身份、怀旧、乡土、地方、社群、仿象、拟真等问题重新被美学提上日程,艺术与美学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主体需要重新激活对空间的诗性体验,以此来实现审美共鸣与身份认同。所以,空间压缩带来了主体对空间更为强烈的“美的规律”的生产。这些可以是对自然故土的怀旧、对殖民区域的痛苦反思、对曾经家园空间的追忆、对民族社群空间的认同,等等。“对体验过的场所和空间的记忆,倘若这是真的,那么历史就确实必须让位于诗歌,时间必须让位于空间,成为社会表现的根本材料。空间意象于是就对历史表明了一种重要的力量。”[14](P.274)在文学创作进程中,空间已经成为作家进行描写和构思的“客体对象”,甚至直接能够成为文本中的意象表达,承载主体的审美意识。比如以余光中、洛夫、严歌苓、白先勇为代表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空间往往成为激发他们文学创作的动力。从空间放逐到诗意怀乡、从空间漂泊到身份认同,这种忧伤而甜蜜的诗意感怀正是在现实空间压缩的同质化场景中得到释放,也成为文学艺术守候的一方心灵净土。“不论当时挥笔的作者是少年、壮年或晚年,二十一岁以前在那片华夏山水笑过哭过的日子,收惊喊魂似地,永远在字里行间叫我的名字。”[15](P.2)
二、知识形式:空间符号与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话语释放
经过主体实践与体验的空间被赋予了场所、景观、地方、本土等特定的美学符号意义。索亚“第三空间”中精神空间的极度释放、鲍德里亚的空间符号批判、詹姆逊的“超空间”与视觉空间表达等等,这些都凸显出空间本体的美学与符号指向。具有美学意义的空间符号也构成文论知识系统中文学形象、文学意象以及文学典型的组成部分,并且也涉及审美情感、思想内容、意识形态、语言结构等问题。“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型它就不可能表现。而这种构型过程是在某种感性媒介物中进行的”[16](P.180)。空间符号纳入文论体系之后,可以通过“符号结构”“形式美感”等建构出从文本内部分析到文学情感意义的知识系统。根据结构主义“深层结构”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空间符号的深层意蕴是意识形态,这也正契合了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询唤机制”。文学中的空间符号一方面构成文学形象、文学意象等内部研究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构建出从审美符号到意识形态的文本反思知识线索。
(一)空间符号的审美意义与文学形象建构
文化符号作为主体精神实践的产物,主要是通过语言、形象或一系列抽象形式而表现意义。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前,知识界一直认为意义源自事物本身。卡西尔则认为符号构成事物意义和内容的“形式”,是融合了主体先验感性内容和理性思维的综合体。主体依靠符号来阐释世界,符号也能够把具体感性的表象材料抽象为意义普遍传达的形式。“在任何语言‘记号’中,在任何神话和艺术的‘形象’中,本质上超出全部感觉领域的精神内容被翻译成可感觉的形式,成为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东西。”[17](P.209)符号构成美学形式研究的重要承载,并被恩斯特·卡西尔、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等美学理论家分别界定为“生命形式”“有意味的形式”以及“情感形式”等维度。空间符号构建出空间审美实践的形式载体与文本落脚点,并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知识形式。它凝练了主体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艺术生产的对象化结果。索亚的“第三空间”概念就蕴含了丰富的美学内涵,也可以视为独特的文学文本符号。索亚认为“阿莱夫”在文学艺术中的景观表现与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空间设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看见阶梯下方靠右一点的地方有一个闪烁的小圆球,亮得使人不敢逼视。起初我认为它在旋转;随后我明白,球里包含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场面造成旋转的幻觉。”[18](P.306)从阿莱夫中可以看到大海、黄昏、迷宫、城市等大千世界,也能够看到自己的脸庞。阿莱夫正如独特的文学意象,充满丰富的感性思想与审美想象。索亚在《第三空间》的最后一章,系统对阿姆斯特丹城市空间进行描绘,列举了众多的空间符号并融合自身的审美体验,使特定地理空间焕发出景观意蕴。神圣静谧的修道院、独立整齐的公寓楼房、闲适自由的咖啡馆、穿梭城市的自行车、曲径幽深的街区小巷,这些不仅凝练出城市历史文化的表征符号,更是成为唤醒主体审美意识与怀旧情愫的艺术形式,传达出自由、诗意与灵动的生活乐章。“过去无处不在,在狭小的幽暗处、在曲折的走廊上、在布满鲜花的角落里、在没有窗帘开开闭闭的窗户中。其中的日常生活已成了一种拥挤的纪念品,按照一定比例以当代密度铭记了至少四个多世纪的地理历史。”[19](P.356)第三空间建构出具有家园、景观、本土、环境等美学意义的概念范畴,这也是按照“美的规律”精神生产的结果。由此,空间成为一种文本符号,融入到文学和美学的形式构建中。
如果说索亚立足于城市空间的审美想象建构出“第三空间”符号序列,那么鲍德里亚和詹姆逊则将视角深入到现代消费社会、影视视觉文本的“超空间”领域,生发出更加具有“元空间”色彩的符号体系。空间符号不仅仅呈现出静谧、自然的审美景观,更是成为诉诸于主体视知觉“深度空间”的虚拟化符号意象,表征出主体在后现代视觉文化中的生存状况。鲍德里亚延续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将现代工业的空间、社会、主体的三元辩证法更改为空间、消费和符号之间的动力关系。商品、物质、图像、审美等借助于完备的市场体系和新传媒技术渗透进主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构建出一个精致、完整且表面上“自由”“平等”的空间。现代社会主体的“生产空间”已经让位于“消费空间”,空间形态逐步呈现出后现代“形式化空间”“符号空间”等。消费社会不仅仅带来“物体系”层面的主体满足,更是生产出象征主体身份、地位、权力、阶级以及审美等方面的差异性。“如果我们将消费视为一种生产,符号的生产,其中,在(符号的)交换价值的一般化基础上,这种生产也进入了体系化的进程。”[20](P.68)而空间符号则构成消费社会的重要景观,并大量体现在电影、戏剧、建筑、公园、城市涂鸦墙等空间领域。比如迪士尼公园就体现出艺术“仿真”的虚拟空间,该空间是对现实世界的“全息投影”,主体徜徉其中感受到的是空间符号的“诱惑”和逼真幻觉的审美体验。城市涂鸦更是将艺术区、贫民区等进行艺术化改造,促使特定空间具有审美力量。“这些墙绘将在艺术史上留名,因为它们巧妙地用线条和色彩在光秃秃的墙面上创造出了空间——最美的画总是那些错视画,它们创造了距离和精神的错觉。”[21](P.109)空间符号凸显出后现代艺术的“自身重叠”与“美学的快乐”,而数字赛博空间的虚拟仿象更是建构出了一种无深度感的符号能指序列,比如电影《黑客帝国》中的色彩缤纷的数字超真实空间,等等。
(二)空间符号的审美意识形态指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强调把空间生产以及文学艺术活动放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探究不同知识场域之中的动力学辩证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2](P.2)文学艺术绝非仅仅是局限在“为艺术而艺术”场域中的“形式游戏”,更是通过审美以文化批判的力量介入到社会现实场域,给主体的自由生存提供现实方案。空间符号作为后现代主体空间审美实践的产物,一方面成为特定的文学形象与文学意象,将空间本体视为蕴含情感话语、推动文本叙事、构建深层结构的能动存在;另一方面,它也延展出文学艺术场域并进入到广阔的文化场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反思色彩。
首先,空间符号的审美表达强调了文本蕴含的对抗性元素。后现代消费社会固然产生了仿象的“超空间”样态,并潜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询唤”机制;那么同样也存在普通民众的、个体的、自由的空间符号表达。鲍德里亚高度肯定了城市街头以及贫民区、艺术区的涂鸦运动,认为此种特定空间的“公共艺术”标志出身体与主体的自由。涂鸦运动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纽约等一些大城市,本是一些年轻人和具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家们在街头巷尾的空间中进行自由的绘画表达,随后延续到了地铁车站、停车场、摇滚俱乐部等区域。涂鸦自身的随意性、无意义性恰恰实现了对符号所指意义的对抗。强烈的色彩、舞动的线条以及无深度感的画面内容等建构出独立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文本能指的“漂移”中实现审美形式的释放。“它把已经解码的城市空间变为领地:某条街、某堵墙、某个城区通过涂鸦而获得生命,重新成为集体的领地。”[21](P.107)鲍德里亚同样对巴黎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大楼的空间设计高度赞赏,认为该建筑将自然生态与现代文明、空间遮蔽与艺术欣赏实现了完美融合,体现出诗性建筑的特点。主体建筑周围是一圈巨型透明玻璃墙,两者之间是种植了大量植物并具有良好生态的花园,艺术、科技、人文与自然实现完美统一。这是对审美仿象的调整,体现出文学与诗性的场所感。
其次,空间符号建构出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视野。符号空间是具有审美意蕴的存在,它被主体生产出来的同时又凝聚了历史文化;而现代主体身处其中进行审美“再体验”“再认知”之时,两者就传达出阶级、权力、身份等一系列社会结构内涵。本雅明立足于现代主义文学基础,试图在城市空间中找出恢复艺术“灵韵”、重塑审美现代性的知识方案。巴黎的“拱廊街”则构成了色彩鲜明的异质空间,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城市发展的时间幻象,并实现时间空间化的转型。拱廊街虽然也具有商业属性,但是其设计往往细致精巧,光线也较为充足,顶部由玻璃和钢铁构架进行覆盖,这既是一个防风挡雨且没有车马喧嚣的独立空间,也能够与外部商业大街紧密联系。拱廊街给都市个体创造出类似海德格尔所认为的审美体验“共在(Mitsein)”状态,进而与资本主义的空间霸权与时间幻象进行对抗。“这种变化多端、五颜六色的生活只能是在灰色鹅卵石中、在灰色的专制主义背景前生发出来。”[12](P.101)同样,詹姆逊认为面对后现代文化“超空间”图景,主体可以借鉴凯文·林奇《城市意象》里自身在地图中的定位方式,将理性认知纳入地理景观、将文学文本纳入社会结构领域,并以意识形态反思指导主体的审美活动。“‘认知绘图’正可提供这种一个具教育作用的政治文化,务使个体对其自身处于整个全球性世界系统中的位置有所了解,并加以警觉。”[23](P.514)同时,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对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小说《吉姆老爷》进行阐释,将大海空间符号与主人公吉姆的行动进行融合,发掘其中的现实异化、殖民扩张等意识形态问题。康拉德将文本叙事放置于广阔的地理空间之中,主人公吉姆在大海航行并先后经过孟买、加尔各答、仰光等城市,建构出西方文明与“蛮荒世界帕图桑”之间的空间对抗。帕图桑作为另类世界中的特定空间意象,隐喻了一个安静、自然而又脱离资产阶级空间异化的场景,此种乌托邦式的空间想象也给文学增添了现代主义色彩,凸显出“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而大海空间符号则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主人公的自我救赎行为是在大海中完成的,并与世俗生活具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促使吉姆的逃离具有现代主义审美自律的意味;另一方面,大海也是资产阶级不断进行空间扩张,实现空间规训的场所,暴力、权力、商业、劳动等也往往通过大海来展现。可见,现代小说文本的大海符号和传统文学描写有所不同,它体现出审美空间救赎与资产阶级空间生产相融合的意识形态效果。“群体和生活方式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内仍然还会存在,还没有被还原到宗教唯美主义主流的偶像和忧郁意象。”[24](P.239)
三、知识景观:空间批判与文学理论“价值论”的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空间实践、空间符号、审美意识形态等理论建构起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以学科互涉的方式实现文学理论话语“向外转”的知识景观,实现知识从“有限生产”到“大生产”的转型。在此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再次焕发出崭新的活力,推动文论知识呈现出“实践论”“审美论”“符号论”“意识形态论”等由内到外的研究特征,其中蕴含的“美的规律”“场所精神”“第三空间”“认知绘图”等理论可以有机渗透进文学活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文本论等相关知识范畴内部,凸显出空间元素在文学批评与分析中的功用。以空间理论为契机,文论知识“大生产”模式已经开启,哲学、美学、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等纷纷展开与文论知识互涉的进程。
(一)另类空间的审美意义释放与文论知识反思性的加强
空间生产不仅仅凸显出主体和社会自然之间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关系,更是内蕴了空间区隔、空间差异等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一直秉承的“空间”“社会”与“主体”三者之间的辩证动力关系。空间符号则通过审美意义的承载、空间形象的凸显以及意识形态的传达,完成了空间理论与文学文本的融合。由此,空间差异在文学中得到凸显,另类空间的诗性价值得以释放,文学中的空间景观更加多元,文论知识的反思性也得到加强。审视空间差异的场景,福柯立足于微观政治论的视角进行反思与批判,并且将空间与资产阶级文化权力进行融合,提出“另类空间”与“异托邦”的空间正义解决方案。另类空间不仅与主流的社会空间保持距离,也凝练出自由多元的审美意义,这是形式各异且充满艺术想象的“异托邦”空间。比如剧场和影院空间,它们能够通过舞台、银幕等艺术技巧将不同空间进行融合,最终创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感的审美文本,这就是一种普遍的异托邦存在。“异托邦有创造一个幻象空间的作用,这个幻象空间显露出全部真实空间简直更加虚幻,显露出所有在其中人类生活被隔开的场所。”[25](P.57)从空间理论的视角而言,“异托邦”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反思与批判的方案。从文论知识体系而言,“异托邦”促使文学创作和接受主体能够更加关注另类空间的诗性元素,将平时已经习惯化的碎微空间进行审美观照,发掘其灵动、自然、形象的特质。比如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就重新发掘出抽屉、柜子、鸟巢、角落、家宅等空间的感性审美内蕴,这些符号往往与个体童年回忆、孤独的情感体验、温暖的栖居等情愫密切联系。由此,文学就不再单纯是对自然现实的模仿、主观情感的表达或者是抽象朦胧意象的追寻,这种由空间符号形式所带来的表征意义呈现同样参与进文学活动领域,引发作家的创作激情并且成为读者实现审美共鸣的载体。
“只有在距离的基础上他才可能对自然产生真正的审美观照,此外通过距离还可以产生那种宁静的哀伤,那种渴望陌生的存在和失落的天堂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浪漫的自然感觉的特征。”[26](P.389)陌生的、另类的、有距离感的空间便蕴藏着审美解放的动力。愈是与总体化空间保持距离,并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愈是具有强烈的审美对抗意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艾芜的边疆异域、萧红的北方大地、废名的乡村风景、张爱玲的都市描绘、赵树理的山西民俗、张炜的高原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以及奈保尔的西班牙港、普鲁斯特的贡布雷往事、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等等,这些文学空间符号一方面完成了意象的风格化表达,另一方面则凸显出另类空间的差异性伦理,一种在总体化空间之外的诗性精神。环保主义者约翰·缪尔曾经诗意地描绘他在“荒野”中的视知觉感受,从而凸显环保运动的意识形态伦理。“我们昨晚在群山中睡得多么深沉呵、酣卧苍树星辰下,静听庄严肃穆的瀑布声,还有许多甜美和谐的细碎声音抚慰着人心,低语者安宁。”[27](P.29)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一直都处在另类空间的游荡过程中,从特立尼达岛、西班牙港、英国以及对印度的憧憬,他时刻感受到空间与自身身份的“他者化”存在,并激发起创作的欲望。在文学文本中,熟悉或陌生的地理空间便成为触发作家艺术构思的机制。故乡的回忆、孤独的沉思、直觉的空间感受等等,这些都化作诗意的语言文字,表现出身份认同的焦虑与个体的抗争。“这已经驱使我更进一步地撤退。我的真正的生活,我的文学生活,注定要在别的地方。”[28](P.127)文学中的另类空间表达不仅实现了审美意义的释放,丰富了文学形象塑造的范围,更是内蕴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反思与差异性意义。此种意义可能与民族身份、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文化认同、感性自由等问题密切相连。这也促使文论知识体系进一步“向外转”,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凸显文学的审美价值。
(二)流动空间的公共性建构与审美现代性延续
伴随全球化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商品生产和消费更加灵活多元,数字传媒技术也带来新一轮的空间压缩,空间逐步呈现出碎微化、主体化、生活化与流动性特征。赛博空间的虚拟仿象、主体信息交流的便捷、影音图像的审美革命以及全球文化空间网络的整合等等,这些都破除了现代空间的模式化静态生产行为,并转向更加自由灵活的流动空间。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后现代主体自由的物质生产实践方式与日常生活空间的流动建构出全新的空间体验模式,网络社会的发展更是促使主体、符号、信息、技术、商品等高速流动。主体的流动也带动了更深层次的文化空间、艺术审美空间以及虚拟空间的变革,并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流动空间包括了构成全世界每个网路之节点的地方均质建筑的象征联系,所以,建筑避开了每个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并且被奇幻世界之无穷可能性的新想象捕获,潜藏于多媒体所传送的逻辑之下。”[29](P.512)网络社会正是消解了传统地方空间(local space)的家园感,而以赛博空间、超空间、叙事空间、并置空间以及众多虚拟影像空间符号构建出以主体日常生活为核心的“空间场”。该“空间场”融合了主体对生活空间的视知觉感知、网络空间的身份代入以及虚拟精神空间的确认等等,是一个结合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的主体实践场域。流动空间的实质正是不同主体“空间场”的交往,是主体生产关系、空间关系与审美交流的重构。比如游戏赛博空间带来虚拟的审美沉浸效果,在另类空间中释放感性体验,超越了主体所处的实际空间。从花香鸟啼的市井村落,到天寒地冻的冰雪极地;从狼烟四起的险要关隘,到异域世界的魑魅魍魉,不同的玩家主体进入特定的游戏空间,实现“空间场”的流动与交往。与此同时,由“赛博格作者”(cyborg author)引领的超链接文学在传统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借鉴电影蒙太奇的共时拼贴技巧,将不同文本放置于网络内不同空间的“超链接”内部,以“人——机”互动的方式实现文本、多媒体影像以及虚拟赛博空间的融合。作家马修·米勒的网络文学《旅行》就将文本放置于美国地图的超链接中,接受者点击某个州的链接,相应的文本叙事与空间景观便显现出来,成为具有多媒体“散文游记”特色的文本。“一个超文本包括主题和主题之间的链接,以及段落、语句、词语,抑或是数字化图像和视频的剪辑。……电子超文本并不是简单无序的堆砌,因为创作者用电子链接确定了文本碎片的关系。”[30](P.5)不仅赛博文本呈现出“空间场”流动的特质,后现代文学也通过叙事革命与空间并置的技巧推动主体审美体验的自由转换。法国作家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以佐治和其他几位骑兵的撤退经历为背景展开叙事,将现实空间与回忆空间、空间碎片与时间变幻结合在一起,呈现出表面破碎但内部结构巧妙整体的面貌。旅馆房间、火车车厢、集中营、果园、战场等空间意象交叉出现,营造出“空间意识流”的叙事景观。“为了理解这些质变,必须找回活动的、实际的身体,它不是一隅空间,一束功能,它乃是视觉与运动的交织。”[31](P.35)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同样采取了空间并置的技巧,现实空间与精神空间在主人公的经历中随处浮现,建构出真实与想象相交融的空间意象。这些意象在文本中实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义滑动,彰显出新的文学叙事形式。“我想象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32](P.48)可见,“空间场”的流动不仅表现在后现代主体的数字信息交流以及网络“赛博社区”的建立,更是渗透进文学创作、文本形式、文学接受、审美共鸣等领域,创设出共时性、并置性与空间化的文学分析视角,也适应了后现代“文学性”延展、美学知识播撒的文化景观。这正如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所提出的“平滑空间”与“游牧美学”思想。平滑空间以大海、草原、沙漠、冰原、音乐、景观等为代表,是一种没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空间区隔的自由流动空间,并与资产阶级所营造的城市、传媒“条纹空间”相对立。在平滑空间中,主体可以如“游牧”般自由驰骋,饱览数字艺术带来的无限风光与瑰丽奇异的虚拟仿真景观。“(视觉功能)还能够重新给出平滑空间,解放光线,调制颜色,恢复一种轻盈的接触性空间——此种空间构成了平面之间相互作用的未限定的场所。”[33](P.716)
空间流动蕴藏着新的自由解放的力量,并能够有效与资本主义理性空间霸权进行对抗,实现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时代诉求。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是资产阶级空间扩张的结果,并以城市空间来消泯第三世界游牧文明的话,那么后现代的空间流动却建构出“游牧者共同体”“赛博空间社区”等公共空间形态。工人阶级、普通民众、艺术家、草根群体、贫民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民族聚居区域、荒野景观等等,这些在另类空间中生存的主体,可以借助“空间场”的流动重新树立文化与符号自信。“那些能够负担得起权力的人只是生活在时间中。那些负担不起权力的人则生活在空间之中。对前者而言,空间无关痛痒。对后者而言,他们却需拼尽全力让空间变得重要。”[34](P.40)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伴随审美现代性应运而生,不同主体能够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从审美到意识形态的文化反思路径。审视当代文化图景,主体的“空间场”可以借助赛博空间、城市公共艺术、大地艺术、超链接文本、后现代文学与影视等组建自由的“文学艺术社区”,促使主体与主体之间产生审美共鸣,并进一步介入到社会问题中。约瑟夫·博依斯的公共艺术《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就是在卡塞尔城市广场的空间中展开的,每位市民都可以参与其中并栽上自己的一棵树。该艺术以朴素“共享”“参与”的理念实现艺术精神与生态意识的融合。而中国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以及杭州G20峰会“最忆是杭州”文艺晚会等都将富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诗歌、戏曲、舞蹈、散文等进行多方位艺术表现,在美轮美奂的山水景观和诗意盎然的诗词歌赋中呈现中华文化之美。比如“最忆是杭州”晚会就彰显出丰富的空间意象符号:无论是对《春江花月夜》的实景呈现,还是《梁祝》的越剧与舞蹈表达,都在西湖之上的公共空间塑造,实现了全球空间的中国文学形象传播与审美符号共鸣。
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空间形象彰显,到“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的空间离愁表达;从“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哀婉感叹,到“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雄伟磅礴,空间一直构成着主体精神实践的对象,也成为文学艺术中显著的符号景观。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以空间生产为知识基础,强调主体、空间与社会的三元辩证关系,并且以“美的规律”和“本质力量对象化”来凸显空间的诗性特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通过“第三空间”“另类空间”等概念一方面建构出空间符号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则发掘符号形式内蕴的身份、阶级、文化等深层话语价值。这给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本论等理论提供了崭新的知识学资源,促使空间元素成为探究文学活动、创作机制、文本意象、审美价值、对话共鸣的重要视角。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也推动了文论知识“大生产”的进程,将文论与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学科进行知识互涉,使文学研究与文论知识进入宏大的文化场域,并更加关注主体的诗性存在问题。这正如泰戈尔的诗句:“世界在踌躇之心的琴弦上跑过去,奏出忧郁的乐声”[35](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