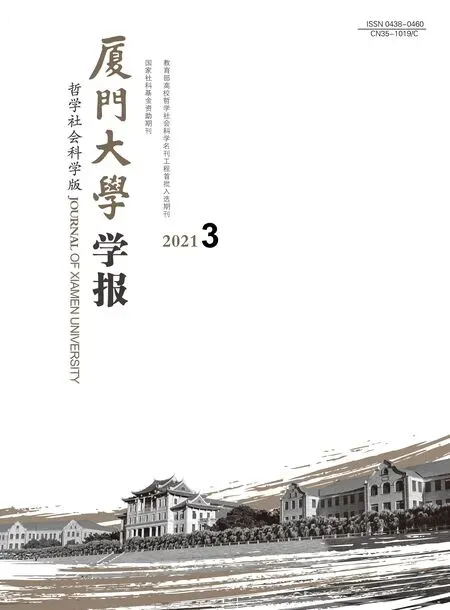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述论
2021-04-17陈明光靳小龙
陈明光,靳小龙,毛 蕾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唐宋的土地产权体系,由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私田产权和官田产权三大类构成。其中,自然资源是指与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能被利用来产生使用价值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自然诸要素,包括土地、水体、动植物、矿产等。一般而言,我国现代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建设,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监管权等不同层面的制度规范。在中国古代,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其实也包括这些层面,并且有过不小的变化。例如,历代的 “山泽之禁” 或者 “弛山泽之禁” ,都意味着山泽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监管权的变化。①例如,关于秦汉时期的变化,如《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载: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 (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731页)《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载: “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 (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18页)汉武帝时,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 (第1429页)古代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变化,也包括水体产权以及与水体相关的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的变化,宋代的 “废湖为田” 和 “退田为湖” 就是典型事例。唐宋国家对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治理,不仅涉及产权关系,也关系到财政问题,并且与地方经济秩序、自然环境保护等的治理也有诸多关联。关于中国古代的盗耕种,学界尚无专题研究,近期我们撰有《论唐宋国家治理 “盗耕种” 与私有土地产权及财政考虑》一文,对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私有土地问题加以讨论。②该文在 “第四届财税史论坛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上发表。本文则论述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相关问题。
一、唐宋有关盗耕种的立法与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
盗耕种,是唐朝首次在法律文本运用的法律术语,并有专项法律条文。《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称: “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苗子归官、主。(注:下条苗子准此)”①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4-245页。这条律文明确地把盗耕种涉及的土地产权分为公有和私有两大类。这条律文也适用于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
唐朝针对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有专门的立法。首先,关于水体资源公共产权。《唐律疏议》规定: “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注: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 【疏】议曰:
有人盗决堤防,取水供用,无问公私,各杖一百。故注云 “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同” 。水若为官,即是公坐。 “若毁害人家” ,谓因盗水泛溢,以害人家,漂失财物,计赃罪重于杖一百者,即计所失财物, “坐赃论” ,谓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 “以故杀伤人者” ,谓以决水之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杀伤者,一同盗决之罪,故云 “亦如之” 。②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第505-506页。
其次,关于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的归属。例如,因水流改道出现的 “新出之地” 的产权处理,唐朝《田令》规定: “诸田为水侵射,不依旧流,新出之地,先给被侵之家。若别县界新出,依收授法。其两岸异管,从正流为断,若合隔越受田者,不取此令。”③《宋刑统》卷一三《户婚律》 “占盗侵夺公私田” 条引《田令》,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水流改道引起的 “新出之地” 本属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具有公共产权的原始属性。对此唐朝《田令》区分不同情况作出归属处理。一是优先补偿给被侵失地之家,即成为私有产权;二是 “新出之地” 不在被侵之家属地的 “别县” ,则 “依收授法” ,就是根据《田令》的有关规定,先收为公有田地,再酌情授予该县缺地少地的农户。但是,如果被水侵之家按规定可以越县受田,则另作别论。
再如荒地。《唐律疏议》称: “不耕谓之荒,不锄谓之芜。”④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 “诸部内田畴荒芜者” 条【疏】议,第248页。可知荒地包括私荒田、官荒田,以及作为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无主荒地。对荒地的产权归属,唐代法令有三种处理规定:一是荒废的私田,田主拥有私人产权和优先经营权。例如,唐朝官员选举考试的一道判案试题是: “诸畿县置屯田,佃百姓荒地。主令复业,请自耕种,屯司不与。县司执申,若不还地,人即却逃。”⑤董浩等编:《全唐文》卷四〇八,贺兰广:《对屯田佃百姓荒地判》;卷九〇二,李暄:《对屯田佃百姓荒地判》,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81、9414页。可见 “百姓荒地” 的私有产权是县司为之申诉复业的依据。二是荒废的公田即官田,仍由官府掌握产权。对于公私荒田的不同产权归属,唐《田令》区分得很清楚,《田令》规定: “诸公私[田]荒废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听……私田三年还主,公田九年还官。”⑥天一阁博物馆等:《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田令》(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8-259页。三是作为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 “无主荒地” ,具有公共产权的原始属性,既允许私人开垦,也可以由官方支配。例如,唐《田令》规定: “诸田有山岗、砂石、水卤、沟涧之类,不在给限。若人欲佃者听之。” “诸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于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⑦天一阁博物馆等:《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田令》(下册),第255页。不过,受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传统观念影响,唐朝政府对于无主荒地具有普遍性的管辖权和优先处理权,所以《田令》规定官府可以把宽乡的无主荒地授给五品以上官员充作永业田。五代也是如此,如广顺元年(951)八月,王景言: “幽州饥,继有流民入界。” 周太祖敕称: “其沧、景、德管内甚有河淤退滩之土,蒿莱无主之田,颇是膏腴,少人耕种,可令新来百姓量力佃莳。”①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六七《帝王部·招怀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012-2013页。
上述唐朝关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立法规定涉及的土地资产产权,如水流改道的 “新出之地” “无主荒地” ,如果发生盗耕种,也适用以 “盗耕种” 律文论处。
宋朝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立法方面,除水体资源之外,对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资产产权进一步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庆元条法事类集》卷四九《农桑门·农田水利》收录的《田令》称:
诸江河、山野、陂泽、湖塘、池泊之利与众共者,不得禁止及请佃、承买,监司常切觉察,如许人请佃、承买,并犯人纠劾以闻。河道不得筑堰或束狭以利种植。即潴水之地,众共溉田者,官司仍明立界至,注籍。(注:请佃及买者,追地利入官)②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桑门·农田水利》,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4页。
所引《户婚敕》也规定: “诸潴水之地(注:谓众共溉田者),辄许人请佃、承买,并请佃、承买人各以违制论,许人告。未给、未得者,各杖一百。”③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桑门·农田水利》,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683页。《赏格》规定: “诸色人告获请佃、承买潴水之地(注:谓众共溉田者),每(取)亩钱三贯(注:一百贯止)。”④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桑门·农田水利》,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685页。这种法令仍然赋予这些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公共产权的原始属性。
同时,宋朝也制定了关于土地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转换的法令。一是对江河 “不循旧流而有新出地” 的处置。《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田水利》载: “准《田令》,诸田为水所冲,不循旧流而有新出之地者,以新出地给被冲之家(注:可辨田主姓名者,自依退复田法),虽在它县亦如之。两家以上被冲而地少给不足者,随所冲顷亩多少均给。其两岸异管,从中流为断。”⑤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桑门·农田水利》,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683页。比起上引唐《田令》,宋《田令》规定 “虽在它县亦如之” ,进一步突出了被冲之家从 “新出地” 获得补偿的优先权。所谓退复田,既有荒废的民田,也包括水流新出之地。如果盗耕种,则 “论如《盗耕退复田法》” 。⑥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〇《农田杂录》载,绍圣二年(1095)三月三日,工部言: “诸黄河弃堤退滩地土堪耕种者,召人户归业,限满不采,立定租税,召土居五等人户结保,通家业递相委保承佃,每户不得过二顷。(此处当有缺字)论如《盗耕退复田法》,追理欺隐税租外,其地并给告人仍给赏。” 从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961页。
二是关于碱地的处理。《庆元条法事类集》卷四九《农桑门·劝农桑》引《赏令》称:
诸有碱地,县令、佐能劝诱民户开耕者,先具堪与不堪开耕,看望四至顷亩,报主管官检察籍记,申州审实,申茶盐司,于他处差官验讫,内堪者,令开耕。⑦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桑门·劝农桑》,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682页。
可见碱地作为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也具有公共产权的原始属性,如果要让私人开垦并转化为私有产权,必须先经官方实地勘察,允许后办理地籍登记。同时,宋朝《赋役令》规定: “诸人户开耕碱地种成苗稼者,令、佐亲诣验实,标立顷亩四至,取乡例立定税租,以五分为额,仍免四料催科。”①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集》卷四七《赋役门一·拘催税租》,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612页。淳熙六年(1179)五月,浙西提举颜师鲁言: “今乡民于自己硗确之地开垦,以成田亩,或以陈起租税,而为人首。闻官司以《盗耕种法》罪之,将何以劝力田者?乞止令打量亩步,参照契簿内元业等则起立税租,毋得引用《盗耕种法》辄夺而予他人。” 朝廷从之。②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二七《限田杂录》,第6100页。可知碱地经私人开垦后要转化为私有产权,必须以交纳税收为最终依据。如果能交纳税租,就不予盗耕种论处。
宋朝关于 “碱地” 产权转换为私有必须以交纳租税为最终依据的立法精神,也适用于荒地。在唐代荒地产权规定的基础上,宋代进一步把荒地产权划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为 “私荒田” 。如徽宗政和元年(1111)七月,臣僚言: “私荒田,法听典卖与观寺。”③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一《农田杂录》,第5963页。可见 “私荒田” 的产权属于私人,可由田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典卖。不过,在战争环境下,宋朝政府也有把 “公私荒田” 一起拨充屯田的特殊处置。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五,绍兴三十年七月戊戌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108页。另一类称为 “在官荒田” 或 “没官荒田” “系官荒田” ,其中包括作为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 “天荒田” ,其产权归官方处置。《庆元条法事类集》卷四九《农桑门·劝农桑》引《赏格》称: “有碱地,县令、佐能劝诱民户开耕收刈苗稼者(注:系官荒田有碱,召人请佃开耕,收刈苗稼者,亦准此)三顷,升半年名次;七顷,升一年名次;十顷,减磨勘一年;二十顷,减磨勘二年;三十顷,减磨勘三年。”⑤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桑门·劝农桑》,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682页。政和元年五月,臣僚言:
天下系官田产,在常平司有《出卖法》,如折纳、抵当、户绝之类是也;在转运司有《请佃法》,天荒、逃田、省庄之类是也。自余闲田,名类非一,往往荒废不耕,虽间有出卖,请佃之人又为豪右之侵冒,输官租赋十无一二,欺弊百出,理难齐一。其请佃人户又以经系官田,不加垦辟,遂使民无永业,官失主户。公私利害,所系非轻。乞命官总领条画以闻。
六月,户部侍郎范坦奏称:
奉诏总领措置出卖系官田产,欲差提举常平或提刑官专切提举,管勾出卖。凡应副河坊沿边招募弓箭手,或屯田之类,并存留。凡市易、抵当、折纳、籍没、常平、户绝、天荒、省庄、废官职田、江涨沙田、弃堤退滩、濒江河湖海自生芦草荻场、圩垾湖田之类,并出卖。⑥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一《农田杂录》,第5962-5963页。
其中列举的天荒田、江涨沙田、弃堤退滩、濒江河湖海自生芦草荻场等四类,都属于自然资源土地资产,这时已经明确地被划归 “系官田产” 。
宋朝对系官田产中的自然资源土地资产,或予出卖给私人,或拨充职田、屯田等官用,⑦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六八载,嘉泰三年(1203)十一月,宁宗南郊赦文称:官员职田, “在法以官荒及五年以上逃田拨充” 。第8083页。更多的是招佃取租。如熙宁二年(1069)八月, “中书言:‘黄河北流,今已淤断,所有恩、冀以下州军,黄河退背田土顷亩不少,深虑权豪之家与民争占,及有元旧地主因水荒出外未知归请。’诏河北转运司:‘应今来北流闭断后黄河退背田土,并未得容人请射及识认指占。听候朝廷专差朝臣往彼,与本处当职官同行标定讫,收接请状,纽定租税,均行给受。’”⑧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七《农田杂录》,第5958页。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戊子,中书省欲差朝官 “诣河北东西、府界沿河,与州县同括民间冒佃河滩地土,使出租” 。刘挚建议说: “括田取租,固未敢言不可,但恐遣使不便。不若下转运司令州县先出榜,令河旁之民凡冒佃河田者,使具数自首,释其罪,据顷亩自令起租,严立限罚。若限满即差官同河埽司检按。”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〇,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21页。宣和元年(1119)八月,农田所奏:
应浙西州县,因今来积水减退露出田土,乞每县选委水利司谙晓农田文武官,同与知、佐,分诣乡村检视标记,除出人户已业外,其余远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荡及湖深退滩、沙坠等地,并打量步亩,立四至坐落,著望乡村,每围以《千字文》为号,置簿拘籍,以田邻见纳租课比扑,量减分数出榜,限一百日,召人寔封后(投?)状,添租请佃。限满拆封,给租多之人,每户给户帖一纸,开具所佃田色、步亩、四至、著望、应纳租课。如将来典卖,听依《系籍田法》请买,印契书填交易。②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三《检田杂录》,第5964-5965页。
政和末年,西城所管辖的官田收入中, “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③《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二·赋税》,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2页。。这些河滩地土、天荒田、草葑茭荡及湖深退滩、沙坠等地,都属于自然资源土地资产,这时都被一一检视标记为官田,或 “括田取租” ,或 “添租请佃” 。
宋朝在沿承唐朝盗耕种法的基础上④窦仪等编、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卷一三《占盗侵夺公私田》规定: “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苗子归官、主。” 律文与唐律相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又制定《盗种法》《盗耕退复田法》《盗决侵耕之法》等法律,同时用敕、格、令等法律形式加以补充。这些法令也适用于处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宋人对耕盗种行为,也使用 “侵耕冒佃” “侵冒” “冒种” “冒占” “冒佃” “侵冒” 等俗语加以表达。
总之,不管是在唐代,还是在宋代,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都受到法律保护。宋朝进一步扩大唐朝以来政府对自然资源土地资产行使的普遍管辖权和优先处理权,直至把 “天荒田、江涨沙田、弃堤退滩、濒江河湖海自生芦草荻场” 等都划归 “系官田产” ,明确地赋予官有产权。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就是以这种产权规定和盗耕种法令为法律依据的政府行为。
二、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财政考虑
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无疑具有明显的财政考虑。
唐朝鼓励地方官员采取措施,劝课开垦包括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在内的 “公私荒田” ,以此作为地方官员考绩内容之一。唐《考课令》规定: “其劝课农田能使丰殖者,亦准见地为十分论,每加二分,各进考一等(注:此谓永业、口分之外,别能垦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劝课以致减损者(注:谓永业、口分之内有荒废者),每损一分,降考一等。”⑤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考绩》,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7页。《唐律疏议》还规定: “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若于宽闲之处者不坐。” 对此,【疏】议解释说:
王者制法,农田百亩,其官人永业准品,及老小寡妻受田,各有等级。非宽闲之乡,不得限外更占。……又依令: “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 “应言上不言上” 之罪。⑥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第244页。
显然,于宽乡多占之田包括开垦荒地, “律不与罪” 之律也包括 “盗耕种” 律文。但是,【疏】议也指出,在宽乡垦辟包括荒地在内的 “剩田” ,仍然必须事先向官府申请备案,否则要依 “应言上不言上” 论罪。这体现了唐朝政府对无主荒地所具有的普遍性管辖权。
在唐朝前期,鼓励开垦荒地最直接的财政效益是可以增收地税。在唐朝后期,特别是在农业经济凋弊的阶段,唐朝政府采取减免一定年限税收的政策鼓励私人开垦无主荒地,提高纳税人的税负能力,限期过后依然要征收赋税。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69)十二月辛酉, “敕京兆府税宜分作两等,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税六升,能耕垦荒地者税二升”①《旧唐书》卷一一《代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4页。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六《水利三》,第6140页。。太和三年(829)五月,中书门下奏请改善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办法,其中指出: “如称垦辟田畴,则云本垦田若干顷,在任已来加若干顷,并须申所司,附入簿籍。如荒地及复业户,自有年限,未合科配者,亦听申奏,明言合至其年并收租赋。”②王溥:《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04页。会昌元年(841)正月,武宗制称: “如有荒闲陂泽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垦辟耕种,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税限;五年之外,依例收税。”③王溥:《唐会要》卷八四《租税下》,第1543-1544页。五代时期的有关政策也是如此。④例如,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二月敕曰: “宜令逐处长吏遍下管内,应是荒田,有主者一任本主开耕;无主者一任百姓请射。佃莳三年内,并不在收税之限。” (《册府元龟》卷七〇《帝王部·务农》,第793页)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正月乙卯制称: “……应天下户口,夏税见供输顷亩税赋外,一任人户开垦荒地及无主田土,五年之内,不议纳税。” (《册府元龟》卷九五《帝王部·赦宥第十四》,第1135页)这反映出唐五代政府鼓励开垦自然资源土地资产时经济效益与财政效益兼顾的政策取向。
有如唐朝,宋朝为了鼓励垦荒,也制定了免税、减税政策。如乾德四年(966),太祖下诏: “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⑤《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二《政事三十五·田农》,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58页。《赋役令》规定: “诸人户开耕碱地种成苗稼者,令、佐亲诣验实,标立顷亩四至,取乡例立定税租,以五分为额,仍免四料催科。”⑥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集》卷四七《赋役门·催拘租税》,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612页。“诸己业田已有税额而后加垦辟若栽植桑柘者,不在增税之限。”⑦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集》卷四七《赋役门·受纳租税》,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621页。至道三年(997)七月,太宗诏: “应天下荒田,许人户经官请射开耕,不计岁年,末议科税,直候人户开耕,事力胜任起税,即于十分之内,定二分永远为额。”⑧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六三《农田杂录》,第7698页。特别是经北宋末年战乱对地方农业经济的较大破坏之后,南宋多次调整包括开垦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在内的荒田起税政策。例如,孝宗乾道四年(1168)二月,知鄂州李椿言: “本州荒田甚多,往岁间有开垦者,缘官即起税,遂致逃亡。乞募人请佃,与免三年六料税赋,三年之外,以三之一输官,所佃之田给为已业。至六年,递增一分,九年然后全输。或元业人有归业者,别给荒田耕种。” 获得批准。⑨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八四至八五《垦田杂录》,第7491页。
比起唐朝,宋朝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时带有更加明显的财政考虑。
第一,有关政策法令更加明确地指出,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是为了增加税收,特别是纠查逃税。以治理荒地的盗耕种为例。哲宗绍圣二年(1095)三月,工部言: “诸黄河弃堤退滩地土堪耕种者,召人户归业,限满不来,立定租税,召土居五等人户结保,通家业递相委保承佃。每户不得过二顷,论如盗耕退复田法,追理欺隐税租外,其地并给告人,仍给赏。”⑩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〇《农田杂录》,第5961页。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三月,明州上言: “契勘广德湖下等田亩,缘既已为田,即无复可为湖之理,不免私自冒种,非惟每年暗失官租三千余硕,而元佃人户词讼终无由止息,又因缘有争占斗讼,愈见生事。欲乞依旧为田,令元佃人户耕种。”⑪《旧唐书》卷一一《代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4页。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六《水利三》,第6140页。绍兴十五年(1145)二月,王鈇措置两浙经界时,上奏说: “人户将天荒产段并淹泊之类修治埂道,围里成田,自系额外产土。欲令逐州知、通、令作一项保明,供申朝廷,量行起税。”①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一二八《赋税》,第8174页。孝宗乾道四年五月,湖北运副杨民望言: “诸州荒田,多无人开耕,间有承佃之家尽力垦辟,往往为人告讦,称有侵冒顷亩,官司从而追纳积年税租,遂致失所。乞自今后,遇有亲耕之人,止催纳当年租税,日前者并与蠲放。”②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一八《垦田杂录》,第6095页。乾道年间(1165—1173),湖北转运司下达处理盗耕种荒田的 “指挥” : “应见佃荒田之家,如有开辟过数,止令输纳旧税,更不通计。其妄执契书告讦之人,官司不得受理。”③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八七《垦田杂录》,第7493页。他们的建议都获得批准。可见宋朝治理 “盗耕种” 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重要目的,在于纠查逃税,增加田赋收入。盗耕种者只要交纳了赋税,就不以盗耕种论处。这与上述宋朝处理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私有化时以纳税为最终依据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宋代实施盗耕种法是把财政利益置于首位的。
第二,出于增加中央财政专项收入的特定考虑。对此可以南宋开展治理盗耕种沙田、芦场等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专项行动为例加以说明。
关于南宋初期淮东、浙东、江东三地开展盗耕种沙田、芦场专项治理的经过,李心传《建炎杂记》甲集卷一五《都下马料(淮浙江东沙田芦场本末)》有专门记载。不过,宋朝对沙田、芦场产权及应征租税的治理并不始于南宋。
前已指出,宋朝把沙田、芦场这两项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列为系官田产。沙田,又称沙洲田、江涨沙田。另有海田,又称海退泥田④《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农田》载:绍兴六年(1136),诏 “诸路总领谕民投买户绝、没官、贼徒田舍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 。第4191页。,也是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土地资产。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一二《版籍类三》 “沙洲田” 条载: “绍圣《常平兴修法》:‘陆可为水,水可为陆。海退泥淤沙塞,碱卤可变膏腴之类,许民陈请,依法成田请税。’” 其 “海田” 条载: “初,香严寺福清上下洋田与民讼不决。熙宁二年,程大卿师孟表其状于朝,明年可其请,令自今沿海泥淤之处,不限寺观、形势、民庶之家,与筑捍为田,资纳二税。” “(福清)海中又有放牧地八百里(海坛里),皇佑中,许民请射如荒田法。今或可耕。”⑤除海田之外,宋朝对海洋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征收的专项税收还有 “砂岸租钱” 或称 “砂岸钱” “砂租钱” ,主要是对宁波一带海洋渔场、海岛田地和海涂征收的,其中一部分征收对象也是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参见倪浓水、程继红:《宋元 “砂岸海租” 制度考论》,《浙江学刊》2018年第1期。可见北宋时期对于沙田、芦场、海田的请射开垦和 “成田起税” ,已经有《常平兴修法》《荒田法》可循。
南宋绍兴年间,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困难,宋廷把出卖或者治理 “兼并之家” 盗耕种沙田、芦场,作为浥注中央财政的新手段。例如,绍兴六年(1136)二月庚戌,高宗根据三省的奏议, “诏江、浙、闽、广诸路总领卖田监司榜谕人户,依限投买乡村户绝并没官及贼徒田舍与江涨沙田、海道泥田,昨为兼并之家小立租额佃赁者,永为已业,更无改易”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八,第1614页。。其后更是开展对盗耕种沙田、芦场并起税立租的专项治理。
绍兴二十七年(1157),宋廷为解决和籴 “都下马料” 的经费来源,决定治理淮东、浙西、浙东三地的盗耕种沙田、芦场, “将以其租为马料之费” 。⑦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都下马料(淮浙江东沙田芦场本末)》,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6页。当年十二月乙未,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潇 “被旨措置镇江府沙田” ,提出治理方案为: “乞委官检踏打量,取见的实顷亩数目措置,各随田地肥瘠高下,轻立租课,就令见租火客耕种,专委知县拘收桩管。如形势之家尚敢占吝,不即交割,即具名闻奏,取旨施行。所有以前违法占种人户收过租课,合尽行追纳入官。”①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九《农田杂录》,第5971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都下马料(淮浙江东沙田芦场本末)》载,绍兴二十九年五月, “福建江海之滨,亦有新出沙田。户部闻之,遽下常平司出卖。而殿院任信儒以为,此皆民间自备钱本兴修,数年之间,偿费未足,望少宽之。乃止” 。第337页。高宗即下诏: “人户冒佃,积年收过租课,特免追纳。其田疾速拘收措置。”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八,第2929页。这是要把被盗耕种的沙田、芦场全部 “拘管” 为系官田产,仍然由现佃人耕种,但转而直接向官府交租,完全剥夺 “形势之家” 既有的占有权、出佃权和收益权,只豁免他们之前获取的租利。次年正月,议事者认为: “拘收入官,固有目前之利,数年之后恐更费力。不若令见占人且行管佃,净认租课为便。”③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九《检田杂录》,第5971页。这就改为继续承认形势之家的占有权和出佃权,但要他们拿出一部分收益作为租课交给官府。我们不妨概括为 “官私分利” 的治理原则。当年二月,高宗诏: “沙田、芦场止为势家诡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户勿例根括。”④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二至三《检田杂录》,第6147页。六月, “诏浙西、江东沙田、芦场,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租,余如旧。”⑤《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农田》,第4190页。可见经过讨论,宋廷把治理淮东、浙丁、江东三地盗耕种沙田、芦场的对象,限定为四等以上主户及形势之家,对他们诡名冒占超过十顷或二十顷的沙田、芦场征收租课,作为国家财政的专项收入。这个治理实施方案仍然以 “官私分利” 为基本原则。绍兴二十九年(1159),朝廷 “以莫蒙经量沙田、芦场失实,责监饶州景德镇税。遂诏尽罢所增租”⑥《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农田》,第4190页。。但是,治理工作并未停止。绍兴三十二年(1162)九月,赵子潇言: “浙西、江东、淮东沙田,往年经量,有不尽不实处,为人户包占。期以今冬自陈,给为已业,与免租税之半;过期许人告,以全户所租田赏之。其芦场量力轻租。” 孝宗诏以冯方措置。⑦《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农田》,第4190页。十一月,因 “民间以为扰,诉讼不绝” ,孝宗 “乃诏沙田、芦场指挥更不施行” 。⑧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都下马料(淮浙江东沙田芦场本末)》,第337页。
总之,绍兴末年宋廷治理淮东、浙丁、江东三地的盗耕种沙田、芦场,分割了形势之家的一部分既得经济收益作为中央财政收益。对此,有不少朝臣和地方官员持有异议。例如,御史叶审言对高宗说: “陛下初欲免岁籴马料,为国便民。然三路辽远,使者岂能尽行?必有强增其数,以希进者,于有力之家,初无加损,而害及贫民,虑致逃移,坐失税额。”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都下马料(淮浙江东沙田芦场本末)》,第336页。莫蒙被贬也是 “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收及贫民”⑩《宋史》卷三九〇《莫蒙传》载: “除户部员外郎。朝廷遣蒙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芦场,上语之曰:‘得此可助经费,归日以版曹处卿。’蒙多方括责,得二百五十三万七千余亩。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收及贫民,责监饶州景德镇。” 第11957页。。 “言者” 都声称是为贫民请命。然而,尽管治理过程中确实出现超出治理范围、起税立租过重等现象,但是有能力 “自备钱本” 开发沙田、芦场⑪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九《农田杂录》,第5971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都下马料(淮浙江东沙田芦场本末)》载,绍兴二十九年五月, “福建江海之滨,亦有新出沙田。户部闻之,遽下常平司出卖。而殿院任信儒以为,此皆民间自备钱本兴修,数年之间,偿费未足,望少宽之。乃止” 。第337页。,甚至盗耕种1000亩以上或2000亩以上的绝非 “贫民” ,而是 “豪强坐据” 。⑫楼钥撰《攻媿集》卷九〇《侍御史左朝请大夫直秘阁致仕王公行状》称: “沙田、芦场议起租税,民以为病,无敢言者。公乃极论之。其略曰:‘沙涨之地,未尝耕耨,施工布种,乃是务本之民。既未能如汉置立田科以劝农,而可扰之乎?芦苇之生,本非种植,各以其力樵刈,必非游手之徒。既未能如古捐山泽之利以予民,而可困之乎?豪强坐据,虽曰非法,然怨不及上。今朝廷遣官增税,怨始有归矣。’上感悟,即令罢去,以便贫民。”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385页。这些反对治理盗耕种者,有的是以偏概全,欲因噎废食,更多的其实是在为 “形势之家” “有力之家” 代言。
过不到三年,从乾道元年(1165)起,孝宗朝廷再次在淮东、浙西、江东三路开展治理盗耕种沙田、芦场并 “起理租税” 的工作。关于其财政考虑,史文明言: “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江东淮东路沙田芦场,顷亩浩瀚,宜立租税,补助军食。’”①《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农田》,第4190页。
乾道年间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在 “官私分利” 的原则基础上,改进 “起理租税” 的具体办法。乾道元年七月,臣僚言: “浙西、江东、淮东路,沙田、芦场多系官户、形势之家请买租佃,未立税额。今朝廷军食用广,每岁和籴。乞将官民请买到沙田围垾成田,见今布种,比附平田,及芦场顷亩并令立税。其经官请佃之数,核实顷亩,别行立租。如不愿租佃者,所属拘收,申取朝廷指挥。” 孝宗下诏派高州刺史幹办、皇城司梁俊彦与杨倓、张津同共措置。②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四三《农田杂录》,第5975页。梁俊彦提出, “官民请买之田立税,请佃之田立租” 。这是要区分不同的产权归属,或征税,或收租。 “沙田折纳米,沙地及芦场并纽折见钱”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都下马料(淮浙江东沙田芦场本末)》,第337页。九月,措置浙西江东淮东路官田所奏称:
诸州县沙田,芦场有见行法起理租税,止缘官户侵耕冒佃,见占顷亩,致失常赋,及租佃人户计嘱州县从轻立租。昨虽绍兴二十八年委官措置,缘督责严速,开具不寔,所立租数,不照乡原体例一等施行,词讼不已,致有冲改。今来除已立式行下州县,开具四至,取赤契、砧基照验。如已经经界,立定二税,即依旧拘催。内沙田若围裹成田,已经成熟,即依平田立税。其官、民户有侵占宽剩顷亩,及有经官请佃之数,并合取见诣寔,照色额肥瘠,比见立税上添立租课。仍许见占田人限一月自首,如限满不首,许诸色人陈告取赏,将所告之数全给告人承佃。……官、民户请佃沙田、芦场,别立租。如不愿租佃,即行拘收,或作官庄,或召人请佃,随宜处置。④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四三《农田杂录》至四四《检田杂录》,第5975页。该方案提出对盗耕种的沙田、芦场的产权作出两种处理:一是私有化,征收二税;一是仍为系官田产,召佃收租。其中特别指出,绍兴二十八年(1158)治理时所立租数,没有依照 “乡原体例一等” 施行,即缺乏一致的征收标准。⑤按,宋代的 “乡原体例” 或称 “乡例” ,有民间和官府两种,各地并不一致。参见包伟民、傅俊:《宋代 “乡原体例” 与地方官府运作》,《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乾道二年(1166), “辅臣奏:‘俊彦所上沙田、芦场之税,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⑥《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农田》,第4190-4191页。。乾道六年(1170)二月,朝廷统一制定了分别按经营沙田、芦场所得征收租、税的比率,规定: “已业沙田所得花利,每米一石,于十分内以一分立租;已业芦场等地田主所得花利,纽钱一贯,欲十分内以一分五厘立租。租佃沙田主分得花利,每米一石,欲于十分以二分立租。租佃芦场等地田主所得花利,纽钱一贯,欲以十分之三输官。”⑦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〇之二七《赋税杂录》,第6207-6208页。这就是也适用于围田起立租税的 “省则” 。⑧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〇之二一《赋税集录》载: “乾道二年五月十一日,诏平江、湖、秀三州已开掘围田,税赋即行除访,将经界后围田今来不经开掘者,候农隙,州委噩明官分头诣逐县,打量的确顷亩,并依省则,纽立合起税色,保明申州,类聚申省部,随税起理。” 第6204页。八月,言者以为: “向来措置之初,止为有力之家侵耕冒占,而奉行之际,乃并人户租产口业,一概打量,加立新租数倍,人户有逃移者。” 孝宗下诏: “已业芦场、草地所纳赋税,并减五厘,租田与减一分。”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都下马料(淮浙江东沙田芦场本末)》,第338页。
可知乾道年间治理盗耕种沙田、芦场的方案,继续实行 “官私分利” 的原则,由中央财政与以 “形势之家” 为主的实际占有者分割利益。宋朝对已经实现私有产权转换的 “已业沙田、芦场” ,沙田按亩产量征收税率为9.5%的实物二税,芦场按所得计钱征收税率为10%的货币税;对作为系官田产被私人占有出佃的,沙田以其所得的20%交租米,芦场以其所得的30%交租钱。总之,宋朝以占有者交纳一定数额的租利,作为承认其占有权和经营权的交换条件。于此再次显示,宋朝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是把财政考虑置于首位的。
三、宋朝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与地方治理
宋朝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与地方治理的关系,就财政经济利益的博弈而言,有三个博弈方:一是中央政权,二是地方政府,三是地方豪强。就治理效果而言,由于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益分配、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豪强的利益博弈,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再结合不同博弈方的得失分别作出分析。
首先,关于治理盗耕种沙田、芦场、海田等。不同于盗耕种熟田,盗耕种此类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必须先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等生产成本,赢利往往要在数年之后。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二载,绍兴二十九年五月,高宗下诏户部停止出卖福建路的新生沙田,因为殿中侍御史任古言: “此皆民间自备本钱兴修,数年之间,偿费未足。出卖太早,其扰不细。” 第3019页。《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一《垦田杂录》载,嘉定二年(1210)正月,知湖州王炎奏: “本州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万硕。前日朝旨决其堤岸而毁之,则一岁损米三十万石。今既许其修筑,复为新田,然必亩纳一石,然后官始给据。夫先纳米后给据,此富民之利,贫民不便也。不若候其修筑毕工,种艺有收,然后亩纳一石。” 第6102页。所以,有能力盗耕种者有限,多出自 “有力之家” “官户、形势之家” 。由于博弈对象相对有限,特别是宋朝中央所采取的 “官私分利” 治理原则,比较能为盗耕种者所接受,加上宋朝中央政权出于增加中央财政收益的迫切需求,加大介入的力度,多次制定和调整有关法规、政策,除了户部主管之外,还曾先后设立提领官田所、措置浙西江东淮东路官田所作为专管机构,数次派遣朝廷命官下地方主持治理活动,因而治理比较成功。如绍兴二十八年的治理效果是: “淮东、浙西、江东三路沙田、芦场之籍,总二百八十万亩有奇。凡为沙田,则起催小麦、米、丝;沙地则起催豆、麦、丝、麻;芦场则起催柴蕟。”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都下马料(淮浙江东沙田芦场本末)》,第337页。中央财政获得不小的收益。这些收益曾经由具有皇帝内库性质的南库掌管,如乾道元年、二年共征收得 “租钱六十万七千七十余缗” ,诏 “并赴左藏南库送纳” 。③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二一七至二一八《农田杂录》,第7728页。淳熙十年(1183)八月,南库改隶属户部,移交钱物账目时, “南库例还户部沙田钱二十三万缗,又在其外” 。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财赋四·左藏南库》,第383页。此后,中央财政继续向地方财政争夺这部分收益。例如,《景定建康志》卷四一《田赋志二》载: “沙租云者,沙碛之地,民垦而业之,或以种谷,或以长芦,而县乃收其租焉。自淳祐八年,田事所差官经理,县不得有其租,而隶之总领所。”⑤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一《田赋志二》,《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98页。
当然,由于宋廷治理沙田、芦场之类的盗耕种,采取招标 “增租刬佃” 的形式,其中也存在吏治之弊。真德秀在《申户部定断池州人户争沙田事状》记录的一桩案例颇为典型,从中可以看到从提举常平司到本州主管官,从原佃人到争佃人,在 “增租刬佃” 过程中不遵守有关法令的细节。⑥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八《对越甲藁·申户部定断池州人户争沙田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120-125页。不过,这些参与争夺 “增租刬佃” 的人户都是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 “形势之家” 。总之,相对于治理盗耕种其他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宋廷治理盗耕种沙田、芦场、海田等的财政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比较良好的。
其次,关于治理盗耕种围田、湖田、圩田等。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东南地区特别是两浙的湖田、围田、圩田等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开发愈演愈烈,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盗耕种行为。按照宋朝保护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公共产权的法令,这种盗耕种行为无庸置疑是违法的。正如卫泾上书光宗所说的: “国朝成宪,应江河、山野、陂泽、湖塘、池泊与众共者,不得禁止及请佃、承买。官司常切觉察,如许请佃承买,并犯人纠劾以闻。及潴水之地,辄许人请佃、承买,并请佃、承买人各以违制论。立法之意,可谓明白。” 他接着指出,在二浙, “自绍兴末年,始因军中侵夺,濒湖水荡,工力易办,创置堤埂,号为坝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犹未至甚者,潴水之地尚多也。隆兴、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几何。而所在围田则遍满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①卫泾:《后乐集》卷一三《论围田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652页。。显然,对如此严重的盗耕种行为,宋廷并没有放任不管。
如同盗耕种沙田、芒场等一样,盗耕种湖田、围田、圩田等也必须先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作为生产成本,获利的时间也比较长,盗耕种者同样多是 “有力之家” 。不过,盗耕种围田、湖田、圩田等对于农田水利资源有着直接的影响,其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更加广泛。同时,宋代围田、湖田、圩田等的开发也有阶段性,而以南宋为盛。因此,宋朝中央在治理过程中,对中央财政利益的考虑,与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的博弈都更为复杂。
中央政府在治理盗耕种湖田、围田、圩田等自然资源土地资产时,面临着短期财政收益与长远财政收益的冲突。开发及盗耕种湖田、围田、圩田等之所以在北宋末南宋初愈演愈烈,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朝廷出于增加中央财政短期收益如皇室收入、军费、省税等的考虑,予以纵容,乃至公开支持。政和年间(1111—1118),浙东由知越州王仲主持的鉴湖湖田化和由知明州楼异主持的广德湖湖田化就是典型事件。②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一《水利上》载,绍兴三年(1133)三月二十九日,绍兴府上虞令赵不摇言: “本县所管夏盖等湖一十三处,自废湖为田,租米皆属御前,省税即隶户部。官吏知有湖田数千硕之利,而不知夺此水利,检放省税,岁乃至万硕。建炎以后,湖租尽入户部。” 吏部侍郎李光言: “自政和以来,楼异知明州、王仲薿知越州,内交权臣,专务应奉,将两郡陂湖废为田。” (第6173页)有关的研究论文,可参见宁可:《宋代的圩田》,《史学月刊》1958年第12期;梁庚尧:《南宋的农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77年;郑学檬:《宋代两浙围湖垦田之弊——读〈宋会要辑稿〉 “食货” “水利” 笔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张芳:《宋代两浙的围湖垦田》,《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寺地遵:《南宋时期浙东的盗湖问题》,《浙江学刊》1990年第5期;庄华峰:《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0卷第3辑;沈世培:《南宋江南圩田开发中政府公共职能探析》,《中国农史》2017年第2期;沈世培:《南宋江南圩田经济地位试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等。
但是,湖田、围田、圩田等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过度开发及盗耕种,也大大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和农田水利的自然系统,危害农业经济,在旱涝之年表现尤其显著,从而损害南宋长期的国家财政利益。对此,时人多有揭示。例如,宣和三年(1119)二月,徽宗诏称: “越州鉴湖、明州广德湖自措置为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陷常赋。又请佃人多是亲旧权势之家,广占顷亩,公肆请求,两州被害民户,例多流徙。”③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三至三四《农田杂录》,第5965页。光宗时,卫泾上书批驳 “围田既广,则增租亦多,其于邦计不为无补” 之论,指出: “殊不思缘江并湖民间良田何啻数千百顷,皆异时之无水旱者。围田一兴,修筑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顿至隔绝,稍觉旱干,则占据上流独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视无从取水。逮至水溢,则顺流疏决,复以民田为壑设。若围田侥幸一稔,增租所入有几?而常岁倍收之田,少有水旱,反为荒土。常赋所损,可胜计哉!”④卫泾:《后乐集》卷一三《论围田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652页。他们所说的对国家财政长远利益的损害,包括废湖为田减少了原有耕种面积,降低了亩产量,从而损害了普通纳税农户人的税负能力,甚至引起民户流移,加上因灾减免赋税,结果损失了 “常赋” 。对于其中的得失,时人也有了比较详细的计算。例如,李心传在《旧闻证误》指出: “明、越州鉴湖、夏盖、白马、竹溪、广德等十三湖,自唐长庆中创立,湖水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涝则递相输放,其利甚溥。自宣、政间楼异守明,王仲薿守越,皆内交权臣,专事应奉,于是悉废二郡陂湖以为田。其租悉属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诏鉴湖田租以备缮修原庙之需,不许他司奏请。他皆类此。由是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税,不可胜计。绍兴元年,李庄简为吏部侍郎,奏请复之。上虞令赵不摇奉诏考究,自宣和元年至今,湖田凡得米三万三千余斛入御前,而纳(减?)放者,省税米十四万六千余斛,得不偿失。”①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三 “王仲薿” 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44页。绍兴九年(1139)五月,权发遣明州周纲言:广德湖 “自政和八年守臣楼异请废为田,召人请佃得租米一万九千余石。至绍兴七年,守臣仇悆又乞令见种之人不输田主,径纳官租,增为四万五千余石。臣尝询之老农,以谓湖未废时,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计七乡之田不下二千顷,所失谷无虑五六十万石”②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一〇《水利杂录》,第7519页。按,史籍关于绍兴年间地方官员对明州、越州废湖为田得不偿失的计算有不同的数字,当是所计算的地域范围大小不同。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一《水利》记载,绍兴三年三月,绍兴府上虞令赵不摇言: “本县所管夏盖湖等一十三处,自废湖为田,租米皆属御前,省税即隶户部。官吏知有湖田数千硕之利,而不知夺此水利,检放省税岁乃至万硕。” 五月,知绍兴府张守言: “被旨令相度上虞、余姚两县湖田复废为湖,经久利害以闻。守契勘民户所纳苗米,较两年号为丰熟,但秋夏雨水稍不应时,其减放之数,以湖田所收补折外,官中已暗失米计四千二百余硕,民间所失当复为数倍。” (第6173页)施宿等撰《会稽志》卷一〇《水·上虞县·夏盖湖》称: “绍兴二年,上虞县令赵不摇言:‘县所管夏盖湖等一十三处为田不便。’吏部侍郎李光奏:‘一方利害,无甚于湖田。乞比较兴湖为田以来,所失常赋孰多孰少,自政和以来以湖为田者,乞复为湖。’得旨:‘张守真经久利害以闻,限三日。’知越州张守言:‘上虞县夏盖湖改为田者一百三十一顷二十四亩,余姚县汝仇湖等湖一十三所改为田八十一顷四十九亩,二年内暗失米四千二百三十六石八斗有零,民间所失当复数倍。乞复废为湖,自此两县可望全熟,委是经久,有害无利。’奉圣旨:‘依。仍自三年正月为始。” (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891-6892页)徐光启撰《农政全书》卷一六《水利·浙江水利》载:绍兴初,傅嵩卿知越州时,陈橐上《夏盖河议》称:夏盖湖 “涸之为田” 之后, “计司常赋亏失尤多,虽尽得湖田租课,十不补其三四。又况每遇旱岁,湖田亦随例申诉,官中检放,与民田等。昨见上虞丞言:‘曾蒙上司差委,相度湖田利害,因点对靖康元年建炎元年,湖田租课,除检放外,两年共纳五千四百余石,而民田缘失陂湖之利,无处不旱,两年计检放秋米二万二千五百余石。’只上虞一县如此,以此论之,其得其失岂不较然,民间所损,又可见矣” 。(参见石汉声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一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88页)。
总之,南宋治理盗耕种以两浙地区为主的围田、圩田、湖田、河田等自然资源土地资产时的政策摇摆和成效好坏,中央财政的短期利益和长远的财政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治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焦点是争夺盗耕种围田、湖田、圩田等的租税。宋人指出,宋朝中央在未作治理之前,不少地方政府以 “起立租税” 为条件,纵容当地盗耕种围田、湖田、圩田等,将所征租税作为本级财政的额外收入,自行加以支用。例如,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知湖州李光言: “自壬子岁入朝,首论明、越间废湖为田之害。蒙独罢余姚、上虞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其类甚多,州县官往往利为圭田,顽猾之民因而献计,侵耕盗种,上下相蒙,未肯尽行废罢。”③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三《水利上》,第6138页。此前他已指出,余姚、上虞两邑县收入的湖田租课有 “数千斛”④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一《水利下》,第6147页。。光宗时,卫泾上书指出,围田 “所谓增租,既不系省额,州县得以移用,徒资贪黩之吏耳!”⑤卫泾:《后乐集》卷十三《论围田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652页。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对有些地方退田为湖的决断就比较明快。如上述绍兴二年宋廷对上虞县夏盖湖、余姚县汝仇湖等地退田为湖的决策。而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地方财政的既得利益,则想方设法加以拖延。史载,绍兴五年,李光上奏建议治理 “明、越间废湖为田之害” 时,还建议: “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 于是高宗 “诏诸路漕臣议之。其后议者虽称合废,竟仍其旧” 。⑥《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一·农田》,第4183页。同样的,如果治理会损害中央财政的直接收益,宋廷也会拖延不决。如钦宗靖康元年(1126)三月,臣僚言: “东南地濒江海,旧有陂湖蓄水,以备旱岁。近年以来,尽废为田。涝则水为之增益,旱则无灌溉之利,而湖之为田亦旱矣。民既承佃,无复可脱,租税悉归御前,而漕司暗亏常赋,多致数百万斛,而民之失业者众矣。乞尽罢东南废湖为田者,复以为湖。” 诏: “令逐路转运、常平司计度以闻。”①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〇《水利上》,第6136页。显然,此时退田为湖,必然损害 “悉归御前” 的租税收益,结果朝廷不了了之。再如,绍兴九年(1139)五月,权发遣明州周纲上奏朝廷,要求废除广德湖的湖田,退还租税, “依旧为湖” 。虽然高宗 “诏依,令转运司疾速措置申尚书省” 。可是,绍兴十三年(1143),明州以 “广德湖下等田亩,缘既已为田,即无复可为湖之理,不免私自冒种,非唯每年暗失官租三十余石,而元佃人户词讼,终无由止息。又因缘有争占斗讼,愈见生事。欲乞依旧为田,令原佃人户耕种。” 高宗即加以批准。②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一〇《水利杂录》,第7519页。可见周纲的建议在数年间一直没有被付诸实行。这是因为广德湖的租课收入属于中央财政收益。③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提点司》载:建炎三年(1129)正月十一日,吏部尚书吕顾浩等言: “越州鉴湖、湖州广德湖、润州练湖所收租课,依靖康元年五月五日指挥,发运翁彦国拘收,专充籴转般代发斛豆斗本钱,皆系常平司所管田产。始者取充应奉,次取充漕计,见取充发运司籴本。伏望追还常平司桩管,以待朝廷缓急移用。” 第4120页。
中央政府出于社会经济影响的考虑,对盗耕种围田、湖田、圩田等的地方豪强,曾采取比较强硬的治理措施。如绍兴十五年(1145)二月,王鈇上报朝廷,称措置两浙经界的内容之一是: “人户将天荒产段并淹泊之类,修治埂道,围裹成田,自系额外产土,欲令逐州知、通令作一项保明,供申朝廷量行起税。”④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四三《经界》,第6108页。这显然也适用于治理围田、湖田、圩田等的盗耕种。
不过,受时局、中央财政状况、地方吏治等的影响,南宋治理盗耕种围田、湖田、圩田等的效果,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如宁宗时盗耕种的治理就缺乏成效。⑤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四六《水利四》载,嘉泰三年七月,臣僚言: “乃者朝廷分遣使者,将奏册曾经有籍开掘之田,许人户入米,仍旧围里,已降指挥,不许稍有过数。窃闻豪民臣室,并缘为奸,广行围里,殆且加倍。又连年亢旱,江湖之滨,涂状旋生,嘱托胥吏,伪造干照,或就悬起立税租,纳钱请佃,多围成田。又所在水荡,自来止是栽种茭芦菱荷之属,不妨潴水。今亦凭籍再围指挥,影射包占,不顾众户灌溉之利。” (第7545页)食货六一之一四八载:嘉定七年(1214)七月,臣僚言: “嘉泰以来,权奸用事,私欲横生。其微至於西湖草塘,亦复徇情,听民请佃,日渐月积,种荷之地寝广,而湖面之水愈狭。” (第7546页)食货六一之一四九至一五〇载:嘉定十五年(1222)四月,臣僚言: “越之鉴湖,受溉之田几半会稽。往者累任帅臣时加浚治,故民被其利。今官豪侵占殆尽,填淤益狭,所余仅一衣带水耳。兴化之木兰陂,始为富人捐金,兴筑民田万顷,岁饮其泽。今酾水之道,多为巨室占塞。” 第7547页。所以不能笼统言之。
最后,关于治理天荒田的盗耕种。前已指出,宋朝从一开始就立法把天荒田这类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列为 “系官田产” ,治理法规与政策都比较明确,成为地方治理的常规内容之一。但是,治理能否取得效果,则须视地方政府官员的作为而定。宋朝治理盗耕种天荒田的主要内容也包括 “诡名挟佃” 和包占,和治理盗耕种私有田产的 “诡名挟佃” 和包占一样,从总体上看是失败的。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宋朝以赋税征收为主的农村地方治理,依靠的是地方州县的 “公吏” 以及主要由形势之家把持的乡司。州县公吏与乡司之间的相互利益输送,使得南宋中央的赋税治理难有成效。⑥王棣:《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宋朝治理荒田的盗耕种从总体上看之所以成效极其为限,主要也是州县公吏与乡司之间的相互利益输送所致。
四、余论
关于宋朝是否实行 “田制不立” 及 “不抑兼并” 的政策,近年来学术界有所争论。其中,杨际平先生认为,古今人所说宋朝 “田制不立” 的 “田制” ,其含义之一是指各种土地政策、土地法规;这种意义的 “田制” ,从两汉至宋代都有。①参见杨际平:《宋代 “田制不立” “不议兼并” 说驳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薛政超:《也谈宋代的 “田制不立” 与 “不议兼并” ——与〈宋代 “田制不立” “不议兼并” 说驳议〉一文商榷》,《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杨际平:《宋代 “田制不立” “不议兼并” 说再商榷——兼答薛政超同志》,《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杨际平:《论北朝隋唐的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李华瑞先生认为: “在经济活动中,土地兼并主要是指土地所有权(产权)的转移” , “宋朝对于土地兼并(买卖、交易)是不加抑制的,而对于既成事实的土地占有也不能‘制限’” , “对于土地兼并活动宋朝不加抑制,但是对兼并活动之后不断生长的兼并势力对国家赋役造成的危害则有清醒的认识” ,并且采取 “无所不在的抑兼并” 措施。②李华瑞:《宋代的土地政策与抑制 “兼并” 》,《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他们的这些见解颇值得重视。
如果从土地政策、土地法规和土地产权的角度加以审视,如同本文所考察的,宋朝进一步扩大了唐朝以来国家对自然资源土地资产行使的普遍管辖权和优先处理权,直至把 “天荒田、江涨沙田、弃堤退滩、濒江河湖海自生芦草荻场” 等都划归 “系官田产” ,明确地赋予官有产权;同时宋朝继承发展唐朝的《盗耕种法》,制定了《盗种法》《盗耕退复田法》《盗决侵耕之法》等专项法律,并用敕、格、令等法律形式加以补充,作为治理耕盗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的法律依据,其中包含着干预土地产权转移、抑制兼并势力、维护国家赋税收益等多种考虑。其实,不止是对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宋朝对私田也同样制定了产权保护制度,实施《盗耕种法》,并制定包括对私有逃田产权处置的有关政策,作为与《盗耕种法》并行的经济法,其中同样包含着干预土地产权转移、抑制兼并势力、维护国家赋税收益的意图。③关于宋朝处理盗耕种私田与土地产权、财政考虑和地方治理的关系问题,我们拟另文论述。
总之,《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称: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而又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 这一概括失之笼统。我们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和阐释所谓宋朝 “田制不立” “不抑兼并” 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