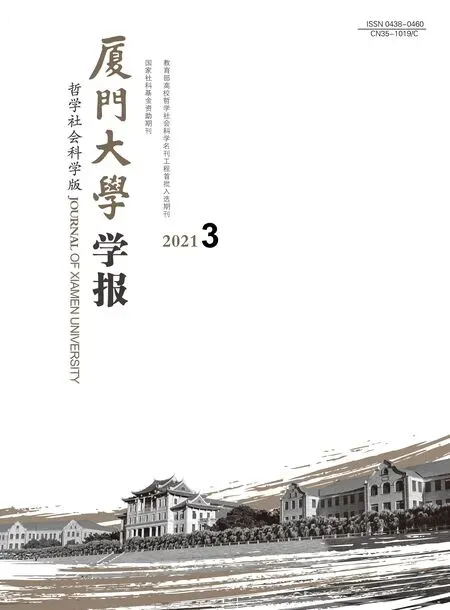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的 “新法接生”
——记录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开端
2021-04-17何秀雯
王 宇,何秀雯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361005)
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往往以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社会运动为落笔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等在文学中均获得充分表现,有关这类记录大历史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也相当充分。相对而言,50年代的 “新法接生” 运动显然就是小历史。所谓 “新法接生” ,指现代妇产科学的接生方法,要求接生人员遵循临产规律,做好清洁消毒工作与产前、产后的检查护理,防止新生儿破伤风和妇女 “产褥热” ,切实地保障妇婴的身体健康。以此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数量其实不少,且体裁多样、类型丰富,包括小说、剧作、木刻、年画等①以 “新法接生” 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主要包括茹志鹃《静静的产院里》(《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徐怀中《卖酒女》(《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马烽《两个收生婆》(《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6期)、谷峪《接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化石《山村接生员》(《红岩》1954年第3期)、严动《助产士小陈》(湖北文艺编辑部辑:《一样土色,两样庄稼》,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刘任涛《生命摇篮》(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管桦《在妇产院里》(《文艺红旗》1959年第7期)、李逸民《一个婴儿的诞生》(《火花》1960年第3期)等小说,曾克《第十四个儿子》(《新中国妇女》1953年第12期)、姜吉德《老接生员》(《山花》1959年第11期)、且宁《模范接生员常秀花》(《新中国妇女》1953年第6期)、李龙添《有青生娃娃》(《新观察》1953年第5期)、赵燕高《苏奶奶——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回族新法接生员苏金英》(《朔方》1963年第5期)等报告文学,白瑶等集体创作的歌剧《接生》(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舒慧的独幕话剧《山沟里的接生员》(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孙芋的独幕话剧《妇女代表》(《剧本》1953年第3期)、季康和公浦编剧导演的电影《摩雅傣》(《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等剧作,以及布和朝鲁的木刻《接生员同志到了》(《美术杂志》1958年第3期)、周霖的年画《接生员》(《美术杂志》1963年第6期),等等。,但常常被当时和后来的研究者所忽略①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 “新法接生” 并未引起研究者关注,仅是一些学者对茹志鹃小说《静静的产院里》展开研究,如侯金镜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茅盾的《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冰心的《 “一定要站在前面” ——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里〉》、孙民乐的《十七年文学中的 “百合花” 》、马兵的《从 “医院” 到 “产院” ——大跃进时期现代性问题的一个个案考察》等文章,大多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创作个性、艺术风格、现代化发展等角度探究该文本的叙事建构。很少有学者从生育、生命权力、 “新法接生” 等小历史视角介入研究。刘传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卫生改革运动中的政治与性别——重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一文,从生育改革运动的视角重读《静静的产院》,探究了生育改革运动的政治意义及其对妇女的影响,但并未脱离 “大历史” 式的研究范式,也未曾注意到生育改革运动对生命观念、家庭伦理关系、生命权力的重要意义。显然,从 “大历史” 视角考察50年代文学已成为文学研究的常态。。实际上这些或许名不见经传的文本有着丰富的文学人类学意义:它们记录了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开端。 “生命治理” 是福柯探究现代权力的运作模式时提出的概念,它是用一种不同于 “肉体” 规训权力的生命权力来调节人口的生命活动,让生命在更为安全、更为健康、更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②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必须保卫社会》等著述中探究了两种权力机制,即封建权力的 “使人死,让人活” 和现代权力的 “使人活,让人死” 。前者强调君主对生杀予夺大权的掌握,他们通过掌控死亡治理国家,治理方式更为直接、暴力;后者绝非简单的生死权力倒置,而是权力的深层发展,国家通过对 “生” 的掌控实现对生命体的控制与管理。现代权力主要有两种运作形式: “肉体的规训” 和 “人口的调整” 。规训权力通过监视、约束、惩戒人的肉体和行动而运转;生命权力则是以 “物种的肉体” 及其生命过程(如生育、健康水平、寿命等问题)为载体,让生命在更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甘心成为权力的治理对象。福柯的生命政治探究的就是政治权力同人的生物性存在之间的二元关系。参见刘冰菁:《福柯的 “生命政治” 概念的诞生》,《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2期。“新法接生” 是新中国生命治理的重要措施,它不仅是一场现代化医疗卫生技术的改革运动,更是一项极具启蒙与解放意味的革命运动,是 “中国农村妇女接触到新政府的最早事件之一”③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8页。,它打破了传统乡土中国的生育习俗以及相关的种种神秘想象,重塑了传统的生命观念,掀起了一场身体与生命领域的现代性运动。透过 “新法接生” 这个 “小历史” ,我们既可以重新审视50年代文学文本在记录民族身体、生命史方面的特殊意义,还可以以点窥面,审视民族国家生命治理的发展历程,观照 “大历史” 式的文学研究视域未曾关注过的生命文化史景观。这些文本呈现出民族国家对生命权力、生育习俗、家庭伦理关系、妇女身体的改造,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再造。50年代文学中的 “新法接生” 不仅记录了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开端,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职业女性——产婆/接生员形象序列,在中国职业女性形象史留下特别的印记。
一、文学文本生产的相关知识背景
20世纪50年代的 “新法接生” 运动主要是通过 “改造旧产婆” 与 “培养新式接生员” 来完成的。在这场生命治理运动中,旧产婆并未被完全抛弃,而是成为被改造、争取的对象。这种选择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新中国初期妇婴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需要借助旧产婆的力量;二是旧产婆在传统生育文化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她们直接管理着个体生命的诞生,是国家生命治理工作展开首先要面对的对象。
产婆(又叫接生婆、收生婆、稳婆、隐婆)一职起于东汉,兴于唐宋,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一个以接生为主、兼具多种职能的行当,在民间妇女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④明清时期,产婆既负责民间接生,也为官府服役,承担的职能如辨别入选宫廷的女子容貌和贞洁、奶娘乳汁厚薄,协助衙门为女性验身、验伤等。参见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年,第35页;凌濛初:《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37页。“收生有年,五更半夜,不得安眠。手高惯走深宅院,几辈流传。看脉知时辰近远,安胎保母子完全。搧镘的心不善,刚才则分娩,先指望洗三钱。”⑤陈铎著、杨权长点校:《陈铎散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在前现代中国,产婆不仅要帮助孕妇分娩,同时也是仪式化生育活动的执行者,她们通过 “洗三” “弥月礼” “掰百岁” 等仪式使新生儿在家庭、社会中获得合法位置, “为整个家庭营造出祥和与安全的气氛”①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7页。。因此,人们看重产婆的不仅仅是其接生功能,更是她们所承担的 “仪式化生命督导者” 职能。但时人也看到产婆收生时的诸多弊端: “一近产妇,有多少做作。揉之夺之,使之努力。不知时候未至,用力罔然,且有逆生横产之祸。又有故为哼讶之声,或轻事重报,以显己能,以图酬谢。因致产妇惊疑,害尤非小。”②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第512页。产婆往往贪图钱财、看重名利,缺乏系统的产科理论知识,收生时常常故弄玄虚,危害着产妇和婴儿的生命。随着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产婆的接生方法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与抵制,她们也成为被规范、改造,甚至取缔的对象,代之而起的是一批科学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接生从业者。
19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通过开办医院、培训产科医生、译介书籍等将先进的妇婴卫生知识传入中国,力求改变传统的接生方法。尽管传教士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与政治目的,却也客观上推进了中国妇婴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民国以后,逐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生命治理模式,通过调整与人口关联的诸种因素,从而实现 “使人活” 的现代生命权力治理。接生方法的改革是现代中国生命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民族国家逐步展开改造与重塑接生婆的工作,力求改革传统的生育观念、生育制度与生育习俗,保护妇婴的生命安全,从而实现 “强种” 目的。1913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颁布了《京师警察厅暂行取缔产婆规则》,强制性取缔未经许可、非法接生的 “老婆娘” ,同时也严格规范产婆的接生行为,提出了 “十不为”③“十不为” 指的是:不得不应招请;不得索要重资;不得打胎;不得危害产妇及生儿;不得掉换、买卖男女婴孩;有难产时须令本家请求医生,不得以非法下胎;不得妄用神方及其他俗方与产妇及生儿服食;不得于产妇及生儿妄施针灸;产畸形怪状时须呈报官厅,不得妄为处置;不得宣布产妇秘密阴私及挟持需索。参见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2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69-70页。,更加关注产婆临床接生、助产的职能,并赋予她们新的社会职责:产婆要将其接产婴儿的 “地址、门牌、户主、姓名、男女、出生月日及有无死亡等项详细列表报由该管警察署,月终汇总呈报本厅”④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26册,第70页。。1928年8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管理接生婆规则》⑤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内政公报:《管理接生婆规则》,《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28年第5期,对已有的接生婆登记造册,并为其营业规范作出具体规定,将个体生命的诞生、管理纳入国家医疗卫生行政体系,让生命统计学取代传统的生命接纳仪式。尽管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推广新接生法,但传统的接生方法依然活跃,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产婆仍遵循旧法进行接生,危害着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健康, “仅凭粗略的估计,我国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产妇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五”⑥程之范:《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
新中国成立前期,毛泽东在驳斥马尔萨斯的 “人口决定论” 观点时指出, “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⑦毛泽东:《六评白皮书——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人民日报》1949年9月17日第1版。。 “人多是好事” 的政治观念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育政策。同时,为了恢复战后生产经济活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尤为重视人口的生产性功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人口增长的生命治理政策。20世纪50年代的 “新法接生” 运动既满足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人口要求,也契合普通民众(尤其是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 “人财两旺,小孩子不死,大人不病”⑧敬桓:《谈广大农村妇婴保健工作问题》,《人民日报》1949年7月5日第4版。的生命诉求。
早在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就大力提倡新接生法,积极向边区妇女普及生育科学知识,并通过短期培训班改造旧产婆、培养新式接生员,郭钧的木刻《宣传新法接生》①郭钧:《宣传新法接生》,古元、李树声主编:《延安文艺丛书 美术卷》第12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形象地呈现了 “新法接生” 在边区的宣传与推广。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第1版。。1950年8月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新中国妇婴卫生工作的重点是 “培养乡村卫生员与改造旧产婆,其中改造旧产婆工作尤其重要。不首先做到这一点,农村中最迫切为害重大的婴儿死亡问题就无从解决”③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医杂志》1951年第1期。。8月20—23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 “改造旧式接生婆,推行新法接生,减低脐带风、产褥热的死亡” 的基本任务④《中央卫生部举行座谈会讨论进一步展开妇幼卫生工作》,《新华社新闻稿》1950年第107-136期合集,第250页。,全国各级卫生部门也纷纷召开座谈会,颁布执行各种改造旧产婆的行政法规,为 “新法接生” 的推广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人民日报》《新中国妇女》《妇婴卫生》等报纸杂志也刊载了许多 “改造旧产婆” “培养新式接生员” 的文章,着重批判旧产婆的封建落后、愚昧无知,探讨旧接生法的危害,并积极倡导推行 “新法接生” 。 “新法接生” 运动不仅使接生方法走向科学化、卫生化与规范化,同时也催生出一个基层社会特殊的职业妇女群体——接生员,她们不仅掌握着科学的接生方法,保障了妇婴的生命安全,更是凭借这一职业技能成为国家生命治理的具体执行人。于是,20世纪50年代以 “新法接生” 为题的文学文本专注构建这一职业妇女群象,揭示了其现代身份的形成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总之,20世纪50年代的 “新法接生” 运动延续着现代民族国家生命治理历程的内在逻辑,揭开了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序幕,国家凭借这场接生改革运动介入到个体生命的诞生与发展,使国家力量直接作用于生命个体,将私人化的生育事件纳入国家公共医疗卫生的行政体系。正是在生命政治的层面上, “新法接生” 运动成为一项极具现代性意义的生命活动,文学文本全面、立体地记录了这一活动的发展历程。
二、产婆/接生员形象与生命观念的变迁
在以 “新法接生” 为题的文学文本中,作家们形塑了一个以接生为业的特殊的活跃于基层社会的职业女性形象序列——产婆、接生员,并通过对比产婆与接生员形象、新旧接生方法的优劣呈现了民族国家生命权力在乡村的再分配,及其对传统生命观念的整合与改造。
产婆一职在前现代中国妇女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 “男女授受不亲” 的礼教约束下,她们凭借性别优势为产妇接生,掌控着民间社会生命诞生的奥秘。然而,其接生方法却是前现代神学信仰下简单、粗暴的经验性接生法, “坐婆疏率,不候时至,便令试水;试水频并,胞浆先破,风飒产门,产道干涩;及其儿转,便令坐草,坐草太早,儿转亦难,致令难产”⑤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之十七,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262-263页。。因此在现代医疗话语体系中,旧产婆的接生方法被界定为一种技艺而非医疗技术,缺乏科学的理论知识和卫生观念。在歌剧《接生》中,旧产婆徐大娘 “求神求鬼” “开屉开柜开生门” “搥、打、砸、蹲” “裤带勒” “扁担压” “秤钩子钩” 等方法继承了传统接生技艺的 “精髓” ,给产妇王大嫂造成极大伤害。她还积极宣扬女性 “养孩子就是命中注定要遭罪的” 这一悲剧宿命论,极度地轻视产妇分娩时的身体感受,把控着女性怀孕、分娩、坐月等生命活动。而以助产士白同志为代表的 “新法接生” 则试图打破这种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念,强调对妇女身体健康与生命体验的关注,树立起尊重生命、崇尚科学的现代生命观念。白同志不仅解决了旧产婆无法处理的 “横生倒养” ,还用科学知识解释了 “摔土坯” “开生门” “立撞客”①“摔土坯” :旧产婆通过摔土坯来预测新生儿的性别,摔出的土块是齐碴就是男孩,斜碴则是女孩; “开生门” :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旧产婆为产妇接生时,要打开产房中所有门,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产妇打开产门,顺利生产; “送撞客” :旧产婆认为产妇因冲撞了 “鬼” “神” 而难产,即 “撞客” ,因此要烧香、焚化纸钱来 “送撞客” 。等乡村社会围绕生育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迷信活动,颠覆了传统的生命信仰机制,完成了一个由身体到思想的全新再造。同时,她也着重强调了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求神,求鬼,神鬼多咱救过咱们?只有人民政府,只有共产党才能帮助咱们呀!” 如此,国家不仅成为先进科学知识的传播者,更逐步地掌控着乡村社会的生育活动, “将妇女的生育行为从地方关系网络和制度中移除,并使其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重新建构” 。②Joshua Goldstein, “Scissors,Surveys,And Psycho-Prophylastics:Prenatal Healthcare Campaigns A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1949-1954”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Vol.11,No 2,June 1998,p.154.《接生》将这场接生技术的改革运动同民族国家基层权力的建构相关联,以旧产婆和助产士的博弈来呈现国家对乡村生命权力的挪移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生命权力的挪移并非一蹴而就,当徐大娘提出要学习 “新法接生” 时,得到白同志认可: “新旧在一块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上了年纪的人经验多,再懂得些新法子就好办了。”③白瑶、孙序、赵世匡等集体创作,于大波、李洗作曲:《接生》,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5页。
在新中国生命治理的框架中,旧产婆不仅在技术层面上习得科学接生方法、提高接产技能,也改变了其原有的身份认同,从 “仪式化的生命督导者” 转变为技术化的接生员。在传统社会中,产婆的 “社会功能大于医疗功能” ,人们关注的重心不是其接生水平的高低,而是她们作为 “仪式化生命督导者” 的权威性。老舍小说《正红旗下》中老白姥姥之所以备受敬重不仅因其娴熟的接生手法,更缘于她是民间生命接纳仪式 “洗三”④“洗三” 既是一种婴儿的养护方法,又是非常重要的生命接纳仪式,婴儿出生三日后,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并为之祈福。参见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儿科分册,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95页。的主持人,经她手 “洗三” 的新生儿不仅获得了美好祝福,还可以彻底地融入到家庭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的认可。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 “新法接生” 运动中,旧产婆原本承担的 “文化功能早已变得无关紧要而被搁置”⑤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17页。,人们越来越重视的是其作为接生从业者的医疗功能——如何运用科学的接生方法为产妇接生,她们逐渐地被改造为技术化的接生员、国家生命治理的具体执行人。这一身份认证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基层女性现代身份的建构——一如同时期的许多妇女解放叙事那样,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新中国以现代医疗技术为手段主动地介入到最具传统性的个体生命活动中,并在文化层面上重塑了传统生命观念,破解了仪式化生育的奥秘,颠覆了民间生命诞生的信仰体系,使传统的价值观念全面萎缩, “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⑥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7年,第15页。,这无疑是一个现代性袪魅过程。技术化的接生员成为新中国管理生命的重要媒介,《生命摇篮》中的杨慧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主持乡村传统生命仪式 “掰百岁”⑦“掰百岁” 是指在孩子百日宴这一天,家人将一面项圈套在孩子脖子上,让参加宴会的人依次上前掰馍馍并送上祝福,人们相信这种让孩子与世间诸相、人等发生关联的仪式能够让孩子无灾无难、健康成长。参见李洁:《 “人” 的再生产——清末民初诞生礼俗的仪式结构与社会意涵》,《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的资格,她凭借 “新法接生” 获得了乡村伦理与历史理性的双重认可:既是新生儿的干妈,又成为乡村新生命诞生的督导者。与旧产婆 “凭借其娴熟的辞令和仪态成为新生儿步入家庭场所的仪式督导者”⑧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193页。不同,她背后运行的是民族国家生命治理的价值理性诉求,呈现了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崇尚科学、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念。此外,老汪签发的 “准生证” 、杨慧兰管理的产妇登记表等现代人口统计方法也将新生儿的诞生从民间传统生命仪式规范中彻底抽离,并纳入到新中国生命治理的总体规划中。①如第一章所述,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将人口作为一个数字化、档案化的对象进行管理,也体现了其遵循现代生命治理的发展逻辑,以生命统计学代替传统的生命接纳仪式。但从管理范围和实施效果来看,新中国建立了更为完善、系统的医疗卫生行政体系(尤其在乡村),全面、彻底地实现了对生命的治理。
“新法接生” 文学文本中产婆/接生员形象序列的建构不仅揭示了民族国家生命治理发展循序渐进的历程,也呈现了中国生育卫生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茹志鹃《静静的产院里》的潘奶奶、谭婶婶、荷妹三代接生从业者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乡村生育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妇女走出家门获得解放的过程。 “新法接生” 让默默无闻的普通妇女谭婶婶成长为乡村新一代的生命治理者—— “接生员” , “大家见了她,也好像带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敬意” 。②茹志鹃:《静静的产院里》,《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谭婶婶在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中地位的上升,意味着现代医疗卫生技术及其背后强大的民族国家力量在传统人情社会关系网中的成功渗透。因此,人们对接生员谭婶婶的信任就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信任,就是对新中国生命治理的拥护。产科医生荷妹则是在接生员谭婶婶 “新法接生” 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凭借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工具进一步完善乡村现代化生命治理空间的建设。她大刀阔斧地改造产院,佩戴护士帽、带领孕妇做体操、修建自来水管、实施难产手术等一系列改革如同一阵风般, “把一切都搅乱了” ,但也把一切引到 “好了还要好” 的现代化变革道路上,彻底地改变了乡村传统的生育观念与文化习俗。这三代接生者形象不仅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 “新法接生” 运动的发展阶梯式进程,更以三代女性人物的成长历程显现了民族国家对乡村生命权力、日常生活风貌与习俗的逐级改造。
由此可见,有关 “新法接生” 的文学叙述,不仅提供了产婆/接生员这样一个基层社会特殊的职业妇女形象序列,也记录了新中国乡村生命权力再分配与生命观念重塑的进程。这项生命治理措施不仅直接改善了产妇的生产环境,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更是让传统的 “生命仪式督导者” 旧产婆转变为技术化、现代化的模范接生员。以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生命观念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改写了中国的生命史。
三、母体与国族
我们还可以联系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对女性生育职能的论述来更进一步展开本文的论题。在晚清救亡图存的背景下, “保国强种” “卫生强种” “卫生救国” 成为重要社会思潮,女性因其生育职能被推向政治舞台,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③金天翮:《女界钟》,陈雁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页。。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建构的理想女性镜像是 “国民之母” ,女性的角色功能从为家族绵延子嗣提升至为国族 “传种改良” ,女性身体健康也成为定义 “国民之母” 的重要指标,废缠足、兴女学等社会运动皆围绕培养身心健康的 “国民之母” 而展开。 “由于健康母体产生健康婴儿,健康婴儿代表未来强大种族的逻辑,母性的保护作为一项国家与社会的事业被提了出来。”④赵婧:《母性话语与分娩医疗化: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4期。母体康健与否超越了现代妇产科的医学范畴,与种族兴旺、国富民强等目标联系在一起,成为关系现代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然而,无论是正统中国文化还是民间社会生活中,妇女怀孕的身体、分娩过程、生理体液等往往与污秽、禁忌等观念相联系,被建构为一种能带来危险、引发祸乱、打破秩序的 “不吉” 象征系统。因此,分娩中的母体、触碰到产血的接生婆、未经清洗的婴儿都是要被 “秩序” “正统” 区隔的所在。①英国学者道格拉斯提出污秽即是无序、混乱的生命状态,其危险力量会沾染到一切接触者,因此要将之区隔起来。参见道格拉斯著,黄剑波、柳博赟、卢忱译:《洁净与危险》,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43页。如巴金《家》中为避免给家族带来 “血光之灾” ,即将分娩的瑞珏被驱赶离家,在一个偏远的阴暗潮湿的房子等待生产。女性分娩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秩序,其本身的角色与地位也发生改变,传统家庭社群对这种变化产生恐惧,认为它会引起纷争、招致灾祸,因此生产后的女性需经过宗教仪式的 “净化” 才能重新回归家庭。②Emily M.Ahern,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Studies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Margery Wolf&Roxane Witk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95-196.显然只有彻底地改变这种旧习俗,颠覆传统的母体污秽观,才能有效地改善女性的生命健康状况,使之更好地履行生育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战后经济恢复、社会发展对人口的需求,女性的生育功能被再次凸显,新中国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延续了晚清以来 “国民之母” 的建构逻辑,高度重视母体的生命健康同国族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 “新法接生” 运动不仅保障了妇婴的生命安全,更彻底地改变了 “生孩子是最下贱的事” “血房不吉” “下半身的话是丑事” 等传统生育观念,打破了诸多文化旧俗,并在国族话语中完成了对女性身体观念的再造。而文学话语显然参与了这一过程。《老接生员》中的接生员罗满妹跨过布依族用来 “忌月子” 的 “木标”③按照布依族的规矩,妇女分娩时,丈夫要在家门上钉上木标,任何人都不得进入产房, “木标” 相当于一种区隔的符号。,进入产房,为三妹接生;《有青生娃娃》中的阿婆不再迷信 “分娩不吉” 的预言,准许陌生人在自己家中生产。原本私密化、污秽化的母体在 “新法接生” 建构的科学话语中成为可触碰、可治理的对象,分娩也由 “最下贱的事情” 变成国家大事,这种身体观念现代转型的完成正是源自前面我们反复讨论的民族国家生命治理的逻辑。从晚清 “国民之母” 的提倡,到20世纪50年代的 “新法接生” 运动,文化逻辑一脉相连,国族话语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女性生育活动公共化、社会化。 “母亲” 已然成了民族国家相当认可的女性的重要角色身份。
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的 “新法接生” 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母体污秽观,也再造了女性分娩的身体经验。早在明清时期的世情小说中,作家就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妇女妊娠、分娩时的生命状况与身体感受。如《金瓶梅》就详细记叙了潘金莲怀孕时无力、困倦、厌食等反应, “眉黛低垂,腰肢宽大,终日恹恹思睡,茶饭懒咽”④兰陵笑笑生著,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重校本(2)》,香港:梦梅馆,1993年,第355页。。李瓶儿分娩时,作者借介绍产婆蔡老娘的滑稽小曲再现了古代妇女生产时的慌乱场景: “横生就用刀割,难产须将拳揣,不管脐带胞衣,着忙用手撕坏。”⑤兰陵笑笑生著,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重校本(4)》,香港:梦梅馆,1993年,第1185页。而一些现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则是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将产妇身体建构为极具文化批判意味的象征性意象,如白朗、萧红、张爱玲、苏青等人在作品中细致地刻画了一幕幕血淋淋的生育场景,记录了女性早孕、分娩、丧子等最原始的生命苦难,表现出现代女性对生育的怀疑与拒绝,以及女性个体发展同家族血脉延续、国族命运之间的抵牾。与以上两种类型的身体表述不同,在 “新法接生” 文本中,国族话语左右着女性对自身生育的态度和感受,国家的生命意志不断地规范个人的生育行为,女性复杂的、个性化的生育经验也被整合成规范化的民族国家身体记忆。作家们在国家生命治理的框架下,从两个角度讲述产妇生命体验。一是从现代医疗话语的角度呈现旧接生法给产妇造成的身体疼痛,他们将 “旧法接生” 主导的临产日描写成女性遭受 “刑罚的日子”⑥萧红:《生死场》,上海:容光书局,1935年,第95页。,分娩时产妇受到非人折磨。如《第十四个儿子》中的李大嫂饱受 “祖先传下来的各种办法” 的虐待:她被人用绳子吊在梁上;请娘家的兄弟 “和她背对背的背起来,拼命蹦跳” ; “让她嘴里嚼一缕头发” ; “用砍竹刀子,砍开了产妇的下部” , “刀口足有一寸多长,糊着凝固的血块。” 产妇最终不省人事地晕倒在 “小河样的血水中” 。①曾克:《第十四个儿子》,《新中国妇女》1953年第12期。这种野蛮、粗暴的助产方法给产妇身体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伤害,并将她们推到生死一线的危机时刻。②这类描写与萧红笔下的瘆人的生殖场景不同:前者是从生命政治的视角界定女性的身体感觉,认为是旧社会不合理、不科学的旧接生方法造成并加重了女性分娩的痛苦,而这种生殖痛苦可以通过新社会接生技术的改革得到疗救;后者则是从文化批判的视角揭示在男权社会中怀孕女体遭受到的身体折磨与精神伤害,同时也表明生殖疼痛是由女性特殊的身体结构造成的,是无法避免的、令人恐惧的原始疼痛。在这些残忍、瘆人、慌乱的旧法接生场景中,我们看到了几笔有关产妇个人身体感受的描摹,李大嫂 “深陷的眼睛紧闭着,脸色就和草灰难以区别。那如同被水浸肿的残白嘴唇还在微弱的翕动”③曾克:《第十四个儿子》,《新中国妇女》1953年第12期。。但很快又被纳入到新/旧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用以揭露旧接生法的愚昧、落后,彰显新接生法的优越性。二是从精神与身体在新社会获得双重被拯救的角度揭示 “新法接生” 对产妇身体及其生命体验的再造。作家们将 “新法接生” 视为疗救女性生殖疼痛的力量,《助产士小陈》《第十四个儿子》《卖酒女》等作品反复写到新接生法如何通过 “强心针” “止血针” “扭转胎位” “产钳手术” 等临床技术使产妇毫无痛苦、顺利平安诞下婴儿。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很难看到 “新法接生” 带给女性崭新的生育体验、身体经验,看到的只是这样一些高度概括性的句子: “周家儿媳平安地生下孩子” ; “李大嫂在睡梦中诞下婴儿” ; “景颇族女人不到一个钟头诞下了双胞胎” ……作家们对新接生法及其效用的叙述掩盖了对产妇身体体验的描摹,他们叙述的重点不再是 “新法接生” 带给产妇个人的全新身体感受,而是要塑造一种承载国族生命意识的集体性身体景观,以此显现国家对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之情: “云雀在竹林尖端飞翔着,向世界宣告新生命降生的喜讯” ; “婴儿哇的一声哭出来,满屋子里的人高兴得不得了” ; “他已经是新中国的一位小主人了” 。④曾克:《第十四个儿子》,《新中国妇女》1953年第12期;赵燕高:《苏奶奶》,《宁夏文艺》1963年第5期;严动:《助产士小陈》,湖北文艺编辑部辑:《一样庄稼,两色土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5页。在这样的文字中,产妇对新生命丰富复杂的感受却是缺席的。因此,在这批文本中,身体一方面处处在场,另一方面又处处缺席。
造成这种身体 “在场缺席” 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作家的性别身份限制了其叙事视角的选择。 “新法接生” 文本的男女作家比例是10∶1⑤笔者整理了20世纪50年代近四十部 “新法接生” 的文本。这些文本的作者只有四位是女作家,分别为茹志鹃、曾克、白瑶和舒慧。,男性作家无法切身感受到女性的分娩体验,仅是抓住医学概念、生育笼统性特征来表述产妇的身体感受,提供一种概括性的、抽象的身体摹写,缺乏对女性身体更为细致、具体的考察。二是民族国家生命治理的逻辑遮蔽了女性个体性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或者说后者必须经过重重规范化才能进入文本。国族话语凭借现代医疗技术实现其对生命的治理,将原本自由、松散的民间孕产活动导向由国家所认同的、合乎妇产科学知识的生命健康行为,与此同时,产妇个人化的身体也被建构成由民族国家生命治理技术统摄的 “母体” 。因此,产妇个人的身体感受当然就很少出现在文本中,作家们将之概括为一种痛/无痛、悲惨/幸福、危险/平安的简单二元对立项。也就是说,这类文本要表述的是一种整体性、高度概括性的生育体验,要建构的是一种符合国族利益、现代妇产科学规范的生育/母性职能——这已然是我们在本小节开头所提到的晚清 “国民之母” 话语的遥远回响。个体生命复杂的身体感受被 “母子平安” “人财两旺” “民强国富” 等国族集体性生命诉求遮蔽,产妇的身体尽管 “在场” 但又是 “缺席” 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其他类型的文学文本中,也存在着这种身体的 “在场缺席” ,作家们积极地塑造被革命意识、革命精神规范化的社会身体,遮蔽、抑制身体的自然属性,将原本私人化、个性化的身体改造成公共化、国家化的集体身体。
总之,新中国初期,以 “新法接生” 为题的文学文本将女性的生命健康同新中国的繁荣发展联系在一起,文本中所呈现的产妇生命体验不仅再现了现代医疗技术对传统身体观念的改造,更呈现了女性身体国家化的进程。
四、生育事件的公共化与家庭伦理观念的变迁
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 “新法接生” 不仅是一场现代医疗技术的变革,更是一场充满启蒙与改造意味的现代性运动。这场接生改革运动不只关涉到人口生产、女性身体健康与个人发展,更是要将私人化的生育事件纳入到公共领域的生命治理体系中,并借此整合、改造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进而将民族国家的权力渗透到家庭日常生活领域,从而再造日常生活。
家庭是 “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页。。父子、婆媳之间亲子关系构成了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社群生活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职权划分也更为清晰, “外边的事儿由你做主,屋里的事儿由我做主”②刘任涛著、罗兴绘图:《生命摇篮》,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96、99页。。传统 “男女有别” 的家庭伦理观念在妇女生育问题上显得更为突出,生育是一项极其隐秘的 “屋里事儿” ,是一个壁垒森严的 “生活堡垒” ,而公开 “讲这些鬼东西,真羞死人” 。③新华社南昌讯:《罗桂香怎样推行新法接生》,《新华社新闻稿》1952年第849-863期合集,第803页。20世纪50年代这批表现 “新法接生” 的文本打开了这扇紧闭的神秘 “生门” ,并调整改造了 “男主外、女主内” “男女有别” “孝悌顺从” “言听计用” 等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建构起契合时代的新型家庭观念与结构。
在《生命摇篮》中,作者以 “新法接生” 为题,建构起一个全新的内与外、旧与新、乡村与城市等多重话语并置的叙事空间, “屋里事” 的主事人李大妈、马山大妈之所以对 “新法接生” 深恶痛绝不仅缘于冯助产士工作中的过失,更多地是因为 “新法接生” 打破了原有的家庭伦理秩序。外来的助产员杨慧兰竟然要直接干预生育这件隐秘的 “屋里事” ,挑战着她们作为 “屋里事” 主事人的家长权威及其在乡村秩序中的位置。因此,马山大妈对 “城里来的” 杨慧兰有着天然敌意,在二人的对峙中,形成了一种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与乡土社会伦理之间的对抗关系,乡土力量呈现出明显 “优势” ,仅凭杨慧兰现代化的医疗卫生技术难以抗衡乡村传统的生育习俗与伦理秩序,必须求助第三方力量的强势介入。因此,作者在文本中刻意塑造了一个民族国家权威的代言人形象④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民族国家权威的代言人多为男性。:区长,这个中年干部沉着冷静,在乡里群众间拥有极高地位,在 “新法接生” 工作遭遇瓶颈时给予极大帮助,尤其在翠珍难产时,他成为助产员杨慧兰的坚实后盾,使之顺利地开展手术,救治产妇和婴儿。以区长为代表的民族国家话语力量不仅为 “新法接生” 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更是弥合内与外、旧与新、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润滑剂。他巧妙地挪借家庭血亲关系来开展工作—— “先动员你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和奶奶” ,并以 “新法接生” 为切口解构原有的封建家长制权威,形塑新的统摄家庭发展的领导力量,打破了传统 “男主外、女主内” 、 “屋里事” 与 “屋外事” 的家庭日常生活范畴,并且积极主动地介入私人化的家庭生育活动中。
“新法接生” 的文本也塑造了一系列丈夫形象,他们不再是严守礼教大防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地参与家庭生育活动,尽管他们没有直接从事具体的接生工作,却也在这场生育改革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小说《接生》中的宝森能够看到新接生法的优越性,并在妻子难产时,力主请来接生员二秀,让她替代旧产婆三换奶奶帮忙接生,最终迎来了家里人满心期盼的 “人财两旺” 。宝森和宝森娘对新旧接生法的不同选择、两种接生方法的博弈都间接地印证了家庭权力结构的改变,盲目 “孝悌顺从” 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在这场接生技术的改革实践中不攻自破。这种叙事逻辑在此类文本中屡见不鲜,青年们仰仗民族国家话语的权威力量重新整合传统家庭权力关系,建构起以革命道德为核心的新型家庭结构,从而推动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群的 “移风易俗” 进程。在小说《山村接生员》中,作者将 “新法接生” 与 “新种耕种” 相关联,呈现了乡村人口生产与农业生产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并进式的变革:一是器物技术上的新旧对立,即新种/旧种、新法接生/旧法接生;二是家庭权力话语的新旧对立,即张大娘、张大爷/海山、厚英之间形成的对话关系,这种家庭结构关系的调整浓缩了新中国初期家庭权力关系的改革。小说中,张大娘将媳妇的难产归咎于 “新法接生” ,张大爷 “总认为是不该点‘中大二四一九’麦种” ,让怀孕的媳妇跟着受累。①化石:《山村接生员》,《红岩》1954年第3期。尽管 “老一辈儿” 因循守旧,但他们却代表着中国人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生命诉求,即 “人财两旺” , “子孙辈辈,要图个长远” 。而 “新法接生” 与 “新种耕种” 既契合这种传统的生命繁衍不息的诉求,同时又改变了传统家庭父子/婆媳之间等级关系,建构起融洽和谐的新型家庭结构关系。
“新法接生” 不仅解构了原有的家庭等级秩序,建构起以革命情感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关系,还彻底地改变了将生育私人化、隐秘化的家庭事务属性。妇女怀孕、分娩不再只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一个公共事务,是民族国家生命治理工作中关键的一环。在管桦《在妇产院里》、李逸民《一个婴儿的诞生》、茹志鹃《静静的产院里》等作品中,作家们围绕 “新法接生” 建构起一个现代化的公共生命治理空间。在公社妇产院里,医护人员不仅为产妇免费接生,还悉心、细致地照顾产妇和新生儿: “产妇等小孩一落地,就躺在床上,不要她动一动了,烧,洗,煮,弄大人,弄小孩,都是我们来,到出院的时候,一个个都长得胖胖的……”②茹志鹃:《静静的产院里》,《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以 “新法接生” 为代表的医疗卫生技术切实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生育习惯与风俗,妇产院成为新的分娩场所,孕产妇、婴儿和医护人员之间形成了具有 “委托生命意识”③巴慕德提出,现代医学的发展有两大革命性的突破:一是对科学真理的探寻;二是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形成的一种 “委托生命意识” , “它逐渐地成为决定医生和护士对待病人态度的根本性准则” , “因此,与病人相关联的每一件事情(健康、生命、隐私)被医护人员看作是一个神圣的托付,医生会将治疗过程告知上帝和同伴” 。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London:United Council for Missionary Education,Edinburgh House,2 Eaton Gate,S.W.1,1921,pp.17-19.的现代医患关系,妇婴在这里可以得到细致的照顾,妇产院成为一个比家庭更专业化、技术化的公共生命治理空间。以魏兰芝、王英兰、谭婶婶、荷妹④魏兰芝是管桦《在妇产院里》中公社产院的助产士,王英兰是李逸民《一个婴儿的诞生》中公社妇产院的院长,谭婶婶、荷妹是茹志鹃《静静的产院里》中公社产院的接生员和产科医生。等为代表的国家生命治理力量介入传统的家庭结构中,替代了原有的婆媳/母女之间的生育照看模式,在家庭之外建立了一个非血缘、非伦理的,以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为核心的,以革命情感为纽带的生命治理空间。这就将传统家庭的血缘伦理 “看护关系” 改造为现代化医疗的 “委托治理” ,妇女的分娩、新生儿的养护已从过去自由的民间习俗行为模式逐渐地变成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主导、国家行政力量积极干预的公共化健康行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凭借 “新法接生” 建构起公共化、现代化的生命治理空间,又以革命情感、乡村伦理关系弥合医疗化分娩所带来的 “冰冷” 的医患关系。早在民国时期,《妇女月报》《女子月刊》《妇女界》等期刊杂志刊载了诸多 “分娩医疗化”⑤“分娩医疗化” 指 “西方18世纪以后新的助产术应用于分娩领域的过程” 。参见赵婧:《母性话语与分娩医疗化: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4期。的文章⑥绿萍:《母亲日记》,《女子月刊》第2卷第10、11期,1934年10月1日、1934年11月1日;君平:《产妇》,《女子月刊》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1日;冬莹:《产妇日记》,《女子月刊》第3卷第2期,1935年2月1日;振华:《产科医院回忆录》,《妇女月报》第3卷第6期,1937年6月10日;诚:《一个产妇的牺牲》,《妇女界》第3卷第12期,1941年10月31日。,真实地记录了产妇对医疗化分娩、产院、临产室、产钳等现代医疗卫生设施与技术的恐惧感: “这室(生产室)面积很大,设备也颇完备,不过在产妇的眼中看来,无异是一个刑场。那高高的产床,也就是一座刑台”①振华:《产科医院回忆录》,《妇女月报》第三卷第6期,1937年6月10日。; “一切都感到生疏,虽然我的家里,没有这病室一样干净,漂亮;但总有些不惯……各人(病室里的人)都仿佛含着一种生硬,势力,忌妬的意味”②君平:《产妇》,《女子月刊》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1日,《中国近代女性期刊汇编》第七册,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3389页。。针对这一问题,20世纪50年代 “新法接生” 文本的作家们有意将现代医学技术与世情伦理关系相结合,以一种革命激情消弭现代医疗技术给孕产妇及其家属带来的恐惧与不安。
总之,上述文本形象地记录了新中国不仅借助 “新法接生” 进行人口生产、生命治理,还以此为契机打破传统、私人化的 “小家” 结构,建构起现代、公共化的 “大家” 空间。家庭的边界被打破,传统的家庭结构被重新整合、改造,血缘性的父亲、母亲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国家理性、革命理性为核心的国家话语代言人形象和以科学观念、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医疗从业者形象,如此就形塑了新的家庭伦理观念与结构秩序。
20世纪50年代以 “新法接生” 为题的文学文本不仅再现了民族国家政治权力对人的生物性存在的介入,记录了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发展历程,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职业女性形象序列——产婆/接生员,在中国职业女性形象史留下特别的印记。并且,这些文本由此揭示出基层女性现代身份的建构历程:她们从前现代的仪式化的生命督导者转变为现代技术化的医疗工作者,成为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具体执行人。这种身份转变既指向了妇女的解放与发展,也推进了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再现了现代生命技术对传统生命观念、文化习俗的改造过程。在 “新法接生” 建构的现代叙事空间中,产妇身体及其生命体验的表述虽呈现出模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却也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生命治理图景,揭示了那一时期中国人特有的身体与生命史进程。这场接生改革运动还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权力格局与等级秩序,建构起以技术理性、革命情感为纽带的公共化生命治理空间,形塑了新的家庭伦理秩序与道德观念。因此,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的 “新法接生” 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极具特色的生命社会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