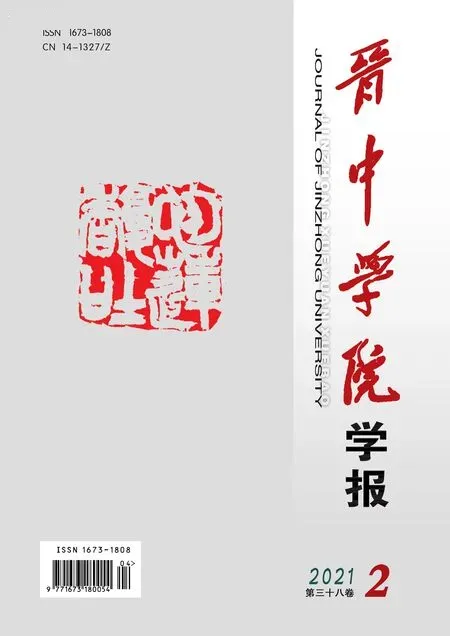回顾与展望:2020年晋国史研究述评
2021-04-15张磊
张 磊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48)
晋国史研究是构建晋文化体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时间段是从叔虞封唐至三家分晋(1),区域以山西为主体,兼及今河南、河北、陕西和山东的部分地区。2020年,关于晋国史研究著作2本,论文30篇(其中报刊公开发表论文26篇,硕士学位论文4篇),对于一个断代的区域史研究而言,成果已属可观。众多研究中,伴随着多学科参与及出土资料的增多,晋国史研究逐渐呈现出理论性强、多学科交融、总结性成果频出等特点。
一、关于晋学理论的探讨
关于晋学理论的探讨以往研究已多有涉及,2020年安介生《表里山河:山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出版,总结并推动晋学理论向前发展。该书是作者多年来对晋学研究论文成果与思想的集中展现,其中晋学研究区域论较多涉及晋国史研究。他主张将晋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小晋学”应该向“大晋学”发展,先秦时期三晋文化研究是晋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山西区域的人地关系、民族关系、区域差异应该是研究的重点。[1]安介生晋学理论的探索实际上是对以往理论的深化,同时将历史地理区域论进一步细化,较多富有体系性与前瞻性的方法论对于晋国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有一定指导价值。
伴随着《表里山河:山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学术评论》2020年第4期开专栏讨论“区位视角下的晋学研究”,众多学者亦撰文讨论晋学理论构建。郝平撰文认为,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形势学说应该视为“古典区位论思想”,散见于史籍、地方志中的形势论大多是从军事及政治视角切入,缺失了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考察,同时作者肯定了安介生将传统的“形势论”与现代历史地理“区域学说”相结合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第一,安介生将区域讨论深入到山西内部,注重对各地理亚区不同区位的讨论;第二,在处理人地关系的理论上,安介生并未陷入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沼,而是同时看重人与地的重要价值,在对传统“形胜”学进行修正的同时,继承与发展了法国年鉴学派;第三,肯定了安介生提出的“跳出山西看山西”以及“共同体”的概念,认为若要推动地方学的长足发展,开阔研究视野与继承性创新势在必行。[2]张俊峰肯定了安介生从移民、民俗等角度开展社会史研究,合理的区域划分对于地域史研究是必要的,区域理论的探索对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3]仝建平认为安介生所提倡的“大晋学”“三部论”“区位论”以及整体与亚区、大视野与小视野同时兼顾的理论及实践促进了晋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对山西区域研究具有重要价值。[4]
二、晋国人物、地理及相关史实考证研究
晋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涌现出许多历史名人,关于晋国人物的研究较为常见。刘晋梅主要从文史互证的角度对《史记·晋世家》中所见晋国人物进行梳理,其中不乏将人物性格、命运置于特定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5]高瑞瑞通过史料分析认为叔向秉持的“礼”已与西周传统迥异,其礼的指向并非周王室而是晋国,经过改造后的“礼”实质是为了维护晋国的盟主地位。[6]金悦《重耳与刘备比较研究》通过不同时空的人物对比,认为《三国志》在塑造刘备时确曾借鉴《左传》中对重耳形象的描述。[7]
晋国结盟现象的考察集中展示了宏观视阈下晋国史的对比与研究。王思祺、李健胜独辟蹊径,历数《左传》中弃盟与改盟现象有八次,均与晋国相关,体现了春秋时期以晋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性,同时昭示了社会信用机制的弱化。[8]王一民从对国际关系学科同盟理论的商榷出发,对春秋晋楚争霸阶段诸侯国之间的结盟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总体上结盟与国家实力成正相关。史实表明不同形势、不同阶段诸侯国之间的结盟行为变化较大,结盟行为并非由单个因素决定,而是基于联系和转化思维下的综合考量。[9]
由于受到“晋无公族”政策的影响,晋国史发展中一直伴随着晋国公室与卿族的关系转换,各卿族势力此消彼长,公卿势力不断变更,故而关于晋国卿族研究一直是晋国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2020年这一研究继续深化。武思梦详细梳理晋国韩氏的发展过程,探究韩氏起与落的原因,认为韩厥在韩氏发展中至关重要,自韩厥位列晋卿开始,韩氏在晋国政坛始终位列显贵直至三家分晋,韩氏一门的发展模式值得探究。[10]谭笑从春秋晚期士人“求富”现象激增出发,认为“求富”是一种社会语境的变迁,关乎春秋中后期的社会重组,是以“礼”让渡到以“利”作为社会规范的反映,晋国正是这一社会趋势中的引领者,晋卿以“求富”为始,又用“富”来招贤纳士并管理封邑,从“富”着眼有利于把握晋国卿族坐大的原因机理。[11]
晋国历史地理的相关考证和探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杨保红认为晋启之“南阳”一为区域称谓,一为城邑名称。围绕三家分晋,分晋前赵、韩在河内南阳地均有城邑,分晋后由于三国疆域多有交错,河内南阳地成为轴心区域,韩、赵、魏三国频繁争夺。[12]张磊对晋古绵山地望进行考证,从晋文公时期晋国疆域、大蒐礼地域选择、晋国战略重点等角度着手,认为翼城绵山的可能性较大;介子推生前可能只是晋文公身边的微臣,身后由于《庄子》《九章》《吕氏春秋》《史记》等文学化的渲染,介子推其人其事在流传中大放异彩。[13]成运楼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考察城濮之战前晋国的战略选择,认为晋南簸箕形的地理格局与曲沃代翼产生的次生性政治风波是影响晋国争霸策略的关键,纵向南下勤王争地,横向联盟稳固同盟,这种纵横排阖的争霸战略是晋国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14]李广洁认为晋国霸业与对太行诸陉的控制紧密相关,春秋晚期太行山已经成为晋国的“内山”,在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亦为三晋跻身战国七雄奠定了基础。[15]
对以往基本形成共识的问题,仍有学者进行质疑且提出新观点,这种探究值得肯定。徐志超从《史记》多处对三家分晋的记载出发,梳理三家分晋过程中各历史事件前后相因的关系,并初步探讨三家灭晋的政治意义,认为《史记》中各处对三家分晋的记载并不矛盾,也从侧面说明三家分晋应置于长时段中进行探究,三家分晋对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有较为深远的影响。[16]王博认为不应对晋国“作爰田”进行过分解读,以往赏田说和车赋说或可商榷:晋惠公“作爰田”实质是安抚韩之战阵亡士兵的家属,其范围仅限于国都附近,目的是为了拉拢国人,这一政策并未形成常态化,未有深远影响。[17]刘晓从封建观念动态演变的角度对叔虞封唐的说法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因戏封侯说出现较晚不足为信,而天命说、善射封侯说与以德封建说三种说法都可以从史料中找到合理解释,或是因为三种说法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包含了一部分受封信息,三说合一或可更好地解释叔虞受封的原因。[18]
三、出土资料与晋国史研究
2020年是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山西省文物局、临汾市委宣传部以及山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纪念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暨张颔先生诞辰100周年系列学术研讨会,涌现了大批关于侯马盟书的研究。栗芳《侯马盟书的书法价值研究》对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特点及书法创作进行初步探讨,认为侯马盟书在笔法、章法、形体上多有独特之处,学习篆书时可以盟书为母体。[19]张美艳主要运用现代书法理论观察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价值。[20]余梅认为侯马盟书文字是中国先秦汉字发展史的鲜活标本,对秦篆影响深远。[21]值得关注的是,在学术研讨会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式对外发布了2020年在运城市垣曲县北白鹅村的考古成果。2020年4月至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垣曲文物旅游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1 200平方米,墓葬9座,灰坑17个,出土各类文物500余件套,其中带有铭文的铜器近50件套,更详细材料仍有待相关考古报告的公布发表。
谢尧亭《晋国兴衰六百年》一书是由山西省文物局组织编写的晋文化系列丛书,这本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兼备的专著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即将近年来出土的关于晋国的考古成果以讲故事的形式连缀起来,传统文献和实物遗存相结合,具有一定创新性与趣味性,不但实现了对数十年来晋国史相关考古成果的总结与整理,又着实在晋文化的公众传播上树立了很好的典范。[22]正如石磊对这本书的评价:在丰富的出土文物中对晋国历史进行了清晰的表达,又在细节处着墨甚多,雅俗共赏的同时不失为一部上乘的学术专著。[23]
201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闻喜邱家庄一座大型东周墓进行发掘,目前发掘报告仍未发表,仅有相关介绍。陈海波《山西闻喜邱家庄东周大墓》一文对2018年至2019年载闻喜邱家庄发掘的一座大型东周墓进行了介绍,出土器物具有明显晚期晋文化的特色,作者推测其为晋公或夫人墓。[24]
近年来,随着安大简、清华简等一批新资料的问世与公布,从出土资料中探索历史问题成为研究新领域。王化平对安大简所见《魏》抄写10首诗(9首本见于《唐风》)以及《侯》抄写6首诗,均见于《魏风》的现象进行探究,作者敏锐指出这种现象或与三家分晋后魏国占有故唐地有关,原本主要描写涑水流域的《魏风》为安大简《侯》所抄,则证明“侯”或为地名,或为爵位,以地名的可能性较大,至于“侯”地望问题,有待考证。[25]文章对安大简相关问题的探讨表明三家分晋是探讨春秋战国之际晋及三晋历史问题的大背景,学术界确应重新认识三家分晋这一历史过程,从长时段、历史变革以及人地互动的角度对其重新考察。夏大兆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左传》《国语》中所见晋人、楚人引用《诗经》的现象进行梳理,并将出土资料安大简与之进行二重比较,得出安大简《诗经》极有可能是流传于晋地而由入楚的晋人抄写而成的结论,并认为这一现象实际上标示了晋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过程,是春秋战国之际中华文化南北融合的代表。[26]李殊根据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吴伐郯的相关史实,推测晋吴邦交的时间应该为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系年》中所载的鲁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说当另有来源;晋吴邦交大体经历了建交、会盟、疏离等阶段,《系年》亦可证实。[27]运用考古资料对晋国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是晋国史研究持续深入的标志。谢耀亭《赵氏戈铭考略——兼论赵卿墓墓主》对太原市南郊金胜村251号墓出土的一件铜戈铭文进行探讨,认为“”字即为“胜”字,据此推测此戈主人为邯郸赵胜。小宗之器出现在大宗墓中可能与“范中行氏之乱”有关,赵简子最有可能将此带有功勋意味的战利品随葬,进一步证明太原金胜村251大墓墓主即为赵简子。[28]李春燕从考古资料入手对春秋晋国及战国韩赵魏三国的城邑进行梳理研究,试图探讨春秋至战国时期晋文化区域内城邑的分布规律,认为春秋早期晋国城邑基本是环状都鄙制分布,随着区域发展的不协调,逐渐形成了多中心城邑分布格局;韩赵魏沿着这一城邑发展趋势继续强化,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邑分布模式。[29]活跃于春秋时期的陆浑戎曾为晋国接纳安置,并与晋国结盟,甚至参与了秦晋崤之战,丁大涛主要根据2013年发现于洛阳市伊川县徐阳村的戎人墓葬及车马坑对其进行考察,认为陆浑戎促进了中原地带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与鼎革,其深远意义应该引起足够重视。[30]王瑞华对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中发现的带有青铜甲片的车辆进行了研究,认为防护甲主要起防御作用,在战车功能上,其与上马墓地3号车马坑出土的2号战车异曲同工,都是以防御为主的守车。[31]
利用考古资料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有助于扩展晋国史研究领域,不同方法和视角使多学科对话与合作成为可能。薛睿《山西出土编钟研究》以出土的晋国编钟为研究对象,交代其历史信息的同时特别注重从音律、音阶、音列等方面对编钟的音乐本体展开专业性探讨,如西周时甬钟为四声阶,春秋初年发展为五声阶,到了春秋中期以后音列更加复杂多变;此外,作者从编钟入手观察三晋不同阶段、区域的文化特性,亦值得肯定。[32]胡春良重点对2019年山西警方从海外追回的青铜器晋公盘进行了铸造技术层面的解读,认为其采用了阴线雕刻、浮雕、圆雕、透雕等多重工艺,并且巧妙运用机械设计装置,与刖人守囿车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代表晋国青铜制造的最高技术。[33]
四、晋国史研究展望及建议
(一)区域差异:积极践行新区域理论
历史地理区域理论指导下的晋国史研究方兴未艾,安介生、郝平、仝建平等倡导的“大晋学”理论逐渐成熟,进入总结沉淀期。晋国史研究作为“大晋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实应更加关注历史上晋国自然地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首先应该“向内求”,即探究晋国区域内部的各个“亚区”之间的差异性与相关性;其次亦应“向外看”,即将晋国历史地理的发展与其他诸侯国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更利于把握晋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地互动的独特性。就晋国历史地理研究本身而言,沿革地理考证的相关成果已较为丰富,晋国军事地理、晋国经济地理、晋国文化地理以及晋国城市地理等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在沿袭地理研究基础上借鉴现代研究方法开展深层次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二)多元融合:开拓更大时空性视野
多学科、新视角关注下的晋国史研究已经初见雏形。从地缘政治、文史互证、计量史学等角度对传统单纯依靠史料关怀下的晋国史研究进行复盘和重置,从而得出较为新颖的观点,一方面仰赖于晋学研究理论的实践创新,另一方面也是晋国史研究推陈出新以及多年积累的结果。
当前晋国史研究成果基本形成了以历史学、考古学为主导,兼及文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学、艺术学、文化旅游、机械工程等多学科交叉互动的研究现状,为晋国史研究提供了更加新鲜的理论活水,新视角下的晋国史研究更加开阔多元。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曾指出,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4]164,可以说多学科关照下的晋国史研究在开创晋国史研究新领域的同时,也正在积极推动晋国史研究在构建晋文化体系中的效力,以期真正打通多学科界限,将文化力转换为生产力。
虽然晋国史研究目前在学科融合上已经有所突破,然而仅仅是个开端。作为晋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命题之一,晋国史是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源泉,源远才能流长,在继续强化对晋国史领域各问题探究的同时,要加强同各学科的融合力度。晋国史研究人员应该跳出传统研究的畛域,主动探索晋国史同文化旅游、教育实践、文艺创作等方面的结合,在维护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推动历史研究走出深闺,与更多元的产业与业态进行交融对话。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晋国史研究也应该肩负起经世致用的重担,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在产业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的驱动作用。
此外,晋国史研究作为地方学之一,尽管研究区域是以历史上晋国的疆域范围为主,但绝不能陷入“晋国史只言晋国”的误区。地方研究离不开对全局的把握,地方学也并非孤立存在[35],晋国史研究的持续开展需要全局、全时意识,即在地域上应该与同时代的所有诸侯国进行横向对比研究,在时间上应该上延下及。最起码对夏商周、战国时期的很多相关问题要密切关注,才能形成连续时空视阈下的晋国史研究,从而避免“本地人言本地史”的尴尬境地,以开放的姿态吸引更多研究人员参与,与其他地方学形成良性且长期的互动效应。
(三)出土资料:研究成果亟待体系化
目前关于晋国史出土材料已较为宏富,尤其是带有铭文的资料较多,数十年来新的考古资料持续问世(如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出土九代晋侯墓、侯马晋都新田遗址、绛县西周倗国墓地、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太原晋阳古城等),晋国史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单纯依靠传世文献的阶段。2020年王化平、夏大兆、谢耀亭、李殊对清关简、安大简以及金文资料的相关研究着眼于出土资料背后的晋国史研究信息。随着新考古资料的不断问世,基于出土文献与考古器物的研究将会持续深入,以传世文献为主撰写的《晋国史纲要》《晋国史》等当中的一些观点亦需要进行修正补充。从晋国史研究整体而言,晋国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如若都有相应的考古资料进行佐证,则从考古角度重新书写晋国史将趋于可行。目前谢尧亭等已经就此做了一些工作,然而从晋国史研究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撰写一部以出土资料为主线、科研价值更高、更具总结性的晋国史仍有其必要性。
(四)公众史学:做晋文化的源头活水
由山西省文物局组织编写的晋文化系列丛书兼具科研性与趣味性,在晋文化公众普及方面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山西省“十三五”文化强省规划》等相关政策为晋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环境,晋国史研究正逐渐走出纯粹学术研究的殿堂。随着文博、文旅、文教的融合和发展,广大群众对晋文化源头晋国史的认识诉求愈加强烈,学界研究力量逐渐壮大,新生代的研究团队逐渐成型,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也从多元化的角度对晋国史研究进行多维度的关怀与探索。晋国史研究正逐渐走出一条科研持续深入、视野逐渐多维、文化公众表达的良性发展道路。
注释
(1)以往一般认为三家分晋发生在公元前453年或公元前403年。最新研究表明三家分晋应该是一个历史过程,徐志超《三家分晋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2期)认为韩、赵、魏三国最终完成三家分晋的标志是公元前349年,赵肃侯将晋静公迁往屯留(今长治市屯留区),静公沦为家人,晋国最终覆宗绝祀,三家分晋结束,因此晋国史研究的时间下限可延至公元前3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