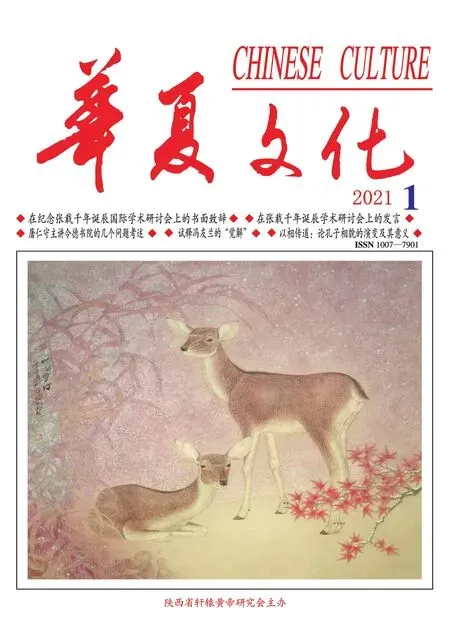关于《中庸》“诚”含义的辨析
2021-04-14赵红梅
□赵红梅

“诚”的思想起源可追溯至原始的宗教祭祀。如《礼记·祭统》记载:“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诚”最早的含义就是指祭祀时的敬慎之心。因为在祭祀中“诚”有沟通天人的作用,所以后来“诚”逐渐发展成为儒家天人之学的重要范畴,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涵。“诚”在《中庸》中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而“诚”的含义又是多重的,本文试从天道之“诚”、人道之“诚”两个方面分析《中庸》之“诚”的内涵。
一、诚的天道内涵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以下简称章节)即天道的性质是“诚”。朱熹对“诚”的解释是:“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以“真实无妄”作为天道的性质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来源于对祖先、神、天的祭祀活动。三代时期,“天”、“帝”的人格神内涵十分清晰,人们希望通过虔敬的祭祀活动祈求天赐福禄,同时天的悠远神秘、博大精微又使人们心存敬畏,使祭拜者在整个祭祀活动中必须处于一种虔诚的宗教情感状态中。由此,天、人就由“诚”这种宗教情感联系起来。“诚”由祭祀者的虔敬之心逐渐发展为天道诚信不欺的性质。《中庸》明确提出“诚”是天之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意志性和神秘性,同时凸显了天道真实无妄的性质。天道之“诚”的确立使人们既不至于走向崇拜怪力乱神的极端,也不至于走向追求现世享乐、追名逐利的极端。因此天道之“诚”作为人道的来源,从根本上为人道树立了人文理性的特质。
另一方面,天道之“诚”的思想来自古人对天之所以为天重要功用的观察总结。古人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发现天有化育万物的功用。《中庸》讲:“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第二十五章》)“诚”是自我完善的,道是自己运行的,“诚”伴随着事物的发端、发展与终结,没有“诚”就没有万物。自然界的日月运行,四季更替,风霜雨雪都有条不紊,万物在自然界规律的变化中生长繁衍。天地呈现出的这种规律性,在古人看来就是真实无妄,厚德载物的性质,这是古人对天地最朴素的认识。对于天道之“诚”和“成物”的性质,《中庸》做了进一步说明:“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第二十六章》)天地之道就是“诚”,天地只有一个,而它生成的万物却是不可计数的。因为天地具有博厚、高明、悠远的特点,因而能够化育万物。古人由此总结出天道真实无妄、诚信不欺,自强不息的品质。这里“诚”具有较为原始的本体含义,“诚”似乎是万物发生演变的依据,不“诚”则无物,但是《中庸》并没有对“诚”何以具有这样的功能给予更多的解释,可见“诚”作为天道的内涵已经有了原始的本体意义,但本体思想尚不成熟。
《中庸》讲:“天命之谓性”,是说万事万物的本性都由天所赋予,不独人有人性,物也有物性。这个天所赋之性就是万事万物成其为自己的根据。人性不是由每个人出生后的后天因素决定;人性是天定的,因此人本身就具有超越性,本身就具有天道的成分。天命之“性”是人通过修养达到“道”的根据。人性是人所共有的性,其特点就是“诚”,“诚”又在于明善。而恶又是如何而来的呢?偏离甚至违反天赋的性,就是恶。所以“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遵循人的本性。人若能有意识地遵循本性行事,且将尽性这件事做完全就达于“道”的境界了。“道”又为何要修呢?首先,《中庸》讲:“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就是说人天天吃饭,却很少有人能知道饮食的真正滋味。人们的日用生活无不是“道”的体现,但很少有人意识到“道”在其中。人对于“道”的无意识状态,就造成了人的眼界与心境碍于一事一物,无法达到“道”的境界。其次,《中庸》讲:“君子之道费而隐。……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是说明人即使意识到人性源于天道,要做到尽性也绝非易事。君子之道广大而精微,周遍而不显现,即使最普通的人也可以知“道”,但到了精微的境界,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知。君子之道,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实行,但要将“道”遵循到极致,即使是圣人也有很多做不到的地方,这就是尽性的难处。正是因为以上两点,人虽然有天之所命的人性,却依然要在日用生活中修身养性,其最终目的就是使有限的个体生命达于无限的天道,能够与天地参。
从“诚”的起源来看,“诚”含有浓厚的宗教信仰色彩。但在儒家文化中,天的神秘性是逐渐降低的,人们并没有将人生的终极意义寄托在对天的宗教信仰上。但是这并不代表儒家没有超越性的一面。人的“性”与“命”是天注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生而具有上达于天的超越性,人们的世俗生活也就具有了“天道”的意义。因此,儒家文化强调人们要在平凡的生活中,普通的事务中发现本性,完善本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以及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通过成全自己的本性,成全他人的本性,成全万物的本性。人的终极意义不是向身外求索,人的命运不是由外在的神灵主宰。人生的意义与信仰要通过反求诸己来实现,通过对自身之性的完善,使自身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
二、诚的人道内涵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说“天命之谓性”,就是说“诚”是天所赋予人的本性,人道就是要恢复、完满天所赋予的本性。“诚”涵盖了人道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包括“诚者成己”、“至诚尽性”、“至诚能化”三个方面。“诚者成己”是说个人修养的层面。“至诚尽性”是说人总是处在关系之中,人的自我修养不是与他者孤立的过程,人在完善己性的同时,也是完善他性的过程,因此“至诚”不仅能够尽己之性,也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最后“至诚能化”是“诚”的最高境界,人了解了自己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后,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能与天地共同化育万物。
“诚者成己”蕴含了儒家修身养性的一套方法。“诚”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品质,朱熹在对“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注释中说:“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中庸章句》)就是说人要追求真实、诚信的品质。人虽然生来就有天赋的自然本性,但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不符合中道的情感与欲望的驱使,偏离自然本性,使天道不能在平凡的个体中完全展现。然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为人的意义就在于追求自身道德的提升和完善。因此人道就要使人性回归到真实无妄、诚信不欺的本性上来。“诚”作为道德品质而存在,就为人道设定了前行的方向和目标。
其次,《中庸》认为修身的起点是明善,“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第二十章》)如果不能辨明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自然就无法在众多事件中把握中道,因此明善是修身的基础。而善是天赋予人的本性,遵循善的本性行事,就能顺乎道,这就是《中庸》第一章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身的基本原则是“择善而固执之”。《中庸》举颜回的例子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第八章》)这是说遵循善的本性,做事时时选择中庸之道而行,一旦确认是善的行为,就牢牢记在心上,不使它失去,这样便可成为圣贤。看起来简单的道理,实行起来却是困难的。《中庸》借孔子之语告诫人们:“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人们都说自己懂得了中庸之道,却一个月也不能坚守,这就是普通人难以成为圣贤的原因。这其实是知与行的问题,知而不能行,实则为不知,故“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第二十一章》)真正懂得了“诚”的道理,自然就会做事不偏不倚,公正明达;反之若处理事情都经过仁义的考量,能够做到中正明达,那么他也就达到“诚”的境界了。因此,个人的修养,要做到知行合一。
除了修身的原则,《中庸》还列举了具体的修身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的学习方法是从古代圣人身上传习下来的。孔子描述舜的德行是:“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第六章》)“好问而好察迩言”指舜好问又善于从平常的话语里发现道理,这正是问与思的方法;隐恶扬善则是要明辨析理;“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笃行中道。
人通过一系列的修养方法,能够恢复自然的本性,这并不是人道之“诚”的终结。“诚”不仅要尽己性,还要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不仅要成己,还要成人成物。人的修养过程并不是孤立于他人、孤立于社会的,人处在五伦之中,修身的过程正是在处理各种对待关系时做得恰到好处。叶秀山说:“世间之所以有道德问题,乃在于世上总有‘他者’”,“世间一切的事,都是有对的,所以事事都是‘事关他者’的,所以事事都要讲‘中庸’。”(《试读〈中庸〉》)这是说人的修养不仅要着眼于自身,更要着眼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在父母、朋友、君臣等的关系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不仅是对己性的成全,更是对“他者”之性的成全。
最后,人道之“诚”是要引导人们达到“至诚能化”的境界。至诚的境界是“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第二十六章》)即圣人内心之“诚”逐渐外化,即使不显现,也会自然显露,即使不运动也会自然变化,无所作为也会自然成就。“至诚”的人不仅完善己性,也使其所处的环境达到了和谐的状态,这是“诚”外化的结果。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唯天下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达到至诚的境界,人类就可以帮助天地化育,从而使自己立于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不朽地位。
三、结语
“诚”作为天道与人道合一的载体,在中国伦理精神的构建中占有重要地位。天道之“诚”的本体世界为人道之“诚”提供了形上的根据。只是《中庸》中天道本体的思想刚开始出现,还不成熟。“诚”何以具有天道的性质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其次,修身之“诚”有一大特点是来源于古之圣贤的言行,也就是说对“诚”的论证是基于古代的社会习俗或古人的言行,这就使“诚”缺乏哲学的根基,这也导致了儒学后来难以应对佛、道的学理挑战。
“诚”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之一,后世不断有学者对“诚”进行理论完善。如孟子在《中庸》的基础上,将《中庸》中笼统的性细分为性与心,论证了人明善的能力来自人心的善端,并提出“反身而诚”的命题,丰富了“诚”的内涵。但“诚”的价值真正得到凸显是在北宋时期,周敦颐在《通书》中结合《周易》与《中庸》的思想,详细论证了“诚”作为天道的来源,并以天道贯通人道,才使“诚”成为完善的哲学概念,也为传统儒学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