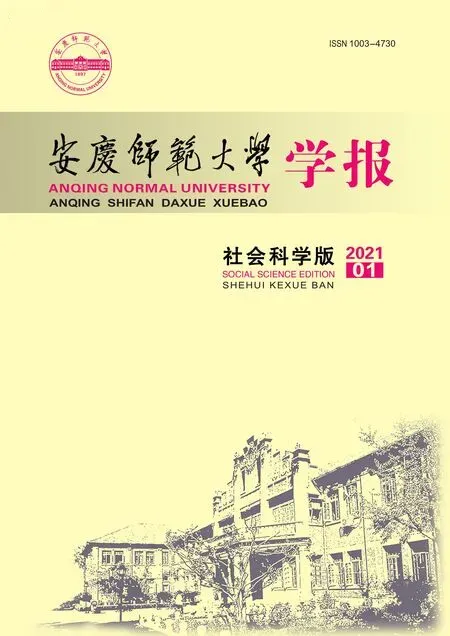梅鼎祚《玉合记》的接受与批评
2021-03-13方盛汉贺佳欢
方盛汉,贺佳欢
(1.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梅鼎祚的《玉合记》一般被称为昆山派扛鼎之作。写成后,汤显祖、屠隆、李贽、王骥德、吕天成、沈德符、徐复祚等当时曲论家对该传奇都有精到评论,这都极大推动了梅氏作品传播,也推广了皖籍曲家的影响力。
一、风流节侠 以情为戏
梅鼎祚青年时代善交游,与汤显祖的关系极为莫逆。万历四年(1576年)春,二人在宣城见面,汤显祖作诗有“自是吴歈多丽情,莲花朵上觅潘卿,春妆夜宴怜新舞,愿得为欢送新生”(《戏答宣城梅禹金·四绝》),此处吴歈即指昆曲,潘卿为其家班女伶;在万历五年(1577年)所作《寄宣城梅禹金》序中写到:“禹金秋月齐明,春云等润。全工赋笔,善发谈端。”万历十四年(1586年)年八月,时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的汤显祖为《玉合记》作序,作了《玉合记题词》。他们到了晚年,还常以书信互相问候。汤显祖弃官之后,心情抑郁,书信和诗中均提及梦见梅鼎祚的情形,他在《寄梅禹金》诗序中说道:“半百之余,怀抱常恶。每念少壮交情,常在吾兄……醒殊怅怅,户外报凤衢书来,何其异也。因书梦以寄。”(《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六),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玉合记》成,梅鼎祚变卖姬妾首饰刻印,他在《与汤义仍太常》中所言:“《玉合》刻竣,乃费我姬人金步摇耳。吴越之间盛行乐部,正缘大序关之以卖珠饰椟也。”[1]汤显祖所作《玉合记题词》评其:“予观其词,视予所为《霍小玉传》,并其沉丽之思,减其秾长之累。且予曲中乃有讥托,为部长吏抑止不行,多半《韩蕲王传》中矣。梅生传事而止,足传于时。”[2]汤显祖的序言是对梅氏的鼓励,指出了《玉合记》超越自己作品之处,做到了取长补短。但是此处《霍小玉传》到底是指未创作成功的《紫箫记》传奇还是改本《紫钗记》,学界存在争议①如赵山林认为指的是《紫箫记》,《从曲家尺牍看昆曲的传播接受》,《中国昆曲论坛·2008》,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夏写时认为是这里的“霍小玉传”只能“始末皆本蒋昉所撰《霍小玉传》”之改本《紫钗记》;《玉合记》既写于万历14年(1586年),那么《紫钗记》肯定在之前。“秾长之累”则改本《紫钗记》则为已成之作。见《夏写时戏剧评论自选集·上》,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121页。。其实从创作时间上判断,此处指《紫箫记》更为符合事实。
同样关于《玉合记》的创作年代,学界也存在分歧。郭英德认为《玉合记》创作于万历十二年,即1584年[3];朱万曙认可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卷三《梅鼎祚年谱》,确定为万历十四年(1586年)所做[4];候荣川认为作于万历十三年[5](1585年)。根据梅守箕《玉合记序》以及郭英德先生的观点,定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较为合适。
所以三部传奇《紫箫记》《玉合记》《紫钗记》分别成书于1576年、1584年、1587年;在体制长度上,分别为34出、40出、53出。吕天成说:“《紫钗》仍《紫箫》者不多。然犹带靡缛。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真堪下泪,真绝技也。”[6]121这是汤显祖本人十年对于同一题材的再创造,而《玉合记》是在另一个角度不折不扣地吸收《紫箫记》的精华。
徐朔方已经指出汤显祖的《紫箫记》是梅氏创作《玉合记》的基础[7],此符合事实。从细节方面亦可证明,《紫箫记》第二出是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朔旦,兼逢立春,《玉合记》也是正月初一碰上立春。从大处看,《玉合记》的创作内容抓住了情与侠这两个关键的问题。《玉合记·标目》末尾明确标明“章台咏,风流节侠,千古播词场”,句末四句诗:“李王孙仙游浊世,许中丞义合良缘。柳夫人章台名擅,韩君平禁苑诗传。”“风流节侠”亦是《玉合记》全剧所全力表现的主题之一。
梅鼎祚为何选择“章台柳”这个题材,并非其所言的游戏之作,他正是看中了其令人欣羡的爱情经历以及所倡导的侠客精神。改编《柳氏传》,正因为突出柳氏对韩翊的坚贞,李王孙、许俊等对美好爱情的成全,体现出作家“主情”一面。在《柳氏传》中,柳氏本为李王孙幸姬,韩、柳二人的婚姻是“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后将柳氏赠给韩翊,可见当时女子地位的低下;在《玉合记》中李王孙是在考察了韩柳二人感情后才相成全,这都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之上,且《玉合记·义姤》交代:“妾方待岁,不止周星。弄管持觞,既免蒸黎之过;称诗守礼,何来唾井之嫌。”表明了柳氏的忠贞和对爱情的坚守。梅鼎祚有意识地淡化柳氏姬妾的身份,有意识的抬高柳氏的出身,同样也使得柳氏更加符合时代背景所要求的女性形象。第三出《怀春》中柳氏曾唱“奴家生来二八,方且待年”,待字闺中,完璧之身。“我性厌繁华,情躭藻翰,合欢裁扇”,体现个人情趣;第三十一出《砥节》中柳氏重复“破镜难圆,破镜难圆”,极为期待和韩郎相见,后来由于沙母的帮助以及沙妻的嫉妒始终未能使沙吒利近身,也就是她从始至终只属于韩翃一人,这是极为符合当时社会守节风气的。
《紫箫记》缺少侠客,《紫钗记》有侠客黄衫客,《玉合记》尚侠。《玉合记》有许俊,这承袭了唐传奇《柳氏传》中的许俊形象,倘若没有许俊的慷慨义烈,也没有最后的完美收场。传奇第三十七出《还玉》,写李王孙闻知柳氏为沙咤利劫走后,许俊当即慷慨激昂地表示“如此小事,左右的备马来”,并要韩翊写一书以作见到柳氏之凭信,反映其智勇双全、侠肝义胆。许俊亦“颇以义烈自许”,正如《标目》中所言“雄威看许俊,立时飞马,夺取孤凰,把当年玉合,再整新装”;《李卓吾评点〈玉合记〉》《还玉》眉批有“世间有如此快人”“真汉子,真豪杰,真丈夫,今天下亦有其人乎?”“勇烈汉子亦自不乏风流韵味,妙人妙人”“异人!异人!”,极为拜服。梅守箕《玉合记序》评价许俊“出其不意,其疾如风,去若脱兔,若决积水于千仞,又在尊俎之间,有折冲焉。贵拙速,不贵巧迟,斯其效也”[8],对许俊尊俎折冲、勇猛制敌取胜给以高度评价。
徐复祚在《南北词广韵选》中感叹豪杰精神之可贵,“章台柳落于沙咤利之手,赖许虞侯而出。今虽有虞侯何益哉!读禹金《玉合记》,追忆往事,为之三叹,因识于此”,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唏嘘哀哉。徐氏虽对梅鼎祚骈俪风格颇有微词,但是对于文中许俊的英雄气概赞赏不已。梅鼎祚杂剧《昆仑奴》同样以侠客作为主角,取材于唐末杜光庭创作的唐传奇《虬髯客传》,他不避陈旧的素材,敢于重写翻新。
梅鼎祚“主情”“尚侠”,是梅氏青年时代任侠仗义的体现,也与晚明时代精神相关。屠隆在《栖真馆集》卷十一评梅鼎祚“倜荡有英雄器略”,梅鼎祚在《昆仑奴传奇引》中自述“余少好谭剑,然未有所遇”,这些都完整呈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其重情正是受到汤显祖“至情论”以及李贽王学左派之影响。有论认为李贽虽与梅鼎祚并未直接交往过,但是通过汤显祖,还是对其戏曲创作产生了影响,其结果是“以情”为戏[9]。
二、以词为曲 才情绮合
《玉合记》不仅受到汤显祖的影响,其问世后受到曲评家们的极大关注,但是褒贬不一。
吕天成《曲品》将梅鼎祚列为“上之中”,评其“名家隽胄,乐苑鸿裁。贡京同贾谊之入秦,作客似陆机之游洛。著述不遗鬼妓,交游几遍公卿。”[6]90评《玉合记》:“许俊还玉,诚节侠丈夫事,不可不传。词调组诗而成,从《玉玦》派来,大有色泽。伯龙赏之,恨不守音韵耳。《金鱼记》当退三舍。”[6]125评《金鱼记》还特意强调“自《玉合》出,而诸本无色”。吕氏指出梁伯龙欣赏《玉合记》,同时《玉合记》吸收了《玉玦记》营养特质,才情绮丽,缺点为不守韵律。在章台柳题材剧作中,吕氏认为《玉合记》已经青出于蓝,首屈一指。同样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论及《练囊记》时云:“传《章台柳》插入红线,与《金鱼》若出一手。自《玉合》成,而二记无色矣。”和前者所论相同。
王骥德《曲律》卷四评其:“宛陵以词为曲,才情绮合,故是文人丽裁。”[10]127“问体孰近,曰:于文辞一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摛华掞藻,斐亶有致;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10]131王骥德对其语言“以词为曲”之评甚为精确,将其列为文辞派,总体是褒奖的;并将其和汤显祖作品进行比较,可谓各有其长,并相得益彰。
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提及“阅梅叔诸曲,便觉有一种妩媚之致”,他将《玉合记》列为艳品,列在“妙雅逸艳能具”六品之四,“骈骊之派,本于《玉玦》,而组织渐近自然,故香色出于俊逸。词场中正少此一种艳手不得,但止题之以艳,正恐禹金不肯受耳。”[6]548“组织渐近自然”正是其超过《玉玦记》之处,也是其正在转变提高之处。其骈骊伴有俊逸,祁彪佳准确感受到“艳”,并在某种程度上欣赏之,这种艳其实正是走向平淡自然的重要一步,但还是担心梅鼎祚并不能完全接受。祁氏尤为重视其“风流蕴藉”,他在评吴鹏的《金鱼记》时说:“此记传韩君平非不了彻,但其气格未高,转入庸境。益信《玉合》之风流蕴藉,真不可及也。”风流蕴藉也即《玉合记》写出了韩君平风流潇洒,含蓄有致,多情打得成双。且剧作整体上以情动人,文字不矫揉造作,浑然天成,此亦《玉合记》之精髓,其他作品难以企及。祁彪佳也将《紫钗记》《紫箫记》列入艳品,他视此三种传奇同一品级,也可见三者之间的艺术联系。
屠隆看中该作“本色”一面,屠隆《章台柳玉合记序》:“洄洑顿挫,凄沉掩抑,叩宫宫应,叩羽羽应,每至情语出于人口,入于人耳,人快欲狂,人悲欲绝,则至矣,无遗憾矣。”对其辞藻以及情感渲染给予充分的肯定。梅氏《答屠长卿》中言及得屠氏大序,“从枕上跃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样作为文词派传奇家,二人惺惺相惜,相互欣赏。
但一些文人尖锐指出该作所存在的问题。沈德符《顾曲杂言》:“梅禹金《玉合记》最为时所尚,然宾白尽俱骄语,饾饤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语,正如设色骷髅,粉捏化生,欲博人宠爱,难矣!”[6]63很不满意其辞藻的堆积。徐复祚认为:“士林争购之,纸为之贵。曾寄余,余读之,不解也。……余谓:若歌《玉合》于筵前台畔,无论田畯红女,即学士大夫,能解作何语者几人哉!”[10]25徐氏反感之情尤为强烈,虽然名气很大传播很广,但此作违背了“传奇之体”,文辞难懂,观众难解。毋庸置疑,《玉合记》中确有“骈俪”之气,宾白都大量用典,有些甚至不符合人物本身的身份。如《玉合记》第五出《邂逅》中【前腔】侍女轻蛾言“谁引你来,纵瑶池有路无青鸟”“你错认三偷阿母桃”,用西王母的典;第十七出《言祖》中韩相公家的小园丁上场言“花气浑如百和香,不辞啼 妬年芳。楼台深锁无人到。绿树阴浓夏日长”,这是分别集唐人杜甫、李商隐、许浑、高骈诗歌;“你看这烟中蝉咽凉柯,燕雏午幕,新桐饮露,密柳眠风,却就是初夏景象。”言辞随处用典、辞藻华丽真难和园丁小童挂钩,也不符合人物特色,但是接下来他调戏丫环轻娥,充满着插科打诨,符合其丑角特色。这也体现出这个人物的矛盾性以及梅氏刻意重骈俪。而全剧无处不是诗,无处不是曲的现象俯拾皆是。这就极大影响到舞台上的表现力。
明人王思任也表达出同样看法,评价《牡丹亭·惊梦》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时评价道,“情文飘动,人自软心,觉《玉合》深晦没理”,此处抬高《牡丹亭》,认为《玉合记》言辞深涩隐晦,语意不明,于理不通。清人张岱同样认为“杨升庵、梅禹金、曹能始藏书甚富,为艺林渊薮。其自所为文,填塞堆砌,块而不灵,与经筒书厨亦复无异,书故多,亦何贵乎多也。”此外,明清两代如沈德符、徐渭、李调元等人所论大同小异。近人吴梅认为:“《香囊》以文人藻采为之,遂滥觞而又文字家一体。及《玉合》《玉玦》诸作,益加修词,本质几掩。”[11]这亦是综合发挥吕天成、王骥德的观点,点出了《玉合记》存在的问题。
当然梅鼎祚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晚年自我反思“意过沉而辞伤繁也”,需“兼参雅俗,遂一洗浓盐赤酱、厚肉肥皮之累”的语言风格。但是他晚年还是对《玉合记》的广泛传播感到自豪,并不否定其文学影响力,他在《长命缕记序》中有:“凡天下吃井水处,无不唱《章台》传奇者。”(《鹿裘石室集》文卷四)徐复祚的“滥觞于虚舟,决堤于禹金”的著名观点确实影响了时人以及后人的评价与态度,但依然阻挡不了其流传之广,这本身也是作品有其独特的魅力。
《玉合记》之所以受到曲论家的关注和重视,一方面缘于梅鼎祚的戏曲成就之高,此外这类作品也恰恰代表了当时的戏曲风格潮流,追求语言文辞之骈绮。
《玉合记》为梅鼎祚早期作品,其风格和汤显祖的《紫箫记》相似。两部作品都被搬上舞台,并被后人放在一起评价,如熊文举观剧诗有《宜伶泰生唱〈紫钗〉、〈玉合〉,备极幽怨,感而赠之》五首:“宛陵临汝擅词场,钗合玲珑玉有香。自是熙朝多隽管,重翻犹觉艳非常。”(熊文举《雪堂先生诗选》)宛陵、“玉”分别指梅鼎祚、《玉合记》;临汝、“钗”分别指江西临川、《紫钗记》。“艳非常”也反映出剧场演出时两剧之风格,这也和祁彪佳将其列为“艳品”如出一辙。当然这种文辞风格在戏曲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语言风格的雅化,才能更进一步促进后期文人传奇的创作。
三、关目曲折 求趣尚奇
除了语言追求骈绮风格之外,《玉合记》尤为重视关目结构的安排,结构性物件玉合也在剧作中多次出现,衔接贯穿全剧。梅鼎祚向来崇拜李贽,李贽对其亦十分赞赏。李贽在《焚书·卷四》评价《玉合记》:“此记亦有许多曲折,但当紧要处却缓慢,却泛散,是以未尽其美,然亦不可谓之不知趣矣。”戏曲结构曲折,并非平铺直叙;问题在于次要人物过多的穿插影响了主线的发展,导致紧要处却缓慢泛散;戏曲节奏虽有破坏,但剧作整体上却有趣有味。
在《李卓吾批评玉合记》(《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中,李贽也是特意对其戏曲关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第三出《怀春》当柳氏感叹昼长人静,不奈幽怀时,批语“关目好”;第七出《参成》,当柳氏自伤身世时,眉批“真,真,关目都好”;第十一出《义诟》,当轻娥发现柳氏、韩生都不在家的时候,眉评“关目好”;这三处极好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第一处生动地描绘了柳姬的“怀春之情”,为后续的情节顺利进行做了铺垫;第三处在几番试探韩生后,柳姬与韩生将在李王孙的引荐下相会,推进了关键情节的发展。
第二十三出《祝发》出,当柳氏断发时有“出于不意,方有关目”之评。当然也有关目做得不恰当之处,第二十六出《入道》,当轻娥寻找李王孙时,看见一个道人很像李王孙,向他询问,眉评“既像李王孙,一见便合疑心,何故又先问他,少关目”,表达其中的疑惑。李贽一如既往地重视戏曲关目,在诸家都在品评其戏曲文辞绮艳之时,李贽集中关注其戏曲的内部结构安排,并给与了比较中肯的评价,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李贽也公正指出其关目的不合情理处。如第五出《邂逅》柳姬绣完绣幡,眉批云:“前日绣得大半,今日还有小半,茶熟便完,亦少关目。”第二十三出《祝发》柳姬和轻蛾分别扮尼、道,互相称对方为“佛前的天女”和“王母前头的许飞琼”,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其实很难有此闲情雅兴,所以眉批云:“哪得如此从容,删。”柳姬安排轻蛾去道观做道姑,柳姬也自断己发入了佛寺,李贽评价:“不合先自分路,直待贼兵紧急之时,各自分头,出于不意,方有关目。”其实李贽是重视“祝发”关目的,其评《琵琶记》第二十五出《祝发买葬》:“如剪发这样题目,真是无中生有,妙绝千古。故做出多少好文字来。有好题目,自有好文字也。”所以他评论梅鼎祚《祝发》一出的安排是符合情理的。
当然也有关目不合理处。第二十六出《入道》轻蛾去寻李王孙,路上碰见一道人,向他询问,又觉得“仙长倒大像李王孙”,犹疑不决,因此李贽眉批云:“既像李王孙,一见便合疑心,何故又先问他,少关目。”指出其不合情理。
李贽还尤为追求关目情节之“奇”,如《焚书》:“韩君平之遇柳姬,其事甚奇,设使不遇两奇人,虽曰奇,亦徒然耳,此昔人所以叹恨于无缘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乃不费一毫力气而遂得之,则李王孙之奇,千载无其匹也。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费一时力气而遂复得之,则许中丞之奇,唯有昆仑奴千载可相伯仲也。”《焚书·卷四》:“世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亦岂少哉!唯不遇奇人,卒致两地含冤,抱恨以死,悲矣!”李王孙和许中丞乃二奇人,李贽看来,许中丞略奇一筹,“然君平者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许俊奇杰,安得复哉?此许中丞所以更奇也。”唯奇,才促成奇情、奇侠。李贽极为赞赏这种“奇人”,这与他的个人品格也是一致的。其关注“奇”,把握住了其审美品格。如李王孙,既是广交名士、仗义疏财的君子,又是一位能够成人之美,散尽家产的异人,还是一个不理俗务、不求名利的仙道之人,是名副其实的奇人之一。李王孙主动撮合韩生柳氏,设酒宴执意将柳姬配与韩生,“韩郎,你名士无虚;柳姬,你佳人独立。便相配偶,不必迟疑。”成全了韩生柳氏的爱情,随后又将自己的家计尽赠予二人,“怎做得守钱的虏”,李贽对此眉批云:“真丈夫。真英雄,若守钱虏不止虏也。”
但关目曲折,求趣尚奇也会引致叙事节奏的拖沓,发生错位。如次要人物和副线的戏份穿插太多,会使主线拖沓松散,支离破碎。
曲坛一批重要文人关注到梅鼎祚的戏曲作品,这反映出梅鼎祚曲作之影响;《玉合记》广受关注,反映出作品思想的进步以及艺术水准的高超。此外,梅鼎祚和汤显祖之所以在思想上相通,性情相近,有一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青少年时期都师承于宁国知府罗汝芳,当时已是王学左派中坚、著名理学家。罗氏1562年出任宁国知府,并借宣城开元寺创办志学书院,邀请地方大儒如梅守德等人主讲,这极大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和心学重镇的形成。正是这样的薪火相传使得地域家族兴旺,人文昌盛。梅鼎祚只是明清皖籍曲家之一优秀代表,《玉合记》也仅是明清皖籍戏曲作品之一代表作,但也正由此彰显出皖籍曲家对于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文化史所作出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