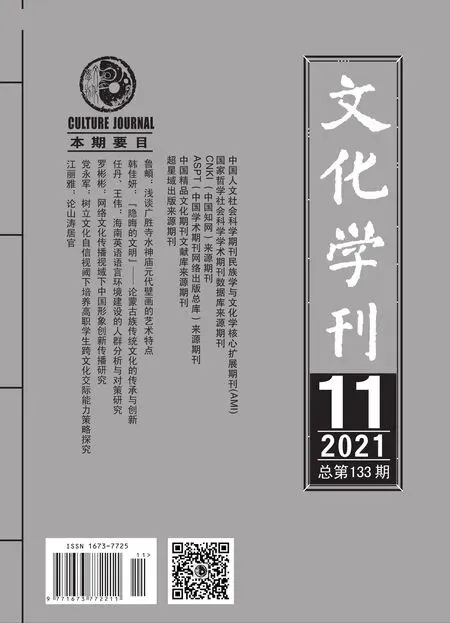身份认同视角下电影《热带雨》中东南亚华人女性形象分析
2021-03-08赵文竹
赵文竹
随着女权运动和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电影市场对女性角色形象和女性视角的刻画与描述日渐增多[1],对女性主体的表达与叙事也更加关注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电影《热带雨》是采取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女主角“阿玲”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转变呈现为切入点,阐释其东南亚华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冲突。
电影中不同语种切换体现文化认同的变化,通过对不同语言的使用与切换能看出女主人公心态上的变化。如果说作为片名的“热带雨”是一种隐喻手法,那么,文中女主人公的语言切换可以解读为电影中她内心对于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上的体现。
当代新马华人对于本土华人文化的关切和担忧,在一定程度内表达了当代东南亚华人女性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情况。结合以上原因,本文将基于新加坡电影《热带雨》探究电影背后的当代东南亚华裔女性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并结合电影材料分析其成因与影响。
一、电影《热带雨》女性形象分析
电影《热带雨》主要围绕马来西亚华人女性“阿玲”婚后随丈夫定居新加坡多年后,随着多次尝试试管婴儿仍备孕失败而爆发的困境后阿玲的形象发生的变化而演绎,电影试图对跨国背景下的亚洲女性经验进行艺术还原,并由此牵扯出新移民文化语境中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不管是面对日常危机或危机下的日常,主角情绪乃至镜头语言都充溢着隐忍、克制甚至谦卑[2]。相较于生育、背叛、死亡、离婚等生活困境,影片着力渲染的恰是女主人公面对这些生活变故时的隐忍、克制和谦卑。
社会文化方面,没有孩子的夫妻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和双方家庭的压力,而其中妻子的社会身份使女性承受的压力更大。《热带雨》中东南亚华人家庭也面临这一的问题。女性身份认同的焦虑主要来自于社会期待的压力,为母则刚或母亲天性的牺牲属性,同时女性的性别困局也是由意识形态编码下内在合法性男性的“缺席”造成的[3]。影片中男性形象是缺失的,主要的男性形象都隐喻着父权文化主导的社会对女性自我认同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消极的一面。例如,阿玲的丈夫将照顾患阿尔莫子海默症父亲的重担直接抛给了妻子,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却被阿玲全盘接受,是出于她对自己妻子身份的认同,同时也体现她将丈夫的父亲视为亲人。这种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与她所处的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加坡相冲突,而语言使用的变化体现着文化认同的变化。
文化认同方面,由于新加坡施行以英语为主要通用语的语言政策,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几乎不使用中文。同时出于适用性考虑,学习者在中学毕业后可能没有运用中文的语境,当地人忽视中文教育。阿玲与学校同事沟通时,即使双方都是华人仍主要使用英语,电影里面新加坡学生通过英语字母对汉字进行标注也印证中文在当地华人的文化认同中处于他文化。而阿玲的家乡马来西亚华人即使同样属于少数族裔,但华语学校的开办保留了华人的文化传统。
角色伟伦对中文的态度也体现出他的文化认同,表面上,他热衷学习中文的理由是其父亲让其接手家族产业便于与祖国大陆通商。实际上,是其自身对阿玲产生的情愫促使他学习并使用中文与阿玲沟通。所以,语言使用的变化需要结合角色形象具体分析。围绕着阿玲的婚姻困境、女性身份认同,探究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与女性身份认同情况,随着贯穿全片的阴雨天的结束,似乎阿玲找到了个人追求的答案。
二、身份认同视角的女性形象解读
(一)身份认同与语言使用
身份认同作为社会文化和超语研究中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体现出语言使用者对其自身承载的文化的观点,即对于行为主体自身的认知行为。这种身份认同通常体现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认同感及国家认同感,以其使用的语言为外在表征。
角色阿玲作为中文教师,她的中文课堂处于一个将本应作为母语的中文作为二语进行教授的教学环境中,这种语言使用的环境也从侧面隐喻着东南亚华裔女性的身份认同困境。语言是由学习者个人社会文化背景、自身发展情况,自主通过命名语言(Named Langauge)进行的语言实践。语言实践的主体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时将某种文化视为自我,将何种文化视为他者,基于文化角度进行身份认同需要借助文化机构的运作使得个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之中,继而实现主体的身份认同情况[4]。阿玲的身份认同过程反映出她与所处如一开始的异国婚姻困境、与自己学生的暧昧等环境的关系,体现她在挣扎中自我认识及对身份认同的发展过程。
(二)对于跨国婚姻的妻子身份的探讨
《热带雨》通过长镜头和阿玲的独白,直白地展示了阿玲的处境和焦虑。此时,她以一个作为长期期盼孩子的已婚妇女的身份坦诚地以平静的口吻诉说自己的困境,长期的备孕失败磨灭了她对于婚姻生活的一切热情,同时时刻加剧她的身份焦虑。作为妻子仿佛没有成功怀孕就是她的责任,丈夫的漠视与不负责使她对自己作为嫁到新加坡多年的外国妻子这一身份更为痛苦。
孕育生命需要夫妻双方的参与,很显然长久以来的失败不应该草率地被归咎于阿玲,但《热带雨》中的女主角——中文教师阿玲,却在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这样的自我折磨,顺从并接受了长达几年的折磨。滂沱大雨中缓缓升起的新加坡国旗,给了我们一个暧昧的回答。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阿玲与她的丈夫虽然都属于东南亚华裔,但是她来自相对落后的马来西亚,她在大学后嫁给来自新加坡的丈夫并随他去往新加坡成为一名社会上本应受人尊敬与爱戴的语文老师。社会身份与文化认同的矛盾让她产生焦虑。
《热带雨》试图对跨国背景下的亚洲女性经验进行艺术还原,并由此牵扯出新移民文化语境中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热带雨》作为影片名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隐喻阿玲焦灼的情绪和心情[5],闷热的漫长的无望的雨季犹如她毫无责任心的丈夫和婚姻。在妻子这一身份上由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巨大的不公的压力同漫长的雨季一样令人厌恶。这也为后续戏剧化情节中,阿玲与学生发生关系后怀孕提供戏剧化效果。最终,阿玲选择回到马来西亚独自抚育后代,而当她回到老家与在园子中晾晒刚刚清洗干净的衣物的母亲时,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万物都闪烁着璀璨的勃勃生机。电影刻意在拍摄时通过晴天与阴雨天的对比,突出阿玲的心态变化。
同时通过母亲与阿玲的对话,阿玲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从妻子这一束缚她的身份中跳脱出来,她的身份即将转变为母亲,同时作为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也将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
(三)对于新加坡的语文教师身份的探讨
尽管华人在东南亚依旧保持着77%以上的人口比例,可出于历史原因,英语作为官方行政语言的新加坡,中文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变得微弱[6]。电影中阿玲试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她了解仅有的几位对中文感兴趣的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出于与中国做生意而非出于对这一语言与其承载的文化热爱时,作为老师,都难免会因为遇上不求上进的学生而产生职业价值上的挫败感。在中文使用率本就不高的新加坡,学生乏善可陈的积极度则使这种挫败感更加突出,其中的对话“为什么不写中文名字?”“忘了嘛~~~”Peter Chan流利却吊儿郎当的答复,实在很难让人判断,他究竟是真的忘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还是明知中文名,却根本不愿填在试卷上。虽然自此之后,影片没有再费更多的笔墨和镜头去呈现Peter Chan这一角色,但年轻一代华人对中文怀揣的态度,却已经不言而喻。这种古怪的疏离感不仅来自于学生,甚至在日常和年纪相仿同事的寒暄中,也有着掩饰不住的吊诡。同样的黄皮肤、同样的黑瞳孔、同样的黑头发,却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看似可以互相理解,但从来没有相互体会,表面上越是亲热,背地里越是陌生。只是单纯地因为在新加坡国际化的发展中,中文无法满足人们对更高价值和更大收益的追求,便遭到了华人乃至教育部门的冷落与抛弃。而作为中文老师,原本担负的使命——延续华语族群的传统意识,在新加坡愈发现代化的浪潮与资本主义汹涌的逐利惯性中,似乎被异化成了某种不合时宜的原罪,并被温吞而果决地孤立。
(四)对于家人身份的探讨
电影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胡金铨的武侠片,似乎只剩下阿玲瘫痪的公公一个观众,就连硕果仅存的武术比赛,在海报和记分牌上,也满满都是英文。死气沉沉的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失落感,往往需要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庭才能填补。然而回到家里,只有瘫痪在床的公公等着她照顾,保姆在等着她付钱。偶尔,阿玲还需要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积蓄中拿出一部分,接济身在马来西亚并不成器的弟弟。原本应当承担,或者至少一同分担的另一半在这个时候仿佛人间蒸发,甚至一丝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觅:不论是衣架上的一件外套,还是书桌前的一张合照。如果是一个人独身也好,哪怕失落,至少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真正可怕的是,一边机械地重复着毫无认同感的工作,另一边还要负荷自己生活之外大量的日常琐碎,长此以往,只会将一个人彻底掏空。而更让人细思恐极的在于,B超检查的医生轻描淡写的两句话“我那个也一样,整天找不到人的。我家小孩也是整天讲English,华语也是很差的”。这种疲惫而疏离的生活,并不是只有阿玲一个人在过,这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焦虑作为一种常见现象普遍存在。
阿玲的公公在伟伦来家中补习时为少年指点汉字的写法,阿玲自然地融入其中。热带雨时刻体现着女主人公的变化,关系复杂的三个人由于共同出自不同目的而对中华文化的留恋成了“家人”,阿玲早已把公公当作家人,而每次阿玲伤心时公公会示意写着“乐”的书法作品来宽慰儿媳,他们将彼此当做家人,却又没有一丝血缘上的关联,当阿玲意识到这一点时,无疑使她对家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冲击。
三、结语
身份(ID),即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拉丁语statum,也是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表征[7]。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则是对自己处境的担忧,担忧自己无法与社会及其标准一致,从而会被夺取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能破坏人们生活的节奏、价值观、世界观,甚至会无意识地否定自己,电影中女主人公阿玲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同样映射现实中东南亚华人女性的现实问题。
随着情节发展,伟伦的介入,这一个同样孤独、同样寂寞,同样地对没落的中华文化及人情冷暖怀抱有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的孩子,甚至他们发生关系后,也并非爱人。但一方面,作为对传统伦理的恪守者,阿玲无法因外界的道德坍塌,便随波逐流地踏入礼崩乐坏的漩涡;另一方面,作为新生代的继承者,郭伟伦的力量也不足以改变社会大众对现行规则的臣服。他像一剂猛烈的催化剂,加速了漩涡中阿玲的觉醒;同时,亦扮演了当代社会里,一丝不太和谐的杂音。《热带雨》从容地将社会层面的政局动荡、性别刻板观念;文化层面的语言冲突、文化传承;还有个人层面的婚姻危机、空巢家庭乃至师生恋问题,巧妙地整合到了一起。阿玲最终在落后却相对完整保留了华人文化的马来西亚,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在这里她最终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与满足。作为一部体现跨文化冲突下华裔女性个人形象的作品,女性形象鲜明的变化是通过她自身的言行举止及“热带雨”来进行隐喻刻画的。阿玲的人生追求一直在变化。她从最初对生育的渴望转向追求关注自身的变化,追求做为女性个人的生活,不再困于让她产生身份认同焦虑的某一身份,最终个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达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