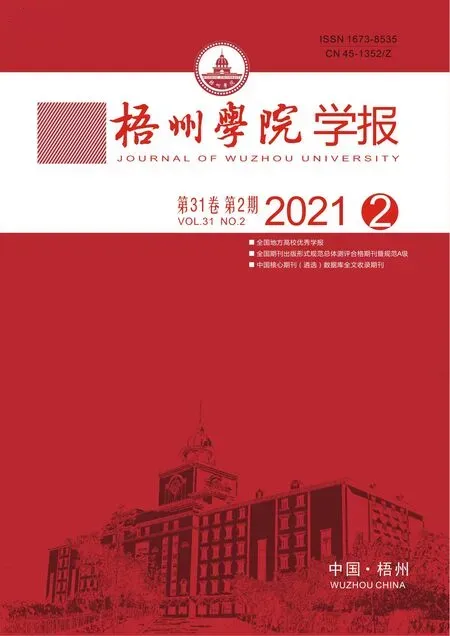闽南打城戏研究
2021-03-08王荟
王 荟
(集美大学 音乐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现今的福建泉州,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自称“打城人”,表演“打城戏”,有着“打城信仰”、传承“打城文化”,并且构筑出一个充满“打城文化符号”和“打城精神”的“打城空间”。打城戏是闽南地区特有的地方戏种,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闽南文化元素,而且有着依附于宗教(佛教、道教)法事的特殊身份。彼得·凡·德尔·龙(Pier van der Loon)曾说过,“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历史上没有一个戏班,唯独中国的佛教、道教,脱颖而出成立戏班,这就是‘天下第一团’,它的名字叫‘打城戏’”。换言之,濒危剧种打城戏是世界上唯一从汉族宗教中孕育而出且保留至今的剧种。它跟梨园戏、高甲戏等其他剧种相比,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便是它带有宗教文化的标签。
一、闽南打城戏的历史渊源
打城戏形成以来并没有正式的名称,闽南老百姓一直沿传“和尚戏”“师公戏”的称呼,也没有人将其作为一个正式剧种来看待。直到1956年福建省派人到泉州执行戏改,陈哮高、顾曼庄等把泉州编剧召集起来分工写剧种史,并观看了打城戏表演,初步了解打城戏的历史概况,于是定名为“打城戏”,上报到中央并得到了批准,从此剧种中才有了“打城戏”的名称[1]。
抗日战争期间,打城戏大部分艺人转业、改行,以致其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后,打城戏得到扶持和恢复。1952年12年,泉州市文教科和文化馆,把打城戏旧戏班艺人集中起来,组成泉音技术剧团。当时演员只有37人,整理演出了《潞安州》《刺朱鲔》等8个剧目。1957年改称为泉州市小开元剧团。1958年到1959年,编演了现代剧《一阵雨》和神话剧《龙宫借宝》,分别参加福建省第二届戏曲现代戏汇演和第三届戏曲会演,获得好评。1960年,剧团正式批准为国营泉州市打城戏剧团。曾整理、改编演出了古装戏《少林寺》《大闹天宫》《火焰山》《真假猴王》《吕四娘》《郑成功》和所编历史剧《李卓吾》《李九我》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剧团被迫解散,主要艺人相继去世,所有资料付之一炬,剧团无法恢复[2]。
1990年,吴天乙在泉州、晋江等地招收30余位打城戏学员,成立私营性质的民间职业剧团,即“泉州打城戏剧团”,由吴天乙任团长。在3~4年的学习期间,吴天乙夫妇抢救的剧目有《目连救母》(可演三夜)《卢俊义》《火烧少林寺》《西游记》《陈靖姑》等。1994年,政府下令剧团解散。时隔4年,1998年8月,吴天乙再次面向社会招收了20多名演员集中培训,成立私立性质的民间职业剧团,即“泉州市天乙打城戏剧团”,并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排练了一台大戏和两台小戏。2008年打城戏被评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泉州市打城戏传习所”,并有配套经费。因打城戏传习所挂靠在泉州市高甲戏剧团名下,此举动引起吴天乙等诸多打城戏老艺人、社会人士的强烈质疑,呼吁吴天乙和黄莺莺另申请一个“打城戏传习所”,并注册“吴天乙打城戏传承中心”。2015年7月,此传承中心应邀香港康乐署参加“2015年中国戏曲节”,在香港大会堂连演三晚《目连救母》,呈现一票难求、座无虚席的空前盛世。2012年,政府根据非遗的保护条例,在泉州艺术学校设立打城戏班,招收30余位打城戏学员,并在泉州、厦门一带参与草台演出及全国的比赛,以换救濒危剧种打城戏。
二、闽南打城戏的种类
在传统社会,艺人属于游民的一种,是脱离了社会正常秩序与社会网络的无根一群,是脱离了宗法家族和主流社会有效控制的一群[3]。这样一群无根一族构成的场域——“打城戏空间”,其内部组织是一个充满内部矛盾、腥风血雨的权力场域。按政府对于打城戏文化资源的分配情况来看,可划分为两个组织群体。
其一是打城戏组织是“吴天乙打城戏传承中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城戏传承人吴天乙为引领者,1990年和1997年培养的两批打城戏表演者为主要成员。传承中心的艺术水平在当地社会均被认可,并在国际戏曲领域有不菲成绩(多次获奖)。吴天乙打城戏传承中心平时没有常规训练和演出,也无政府资金、场地的扶持,只有遇到演出任务时才会召集门内弟子进行排练、参与演出。徒弟们多分布在泉州、晋江、石狮等地,由于他们扎实深厚的戏曲功底、神行百变的舞台表演、字正腔圆的唱腔和轻如飞腾重如霹雷的武功,使得正值青壮年的他们成为泉州、晋江等地职业高甲剧团的顶梁柱,另外一部分徒弟因打城戏剧团的解散已改行从商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另一个打城戏组织是泉州艺术学校打城戏班。正是因为打城戏于2008年被评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和泉州政府将打城戏的培育基地放在泉州市艺术学校并设立打城戏班,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伍志新负责。2013年9月正式招生,3年共招收33名学员,年龄为12~18岁。目前政府将打城戏班纳入泉州高甲剧团管理,资金、剧场、伴奏乐队、行政管理等均由高甲剧团负责。
三、闽南打城戏的文化价值
(一)历史文化价值
打城戏的前身是来自两支宗教戏班的合流,即道教的“小兴源”班和佛教的“小开元”班。然而在闽南民间,因道教家族内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传承制度和生存体系,所以道教“小兴源”班的后代在现今社会里依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道教打城仪式也非常普遍地存在于道教功德当中。曾经红极一时的“小开元”戏班,现在其后裔已经难寻踪迹了。回顾对打城戏的研究,在学术界仅存有一些关于佛教打城仪式、开元班的史料,如荷兰学者高延(J.J.M.De Groot)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在厦门所见的葬礼,此田野日志《佛教丧葬仪式》(BuddhistMassesforTheDeadatAmoy)于1884年正式出版;1991年《福建目连戏研究文集》收录了美国学者肯尼斯·迪安撰写的《福建戏剧和丧葬风俗中的雷有声和目连》一文,文章对距离泉州不远的莆田以东25km江口进行的一场佛教超度法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4];骆婧曾前往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找到香花僧保存的“打火城”科仪本,其中详细记录佛教打城仪式的步骤。也就是说,距今100余年间,学术界普遍认为“香花和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几近绝迹,佛教的打城仪式由寺庙中的法师念经打禅而取代,它已成为一段闽南宗教文化中的“历史记忆”。笔者认为,打城戏中借鉴了大量的佛教故事和佛教文化元素,佛教打城仪式是打城戏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笔者在泉州长期的田野调查中,于2015年5月在石狮地区揭开佛教功德的“真实面纱”,看到了披袈裟、带佛珠的法师现身在佛教打城仪式的现场。仪式由当地德高望重的“香花和尚”——天培法师主持。笔者是在现代社会中观察到鲜活的佛教打城仪式的研究者,即打城戏的前身,遂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细致地记录、分析、阐释佛教打城仪式的过程、功能以及宗教符号象征意义。笔者沿袭打城戏前辈们之研究,继续整理和梳理打城戏的历史文献资料、科仪本、佛道教打城仪式、田野资料等。诚然,打城戏这一议题在闽南社会乃至中国传统艺术场域当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应当得到关注并及时挽救与梳理。
(二)社会文化价值
打城戏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不容忽视。从非遗层面上看,打城戏被评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政府将其放在高甲剧团名下。政府又于2013年在泉州艺术学校开设打城戏中专班,截至目前30几位学员都已有3年的学戏经历,这批学员毋庸置疑地将成为打城戏传承的希望。文化资本分配不平衡导致打城戏艺术角色出现分裂,呈现出双重身份的认同选择,表现出两种文化态势,也就是即两位国家级传承人分别代表两种打城戏的传承体系:一是以伍志新为代表的国家打城戏传承人的“打城戏传承中心”,另一是以吴天乙为代表的国家打城戏传承人的“打城戏传承中心”。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之发所光大。
从现实层面上看,研究闽南打城戏就是在研究闽南传统戏曲,也就是在研究戏曲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戏曲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改变文化人类学西化的倾向,立足本土和闽南文化,是真正地使人类学学科民族化、本土化和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人类学分支学科。从闽南戏曲文化上解读传统闽南社会、闽南族群文化特征以及闽南族群认同理论,可从现实上提供研究社会政策的可行性。
(三)戏曲的艺术文化价值
戏曲的研究,实则是戏曲与人、戏曲与社会的研究,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是重要的切入点和研究方向。不管是打城戏,还是莆仙戏、高甲戏,站在一个更高的闽南戏曲研究的视野中,会发现研究戏曲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在于深入地阐释了闽南地区社会和族群认同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上看,研究闽南戏曲的历史脉络、仪式演变,有助于准确地解释闽南地区闽南族群文化特征的复杂性,并可以反哺闽南地区传统文化的建构。在族群认同理论当中,戏曲的闽南族群认同研究将丰富和发展戏曲与族群认同及戏曲人类学领域研究。
四、结语
闽南打城戏在过去30多年一直被赋予“封建迷信”的烙印,导致打城戏式微情况严重,并且部分资料已散佚,现已较难找到正统的打城戏演出,田野资源十分有限。也正因如此,闽南打城戏研究的迫切程度被提高,梳理和研究打城戏曲文化迫在眉睫。打城戏的研究立足于闽南地方社会,透过田野访谈、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梳理打城戏的历史渊源、种类、文化价值,其中包括闽南族群对打城戏聚合和分化的历史认同过程,以及闽南族群对打城戏的社会认知,从而反思闽南社会对闽南文化认知的共性和差异性,阐释其在闽南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及其与闽南族群的多重认同关系,构筑一个呈现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闽南打城戏与闽南族群的认同空间,为闽南打城戏的传承和闽南族群的凝聚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