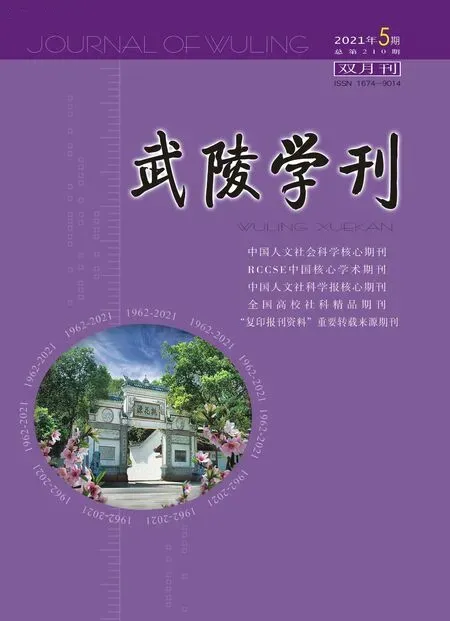南朝诸王幕府与宫体诗的产生
2021-03-08宗伟
宗 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38)
宫体诗的特点,一是题材内容上以女性、艳情为描写内容,形成轻艳的诗风,二是继续永明年间追求声律、辞藻的特质,形成“清辞巧制”和“雕琢蔓藻”的表现形式,其开创者徐摛和庾肩吾在天监年间先后进入晋安王府,两人轻艳的诗风影响了萧纲的创作,普通四年(523年)萧纲任雍州刺史,在此期间萧纲的文学集团初具规模,其诗风也日臻成熟,至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纲入主东宫,这种诗风开始蔓延全国成为流行的诗风,并被后世史书冠以宫体诗之称。文章从宫体诗的题材源流和创作实践上论述南朝诸王幕府和宫体诗产生之间的关系。
一、宫体诗题材溯源与刘宋乐府民歌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云:
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词》、《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则惠休,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1]
刘师培认为宫体诗好为侧艳之词的传统始于晋、宋乐府,以及刘宋的鲍照和汤惠休。胡大雷在《宫体诗与南朝乐府》中说:“自东晋以来,文士逐渐接受南朝乐府,至梁时大量拟作;与此同时,南朝文士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侧艳之词’的传统。”[2]归青《南朝宫体诗分期论》认为:“宫体诗既有乐府民歌的源头,又有咏物诗的源头。这两个源头在新变诗中得到汇合,并受到了新变诗学思想的洗礼,这时诗人只要把笔墨的重点由山水田园、月露风云转移到女色艳事上来,类似于宫体诗的作品就很容易产生了。”[3]可以说,宫体诗以描写女性为主的轻艳诗风,追求辞藻的华美,首先和南朝乐府民歌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南朝的乐府民歌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由发展到为皇室所重,最后又为文士所用的过程。宋少帝刘义符曾制作过吴声《懊侬歌》三十六首和《前溪曲》七首,临川王刘义庆在江州创作过西曲《乌夜啼》,随王刘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王刘铄为豫州造《寿阳乐》,宋孝武帝刘骏曾创作吴歌《丁督护歌》六首。王运熙在《刘宋王室与吴声西曲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刘宋王室人员的大力提倡并参与写作,影响巨大,容易形成社会风气”[4]。同时,刘宋诸王也是民间舞曲的爱好者,为《白纻舞曲》创作歌辞者有南平王刘铄和宋明帝刘彧。南平王刘铄曾创作过《白纻曲》,宋明帝刘彧曾作《白纻篇大雅》。宋孝武帝将《鞞舞》和《拂舞》以及杂舞,用钟石等乐器演奏,在朝廷宴会上施用,极大地提高了俗乐的地位。正是在刘宋皇帝以及诸王的喜欢乐府民歌风气的影响下,从元嘉末至于泰始、大明年间,出现了鲍照、汤惠休这一派的诗人,以创作“委巷中歌谣”而著称于世。
刘宋皇室喜好乐府民歌的风气首先兴起于刘宋诸王幕府中,尤其是宋文帝诸子之中。南平王刘铄曾创作过一首《白纻曲》,“仙仙徐动何盈盈,玉腕俱凝若云行。佳人举袖辉青蛾,掺掺擢手映鲜罗。状似明月泛云河,体如轻风动流波”[5]1214。白纻舞是六朝时期盛行于江南地区的民间舞蹈,这种江南地区流行的舞曲和七言歌辞的结合很适于描写女性。刘铄《白纻曲》全篇都在描写舞女美貌及其跳舞时动人的姿态,玉腕俱凝,佳人举袖。刘宋诸王除了自己创作这样的舞曲歌辞外,还会命身边的文人进行创作,如鲍照奉始兴王教而作的《代白纻舞歌词》四首,前两首用华美的辞藻描述宴会的欢乐和居处的华贵,其中自然不乏对舞女舞姿的描写,如“吴刀楚制为佩袆,纤罗雾縠垂羽衣。含商咀征歌露晞,珠履飒沓纫袖飞”[6]288。此外鲍照又有《代白纻曲》二首,其一云:“朱唇动。素腕举。洛阳少童邯郸女。古称渌水今白纻,催弦急管为君舞。穷秋九月荷叶黄。北风驱雁天雨霜。夜长酒多乐未央。”[6]280描写邯郸的舞女红色的嘴唇轻动,白晳的手腕高举,在急促的弦管声中为君王歌舞。这些舞曲歌辞都将舞女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与宫体诗将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是相似的。
归青在《宫体诗渊源论二题》中认为:“除了哀怨题材外,乐府诗中还有一些描绘女性形象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宫体诗影响。其中对女子形貌刻画的内容,虽然在乐府原作中并不多见,却同样引起了宫体诗人的兴趣,他们在拟写中对这部分内容加以放大后就使拟作蜕变为宫体诗了。”[7]刘铄在汉乐府《相逢行》中单独选取最末六句,“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8]744,自创新题《三妇艳》。刘铄《三妇艳》诗云:“大妇裁雾縠,中妇牒冰练。小妇端清景,含歌登玉殿。丈人且徘徊,临风伤流霰。”[5]1213《相逢行》重在铺写富贵人家之种种享受,而《三妇艳》只取最后描写三妇的六句,把对三位妇人的描写作为诗歌的全部内容,这一新题在刘宋时尚未受重视,但在齐梁陈三朝却备受文人的喜爱,王融、萧统、沈约、王筠、吴均、刘孝绰、陈叔宝、张正见等都争相创作这种新题诗。沈约《三妇艳》诗云:“大妇拂玉匣,中妇结罗帷。小妇独无事,对镜画蛾眉。良人且安卧,夜长方自私。”[5]1616值得注意的是,沈约的《三妇艳》诗将描写的场景和物品由堂上转为了卧室之内,也将末尾的丈人变成了夫婿良人。陈叔宝作《三妇艳》词十一首,其十一云:“大妇年十五,中妇当春户。小妇正横陈,含娇情未吐。所愁晓漏促,不恨灯销炷”[5]2502,已经完全将这种题材的诗歌变成了宫体诗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乐府描写女性题材的诗歌在宫体诗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在文人创作拟乐府的过程中,宋孝武帝刘骏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刘骏诗文造诣在刘宋皇室中属于顶尖水平,又喜欢创作乐府诗,在孝建、大明年间围绕其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可惜宋孝武帝刘骏并不是一个宽容的君主,在位期间先后杀害了南平王刘铄、竟陵王刘诞、颜竣、王僧达,并将鲍照贬出京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个文学团体在创作上的影响,但是这种学习乐府民歌,将男女之情、女色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宫体诗的兴盛。刘骏创作过《自君之出矣》,据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九》记载:“汉徐干有《室思诗》五章,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时有已时。《自君之出矣》盖起于此。’”[8]1435徐干的《室思》六章,每章都是五言十句的古诗,后人摘出第三章末尾四句,敷衍成诗。刘宋时期作过《自君之出矣》诗的人有鲍令晖、刘骏、刘义恭和颜师伯,其中只有鲍令晖的诗是五言十句,刘骏、刘义恭和颜师伯的诗都不同于徐干的原诗。刘骏诗云:“自君之出矣,金翠暗无精。思君如日月,回迁昼夜生。”[5]1219刘义恭诗云:“自君之出矣,锦笥废不开。思君如清风,晓夜常徘徊。”[5]1246颜师伯诗云:“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举。思君如回雪,流乱无端绪。”[5]1247刘骏、刘义恭和颜师伯的诗都是五言四句诗,将原来五言十句的古诗改为五言四句诗,吸收了南朝民歌的特点,便于集中笔墨抒发男女相思之情,而且这种集体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刘骏还有一首《夜听妓》诗,这首诗歌对于宫体诗人的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其诗云:“寒夜起声管,促席引灵寄。深心属悲弦,远情逐流吹。劳襟凭苦辰,谁谓怀忘易?”[5]1222此诗重在表现诗人听乐的感受,情思深沉。同时的鲍照也创作了《夜听妓》诗,其一云:“夜来坐几时,银汉倾露落。澄沧入闺景,葳蕤被园藿。丝管感暮情,哀音绕梁作。芳盛不可恒,及岁共为乐。天明坐当散,琴酒驶弦酌。”[6]619也是重在描写夜晚听远处丝管哀音的感受。然而到了梁代,同题的作品已由听觉的感受描写转为视觉的描写,重在欣赏舞女的美色与舞姿。萧纲的《夜听妓》诗已经是一首典型的宫体艳情诗,其诗云:“合欢蠲忿叶,萱草忘忧条。何如明月夜,流风拂舞腰。朱唇随吹尽,玉钏逐弦摇。留宾惜残弄,负态动余娇。”[9]337萧纲以白描的手法极尽能事地描摹了舞女的纤腰、朱唇、玉钏,这便是艳情诗的典型特点。
围绕刘宋诸王和宋孝武帝对于乐府民歌以及艳诗的喜好,刘宋文士开始侧重创作抒写男女之情以及吟咏女性的诗歌。如鲍照的《学古》描写两个洛阳籍的少妾:“嬛绵好眉目,闲丽美腰身。凝肤皎若雪,明净色如神。骄爱生盼瞩,声媚起朱唇。衿服杂缇缋,首饰乱琼珍。调弦俱起舞,为我唱梁尘。”[6]369用了大量笔墨去描写两位少妾的腰身、眉目、肤色、朱唇、衣饰,末尾处又说在床上已经放置好了两套色彩鲜明的衾被和一对用角装饰的枕头,让人浮想联翩。胡大雷《试论南朝宫体诗的历程》总结说:“虽然有诗人真实的自我在参与并叙述,可诗人所写的对象是娼妓,着力于女方容色的描摹,并最终引向衽席床帏,是描述型的,这些都成为日后宫体诗的典型写法。”[10]归青在《宫体诗渊源论二题》中认为:“正是因为有了鲍照对艳诗的大力写作,才会有文人艳诗的创作的高潮,从而也就为宫体诗的产生作了某种准备。”又说:“尽管宫体诗是以新变体的面貌登上诗坛,并不主要承继休、鲍的艳诗,但他们在客观上为宫体诗的出现营造了氛围,准备了条件,则是毋庸置疑的。”[7]鲍照在刘宋皇室的影响下把文人艳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刘宋诸王对乐府民歌和艳诗的喜好促使刘宋文士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形成描写女性的艳丽诗风,为宫体诗侧艳之词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宫体诗与竟陵王幕府咏物诗
归青在《论体物潮流对宫体诗成形的影响》一文中认为:“从诗歌角度来探讨体物潮流对宫体诗的影响,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咏物诗。我以为在宫体诗的所有源头中,咏物诗可以说是最直接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咏物诗是宫体诗的主源,宫体诗是咏物诗的延伸或变种,从咏物到宫体存在着逻辑的必然。”[11]咏物诗在齐梁年间兴盛,而竟陵王幕府文士的诗歌创作正是以咏物诗为主,完成了从咏物到咏人,从体物到宫体的转变。
竟陵王幕府文士的咏物诗在永明年间吟咏的多是自然景物以及人工器物,不过这种情况在建武至天监年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以竟陵八友之中历仕齐梁两代的沈约为例,其咏物诗中出现了吟咏女性生活物品的诗作。沈约的《十咏》二首,分别描写了领边绣和脚下履:
纤手制新奇,剌作可怜仪。萦丝飞凤子,结缕坐花儿。不声如动吹,无风自褭枝。丽色傥未歇,聊承云鬓垂。
丹墀上飒香,玉殿下趋锵。逆转珠佩响,先表绣袿香。裾开临舞席,袖拂绕歌堂。所叹忘怀妾,见委入罗床。[5]1652、1653
《领边绣》在描写领边绣的精美之后,结尾想象丽人穿上之后,云鬓垂下,美艳动人的场景。《脚下履》“裾开临舞席,袖拂绕歌堂”,也是想象美人穿上履之后开裾拂袖出现在舞席和歌堂的场景。沈约的乐府诗《洛阳道》写洛阳的佳丽,重在描写她们的衣饰,其中“燕裙傍日开,赵带随风靡。领上蒲桃绣,腰中合欢绮”四句描写洛阳女子的裙带、领上绣和腰间绮。关于沈约在描写女性物品上的进步,傅刚在《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中评价说:“细心的读者已发现此诗采用了不同于《六忆》的写法,即贴近于美人身体衣物的工笔刻划。诗歌不仅写了裙和带,还写了领上的绣和腰中的合欢绮。前者也可以在乐府民歌中找到,后者却是新的表现,它对宫体诗所起的启发作用,超过了《六忆》的艳情内容。”[12]
沈约的诗作不止于描写女性的物品,还由物及人开始描摹女性,有新婚少女、舞女以及美人,其中有不少露骨的描写。其《梦见美人》诗云:“果自阊阖开,魂交睹容色。既荐巫山枕,又奉齐眉食。立望复横陈,忽觉非在侧。”[5]1640该诗描写了梦中与美人交往的过程。《乐将殚恩未已应诏》诗云:“轻肩既屡举,长巾亦徐换。云鬓垂宝花,轻妆染微汗。”[5]1646其中四句描写宴会上舞女的身体动作,以及跳舞之后汗染轻妆的细节。《少年新婚为之咏》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新婚少女优美的姿态及华丽的服饰和佩饰,描摹得非常精细,“腰肢既软弱,衣服亦华楚。红轮映早寒,画扇迎初暑。锦履并花纹,绣带同心苣。罗繻金薄厕,云鬓花钗举”[5]1639。
与沈约同时,参加过永明文学创作的一些诗人也出现了一些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如高爽的《咏酌酒人》,江洪的《咏美人治妆》,王僧孺的《咏宠姬》,诗云:
长筵广未同,上客娇难逼。还杯了不顾,回身正颜色。[5]1542
上车畏不妍,顾盻更斜转。大恨画眉长,犹言颜色浅。[5]2075
及君高堂还,值妾妍妆罢。曲房褰锦帐,回廊步珠屣。玉钗时可挂,罗襦讵难解。再顾连城易,一笑千金买。[5]1767
《咏酌酒人》描写酌酒的侍女,筵席之上,贵宾骄纵,然而酌酒侍女还杯不顾、回身正色的行为,生动地表现了侍女虽然身份卑微,却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愿舍弃尊严讨好贵宾。《咏美人治妆》写一个美人上车之后,担心自己不够美丽,认真打量自己,又是觉得自己的画眉太长,又是觉得自己的颜色太浅,十分可爱。《咏宠姬》描写深宅大院之中一个受宠的姬妾,曲房锦帐,回廊珠屣,解去玉钗和罗襦,博得君子的宠爱,为了爱姬的回视和一笑,主人愿意用连城之宝和千金之物交换。这些以女性人物为描写对象的诗歌,虽然数量少,也没有宫体艳情的色彩,但起码说明在萧纲宫体之前的永明诗人群体,已经对于女性形象有了明显的关注。
以竟陵王幕府为核心的诗坛于永明年间在诗歌题材上发掘了咏物诗,在诗歌形式上提倡讲究声律和辞藻的新体诗,在建武年间以至梁初的天监年间,他们融合新体诗的形式与咏物诗的题材,创作了一些吟咏女性物品,以女性为审美对象的诗歌。宫体诗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宫体诗的先行者徐摛的诗风也不是偶然形成的,在永明文学到宫体文学出现的二三十年间,曾经活跃于竟陵王幕府的这批文士已经开始了这种新变,在当时极为兴盛的咏物诗中出现了描写女性及其物品的诗坛风气。
三、梁代诸王幕府与宫体诗的形成与流播
萧纲普通四年(523年)出任雍州刺史,至中大通二年(530年)被征为扬州刺史,在雍州的八年,萧纲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文学倾向。据《梁书·徐摛传》记载: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中大通三年,遂出为新安太守。至郡,为治清静,教民礼义,劝课农桑,期月之中,风俗便改。秩满,还为中庶子,加戎昭将军。[13]493
中大通三年(531年)五月二十七日,晋安王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同年徐摛出为新安太守,宫体诗已经开始流行于京城,甚至引起了梁武帝的注意和不满,所以萧纲来到京城之前,必然已经形成了明显有别于京城文风的文学倾向。这种文学倾向就是诗风的宫体倾向,因为在雍州时期萧纲及其幕府文士的诗歌创作已经展示了这样的特质。
雍州对萧纲影响甚大,以其为中心的宫体文学集团有着雍州幕府的深刻印记。刘祥在《州郡的突进:论萧梁地方藩府对京师文学场域的干预》中说:“萧纲在藩邸月夜清游、良宴赋诗、评论文史,独特的文学场域促成了文学的新变。而在成为太子后,受礼法所限,对京师生活有所不满,一再怀念雍州旧游。上引《答张缵谢示集书》也是用‘伊昔’开启对藩邸生活的回忆,均可见雍州时期对萧纲影响之深远。”[14]在雍州时期,萧纲的诗风已经成熟,在其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梁书·庾肩吾传》记载:“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13]766《南史·庾肩吾传》记载:“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15]在雍州幕府时期,在萧纲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士集团,宫体诗的核心人物庾肩吾和徐摛都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陆杲、刘遵、刘孝仪、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王囿、孔铄、鲍至。这个文学集团也进行了宫体诗的文学创作,例如萧纲有一首和诗《和徐录事〈见内人卧具〉》,原唱为一位姓徐的录事参军,很可能就是徐摛,而且只有在晋安王时期,其僚佐才会有录事参军一职。萧纲的这首诗极力铺陈卧具的精美华丽,描写红帘轻帷深处一位女子正端坐闺中缝制卧具,已经具备了宫体诗的特征。
由此可见,宫体诗产生于晋安王萧纲的雍州幕府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在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纲成为皇太子之后,才将这种轻艳的诗风由地方引向京城,又由京城影响地方。我们必须承认,萧纲成为太子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如若不是萧统的突然去世以及萧衍国赖长君、放弃立嫡长孙的想法,萧纲都不可能成为太子。萧纲的新变之诗是建立在前代诸王幕府文学集团群体诗歌创作的基础之上,是南朝诸王幕府文学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结出的硕果。因为中大通三年(531年)突然的政治变局,萧纲入主东宫,并成功将这种追求“吟咏情性”和“情灵摇荡”的诗风带入京城,幕府之诗演变成为宫体诗,但是宫体诗背后的幕府背景,却不可磨灭。
宫体诗在萧纲入主东宫之后,并没有立刻产生广泛的影响。清水凯夫《梁代中期文坛考》认为:“从中大通三年到中大通六年期间,太子萧纲集团是脆弱的,不得不沉沦下去。”[16]151其核心成员徐陵在中大通三年(531年)被外放为新安太守,庾肩吾中大通四年(532年)任萧绎的平西录事参军。归青《南朝宫体诗分期论》认为萧纲文学集团面对宫体诗在当时尚没有赢得足够的地位,还比较受轻视的局面,集中力量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联合萧绎的力量,对裴谢诗风发起攻击;二是编纂了《玉台新咏》;三是初步构建了宫体诗理论。宫体诗真正在梁代诗坛取得统治地位是在大同之后,正如《隋书·文学传》所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17]可以说,在大同年间宫体诗由京城向地方传播的过程中,湘东王萧绎的幕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萧纲的东宫和萧绎的幕府双峰并峙,共同将宫体诗推向了鼎盛的局面。萧绎及其幕府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萧绎幕府通过文士流动和书信往返的交流方式,展开地方幕府与京城文学的互动,共同构建宫体诗的理论,共同开展宫体诗的创作实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文士交流上,庾肩吾在中大通四年(532年)由东宫通事舍人出为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正是萧纲立为太子的第二年,庾肩吾在萧绎府中历仕中录事参军、谘议参军之职,于大同年间才返回东宫任太子率更令。庾信由东宫抄撰学士出为湘东国常侍,转任安南参军。徐陵在大同三年(537年)任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这三位文士都是萧纲东宫文学集团的中坚力量,充分说明了两个文学集团之间在文士交流上的密切,且都在中大通三年(531年)之后到大同年间出任湘东王萧绎幕府的官职,这个时间节点也很值得注意,恰恰是宫体诗亟需力量的时候,可见三人的任职不是偶然的现象,是萧纲和萧绎自觉地利用文士任职的交流,沟通两府的诗文创作的交流,从而实现宫体诗革故鼎新的目的。在书信往来上,萧纲有《与湘东王书》《答湘东王书》《又答湘东王书》,其中《与湘东王书》是表达自己文学主张的一篇文章,清水凯夫认为:“《与湘东王书》是企图排斥‘古体派’及‘谢灵运派’的文体而扩大和发展‘宫体’。”[16]186《与湘东王书》云:“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9]718萧纲面对重新树立京城文体的问题,抬高湘东王萧绎的文学地位,继而笼络湘东王萧绎与自己共同努力,构建一种崭新的健康的诗风。萧纲和萧绎之诗最多,有七题十首,其中《和湘东王〈古意咏烛〉》《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都具备宫体诗的特色。此外,刘孝威《奉和湘东王应令》二首,庾肩吾《奉和湘东王应令》二首,都是奉萧纲令和湘东王萧绎的《春宵》和《冬晓》,萧纲自己也创作了《和湘东王三韵》二首,是和湘东王萧绎的《春宵》和《冬晓》的,可见这两个文学集团之间交流的密切。
其二,萧绎幕府成为宫体诗在地方上的中心。兴膳宏在《〈玉台新咏〉成书考》中说:“遗留下同皇太子唱和之作的诗人们,当然是和他在日常有很多接触机会的人。这样再来看《玉台新咏》的卷七、八,就会强烈地感觉到:在这两卷中,以皇太子为主、湘东王为副的文学同人们(也就是宫体诗主要担当者们)通过相互交友关系写下的诗作,构成一个庞大的中心体。卷八留下姓名的诗人中,从刘遵开始到徐陵为止,几乎全都是皇太子萧纲或湘东王萧绎的部属。”[18]湘东王萧绎在长期出镇的过程中,幕府集聚了大量文士,如王籍、刘孝绰、刘缓、鲍泉、阴铿、徐君蒨、孔翁归、朱超等。在中大通三年(531年)之前,萧绎与“古体派”的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刘之遴和顾协都有密切的交往,和“谢灵运派”的王籍、伏挺也有深交。在中大通三年(531年)之后,随着萧纲成为太子,萧纲原来的文士在东宫与湘东王的幕府之间频繁交流,萧纲通过书信抒发自己的文学主张,并积极拉拢萧绎,使萧绎最终成为宫体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萧绎的幕府也成为除了东宫之外的又一处宫体诗的创作中心。萧绎作《班婕妤》和《春宵》《冬晓》,唱和萧绎《班婕妤》的有何思澄《奉和湘东王教〈班婕妤〉》,孔翁归《奉和湘东王教〈班婕妤〉》,唱和萧绎《春宵》《冬晓》的有萧纲及其东宫文士刘孝威和庾肩吾,以及湘东王幕府中的刘缓、刘孝先、萧子晖。这两次唱和展现了萧绎及其幕府在宫体诗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宫体诗创作在方镇上一个的中心。
南朝诸王幕府是宫体诗产生的载体,也催化了宫体诗的成熟。宫体之所以出现在梁陈而未出现在宋齐,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契机,即藩镇诸王合理合法成为太子或皇帝且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因为昭明太子萧统的突然薨逝和梁武帝立长不立嫡的想法,萧纲由藩王成为皇太子,又在梁末成为梁简文帝;因为侯景之乱,湘东王萧绎也在平乱的过程中积聚实力,登基践祚成为梁元帝,这两个本该优游卒岁的宗室藩王皆因为意外的政治事件成为皇帝,让本该成熟于诸王幕府中的文学成熟于京城宫廷之中,这是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的。后来继承宫体诗大纛的人物又是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三位帝王,他们推波助澜使宫体诗完全成为宫廷文学。然而宫体诗从题材内容到创作实践都源于诸王幕府,其产生于诸王幕府,勃兴于诸王幕府的发展过程却被今日研究所忽略。当然产生于诸王幕府中的文学成为宫体甚至宫廷文学也有其必然性,因为东宫和宫廷是诸王政治上所欲登上的顶峰,产生于诸王幕府中的文学在合适的条件下自然流向东宫与宫廷,可以说梁陈宫体文学就是一种极致化的诸王幕府文学,也是诸王幕府文学的最终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