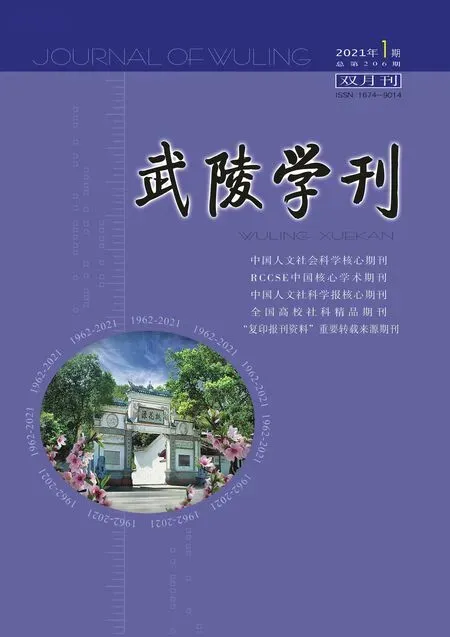国族、华族、中华民族:保教风潮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及其流变
2021-03-07钟艳艳
钟艳艳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民族意识勃兴,这是当时国人基于内外情势做出的反应。也正自那时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才萌生出历史生命。张之洞作为身处内忧外患日渐加剧的晚清社会的封疆大吏,提出了基于封建帝制意义上的保国主张,以“独尊孔教”来保存作为国粹的礼教,以求在文化传统的延续层面维护古老的夷夏国族空间;康有为作为频繁活动于政治舞台的南海圣人,主张“复原孔教”,通过挖掘孔教中的宗教特质来建立孔教、恢复礼制,希图重塑以孔教为基因的华族国魂;梁启超则是短暂地涉身于保教风潮之中,其后便由昌明圣教转为“淬厉孔教”,主张发挥孔教的德性维度,以便于从批判性发展的角度将孔教思想容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及未来命运之中。通过梳理三人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和主张,可以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上“被塑造”的过程。而以保教风潮为历史背景,能更好地凸显宗教之于政治、宗教之于民族、政治之于民族的复杂关系。
一、作为国粹的“礼教”:张之洞的国族空间与保国构想
“国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首次出现于《礼记·檀弓下》,即“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1],大意指“宗族、宾客”。后来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将国族阐发为由家族、乡族、部族循序形成的对外具有排他性的联合性群体。台湾学者沈松侨曾将国族理解为独立主权国家内部超越血缘、信仰、祖先崇拜等束缚,通过共同文化、语言、风俗、历史和政治性利益等纽带,将不同种族、不同社群的人组合而成的一个互相认同的人类共同体[2]。张之洞视野中的国族以“类”属性为区分标志,如《易·同人》的“君子以类族辨物”[3],国族是基于多种“类”的分别而形成的目的共同体,这一目的即是保国。保国理想的形成首先是出于现实考量。晚清社会面临的严峻政治危机与士绅头脑中繁华的天朝样貌形成鲜明对比。张之洞等虽沉湎于中国“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灵淑,风俗和厚,邃古以来称为最尊、最大、最治之国”[4]9717的昨夜梦境中,却又不得不直面“今日国家大势,中原无事,金瓯屹然。溯自咸、同以来,发、捻、苗、回之变乱,寇虽多而难卒平,燕、秦、晋、豫之旱荒,灾难深而民不变”[5]的混乱现实。且张之洞作为权倾一时的当朝官员本身也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当时的他所面对的除却绵延数十年的国际危机外,还有国内民族争端,这时的民族问题主要以满汉对立为主。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在遗折中仍忧心满汉关系问题,再三强调“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6],足以体现他对民族问题的重视。也正是基于对满汉矛盾问题的处理,张之洞逐渐形成了满汉一体的初步国族观念。
满汉矛盾是有清一代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而抑制反满、排满情绪则是张之洞保国构想的步骤之一。满汉矛盾引发的社会问题频发于下层群众之间,且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牵扯因素多、耗时久。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荆州旗民由于“观划龙船积衅未释,旗丁寻隙纠毁咸宁、武昌二县客民铺面会馆,伤毙人命”之事被登记在案。张之洞将满汉矛盾称为“旗民”矛盾,“民”专指汉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二十五日,荆州东门外距城五里多为汉族居住的草市后街泰山庙演戏酬神。旗人小福意欲上台看戏,管台的民人庞家顺将其阻拦,小福“夺梯上台,愈上愈多,将庞家顺殴打摔至台下,庞家顺惨呼救命,以致激成众怒”[7]837。之后,旗人百余人与民人千余人混相殴打,旗人被赶出泰山庙。而旗人在返回满城时途径东门二里外沙坝,遇到居住草市的民人王大福,旗人为泄愤将其打成重伤,随后在满城网罗数百旗人持刀枪重新返回草市“报仇”,最终导致双方共约四十七人受伤,其中民人王大福、郭光涣因伤毙命。类似案情在晚清反满、排满情绪下屡次发生。即便已经处于王朝末期,张之洞仍以“弹压”为主要手段处理满汉矛盾,除却维护满清帝制的政治动因外,还有把国家视为一个大的“容器”来容纳各民族以实现其保国总目标的现实动因。
“中国涵濡圣化二百余年,九州四海同为食毛践土之人,满、蒙、汉民久已互通婚媾,情同一家……今中外大通,乃天子守在四裔之时,无论旗民,皆有同患难共安乐之谊。”[7]1421张之洞揭示了满、蒙、汉人共居中国的和谐历史,并从人种上把满、蒙、汉同归黄种,指出“黄种古,白种强,黑蠹棕微红种亡。我黄种,遍东方,满蒙汉人都一样”[8]4250,并号召“满蒙汉皆同是黄种,同种团结外人难动摇”[8]4277,试图以此来强化满、蒙、汉同居一国的历史共性,并初步从满、蒙、汉共同濡化于儒教氛围的文化生态出发,提出“我圣教,莫抛荒,文明国粹保久长”[8]4264的独尊孔教、发扬国粹的保国构想。
“国粹”在张之洞来看,是一个国家最为擅长且发展精细的包含学术、技能、礼教和风尚在内的物质文化体系,通过对国粹的“宝爱护持”,国家能获得强化国力和国族认同的本原。而国粹之于中国的形式是在宗法制之下使群居生活有所遵循的礼教,重宗法是对传统群居模式的延续,重礼教则是对国族共有文化的传承。礼教是孔教学与行的中心内容,通过护持以礼教为核心的国粹,国族认同有望获得深化,这正是张之洞在面临内忧外患时亟需的意识形态支持。
张之洞视野中的礼教由三纲、五伦及其相关礼制构成,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所在。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4]9704,五伦为“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4]99715。在张之洞看来,正是以三纲五伦为基础的礼教塑造出孔教的根本精神。礼教者,“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4]9716。礼教自孔圣创制以来经历了以教为政、政教并行等多个历史阶段而畅行至今。张之洞认为,中国虽经历了多个朝代更迭,但在混乱时期仍能保持人心凝聚不至于离散的关键在于纲常名教、礼义廉耻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动摇。他指出,当下青年常常舍本逐末,“日诵哀、皮、西、黎(A,B,C,D)为自强之学”[4]9704,仅仅掌握西方文化的表面便自以为把握了西方富强之实政、爱国之忠悃的方法内核,实际上是捧心失步,只益其丑。而“有志之士但当砥砺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4]9769,如此便能国势日强、儒效日彰。由此,张之洞将昌明圣教的保教思路揉入保国构想之中,保教也就同时具备了强国与爱国的二重功能。
如何昌明孔教以强化国族认同?张之洞提出著名论断:庙产兴学。庙产兴学的提出有其宗教生态背景:“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张之洞洞察中国宗教发展、变迁的交融互鉴历程,同时对三教间的交流与融合有较为精到的理解。他提出,“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只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4]9740。此外,寺田变更为学堂田产后,“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4]9740。以上可见,张之洞认识到佛、道二教与儒教间的依附关系,精准地抓住儒教之于中国宗教与文化生态的核心地位,最终将这种认识一以贯之地运用于其保教实践之中,而这又是以强化国族认同为归宿。
当然,张之洞并未将尊孔教—承国粹—保国族的思路作为构建国族空间和保国的唯一路径,他的角色更多是洋务运动中的实干家,曾主持并参与到多个省份的书院、铁路、电力和矿业等的实际运作中。他亦曾提出不仅要了解中国今日地理、国朝疆域、海陆边界以对中国地理有总体的把握,还需掌握地球全体及外国名山大川、重要都会、港口险要、人种风俗和宗教政体以对世界有全面的认识,最终全面启发国民爱国、爱种、爱教之心。张之洞的保国思路是在对传统中国历史、文化风貌极具自信的基础上展开的,他自信通过中外种种的对比一定能激发起仁人志士爱国爱种爱教之心,进而有保国保种保教之行。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观点来分析,张之洞的国族建构主张实为一种“官方民族主义”,是对“民族与王朝制的刻意融合”[9]。国家通过由上至下推进的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使得“包含多样性和地方性的文化趋于同质化”[10]。而张之洞试图在精神上捍卫国家主权的努力未能攥住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千年根基。他抓住的礼教早已不再是“最优的人际关系”[11]55,也不能代表孔教与儒学的思想精华,只留下极不适应新社会状况的旧印象,因而以独尊孔教为主核的保国理念也就迅速地淹没于时代浪潮之中。
二、作为国魂的“宗教”:康有为的华族认同与保教设计
“华族”是康有为用来概括共同生活于中国的满、汉、蒙、回、藏人的总称,也称“中华国人”“中国族”。康有为的华族观念摆脱了张之洞式的对一姓主族帝国的维护,他从语言、宗教、历史等多角度论证了各族有通行共用的语言、风俗和文字,以此为基础他主张各族“熔铸而合同”来共建中华,这已初步接近复合性中华民族概念。
从语言名称看,中国曾被有些国家蔑称为“支那”,但中国传统经典中并无“支那”一词。康有为在考据《北魏书·文帝志》《官氏志》后指出,“支那”应是古代“诸夏”或“诸华”的变音,也即“中华”。华族是自古有之的“因于外称,顺乎文史”[12]的概念沿袭,进而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华族”的历史真实性自然也就从语言名称上获得佐证。从风俗看,“合于中国之礼者,则进而谓之中国;不合于中国之礼者,则谓之夷狄”,中国古代多以对儒家正统的熟悉、尊奉程度作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标志,而汉族以外的其他王权出于交流交往的需要也积极学习中华的语言文字、礼俗服器,即康有为所指的“华俗”。正是这种风俗上的交流与仿效加深了夷夏融合程度,使得大地万国没有纯为一族者。正基于此,康有为强调应当效仿欧美注重民族之治,主张“京师设辽、蒙、回、藏四部大臣,而于辽、蒙、回、藏多设大官重镇以经营之,而多开校导以华俗”,而蒙、藏尤需注意,当“教以中华之文字言语,导之以中华礼俗服器,俾风同道一,人民生亲爱之心,交兵无窒碍之事”,通过多种统合语言政俗的手段达成人读华书、人习华俗的局面,继而“爱国统一之心自生”[13]。
“华俗”中的精粹部分在康有为看来即是孔教。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孔教不仅是“汉族之国粹荣华”,还是“中国之正统”,正是孔教发挥着“铸范吾国数千年人民、风俗、国政”[14]115的功能。康有为将这样的血脉文化作为凝聚华族向心力以应对国际国内挑战的抓手,通过弘扬孔道的保教策略将孔教塑造为人心之归宿,以养人身之习安。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将其师保教以保华族的用心凝练为“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15]367。用今天的学术语言表达,即是:康有为将弘扬孔教的一系列措施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
“礼典、法律、风俗,皆为孔教……有夫妇而祀祖先者,皆为孔教。”[14]348在贴近现世的程度上孔教优于佛教,在尊天爱人的程度上孔教以敬天法祖的报恩精神优于基督教。如果说在张之洞那里孔教是纲常名教的代名词尚具有教化之义,那么在康有为看来,孔教只是名副其实的宗教。他不认同孔教无神的说法,认为自日本引入的“宗教”是以狭隘的有神概念作为判定宗教的标准,而孔教以五行演化为根本元素和原则,“木神则仁,火神则义,土神则信,金神则礼,水神则智也”[16],“宗教”观念显然无法囊括优于神道教的人道教——孔教。总的来说,康有为话语体系中的孔教是以孔子为教主,以天道五行为神学观念,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依据,并演化出一系列尊天事地、明命鬼神礼仪制度的有神的宗教。但在康有为看来极具优越性的孔教,其现实境遇并不乐观。“废弃经传,停孔子之丁祭,即间存之,亦废去拜跪矣。甚至举国旧俗,不问美恶,皆破弃而无所存。民无所从,教无所依,上无所畏于天神,中无所尊夫教主,下无所敬夫长上,纪纲扫地,礼教土苴。”[14]317从民间到官方,孔教皆呈衰颓之态。在宗教生态中,孔教的生存空间同时受到外来宗教与本地民间信仰的挤压。“善堂林立,广为施济,盖真行孔之仁道者,惟未正定一尊。专崇孔子,又未专明孔子之学。遂若善堂仅为庶人工商而设,而深山愚氓,几徒知关帝、文昌,而忘其有孔子……外国自传其教,遍满全球,近且深入中土。”[15]268基督教及其在华教会不仅抢夺了孔教的宗教市场,还引发大量教案耗费国力财力。民间又有善堂、淫祀林立,民众仅知关帝、文昌而不知孔子。这都令康有为产生华族瑰宝几欲消失殆尽的危机感,最终推动他提出官方与民间、教与学二重架构的保教设计,意图通过保教来强化民众的华族认同。
在官方“教”的层面,康有为主张皇家恢复祭天祀孔之仪与帝王临雍之礼,并以国家政令形式在全国立孔庙,如其追随者陈焕章所言:“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兰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17]他主张恢复庚子拜经传统,“每逢庚子日大会,会中士夫衿带陈经行礼,诵经一掌,以昭尊敬。其每旬庚日,皆为小会,听人士举行”[15]268。在官方“学”的层面,康有为以治教分途为基本原则,提出设立专职的“教部”,县设教逾,府设宗师,省设大宗师,国设教务院总长;他主张另立“道学”一科,广征孔道大儒,授予官职并散发到州、县、乡中讲明孔子之道,同时在南洋诸岛建学堂设教官以传孔子之道,乡市安排公举士人为讲生,为乡市男女宣讲六经、四书及孔子忠恕仁爱之道,具体安排仿照庚子拜经制度施行。而在民间的保教设计中“教”的成分明显多于“学”,这是康有为出于智性水平的刻意规划。基于对孔教范围的框定(有夫妇而祀祖先),康有为几乎将全体华族都列为孔教信徒,因而主张民众免费登记入孔教籍。根据入籍实际情况,“各乡籍满百数十人者,皆立庙祀天,以孔子配。设讲生,以来复日男女长幼皆沐浴,诣庙跪拜行礼,或手经一卷自诵之,听讲生说经一章。有歌者合歌孔子大成乐歌以释菜,或兼香花清酒,皆从旧俗”[14]369。
通观康有为以强化华族认同为旨归的保教主张可以看出,他完全将孔教放置在宗教视域中作功能性考察。他借用孔教为宗教符号来综合表现华族的社会精神气质、道德、美学风格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与秩序观念。借用孔教,康有为希望在华族中“建立强有力的、普遍的和持续长久的情绪及动机,依靠形成有关存在的普遍秩序的概念并给这些概念披上实在性的外衣”,以使“这些情绪和动机看上去具有独特的真实性”[18]111。五行的神格化是他为孔教强行穿上的神学外衣,祭天配孔诸仪是他塑造华族共同世界图景的宗教仪式和手段。他试图凭借所建立的种种“象征”在民族之间强化一种共同的情绪及公共行为,即华族认同。从结果上看,康有为的设计失败了,但孔教会却真实地建立起来了。1913年9月24日在曲阜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海外的孔教组织也紧密配合着国内的保教活动。在一定时期内,孔教曾实实在在地担当起塑造华族认同的责任,抛开价值评判,康有为的保教设计也确实在国内国际视界中凝练出一种孔教样态的中国国魂。而他的学生和批判者梁启超在短暂地追随保教后便转而寻求保种的精神原动力,无疑能恰当地反映新旧转折之际新知识分子的救国新动向。
三、作为国性的“德教”: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建构与保种精神
梁启超在思想史上被定位为“中华民族”概念的首创者。他对民族与民族主义有着精到的阐述,而其思想体系中构成中华民族独立性的理论支撑在于:民族意识(即中国民众在接触异种文化枢系时“对他而自觉为我”的基本精神)的发明。梁启超正是从这种“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入手来论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意识的初次自觉在自名为“诸夏”之时。梁启超将“诸夏”名称的确立理解为大禹时代大洪水导致的结果,是部落相接时“自觉为我”意识的初现。此后“诸夏一体”的观念便深入人心,且经过“若干异分子之结合醇化”后文化内容也不断丰富,中华民族遂融合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的一大民族。
首先,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是各族进化、退化、合并及迁徙的结果,且多元中亦有骨干。梁启超从地理空间上将中华民族分为八大民族分布区:诸夏(以河南、山东为主)、荆吴(湖北、安徽等)、东夷(山东濒海半岛等)、苗蛮(云、贵、广西等)、百越(浙、闽、粤)、氐羌(川、陕、甘)、群狄(山西、直隶大部、河南、山东)、群貊(辽东及直隶北部)。这八大民族全部或大部“今已完全消纳于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以“诸夏同化力”为首要因素,汉族以其强大的同化力融合吸收别族而共成中华民族,期间经历了千百年来由政治上征服转变为文化上征服的漫长过程,这也反映出汉族即梁启超所指的中华民族之“骨干”。
其次,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经历了语言、婚姻、宗教等多方面的交流融合。在语言上,汉族的象形文字优于其他民族的语言体系因而成为传达思想的通用工具,在书同文的条件下促进了不可分离之大民族的形成;同姓不婚制度排斥血族婚姻而强化了异族杂婚,加速了民族间融合;儒教庞大的思想体系也被梁启超赋予了天然优越性,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具有极强吸引力。且儒家思想中的天下观念具有较强包容性,其伴生的“无外”原则“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界限清晰、斩钉截铁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边界”[11]34。这使中华民族与中国不仅成为地理事实,还是社会事实,强化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承认度。
中华民族能立于世界,亦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15]533,这种独立精神即是“国性”。国性是“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其信条具有大威德……镕冶全国民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19]400。国性涵濡且内化于百姓日用之间,可以助长而不可创造,可以改良而不可蔑弃。国性包含国语、国教和国俗,当国性衰落时,无一人不怀疑,无一人不轻侮,无一人不厌弃。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之精神正在遭遇空前的认同危机,于是“淬厉其良而助长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便成为培养、改良国性以维护中华民族之独特民族精神的方法导向。其后,“国教”成为其淬厉的主要对象之一。
梁启超的宗教观受近代宗教学理论影响,对宗教功能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在建构中华民族独立精神时,他主要强调宗教与政治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宗教对民族气质的塑造功能。梁启超直言宗教为政治的附属物,无宗教则无统一。在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上,宗教是类似军队的存在,是在人的自由之上悬设一个无形之物以使其精神结集于一体,这种类似于军队精神的宗教精神已经在野蛮时代发挥了极强大的统一民志的功能。而当今世界则是将宗教与种族相结合共同塑造独立的统一国家的联合。宗教在塑造民族气质方面是“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15]11。中华民族宗教精神的一大特性在于重报恩精神,报恩是伦常名教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国宗教创立教义、固定教俗、确立教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之本原,梁启超进一步将目光溯源至孔教塑造民族特性的功能上来。
孔教精粗并举、体用兼备,且敷教在宽,并无宗教上的排他性,最适宜用来对国民进行伦理教化。受康有为影响,梁启超也认同多立孔庙,并将孔庙塑造为中国的教堂,提出模仿基督教的礼拜日于教堂顶礼听讲的仪式设计,使民众涵濡于孔教经义之中以去暴就良。他要求时务学堂的肄业诸生应承担起传播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的责任,一切行动皆以昌明圣教为主。此外,梁启超还极为重视孔教在海外的传播。他号召海外华人在繁华闹市中倡义募捐以建孔庙,并“立主陈器,使华工每值西人礼拜日,咸诣堂瞻仰拜竭,并听讲圣经大义,然后安息”,这不仅能使民众日益向善,还能使“西人睹此威仪,沾此教泽,亦当肃然起敬,无敢相慢矣”[20]。
但是,梁启超的保教热情是极短暂的,在接触严复思想后他自称如千年闷葫芦被严复寥寥数语揭破,意识到“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15]579,孔教不可保也不必保,且所保之教早已脱离孔教原貌。梁启超指出,历史上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不胜枚举,“贱儒务曲学以阿世,君相托教旨以愚民”,这皆使得孔学的真面目湮没不见。归根结底,提倡保教者有四弊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15]676孔教在本质上是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孔教精神多见长于实行而非信仰,此其一;宗教发端于情感,以“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为精神鼓动进而产生神秘的宗教体验,而孔教并无这种情感,此其二;宗教有其自然消亡论,而孔教亦有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桎梏存在。“在健全之社会,此不顺应之一部分常能缘自然淘汰之作用,渐渐蜕减,不甚假于人力”[19]400,此其三;梁启超认同政教分离模式,保教一定能使教强,然而教强并不利于国家发展,且立教将使人的心思才力为教治所束缚,一切“专门学”皆应脱离宗教的羁绊才能获得自由的良性发展,此其四。
在否定保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后,梁启超转而寻找孔教土壤中有益于提升中华民族整体国性水平的德教营养,并“以德教为己任”来“淬厉孔教”。梁启超指出,儒学传统实为一种以伦理规范为底色的自我超越之学,其中蕴含着浓重的诸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私人对私人的道德规范,而缺乏西方包含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的私人对团体的伦理价值,因此急需发展一种新道德来塑造国民的保种意识,即养群德。梁启超的群德理论建基于群居状态下对公德与私德的判分,私德是有助于个人道德完善的价值观,是立人的根本;公德是促进群体凝聚力的价值观,是立国的根本。但在小己之私利与大群之公义的价值选择上,梁启超强调个人在群中对私人权利的让渡,即个人在“以己克己”式的克己复礼过程中对道义性私利的追求,孕育出以死利群的最高群德境界。
以死利群中包含着对死与不死的价值判断。不死者“一曰家族之食报,二曰名誉之遗传”,而孔教正是以名为教,积善有余庆与积恶有余殃是“不死”的名的因果报应,以此为奖惩机制来敦促个人“造善业”,使死灭的“吾辈之个体”转而以“名誉之遗传”的形式永存,个人也就能更加积极地团结、生活于和谐的群中。这是将以死利群的个人牺牲精神冠以集体自豪感的冠冕,通过价值赋予,内在的人性要求获得了外化表达。经过价值观上的设计,梁启超将孔教精神萃取为德教,强调德行修养对于当日中国生存下去的必要性,这种思想固然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也不失为一种高境界的思考。诚如格尔茨所说:“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是鲜明的,不仅是因为他们赞颂某种高尚的东西,而且因为他们谴责某种卑劣的东西。”[18]161梁启超注意到孔教中失去时效的价值因而对之进行理性的扬弃,而他的后来者们甚至走得更远。无论如何,以保教为抓手来塑造中华民族认同、获得民族建国自由的努力至此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点。
结 语
如果将张之洞视为晚清保教风潮的官方代表,那么康有为与梁启超则分别代表了新旧时代两种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的迥异态度。通过以他们为代表的各阶层、各身份知识精英的努力与活动,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逐渐明朗化。中华民族从狭隘的汉民族发展为满汉一体、五族共和,经历了从单民族到合诸族的转换后初步具有了多元一体的民族雏形。而无论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宗教都是三人思想体系内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工具。孔教作为一种宗教意味浓厚的家国思想的剪影,本身承载了厚重的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积淀,而中国新旧时代的转换亦能从张之洞到梁启超对待孔教的态度和他们借孔教以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方式、程度来获得一个侧面的展现。经过他们独尊孔教、复原孔教、淬厉孔教的剔除过程而塑造出属于中华民族独特民族精神的“共同过去”,直接促成了民族国家“混凝土式文化结构”[21]的形成。他们虽然走得不够远,但这种有益的探索却成为永久的历史标杆,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也需要更多这样的试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