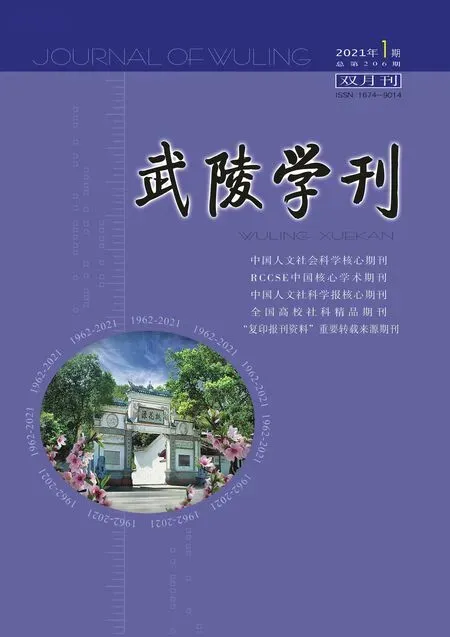战国秦汉时期的思想流变与汉初政治哲学的选择
2021-03-07袁宝龙
袁宝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战国时代的诸子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景致,其时学派林立,思想碰撞,蔚为壮观。儒、法、道、墨、阴阳、名、农、纵横诸学派之争鸣,皆试图基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来解构现实、阐释世界,为饱受乱世之苦的时人找寻破解之道。尽管诸说纷纭,其旨各异,但这一时期诸学派的发展普遍呈现出这样一个总体特征:既重理论探索,亦重现实实践,即除理论阐释外,也从现实层面来探索和想象理想的治国之道。秦的统一终结了诸说并存的局面,这既是秦人尚法的现实映射,也是诸子争鸣、思想交汇的必然趋势。秦之速亡以及西汉继之而起,又使得思想层面再次面临诸家并作的可能。不过在汉初政治哲学的自然选择过程中,风云一时的儒法两家皆因种种原因未能入围,黄老之学在各方面均表现出一统汉初的必然性,“黄老无为”时代由此开启。
一、战国时代的诸子争鸣与秦的统一
孟子与荀子是战国时代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二人对儒家精神的继承与创新,反映出儒学对理论的终极思考以及对现实的关注与回归,战国也因此成为儒学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孟子与荀子均在传承儒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阐发儒学的精神内涵,映射出久经乱世的民众对于清平盛世的期望与向往。两人的诸多观点,既有相似,又存差异,大致折射出战国儒学的总体发展脉络。
如何看待天,以及如何看待三代以来的天命观,是战国时期各学派孜孜不倦、努力探寻的终极问题。孟子讲天命观,他始终认为天是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神秘力量,孟子称:“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1]作为哲人的孟子认同天的强大,同时又认为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顺应天意。不过总的来说,孟子未能超越天命观的基本范畴。面临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局面,孟子亦不再仅仅停留于指责层面,而是尝试寻找破解现实矛盾的良方。孟子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欲达此境,必须放眼人寰,建立超乎诸国之上的视野,超越战国诸雄的国家局限,进而开启了战国儒学的思想转换[2]。这一点对于战国儒家乃至诸子学说皆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相比之下,此后的荀子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天命理念的重建。荀子对于天有着与既往理论家们完全不同的理解,经其阐释过的天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对此,侯外庐指出:“儒家的天道观到了荀子手里就变了质,即由有意志的天变为自然的天、物质的天。……荀子扬弃了道家的神秘的‘道’,撷取了其中的自然观点,因此他所谓的‘天’不是孔孟的有意志的天,而是自然的天,不是道家观念的天,而是物质的天。”[3]477-478荀子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4]362,把世上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比之天地之变与阴阳之易,这其实就是把天的主观意识排除在外。荀子试图超脱于天命之外来看待宇宙,即“制天命而用之”,表现出鲜明的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特征。换言之,荀子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春秋以来遗存的神学政治全面消解,激励当政者励精图治,以期人可胜天。
除此之外,荀子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创建了万物轮回的循环宇宙观。荀子称:“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4]569与孔子怀念遥远的周公时代不同,荀子以轮回循环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承认王朝更替的合理性,儒学的政治倾向因此从因循守旧转为革故鼎新,这使儒学成为新兴王朝官方政治哲学的机率大增。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更多地存在于理论层面,且二者仍能于思想抗争中追求平衡,形成均势,那么,进入战国以后,双方的争论更加直白激烈,这种争论对现实的影响也更加明显。战国诸雄皆争于力气,礼乐精神与先王之道在政治哲学层面渐成明日黄花,被不断边缘化。法家理念开始贯彻于国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消长进退形势无疑由群雄逐鹿的政治现实所决定。吕思勉指出:“法家精义,在于释情而任法。……法家之义,则全无感情,一准诸法。法之所在,丝毫不容出入。看似不能曲当,实则合全局,通前后而观之,必能大剂于平也。……法家贵综核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之情形。执旧说而谬以为是,法家所不取也。职是故,法家恒主张变法。”[5]战国七雄均试图通过变革旧制在诸国争夺中占据上峰,魏文侯用李悝变法,首开战国变法之先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行之魏国,国以富强”[6]1124-1125,魏国因变法率先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从此以后,楚、齐、韩、秦诸国竞相效仿,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由此开启。李悝成为法家思想的重要开创者,所撰写的《法经》影响至为深远,至汉初犹为萧何所看重。
亦是从李悝变法开始,政治现实层面的儒法之争以极端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双方观点差异之剧使得彼此矛盾几无调和的可能。然而,由于二者在现实回报上的巨大差异,胜负的天平迅速向法家倾斜。这一结果决定于当时的历史现实,也可以说诸国变法的风潮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除儒、法以外,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正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者,其所谓“道”,意指宇宙中的最高原则。道家的思想是一切从“道”,强调万事万物皆应顺应自然。而道家学派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追寻宇宙中的“大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7]62-63关于“道”的形象形状,老子如是描述:“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7]31-32意即“道”似物而非物,有形而无形,象征着宇宙中最为广博的概念。中国古代向来对“天道”极为重视,只不过《老子》更明确地强调了先天地而存在的“道”的优先意味,把原本与具体现象解释相关的“天道”与“阴阳”变成了富有哲理意味的思想,并以此现象笼罩和涵盖一切[8]。战国时期的庄子进一步发展了“道”的概念,庄子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9]213,又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9]350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哲学表现出强烈的思辨性特征,往往于同中求异,异处见同,如老子称“强大处下,柔弱处上”[7]185,又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7]187又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人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7]120均表现出高明而玄妙至极的特征。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另一重要学派。据《墨子间诂·墨子传略》:“墨氏之学亡于秦季,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太史公述其父谈论六家之旨,尊儒而宗道,墨盖非其所喜。故《史记》捃采极博,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然则非徒世代緜邈,旧闻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时具存,史公实未尝详事校核,亦其疏也。”[10]可知秦季之时,墨学已然式微,然于春秋战国时期却有极大的影响力。“兼爱”为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墨子认为,乱世之所以出现,原因就在于缺乏彼此兼爱。墨子以当时的政治现实为证来阐明自身的理论:“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11]158墨子以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11]159,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状态。此外,墨家认为天有意志,且为万事万物之主宰。墨家亦有着强烈的神秘主义倾向,主张明鬼。以务实清醒著称的墨家有尚鬼的倾向,看似矛盾,实则有其必然性,其原因在于,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墨家需要一种信仰力量作为超出自己狭隘经验范围的精神支撑[12]50-60。
此外,战国阴阳家亦对世界的本原做出深刻思考。战国时期齐人邹衍为先秦阴阳家的集大成之人,史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13]1369。以邹衍为代表的战国阴阳家尝试运用五行的观点来解释世界,把金、木、水、火、土视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五德终始说的观念:“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13]2344邹衍的历史观具有多种因素,既有从天地未开到人世繁荣的进化论成分,又表现出循环论的成分。五德终始说关于周代火德已衰,必将有水德取而代之的说法,即在理论上论证了周之必亡,新圣将兴,符合战国诸侯对理论的需求[14]。五德终始说在秦始皇实现统一之业后,被吸纳进秦帝国的政治文化体系之内,光耀后世,影响深远。
战国的诸子争鸣成为《吕氏春秋》成书的现实前提。《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前夕的战国晚期,由秦相吕不韦依托门客编撰而成,“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13]2510。《汉书·艺文志》把《吕览》列为杂家学派,侯外庐同样认为,《吕氏春秋》“兼”“合”以前各派学说编集而成,为“兼听杂学”糅合而成[3]658。从吕门食客的身份构成以及书中表现的学术观点来看,此书确为多家学人集体创作而成,有着鲜明的“杂家”特征。元人陈皓称:“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15]由此可知,《吕氏春秋》成书的重要使命就是在诸说纷纭的时代背景下,把诸家之学熔于一炉,创造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价值准则,同时完成思想的统一,为即将实现统一的秦王朝提供一套新的政治哲学体系。
李泽厚先生认为,战国时期,儒家为各思潮、学派合流之主导力量,有其实在的社会历史基础。《吕氏春秋》试图实现这种合流趋势的统一,为即将代周而兴、建立统一稳定的新王朝作出理论建树[12]145。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吕氏春秋》对于先秦诸子之学皆有所吸收,其中也包括“大一统”理念以及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大九州”等理论,这些理论都在秦汉时代气势恢宏的“大一统”文化中有所体现。
概而言之,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感慨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对“大一统”局面的热切渴望。此后经孟子、荀子等人的阐释发展,儒家“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力日益显著,至战国晚期已经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期盼。邹衍创建的“五德终始说”,表明历史发展、王朝更替周而复始的动态特征,为王朝更迭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前述流派的几种思想精髓皆为《吕氏春秋》吸纳,并在《吕氏春秋》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辉。
二、秦汉之际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格局,帝制时代的政治思想也因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豪迈气息。回溯秦人渐兴历程,始为边陲小邦,经数百年之发展演进,卒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实多获益于商鞅入秦带来的法家思想。而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贯彻始终乃至改易秦的国运,与秦人宗法势力相对较弱存在因果关系,文化底蕴相对不足的现实也有利于秦帝国统治者以大开大阖的态势寻找新的政治哲学与统治思想,无所羁绊。不过,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经数百年之洗礼浸润,对法家思想的恪守已经成为秦人的群体信仰,因此新哲学的建构,必然无法真正逃脱法家思想的理论框架。
然而秦始皇身为千古一帝,超迈绝伦,独步古今,他已然不再满足于在传统法家体系下因循守旧,而是试图基于天下一统的现实形势,进行新的开拓与创造。刘泽华指出,秦始皇自称“皇帝”,突出的是理性、创造性和社会的至上性。此外,又称“天子”,则更多地彰显为神性特质。秦始皇的帝王专制主义理念集先秦思想文化之大成,并与权力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秦代神圣至上的皇帝观念[16]。其建构,则是以秦人一以贯之的法家思想为母体,复吸纳了先秦以降卓著的政治文化成就精炼凝聚而成。从这一点来看,秦人虽未直接采用《吕氏春秋》的理论成果,但在建构过程中借用了其引领精神与基本范式,对诸家之学表现出接纳包容的态势。
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儒学始有机会首次上升到国家官方思想层面。然其地位自不能与法家同日而语,焚书坑儒事件又使得儒家突遭变故,自此一蹶不振。终秦之世,法家的统治地位从未受到实质性的威胁。
相比于秦代,西汉以布衣卿相开国,其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也表现出与秦时迥然不同的差异。刘邦及其追随者多出身市井,因此刘汉政权在政治哲学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开放性与盲目性。秦汉之际舍法家之外,可供汉室君臣遴选取舍的政治思想与治国理念范围极广,不一而足,刘邦君臣也确实做出了诸多尝试。史称:“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陆贾造《新语》。”[6]81刘邦的此种安排体现了他对多种理念的开放性原则,在这些出身不同、学识取向有异之人的共同努力下,汉代帝国文化制度的初步建构就此完成。
可以说,汉初在政治哲学的选取上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取向,即以能够在客观上使汉代统治稳定长久为第一要义。然而以此为准绳,真正可以作为新文化核心精髓的对象依然未出儒、法二途,这也是经过声势浩大的诸子争鸣过后,最为成熟、最具体系性的两大流派。于汉初君臣而言,对法家最直接的历史经验是以尚法著称的秦帝国二世而亡,汉初社会对于法家思想的最初印象皆源于此。相比之下,于秦时经历过大幅起落的儒家思想则在汉初表现出复苏的迹象,受到统治者的格外青睐。儒法两家于秦汉之际升降起落的个中原因在于,在秦朝政治哲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家被视为秦亡主因,那么理念与之相左的儒家思想的合理性自然因此得到肯定。
以高帝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者在建基前后对于儒学的态度有着明显转变。刘邦微时,“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13]342-343。郦食其之初见沛公,便遇到重重阻力:“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13]2692直到郦食其责以大义,进以奇谋,刘邦始以礼待之。不过,此时刘邦的态度转变应更多归因于郦食其的个人韬略,而非刘邦对儒学态度的总体转变。即便郦食其本人,最终也如弃子一般以身殉汉王基业。刘邦对儒学态度的真正转向其实是在汉朝建基之后,在此过程中陆贾与叔孙通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大儒陆贾是汉初儒学最主要的宣扬者与倡导者:“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3]2699陆贾得以于高帝前称《诗》《书》,有赖于此前立下的烜赫勋业,其于汉初群臣中的地位非郦食其所能望其项背。纵然如此,真正引发刘邦警觉乃至面露惭色的,还是因为他提及秦亡汉兴之道,切中高帝的夙寐之思。这一时期刘邦于儒学的态度有所转变,不过总的来说仍然基于战略层面,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陆贾称:“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17]17表现出鲜明的抑法兴儒态度,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刘邦对于儒法二学的认知与判断。
刘邦之所谓“居马上而得天下安事《诗》《书》”固为率尔之言,但也显示出刘邦集团取得天下后,并未真正做好治理天下的思想准备。陆贾就是在此种现实面前,提出了“逆取”得天下而“顺守”治天下的主张。欲达此目的,就必须改变、优化现实的政治理念与权力结构,革易对儒生的态度,起用儒生以实现王统与教统的结合[18]。陆贾对刘邦的影响自然不容忽视,不过儒家思想真正触动刘邦心弦的是叔孙通制礼事件。汉五年(前202年),时汉已得天下,“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两年后,长乐宫建成之际,这套礼仪首度展现于人主座前,时文武百官入朝,各居其位,以待至尊,“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3]2722-2723如果说在此前与儒学的诸次交集中,高帝刘邦始终未能摆脱现实性、功利性的窠臼,那这一次叔孙通制礼则在很大程度上使刘邦真切地意识到儒家礼乐所具备的强大力量,并为此深感震撼。叔孙通以特有的灵通与机敏,适时巧妙地将儒家理论学说以实用的方式表现出来,使汉初君臣直观地感受到儒家礼制的独特功效,无疑为儒学的兴起提供了宝贵的契机[19]。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在方经秦代苛政的汉初社会,主张仁政、民本的儒家思想越发为时人怀念,在这种朴素而普遍的公共情感的感召和陆贾、叔孙通的共同努力下,儒学的影响力日益壮大。
汉初儒家思想在国家政治层面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选择上,西汉一改秦人以天下为郡县的旧制,转而引入与秦朝郡县制迥异的分封制。地方行政制度的这种变革,直接目的自然是惩于秦以孤立无援而亡的教训,此外也与时人的怀旧思想有关。吕思勉先生指出:“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业已不可复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于是有汉初之封建。”[20]如果说异姓王的分封是迫于创建基业后分割既得成果的现实压力,那么继之而起的同姓王分封则在表明汉初确有试图向周代回归的倾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乐精神与儒学思想在社会各层面的旺盛生命力。诚然,汉初分封,土地广阔、百官如朝廷、王国治民实为战国历史的再版[21]。也就是说,西汉所继承的是楚制而非周制,汉之分封与周代分封的实质相去甚远。不过无论如何,至少汉代分封从其基本思想与精神意旨上,符合周代精神与孔孟之学,具有一定的儒学倾向,也可以映射出当时儒学理念的影响力之大。
不过这种具有强烈复古之意的政治举措,在构想之初就已注定败局,其失败不仅仅是由于集权帝国体制与郡国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更重要的原因或在于重行分封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时人对汉代统治者皇权合理性的思考与置疑。叔孙通制礼,是儒家思想在现实功用上的又一次体现,它在形式上使刘邦具备了天子权威,但仍然未在理论层面合理地解释刘汉皇权的合理性。出身市井的刘氏缘何可以一如当年周天子一样分封诸国?这种思考自汉初以来,延续数世,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得以在公羊学理论的框架下得到解释。然而总的来说,汉初的社会秩序已经初步建立,尽管皇权合理性的问题未能迅速解决,但是当时天下方经大乱,丧败之余,百废待兴,理论困惑的急迫性自然让位于更具现实意义的经济生活,故于高惠之时,汉室的皇权问题几未受到实质性的质疑问难。
如前所述,汉惩亡秦之弊,表现出一定亲儒远法的学术倾向,不过在汉初官方统治哲学的取舍建构中,法家依然表现出不让儒家的强劲态势。其中原因大致如下:首先,尽管叔孙通自称儒家之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而汉初百废待兴,从国家治理与行政管理的实效来看法家思想无疑更胜一筹;其次,尽管儒学在秦时上升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但其影响力仍然远不及法家。故秦时法家人才之盛远胜儒家,故经历秦末战乱后,具有法家背景与吏治才干之人便成为汉初官吏的重要来源。
以汉相萧何为例,他的身上就有着明显的法治倾向。作为秦王朝一名精明能干的县吏,萧何精通秦的法律条文。他所秉承的思想准则,正是秦时的法治思想,这是他作为前朝一名“文无害”的县主吏习之有素的法治精神。而萧何作为标志性人物,表明汉初在统治精神上继承了秦朝尚法的传统[22]。可以说,汉初政权的稳定正是建立在法制初建的基础之上,“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裙后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6]1096。此与前述“萧何次律令”所指当为一事。曾为秦吏的萧何,其所作的“九章律”必然深受秦法的影响,“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23]。此已明言,萧何的《九章律》远效《法经》,近承秦律,这也是汉承秦制在律法层面的现实体现。不过,由于汉初强劲的“过秦”风潮和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纯粹的法家之盛如昙花一现,旋即终结。
三、“黄老”时代开启的理论逻辑与必然因素
秦急政而亡,刘邦于秦末战乱与楚汉争雄中最终获胜,实现了秦帝国之后的再度统一,气势恢宏的两汉时代由此发端。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稳定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首个巅峰。汉初的布衣卿相自无任何统治经验可言,故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上多因袭秦制,只是根据现实需求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开拓与发展。随着西汉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政治经济形势逐步稳定,顶层设计不断完满,这种开拓与发展开始以更为豪迈的姿态显现出来。
汉初天下,方值秦末战乱与楚汉相争的战火荼毒之余,山河破碎,千疮百孔,如何在这片废墟之中巩固基业,成为刘邦集团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3]1417《汉书·食货志》亦云:“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6]1127当此之时,休养生息实为汉初社会的第一要务。这种强烈又迫切的现实需求成为推动黄老之术走上最高政治舞台的强大动力。也可以说,汉初对黄老政治的选择是对现实问题的及时回应,代表着汉初统治集团的集体意愿。
一般认为,黄老政治的最终确立完成于萧规曹随之际。然而,在此之前,与民休息的精神已经在政策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据《汉书·食货志》,“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6]1127,文帝时期一度免除田租十二年,十五税一的政策于景帝时期又进化为三十税一,可以说整个西汉前期,“轻徭薄赋”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不过由于累年战火,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非短期内可以实现,汉初君臣亦已经意识到这一政策的长期性,这种主观自觉成为“黄老无为”精神确立的重要前提。萧何为相多年后去世,曹参继之为相,此度萧曹二人的权杖交接也标志着汉初政治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为汉相之前,曹参曾为齐国相,以盖公善黄老术,乃与面谈,盖公为言黄老,参从之,以其术治国,齐民大悦。“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13]2028-2029
萧何死后,曹参为相,原本仅以齐国为施政对象的黄老之术也因曹参政治地位的提升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汉代黄老无为的时代就此开启,并深刻影响了西汉前期的政治与文化格局。“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却。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13]2029萧规曹随,守而勿失,民以清净。黄老之术也确实完美地契合当时与民休息的需求:“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6]1127可以说,汉初政治无力与民不聊生的惨淡局面,使社会又退回到不同领域未加分化的原生性形态之中,这就为主张“清静无为”思想的黄老之学提供了最大的生存空间[24]。除现实因素以外,黄老之学得以成为统治哲学,亦可于学术层面给出合理性的解释。
事实上,前文已述,战国晚期诸子合流的迹象已经较为明显。然秦尚法,秦始皇实现统一后,以强大的行政手段独尊法术,学术层面诸家并峙的历史自此终结。秦之速亡,与秦始皇此举不无关系。与此相比,毫无文化积淀的西汉王朝则自然而然地顺应了这一潮流,一如《吕氏春秋》是战国晚期诸学合流的产物,汉初的这一产物便是“黄老”之学,二者意旨相近,但结局却相差远矣。
在休养生息的时代主旋律下,纯以法家精神为引领的秦代政治哲学几无立足之基,其为“黄老”所取代,实为历史之必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黄老政治与秦代政治二者的关系极为复杂,既有显著差异又有内在联系。因此之故,黄老之学在兴汉功臣群体内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陆贾称:“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17]59《汉书·陈平传》:“(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6]2038张良曾自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13]2048亦可见其受道家思想影响颇深。
罗新指出,黄老之学,正是一种杂糅了诸种学说而自成体系的新的统治学说。阴阳五行、三晋法家、楚国的老子清静思想等,都可以在黄老之术中找到印迹,黄老所关注的并非抽象的哲学体系,而是治理国家、控御臣下的君人面南之术[22]。黄老之学既与法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那么可以说在黄老之学盛行的时代,法家并非真正式微,而是隐藏于黄老学说的外壳之内。金春峰进而指出,汉初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但其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其所纠正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但并未改变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25]。事实上,前述萧规曹随,固然表明曹参顺其自然的“无为”意旨,但同时也表明曹参执政时期肯定并延续了萧何时期以法家为主的理念,只不过秦代积极奋进的法家精神不断衰退变异,作为这种衰变成果的黄老之术则取代儒家与法家,成为汉初的官方统治思想。
黄老之术能够凌驾于儒法之上大行其道,有其历史因素:一方面,黄老清静无为的意旨表明了统治集团休养生息的决心,藉此恢复国力;另一方面,作为统一的集权国家,依然要依赖法家思想进行管理运转。所以兼具前述两个特征的黄老之学被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黄老之学在兴盛之初就已经注定其只是历史进程中的过客而已,这种历史造就的鼎盛必然不足以支撑其久盛不衰,毕竟汉初百废待举的现实总有改变之日,与秦代法家相比,汉初的黄老之学更像是衔接两种政治哲学嬗代的过渡状态。
总而言之,黄老治国论表现出综合百家之势,对法家思想的吸纳使其截然不同于老庄的意旨,可以说这是黄老道家为适应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环境以及列国变法图强的社会需要而做出的理论调适,丰富了道家治国论的理论形态,是先秦道家治国论的新阶段、新形态[26]。黄老之术除了恢复国力,带来现实回报,同时也为学术思想的复苏与争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6]90,进一步为诸家学派的复苏繁盛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各种思潮自此开始了野蛮成长、自由发展的历史。我们不能忽略这种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对于汉初学术复兴的巨大促进作用,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潜藏于表层之下的儒学在与其他思想的交汇融合中进一步完善自身,静静地期待云开月明的历史时刻。
可以说,秦王朝首开君主集权官僚制帝国之先声,汉人踵其后,承其精神,集其制度规章大成,遂得开创旷古未有之盛世。总的来说,汉代依然坚持政治、经济大一统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经秦帝国之努力,大一统已经在实践层面臻于成熟。秦人以二世而亡,时人多归罪于严刑峻法之故,汉虽一承秦制,但仍在基本的治国理念层面力求谨慎,在总结周秦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两汉统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实,努力寻求法家以外的理论选项。从政治哲学以及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期都是休养生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因黄老无为的自身特征,故于意识形态层面并无统一的指导性纲领,诸家思想因此得于社会各个角度中漫延弥漫。
在此时期,“过秦”反思成为一时潮流,对于秦文化中既有的功利性予以纠正,成为必要且必须之事。贾谊称:“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篲,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箒,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27]97贾谊是汉初过秦的代表人物,他从“攻”与“守”两个角度分析秦之兴亡,得出了“攻守异势”的历史认识,进而提出了具体的仁义治国理论。此外,作为汉初“六经”的重要传人,“六经”经传内蕴的仁爱、礼治思想,成为贾谊“过秦”历史总结的思想基础[28]。如果说,秦末纷乱之际的社会现实作为加速秦亡的催化剂为刘邦等人所喜闻乐见,那么当此之时刘邦自己登基为帝,自然会备加留意前述种种威胁皇权安定的潜在危机。
如前所述,亦是在此一时期,高祖皇帝逐渐意识到儒学的巨大力量,也便开始尝试运用儒学的力量来化解这些社会的沉疴顽疾。作为汉初的启蒙家,陆贾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行哉?”[17]118贾谊则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27]215“孝”遂成为汉初统治者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汉帝国的文化氛围内,刘邦以下诸帝,皆对“孝”推崇备至,非但言传更加以身教:“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司马贞《索引》称:“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13]382汉文帝尤以孝著称,袁盎曾备称其孝行:“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远矣。”[6]2269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孝”这一伦理概念的强调,西汉政权才能够在黄老无为的文化气氛下实现伦理道德的重新书写与建构,“孝”可谓西汉政权实现自身文化体系建构中最为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环节。
可以说,正是以陆贾、贾谊为代表的汉初思想家、政治家,在着力批判秦以“威德”为核心之皇权政治,大力倡导法先圣、尚德行、施仁政等儒家治国理念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西汉时期所特别推崇的“孝德”便具有了保证其滋生、成长的肥沃土壤,并由此而逐渐形成、确立起来。秦之天下终得转变为汉之天下[29]。这不过是儒学精神在汉初社会悄然生发的一例,已然表露出儒学复盛的微弱光芒。诚然,任何一个领域中以任何形式开展的“有为”性尝试,都在根本原则上与黄老无为的精神意旨相背离。然而社会又是向前发展、始终求新的,这种背离由微而著乃至于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必然而无法避免的,“孝”观念的勃兴不过是汉初以来“有为”精神对“黄老无为”统治地位发起一轮又一轮侵袭的缩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