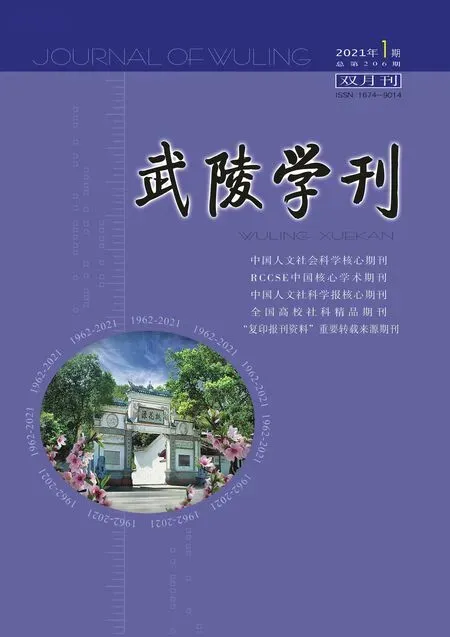《管子》“四维”德教思想探微
——基于《管子》道之本体论
2021-03-07黄少雄
黄少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前 言
《管子》一书为托名管仲之作,有关具体作者的讨论,今学者多认为非一人所作,或可视为包含部分齐稷下学士在内称为“管子学派”的群体所作。如张岱年所言:“《管子》一书是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依托管仲而写的著作的汇集,可称为‘管子学派’的著作,这些推崇管仲的学者可能亦是稷下学士,但只是稷下学者的一部分。”[1]《管子》虽非管仲亲作,但不可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管仲的思想。学者何隼认为:“盖《管子》者,战国秦汉间人所辑关于管仲治绩之载记,益以当时官吏之书奏论著而为之者也。”[2]耿振东则在典籍记载中寻求线索,认为“有历史迹象表明,管仲的思想学说在春秋时代就已经通过官守的方式在世代传播了……正是这个传播群体的存在,才奠定了战国管子学派顺利出现的历史基础”[3]28-29。
《管子》既详细记载了管仲执政齐国的政令、政策,又有大量管仲及齐桓公的问对与事迹,这些内容若没有可靠的材料作基础,恐怕很难做到记述准确、详实。基于此,徐汉昌认为:“书中典章政教、管子言行等史实之材料……可能有齐国政府之档案资料。讲思想之文字,可能小部分出于管仲之口,而为他人所记录,大部分则是稷下学者,就管仲言行与思想,引申发挥,依托于管仲。”[4]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合理推测,《管子》是“管子学派”在官府材料或口耳相传的原始材料基础上引申而来的,反映了管仲执政思想的治国之书。
推论《管子》和管仲之间关联性的价值在于,如果认为《管子》是管仲执政经验的文本性阐述,那么《管子》中所记载的执政思想就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空泛之论,而是经过齐国政治实践检验的治世良言。再结合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5]的史实,则《管子》所载的施政理念自然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
一、“四维”论为国家治理精神纲领
《管子》汇聚各家思想,其中“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6]。言“杂”不代表《管子》没有思想主旨,张岱年反对将《管子》简单视为各家言论的大杂烩,认为“《管子》基本上是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著作,具有自己的中心观点”[1]。
古今各家学者虽对《管子》各篇看法不一,但大都首重《牧民》等篇章,认为《牧民》等篇最能体现管仲的执政思想①。《牧民》开篇即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7]3,甚至“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7]11,提出了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四维”论。后人多从义理角度解读“四维”论,如宋人欧阳修称叹“四维”为“管生之能言也”,认为礼义廉耻是治国理民之根本,“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8]。但因《牧民》篇未进一步阐明“四维”的深刻内涵,解答何以将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的哲理基础,是故留下一桩千古“疑案”。唐人柳宗元就此怀疑“四维”立论的合理性,他认为廉耻在义理上属于“义”的范畴,因此廉耻不应与礼义相称,故言:“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9]应柳氏之论,林素英以关键词检索先秦典籍,发现确实少有将礼义廉耻并称,甚至少有廉耻并称者[10]。
依耿振东之见,学者多计较于《管子》论述的真伪之辩,拘泥于某些言论是否有悖圣训,却忽视了《管子》本为一有机整体的事实。若将托名者和托名之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从中抽取一些自成体系的治国之论,是一件有益于治术的事[3]668。
《管子》的德治思想包含层次分明的体系,其核心内容即是礼义廉耻之“四维”。礼义廉耻是儒家惯用的伦理术语,指人所特有的伦理德性。相较而言,儒家更强调道德的自觉,如杨婷总结儒家的道德特点为:“道德自觉是先秦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家国同构理想模式的逻辑起点,并如一根红线贯穿始终。”[11]与儒家所不同的是,《管子》解释礼义廉耻,曰“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7]11,更强调道德的社会规范性,颇有政令的味道。是故何隼称《管子》之道德教化为“以政作教”,“四维”即是此政教的“节目”。这种以“四维”为核心的政教一体模式,是《管子》“伦理政治之中心思想”“政治之理想的目标”[2]。何氏之言脱离了单纯从义理角度阐释“四维”的窠臼,将“四维”看作贯穿《管子》德政的立命根本,使“四维”具有了国家治理精神纲领的政治属性。
二、“四维”立论的道德本体论基础
“现实的政治统治和治理模式形形色色……但每一种模式都具有自己的哲学理念。”[12]回到柳宗元所提出的疑问,为何在《管子》中,廉耻得以与礼义“相抗”,并称“四维”呢?是随意为之,还是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哲理内涵?与先秦诸子相同的是,《管子》也从天道中寻求政治治理的形而上源头。“《管子》四篇”②是稷下黄老道家的代表作,其中的本体论思想多有与道家相通之处。《老子》中的道是不可言说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13]3。《管子》中的道亦是“虚其无形”[7]770的存在,“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言无形也”[7]760。《老子》之道于无名与有名的动态转变中,使道下降人间,与万物发生了联系,“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13]5。《管子》同样从道为万物生养根本的角度,赋予道“万物本体”的内涵,“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7]1182。然而与道家所不同的是,《管子》不偏重于道的形而上属性,而更强调道的形而下效用③,此一点颇与儒家相似。道之用即是生养万物,“《管子》四篇”称道的此种效用为“德”,认为唯有效仿道之德,方能体会道的精髓,“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知得以职道之精”[7]770。而政治,“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7]307,政扮演了施德以安定物命的角色。执政者率道而行,制定礼法制度,规定万物之命,使其各得其所,所谓“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7]563,“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7]5684。如此一来,道就与政治发生了联系,决定了政治的手段和目的。故唯有体道、悟道、用道的执政者方可称为人间的领袖,“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7]42。
《管子》亦从历史经验论证道与政治的联系,“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7]44。上古君王中,《管子》尤其重视尧舜、桀纣的兴亡教训。尧舜“非生而理也”,桀纣“非生而乱也”[7]472。他们之所以功业不同,在于桀纣“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7]1172,失却道生养之意,以故遭天道委弃,身死国灭,“桀、纣,天之所违也,故虽地大民众,犹之困辱而死亡也”[7]1186。《管子》以权威化的天道解释历史规律的观念,加强了道和政治的联系,为执政者率道而行的天赋责任平添了警惕和迫切的意味。
道虽无言,但在天地之间有其表象,此表象大略谓之“阴阳”,细分谓之“四时”,是故《管子·四时》曰:“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7]838在《管子》看来,阴阳四时等自然现象是古今不变的“常道”,“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7]21。此“常道”维系天地运行有序,“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7]1168。《管子》进一步将阴阳四时之“常道”扩展为万物皆备的属性规定,“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7]246,在此逻辑下,执政者欲率道而理万物则必然要以天地为纲。
是故《管子》在不同篇章中多次强调执政者应象法“四时”,“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日月,佐于四时”[7]126,“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7]2,“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7]837-838。天地既以“四时”为“维”,人事自然也应有其“四维”,所谓“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地莫之载则地以沉矣……又况于人”[7]799?故曰:“守国之度,在饰四维。”[7]2可知,“四维”论的提出是《管子》天地之道与政治理论一以贯之的必然产物。
林素英认为,宋人欧阳修称“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显然将“四维”区分为攸关主体和客体的两部分[10]。此种说法颇符合《管子》阴阳两视的辨证思想。《管子》认为在一阴一阳之中蕴含天道,“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遵循这种阴阳变化之理可以“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7]886。是故《管子》将政策亦区分为阴阳两端,所谓“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7]855。德与刑,一则注重积极引导,一则注重消极防范,二者既相区别,又应和合,以共同协调政事。
既然“四维”是天之“四时”在人事的映射,刑德为“四时之合”[7]838,则“四维”亦应蕴含积极和消极的阴阳之道。“四维”中礼义同源,“义出乎理,理因乎宜”[7]770,“义”源自某种恰如其分之理,顺应此理即是顺从道,“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7]557。“礼”则是义之具体化,“礼出乎义”,“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7]770,是一种制度性呈现。礼、义同出于理,顺理即是有道,则礼、义即为人世间以道为准则的规定。《管子》之礼“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7]198,规定了人事的名分,君臣百姓各守名分则可“名正分明,不惑于道”[7]551。因此,礼义即是人之主体积极循道之客体的阶梯,对应天地常道之“阳德”。
“廉”本义指堂屋的侧边,首见于《仪礼·乡饮酒礼》:“设席于堂廉东上。”郑玄注:“侧边曰廉。”[14]《说文解字注》曰:“堂之边曰廉……堂边有隅有棱,故曰廉。又曰:廉,棱也。引申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15]444可知由廉之本义引申出清廉节俭之义,比喻人守正有节制。耻即内心羞辱之感,《说文解字注》:“耻,辱也,从心耳声。”[15]515
以廉耻为“四维”之一,与《管子》的人性论有关。万物以道为本体,道之在人则曰“中正”,故《管子》言:“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7]778,“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7]307。人之所以失其中正,与道交远,在于为物所惑,故曰:“(圣人)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7]510廉耻之设即以廉抵制物欲,使人“立身于中”而“养有节”,可得“意定而不营气情”[7]1012之功。物欲之害更甚者会导致失国灭身。《管子》以齐桓公之口道出先君齐襄公不修廉耻而招祸的故事。襄公其“高台广池,湛乐饮酒……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以致“国家不日益,不月长”[7]396,后遇国内叛乱而身死④。是故《管子》曰:“先王重荣辱……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7]254为物欲之不善而有祸,甚为可辱。以廉耻立维,即是以廉耻消极防范人之主体离道甚远,对应天地常道之“阴刑”。
正如《管子》尚阴阳和合,礼义、廉耻虽各具积极、消极之效,但二者之间需相互协调方可顺利施行。《管子》曰:“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7]53又曰:“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7]266可知《管子》立维绝非将各维视作相互独立的个体,而是既关注各维之间不同的阴阳属性,又强调各维之间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因其是动态关联的,故“四维”之中缺一不可,否则“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7]3。谢源和亦言:“这四个元素,表面上虽是四个不同的名称,但实际上彼此间的关系,是具有一贯的连环性,缺一不可的。”[16]基于此,唯有各维之间互相牵连,“四维”方可编织成网罟纲略的“国家道德论”体系,发挥其“纳民于轨物”的国家治理精神纲领的效用⑤。
三、“四维”德教的具体节目
谢源和认为,《管子》的政治思想尤其注重国民道德的培养,其具体方法就是以“四维”施行四元道德教育,这种道德教育的方法较法治而言更为“治本”[16]。“四维”道德教育之所以有如此成效,在于其有教化成俗之能。凡治国者,莫不希望百姓行为端正,“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此二事是教化的结果,“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7]56。所谓教化,即“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7]106,是一个由浅及深,由表及里,包含政治教育、环境教育、民俗教育的长时效、多方位、多角度的有机系统。此教化系统如“秋云之远、夏之静云”[7]636,动人之情,引导心性,使“君民化变而不自知”[7]256,使夷貉不开化之民变化气质以相敬爱,“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7]605。
欲以“四维”行教化,需君主自身先做一个道德的表率。西汉贾谊认为推行“四维”教化以君主先行为重,论曰:“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17]耿振东认同贾谊观点,认为“实行‘四维’教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君上能否先臣下以‘四维’的标准躬亲行之”[3]107。君主需自先奉行,盖因百姓视君主之善恶如目前,“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君有善行则民喜而从,有过则民恶而不从,“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7]598-599,故曰:“治官化民,其要在上。”[7]554
《管子》认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7]550。然道虽为一,但举用有所不同,所谓“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7]1182。由于身份地位不同,人之常道亦有异。在君主则“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7]1167,君主之常道中内涵礼义的要求,欲“牧万民”则应以礼治国。《管子·中匡》总结七项国之大礼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7]386此七项牧民措施是国礼的具体表现。欲“莅百官”,一则应以义任官职,非有德者不以尊位,“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7]59,不以私好偏爱轻与爵禄,“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7]306;二则令出必行,不以喜怒干扰吏治,“喜无以赏,怒无以杀”[7]1198。
君主富有天下,然地力生之有时,民力用之有倦,若取用无度,纵容物欲,则必然导致国贫而生祸乱。正如《管子·权修》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7]49又曰:“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7]51故《管子》格外强调君主应修廉耻,曰:“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7]76《管子》从君主为天下人道德表率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君主不廉而有祸害的内在机理:若君主贪图物质享受,则上行下效,君主喜爱的饮食衣物,臣下也会尽力索取尝试,“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7]17。如此则上下皆怠惰慵懒,不务本职,而至有亡国的危机,“外淫于驰骋田猎,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7]231。故圣明君主会节制欲望,以避免妨害道德教化的推行,“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7]1007。
臣下之常道,“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终而复始”[7]1167。《管子》于臣道强调一“忠”字,曰:“多忠少欲,智也,为人臣者之广道也。”[7]252管子所谓忠的对象非特指君主一人,管仲曾言:“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7]332故公子纠亡而管仲转相辅佐齐桓公,此为非忠于一人,而忠于国家社稷的大节义⑥。不忠于君主一人,则不必委身阿谀,“不宾事左右,君知则仕,不知则已”[7]619,而其精力全在于国家之建设,“若有事必图国家,遍其发挥,循其祖德,辩其顺逆,推育贤人”[7]619。居官奉事以礼义的标准尽职尽责,“事君有义,使下有礼”[7]619,匡正君主之过失,“君若有过,进谏不疑”[7]620。平日闲处则以“四维”德行安身立命,“居处则思义,语言则谋谟……义以与交,廉以与处”[7]619-620。《管子》盛赞如此之臣为“有道之臣”[7]620。
君臣相率奉行“四维”教化,已先在权力阶层打下坚实基础,则易在全社会形成上下交通的道德教化氛围,使君臣民在同一精神纲领下形成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故曰:“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则百姓上归亲于主,而下尽力于农矣。”[7]550此亦是上行下效之理,所谓“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7]923。权力阶层先行“四维”而守己常道,则百姓心服,“四维”教化易于推行。
民之常道,在父母则曰:“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始。”在子妇则曰:“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7]1167民之道侧重于人伦关系,使父子、夫妇之间以相互负责、相互亲爱的温情联系为统一的有机体,百姓在温情的生活氛围中,乐得安身,积极生产,进而可得社会整体上下无怨、和谐有序。
民之道不出人伦,盖因道本就在日生日用之间,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故《管子》曰:“道满天下,普在民所。”[7]938又曰:“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7]935因此“四维”教化本不必另辟蹊径,只需教民敦伦尽分,故《管子》曰:“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7]759
至于以“四维”教民的具体落脚点,《管子》曰:“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7]56《管子》唯曰其小,非不顾其大,盖因“四维教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积微成巨的过程”[2]107,亦唯有从小做起,方能成就其大。“四维”教化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它需要国家上下先达成一致的精神认同,再由执政者率先垂范,进而在社会中营造利于“四维”推行的生活氛围,最后从小处着手,修小德,禁微邪,化民俗。如此循序渐进,长期熏染,才能达到“四维”教化的最终目的。故《管子》曰:“终身之计,莫如树人。”[7]55
为营造有利于“四维”推行的社会氛围,《管子》亦重视政策、环境等客观因素对人主观心性的引导作用。《管子》建议“立五乡以崇化”[7]55,各乡置乡长以督促道德教化,并令乡长每年正月推举品德优良的百姓为贤才。据《管子·小匡》载,齐桓公亲问各乡长,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7]416以政策引导,极大地增强了百姓修养“四维”德行的积极性,“是故民皆勉为善”[7]418。
《管子》又根据百姓从事职业的不同,将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各阶层按照职业特点分别定居在不同区域,“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7]400。这种简单地根据职业不同而划分居住区域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固然有些机械,容易导致社会阶层僵化,有碍群体流动。但不可否认,此种制度为“四维”教化的施行提供了便利。以士为例,“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7]400。士同居一地,出言皆合礼义,则在定居地形成了共同的话语场,生活在这种氛围中,行“四维”是一件极自然的事。于是士群“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7]400,形成了稳定的道德认同,其结果是“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7]401,于是“四维”教化就以一种极简单又收效颇丰的形式顺利施行了。
四、“四维”德教的目标
道既是万物之本体,“四维”是导民于道的阶梯,则“四维”教化的总目标必然在于使天下万民合于道之境地,“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7]568。由此可见,“四维”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道德教化,而且是超越政治组织的、内涵形而上因素的精神指归。《管子》的“四维”教化目标可称为以道立论的“一体”之政,所谓“先王善与民为一体”[7]565-566。
所谓“一体”,不是忽视差别的清一色类同,而是如人之身体一般,各器官虽职能不一,但血脉相通、气息相和,在同一精神认同下举国上下的大协调、大和合。在此“一体”之政下,君主如身体之心,扮演思虑的角色。君主以道体国,拟定治则,安乐百姓,推行教化,“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7]583。臣下如身体之有九窍,以“四维”之义理协助君主,尽其职分,“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7]759。百姓则安分守业,以“四维”之教化精神处世,积极配合国家政策,“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7]80。
既然举国为“一体”,则君主自然以民之需求为己之需求,以民之利益为己之利益,“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7]565。民之所欲,概言之唯富贵安乐,故政令之施向唯在于从民所欲,除民所恶,“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7]13。而继以道德涵养其心性,推行“四维”不辍以使民和合,“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7]176。
结 语
如前所述,《管子》以礼义廉耻并列“四维”,绝非仅为义理层面的简单罗列,而是由其以道为世界本体的哲学思考,通过天道与人事相映的逻辑所引申出的治国纲要。《管子》中直接论述“四维”的言论虽简,但“四维”教化精神实则贯穿《管子》各篇,内涵形而上的哲理支撑和形而下的政策辅翼,包含君臣民三层次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民俗教育等多角度的精密体系。从现代的角度看来,此种体系固然过于强调“安分守业”,使“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7]401-402,存在阶层固化的弊端,但其中蕴含的德教经验对当代公民道德教育无疑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8]《盐铁论》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19]新时代中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法治对于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公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不仅有法治领域的问题,亦有道德领域的问题。《管子》虽列法家,但亦对道德教化的作用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故而,道德建设不仅不可忽视,亦应放在重要的位置。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要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20]
然而道德建设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执政者以充足的耐心、长远的决心,在一以贯之的精神指引下,以简单易行便于群众理解的方式长久施行。《管子》“四维”论提示我们:道德建设的关键着手点在于领导干部要做好道德榜样,在道德教育中起积极引领作用;同时,道德建设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喊喊口号就能收到成效,它不仅要有相应的政策制度作保障,而且要结合群众的实际生活,多角度多层面相互配合,营造有利于道德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道德建设要不捐细流,从细微之处做起,将道德要求融入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化民成俗”,从培养道德习惯做起,并使之成为群众内心的情感认同,久久为功,方能提高全民的整体道德素质。
注 释:
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称:“吾读管氏《牧民》……详哉其言之也。”南宋黄震《黄氏日抄》曰:“管子之情见于《牧民》、《大匡》、《轻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简明。”
②“《管子》四篇”即《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
③钟泰认为,《管子》道论与《老子》最大的不同在于“《老子》多言治道之体,而《管子》则于用为详”。详见钟泰《中国哲学史》第19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④详见《管子·大匡》。
⑤谢无量称《管子》“四维”德教为“国家道德论”,其目的在于“纳民于轨物”,即使民无奸邪之行而致力于生产。参见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175-176页,台湾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⑥据《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