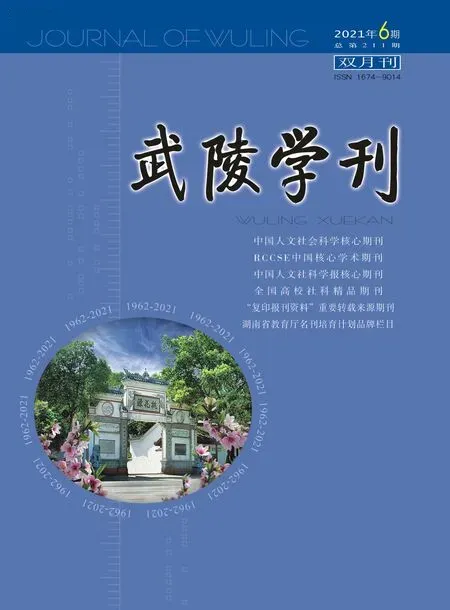唐才常的文学观探究
2021-03-07王志华
王志华,李 曦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唐才常为晚清湖南维新派代表,与谭嗣同合称“浏阳二生”。他积极投身政治,以《湘学报》等刊物为阵地鼓吹新政,学界对其作品的研究亦因其身份而多聚焦于政论文章,鲜少涉及其传统文学作品及文论思想。检视唐才常诗文作品的创作轨迹及后世传播情形,发觉其传统文学作品曾一度得到更广泛地传播,其作品风格主旨与创作理念又具有多面性。本文通过追踪其创作师承、写作心态及理论革新的变化过程,探究以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革命党人文学创作的具体面目,揭示其文学观中体现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及审美价值,打破长久以来将唐才常视为新文体与政论文作者的单一刻板印象。
一、从创作轨迹看唐才常的文学观
探究唐才常的创作历程可发现,他幼承庭训,以经世为创作高标,后在书院进一步精进写作能力,并初获声名,进而在担任四川学政期间接受系统的时文写作训练,后又废时文而以维新派自创文体屡屡发表宏文大作,引起政界学界注意。在这一过程中,唐才常的文学观叠合了时代与个人际遇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政治理念的凸显、社会发展的印记及审美风格的变化。唐才常的成长经历及创作发展反映出他创作理念与方法的更迭演变。
唐才常之父为塾师,教学有别于只知迎合八股应试的普通塾师,他“为教不尚八股试帖,务崇实学……常聚集生徒讲习,备举经籍中微言大义”[1]681。受父亲的影响,唐才常十二岁时,已接受了基本的经学训练并树立了求学目标:“才常已通诸经。父贤畴授学之余,日夕以古代先圣豪杰之学行事迹为之解说,才常于是慨然有志于经世之学,思以国家为己任。”[2]7唐才常少年聪俊,应试之路初期颇顺畅,二十岁时即“以县、府、道三试冠军入评”[2]8,为当地一时之盛。此后,就读于校经书院,在此期间的创作秉承着早年间的志学祈向,具有鲜明的经世色彩。康有为评价其两湖书院课卷道:“黻丞博极群书,文章奥玮,而当闭塞之时,能讲中外之学。此虽书院应课之文,而淹贯博雅,已轶群伦,其墨迹所存只此,应为天下后世所共称护之。”[2]105康有为主要着眼于其文章内容博雅,但未对创作风格作针对性评价。而书院老师对唐才常课作的评价则相对具体客观,其诗作《端午日四咏》被评为“古诗题外见意,亦类骈枝,但其笔气横溢为可喜耳”[2]67。“文字各有体裁,古今豪杰能文之士,莫不敛才就范,谨守绳尺,盖不如是即不足以传也。”[2]67“作者殆不欲以声偶见长,至其议论行文,笔力坚凝如铸,亦不免有指斥过激之处,得少含蓄益佳,诗清。”[2]69书院老师认为唐才常的诗歌创作未能切合法度,表达过于激烈外露,不符含蓄之旨,形式与结构皆不突出。
而唐才常指点江山阐发政论的论说文则往往得到一致的高度评价,如其文《征兵养兵利弊说》被评为“中国军制之弊,后幅穷极事变,尤令人怅恨不置。此卷言西人兵制,颇得其深,而于振作中国军务之道,言之最详,知是留心时事者”[2]136。策论《问吐蕃、回纥不能得志于唐,而契丹、女真、蒙古,皆得志于宋,能言其故欤?》被赞为“侃侃而谈,饶有英气!”[2]153可见唐才常的课作多以立意内容取胜,而形式辞藻则相形逊色。与湖南鼓吹新政的风气相映衬,唐才常的此类文章被收入其时湖南学政江标编校的《沅湘通艺录》中,据此书选录标准:“四书之文尤为湘士所夙诵,通经史不易,发扌为为文,博而不乖于正者,以万亿计,最而集之,不能胜梨枣,此略见一斑耳。”[3]2《沅湘通艺录》共收录了唐才常文章十一篇,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更佐证了唐才常的文章在湖湘当地流传之盛与评价之高。由此可见,唐才常的作文水准虽未在技艺上纯熟老道,却因其激切的表达方式与切中时弊的前卫议论而声名渐起。唐才常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在主观上蕴含了作者激切的经世抱负,在江河日下的社会背景下,他在书院的课艺文章以关怀现实而得到当地社会名流的看重,从而初具文名。
此后,唐才常自二十五岁时起,应四川学政瞿鸿机之邀,承阅卷事宜,历两年之久。在此期间,唐才常的写作训练以应试时文为主,其作文的思想补给则为传统的经史著作。他时常利用闲暇购置大量经史图书,在写给父亲的家信中提到购书事宜:“男嗜书如命,故购之不惜重价,况川中书籍,多湖南所无,装订亦甚精致,不趁此时购置,更待何时?”[4]382根据唐才常这段时期的家书内容,他反复强调经书的重要性:“男于五经多不能背诵之处,殊觉抱惭魂梦。故男此次力将《礼记》温熟,以为下手工夫。盖精于礼者,不独有益治经,亦于身心性命关系匪浅。要之五经无一不宜精熟,既往不咎,来者可追。”[2]33这段时光,唐才常的活动“唯是课读之余,赋诗、读书,及屏息静坐而已”[4]384,并自谓“近日读书,颇有进益处”[4]384,显示出其创作储备的扩展与思想境界的提升。这种内在的输入与扩展,无疑会在其具体的写作训练中体现,自述到:“每抑郁无聊,即喜作史论以浇胸中之垒块。”[4]384
史论虽是唐才常一贯熟悉且擅长的创作领域,但在其逗留四川期间,特殊的个人经历给予其重新审视自身学养能力及学习补缺的机会,也刺激了唐才常写作技艺的精进与创作手法的突破。其文章对经书立意有独到理解,在《湖南设保卫局议》一文中称:“今西国有警察部,无不与《周官》暗合。”[4]234《辨惑上》以经书比附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民权思想:“其实任举《孟子》、《公羊》及六经中一言一例,无弗重民、贵民、公权于民者。”[4]239《论热力下》将电力的作用,以儒家义理的“诚”来理解:“斯电也,在格致家为电,在吾心则为诚。”[4]252唐才常在介绍西方政治体系、科学文化新知的政论文中,以儒家经典的后世阐释为依托,引入新的概念。刘再华认为“这种言说方式成为晚清革命派文学,特别是其政论文学的主要写作模式”[5],至此,唐才常在传统经史教育的基础上,对西方政治思想进行比附理解,并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文章写作模式。这种创作特质是依附于维新派独特的思想体系的,即以公羊学为基础,建构了以孔子为素王的儒家教义体系。这种思想上的特色体现在《春秋三传宗派异同考叙例》一文中,唐才常奉孔孟思想为宗旨,他说“诚于此时汲汲发明孔孟仁民爱物、以元统天、以天统君荦荦诸大端,而为吾教中救世复元之路德,以还尼山真面”[4]267。因唐才常的学术宗仰为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派,他盛称“《春秋》文致太平之宏旨”[4]21,却对《春秋左氏传》持批评态度:“左氏重事,仅沿袭衰周苟且之制,敷衍成帙,而又多刘歆之伪篡,故可断为古学派。公、毂重义,承孔子晚年论定之绪,参用四代,斟酌损益,以治无尽世无尽时之人世界……左氏则纯平古学淆以鹰鼎,非孔子损益三代之制……公、毂于礼彬彬雍雍,端门所受,揭日月而行,左氏何礼之有?”[4]268“左氏则只胪陈衰制,未及圣人受命改制之意。虽偶有同于公羊者,不过据乱世之一二条耳,故事详而义略。《春秋》贵义不贵事,只以左氏作古史观可也。”[4]273
学术立场上的偏好,对文章写作也会带来相应影响。这种认知使得唐才常与奉《左传》为文章写作范式的传统文论互相扞格,显然唐才常不会视《左传》为行文模板与模仿对象,因而其文章写作风格与尚雅正的古文理念相去甚远。刘师培在评论公羊学家的文章风格时称:“近人谓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欤!”[6]296当代学者曹虹将今文经学对文章写作的影响总结为:“今文经学家讲《公羊》学,强调微言大义的发挥,更易受《春秋》属词比事之教的沾溉,引发博丽恢诡之文……加上解经时杂采谶纬之书,也易于受到这类文献‘事丰奇伟,辞富膏腴’之特点的激发,增强行文与想象的奇情异彩。”[7]联系唐才常的政论文可以得见,其文章在修辞上多连用比喻排比,气势恢宏,行文属辞也不囿于桐城派古文家所主张的“雅洁”,不仅在形容词的使用上无多限制,频用叠词,俚语俗谓与外来语、新造语也常夹杂其间,例如轮船、电线、铁路、电机、热力、自会盟、民权、意大利、希腊、普鲁士等舶来词。文章立论主于打动人心,因而多用“呜呼”等表达强烈情绪的语气词,又善使设问譬喻等修辞手法,时人论其与康有为行文有“同一鼻孔出气”的嫌疑。虽然唐文中确实出现多次诸如“剌剌语天下曰”“尘尘地球”“茫茫苦海”等语,稍显烂熟,带有维新党人政论文的鲜明特色,但是在处理传统的文章体裁与内容时,唐才常仍然显示了对结构与措辞的良好驾驭能力。而这种能力其实与其所深恶痛绝的时文写作关系密切。唐才常在《时文流毒中国论》中自叙:“吾未冠以前,低首摧眉,钻研故纸,暝坐枯索,抗为孤诣秘理,沾沾自足,绝不知人间复有天日,复有诟耻之事。”[4]230可知其少年时期曾花费巨大时间精力进行时文训练,具备良好的创作与鉴赏能力,曾因此被聘为四川阅卷,可证其八股写作水平得到时人认可。虽然唐才常在放弃科举后经常痛诋八股文的害处,但这种文体对其文章写作所产生的影响则是难以避免的,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唐才常或多或少沾概了八股文写作训练带来的用笔范式与排篇布局的考量。以《淮川李氏四修族谱序》一文为例,此篇文章有别于唐才常最为知名的创作类型,内容上不涉维新改革,造语无新词,写作手法与内容较少时代背景的展现,可视作其传统古文写作的一个代表。此文开篇由设问“谱之作也,其由《易》之萃义乎”[4]372引申出族谱所承担的礼法上的重要作用,由叙昭穆、定亲疏、制宗法而使得宗族中后人升起敬意,并随之而生爱,孝悌的思想因而伴生,宗族也因此而团结。随后交待了序谱家族的渊源,介绍了这一家族的产生、发展及其中杰出子弟的事迹。最后阐扬了修谱之事的合理性与意义,全篇文字从开端到结尾,不断铺垫,承接自然。这种对文章结构起承转合的处理,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古文写作能力,也透露出八股文写作方式在唐才常创作上的渗透。
唐才常致力时文并吸收经史,为其日后转向宣传维新变革的政论文创作打下坚实基础。他将经史思想融贯于文章写作中,在结构与修辞上继承并创新了时文及古文的艺术风格,在创作笔法上以新式词汇和强烈情绪渲染来组织语言,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政论文写作模式。
二、从作品的传播接受情况看唐才常的文学观
在梳理了唐才常的大致创作轨迹后,可知其文学观的生发及变化情形,而探究其作品的流传情况与评价影响,则可对唐才常文学观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价值评估。
唐才常的作品在清末民初流传主要通过报刊杂志。他生前曾以咄咄和尚及天游居士、蔚蓝、云梦残生等笔名在《亚东时报》上刊载了系列政论文及诗赋,去世后作品也零星登载于地方文学刊物,如《大陆报》分别于1904年第7、8、9、10期的文苑一栏刊登了唐才常的诗歌《感怀》《忆香渠》《怀刘嵩芙》《春宵有感》《草堂书感六首》;又于1905年第2、3、5期的文苑一栏刊发其文《广潘正叔安身论》《论文(连珠十首)》《李白论》《怀刘子璋》等四篇。杂志《豫言》则于1917年的第30、31、32、33、34期连续刊发了唐才常的《论文(连珠十首)》《广潘正叔安身论》《李白论》等三篇文章。杂志《民权素》则于1915年第12期刊登了唐才常的多篇诗文、赋作,在名著一栏刊发了《民主表白序》《湘报序》《淮川李氏四修族谱序》《淮阴侯钓台赋》《渔蓑赋》等五篇文章,其中三篇内容与政论无关;而艺林一栏则刊发了唐才常的诗歌《馈岁》。专门论及古文作法的骈文著述《论文(连珠十首)》,被多种刊物登载,并收录于文论丛书——何藻所辑《古今文艺丛书》中。此书于1913年广益书局出版发行,由诗文、词曲、绘画、雕刻书法、琴棋、茶品、砚墨、纸笔、盆栽、园艺等文艺研究著作凡八十五种汇编而成。此书以古人著述居多,间收清末民初之作,唐才常的此篇文论得以入选,足以证明其创作水准受到时人的肯定。后期各类选集则以收录唐才常的政论文为主,如郑振铎所编《晚清文选》(生活书店1937年版),收入其文章十篇,分别为《唐宋御夷得失论》《史学论略》《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外交论》《通塞塞通论》《师统说》《公法通议》《觉巅冥斋內言自叙》《湘报叙》《各国种类考自叙》。另有王家棫编《国魂诗选》(新中国建设学会1934年版),收入唐才常诗歌一首《送安藤扬洲之燕京》。
综上,在1900至1920年间,唐才常诗文传播主要为传统文章体式的诗赋、序文、连珠体等。这类作品多被登刊在艺林、文苑等专门刊载文学作品的栏目上,并被收入专门的文话丛书。而与之相对的是,这类作品多未收录于唐才常生前自己整理的作品集《觉颠冥斋内言》中。
20世纪30年代以来,唐才常在两湖书院的课卷、主笔《湘报》时的论说文成为传播主体,其身份事迹也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强调,作品多冠以烈士遗作的名目,以期产生时代呼应与回音的效果,以此宏扬唐才常变革之激进、牺牲之无畏精神。如《国魂诗选》序文即称:“盖古人诗歌中,除文人骚客藉以吟风玩月抒情写感外,往往为有益于修养意志之作……修养意志以为民族牺牲,则时穷节乃见之类也。本书举上古以至现代所有适合于上述修养意志之诗歌,自浩瀚群籍中,撷菁萃英,以为国民精神教育之资粮。”[8]1该书将所收编诗歌归为“修养意志”一类,自动区别于“吟风玩月抒情写感”类型的诗作。收录唐才常多篇政论文的《晚清文选》序文写道:“对于老维新党奋发有为、冒万难而不避、犯大不讳而不移的勇气,与乎老革命党的慷慨激昂、视死如生、掷头颅、喷热血以求得民族自由与解放的净胜,我同样的佩服……这一册里有许多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是对症之药,并非泛泛的搜集名篇佳文的一部‘文选’而已。”[9]1同时,关于唐才常的纪念诗文也开始出现,如《国学论衡》1936年第7期刊载了曹昌麟的诗歌《题浏阳谭复生唐佛尘二烈士》,《逸经》1937年第22期则登出了章太炎所作的《唐烈士才常象赞》。至此,唐才常烈士形象的定位基本得到了固化,而基于这一形象所作诗文的指向性与符号意义也都鲜明起来,照应了《晚清文选》《国魂诗选》等选本的择录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才常维新烈士形象未完全影响其作品传播时,也出现了专门针对其政论文章的议论,如姜泣群在1917年出版的《民国野史》一书中,对唐才常文章的个人风格进行了评价:
唐才常文有雄直气,高洁则不及谭嗣同。有一篇发端曰:(唐才常)睊睊然猥顾而鹗视,剌剌然强聒天下。曰又有一篇发端曰:(唐才常)既堕尘球,蹙蹙靡所骋,睊睊然猥顾而鹗视,作而言曰:两篇皆用猥顾鹗视四字,试摹其形,未有不哑然笑者。
又唐文好用叠字,如沉沉者蛤利耶,搏搏者坤灵耶,及尘尘二千余年一文网焉。莽莽二万余里一病躯焉,睊睊眮眮数十百国,聪强发纾,坐教修饬,而仆缘大地之上而环而峙者。一大权衡焉。此类甚多,不可枚举。与康有为之茫茫宇宙、莽莽乾坤,同一鼻孔出气也。[10]75
唐才常的政论文多以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为主要内容,用语多涉及新式词语,颇不同于传统古文,且这类论说文以打动、说服读者为写作目的,在写作手法、谋篇布局上也有别于传统文章的写作特点。凡此种种,使得此类文章形成了迥别于传统古文的写作范式,但因文章的时效与实用性,缩短了文章的创作过程,因此弱化了对文体的雕琢与规范,导致写作方式与措辞风格的雷同,如文中所举唐才常用词多重复、喜叠词,甚至与康有为等人所撰之文趋向雷同,难以分别。因此时人对其文章风格整体评价不高。总之,唐才常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对其个人身份特质的关注一般要凌驾于对作品本身的关注。
在民国初期,各地文学期刊多借前朝名士的遗文散篇装点门楣,并以篇幅与形制简短精悍的诗歌骈文作为刊载对象的主体,而唐才常的部分作品恰好符合这一选录标准。至民国中后期,重新发掘维新党人及革命党人的斗争精神成为文艺界的主流思潮,唐才常的烈士形象被突出,其作为战斗宣传的政论文也再次大放异彩。
三、从新旧交叠的创作理念看唐才常的文学观
由目前唐才常诗文作品的整理可知,其文学创作以文章为主,论、议、说等论辩性文体居多,其余为赠序、连珠若干、书信类等文体。诗赋数量较少,内容以感怀追忆亲友居多。虽然唐才常专门论述文学观念的作品较少,但在日常通信及文章中多少流露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思考。
剖析唐才常政治思想转折,由此观照文学创作理念,有助于理解其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与唐才常维新志士的身份标签相对应,其激烈反对八股时文宣扬新学的言论名动一时,虽时人称其在书院读书之时已“鄙视八股词章空疏谫漏,日与同学中有志之士,精研经史,以经世致用之学相切磋”[2]10,但检阅唐才常与父亲的书信往还,可知其对时文与科举并非持一贯的反对态度,反而一度十分重视。在四川阅卷期间,唐才常几乎在每封家书中都提到关于秋试时间与回乡应考之事,对此异常看重,且心存向往。如他在《上父书》第十一封中写道:“明岁恩科,如春秋两试,男决计不归,如循例秋闱,男拟于四月杪归家,盖功名虽有定分,而人事亦不可不尽也。”[4]387在科考失利后,唐才常在写给友人欧阳中鹄的信中回顾自己的应考过程:“侄卷首篇用《周官》《曲礼》分柱到底,次篇多用选句,三篇用公羊家言,房师彭公献寿极力鼎荐,于二三场尤为倾倒,三场有‘淹贯百家、折中一是’等语,而主司批语亦无甚渣滓,同辈多为扼腕。”[4]397显示出对时文应试的自信与未得功名的愤懑。此后,唐才常对时文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逐渐从质疑批判到否定反对,他在家书中对父亲表达了对时文衰落的预测:“男静观天下之变,时文一道,将来必成废物……(其子)如果能读书,此刻不能不稍从事于此;未审可否参以经史诸义,俾知学问之道,渺无涯涘,有不止此庸陋时文者。”[4]394他同时也对弟兄子侄的立业前景产生担忧并进行干预,认为日后进学的路径应转向经史与格致之学,算学、武备等“较之岁费千百金,课一毫无用处之八股、经解、词章,奚啻倍蓰”[4]429,他在给三弟的信中对此反复强调:“从今以后,弟当肆力于经史……欲为圣贤,则不得不研力于经书,以求义理之真伪。亦不得不精心于史书,以观历代之得失……夫欲知天文地舆,则算学一道,诚不可忽矣。自古圣贤未有不精于算学者。”[2]82“华丞、桂梁,弟可嘱其速肆力于经书,兄将来归家,当进有用之学。盖时事既已如此,时艺在所必废,舆地、格致之学,在所必兴。”[4]422伴随对八股时文弊端的不断思考,唐才常开始反思文章之学的价值含量。
除八股时文外,对于占用当时知识阶层心神精力最多的考据与词章之学,唐才常也进行了激烈痛诋,将其视为赘疣。他对士风进行了辛辣讽刺,认为士子多“沾沾于时文,计较好歹。歹者固不足道,好者亦复有何用处?微独时文然,彼经解、词章,纵能追踪许、郑,继武庾、鲍,当兹变乱将起,试问其能执此御侮疆场乎?……吾不知彼以经解、词章、八股自鸣得意者,又将争胜几时耶”[4]417。唐才常在《治新学先读古子书说》一文中更进一步对经解词章的经世价值予以否定:“尘尘世界,桎梏于文法,昏瞥于科目,沉冥于俗儒,如蛾趋焰,如蚁附擅。其上者能笺注虫鱼,批风抹月,人许、郑而家徐、庾;其下则抱兔园册子,束湿老师宿儒之言,以媒通显;或且睥睨群伦,私尊敝帚。”[4]334除对经解及词章的价值否定外,唐才常在《尊专》一文中对治学路径也提出质疑:“学问之道,不专不成,古今之通病,天地之达忧也。然经史词章,其质性聪颖者,偶涉藩篱,尚能貌袭其华以盗名欺世,而许、郑如鲫,庾、鲍如林矣。夫中士非独不专于新学,即其鹜为文章之业,辄喜兼营并举,苟且涂饰,终其身鲜翔实者。”[4]338他认为当世的读书人中用力于文章者多粗陋荒疏、欺世盗名之徒。从其政论文中可见唐才常在历史纵向维度上对文章写作持整体的否定态度,包括对立意、作用、方法及文统皆有针对性的批评。但考虑到这些论文观点是服务于其政治理念,即反对旧体制,谋求社会各层面的变革,则当以审慎的态度科学对待。
唐才常遗世作品中还保留有部分形制古朴、内容典雅的骈文作品。其中形式最特殊的是《论文连珠》。这篇文章分别在《大陆》《民权素》《豫言》等文学性刊物上登载,并在骈文专栏加以推介。虽然不能明确唐才常于何种心态下创作了这篇兼具文论和骈文风格的文章,但通过考察可窥见唐才常创作中传统的一面。具体来看,这篇文论认为文统的开创与继承导源于《诗经》,“风、雅传正变之音”[4]370;楚辞为《诗经》传统的延续,“屈、贾乃精诚之泄”[4]370。论文以浑朴自然为尚,反对藻饰过多,认为东汉文章在风骨上呈现的是从西汉以来的倒退,“西汉雄深,卓然典谟之制;东京藻俪,渐伤风骨之庳”[4]370。同时,该文从“文因人重”观念出发,将作者人品道德置于衡文首要之位。而对于辞藻的雕琢与形式的整饬,唐才常并不看重,认为“容悦以偶俗,虽雅而伤烦”[4]370。唐才常反对齐梁绮靡文风,却对唐代奏议文给予了很高评价:“燕、许振皇唐之业”“昌黎起八代之衰。”[4]370他指出唐代奏议文的风格是“宗浑厚而屈浮华”[4]370,并因立义高明与蕴含经世思想而成为文章典范。在总结作文宗旨时,唐才常称“必根柢乎六经”,并详细指出文章结构与立意之间的关联,即“文扶质而垂条,理探本而立干”[4]370。同时,他在此文中又论及复古与模仿的关系,认为欧阳修、苏轼及元代诸贤,因为“多濂洛关闽之遗绪”[4]370,而成为其所推尊的摹古代表;而明代七子的复古理论与创作,皆失水准,被讥讽为“优孟衣冠”,究其原因则在于“时艺斯兴”,导致群经要旨蒙尘,故而明代复古之作“未获西京面目”[4]370。综上可知,唐才常的文论观依然以宗经为本,并表现出对语言形式美的反感,他所推崇的作文典范,仍为两汉唐宋时期的古文家,未出前人藩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虽然在《论文连珠》中屡次提到齐梁绮靡文风背离正统、风格卑下,但在具体创作中,唐才常的骈文作品质量与传播广度皆十分可观。除此篇连珠体论文外,还有骈文作品如《广潘正叔安身论》与《李白论》,也曾被民国时多部文学杂志刊载。再联系唐才常对词章的批评,如称“彼经解、词章,纵能追踪许、郑,继武庾、鲍,当兹变乱将起,试问其能执此御侮疆场乎”?从他多以庾信、鲍照等六朝文士作为词章之能士可以推知,在唐才常心中,六朝华丽文风的艺术造诣是得到其认可的。以《李白论》一文而言,其中不乏辞藻华丽、典故富赡之处,如形容李白为“玉屑徐霏,驰俊采于天葩;衙官屈宋,踵前徽于里梓”[11];而《广潘正叔安身论》虽文辞偏重说理,亦有辞采华赡者,如“大风振谷巢林者惧焉,惊涛回飚荡舟者覆焉”[12]。
由上可知,唐才常的文论颇为传统,无新创见,其创作形式则显示出受到时文写作与其所批判的六朝文风影响,这种创作现象要结合其“维新体”政论文来一起辩证看待。作为维新人士中的先锋派,唐才常激进的政治观点必须通过某种有别于典雅文体的新式文体来表达,这是其作品中大量政论文存在的原因,同时唐才常也是一位长期受时文写作训练与古典文艺审美熏陶的文士,其文论与部分作品仍然因袭了传统文学的写作范式。
综上,唐才常的文章创作,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古文写作手法的创新之处,在结构、修辞、用语等方面都产生了有别于传统文章学的写作规范,同时在部分作品中还保留了古典文学传统写作痕迹。而唐才常作品的传播也是以这两种类型为区分,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与传播者,伴随社会发展而起伏变化。同时,他在理论创新上相对滞后,将宗经贵俭作为文章创作的至高标准,但是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仍有不合于其所倡准则之文的出现,尤其是他的政论文,文风雄奇恣肆,虽语涉经典却实指新制。这一复杂的创作面貌与文学观是社会转折时期的产物。对唐才常文学观的研究,挖掘其中包含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可以为后人探究清末民初文学创作的复杂形态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