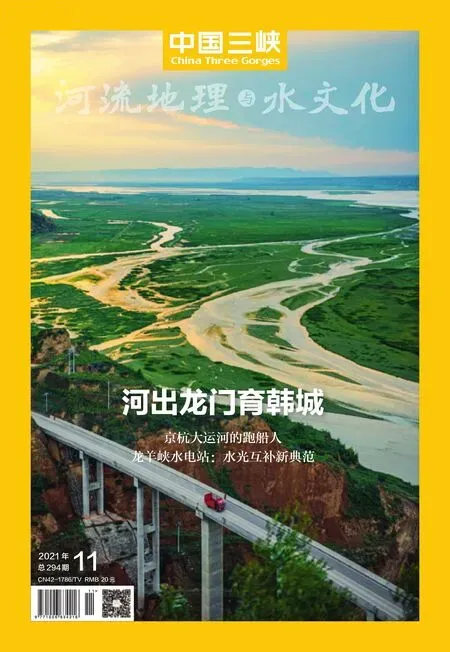汉水的渡过
2021-03-04艾子编辑谢泽
◎ 文 | 艾子 编辑 | 谢泽

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展示20 世纪70 年代襄渝铁路建设的陈列馆一角 摄影/杨军

通过汉中镇巴县巴山镇的襄渝铁路 摄影/杨军
我在每天上班的途中,都要穿过襄阳汉江二桥,悬空数米与汉江的水流相遇,会情不自禁地打量这条清澈、温柔、汩汩东去的河流。我的视线范围内,西边,流水来的方向,几个大小不等的江心岛,结实的黄土,经年泡在水中,上面长满灌木、杂草,还有不知谁种下的一些向日葵、高粱;下游,一大段河床后,陡然起来一块巨大的沙洲,面积达到30 平方公里,与汉江分开的双子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上面建满了房子,都不高,五六层,一派闲适的样子。从桥上远远望去,沙洲只是一层土黄的薄壳,浮在江面上,似乎一排浪头便可将其淹没。我因此常常担心:涨水了怎么办?
过去的汉江,四季中,有胖有瘦。冬天河瘦,秋汛河胖。下雪了,天低垂着,大地一片肃杀,江面上便也不见了那些紫的、绿的、黄的泳帽,只剩下一只红色的、一只白色的航标船,在那里孤独地泊着。秋天,涨水了,往往人们一觉醒来,河水已窜了几米高。满岸的水,怒气冲冲地撞着大堤,水石相激,轰隆作响,腾起一片烟雾,散发出潮湿的腥气,那种气势,仿佛是在“走蛟”。如果遇到干旱,好长时间不下雨,河床便露了出来,住在河边的市民们就高兴了,踩着码头的台阶,下到河边,洗菜、洗衣服、洗玩具、洗拖布……挖沙船也高兴了,把长长的溜槽架起来,大臂伸进江里,轰隆间,就挖出了河心的沙石,也顺带挖出不知哪朝哪代遗落在江里的古币或墓碑来……
这样的汉江,我无法不痴迷。从桥上路过,无数次打量上游,看一江清水,推开万山,滚滚而下,止不住浮想联翩。这是怎样的一江水,从哪里来?它流经的地方,又养育了什么样的子民?形成了哪样的美景和风俗?又有哪些值得说一说的故事?
汉中:巴山镇的偶遇
汉中领10 县,南郑、城固、洋县、勉县、西乡、略阳、镇巴、宁强、留坝、佛坪,个个历史深厚,我却独喜镇巴,是因为这个“巴”字对我的暗示。
巴作国名时,有巴国,存在于三千年前。《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中:“西南有巴国。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巴作山名时,即巴山。词典上介绍:大巴山,中国西部大山,呈西北-东南走向,是四川省与陕西省界山,东端伸延至湖北省西部,与神农架、巫山相连,西与摩天岭相接,北以汉江谷地为界。这里的“江汉谷地”,便是襄阳一带。
巴为族群名时,即巴人。词典介绍:巴族人称巴人,是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中影响深远。
……
一个字,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文化信息,它因此成为古代作家们的一个创作源泉。李白《古风其二十一》:“试为巴人唱,和者乃数千。吞声何足道,叹息空凄然。”刘禹锡作《竹枝》:“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我生在荆山,长在荆山,荆山也属巴山,二十九岁那年,走出荆山,渡过汉江,来到北岸的樊城生活。又十年,再次渡过汉江,住到襄城。襄城依山傍水,山名岘山,小而秀挺,即大巴山的最后一段余脉。
无数次,我站在古老的凤林关前打量周遭,前面是绿丝带一样的汉水,逶迤着东去;身后是巴山的余脉,以依依不舍之态,凝望着汉水,不禁想到金庸老先生夸赞过的:山水城市。
是啊!山水相依——自汉水离开秦岭,进入巴山地域后,他们像一对恋人,一挽手就是千余里。一路上,水是活泼的女孩儿,嘻嘻笑着,弯弯曲曲地走路,还故意撩起无数波涛,逗着山;可山是一位朴实的汉子,它不会花言巧语,只是稳稳地、不远不近地跟着水,照拂水,又及时地在某个地方,孕出一条条小支流,给水提供着补给。
山并非不懂水的情,但他要等风。夜半,趁大地上的人们熟睡之际,风来了,他俩便一起合奏起最好听的歌给水听。水高兴坏了,她伸展着修长的身子,嘴里“哗啦哗啦”“咕嘟咕嘟”地回应着山。
其实谁都陪伴过水,谁都又很快离开了水。石头送它一程,很快变成了沙粒;人送它一程,很快变成了墓碑;唯有巴山的陪伴,以“亿年”计算,但也只到襄阳。他把自己庞大的身躯遁进大地,只留下手臂,对汉水挥手作别。

陕西汉中,巴山镇石羊栈,稻田如诗如画。 摄影/视觉中国
2018 年秋天,作为一名行者,我走进这永恒的山水之间,来探寻它更多的秘密。我们一行三人,开着车,从襄阳出发,在大巴山里面穿行。为了得以窥见巴山的全貌,我们放弃了高速,专走省道或县道。这样的道路一般沿着河谷修建,河谷又在山底,自然满眼都是两山对峙。越往西行,山越高越大,常常将天割成一个长条,谓之“一线天”。我们走时,襄阳晴好,没想到一过安康,便开始下雨,且越下越大,感觉是从长条里漏了下来,针一样扎在路上、树干或叶片上、河面上,以及行人的背上。
正感叹山的无边无际,一个铺有绿色塑胶的篮球场出现在我们眼前。它如此突兀,像一个现代化的标志。我们赶紧停了车,走拢去,原来这里是镇巴县巴山镇政府所在地,小地名叫做关水村。那个现代化的篮球场,是当地铁路部门捐建给镇上小学的。
一路上,我们偶尔也见到了铁路。它挂在半山腰,有时又拐进山洞,像一条穿山的龙。我原本没在意它,现在听了介绍,方知这铁路就是大名鼎鼎的襄渝线,守在它脚下的,是陕西铁路局安康工务段巴山机务车间。
唐朝诗人李白曾吟过“蜀道难”。他口中的蜀道,是指巴蜀地区通往首都长安的道路,就包括汉中地区。镇巴是汉中的南大门,南临四川万源,自然首当其冲。改善这里的交通,是一千多年,世世代代的愿望。机务车间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襄渝线于1968 年4 月开始修建,1979 年12 月才全线建成并交付运营,整整修了十二年。在这里诞生的“巴山精神”,至今仍是中国铁路上的一面红旗。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我断断续续地回忆着李白《蜀道难》,想着十二年的修建有多艰难。那个时候,国力尚不强盛,现代科技水平也低,更多时候靠的是人海战术和战天斗地的精神。多少人在这里奉献出了青春,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那一个个山洞,一根根高达40 多米、50 多米的桥柱,便是他们对青春、对生命的致敬和献祭!我们这一路,因为沿着公路行走,竟然对它视而不见,想来真是惭愧之极!
正这么想着,脚下的土地突然颤抖起来,越颤越狠,然后听见“哐啷哐啷”的声音传来,就见一列火车从半山腰的山洞里钻了出来。它不紧不慢地经过搭在一根根巨大的水泥钢筋桥墩间的铁轨,不过四五分钟的时间,便又不慌不忙地驶进山洞里去了,像是特意提示我们不要忘了过去。
因为雨大,不便行走。是晚,我们便在小镇住下。旅舍临河,河名黑水,但极清澈,是汉水的支流。乱石在河里卧着,身上既有天上的水,又有从上游冲下的水,合奏起“啪啪”、“哗哗”的声音。不大一会儿,水就涨了,河面上腾起一个个雪白的浪花,与此同时,有些石头瘦小了,有些石头不见了,我心里一动,想起那首古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一千年前的一个雨夜,李商隐写下《夜雨寄北》,曾有人说李商隐这首诗写于“徘徊江汉,往来巴蜀”时,这是多大的地理范围啊,难道不能具体一点?举目四望,群山静穆,风雨如晦,小小的驿站孤独地伫立路边,我的心中一声喟叹:就是它了!
商洛:凤凰古镇
湖南凤凰古镇的名气太大了,大到似乎已是独家冠名,所以当友人说这是只西北凤凰,藏在秦岭腹地时,我一时有些恍惚。
凤凰是什么?它是一种神鸟,火红的尾巴,五彩的羽衣,“凤凰于飞,翙翙其羽”;它是楚国的图腾,高高飞翔,“凤凰鸣兮,于彼高岗”。湖南那只凤凰,是旧时的楚地,凭借环境的水灵,及沈从文先生不朽的文字,倒也勉强相称。但这秦巴老林里的小市镇,何也敢名“凤凰”?
我心中有不解,快速“百度”和“知乎”,知道凤凰镇是古时长安通往安康的要道,早在唐武德七年(624)就形成集市,当时叫做“三岔河口”(社川河、皂河、水滴沟在此交汇),清朝时改称凤凰嘴,民国三十年时再更名凤凰。

商洛柞水县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凤凰 摄影/视觉中国
凤凰到了。社川河穿镇而过,将集镇一分为二。一半新城,一半老街,中间靠小拱桥连着。
出新城,上拱桥,人还未站稳,一种别样的气韵便一下子抓住了视线。脚下,七八级向下的台阶,连接着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街道,两侧老式的板壁房,均从檐下拉出一块窄长的白塑料布来,挡着摆在摊位售卖的虎头鞋、绣花香包、纸折扇等。因刚下过雨,空气中有极洁净的味道,又吹来一阵小风,踩在地上干净、光滑的青石板上,看天上的云朵擦着头顶悠悠飘过,人不觉就有些痴了。
劲鼓鼓地顺街道逛,两侧均是板壁房,这是典型的清末和民国时代的建筑,一般两层,上一层有细木格窗棂,是卧房或储物间,下一层拆下门板,主人就能端坐家中做生意。因年代久远,木板壁大多呈了黑色,也有少量酱色,或许是长年刷桐油所致,走近,闻得到淡淡的桐油味。
家家的门脸是都木质的,其它三面的墙,却是土筑或石头砌,门槛全由长条巨石或石板铺成,屋顶都是飞檐翘角的。邻里之间,有的共用一堵公墙,有的各自独立,上面均立着防火墙,是徽派建筑的标志。左邻右舍的狗在门口或屋里山间追逐着打闹,为古镇添了一丝生活的气息。

凤凰古镇上的小摊贩 摄影/视觉中国
这是一条靠旅游来过日子的老街。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着黄色红锯齿边的幌子,上面用隶书写着“百年老字号”“古镇豆腐”“客栈”的字样。还有的幌子极具视觉效果,里面用桃红,处边用大红,大红又都裁成了条状,风一吹,上下舞动,妖娆得很。商户的招牌也做了统一规划,黑底金字木匾额,均挂在大门的正上方,用楷体书写。有两家的房子前另外挂了考究的木牌,一处叫“高房子”的是当铺遗址。另一处“茹聚兴”药铺,曾是红军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徐海东、曾子华等红军将领在此养过病。
洞开的门户里,有的是摆放着圆滚滚的白色编织袋码在地上,装满了百合干、木耳、香菇等山货;有的梁上悬着一条条腊肉,金黄油亮,散发着淡淡的烟熏火燎味儿;有的则放着一个个矮胖的青花瓷缸,里面装着当地名产神仙豆腐、各色酱菜等,琳琅满目。
长约三华里的老街,并不直来直去,而是有好几处拐弯,形成S 状。常常觉着走到尽头了,却不想一探头,眼前又是长长的街道。没有游客,店家们便坐在货旁,平静地看着街面。见人来,也不吆喝,你拢过去,他们才望着你笑笑,你不问,他们也不言语,朴实的如同贾平凹笔下的石头。
在“长盛祥”吃晚饭。这是街上最好的一处老房子,20 多个平方的开间,却有50 米的进深,分成了三进院子,全是木质大梁,木楼板,石板地,干净得想在地上打个滚儿。

河南南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荆紫关山陕会馆局部。 摄影/视觉中国
四个人,点了两壶老酒,七个特色菜,坐上四方桌,长板凳,店家殷殷在旁陪我们说些话,一时吃得醺醺然。晚上,听说我们还没住下,店家亲自领我们去一家酒店。我们顶着满天的星星,在青石板路上歪歪倒倒地往前走。
老板是位老者,党姓,清癯面善。他拿过我们的身份证,扫了一眼,突然说:“今年可把你们遭灾了!”我大吃一惊,旋即明白,心里不由得一阵温暖。登记房间时,老者略带羞涩地说,我们来前,他正在看他写的,发在《汉中日报》上的,怀念母亲的文章。
老者已年过七旬。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慈祥的母亲。原来深山古镇的漫漫长夜,老人都是独坐如俑,无尽地思念母亲。原来这老者也如老街一样,不显山不露水,却自有一番气象,一心一意与青山白云过日子。家里盖起了镇上最好的酒店,围了一个大院子,院墙上的画都是自己画的。去看了两幅,一幅是姜子牙钓鱼,一幅是柳宗元钓雪,见意境也见心境。临结账时,他打架一样硬是少收了我们20 块钱的零头,理由是:“你们今年遭灾了么!”
安康和南阳:寻找失去的记忆
因为汉江,我和家人与会馆碑刻结缘,这中间有一个长长的铺垫——
大江流日夜,会馆映古今。会馆,本意为开会和聚会的馆舍。中国会馆兴起于明初,兴盛于清代,在近代走向衰落。早期的会馆是为了方便举子应试,“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后来会馆之风由京城蔓延到全国,商人会馆反倒后来居上,成为主流。清康熙以降,拜汉水水运发达、襄阳区位优势所赐,山西、陕西、江西、安徽、河南等11 省商人在“南船北马”的樊城陆续修建了21座会馆。这一座座会馆建筑,就像是沿汉江漂来的灿烂明珠,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信息。多少年过去了,汉江上如林帆樯消失,南北商人风流云散,只有幸存的数量稀少的会馆成为商业的历史见证物。这些会馆已然成为襄阳地区商业文明的见证。
关注整个汉江流域的会馆乃至商帮文化,成为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碑刻便是最基础的一环。
碑刻是刻在石头上的史书,这个寻找过程,充满了艰难和失望,同时也充满了希望和满足。
2016 年2 月17 日下午,我们和老朋友刘贵棠到蜀河中学的三义庙校订碑文,这已是第二次校对了。三义庙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所建,带有同乡组织性质。现在已是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三义庙仅存拜殿,三通碑石尚存原处,个别字风化严重。我们用面粉涂抹后发现原来的一些错录,在草稿上更正并拍照。
2 月18 日早上7:30,一股寒气侵袭了刚刚醒来的我。推开蜀河小旅馆的窗户一看,天已下起小雪。我一个激灵,赶紧穿衣,下楼,穿过逼仄的街道,去黄州会馆和杨泗庙校对碑文。天光尚早,街道上空无一人。十年前的今天,在黄州会馆拍摄时不慎坠落差点要了家人的命;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却一致地对会馆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天太早,黄州会馆大门紧闭。我只好赶往杨泗庙,校对完三通碑文后,再急急返回黄州会馆校对另四通碑。几通碑风化严重,连面粉也不敢往上抹了,竭力辨认,订正了几处缺文。
雪越下越大,大有留客之势,我们却只能折返。驱车沿316 国道顺汉江而下,风雪漫天飞舞,想象中,客籍商人的船队从远处而来,在冷水、麻虎、夹河、白河沿线停靠,卸货,交易,补给,但很快又消逝了,只留下远去的帆影这样一个意象,只剩下白茫茫的大地上残存的会馆。
汉水流经陕、鄂、豫三省,南阳也属汉水流域。过去几年,我们只关注到社旗山陕会馆、荆紫关的会馆群,对南阳曾有一个与福建商帮密切关系的天后宫却并没在意。突然一天,南阳朋友发来消息,告诉我们那里保留有多通碑刻。听后,我们顿生要去抄录的强烈愿望,以至于夜不能寐,终于在2019 年3 月16 日,驾车前往。
襄阳、南阳比邻而居,同属南襄盆地,是上苍赐给人们的一块宝地。勤劳善良的人们在这一带稼樯劳作,贸易往来,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天妃庙就是福建商民北往中原,并将信俗移植中原的见证。可惜随着时代的流逝,处在主城区的天妃庙已是门可罗雀,一天也没几个人到访,这倒让我们安静地抄完了6 块碑,填补了旅居南阳的福建官员和商人在异地建立庙宇的文献空白。庙里的僧人中午为我们准备了斋饭。虽然只是一碗汤、一个馍,但一米一粟,皆来之供奉,思其来之不易,已胜似燕翅参鲍。

紫阳北五省会馆中的碑刻记录了汉江商业发展史。 摄影/杨军
趁着天色尚早,我们又匆匆赶到宛城区黄台岗镇禹王村。这里曾有山西会馆,在抗战时期被毁。所幸是碑刻被村里的有心人从公路上桥梁拆下,移到禹王庙里保管,和其他碑刻混杂在一起。趁着天光我们向村民做了调查并用相机对碑刻拍照。
南阳的会馆碑刻除了社旗山陕会馆、荆紫关山陕会馆受到学人关注外,其实民间遗存并不少。次日一早,我们又赶往汲滩校订2013 年第一次去时所录的会馆碑文。汲滩是邓州下辖的一个镇,位于湍河边上。之前已得到了内容,为慎重起见,再来核对。邓州文史学者常振会、侯保国两位先生专门请人开了车从邓州市区赶来帮助。
这些碑集中在镇上的初级中学,立在山陕会馆的东西山墙处,大部分碑文清晰,少部分字迹漫漶难以辨认。比较遗憾的是,大部分碑在当初移动重立时,为了牢固,都将碑石插了一部分在地下,导致每行都有一二个字不见天日。另有一块碑,将捐资题名放在正面,因无法确定是否与会馆有关,本来决定放弃,但不放心地把头凑伸到碑与墙的缝隙中辨认,竟然是《创建山陕关帝庙东西殿碑记》。也就是说:立时立反了!但问题来了,碑与墙之间太窄,根本无法容人站立,连伸个脑袋的空间都不够。大家连声叹息,现在不得不放弃。正在沮丧时,常先生竟然跑到街上买来一面镜子,然后手举镜子伸至碑后,靠着镜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就这样,爱人费力地伸手向碑上抹面粉,人像掉进了面缸;常先生和侯老师脑袋贴着脑袋,一字一字会商确定。一块不足700 字的碑却足足抄了两个小时,待抄完最后一个字时,已经是下午两点。

湖北襄阳,汉江中的柳树已经发芽。 摄影/视觉中国
就这样,我们四处搜罗汉江流域内会馆碑石的线索,进行田野调查,四处抄录,集腋成裘,终于搜集到近两百通移民、工商会馆,以及和工商业内容相关的碑文。无论是在号称“天下四聚”,并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的通商大邑汉口,还是在汉江干流上如旬阳蜀河、紫阳瓦房店之类的蕞尔市镇,甚至在汉江若干支流如南河一线的保康寺坪、神农架阳日湾这些偏僻之所,都有昔日商帮留下的足迹,吸引着我们一一造访,去捡拾和破译他们留下的记忆。这些有关会馆的、移民的、信仰的碑石不仅仅是一部清代汉江流域以及秦巴山区的移民史、垦殖史,还是一部那些勇于进取、不畏险阻、开疆拓土商人们用生命书写的生命史、贸易史、社会史。
沿汉水行走,踏访一个个会馆,或洗净一方方仆倒在地的碑刻,将上面的文字抄录下来,是孤独者满腔的情怀,也是对汉水无比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