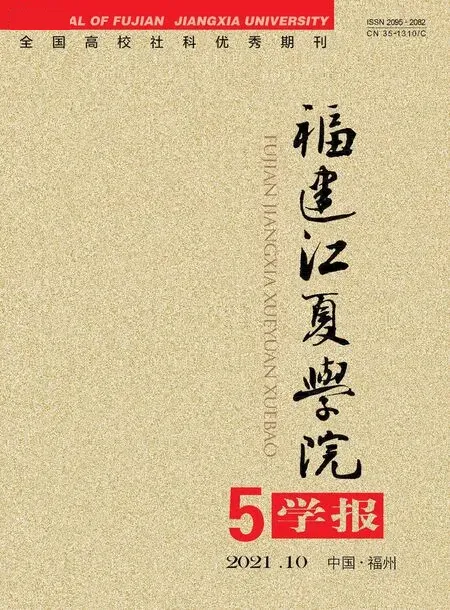中国当代文学生态异化叙事中的救赎
2021-02-27林钰婷
林钰婷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文学批评发展至20世纪中后期,为映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出现了新的研究维度——生态批评。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其伦理立场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爱为出发点,致力于探讨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从种族、地方、阶级、性别等维度探讨物质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由此具有了特定的审美目标——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作为当代生态危机与全球化社会发展双重现实语境下迅速兴起的一种文学批评新思潮,生态批评不仅具有传统的文学批评功能,还对现实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和强烈的使命感,显示出独特的现实批判和反思功能。生态问题早已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们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自然生态遭遇破坏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提出警示。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恩格斯所说的是自然界对人类行为的报复,这种报复造成了人类的生态危机。我们所讨论的生态异化就是指生态在发展过程中违背自然规律的异化,它有别于自然生态随着时序推移的正常发展变化。这种异化是对生态自然规律的颠覆,它打破了生态环境的正常状态、规律,制造出异化的生态环境。中国当代文学叙事文本作为以现实生活为根基的社会映射,自然也有大量生态异化的叙事描述。当然,叙事文本中的生态异化超越了自然生态异化的内涵,在自然生态异化现象的呈现之外还有着体现叙事策略的人为异化。它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手段,蕴含着作者的艺术构思。通过对客观自然的扭曲变形的文学陈述,融入人的情感、人的思绪,将自然空间维度转化为生态心理空间维度,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本文对生态异化叙事的空间形态作分类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生态异化叙事中物理空间向心理空间转化的特点。生态异化叙事空间形态不仅有外在形式的表象,还有心理空间,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及对人物心灵的挖掘,进而指向生态异化叙事的实质——内蕴的自然生态与人性的救赎。
一、生态异化叙事的空间形态
叙事生态空间有静态与动态两种基本状况。静态的生态空间一般以纯自然的状态展现其自然客观的一面,动态的生态空间则以一种发展、流动的状态展现其发展变化的空间面貌。这一动态发展在中国当代文学叙事文本中有时呈现一种扭曲、一种变形。作为一种叙事手法,生态空间的扭曲变形独具艺术创造力,呈现给读者独特的感受。
(一)客观自然景观的生态异化
自然景观作为叙事的空间语境,是人物活动的家园,承载着作者的创作意图,伴随着叙事进程发生转化。
客观自然景观的生态异化表现在叙事者对自然景观的动态描述中,这种描述展现了自然生态自身的繁衍变化。严歌苓《陆犯焉识》开篇就以对照的形式体现了自然生态空间异化的情景。原始荒原的生态环境以一种荒凉同时也以一种自由安详呈现出自然本性:在这样荒野而又自由的生态环境中,大自然和大草漠上的活物和谐相处。在隔着大草漠的“祁连山的千年冰峰”和“昆仑山的恒古雪冠”相伴下,活物们“漫不经意地开销、挥霍它们与生俱来的自由”。这种安宁祥和氛围的改变源自“一具具庞然大物”的汽车和带着枪的“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的到来。于是,大荒草漠的安宁祥和被打破了。文本叙事呈现了与前截然不同的场景,无法与荒漠原住民“相克相生”的人类给草原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自然历史上的两个生态时空在叙事开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铺陈,景物描绘为叙事奠定了生态空间基础和叙事情感倾向。人的介入破坏了生态平衡,给动物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远古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一种纯自然的、自由的莽荒之地显示出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凉、静谧和安宁。闯入的汽车、人群、枪打破了大自然的静谧与安宁,带来了生态危机。[2]这一生态环境的异化为文本叙事作了铺垫,定下了故事基调:人类对自然生态平衡的颠覆与人类的自相残杀这一不堪回首的历史由生态环境异化的叙事背景展开了序幕。
客观自然景观的生态异化还表现在叙事者对生态空间的变形描绘。这种描绘以突破了自然现象规律的状态呈现。如徐坤《三月诗篇》中的春天景象就以反常规的模式呈现在人们眼前,对“暖风”“巡夜猫”以及各种植物的描绘无不带有晦暗的色彩,矢车菊、狗尾巴草“怀着不可告人的阴险绿出地表”,已成名或未成名的花儿“都在阳光灼热目光的经纪下摆首弄姿,明争暗斗出一朵朵含苞欲放的阴谋”,加之“春天沦陷在三月里像一挂浸了水的臭炮,湿湿漉漉,欲哭无音”的比喻,春天的景色一反春暖花开、莺歌燕舞的季节常态,而是呈现一种阴暗、晦涩和沉闷。[3]这是由所选用的比喻“蛔虫一样在城市的腹腔内来回逡巡”“一挂浸了水的臭炮,湿湿漉漉,欲哭无音”,以及“疲于奔命”“不可告人的阴险”“摆首弄姿”“明争暗斗”“阴谋”等对景物的比拟描绘而体现的。这种反常态的季节描绘,有时是由人物行为的直接介入造成的,徐坤《先锋》描绘了这样的夏天:“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大马路和小胡同里,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像灰尘一般一粒粒地漂浮着。1985年夏末的局面就是城市上空艺术家密布成灾。他们严重妨碍了冷热空气的基本对流,使那个夏季滴水未落。”[4]艺术家的出现影响了气候,似乎有些荒唐。联系文本语境来看,这种荒唐正是对那个特定年代各种不学无术的艺术家风行一时的嘲讽。这种生态环境的异化是以人为主角参构的人为生态环境,人的奇异介入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异化,以夸张的形式增强了嘲讽的力度。
(二)主观自然景观——人物幻象中的生态异化
人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人参与自然、融入自然,人的思绪构想与自然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叙事文本在体现人与自然关系时展现了复杂的状态,所表现的可能是人与自然的交相融入,也可能是人与自然的变形关联。幻象就是呈现人与自然变形关联的一种生态异化形象展示,它体现了作者的叙事策略。
幻象是对现实现象的变形,它制造了一种超越常态的生态环境,以对自然的颠覆构筑了超越自然的空间模式。人物幻象中的生态异化不同于自然景观的异化,在这种异化中,自然景观的物理世界并未发生异化,但在人物的幻觉或梦境中,自然景观产生了心理异化。因此,这种异化是基于人物心理异化而产生的。幻觉制造的异化在特定的时空暂时改变了人物、事物与原有生态环境的关系,一旦幻觉消失,生态空间重回自然。
幻觉和梦境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并不常见,但在《雌性的草地》中却占有很大的比重。文本描绘了女子牧马班沈红霞和红军过草地时牺牲在草原上的芳姐子的相遇。这场相遇是以沈红霞目光所见描述的,她清晰地见到女红军的动作神态、女红军背上的血,这些情景显然出自幻象,但描绘却是逼真的。这一逼真的幻象出自沈红霞对女红军的敬仰崇拜。在草地这个空间,幻觉将三十年的时光相链接,三十年前后的人物相关联。这种时空穿越,由幻觉而起,又在幻觉中趋于真实。复活了的女红军形象、动作栩栩如生,人物间的交流跨越了时空达到了高度融合。幻觉中女红军的出现,使沈红霞所处的这片草地异化为三十年前的空间地域。同样在这个文本中,沈红霞还在幻觉中与垦荒时期牺牲在草地上的陈黎明相遇,时光又一次超越现实,将镜头拉到垦荒年代。[5]在这些幻觉中,地点环境、人物形象、动作神情以及心理活动真实可见,以虚幻情景穿插于现实叙事中,具有特定的叙事韵味。
如果说,沈红霞的幻觉是在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定空间中产生的,那么,有时候幻觉则是人为环境制造的,苏童《独立纵队》中小堂就是在一伙顽童的威逼下产生了幻觉,实现了自己“独立纵队”的梦想。这是小堂被顽童们悬吊在横跨空中的水管上,疼痛难忍时产生的幻觉。在幻觉中“小堂的恐惧感奇异地消失了”,围着他嚷嚷的化工厂的男孩们化成了“红旗下排列整齐的”“他的队伍”,化成了一条巨大的写着威风凛凛四个大字“独立纵队”的横幅。这一幻象源自小堂中午午睡时的梦境,梦境的重温居然消除了他被悬吊的痛苦,他在被顽童们用布条塞住嘴巴之前,喊出了“独立纵队成立啦,纵队成立啦,成立啦……”。[6]77-89在幻觉中现实消失,幻象生成。幻象是对现实的悖反,却是对小堂心向往之的梦想的顺应。梦想实现在幻觉中当然是非现实的。这种非现实是在极其残酷的人为空间环境中生成,顽童们残忍的行为制造了对小堂构成心灵与肉体创伤的空间环境,因此,小堂于幻想中的梦想实现实际上意味着人物的毁灭。
梦境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生态环境展示,与幻觉一样,它是基于联想想象,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暂时的颠覆。梦境可能是基于现实的客观世界,将客观世界移植到虚幻的生存空间。上述小堂“独立纵队”的幻觉实际上与他曾经的梦境有关,小堂回忆他的梦境是一面火红的写着“独立纵队”四个字的旗帜,而这一梦境又是与他在现实中的梦想相关。小堂因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在香椿树街感到孤独,在表哥的安慰下,他渴望成为“香椿树街独立纵队的司令员”,这一梦想在现实中没有实现,却在被威逼产生的幻觉中变成现实。苏童《回力牌球鞋》梦境也是关联着现实的。陶得到一双宝贵的回力牌球鞋,极端的爱护使他日夜担心球鞋失去。在夏日午后昏昏欲睡中,陶做了个“短促而奇怪”的梦,他“梦见那双白色回力牌球鞋像两片树叶在风中飞舞,它们在香椿树街上空飞行了一段距离后就消失不见了。”这个梦基于现实又关联于现实结果,当他被梦吓醒后,却发现墙上的回力牌球鞋确实不翼而飞,“现实与梦境的吻合几乎使陶瘫在那堵院墙下”。[6]165梦境的球鞋飞行是虚幻的,而球鞋丢失的结果却是真实的,叙事就在这真真假假中展开。由此可见,梦境、幻象都是基于人物所处的现实世界,是现实在人物大脑中的变形映射。在映射中,它间接反映了人物所处的现实世界。
二、物理空间向心理空间的转化
幻觉、梦境等幻象与人物心理密切相关,通过幻象,将自然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心理空间,表现出人物在特定时空中的心态。幻象制造的生态异化实际上是物理空间向心理空间的转化。
(一)物理空间表象中的心理空间
幻象以物理空间的表象呈现人物心理空间,进而窥探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幻象的物理空间是人物心理空间的印射,幻象的制造生成是作者体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策略。张抗抗《隐形伴侣》中多次出现主人公的梦境,每个梦境都是人物在特定境遇中内心世界的映像。如陈旭向肖潇摊牌,要么马上跟他走,永生永世不分开;要么分手,永生永世不再见面。两难中,肖潇选择了第三条路:不走、结婚。接着出现了肖潇的一个梦境,先是茫茫草原,对将死的马车夫呼喊的救助,而后出现了与结婚相关的情景假设:去教堂举行婚礼,但破四旧,这是不现实的;她选择“旅行结婚”,可由于被老鼠咬坏的帆布箱无法装物而无法前行;要结婚登记,可街道办事处无人。更为荒诞的是她想不起来要和谁结婚。继之而来婚姻法规定的五十岁结婚年龄和自己十五岁年龄的反差。撩开红盖头新娘不是她自己,而她却如释重负。这些情况体现了对结婚的逃避。不走、结婚这条路并非肖潇的最佳选择,内心的矛盾彷徨溢于言表。文本中还有多处梦境,表现了肖潇生活的各种情景。如在北大荒莽莽荒野,陈旭向她求爱被拒绝后,肖潇梦见了临湖的公园,妈妈带她寻野花的情景;在小屋结婚时,“她走进一座冰雪的宫殿”的情景;与陈旭离婚后,她梦见被压在瓦砾堆,满身是伤的情景。[7]这些梦境,或者与肖潇此时的心态相和谐,或者相背离,但其间的关联是耐人寻味的。梦境设置的空间情景由物理空间转化为心理空间。通过生态空间的异化,将其转化为人物的心理空间,是人物心理描摹的一种艺术手法。异化的生态空间制造了叙事空间的内化,使生态空间成为人物心态描述不可或缺的空间因素。
(二)心理空间印射下的物理空间异化
物理空间可能制约或生成人物的心理空间,反之,心理空间也可能对物理空间构成反制作用。即,作为人物生存活动的空间环境,自然景观的异化牵系着人物的处境、人物的内心活动,它可能促成人物心理的发展变化。与此相对,人物的处境及心理也可能作用于自然景物,使之变形。前面所讨论的人物幻觉、梦境所制造的物理空间实际上也是因人物的心理因素所产生的物理空间的异化。这说明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可能互为因果、互相印射。这种印射可以造成人物心理的物理空间异化,也可能造成人物视觉中的物理空间异化。张抗抗《隐形伴侣》中,有一段肖潇赴北京办理调离手续未果,失望回到北大荒所见的情景,以“一个巨大的黄色漩涡”喻天地,以“一粒沙”喻自己,加之“魔鬼的哭声”,星星“穷凶极恶的争吵”,大海的咆哮,“生锈了的地球轴心的呻吟”,汇聚成“愤怒、快乐、摧毁、死亡” 的疯狂合奏。描绘了太阳湮灭、月亮破裂、天空撕成碎片的地球毁灭的图景,显然是对自然景象的变形描绘,更是肖潇心理空间的印射,是其精神世界极度痛苦无望的写照。心理空间使物理空间变形,物理空间又融入人物的心理空间,二者交相融合,交汇构成对人物在某一时空语境下生存状态的叙事。
梦境作为对自然生态空间的超越,其变形有时是基于虚幻的。这种虚幻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并没有现实的基础。这种梦境对自然生态空间的颠覆程度更深,物理空间向心理空间转化的程度也更为明显。苏童《我的帝王生涯》没有确定的年代,没有确定的现实人物,在这完全虚构出来的故事中出现的梦境,缺乏现实基础,处在一种荒诞的虚拟中。作品演绎了似真似幻的虚幻梦境,一是“我”八岁那年看见过的一些白色小鬼,“每逢掌灯时分,那些小鬼就跳到我的书案上,甚至在棋盘的格子里循序跳跃,使我万分恐惧。觉空闻讯赶来,他挥剑赶走了白色的小鬼。因此我从八岁起就开始崇拜我的师父觉空了。”再一是雨夜中所做的噩梦,“在梦中看见一群白色的小鬼在床榻四周呜呜地哭泣,他们的身形状如布制玩偶,头部却酷似一些熟悉的宫人,有一个很像被殉葬了的杨夫人,还有一个很像被割除手指和舌头的黛娘。”这一梦境的逼真使“我吓出了一身冷汗”。第三个梦境是白色小鬼的再度降临,“现在我清晰地看见了他们的面目,是一群衣衫褴褛通体发白的女鬼。他们在我的龙榻边且唱且舞,是一群淫荡的诱惑人的女鬼,冰清玉洁的肌肤犹如水晶熠熠闪光。”这一梦境中“我不再恐惧,不再呼叫僧人觉空前来捉鬼。在梦中我体验了某种情欲的过程。”[8]这是文本中出现的三个与“白色小鬼”有关的梦境。虽然第一个梦境主要是为了引出师傅觉空,虽然梦醒后“床榻上的锦衾绣被依然残存着白色小鬼飘忽的身影”增添了梦境的真实性,虽然“白色小鬼”的出现是因为杨夫人和黛娘等人之死让“我”受到惊吓,但梦境依然是虚构的,它的虚构在于整个故事超越现实而存在的文本整体虚构性。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作者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一个古代帝王的独特世界。 因此,它是对现实生态空间的一种极度变形。这种变形赋予了文本以虚幻的物理空间,而物理空间的生成仍是心理空间的呈现。作为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苏童突出体现了先锋作家的叙事特征,“文化姿态的先锋性,作家群体的当代性,文学技术的实验性和文学思潮的颠覆性。”[9]虽然《我的帝王生涯》的时代背景并非当代,但其叙事构想的时空超越、语言异化的狂欢实验都体现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颠覆。
三、生态异化叙事空间的救赎意义
生态异化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有着其深层的意义蕴含,它的创作并非以生态空间的扭曲变形为目的。扭曲变形是手段,是表层形式,探寻其异化意义,应该在表层异化中探寻深层的寓意。这种深层的意义,可能在于对生态环境现状的反思,也可能在于对生态环境未来的期盼,由此显现了文本生态异化叙事策略中的叙事意义。中国当代作家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关注并揭示生态异化现象深层的社会本质,不仅延续传统叙事对环境的描写、对环境与人的依存关系的讲述,而且将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生态异化中的人性、人的反思。不但展现生态异化的时空,而且制造异化的时空语境,充分调动联想想象、荒诞异化的艺术手法,将叙事手法发挥到极致。体现从生态异化叙事的物理空间向心理空间延伸,进而思考对生态异化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理救赎。
(一)生态环境救赎的隐性呼喊
董强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基于哲学的生态批判精神、和谐发展的生态哲学视野和改造世界的生态实践情怀的特征。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提供了思想的指南;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揭示了生态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动力,从生态交往的角度分析了生态文明冲突与融合的解决方式,即建立在普遍交往基础上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变革。”[10]全球生态危机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并引发了全球社会的关注。生态危机映射在叙事文本中具有其独有的表现形式。空间异化中的生态空间可能呈现出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违背,这种违背映照在叙事文本中可能是人物生存的恶劣环境。对生态恶劣环境的描绘讲述,其中常常蕴含着对生态环境救赎的呼喊。这种呼喊因了叙事文体的艺术性特征,往往不是直露的表白,而是隐含其间,所以,是一种特定语境中的隐性呼喊。
苏童笔下的南方河流,失却了古诗词中“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而以污浊、丑陋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体现了现代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水鬼》中的河流是:“装满油桶的船疲惫地浮在河面上,橹声的节奏缓慢而羞涩。油桶船从桥洞里钻出来,一路上拖拽着一条油带,油带忽细忽粗,它的色彩由于光线的反射而自由地变幻,在油桶船经过河流中央开阔的河面时,桥上的女孩看见那条油带闪烁着彩虹般的七色光。”[6]53这样一条飘着油污的肮脏的河流最终吞没了一个女孩的生命。《西窗》中的河流是南方罕见的二十米宽护城河,许多木排和竹排停泊河岸两侧,通过沿河的居民的眼光,描绘了那一年四季停泊在岸边的木排和竹排,天长日久,风吹雨淋,“被水浸透的圆木上长满了青苔,而竹排的缝隙里漂浮着水葫芦、死鱼和莫名其妙的垃圾”的情景。在这样的河边生活着自私、饶舌、搬弄是非的红朵祖母,说话真真假假,最后莫名消失了的红朵。[6]203《舒家兄弟》中的河流是两岸房子密布横贯南方城市的河流,“河床很窄,岸坝上的石头长满了青苔和藤状物。我记得后来的河水不复清澄,它乌黑发臭,仿佛城市的天然下水道,面上漂浮着烂菜叶、死猫死鼠、工业油污和一只又一只避孕套。”[6]247-248以“烂菜叶”“死猫死鼠”“工业油污”和“避孕套”为河面“景观”的描写,“乌黑发臭”的“城市的天然下水道”的联想,不难让人想见“黑黝黝地密布河的两岸”的房子中人们杂乱无章、丑陋污浊的生活。躺在地板上,浑身滴着水的死去的涵丽;头发花白,为了满足私欲强暴了十几岁少女涵贞的老史……与这肮脏污浊的河流形成一体。丑陋污浊的河流是对原生态自然景观的异化,这种异化下承载的是人类的欲望、堕落、罪恶与毁灭。因此,这样的生态景观是人们意欲改造的。当然,基于叙事文本艺术性的特点,改造的呼声更多地隐含于叙事文本中。
(二)人性救赎的期盼
如前所述,生态空间异化是物理空间向心理空间转化的一种模式,一种艺术手法。因此,在异化的生态空间中我们的视角不仅在于物理的现实空间,而应触及人物的心理空间。
苏童《蛇为什么会飞》仅看标题展现的就是一个异化的生态空间。作为爬行动物的蛇,却具有了“飞”这样的禽类状态,这是物欲横流社会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异化。故事开端于蛇,由此开始了蛇贯穿始终的叙事。六月的蛇灾让这个小城显得恐怖混乱,但人们借此危机,开始了物欲的追求。贺氏兄弟开办了蛇餐馆,动物园变成了世纪蛇园,展览馆展出的都是美女蛇……文本中多次大段对蛇的描绘构成了一个蛇泛滥的城市异象。但蛇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关联着故事中的人物,在盥洗室因看见蛇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的金发女孩,在讨债的拉特公司上班的混混克渊,被追债而最终跳下世纪钟的美男子梁坚,构成了充满现代感的物欲横流的生态环境。蛇甚至关联了人物的命运走向。梁坚在自杀前常常梦见蛇来催他的命。克渊坐在火车上,看见了会飞的蛇。这是克渊感觉中的蛇,与其说属于现实的物理空间,不如说属于克渊的心理空间。在经历了目睹梁坚跳钟,与金发女孩交往因“有病”而受挫的种种磨难,渴望金钱财富、渴望社会地位,也渴望着爱情的克渊,最终以失败告终而选择逃离。[11]蛇在文本中已超越了物化的符号,而带有深刻的寓意。文本通过生态空间的异化,展现了物欲横流的城市生存图景,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小人物内心的焦虑、渴望、追求与失望。与其说文本表现的是对生态环境救赎的呼声,不如说是对人性救赎的呐喊。这种救赎最后以小人物的死亡与逃离告终,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人性救赎与环境救赎相伴随,在对环境救赎的期待中,也伴随着人性救赎。或者说,人性救赎改变了人的观念,从而带来了环境救赎的期望。有些叙事文本在展现生态危机的同时,往往赋予了生态乌托邦理想,在生态环境救赎的同时,隐含着人性救赎的深刻寓意。晓航《一起去水城》就是这样的文本。叙事不仅展现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展现人文环境的恶劣。因此,文本的“逃离”不仅是对生态环境救赎的向往,而且是对人文环境救赎的向往。文本开篇就将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关联,概括了这个城市的两个特点,一是“任何季节都可以随时到来的大风以及与之相随的沙尘暴”,一是“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努力找工作”。这两个特点在故事即将结束,沙尘暴肆虐的描写之前又一次出现,显然具有点题作用。故事讲述了一个从“海龟”变为“海带”的MBA“我”所经历的奇遇。标题的“水城”是人们向往的生态家园,是不受污染的人类生存的乐园。与之相对的,是文本中人物生活的沙尘暴肆虐的城市。文本中有三段大篇幅对沙尘暴肆虐情景的铺陈渲染,“沙尘暴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又一次袭击了这个妄自尊大的城市”,狂风大作,黄沙肆虐。文本描述关涉自然生态的沙尘暴这一恶劣的自然现象之余,还写出对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梦想。冯关的情人余心乐挚爱“天天天兰”:“这真是一盆漂亮的花,即使它的叶子沾满了尘土,也掩盖不了它动人的美丽。”余心乐没有正当职业,当“妈咪”,后又与弟弟一起偷窃旧车,但她却相信爱情,崇尚自然。在她眼中“植物是有情感,有知觉的”,因此她把天天天兰视为“到达这个城市之后唯一忠诚的朋友”,感慨它所遭受的来自当地水和风沙的悲伤。对人与自然的情感在她心目中是关联在一起的。在她看来,作为忠诚朋友的天天天兰又关乎情人冯关。在她眼中,天天天兰有情感、有思想,因此借这一植物预示了这个城市“将遭到更大的风沙侵袭,它的水将继续变酸变少”的生态环境恶化。而这样的环境使“一株特别需要水来呵护的植物”与冯关无法生存。冯关与植物相同的个性,决定了余心乐对冯关生存环境改变的构想:“如果想让他生存下去,他就必须活在一个拥有充沛雨水,拥有真正清泉的城市。”这就预设了故事结尾“一起去水城”的情节走向。而叙事源头的冯关,是制造“我”与情人余心乐,与冯关发妻林岚纠葛的始作俑者。这个依靠老婆生活的寄生虫,这个因为无聊而在网上出让老婆和情人的人,对自然却有着特别的情感与追求,他“因为无所事事,因为怀念自然”而盖了一个湖滨园林,以寄托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由此可见,余心乐与冯关的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对自然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又因恶劣的自然气候而屡遭摧残。这激发人们思考,激发人们变革。最后,林岚决定给冯关以自由。她在地图上寻找了一个城市“水城”,“它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清澈最丰沛的清泉,而且终年雨水不断”。这是适合冯关生活的生态环境,故事终结于“冯关和余心乐最终逃离了这个城市”。当然,逃离只是一种回避,因为人物最终并未改变自然。小说的结尾段设想着“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全都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曾经热爱的这个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风沙日盛,包围了整个城市。留有光明结尾的是城中广大的绿洲,和天天天兰因缺水花朵变小而长出刺。这刺代表着对生态污染的抗争:“那刺坚韧挺拔,代替了叶子,每当风沙狂卷而至时,天天天兰仅剩的叶子就蜷缩起来,而刺们就挺身而出,向着风沙以一种生命的力量望空扎去……”[12]虽然,人类生存条件日渐恶劣,但抗争不止,生态回归就有着希望。这是冯关、余心乐们的愿望,也是文本叙事在末尾留给人们的启示。
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当代社会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程度也日益强化。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生态异化叙事体现了时代热点,它反映了当代社会对生态问题的极度关注,对生态异化的深刻反思。叙事文本中对生态异化的叙事反映了与人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依存、抵牾与协调,与当代社会焦点问题密切链接。
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生态异化叙事除了自然生态异化之外,还侧重于作为叙事艺术手法的人为异化,因此,既是对自然生态异化现象的探讨,又是对文本叙事策略的探讨。综观当代叙事文本,生态异化叙事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叙事形式的丰富多样,语言的独特异化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不同的作家以各自的生活体验和感悟,以敏锐的目光和艺术视角,讲述生态异化的故事。与内容有机融合的生态异化叙事手法也以其变幻多样、突破传统叙事的模式,展现了当代叙事文本特有的艺术构思、叙事手法的独创性、多样性。对中国当代文学叙事文本中生态异化叙事内容与叙事手法的探究,融入到生态批评的文学探索大视野,已成为文本叙事研究的一个可拓展的视点。基于生态批评多学科交融的研究视点与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叙事文本中生态异化叙事的研究融入了文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相关原理与方法,无疑更新了文本叙事的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视野,增强了研究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