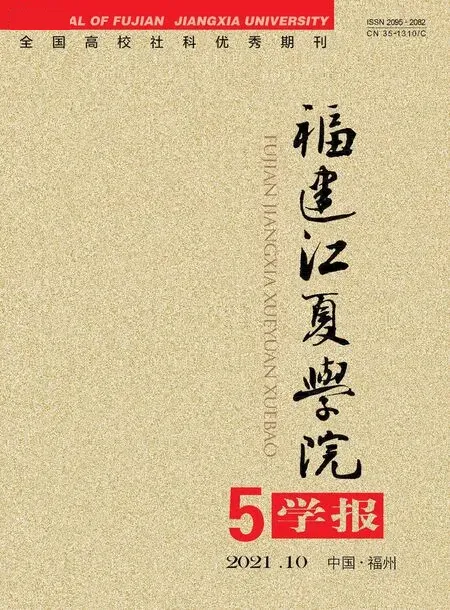正当程序原则在中美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的适用
2021-02-27林臻煜马忠法
林臻煜,马忠法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38)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是各国在引入外资的过程中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安全阀制度。该制度在为东道国经济持续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也将对国际投资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2020年,随着美国在TikTok事件中对中国的发难,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引发我国学者对此的关注和探讨。为规范该制度在各国的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应当得到遵守和重视。OECD早在2008年发布的《经合组织关于外资接受国国家安全政策准则》中,就对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了程序性方面的要求;此外,2013年的罗尔斯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委员会一案(以下简称“罗尔斯案”)①Ralls v. CFIUS, 758 F.3d 296(D.C.Cir.2014).,也奠定了正当程序原则在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适用的法律基础。目前,适逢我国外商投资领域新法相继出台,为了更好应对竞争加剧的国际经济形势,同时避免该制度对国际投资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本文将从正当程序原则的角度出发,进行以下探讨:首先,本文将分析正当程序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适用的意义及可行性;其次,解析该制度自“罗尔斯案”以来在美国的发展变化情况,一方面将有助于我国投资者了解美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现状,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完善当前外资国家安全制度提供比较和借鉴的维度;最后,本文将以我国新出台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为对象,分析正当程序原则在中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的适用困境,并提出制度构建建议。
一、正当程序原则及其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适用的意义
(一)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涵
正当程序起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 justice)②Clause 39 of Magna Carta.,后被美国宪法所吸纳,成为一项宪法性原则③参见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第5条、第6条及1868年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等。。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全球化的推进,大陆法系国家也逐渐构建起正当程序理念,并纷纷将其纳入自己国家的宪法条文或者司法实践中。④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委内瑞拉等国。至此,正当程序原则确立起宪法性地位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⑤关于正当程序原则的全球实践,参见罗智敏:《论正当行政程序与行政法的全球化》,《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1期,第22-31页。,成为约束公权力行使的重要保障。
尽管各国正当程序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非完全相同,但其基本内核却是一致的。在《布莱克法律辞典》中,正当程序的核心内涵被解释为:“任何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听审的权利。”[1]美国最高法院也在司法实践中明确了正当程序条款要求:“被剥夺财产的当事人得到充分的通知和申诉的机会。”⑥Mathews v. Eldridge, 424 U.S. 319 (1976).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20号行政审判指导案例——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中指出,正当程序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可能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应当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向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告知事实,并说明理由,听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8]因此,正当程序原则的核心要求可以被归纳为: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不利行政行为作出的事实和理由,并听取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申辩。
(二)正当程序原则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适用的意义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下简称“安审制度”)是东道国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建立的外资筛选机制,最早由美国设立。2001年“9·11”事件以后,该制度在全球范围建立起来。[3]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资的涌入在给各国带来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应运而生的“安审制度”在平衡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导致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成为各国推行保护主义的工具,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国际投资秩序。如何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缓和国际经贸关系,如何在充分理解各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之动机的基础上兼顾外国投资者对健康市场环境的需求,成为国际投资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正当程序原则表现出其巨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从性质上而言,正当程序原则作为制约公权力行使的重要原则,在公权力与私主体相对抗的“安审制度”中应当予以适用。“安审制度”的主体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机关,比如在中国,安审由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负责;而在美国,相同的工作则由外资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CFIUS”)甚至美国总统来完成。这些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对象是外国私主体,因此,从制约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行政法理念出发,“安审制度”本身应当受到正当程序这一行政法甚至宪法性原则的约束。有学者从全球行政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经济领域私主体会因为各国实行不同的行政规则而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得到普遍承认的正当程序则将发挥着约束与监督国内公权力、确保私人在全球层面得到更好保障的重大作用。[4]有关国际组织为促进正当程序原则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适用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OECD在2008年发布的《经合组织关于外资接受国国家安全政策准则》中提出,资本输入国需满足“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的义务,即采用政府内部监督、议会监督、司法审查、定期监管影响评估等手段对当局进行监督,并保证作出重要决定的是高层级的政府主体。[5]这一建议通过要求当局采取行政监督、议会监督、司法审查等方式,为当事人搭建起了告知、陈述与申辩的平台,体现了正当程序原则的核心要求。
从实践角度而言,相较于制定全球统一的国家安全标准,以程序的正当性约束各国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领域的保护主义倾向更具有可行性。随着国际经济关系摩擦的加剧,世界各国纷纷就外资审查中的“国家安全”给予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定义,而这些定义体现出各国关于国家安全认定标准的不一致性、模糊性与裁量性,并有泛化的可能。鉴于国家安全本身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主权性的问题,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往往会出于对行政机关的尊让,避开对国家安全标准合理性的探讨。因此,投资者若从实质性角度出发对各国审查标准提出质疑是十分困难的,而从程序的角度出发,因为世界各国对正当程序原则具有普遍的共识,并将这一共识反映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法院等主体往往可以从程序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对外资安全审查程序进行监督,为外国投资者提供适当的救济。因此,正当程序原则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应用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与实践上的可行性。
二、正当程序原则在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的适用
(一)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规则
美国是最早建立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国家。具体而言,CFIUS由美国福特总统于1975年设立,美国1988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赋予了CFIUS审查外资的权力,奠定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基础。1992年《伯德修正案》进一步强调了CFIUS对特定类型交易的审查。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以及2008年《实施细则》对美国外资审查程序的委员会成员构成、具体程序、适用范围以及政治责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进。美国2018年新出台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下简称“FIRRMA”)以及2020年颁布的《实施条例》对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进行了程序上的调整和制度上的完善,扩大了其审查范围,增强了国会监督,加大了对来自中国投资的关切,并针对信息的保密性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构建起了一套更加成熟、完备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
具体而言,外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前的安全审查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当事人的申请/申报阶段。目前,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可由三个路径被提起:当事人可以通过提交正式的书面申请(Written Notice)来发动外资安全审查;也可以选择通过在材料方面更加精简的申报程序(Declaration)来启动审查;在当事人不予配合的情况下,CFIUS还可依据职权提起单方面的审查。值得一提的是,申报程序是2018年FIRRMA提出的一个新程序,分为自愿申报和强制申报两种类型,并配有一个专门机制识别属于CFIUS管辖但当事人没有提交书面申请或者申报的交易。⑦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7, S. 2098 /H. R. 4311, Sec. 1710.其次是国家安全审查阶段。这是对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隐患的交易项目进行初步审查的机制,如果外资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进一步评估后仍然认为交易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可能,则审查进入国家安全调查阶段。在这一阶段,委员会将对项目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考察和评价,如果认定交易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则需要提交给总统进行最终决议,总统所做的决定将通过行政令的形式发布。
(二)美国正当程序原则及其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的适用
正当程序原则在美国具有宪法性原则的地位,并在司法实践中被法院广泛运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⑧“No person shall . . .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参见U.S. Const. amend. V.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也有相同的表述。⑨“…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参见U.S. Const. amend.XIV.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地方法院均认可当事人有权得知决议作出的事实基础以及获得陈述和申辩的权利。⑩参见 Mathews v. Eldridge, 424 U.S. 319, 334-35 (1976), Greene v. McElroy, 360 U.S. 474, 496 (1959), Gray Panthers v.Schweiker, 652 F.2d 146, 165 (D.C.Cir.1980).
从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成文法规则来看,尽管法律在程序性事项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并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肯定的是,立法对于外资安全审查的流程以及每个流程所需要的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且规定了CFIUS及总统在每个阶段所做决策的告知义务, 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2008年和2020年《实施细则》中均规定:“在审议申报、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和国家安全调查的过程中,委员会可以(may)邀请交易双方进行会面,交流、明确与交易有关的一些问题”“在国家安全调查阶段,交易当事方可以请求(may request)与委员会成员会面,这样的请求通常会得到批准”。⑪Provisions Pertaining to Certain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Foreign Persons §800.601(b).从语言表述上来看,尽管当事人拥有与审查委员会进行会面和交流的权利,但是这样的会面其实是由CFIUS掌握主导权,内容也多体现为CFIUS对当事人的询问。条文未明确规定总统在作出最终决议后应当将决议理由向当事人进行披露,也未规定当事人拥有对决议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
但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的合议庭在“罗尔斯案”中所作出的判决,部分完善了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立法上的缺陷:
首先,判决明确了法院对外资安全审查的总统决策程序具有审查权。尽管立法规定了“总统针对外资安全审查所做的决策不得提交司法审查”⑫Defense Production Act (2018) Sec.721(e)(3).,但法院认为,除非存在明确且具有说服力(clear and convincing)的证据表明国会有此意图,否则不得排除法院基于宪法性诉求而进行司法审查。⑬Ralls p320.通过对文本进行最自然的解读,以及对有关立法文件以及立法历史的分析后,法院认为国会仅意图阻止对决策本身的司法审查,却没有意图阻止对决策过程进行司法审查。此外,政治问题原则(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也对司法介入外资安全审查提出了挑战。该原则认为,如果处理某一问题将面对政策选择,则此问题应当交由立法或者行政机关而非法院进行处理。毋庸置疑,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法院认为当事人关注的程序性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因此,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对外资安全审查总统决策程序事项的审查权。
其次,判决明确了当事人在受到外资安全审查时有权得知审查决策所依据的非保密性证据,并对此进行陈述、申辩。具体而言,法院认为正当程序原则规定当事人有权得知决策行为作出的事实基础,因此,CFIUS应当向当事人披露作出审查决策的非保密性证据。此外,正当程序原则规定当事人应当具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而针对这一点,地方法院和巡回法院的态度存在差异。地方法院认为,罗尔斯公司这一方面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CFIUS已经履行了立法中所规定的告知义务(如书面告知当事人交易审查被受理等),罗尔斯公司也获得了向CFIUS展示对其有利证据的机会。可以看到,地方法院的观点是只要成文法赋予投资者的权利没有减损、成文法施加给CFIUS的义务得到了履行,正当程序原则就得到了满足,也即只要满足了法定程序,就满足了正当程序;但巡回法院并不认为正当程序原则仅限于成文法中的规定,巡回法院认为,罗尔斯公司向CFIUS展示对其有利证据的机会并不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其应当有权得知最终审查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并有机会对此进行反驳。⑭Ralls, p320.
(三)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罗尔斯案”确立了当事人对审查决策所依据的“非保密性证据”的知情权,但这一权利的行使仍然面临以下困难:
首先,在立法规定中,“保密信息”的范围过大。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有关立法规定了审查程序中“保密信息”的范围。⑮Defense Production Act (2018) Sec. 721(c).根据该规定,除了以下例外,任何提交给总统的信息都将被视为“保密信息”:(1)与行政或司法行为、程序有关的信息;(2)向参众两院或经合法授权的任何国会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披露的信息;(3)涉及美国政府实体或美国同盟国或合作伙伴政府实体的信息;(4)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向第三方披露的信息。⑯Defense Production Act (2018) Sec. 721(c)(1)(2).然而,美国“安审制度”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总统决策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面临CFIUS将决策证据提交给总统,从而使这些证据成为“保密证据”的局面。
其次,“非保密信息”还可能受到“行政特权”(executive privilege)的保护。“行政特权”是宪法根据分权原则赋予总统以及其他行政官员的特权,免除他们向法庭、国会公开发布彼此之间通讯内容的一种权力。当争议信息涉及行政机关对于国家安全的考量时,往往会因行政特权而得到豁免。⑰United States v. Nixon, 418 U.S. 683 (1974).“罗尔斯案”中,CFIUS一方也提出了此类抗辩,巡回法院在最终判决中指出,这一抗辩事由可在案件发回地方法院重审时进行判断和处理。⑱Ralls, p320.尽管该案最后是以和解告终,我们无法得知美国法院在判断“非保密信息”是否属于“行政特权”一事上的标准,但可以看出法院对此事的重视,也反映出当事人想要获得“非保密信息”仍然困难重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FIRRMA新增了两条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可以看出受到了“罗尔斯案”的影响)。一条专门规定了诉讼程序中保密信息的披露,即如果法院认为这些信息对于案件的解决是必要的,那么,这些信息也仅能以非公开形式、单方面地呈现给法庭,而法庭应当将这些信息密封处理。同时,“保密信息”的认定标准来自于任何法律,即其他法律规定的“保密信息”都将适用本条的规定(如前面所提到的行政特权所豁免披露的信息)。⑲Defense Production Act (2018) Sec. 721(e)(3).这一规定完善了行政机关对信息的掌控,杜绝了投资方在庭审过程中接触任何美国法律规定的“保密信息”的可能。另一条则排除了《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中“信息使用”(use of information)等条款的适用。⑳Id.信息使用条款规定了当政府决定将通过电子侦察所获得的情报在法庭作为证据使用以对抗受政府决定、行为不利影响的人时,政府应当在庭审之前通知对方以及法院,政府将使用上述信息。㉑50 U.S. Code § 1806 (c)(e).而如果这些证据的取得具有非法性,或者未得到合法授权,则相对人可以向法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因此,如果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排除了这些规则的适用,那么,投资人将无从得知政府作出决策所依据的证据来源,从而也就丧失了依法对这些证据进行反驳、排除的机会。
综上,尽管“罗尔斯案”被认为是中国投资者对抗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一次胜利,为正当程序原则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上的适用奠定了基础,但从实质效果来看,当事人想要行使正当程序权利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事实上,“罗尔斯案”为美国完善自身在外资审查规定提供了契机和思路,而修改后的法案将进一步限制正当程序原则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
(四)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立法与实践为正当程序原则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的适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该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借鉴。具体而言:
首先,应当明确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程序问题的可审查性。通过对立法文件中“总统针对外资安全审查所做的决策不得提交司法审查”这一表述的分析,美国法院认为这里所谓的“决策”仅指决策内容本身,而不包含决策作出的过程,从而将外国投资安全审查过程中的程序问题与实质问题区别开来,肯定法院对程序问题的司法审查权。这一判断思路具有宝贵的价值,其在极度敏感且专业的国家安全话题下为司法审查开辟出一条可行的进路,从而完善了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了当事人的法定权利。
其次,应当将正当程序原则落实到具体的审查规则上。尽管美国在成文法规则中并未对投资者的程序性权利作出充分规定,但是其在“罗尔斯案”中所构建的普通法规则落实了正当程序原则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的适用。具体而言,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可概括为“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不利行政行为作出的事实和理由,并听取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申辩”。而将这一要求转化成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的具体规则,则表现为“有关部门应当向投资者披露国家安全审查决策作出时所依据的非保密性证据,并允许投资者对此进行陈述、申辩”。需要注意的是,各国可以自行作出保密性证据的判断标准,但必须做到公开、明确。此外,投资者对外资安全审查决策进行陈述和申辩的具体形式也可能不尽相同,东道国可以根据情况作出符合国家政治体制的具体设计。
最后,应当在尊重正当程序的基础上保障行政主体的实质审查权。如前所述,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是东道国外资引入的安全阀制度,其与国家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和专业性,法律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不会改变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内在政治特质。[6]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各国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并收紧安全审查权力。因此,我们应当明确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并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事实上,从专业性角度出发,行政机关就外资国家安全的实质审查权应当得到充分尊重。我们应当将行政机关作出的实质审查决策排除司法救济的范围,与此同时,当事人对安审决策所做的陈述和申辩也应当面向行政机关进行,并最终由行政机关作出判断。
三、正当程序原则在中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的适用困境与建议
(一)中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规则
我国于2006年构建起了外资安全审查的初步框架,其后的《反垄断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査概念。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商务部文件的相继出台, 形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程序规则。㉒参见陶立峰:《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可问责性分析》,载《法学》2016年第1期,第71页。2020年12月19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安审办法》”)出台,取代了原来效力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安审制度”运作的具体规则。
区别于美国,我国外资安全审查规则要求在安全审查范围内的所有并购交易均需提请安全审查,当事人对此不存在选择的余地。2020年新规则对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主体以及流程作出了较大变更,取消了商务部作为“消息传递中间人”的地位,使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取代联席会议成为“安审制度”的主体,减少了内部程序的繁琐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在一般性审查的过程中如果认为交易影响国家安全,则将启动特别审查程序。此外,新规则还取消了“对存在重大争议的交易报送国务院决定”这一审查流程,使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成为作出安审决定的唯一主体。㉓参见《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
(二)中国正当程序原则及其在外资安全审查中的适用困境
正当程序原则作为英美法系的舶来品,得到了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普遍认可。我国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4条确立的“法定程序”审查标准是正当程序原则规则化的体现,《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强制法》也对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提出了原则性和具体性的要求;国务院在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将程序正当列为了依法行政的要求之一。㉔《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发〔2004〕10号。此外,我国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确立了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涵为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不利决定的理由,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㉕如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决定案等。然而,区别于美国,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安审制度”中的适用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
首先,我国外资安全审查立法缺乏对当事人正当程序的保障。尽管2020年《安审办法》的出台对我国安审程序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修改内容并未涉及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美国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法院对外资安全审查总统决策程序的审查权,但是我国未区分程序审查与内容审查,一并将“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排除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范围外。㉖《外商投资法》第35条。此外,美国立法中规定当事人拥有与审查委员会进行会面和交流的权利,法院通过判例确定了外资安全审查过程中当事人对审查结果的陈述、申辩权,以及对审查结果所依据的非保密性证据的知情权。但中国立法仅规定了当事人“在向商务部提出并购安全审查正式申请前,申请人可就其并购境内企业的程序性问题向商务部提出商谈申请,提前沟通有关情况”㉗《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公告2011年第53号,第4条。,“当事人向工作机制办公室申报外商投资前,可以就有关问题向工作机制办公室进行咨询”㉘《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第5条。,“工作机制办公室对申报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期间,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提供相关材料,并向当事人询问有关情况,当事人应当予以配合”㉙《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第10条。。而没有规定审查过程中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主动进行沟通的权利,也没有规定当事人对审查依据所拥有的知情权以及对审查结果所拥有的反驳权。
其次,我国行政法立法仅提供“法定程序”保障,而没有提供“正当程序”保障。在美国,正当程序原则是一项宪法性原则,因此,理论上美国法院可以通过行使其违宪审查权,对任何违反宪法中正当程序规则的行为进行审查。在我国,正当程序并未被列入我国的宪法条文中,且在行政领域的有关立法中,我国也并未采用“正当程序”这个概念,而是采用了“法定程序”的表述。如现行《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针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有权予以审查,并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以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因此,从立法语言的表述来看,我国法律保护的是当事人有明确成文法规定的程序性权利,而非自然法意义上的正当程序。如前所述,我国安审立法中对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的规定是不足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法定程序”不完善的情况下,能否将“正当程序”作为一般的法律原则对当事人进行保护?换言之,在安审立法没有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告知投资者不利行政行为作出的事实和理由并听取陈述和申辩的情况下,投资者能否通过“正当程序原则”来获得这些权利?鉴于正当程序原则并未成为我国的一项宪法性原则,也不像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一样存在一般条款,因此,能否在成文法缺位的情况下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仍然存在探讨空间。
(三)中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规则的改进出路
1.明确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投资者可向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寻求权利保护
首先,明确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中投资者权利具有可救济性。新《外商投资法》第35条第2款规定“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有学者认为,该条款意味着外资安全审查决定被排除在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范围外。[4]但笔者认为,根据文意解释,该条款不排除行政机关或法院对“非法”作出的审查决定的审查权。“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中的“法”应当同时包括实体性法律规定以及程序性法律规定。因此,若当事人的实体性或程序性权利受到侵害,则行政机关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审查决定因其非法性而应受到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审查。
其次,明确在成文法尚未完善的基础上,投资者可依据“正当程序原则”寻求权利保护。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安审立法缺乏对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安审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权利应该如何得到保障?也即,当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办法》并未规定外国投资者具有某些权利的情况下,投资者是否可以从别处为自己的权利寻找法律依据,从而提起权利救济?笔者通过对目前“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情况的观察,认为《外商投资法》第35条第2款“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中的“法”除了包括成文法中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还应当包括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正当程序原则”。因此,当事人可以在缺乏“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援引“正当程序原则”保护自己的程序性权利。
事实上,作为舶来品的正当程序原则是作为“法的一般原则”被引入。[7]国务院在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将“程序正当”列为了“依法行政”的要求之一。在缺乏成文法规定的基础上,法院在实践中仍然普遍认可其作为法律原则的地位,并援引其作为司法裁判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第38号指导案例(“田永案”)中,法院在没有明确成文法依据的情况下,认为“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第104号案例(“赵博案”)中,法院认为:“从行政法治角度来说, 即使法律没有程序规定, 行政机关在执法的时候,也应当遵守正当的程序……这是依法行政必须遵循的最低的程序要求, 达不到这个要求, 也应当视为程序违法。”事实上,美国巡回法院在“罗尔斯案”中采取的态度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一致,均认为“法定程序”的满足不意味“正当程序”的满足,行政机关应当依据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为当事人提供保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将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公理等实定法之外的法源作为裁判理由论证的可行性。㉚参见《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13条:“除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外,法官可以运用下列论据论证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非司法解释类审判业务规范性文件;公理、情理、经验法则、交易惯例、民间规约、职业伦理;立法说明等立法材料;采取历史、体系、比较等法律解释方法时使用的材料;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与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相冲突的其他论据。”由此可见,我国所提出的“依法行政”“依法裁判”等概念中的“法”均包含了作为一般性法律原则的“正当程序原则”,且司法实践确立了在成文法缺位的情况下法院援引“正当程序原则”作为司法裁判理由的正当性。
因此,笔者认为,“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中的“法”包含“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安审立法对于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并未作出充分的规定,当事人仍可以援引“正当程序原则”,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要求行政机关向其披露决策所依据的非保密性证据,并提供陈述和反驳的机会。
2.进一步完善外资安全审查领域成文法规则,加强立法对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的保护
目前,以促进和保护为立法宗旨的新《外商投资法》已经出台[8],2020年12月《安审办法》也浮出水面,然而,两者在投资者保护上的规定犹如天壤之别。事实上,我国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仅对安审流程作出较为笼统的规定,如第9条规定“特别审查应当自启动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但并未提及特别审查程序的具体流程和机制,为后续立法留下空间。笔者认为,无论是出于以“对等原则”缓和中美经济关系的目的,还是出于顺应外商投资领域立法趋势的目的,都应当增加我国“安审制度”中对投资者正当权利保护的规定,尤其是要求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在作出最终不利决定时,告知当事人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性证据,并提供当事人对审查结果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因此,鉴于我国安审立法中对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保障的缺失,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安审立法中“总体规则”+“实施细则”的立法模式,对我国安审程序和规则作出进一步补充。
3.在保障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的基础上,确保对外资安全审查决策进行实质审查的主体为行政机关
第一,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流程内部增加“复议”程序。如前所述,“正当程序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告知利害关系人不利行政行为作出的事实和理由,并听取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申辩。然而,这样的程序往往涉及到国家对外资安全问题的实质性判断。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取消了对安全审查内容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倾向,且国际社会的主流做法也是多将国家安全概念的解释权上收,体现了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较为浓厚的政治性色彩。鉴于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专业性、政治性,以及司法机关出于自身专业局限而对行政机关的尊让心态,笔者认为,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实体性问题应当交由专门的行政机关进行判断,法院不应当成为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作出改变原有安审决策的主体。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在最终的安全审查决定作出前设立一个“内部复议”程序。在该程序中,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应当向当事人披露作出决策所依据的非保密性材料,给予当事人陈述和反驳的机会。此外,鉴于目前《外资安全审查办法》中并未对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的组成人员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在“内部复议”程序的制度设计上,笔者建议该程序中的审查人员相比第一次审查时的人员应当具有更高的行政级别。这一内部“复议”机制的存在既满足了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也保障了外资安全审查的专业性。
第二,法院对安全审查决策的司法审查仅限于形式审查,实质审查权归属于行政机关。尽管如前所述,当事人的实体性或程序性权利如果受到侵害,则行政机关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审查决定因其非法性而应受到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审查。事实上,在缺乏明确国家安全定义的情况下,投资者就实体性权利提起救济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因此,尽管该条款应当被解释为不排除对安审决策进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审查的可能,但实践中其效果仅限于对投资者程序性权利的保障。此外,当投资者以《外商投资法》第35条第2款为基础对侵犯自己权利的安全审查决策提起诉讼请求时,笔者认为,为尊重行政机关对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实体性问题的判断权,法院对于非法安审决策作出的判决应仅限于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依法作出审查,而不包括法院直接代替行政机关作出最终决定。比如,当事人认为我国安全审查机关并未向其披露非保密性证据,或者未给予其陈述、申辩的权利,此时法院的判决仅限于责令行政机关撤回生效的实质审查决定,向当事人披露决策所依据的非保密性证据,并提供当事人对审查结果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在此基础上由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实质性审查和判断。也即,为尊重行政机关对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实体性问题的判断权,应当确保行政机关是实质审查的唯一主体。
四、结语
中美经济摩擦是当代国际秩序与竞争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在国际投资领域,外资国家安全审查作为东道国外资准入的安全阀制度,在审查标准上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色彩。因此,以审查程序作为切入点、以正当程序原则作为理论依据来实现投资者保护无疑更具可行性。
“罗尔斯案”是正当程序原则在美国安审领域中一次成功的适用,但经过对美国现有制度和规则的研究后,可以看到投资者在安审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仍然是不充分的,这一问题在FIRRMA出台后变得更加严峻。中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立法更是缺乏对投资者正当程序的保障,可能会使我国在此方面受到国际社会的攻击和指责。鉴于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当首先明确《外商投资法》中安审决策的终局性条款并不排除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非法安审决策的审查,且在安审“法定程序”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法院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中的裁判精神,允许当事人依据“正当程序原则”寻求权利保护。此外,我国应当在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基础上,以“实施细则”的形式进一步改进现有“安审制度”,完善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此外,应当在保障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的基础上,确保对外资安全审查决策进行实质审查的主体为行政机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可以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流程内部增加“复议”程序,提高“复议”程序中审查人员的行政级别;另一方面,则应当约束法院对于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决策的司法审查权,确保其仅具有形式上的审查权。
推动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国家外资安全审查中的适用,是我国“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理念下的应有之义。其一方面贯彻了我国依法行政与行政公开化的理念,有助于避免国际社会的指责;另一方面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有助于在尊重国家安全主权的情况下保障投资者利益,化解不必要之冲突,维护健康的国际投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