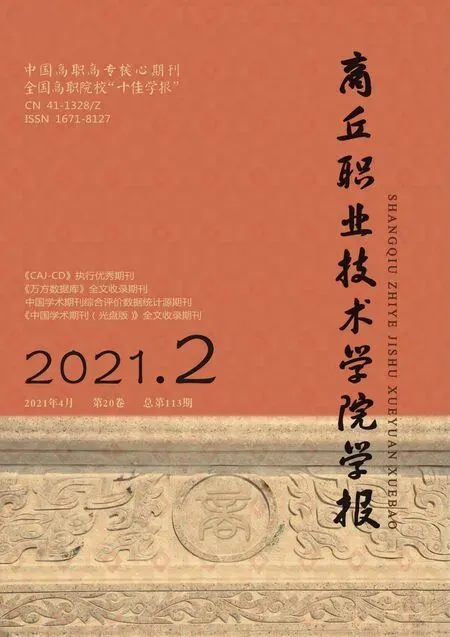社会生态预警小说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使女的故事》
2021-02-13曹颖哲陈婧绮
曹颖哲,陈婧绮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位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虽年逾八十,仍笔耕不辍,因其作品题材广泛、文体多样并具有鲜明的创作特色,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并于2019年获得英国文坛最高奖项——布克奖。1985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了其经典之作——《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借助《使女的故事》中所虚构的故事,传达了其对女性生存现状的不满与批判,以及对女性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期盼。这部作品不仅是作家对女性生存与命运的思考,更体现了她对整体社会生态的深切关注。“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则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后者包括但不局限于两性关系。《使女的故事》中对未来社会秩序的担忧及构建和谐社会生态的愿景,与“疯癫亚当”三部曲《羚羊与秧鸡》《洪灾之年》《疯癫亚当》等作品中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一同构成了阿特伍德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强烈的生态意识。如果说“疯癫亚当”三部曲属于自然生态预警小说,那么,《使女的故事》则是一部社会生态预警小说。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重要分支,也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其权威理论家西蒙·德·波伏娃从存在主义哲学中借用的“他者”“内在性”“超越性”等概念,不仅可以用于女性生存境遇及出路的分析与探讨,其独特的存在主义立场也可以运用于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使女的故事》,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作品中的女性主题,更可以透视出作品中所折射的生态内涵,揭示作品的深刻的社会生态预警性质。
一、极权压迫下的“他者”困境
波伏娃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2]序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里,构建了一个极端的男权社会——基列国。男权的压迫使基列国的女性沦为他者,而神权则对女性的这一地位起到了巩固作用。
(一)男权的压迫
在基列国这个男性垄断了一切权力的社会里,男性代表了积极、主要及合理,女性则代表消极、次要及反常。基列国成立后,女性被划分为主教夫人、嬷嬷、经济太太、使女、马大及荡妇。她们失去了工作,财产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移到家庭里的男性手中。被剥夺工作和财产的女性不得不从社会转向家中,就连地位最尊贵的主教夫人也被束缚在家中,彻底沦为了他者。
在基列国,拥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归为“使女”,她们被迫为没有子嗣的当政主教们服务,沦为他们的生育工具。每个使女的脚踝都会被刺上1个眼睛和4个数字的编号,这标志着她们已成为基列国的国有资源。使女身处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下,一切都高度统一——穿戴一致,吃住行格式化,处处受着监管。她们戴着宽大的白色双翼头巾,被迫与外界隔离,全身被“血一般的红色”[3]8长裙包裹,穿平跟红鞋不是为了跳舞,而是保护脊椎以免影响生育。使女在基列国存在的全部价值就是生育,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被抹去,完全沦为男权制度下的他者。
基列国的主教夫人们看似地位尊贵,并享有上层社会的优越条件,但其在家里却连进入丈夫的书房的权利都没有。她们要么不断地编织围巾、照料花园,似乎这样才能带给她们些许自由的感觉;要么就藏在卧室里借酗酒来麻木自己,迫使自己接受现在的生活。其中,赛丽娜·乔伊曾经是位才华横溢的女高音歌唱家,其嗓音优美动听,演唱情感丰沛,因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而广为人知。但在基列国成立后,她却再也没有机会将自己的才华展现给世人。往日充满个人魅力的女高音,而今只能依附、顺从丈夫,同时还得忍受那些不断前来为丈夫生育的使女们。虽身为主教夫人,乔伊却只能整日囿于家中,处于封闭、被动的状态。男权统治下的她,再也无法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去实现自我价值,只能麻木地遵守男性统治者制定的价值体系与行为准则,因而陷入他者的悲惨困境。正如波伏娃所揭示的,男权社会的男性承认女性对生育所起的作用,但所承认的只是“她携带并养育了由父亲单独创造出来的活精子”[2]10。
(二)神权的压迫
基列国的当权者借《圣经》里不能生育的利亚让使女代替自己和拉结孕育生命的故事,为使女的存在和“授精仪式”编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授精仪式以主教朗读《圣经》开始,在主教同使女例行公事般地结合后,仪式结束。仪式的整个过程要由主教家中的司机和佣人马大们在场见证。“基列的荒唐在于它否认‘人’是社会结构中不可侵犯的结构单位”[4]。授精仪式让本应是爱与私密的性变成了毫无人性的仪式。授精仪式对于使女和主教夫人来说都是一种羞辱,使女夹在主教与主教夫人之间,被迫充当生殖器官,完成没有感情的生育过程,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而主教夫人却不但不能以妻子的身份阻止使女来到家中,还要在每一次的仪式中亲眼见证整个过程,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她们为了维护自尊,只能尽力压抑自己的情绪。
基列国的使女不但沦为主教的生育工具,而且没有属于自己的姓名。她们仅有的名字是表示所属关系的“of”,即奥芙,若加上所服务主教的姓名,如“offred”,则表示其是属于弗雷德的使女。“名字代表了历史、身份和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命名和解释等语言符号活动使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5]。使女们被剥夺了姓名,也就丧失了主体性,同时失去了按照自己心意孕育生命的权利。为了生育,她们被剥夺了一切自由,连吃饭也只能以生育为目的——成为“一个有用的容器”[3]69。嬷嬷会安排她们吃一些健康餐,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在管教她们时却会毫不留情地鞭打她们的四肢,人们不在乎她们是否四肢健全,在基列国,使女要做的就是子宫健康,能够生育。更可怕的是,在一次次的扭曲价值灌输下,这种畸形神权衍生的观念被使女们内化成她们自觉的要求。一位原名珍妮的使女,在感化中心忏悔时,讲述了她被轮奸和流产的经历,却被嬷嬷训诫,说珍妮不应该引诱男人,是上帝为了教训她才发生这种事。在以后的忏悔中,珍妮为讨好嬷嬷而自我责备,受到嬷嬷的赞扬。最终,珍妮彻底迷失了自我,成为奥芙沃伦,变成主教的生育机器。使女们仅仅作为生育工具而存在,一旦成功为一个主教生了孩子,立马会被送进下一个主教家中,改名换姓成为另一个“奥芙某”,继续生育。至此,她们被畸形的神权物化,彻底沦为神权压迫下的牺牲品。
二、内在性束缚中的自我迷失
“‘内在性’描述的是一种无休止地重复着对历史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工作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女性一直处于封闭、被动、毫无作为的生存状态”[6]。波伏娃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2]309整个文明体系逐渐造成了女性被内在性所束缚的情况。基列国的女性被灌输生育至上的观念,即女性需要顺从男性,安于家中,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这种观念逐渐内化为基列国女性的内在性,导致她们从根本上深受男性的主导思想的影响,意识不到女性身为他者的窘境,心甘情愿地沦为男性的附属甚至帮凶。
(一)男性帮凶
嬷嬷心甘情愿地扮演着男性统治女性的帮凶。屈服于男性极权的嬷嬷常带着乞丐般低三下四、战战兢兢的媚笑,对男性当权者做出俯首称臣的姿态。她们对男性当权者谄媚,转眼却严厉地训诫使女,训斥她们应该把进入主教家庭前训练的日子当作在军队里服役。嬷嬷认为,使女“不是在坐牢,而是在享受特殊待遇”[3]8;使女应当珍惜在基列国统治下免受危险,不用担惊受怕的日子,并把使女身份视作一种享受自由的特权;使女对眼下所不能接受的一切总有一天会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嬷嬷自我洗脑而不自知,反而站在女性的对立面,时时刻刻规训使女。她们忽略了正是男性极权统治将女性推向了迷失自我的境地,导致女性处处受限,不再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现实。嬷嬷之所以有这种认知困顿,是因为她们无法挣脱内在性的束缚。
主教夫人赛丽娜·乔伊在基列国成立前,为了帮助丈夫的事业,到处宣扬女性应该安于家中相夫教子的观念,呼吁女性把照料家庭视为神圣的义务。由于内在性的束缚,她把支持丈夫当义务,因而成为男性帮凶,亲手把全体基列国女性推向深渊,走上扼杀自我意识的绝路。
(二)男性附属
基列国主教的仆人马大负责操持家务、照顾使女。其中,马大卡拉羡慕使女,她甚至表示:“假如我再年轻十岁,假如我还没有结扎,可能我也会那么做,其实并不是太坏嘛,毕竟不是什么苦力活。”[3]10卡拉从心理上接受男权统治,毫不质疑地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及他者身份,仅狭隘地看到使女无须做家务的轻松,却无法客观清晰地意识到使女同自己一样,同样遭受男性当权者的压迫与奴役,并且受尽羞辱。卡拉被男性极权统治洗脑,丧失了判断力,陷入了自我意识迷失的窘境。使女奥芙沃伦被嬷嬷洗脑,以为主教孕育生命为傲。她挺着大肚子出门,故意去使女们采买的商店里炫耀自己,脸上神采飞扬,而其他使女既嫉妒又渴望,期盼能够像她一样怀孕生子。此时的使女们俨然忘却了羞辱,心甘情愿地接纳了使女的身份,接纳了生育第一的观念,甚至以此为荣。
在内在性的束缚下,基列国的女性无法正视自我价值,心甘情愿地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将生育视作一切,她们实现自我的方式是“在孩子身上自我完成和自我超越”[7]。她们囿于次要者的地位,无法主动争取主体地位,更无法解放自我,享受自由,最终陷入屈从他者身份的困境。
三、争取独立平等,成为自由的主体
波伏娃指出,女性作为“他者”“第二性”,“在所给予她们的客体即他者角色和坚持自由之间犹豫不决”[2]56。她认为,若想摆脱这种困境,女性就应走出家庭,走进社会,走进生产,超越自我。基列国的女性尽管处于男权和神权的双重压迫之下,也有部分女性一度因为内在性的束缚而迷失了自己。但是,她们最终还是通过树立坚定的信念、坚持自我、追求独立,摆脱了他者困境,超越了内在性,争取到女性独立与两性平等,改变了极权统治下女性的命运,使自身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一)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神权和男权的高压之下,使女们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但压迫愈强,她们对自由愈是渴望,在对自由的怀念和向往中,她们的自我意识一点点生根发芽。奥芙弗雷德走在采买的路上,她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往日自由快乐的时光。她路过河边时会想起那些赛艇运动中充满活力、你追我赶的年轻人,追忆那些作为独立个体时的美好生活。当身着短裙和高跟鞋的游客来到基列国时,奥芙弗雷德内心对穿着自由的向往与渴望让她无法自拔地停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群游客。在房间躺下休息的时候,奥芙弗雷德会强调躺和放倒是不一样的,放倒是被动的,躺下是她主观意识下的行为。她珍视每次自主选择的机会。此外,她意识到:“名字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于是,我把那个名字珍藏起来,只待有朝一日有机会将其挖出,使之重见天日。”[3]88这些都是她追求自由的表现。在主教家时,没有书写工具,没有倾诉对象,奥芙弗雷德就臆想出一个“你”,在脑海里不停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期盼能与现实世界链接,强化自我意识,不被基列国思想同化,这是她自我意识觉醒、逐渐超越自我的体现。渴望真实自我的使女们,会趁着嬷嬷们不注意的时候,越过床与床之间的间隔,相互触碰,相互慰藉,通过唇语,互通姓名,找寻真实的自我,默默反抗。奥芙弗雷德曾在主教家住着的房间橱柜底部发现一句话“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3]54——“永不要被恶人打垮”,这是之前一位使女所刻下的。这句密语代表着使女在向世界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这是她们自我意识无声的萌芽与觉醒。
(二)主体意识的树立
基列国的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她们抓住点滴机会对抗基列国的各种规则,反抗男权和神权统治,挣脱自身内在性的束缚,争取自由和独立,进行挑战极权、超越自我的勇敢尝试,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自由的主体。在被禁锢的日子里,奥芙弗雷德渴望通过触摸物品来丰富自己的感官,她竭力地感受着触感带给自己的真实体验。她抓住帮马大做面包的机会,体会类似触摸肌肤的感觉,“我渴望触摸除了布料和木头之外的东西,我对触摸这一动作如饥似渴”[3]11。她会在心中哼唱一些往日从母亲的旧卡式盒带上听到的禁歌,享受片刻逃避规矩的自由。她享受洗澡时触摸头发的奢侈,意识到“我必须呈上的是人为的我,而不是本来的我”[3]69。她将黄油藏在鞋里,独处的时候用它护理皮肤,这是她对自身被定义为生育机器而只需要保障身体内部健康的反抗。对外貌形象的追求是她坚信终有一天能够离开这里、摆脱使女身份的动力。她一遍遍地念叨着自己原来的名字,以此警诫自己不要忘记往日曾作为自由独立的主体活在世间。
主教夫人让奥芙弗雷德与尼克私会是她对大主教权威及基列国制度的挑战;奥芙弗雷德和莫伊拉冒着被发现的危险,违反规定,悄悄约在卫生间交流信息,是她们对自身权利的积极争取;莫伊拉制订逃出感化中心的计划并加以实施,在经历了第一次失败之后,被拖回感化中心,遭嬷嬷毒打,脚肿到无法下地,仍然选择伪装成嬷嬷的样子第二次出逃,是她对自由的勇敢追求。这些都是基列国的女性追求作为自由主体的冒险与尝试。
四、结语
阿特伍德曾把科幻小说分为真正的科学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以及预测性小说。作为预测性小说,《使女的故事》展现了阿特伍德对“可能发生的事情”[8]的预测,其叙事的终极目的既非再现现实,也非表现情感,而是对人类未来生活的一种预设,是关于人类命运的寓言,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可以说,《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但却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小说,归根结底,它是一部关于“人”的小说。作者借女性隐喻一切处于极权之下或面临灾难的弱势群体,如时代落伍者、社会底层人士、被边缘化的人等等,甚至用以折射其对加拿大民族身份、世界人权等问题的思考。因此,《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以女性故事为载体,就未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态给人类以警醒的一部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