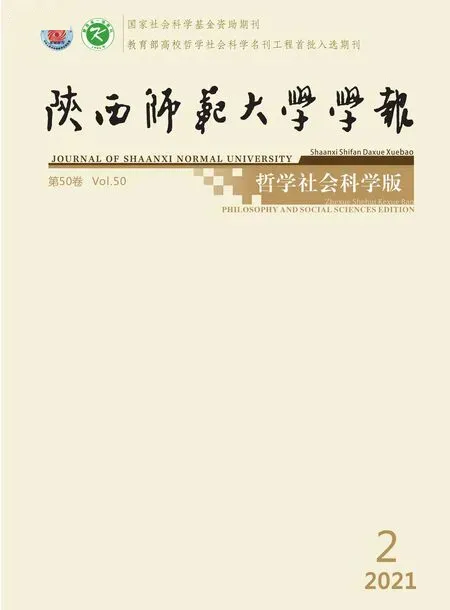21世纪新加坡酬神戏演出的困境与求存之道
2021-02-01王琳
王 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成果颇丰,在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等多重维度全面开花,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对华文文学在当代的生存现状进行思考,在研究视域上给予本文一定启发。比如程国君的《〈美华文学〉与汉诗拓展——美华诗歌的诗体探索与全球性主题展现》就是对当代汉诗走向海外的多元发展及其所表现的现代性思想进行研究,进而去关注全球化视野下海外华族文化的生存现状与当代价值。[1]
就戏曲领域而言,在进入新世纪全球华族戏曲发展整体式微的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其在当代社会的存在价值。以新加坡酬神戏为视窗,去探索华族戏曲在新世纪的存续命运,不只可以辐射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演剧情况,还是对其他海外地区华人社会戏曲生存现状的透视。21世纪学界多聚力于对新加坡华族戏曲的在地化研究以及对剧院戏曲的艺术性探讨,尚未有人对民间酬神戏进入21世纪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本文从这一空隙去探究传统戏曲在华人民间社会的生存状态与当代社会价值,不但有利于反映出新世纪新加坡华族戏曲的生态全景,更有利于发掘传统华族文化在当代传承的现实意义。
一、 19—20世纪新加坡酬神戏演出的历史回顾
新加坡的酬神戏肇始于19世纪上半叶,1842年美国远征探险司令官威尔基斯在《航海日志》中记录了新加坡华人在游行神会上的戏曲演出[2]476-478,这是目前所见新加坡酬神戏,亦即华族戏曲演出的最早记录。据当时在新加坡任职的沃尔根描述,人们“在庙宇前的方形广场围起高墙,建起临时戏台供戏曲演出……华人的神显示出特别喜爱戏曲”[2]478。这一时期的酬神戏不只是华人借助原生文化圈与新的生活环境相调适的产物,更是当时华人在海外社会的主要精神娱乐。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华族戏曲整体发展欣欣向荣,除了延续19世纪酬神演戏的传统外,戏曲还在商业化的戏院与游艺场演出,业余剧团也开始崭露头角。虽然有了更为广阔的演出空间,酬神戏依然是华族戏曲演出的重要阵地。据宋蕴璞描述:
新加坡内华人所建之关帝庙、大伯公(土地神之类)庙皆甚多。殿前亦设有戏台,遇神诞日或有许愿者则演剧以饗神。上焉者,演上海大戏,次则粤班戏、闽班戏、潮州戏,又次则傀儡戏,庙最小者则演小傀儡戏……每次演戏率以三日为期,常有数处同时并演者。演时观者男女毕集,昼间尚少,晚间尤众,直至夜深戏止,始纷纷散去。计每次演戏所费,多者千数百元,少或数百元,至少亦数十元。通计全年演戏之费,约不下数百万元,亦可谓巨矣。[3]149
20世纪初的酬神戏主要以潮剧、闽剧和傀儡戏为主,偶演粤剧和京剧(1)宋蕴璞所说“上海大戏”即京剧,由于当时来新加坡演出的京剧艺人多来自上海,因此新加坡称京戏为上海班。参见周宁《东南亚华语戏剧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4页。。从宋蕴璞统计的酬神戏演出费来看,20世纪30年代左右新加坡全年的酬神街戏演出应该不下几千场,其演出盛况可见一斑。
与中国酬神戏的主阵地在乡村不同,新加坡的酬神戏因受宗乡社团的控制而集中在城区发展,在当地被称作“街戏”。进入20世纪,新加坡酬神戏才逐渐深入乡间。随着新加坡城市人口开始膨胀,华族以方言群为单位向市区外扩散,形成众多华人村落(新加坡称“甘榜”),其在农历新年、神诞日、中元节的祈福禳灾习俗为酬神戏在乡村演出提供了广阔市场。例如,万里港福德祠在甘榜时代每逢大伯公诞和中元节,会请戏班合办大型祭祀活动。[4]随着华人社群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筹建神庙、举办迎神赛会已经不再是宗乡组织的特权。在帮权庙宇之外,乡土小庙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1910年一位普鲁士贵族下乡游玩时见到华族村落的神庙戏台有酬神戏演出。[2]4961927年榜鹅甘榜登加村村民合力修建了供奉天后娘娘的神庙[5]25,每逢神诞演戏酬神。数量多、分布广泛的华人村落成为酬神戏的演出重镇。1942年日本占据新加坡,在商业化戏曲演出被严重波及的时刻,酬神戏反而常演不衰。“日本占领时期,木偶戏班常有酬神戏演,跑遍后港、樟宜等海南人聚居的山芭”[6],乡村社会的酬神需求一度成为日据时期新加坡职业戏班生存的主要支柱。
战后新加坡华族戏曲再度繁荣,并在20世纪50年代迎来最后的黄金期,酬神戏也随着复苏的演剧大环境而继续兴盛。华人社会巨大的酬神需求直接影响到当地戏班与剧种的命运:20世纪50年代的酬神戏几乎是潮州班的天下,潮剧也因此迎来最辉煌的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福建歌仔戏和歌台开始抢占酬神戏市场,并借助街戏舞台发展起来;粤剧则因较少用于酬神演出而逐渐衰落。
1965年新加坡独立,其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变化极大地影响到华族戏曲的生存,尤其对酬神戏发展形成致命性打击: 一则华族村落变成组屋,打散了方言社区,乡村民俗文化受到冲击,不仅导致酬神戏演出机会锐减,还失去了其庞大而固定的观众群; 二则政府在乡村征地使得许多庙宇和戏台被拆除,如后港斗母宫建于1924年的大戏台因政府要拓宽马路在1998年被拆除。除了某些帮权庙宇被保存下来,其余稍有财力的庙宇三五结伴组成联合宫,大多乡土小庙则沦为散布在组屋区里的神坛,酬神戏赖以生存的宗教祭祀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三则政府出台专门针对酬神街戏的限制政令,如1974年发布的限制噪音条例,1975年发布的限定戏班演出场所条例以及限制夜戏演出时长条例;四则观众的流失,一方面电影、电视、歌台、话剧等多样化娱乐的兴起夺走了大量戏曲观众,另一方面随着老一辈移民的离世,在新加坡出生的华族后裔受西方文化影响甚深,对用方言演出的戏曲及宗教习俗缺乏相应的文化认同;五则是演出酬神戏的职业戏班多因生计困难而解散,少数幸存者又因政府禁止雇佣童伶而陷入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困境。[2]545-554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后酬神戏随着新加坡的政治独立、经济现代化以及主流文化的西化而走向没落。
二、 酬神戏在21世纪陷入发展困境
进入21世纪,新加坡酬神戏的演出情况延续了20世纪末的低迷状态,观众严重流失,许多职业戏班因此解散,导致酬神戏在21世纪陷入发展困境。21世纪的酬神戏由于观众严重流失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酬神戏。据2012年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为庆祝妈祖诞,本地一些庙宇和会馆邀请多场木偶戏同天竞演,乃难得一见的热闹景象,然而观众就只有庙里的妈祖和众神。[7]无独有偶,2017年的《联合早报》报道:“红山熟食中心附近的一个空地上,正上演着酬神街戏,观众席里没有半个观众。”[8]酬神戏虽为祀神而设,其娱人功能亦不遑多让,尤其在新加坡庙会文化出现后,酬神戏的娱人功能甚至更加突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马巴实龙岗村的几座华人庙宇经常搭台演戏,台前有江湖佬卖膏药、小贩卖零嘴,还有讲古表演,村民齐聚,热闹非凡。[9]当时的庙会既有庙祭,还有庙市,更是庙节,是神庙剧场世俗化以及酬神戏由娱神向娱人功能转变的必然结果。据老赛桃源潮剧团前任班主许亚峇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酬神戏演出时“台下挤满观众,全村都出动,人神争着看戏”[10]。如今随着传统乡村庙会的消失,酬神戏真正成为了祭桌上的供品,“除了庙内神明和台下一排供‘好兄弟’看戏的空椅子,看不到任何观众”[10]。
观众流失导致不少职业戏班退出历史舞台。据统计,“至少从2000年以后酬神戏广告里,可以发现好几个历史久的剧团名字已完全没有再出现(或许已经停业),如莺燕、双飞燕、快乐、新柏华、新时代、福禄寿(已停业二十余年)。老招牌的新麒麟与麒麟的团主锦上花于1992年逝世后,这两团就走进历史”[11]15。此外,拥有174年历史的新荣和兴潮剧团于2001年解散;1980年才成立的金鹰潮剧团于2007年解散;传承了四代人的百年福建戏班新赛凤闽剧团于2014年解散;拥有91年历史的歌仔戏“筱麒麟”剧团于2018年解散。老牌职业戏班的辞世对酬神戏演出主体而言损失巨大,这说明在迈入21世纪的20年间华人社会的酬神需求已经不足以维系戏班生存。
而幸存的戏班又面临着演出队伍老龄化、后继乏人以及戏班组织松散,经营艰难、入不敷出的困境。据2012年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潮州木偶戏新赛宝丰班班主吴亚荣以76岁高龄支撑着戏班运作,在8个月间演出不到10天。据悉该情况已持续了10年左右,因戏班经营不善,演员和乐师都为兼职,有戏则聚、无戏则各忙生计;海南木偶戏新兴港琼南剧社一年只演出了8场,该班成员20余名皆乐龄(新加坡对60岁以上年龄段的别称)人士[6]。据2017年的《联合早报》报道,创立于1864年的老赛桃源潮剧团,现今除了新科班主和两名年轻女鼓手外,团里其余人都已年长,其中57岁的台柱阿光无戏时以送货为生。[10]可见,幸存的戏班亦在勉力维持。
进入21世纪在华族戏曲整体衰落的背景下华人社会的酬神需求俨然成为决定戏班命运的关键。通常情况下各地缘帮的庙宇会聘请该籍地方戏演出酬神,但潮剧班因擅演神仙戏、唱词优雅而受到欢迎。即便是福建帮庙宇后港斗母宫的“九皇诞”也会安排数场潮州剧目酬神[9];福建帮的韭菜芭城隍庙作为支持歌仔戏发展的主阵地,在城隍神诞正日亦安排潮剧酬神[12]。相比之下,较为通俗的闽剧(主要指歌仔戏)在酬神市场不占优势。木偶戏带有驱凶逐煞的原始功能,因雇佣费用较低也能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因此,本地潮剧班和木偶戏班在新世纪早已萎缩的酬神市场尚能喘息。
然而酬神戏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并因其演出惯例的凝固性而难以与时俱进。酬神戏通常有一套仪式化的演出程序,以潮剧班为例,其演出时要在第一天下午以“净棚”(《李世民净棚》)驱凶,“扮仙”迎福开场。扮仙戏又称为例戏,有固定戏码:《跳龙门》《六国封相》《十仙庆寿》《跳加官》《送子》《京城会》,都是一些吉祥内容。正式剧目则于夜场开演,通常以《团圆》开头,最后一晚演出结束需“洗棚”煞尾。[13]576这些带有宗教仪式性质的演出曾在新加坡华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趋吉避凶的美好寓意是华人在异域他乡求存的内心祈愿。然而对于在西方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华裔而言,酬神戏中的繁缛宗教仪式在社会科学体系中被消解,例戏的美好寓意因缺少文化认同而不被理解,整场戏的演出水平与进入剧场、被精雕细琢成艺术的戏曲表演判若云泥。失去观众的参与,酬神戏就如无水之源,只能不断消耗原有的演出水准而无法实现自我更新。
除了上述内因之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影响到酬神戏在21世纪的发展。首先,歌台继续抢占酬神市场。歌台属于新加坡特产,是20世30年代野台戏进入游艺场后,融合歌舞秀、杂技、话剧等各种娱乐而成的综艺形式,表演时在华南方言中融入马来语调和出新加坡特色,深受民众欢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歌台在酬神市场的占比份额就已经影响到传统戏曲的生存,进入21世纪这种影响更加显著,尤其中元节的酬神戏几乎已是歌台的天下。新加坡的中元庆典持续整个农历七月,是戏班一年中酬神演出最忙碌的时期,许多职业戏班赖此为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丁荷生认为,“歌台取代戏台成为七月中元节主要活动,这是表演形式进化的必然结果。以前有庙就有戏台,因为神明很喜欢看戏,所以必须演戏给神明看。不过,随着时代发展,本地大多中元会理事如今都不请戏台,只有规模较大的庙宇还维持着这一传统,导致近十年许多戏班都陆续走入历史”[14]。歌台的迅猛发展无疑加速了酬神戏的衰落。2017年韭菜芭城隍庙庆典期间除了传统酬神戏外,还呈献了3晚歌台表演,并举办“歌台红星大奖”以吸引观众。[15]2018年位于盛港西的包公庙首次主办“国际包公文化节”,除了聘请木偶戏和歌仔戏酬神之外,还聘请了歌台表演。[16]歌台在酬神市场显现出的强有竞争力是21世纪新加坡本土文化抬头、华族传统文化没落的真实写照。歌台所代表的草根文化与快餐文化符合时下高速发展的社会民众的精神娱乐需求,因而能占据中元酬神市场。然而,如今的歌台以表演歌舞和脱口秀为主,甚至常以低俗手段取悦观众,早已失去传统酬神戏趋吉避凶、祈愿美好的文化内涵,彻底沦为一种大众狂欢。
其次,酬神戏受到疫情影响,却无法转入线上演出。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疫情常态化要求各种场合尽量避免人群聚集,减少户外文娱活动,对于演出机会本就寥寥无几的酬神戏而言可谓雪上加霜。韮菜芭城隍庙原本安排好14个来自汕头、厦门、台湾、马来西亚和本地的潮剧团以及歌仔戏班轮流上演酬神戏,皆因疫情被取消。[12]老赛桃源潮剧团班主沈炜竣表示,新加坡几乎所有戏班中元节的演出都取消了,戏班团员都是兼职,疫情对其生计影响颇大。[17]其他文娱活动如剧院戏曲、歌台、话剧等在疫情影响下皆转入线上求存,酬神戏却因演出场合的限定而无法别投。传统酬神戏即便是寄托华人祈福禳灾信念和承载宗教文化意蕴的扮仙戏,一旦离开神庙场所而进入艺术中心或网络平台,也只能被视作是祈福剧目,酬神戏无法脱离宗教场合而独立存在。因此,目前的疫情常态化情况进一步加剧了新加坡酬神戏的发展困境。
三、 21世纪酬神戏的求存之道
新加坡酬神戏在21世纪的发展虽然遭遇困境,但不乏成功突围的案例。韭菜芭城隍庙酬神戏的献演天数自20世纪末以来逐年递增,并于1998年首次突破百天大关,进入21世纪后也基本维持了百天以上的演出记录,促使其成为21世纪新加坡酬神戏演出的重镇。其成功之道在于: (1) 以“神明爱看戏”的传说为宣传点,引导信众通过报效戏金来酬谢神灵。韮菜芭的“城隍公”神像于1918年自福建安溪而来,最早被安置在新加坡克力路的“老泉安掌中班”木偶戏班,据此流传出“城隍公爱看戏”的说法。[12]该庙总务遂利用这一传说引导信众以报效地方戏的方式酬谢神灵,既能减轻庙宇聘请戏班的负担,又能满足信众投“神”所好、追求福报的愿望。据该总务介绍,原计划2020年的城隍诞因遇上闰四月而特地将酬神戏演出天数延长到144天,以满足更多信众希望通过报效地方戏答谢神明的愿望。[12](2) 借助外援提高酬神戏演出水准,吸引观众回流。城隍庙联谊会从1993年起开始聘请海外剧团来新加坡演出酬神戏,主要以中国广东、厦门、汕头、台湾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优秀歌仔戏或潮剧剧团为主。[18]2009年中国漳州市芗剧团为城隍神诞开锣,首演《梁祝》吸引大批民众聚观,甚至有200多名观众在大棚外站着欣赏。[19]2016年大马西江月歌仔戏团在城隍神诞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许多观众为观赏外国演员的风采前去捧场,看到精彩处还要打赏。[20]海外优秀剧团的加盟,不但成功挽回部分因酬神戏演出水准下降而流失的观众,在与新加坡本地戏班同台竞技时又可通过技艺切磋,提升本地戏班的表演水平。聘请海外剧团成为韭菜芭城隍庙提高观众上座率的法宝。(3) 改善观演环境。2004年韭菜芭城隍庙首次在露天剧场搭建空调帐篷,使观演环境免受赤道天气影响。[5]1742020年又耗资1 300万元兴建韮菜芭城隍庙综合大楼,并建成可容纳500人的多用途剧场[21],为前来参与酬神演出的演员和观众提供更为舒适的观演体验。(4) 打造宗教文化艺术名片,提升新加坡酬神戏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助力本地戏曲发展。韭菜芭城隍庙是21世纪华族戏曲在新加坡传承的重要民间力量,其借助宗教力量来支持华族戏曲发展,又通过如火如荼的献戏酬神活动来加强宗教影响力,将酬神戏打造成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宗教文化艺术名片。这张名片现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华族戏曲交流的重镇,也是全世界华人社会所举办的酬神戏中规模最大的演出活动,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墙外开花墙内香”,作为福建帮庙宇的韭菜芭城隍庙是新加坡主要用歌仔戏酬神的庙宇,在潮剧和木偶戏占据酬神市场的今日,用其影响力为歌仔戏分出一杯羹。
韭菜芭城隍庙不仅推动地方戏在21世纪持续起航,还为海丝路上华族戏曲的良性互动树立起典范。2018年位于盛港西的包公庙首次主办新加坡国际包公文化节,吸引中国安徽、河南、广东、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本地的12个庙宇参加,并聘请中国泉州木偶戏和台湾明华园歌仔戏酬神。其中明华园的歌仔戏每晚都吸引好几百名戏迷前来观看,很多人希望包公庙明年的神诞能再聘请明华园来演酬神戏。[16]包公庙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便利,将本土神庙的祀神庆典上升为国际文化节,在对外交流中提升自身影响力,为酬神演出创造内需,是继韭菜芭城隍庙后又一股支撑酬神戏发展的民间力量。
与此同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宗乡会馆在21世纪依旧承担着助力酬神演出的重任。“南安会馆的凤山寺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二都会办千人宴,同时上演酬神戏来庆祝广泽尊王神诞。到了农历八月二十二则举行盛大祭拜仪式,是会馆、头家、炉主和善信为答谢神恩,请戏班演酬神戏,纪念广泽尊王坐化的日子。”[5]43从1982年开始南安会馆聘请新赛凤闽剧班演出酬神戏,每年两期,从不间断[5]94,属于福建帮的南安会馆通过神诞庆典支持着歌仔戏发展。“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的祖师诞,普救善堂都会邀请潮剧团演出以答谢神恩,报德善堂也会在堂庆或祖师诞时邀请潮剧团演出。”[9]普救善堂和报德善堂都是潮州帮的善堂组织,通过酬神庆典支持潮剧的发展。近年来在福建会馆的支持下天福宫恢复了在20世纪初就已停办的迎神赛会[5]440,宗乡会馆开始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新加坡的宗乡组织脱胎于华人神庙,“早年华人移民进入新加坡开山垦殖,首要设施,先建神坛,供奉家乡所供奉之神明。每当神诞即开大筵,宴请乡邻亲友,必演戏曲……因此各神庙都建有大戏台。这些戏台每年只演几天戏,其余时间空置着,于是聘请私塾先生开课。后来社群壮大,私塾扩建为学校,神庙神坛扩建为宗乡会馆”[5]23。宗乡组织以神权为中心聚合具有地缘或血缘联系的群体,在华人社会充当着帮派领袖的地位,拥有举办酬神活动,实施经济救助以及促进华文教育的职能,并在新世纪发挥着维护、传承华族传统文化艺术的职责。保留华族演戏酬神的传统,支持地方戏曲发展不仅需要民间力量的努力,更是宗乡会馆捍卫自己文化之根的历史使命。
在民间力量与宗乡会馆的影响下,近年来新加坡华人社会开始出现民风回流的现象,为酬神戏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2016年住在宏茂桥一带的画家康松如看到传统戏曲演出,以油画《酬神街戏》重现了周围邻里津津有味看戏的情景,借以探讨21世纪华人社会民风回流的问题。[22]民风回流意味着华人内心对基于酬神戏这一典型文化符号所形成的“共记忆”与“共故事”的召唤。“庙会或酬神戏虽然以宗教信仰为出发,可是它却是民间组织和参与的民众,在一段长时间里,以某个地点为基础进行互动而自然发展起来,构成一个独特的民俗环境,具有非常的草根性。它所衍生出来的文化,虽然绝非庄严华丽的艺术殿堂中的‘高等文化’,却是另一群社会上甚少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民众的文化需求,也代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23]其中,酬神戏的教化作用在华人社会尤为重要,“当年的酬神戏不仅演给神明看,更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消遣。它还代替教育水平不高的父母,教导年轻一辈礼义廉耻忠孝节悌,学会分辨忠奸善恶与是非”[24]。而由酬神戏的闹热性、狂欢性以及全民参与性所构成的独特民俗环境,更是民众乐而忘忧,得到短暂精神慰藉的宝贵时空。民风回流现象表明传统酬神戏在当代社会仍然有其存在的文化价值,重塑酬神戏在当代的社会价值无疑是其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求存之道。
概而言之,酬神戏的形式虽然老化,但其所蕴含的华族文化依然是新加坡华人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更是在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海上丝绸之路上各地区华人保持“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