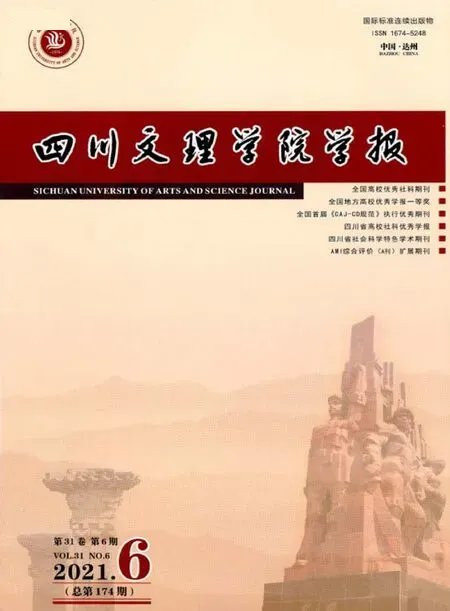从《红楼梦》解读清代女性的闺阁文化意蕴
2021-01-31张誉尹
张誉尹,杜 双
(1.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与历史系,香港 999077;2.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办公室,四川 自贡 643000)
自明朝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市民阶层不断在扩大。至清朝,市井商业繁荣更甚,据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研究表明,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财富总量约占据全世界的三分之一。[1]社会风尚也由明初的质朴尚俭转变为鄙俭崇奢,人对物的要求愈发精巧别致,居室设计上亦能体现出清人对生活美学的追求。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居住空间的布局将儒家宗法制贯彻到底。整所住宅里,内院闺阁是最为私密幽静的所在。它是女子日常活动进行的重要场所,更是主人性格和人格的延伸。《红楼梦》作为闺阁文学的代表,是研究古代女性生活的重要文本。因此,《红楼梦》可为现代学者研究清朝女性闺阁文化和了解清代女性生活提供参考。“闺阁”背后的文化意蕴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
一、闺阁内院的空间布局
在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来在宗法制的影响下,家庭的秩序须符合伦理纲常,长幼尊卑有序,男女有内外之别,住宅空间的区域划分处处体现着礼法。可以说正是严密分化的住宅空间“提供了妇女生活的物质性框架,予男性和女性领域的分离以具体的形式。[2]”空间的严格区分于司马光《书仪》也有记载:“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3]可见不论是民居住宅还是天子行宫,都有内外之分,男主外女主内,不可逾越,内外的公共区域也不可混用。明清时期,居民住宅总体特征为坐北朝南,方正对称有中轴线,富足人家至少有前后两院,以两侧抄手游廊相接。居正中大堂为尊,两侧厢房又以东面为尊。内院通常都在宅子最后面,私设出入通道可使女眷出入不与前门相扰,确保私密性。《红楼梦》中林黛玉初进荣宁二府就是从内院空间进行叙事的,“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却也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的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4]46这一大段描写节奏紧凑,众婆子小厮进退有序,一套下来行云流水,昭示荣府内外有着严格的空间划分,制度森严。林黛玉为女眷故由角门送进内院,轿夫这等外男不可以入,直到垂花门前,小厮们退下,婆子上来,可见垂花门则是介于内外院之间的一道屏障。
内院里女眷们的住处方位也与关系的亲疏、身份地位的高低密切相关。且看:“王夫人忙携黛玉从后房门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是一条南北宽夹道....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了。”[4]50可知贾母和王夫人各自拥有一套独立后院,相距不远,且王夫人与贾政的小院在东,贾母在西。“贾母的婆子们带领黛玉过荣禧堂,来到东边三间耳房...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4]108这三间东耳房,东廊三间小正房,家具坐褥都半旧不新,这就是贾政夫妇二人的居室。这东小院与东廊三间小正房,理应是同一区域,整体属于荣禧堂东边的附属跨院,而东廊三间小正房后门经后廊往西出西角门,便是贾母后院。不知为何以贾母的地位要住在西边,荣禧堂东边的院子面积甚小,且呈长条矩形,不甚大气,想必贾母才愿意住在西侧吧。
又见第七回周瑞家的从王夫人处出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隔着玻璃窗户,只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遂穿西花墙,出西脚门进入凤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丰儿坐在凤姐的房门槛上,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摆手儿往东屋里去...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4]206周瑞家的送宫花路线暗暗说明了凤姐后院处于宅子西后侧,而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中贾瑞躲在西边穿堂儿里,“趁掩门时,钻入穿堂。果见黢黑无人,往贾母那边去的门户已锁,倒只有向东的门未关。”[4]312可以知道贾母的院子与凤姐院子是由一条东西穿堂连起来的,相连紧密,可见凤姐深得贾母欢心。且凤姐与贾琏的卧室居院子正中,符合其主人身份,大姐儿的闺阁在东屋,也彰显贾琏夫妇对女儿的珍爱之意。
林黛玉住的是潇湘馆,且看潇湘馆的布局:“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只见进门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步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间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从里面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则是后院,有一大株梨花倚着芭蕉,又有两间小小退步。”[4]412可以看出潇湘馆如此精巧雅致的院子也有一个后院,于翠绿修竹中层层深入,穿过三间房舍,再穿过一个小门,来到了后院,梨花芭蕉的遮掩下才看到两间小小的房屋,让人想起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来。林黛玉必然是居于后院之中,幽静不被打扰,符合她清冷独处的性子,且与宝玉的怡红院距离较近,也暗示了二人关系更为亲近。
再看宝钗的蘅芜苑,蘅芜苑不与各处相连,需要乘船过得港洞或者从山上盘道而行,过了一个朱栏板桥,接着看到的是“一色水磨砖墙,青瓦花堵……因而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只见许多异草……贾政因见两边俱是抄手游廊,便顺着游廊步入。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4]蘅芜苑抱水而居,以古朴砖墙为屏,四面环石。蘅芜苑本身地理位置已经很偏僻了,不与其他各处大陆连着,院子四周又有石块遮蔽,封闭性已然极强。这符合宝钗在贾府的身份,在贾府她虽然有王夫人这个姨娘,可终究比不得贾母珍爱的黛玉,她在下人眼里也始终是外人,因此她住在蘅芜苑这偏僻处不与其他住处相连,在关系上有亲疏远近之别。
二、闺阁陈设
宗法制决定了房屋住宅须得遵从尊卑长幼等级设立。院子的方位和大小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而室内居室设计则是主人财力和品味的最佳象征。不同于明代居室的简朴情趣,清代室内环境营造在整体风格上更趋华美繁缛,室内的设计风格和家具都更趋于装饰化、精致化、世俗化和奢侈化等。
而卧室,作为供人下榻休息的居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私人空间。卧室不为外人所见,不需要彰显主人的优越之处,故卧室修建设计得不如厅堂恢弘大气,卧室的陈设器物、装饰风格皆更随意自由,更能体现居住之人的脾气秉性。
《红楼梦》第五回就借贾宝玉之眼探究了一番秦可卿的闺房,房内摆放的家具器皿、文人字画都隐晦的表达出秦可卿的风流香艳。“刚至房门……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秦氏卧室墙上挂着的是《海棠春睡图》,杨贵妃醉颜残妆,鬓乱钗横,别有一番风流滋味。旁边的对联看似是应和画上的美人醉酒,也有一种醉生梦死不愿醒来的旖旎。再看“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报过的鸳鸯枕。”[4]149从秦可卿低微的出身来看,这些所谓的武则天的宝镜以及赵飞燕立过的金盘是不是真品无从考证,这些文字都是以宝玉的视角展开,不免添加了人为主观的想象。女子的卧室中有宝镜,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说明秦氏是一个注重打扮的人;《诗经》有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木瓜象征着男女之情,木瓜放在金盘里又多一层富贵奢靡之意;榻与床不同,榻的尺寸较小,高度很低,是作为休闲小憩的卧具,榻有招待贵宾之意,这里秦氏让宝玉睡榻也有此意;而珠帐、纱衾和鸳鸯枕这些床上用品则处处弥漫着夫妻日常生活气息。
《红楼梦》里关于黛玉在潇湘馆的卧室有很多描写篇幅,其装饰风格与秦氏就大相径庭了。“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毕药,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窗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挑逗鹦哥作戏,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教于他念。”[4]432又见第四十回贾母携众人带着刘姥姥赏园,以刘姥姥的视角看黛玉的闺房:“紫鹃早打起湘帘,贾母等进来坐下……黛玉听说,便命一个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4]441这些虽是零零散散的片段,但几处碎片拼凑在一起也有了大概总体的印象。黛玉的闺房偏小,贾母也说这屋子窄,可从卧室的布局设计来看却极尽风雅。卧室外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竹的姿态苍翠,傲然挺直,文人喜竹并因其品行高洁,并常以竹自喻。月光从纱窗倾泻而下,伴着竹叶沙沙作响,所以连贾政也感叹道:“若月夜能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文中没有刻意提及屋内其他器皿陈设,单看书架上满满的藏书和案上的笔砚,可见这间卧室与黛玉身上喜爱文墨且清冷的气质十分相宜,烘托出黛玉高洁的品性。屋内有几,可供读书写字;簟,竹席,由李清照的“红藕香残玉簟秋”可得,还有作为空间隔断的屏障“湘帘”,也是用竹子做成,这两样竹制装饰与屋外的湘妃竹相得益彰,更有幽静凉沁之意。这样清幽的环境里,唯一增添丝丝生气的是那只鹦哥,为黛玉解解闷儿。鹦鹉素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就有着不同象征意义。其一,它的美丽外表、聪明辩慧,以及常年贮之金笼都成为中国古代女性处境的一种象征。柳永的《甘草子》就写出了深闺女子的满腔愁绪:“池长凭阑愁无侣。奈此个、单栖情绪。却傍金笼共鹦鹉”。其二,鹦鹉不同于凡鸟却被困金笼,“古往今来恨莫穷,不如沈醉卧春风。雀儿无角长穿屋,鹦鹉能言却入笼。”曹公将鹦鹉放于黛玉房中,绝非偶然,意指黛玉纵使才资过人却只能和鹦哥一样不得圆满,落得香消玉殒的结局。黛玉房中的装饰还可以从第八十九回宝玉去潇湘馆窥见一二:“一面看见中间挂着一幅单条,上面画着一个嫦娥,带着一个侍者;又一个女仙,也有一个侍者捧着一个长长儿的衣囊似的,二人身边略有些云护,别无点缀,全仿李龙眠白描笔意,上有‘斗寒图’三字,用八分书写着……宝玉指着壁上道:‘这张琴可就是么?’怎么这么短?”[4]518李龙眠即李公麟,北宋时期著名的白描大师,这幅斗寒图仿的是他的画法,自然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嫦娥图了。挂此画在室内,嫦娥清冷出尘的仙姿倒是与潇湘馆的幽冷相为契合。再说嫦娥一人飞去广寒宫,身边无一亲人,和在贾府无依无靠的黛玉一样孤寂。故此黛玉将从小抚弄的琴挂在壁上,也能看出她对从前父慈母爱的生活十分眷念。
《红楼》关于闺房记载详细的还有薛宝钗的房间:也是第四十回刘姥姥进大观园,“进了蘅芜苑院,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4]539-540宝钗素来不喜花儿粉儿的,周瑞家的送宫花那一回就已经明说过宝钗喜素了。蘅芜苑中种植的皆是奇草仙藤,散发着冷冷幽香,倒十分符合宝钗不爱粉红的性格,不脱俗套。况整所蘅芜苑透出冷来,宝钗正是一位服着冷香丸的冷美人,处处都是冷意。再看室内陈设,“雪洞”二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宝钗闺阁的特点:清冷。房内并无玩器,所以室内色彩十分单调。案上放着一只土定瓶,瓶中有几只菊花,颇有几分“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天然去雕饰之感。几本书,一些茶具,就连寝具也是单一古朴的。书中交代了关于宝钗性格的一些线索,比如将大红袄儿穿在里面,在手腕上带着麝红珠子,其实她并不是一味的抗拒红色,而是将自己的欲望喜好选择深埋起来。就如同这间“雪洞”,空无一物,符合她藏拙守愚、稳重内敛的性格。
要说姑娘中屋子最富丽堂皇的应数探春,贾母也对她的房间赞誉有加。“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4]564卧室的布局就很开阔,三间屋子打通,显得明亮大气,与潇湘馆的“曲径通幽”刚好相反。再看器皿摆设,花梨大理石大案、斗大的汝窑花囊、一大幅《烟雨图》、大观窑、大盘、大佛手。探春房内所设的器物一反女儿家的纤小可爱,全部都是大号的,可见探春不是一般寻常的闺阁女儿,有着和男子一样的豪爽做派。探春闺阁的第二个特点是:多。她案上的文房四宝数量已相当可观,就连屋内装饰用的菊花和佛手也放的满满当当。白菊花品性高洁,佛手色泽金黄,放在室内即可观赏又可净化空气,使室内清香。探春用鲜果花朵代替香薰,其天性应是崇尚自然的。且看她壁上挂着的字画,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烟云雾景”,米芾的绘画追求正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的风貌;出自颜真卿之手对联的释义则是“像烟霞一样散漫而不受拘束,像泉石一样隐逸而天然”。仅仅是这室内的字画就有一种天然野趣,与“秋爽斋”的“秋爽”二字极为相宜。探春是三春中最出众的,她有着“裙钗一二可齐家”的能力,文采斐然,处事进退有度。贾母和王夫人对她总是与二春有些不同,更为看重。“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锈花卉草虫的纱帐。”屋子里最能证明探春地位的就是这架拔步床了。拔步床又称为架子床,通常设有四根或六根立柱,三面设有围栏,而且还有床顶。结构较为封闭,隐私性非常强。拔步床的造价极高,雕刻工艺精美繁杂,花纹华丽多样。正是因为其价值不菲所以才能够凸显主人的身份和财富,常作为富贵小姐的陪嫁之物。探春的房里有这样一架拔步床,足以证明其贾府小姐的尊贵身份,也可得知虽是庶出可她在贾府还是很受捧的。
三、闺阁生活
前文主要涉及到闺房的构造空间和陈设艺术,但在居住空间内发生的人为活动同样也值得我们关注。居住空间与居住者的活动需要密不可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方能拼凑出一幅幅活色生香的闺阁画卷。
在繁琐严格的制度教条下,古代女性的娱乐活动大多是抚弄缠绕的针线,赏花烹茶,对镜梳妆。女子都爱妆饰,晨起第一件事便是梳妆。清朝才女王贞仪就有一首《梳头歌》就将女子晨起妆发的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细沐微熏湿双鬓,芙蓉绾髻开帷镜……麟梳缓逐青丝掠,凤篦斜随弱缕扬。纤纤玉指盘翠色,云鬟半偏描不得。花钿贴罢成新妆,腰肢已自慵无力。调朱弄粉亲盘鸦,青入眉峰黛色斜。梳罢背人还对影, 一枝簪得海棠花。”女儿家娇媚慵懒的姿态惹人怜爱,让人对这位坐在镜前梳妆的女子产生无限遐想。《红楼》里也不乏这样的情节,第四十四回,宝玉素日最喜红,一身脂粉气,他的卧室被刘姥姥误认为小姐的绣房。他房里和女子一样有一个妆台,拿出自己的胭脂为平儿上妆。这一段的描写极美,用紫茉莉花研磨的粉一排排的在瓷盒里,轻白红香,甜腻润泽;用花露蒸成的胭脂盛在白玉盒子里,如玫瑰凝脂一般。且上妆手法须轻柔,粉要用玉簪花棒儿轻轻蘸取,胭脂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平儿只觉得鲜艳异常甜香满颊。可见当时女子的妆品工艺已渐趋成熟,更是相当精致,她们对自己的容貌举止都有一定的要求。
“妇容妇德妇工妇言”这四德,女子在闺阁里最常做的就是女工了。宝玉在第八回里离了王夫人去看宝钗,“宝玉掀帘一跨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4]138。宝钗是红楼里最能体现儒家精神的一个人,做人行事深谙中庸之道,也常劝诫宝玉作为男子要承担家业,争取功名。她将女红刺绣看作女人的本分,白天陪着贾母王夫人问话,晚上还得继续做工直至三更天。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生活,这是整个中国古代女性的缩影。女子不事农耕,但须得成日纺织做工补贴家用,故所有女子皆能做工。刺绣也能隐晦的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意,第三十六回黛玉在窗外悄悄瞧见宝钗坐在宝玉床边,拿着他的肚兜绣起来,这让黛玉醋意大发。而黛玉也曾坐在窗下为宝玉做香囊、络子等挂件,刺绣将三个人敏感复杂的关系缠绕在一起,理不清更乱罢了。富家小姐尚可将刺绣拿来消遣时间,但作为低人一等的丫鬟来说,女工是工作分内的事。第五十二回里,病中的晴雯向坠儿骂道:“要这爪子做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4]607可知针线活儿对于女婢来说是很要紧的手艺,是吃饭的家伙。而晴雯在病中仍咬着牙替宝玉缝补雀金裘补了一夜,让人怜爱又感动,好一个忠勇手巧的丫头。
在明清时期,贵族阶层女子读书识字的现象增多。社会风气推崇诗学才女,她们既能为门第添光,也可更好的相夫教子。如明末《女范捷录·才德篇》就抨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夫德以达才,才以成德,故女子之有德者,故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贵乎有德。德本而才末,固理之宜然,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女子之知书识字,达礼通经,名誉著乎当时,才美扬乎后世。”清代之后,女性文学更加繁荣。据单士厘编辑而成的《清闺秀艺文略》中所记载就有二千三百多位女作家的三千多种作品,这还只是三十年间所记录下的,遗漏诗稿尚未计入,数量已是相当可观。女子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很多,她们吟诗作赋甚至结成诗社,女性家族群体成员之间还相互唱和。《红楼》中林黛玉尚在林府时,林如海已经为她请了先生教她读书。黛玉才进贾府时也曾说自己只读了四书,可见书香世家的小姐是要能读书写字的。明清社会吟咏之风盛行,“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造成了许多世家大族,生活在具有丰厚传统的文化氛围中,使得女作家的出现更加具有普遍性。”[5]此时社会涌现出许多女作家群体,而且多以家族关系面世,如江南吴江叶氏家族,家族女性皆擅长诗词,且有集子传世。这一风气在《红楼》更得以体现,她们成立了海棠诗社,作了菊花诗再到螃蟹咏,殊不知女子的才学不输须眉男儿。黛玉时常悲戚自怜,一时伤怀就能随手作篇七言律诗来,是何其的潇洒;宝钗性温平和,作诗也是四平八稳,更有男子的胸襟气阔;湘云见柳花飘舞便能偶成一小令,字字鲜趣活泼。女儿家学诗的风气从香菱身上亦可体现,起初不知音律无法入门,得黛玉的指点后,灯下苦读孜孜不倦,竟能讲出诗的妙处了。虽然读书写字对她这样的下人来说毫无用处,但香菱向学之心却比其他人都真,谁能不说苦心求诗的香菱着实憨厚可爱呢。
结 语
由于古代严格的性别区分,内院闺阁的方位一般在住宅后方,较为私密封闭,不为外人所见。从《红楼》中可知:闺阁的方位布局与主人的身份地位息息相关,闺阁陈列是女主人的性格投射,闺阁活动虽然单一却不乏有趣。即使生活在狭隘的一方天地,女子还是会在清晨坐在妆台前对镜梳妆开始一天的忙碌,午后的阳光洒进碧纱窗,用汝窑白玉杯煮茶品茗,在中秋品蟹对月吟咏,晚间点起一盏油灯绣起碧水鸳鸯。中国古代女性一直生活在伦理道德的禁锢下,内院闺房是她们永恒的牢房亦是承载着欢声笑语的地方。虽为女子有诸多的身不由己,可她们还是想着法儿的让日子变得新鲜有趣。“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算命运如柳絮纷飞不可把握,也想抓着仅有的光亮活着。青春不过一场恣意欢笑,这些明媚女子的笑声不应被人忘记,闺阁里时光也不全是虚度。大观园的一幕幕倾泻灵动如雨落,醉倒了一片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