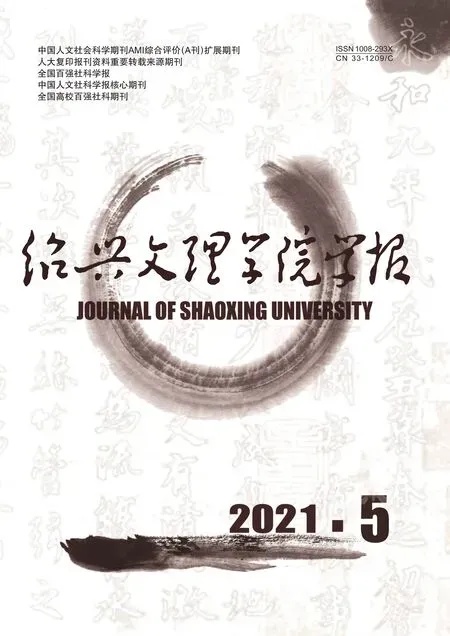绍兴籍翻译家及其译学思想研究
2021-01-31吴彩霞
吴彩霞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哺育了众多文化名人,翻译领域也不例外。在翻译家群体中,曾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绍兴籍翻译家,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周建人、胡愈之、董秋芳、胡仲持、孙大雨、罗大冈、王佐良、王道乾、方梦之和罗新璋等,他们为传播中国文化思想、推进中国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绍兴籍翻译家群体因其历史久、名人多、译学思想丰富在中国翻译史上独树一帜,集中研究绍兴籍翻译家的译事活动,梳理他们的译学思想,对弘扬绍兴文化名人的功绩、推进绍兴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绍兴籍翻译家群体及其主要译事活动
近代历史上的教育家和翻译家蔡元培先生将翻译视为唤醒民众思想意识、培养坚强国民性格的武器。1903年,他将德文《哲学要领》一书译成中文,之后又翻译了日文《妖怪学讲义录》。1907年,蔡元培赴德国留学。留德期间,他编著和翻译了30多万字的书稿,由出版社陆续付印出版。1923年他又编译了《简明哲学纲要》一书。这些译作具有高度的哲理性与思想性,为传播西方文化思想、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直以来,鲁迅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熟知,其实鲁迅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的译作语种多、数量大,即使在去世前他仍笔耕不辍。自1903年他的第一部译作《哀尘》出版,到1936年完成翻译俄文《死魂灵》止,鲁迅共译介了大约244部各种题材的作品,涉及15个国家的110多个作家,总字数近300万字[1]。
出版家兼翻译家胡愈之和其弟胡仲持虽然从事翻译工作时间不长,但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4年,仅《东方杂志》就刊发了胡愈之各种文体的译文200多篇,内容涉及19个国家,有小说、戏剧、寓言,也有文艺理论和科学方面的文章。此外,他与弟弟胡仲持共同翻译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成为当时出色的译作,在启蒙国民思想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绍兴籍翻译家董秋芳的翻译成果同样不可小觑。他于1927年翻译出版了第一部译文集《争自由的波浪及其他》,收录了俄国著名作家如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的7篇作品的译文。之后,他还译介了6种外国戏剧、7首外国诗歌和13篇外国小说与故事。这些译文几乎都是首次汉译。董秋芳称得上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文学译介事业的重要践行者。
著名翻译家孙大雨主要从事英汉诗歌互译和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他除了英译莎士比亚的8种戏剧和莎剧的诗篇外,还翻译出版了《英诗选译集》(1999),该书收录了英国著名诗人近百首传世佳作。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古诗文英译集》(1997)和《屈原诗选英译》(1996)等译作。
翻译家罗大冈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他的主要翻译成就有艾吕雅、阿拉贡等人的诗抄和一些法国名人的文学论文选等。他对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及其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进行了深入研究与翻译。1980年、1985年和1987年,他分别翻译出版了罗曼·罗兰1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母与子》上、中、下册。
英美文学翻译家王佐良在20世纪50年代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1-4卷)的英译工作。1958年,王佐良与巴恩斯合作翻译了曹禺的戏剧《雷雨》。他最为传神和出色的译作当数英国诗歌的汉译,他的译作涉猎了英国诗坛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诗人作品,收录在《英国诗文选译集》(1980)、《彭斯选集》(1985)和《苏格兰诗选》(1986)等作品中。
在4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绍兴籍翻译家王道乾埋头耕耘,在法译汉方面成果丰硕。他所译的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风格清新,语言流畅,蜚声海内外。他的译作主要有《左拉》(1955)、《米晒耳·隆代》(1955)、《红与黑》(1961)、《琴声如诉》(1980)、《情人》(1985)、《红与白》(1998)等,他被誉为汉语世界里的“另一个杜拉斯”[3]。
我国当代杰出的翻译家罗新璋主要从事法国文学译介工作,他的《红与黑》译本是同名小说译本中的佼佼者,被公认为重译外国文学名著的经典之作。他的主要译作有《栗树下的晚餐》(1986)、《特利斯当与伊瑟》(2003)、《红与黑》(2011)、《列那狐的故事》(2013)等,翻译字数达100多万字。
河道中底质主要是淤泥,是污染物比较聚集的地方,常规情况下淤泥自身也具有净化水体的功能,但如果污染物沉积过多,会导致淤泥成为富污染物场所,对水体造成严重的污染。河流底质改善技术可以对淤泥的这种污染情况加以控制,可应用的技术方法包括2种:(1)河道底质清除技术,此技术的应用是将河道中污染最严重的淤泥清除,以避免其引发二次污染;(2)生态修复技术,河道中的淤泥生态特性对河流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作用,因此,可对河流底质泥土的功能进行调整。
以上提及的绍兴籍翻译家都至少精通一门以上外语,他们有的钟情于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引入西方新的文学形式和思潮,推动文艺革新;有的通过翻译作品介绍国外先进的政治、哲学、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新知识和新理念,增进中国读者对世界的了解,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在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这些绍兴籍翻译家积累了宝贵的翻译经验,提出了真知灼见的译学理论,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翻译理论和思想。
二、绍兴籍翻译家的主要翻译特点
(一)以翻译为武器,探索“启蒙与救亡”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失败强烈地刺激了蔡元培的民族自尊心,康梁变法的失利使蔡元培更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先开发民智,培养人才,于是他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为此他弃官南下,开办学堂,翻译著作,编译教材。同样,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认识到要改变“国弱民愚”的现状,首先要改变国民精神,而要改变国民精神,首推文艺,提倡文艺运动。于是鲁迅弃医从文,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周作人在翻译思想上与鲁迅基本一致,他们都深受梁启超等人有关翻译主张的影响,强调翻译工作对“改良思想,补助文明”[4]、引导国人进步等意义重大。因此,当时的这些绍兴籍翻译家都把翻译的目的与动机定位于启蒙与救亡。他们秉承相同的翻译理念,胸怀相同的翻译目的,从事相似的翻译工作。
(二)选择“弱国文学”翻译,拯救“被压迫者”的灵魂
绍兴籍翻译家不仅在翻译目的上一致,在翻译选目上也颇为相似。他们均倾情于弱小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介绍,学界称之为“弱国情结”[5]。鲁迅的翻译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1909年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和周作人合译)和1922年翻译出版的《现代小说译丛》都收录了鲁迅有关弱国文学作品的译文。从《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到“五四运动”前期,周作人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与鲁迅基本一致。胡愈之、胡仲持兄弟以及董秋芳都是在鲁迅的影响下走上了译介弱势民族文学的道路。胡氏兄弟把介绍世界进步文学的重点放在了被奴役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呼号和斗争上。在董秋芳所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当中,弱势民族文学作品占到了四分之三,他还是不少弱势民族作家作品在中国的首译者。可见,在鲁迅的引领下,当时绍兴籍翻译家纷纷倾向于对“弱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是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同时冀望从弱势民族的文化里找到时代的共鸣,获得前进的勇气。
(三)探寻多元翻译策略,彰显“敢为人先”精神
历史上,绍兴始终以“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首创精神走在时代前列。“敢为人先”就是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绍兴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充分体现了绍兴人这种不安于现状、敢为人先的精神。
蔡元培在继承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译即易”的理论思想。王佐良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文化翻译观、文体翻译观、诗译观、理论与实践观等“四位一体”的译学观点。方梦之在探索和研究我国翻译的形成体系时,提出了“一体三环”的译学思想。罗新璋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总结出“离形得似”与“三非论”的翻译观点。
这些成就也反过来证明,绍兴籍翻译家在翻译实践中、在其翻译思想的形成中,都受到了绍兴精神的鼓励和推动。正是由于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奋斗精神,由于求真务实、不断进取的实干精神,这些绍兴籍翻译家才能在翻译实践和译学思想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绍兴籍翻译家的主要译学思想
(一)蔡元培的“译即易”译学思想
1906年,蔡元培出版了《国文学讲义》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蔡元培集中阐述了他的主要译学思想。蔡元培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唐、宋以来“译即易”的翻译理论基础上,对该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和深化。他对“译即易”的理解包含了三层不同的内容[6]391: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这个层面上的“易”就是变换或改变;“易”的第二层意义是简易,也就是说,翻译的作用是使不懂的语言变得使人容易明白和理解;最后一层“易”的意义指传递或传播,即翻译活动除了语言的转换以外,还可以传递思想,传播文化。
在1906年的《国文学讲义》中,蔡元培还提出了“横译”“纵译”与“一译”“再译”之译学思想[6]392。蔡元培所谓的“横译”指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纵译”则指国语古文今译。蔡元培认为,由意识触动而萌发的语言也可称为一种翻译,即“一译”。这一思想是蔡元培首创,饱含着深奥的语言哲理,令人耳目一新。蔡元培所谓的中国独有的“再译”是针对当时我国言文不一的状况而提出的观点,即言语和文字的对等转换可称为“再译”。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这一观点成为提倡白话文的主要理论武器。
(二)周氏三兄弟的“直译”观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在此书中,鲁迅提出了“迻译亦弗失文情”[7]的直译观点,这在当时可谓逆道而行,因为那时的译界崇尚意译,排斥和贬低直译。《域外小说集》主要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它对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盛行的直译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鲁迅在日后的外国作品翻译中处处体现出其严格的直译思想,如作品中的地名、人名、专有名词都一律采用音译之法。小说的形式与篇章结构、文体风格、人物间的对话、叙事内容、情节顺序和特定的文化符号等都基本按原文照译。语句单位、词语表达、修辞手段等方面也不随意变动,不轻易删减或合并句段,即便有时译文读来有点“晦涩难懂”,他也不改变直译的立场。鲁迅认为,为了使中国读者感受到异国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译者应尽可能使译文保持原作的风味,给读者一种异域的感觉。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8]
周作人也一直倡导“直译”。他在1925年出版的《陀螺》的序文中,明确提倡在英译汉时使用直译的方法。他说:“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是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9]他赞同在符合译语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直译,反对过分任意的意译。他认为,直译和意译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通的。
周建人主张的“直译”是“要求不失原文的语气与文情,确切地翻译过来的译法”,旨在“把原文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十足译出来”[10]652。周建人主张的直译包含以下两方面的意义[10]652:一是译文要尽可能忠实于原文,不违背原文的思想;二是所谓的忠实于原文不只是字面意义的对等,还应兼顾原文其他层面的东西,如文体、语气、情感和修辞等因素。在一生的翻译实践中,周建人始终自觉地遵循着这些翻译思想。
在翻译史上,周氏三兄弟的“直译”观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他们所表明的是一种文化态度,他们所呼吁和寻求的是西方先进文化的原质传递。他们一直提倡直译是为了求得西方文明文化的本质价值,并以此来改变封闭已久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也就是说,他们力图通过翻译向国内输入外国真正的先进思想,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他们投身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动机,一是为了引入异国的新文学与新思想,二是为了改良民族的传统思维与心理,三是为了推动民族语言的改造[11]。
(三)王佐良的“四位一体”翻译观
王佐良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他主要从事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英汉互译活动。他的译作在各个角度实现了与原作的高度统一,篇篇堪称佳作。在翻译实践中,他边思索边总结,提出了独到的翻译观。他的这些翻译观逐渐汇成了文化翻译观、文体翻译观、诗译观、理论与实践观等“四位一体”的译学思想。
王佐良阐释了翻译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认为[12]24,文化需要用语言来传递,语言之间的互译可以促进文化的繁荣;反之,文化又可以丰富语言,文化的繁荣可以兴起翻译的高潮。王佐良说[12]18,一个真正熟悉和掌握语言的译者就一定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他进一步指出[12]18,一个译者只了解外国的文化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翻译的过程与目的就是要跨越语言的屏障,实现跨文化的互动与双向交流,因此,“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12]18。
王佐良提出的文体翻译观也独具匠心,其实质是译文的文体适合性。他指出,“不同的文体要有不同的译法”[12]35。广告、通知等应用文的翻译就要用符合应用文文体的语言来译。翻译政论文需要用严谨、庄重的文体来处理。翻译小说要译得有文学情调,具有小说味,可读性要强。诗歌的翻译则要注重意象、格律、音韵等方面的问题,要力图传达诗的意境和情调。王佐良说,“文体学的灵魂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场合”[12]15。他认为[12]19,在翻译实践中,语言与社会场合的关系是译者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译文必须适合特定的社会场合,必须按照原文的文体要求,使用对应的语类和文体,也就是说,译语要体现社会场合的适合性。
在谈到诗歌这一特殊文学形式的翻译时,王佐良指出[13],译者要忠实地传达原诗的意义,诗的语言形式要尽可能接近原作,保持原诗的锐利和新鲜,特别是原文的形象可以直译。最为重要的是,翻译诗作首先得考虑诗的整体意义,也就是先要研究整首诗的气韵、情调和风格,然后再做其他细节的翻译处理。简而言之,就是“译诗须象诗”,即以诗译诗。正因为如此,王佐良一直认为,“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12]54。
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王佐良也有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他在不少文章中多次指出了两者的相互关系,他的“文化翻译观”“文体翻译观”“诗译观”等译学思想就是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思想的最佳诠释,即翻译理论来自于翻译实践,是对翻译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同时,翻译理论又可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他指出,翻译是最结合实际的一种实践活动,同时它又凝聚着许多实用的理论问题。要实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译者就必须刻苦地学习,深入地观察,不断地实践[12]36。
(四)方梦之的“一体三环”论
纵观译学发展史,方梦之对我国翻译体系的形成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体三环”的译学思想[14]。这里所谓的“一体”指译学本体,“三环”是指具有不同性质的、在不同时期形成的译学外部系统的三个发展阶段。译学本体经过多年的孕育,已经不断成熟与完善,它是整个译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也是译学研究和发展的核心。到了20世纪50-60年代,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对翻译理论造成了巨大影响,促使学者对翻译的研究从原来的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从经验感知走向科学引领,这是围绕译学本体的“一环”。20世纪70-80年代,一些新兴学科如符号学、交际学、心理学、信息学和思维科学等相关学科开始兴起与繁荣,这使译学理论产生了深刻变化,促使译学研究从单一学科的研究发展成为多学科、综合性的互交式研究,从而形成了“一环”之外的“二环”。“二环”之外的是20世纪90年代兴盛起来的翻译文化研究,即所谓的“三环”。翻译文化研究的起步促使译学理论研究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具备了多层面、交叉式、全方位的特点。方梦之的“一体三环”论不仅揭示了翻译研究与语言学、符号学、交际学、心理学、美学、信息学和思维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还把翻译融入政治、哲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大背景下进行多维度研究,从而为翻译的研究和形成体系提供了更科学和合理的诠释。
(五)罗新璋的“离形得似”与“三非论”
受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影响,罗新璋提出,翻译要“离形得似”,即要摆脱原作的形式,以求得译作与原作的神似[15]。尽管这个理论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有些理想化,但是这样的译学思想有利于激励译者向翻译的高标准努力,鞭策译者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的翻译水平。“离形得似”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翻译高标准的宏伟目标,而且能切实地引领和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
罗新璋还在《红与黑·译书识语》一文里提出了“三非论”[16]1。在他看来,将外文译成中文时,译者应当摆脱原文的结构形式,尽力把外文译成纯粹的中文,使译文通顺明白,符合中文的语言表达习惯而非外国式中文。其次,文学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同时也是艺术的再现。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译者根据原作的体裁展现文学语言的魅力,而非只是文字翻译。最后,文学翻译只追求“精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精确的译文未必能达到精彩的境界。文学翻译中所谓的“精彩”,就是译文应具有文学色彩,能再现原文的文学气息。罗新璋认为[16]1,若要将外国文学作品译为汉语,第一是要译意,译文不能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第二,翻译应当如写作,在译文中可适当使用骈偶之辞,以增加译文文字之优美,增添译文的文学品味;最后,文学翻译应追求文字的精彩,让读者读后兴趣盎然,余意不尽。
四、结语
中国的翻译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不断发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翻译家。翻译家们凭借着智慧和胆识,将西方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中国,介绍给国人,拓展了国人的世界视野,激发了国人的精神活力,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翻译家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译介给外国读者,弘扬了中国文化,推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绍兴籍翻译家无疑是其中之佼佼者,在中国翻译史上自成一派,独树一帜。他们的翻译成果和译学思想是中国翻译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值得后人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