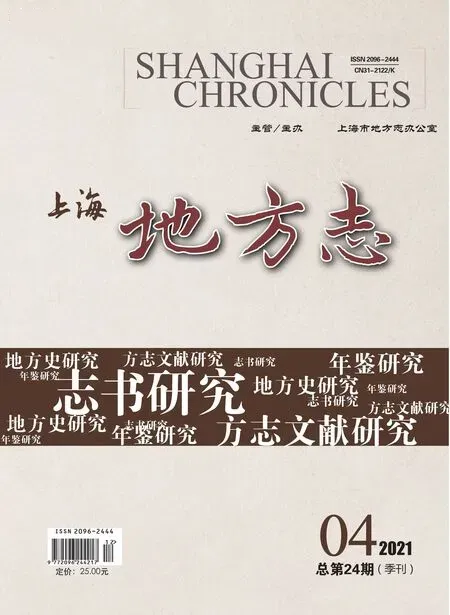从《东京百年史》看地方史的书写
2021-01-31张灵
张 灵
地方史作为一种古老的体裁,有着漫长的编纂历史,在我国,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和东晋的《华阳国志》即属早期地方史。在欧洲,早期地方史多属教会的编年史录,14—16世纪出现《佛罗伦萨史》等著作,法国大革命后,出现《布列塔尼史》《勃艮第史》等省区史、城镇史。二战后,西方史学界认为地方史是“作为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总体面貌”①吉尔伯特莱:《当代史学研究》,台湾文明书局1982年,第285页。。
相对于篇幅浩瀚的全国性史书和体例独特的方志,地方史有着较大的灵活性,既可以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史,也可以是针对社会风俗、文化观念、民间群体等特殊对象的时空构建,还可以是从自身体验出发,对生活方式和环境变迁的个人讲述。只要能遵循史学的基本原则,来论述某地域内一段时期的故事和脉络,都可归入地方史的范畴,像讲述北京的《伶史》《北京警察百年》《北平风物》,讲述重庆的《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华西旅行考察记》《长江激流行》,讲述天津的《天津租界史》《近代外国人记述的天津》《中国之梦》等。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至本世纪中期,我国城市人口至少将增加2亿,上海人口将突破3000万,北京也将接近3000万,城市人口在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向特大城市发展,城市人口在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向Ⅰ型大城市发展②樊纲,郭万达:《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再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第69页。。作为东亚超大型城市的早期样本,日本东京有很多值得我国城市借鉴之处。在地方史编纂上,仅以“东京”两字为题的书籍就汗牛充栋,其中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中国、俄国等外国著述甚至多于日本人所著,既体现东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影响力,也凸显日本独特文化的吸引力,这其中就有美国人爱德华·塞登施蒂格所著的《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1867—1989》。
该书开宗明义,提出“这当然不是任何人的东京,它是塞登施蒂格的”③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页。,表示这部地方史是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历史著述,如书中最常引用永井荷风的诗句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非常陌生,其所选取看待东京的角度也与众不同,浅草公园在商业街和游园会之间的几番沉浮,池袋如何因火车站阴错阳差的选址而崛起为都市副中心,寄席剧场在娱乐产业高度发展后的日渐凋零,透过围绕着个人感悟和体验的“小”事件,以城区扩张、交通发展、文化嬗变、游憩时俗、革命运动、语言修辞等为线条,勾勒出从幕末开国、明治维新到穷兵黩武、一败涂地再到振兴重建、走向现代的东京都市演进史。这种独具风格的全篇布局、资料组合、脉络把握、语言表达都是地方史撰写中值得借鉴的成功之处。书写一部地方史重要的是讲述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内众多人的感同身受,字里行间的“温度”方能让身处其中的人回味昔年最具温情的日子,才可吸引未曾到过的人以此处为蓝本做一个关于未来的梦,从数据、从白描、从旁征中透出的烟火气才会让都市森林中忙碌无歇的人体会到乡愁一词也可以就在此刻、就在脚下。
一、《东京百年史》讲述方式的特点
塞登施蒂格的文字有着相当高的自由度,看似随意的场景描写和事件叙述中很好地把握住历史变迁的重要细节,如明治时期牛肉饮食在东京的广泛推广,棒球如何成为日本的国民运动,其谋篇布局看似杂乱、实则深具规律,让读者在令人惊叹的现场感中切实捕捉到东京城市发展的脉络和趋势。
《东京百年史》全书十二章中每一章都以地理记述、经济社会变迁、市民生活、文化递变等交叉叙述来营造东京市井场景的截面,从中表现出大时代的沧桑巨变。明治维新的万象更新在行人从徒步到坐车的细微中体现,竹制和陶制的炊具取代金属器皿表现日本在战争中的自我毁灭,大型酒店的快速兴建预示着奥运会对日本崛起的指标性宣示。所有看似信手随笔的细节记录,都是城市生长道路上的深刻标记。
(一)地理记述的独特简练
地理区域的变迁是地方史记述的基础对象,然而如何做好地理记述,各种地方史以体例选择和行文风格的不同创造给出不同答案,部分全面介绍的地方史采用摘抄方志的方式,如“昆明之于云南府也,为四州七县之首”①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十八省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记录风俗民情较多的地方史,倾向于笼统简介全貌,突出与风俗相关的地理信息,如“以长治、潞城盆地为中心……历史上的上党地区……在是否亲迎的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分化”②刘影:《皇权旁的山西》,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文化漫谈类的地方史,则乐于采用“壮游”式的地理描述,表现古代文化和地理的有机联系,如“云阳的城里和郊区,没什么贸易场所……江对面铭文的上方,立着一排显眼的房屋,组成一座庙宇,供奉的是战神张飞”③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83页。。
《东京百年史》中由于作者对东京地域的熟悉,采用独特表述方式,使得大地域和小街区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张力和个性。一是东京都市扩张的清晰过程,作者笔下东京的扩张如同一个有机体,在不同时期有着自身的生长规律。江户到明治时代,“下町”的日本桥、京桥一带是东京无可置疑的中心,在明治晚期,大量人口“外溢到东部郊区”④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23页。的本所和深川,大正时代之后,“城市的整体西迁”⑤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350页。使得银座、涩谷、新宿、池袋成为新副都中心,在东京奥运会前后,《首都圈整备法》将东京定义为“以东京中央车站为中心,半径100千米以内的区域”⑥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600页。,形成人口将近4000万的首都圈。二是区域功能的变化,城市的扩张不仅意味着面积的增大,同时也是各种区域功能的重组和调适,充满张力的过程就是城市和人在时空上的融同。日本桥从运河边货栈、商户、仓库云集的商业区转变为银行林立的金融区,再转变为知名的休闲娱乐街区;银座从政府铸币厂到“最激进吸收西方文化”⑦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05页。的所在,从夜市型的消费场所转变成首屈一指的企业总部中心;秋叶原从寂寂无闻的货运站随着山手环线的开通,成为家庭手工制品基地,再到自行车批发场地,后又成为世界闻名的电器街。三是知名建筑的坐标作用,见证历史的建筑物在作者笔下仿佛风涛中巨舰的定锚,如支点般拉开每一幕东京大戏的帷幕。鹿鸣馆,日本“文明开化”的象征性建筑,其风格就是欧化产物,在明治早期是日本全力革新的标志,而后风尚从精英到民间,鹿鸣馆先改为华族俱乐部,再改为保险公司办公楼,最后被拆毁;浅草十二层塔,日本第一座拥有电梯的建筑,是集合百货、娱乐、观光多种功能的早期城市综合体,象征着明治晚期普罗大众的娱乐盛况,在关东大地震后损毁拆除;东京塔,曾经是日本最高的建筑,因和埃菲尔铁塔太过相似而被批评缺乏独创性,却是日本经济腾飞年代最直接的证明,现在高度上已被晴空塔超过。
地理信息对于地方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要精确地反映地域发展,还要能让人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就是在身边的、能体验的,且与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作者记述东京城市“江户时代……的城市中心地带逐渐空洞化”①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482页。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64页。,但仍以温情的笔调记述隅田川的开河节。城市的地理变迁在不同人群中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响,有人迎接霓虹闪烁的夜间,有人怀念深黑中划破宁静的蛙鸣,只有将有代表性的思绪汇总,才能在看似冰冷的数据、标尺、地图中感知到地方史特有的温情。
(二)经济社会变迁的冷静观察
经济运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和规律,从宏观的工业革命、科技爆发,到具体的谋生手段、产业经营,都是整个经济网络变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在地方史中,对经济的描写往往不能采用经济史那种大量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而要在街市变化、居民营收、新业态出现等方面对经济变化的成果加以速写,从而形成地方史中特有的经济社会论述方式。
《东京百年史》中,对经济社会的勾勒首先聚焦于交通方面,“明治维新之后不久,东京的交通运输便开始从徒步和水路运输过渡到车辆运输”②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2页。“1872年夏天,铁路最先开始投入使用”③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8页。“铁道马车出现于1883年……不到十年,东京就开始试验电车”④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5页。“1927年底……东京首条地铁开始运营”⑤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351页。“奥运会结束后紧接着几年,高速公路的拓展也主要集中在东京都的中心地带和西南部”⑥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50页。“新地铁线的建设大约始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到奥运会开幕之前已经大规模竣工”⑦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52页。。可以说,作者用看似分散的文字将东京交通的变迁史完整地勾勒一遍,其中既表明交通对城市发展的推动,“银座能够巩固其身为东京中心的地位,也许正拜这种交通上的便利所赐”⑧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353页。,也表现出交通对居民日常的影响,“摊贩消失,街道变得更便于行人和车辆快速通过”⑨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471页。。
对人口的记述,因其与数字的高度关联性,是《东京百年史》中比较少见的纯数据罗列,而东京的成长让这串数字充满震撼。“江户的50万市民只能拭目以待”⑩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33页。“东京15个城区的人口在大正时期都有所增长……已经突破200万”⑪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482页。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64页。“到了1952年,东京都人口总数再一次突破了700万,1962年,超过了1000万”⑫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480页。“大东京的人口已经成功突破3000万”⑬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601页。。从50万到3000万,反映的是江户到奥运后东京人口的飞跃,简单的数字给予读者难以形容的震撼,可见即便在不强调数据罗列的地方史中,某些经过精心组合的数字依然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令人对规模、发展等抽象名词产生强烈的直观印象。
对产业变化的记述,《东京百年史》采用一套混合语码,一方面是含有数字的归纳总结,“明治时代结束时……3/4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港口地区”“资本达500多万日元的日本公司中,有4/5都把总部设在这三个城区中”①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94—95页。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372页。;另一方面也诉诸较为主观的感受,“以往喧嚣的地方……街头摊贩再度复活”②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471页。“零售业直接迈入过去日本人在纽约和伦敦观察到的状态”③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331页。。这种纯客观描述和纯主观表达的交融,让地方史中那些过往的回响如同暗夜里的萤火,包含生机而又引人憧憬。
(三)居民生活的鱼龙百戏
对居民生活的记录是地方史的重中之重,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不仅能够看出一个时代的剪影,还能从百川汇流的细节中体会时代或快或慢的不停步履。
“民以食为天”在东亚文明的语境中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东京饮食文化变动的频率深刻地反映日本的近代化、现代化。江户到明治时期的激进变革体现在食物上,就是对传统毅然决然的挥别,“牛肉锅是明治时代激进大变革的产物……以前闻所未闻的猪肉、马肉和乳制品也作为文明开化的一部分”④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10页。“取代清酒成为国民饮料的啤酒”⑤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穷兵黩武年代后的物资匮乏,“主食基本只有棒鳕和芋头”⑥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471页。;经济复兴到奥运年代后,传统的茶屋、料理店和各国美食百花齐放,饮食文化上形成传统复兴和大同主义的和谐共存。
在网购兴起前,去“买东西”一直是居民生活中兼具实用性和仪式感的活动,容纳购物和娱乐多重功能的场所始终是居民首选。江户时代,寺庙周边自然形成的商业聚落是其一大特征,“浅草由于观音寺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繁荣的中心”⑦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8页。;明治时代,以三越百货和白木屋代表的百货商店“体现了西式零售业的兴起”⑧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19页。,广告宣传对市民生活习惯的影响深远;奥运会前后,超级市场进驻东京,“是个比美国货还要远销海外的美式经营理念”“超市将食品和非食品类都放在同一个地方供顾客选购”⑨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96—597页。,让世界的商品涌动到东京居民生活中。
棒球“取代相扑成为国民运动”⑩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出现于明治早期,到明治中叶,东京最强的棒球队是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早庆战”从1903年起就是东京最狂热的比赛,“日本棒球始于东京,东京也一直是日本的棒球之都”⑪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94—95页。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372页。。至1925年,东京大学棒球联盟赛成立,1936年,日本棒球职业联盟筹建,棒球始终是东京市民最重视的体育赛事。二战后,在美军扶持下,棒球职业联赛在1946年恢复,大量赞助涌入棒球联盟也是经济复兴的一个侧面写照。奥运会后,棒球场已如街心公园般完全融入东京的城市生活;棒球已成为参与度极高的体育锻炼方式,而观赛又是大众最普遍的娱乐休闲之一。
作为传统的文化娱乐,江户时代的东京“布满了寄席”⑫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7页。,居民只要花少量的钱就能享受到落语等曲艺表演。明治时期,随着东京城市的扩大,寄席数量稳步增加,最多时候超过200个,并在艺人的推动下,逐渐向高雅文化方向发展。在较为稳定的大正年代,大阪的漫才进入东京,形成曲艺上的补充,直到战后,尽管面临电影院、剧场的竞争,寄席数量始终保持平稳。但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寄席骤然衰落,仅存原先的百分之一,各种曲艺转而采取与新媒体结合的方式以求延续和发展,寄席本身只能作为历史文物获得一些保存。
可以看出,《东京百年史》对居民生活进行不惜笔墨、极为细致的描绘,近似美术上的工笔画,纤毫毕现。在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等方面充满温情和诙谐的文字,既是东京居民日常生活的点滴记忆,也是国际化都市成长过程中在传统和现代中不断抉择、融合、再生的完整历程。
4.对文学作品的融汇撷取
在方志体例中,横分门类的要求将艺文进行汇总,除了少数山水题咏,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是独立成篇的。而地方史中则可以较为灵活地运用体现本地风采的文学作品。《东京百年史》就是其中典例,不仅在风物、民俗、乡愁等方面大量选用文学作品,还从旁观者的角度对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意象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进行不同文化的解读,从而形成具有独特感染力的文本。
“四处是过去大名贵族庭院中的假山土丘,在荒废之后就这样弃置在那里”①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85页。,高滨虚子对三菱草地的描写仿佛是东京对江户时代的作别,过去门阀高高在上的一切都在工商业浪潮中重组;“要不就是在观音堂背面念佛堂的后面,在大朴树遮天蔽日的树荫下才会看到的小店”②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久保田万太郎对浅草往昔愉快和热闹时光的追忆,是明治时期大变革背景下,人被历史洪流裹挟中依然有所固执的强韧;“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行尸走肉,就该去看看照明彩灯。你将惊愕不已,大叫出声”③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89页。,夏目漱石不仅是在用“照明灯”的意象比喻文明开化的巨大改变,也包含明治时期“求知识于世界”的决心。
作者还将文学作品的意象和东京的现实进行对比,他转述最喜爱的永井荷风“在空地里偶然撞见的杂草之花,对我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护城河周围的树木”④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35页。,而后通过数据和见闻表示东京地域拥挤,人均公共空地面积仅为华盛顿的四百分之一,强烈的反差使人对东京的人口密度印象深刻;“我喜欢这座房子,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很古老”⑤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44页。,有岛生马的文字对旧事物依依不舍,而实际生活中东京的房屋因为建材、灾害、战争、发展等原因,百年来几乎兴替过三四轮,一个城市在蓬勃发展中总是如蛇蜕皮一样需要有所舍弃,文字里的眷恋更凸显东京城市的迅猛变化;“开幕式当天,东京的交通一度陷入停顿……一时半会之后,人群和车辆嘈杂熙攘的景象才再度重现街头”⑥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59页。,赤冢行雄一段平实的白描,总结前文所述东京为奥运会付出巨大努力,以及所改善的城市面貌和盛会对民众的强大激励;“听人说起白须神社附近在过去被称为寺岛村”⑦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84页。,还是永井荷风,在讲述歌舞伎演员世家时的一句旁记,是东京地名变迁的佐证,重订的地名、有序的号牌,城市在规划、重整中愈发有序,然而曾经的诗意和故事却又因无所依附而消散,城市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成为昨天、今天、明天。
文学对于地方史而言,不仅可以是素材、史料、文献,还可以是一种对地方历史的理解,正如中国人通过触摸杜甫诗句中硬挺感受安史之乱陕甘川的艰难,聆听柳永笔下明艳清丽的开封盛世繁华,呼吸老舍用文字搭建略带风沙的北京城气韵,地方史中的文学是一扇装饰着蔷薇栏的透窗,让后人在看到历史景象的同时,又感受前人的感触和昨日的流芳。
二、《东京百年史》在地方史编纂上的成功方法
《东京百年史》作为一部受推崇的东京历史经典叙述,通过浓墨重彩和精雕细刻,描述东京如何从幕府将军的古老都市,历经百年转变为现代化大都市。细密绵实的撰写带领读者一会身临其境地穿梭于东京的街头巷尾,仿佛目睹居酒屋中的活色生香、市井烟火;一会遨游九天地飞翔在江户城的上空,见证道路如骨架般迅猛生长、灯火点亮沉睡的大地;一会万籁俱寂地置身于曾经繁华的遗迹,诵读昨日诗篇里家园故乡的记忆。历史的书写有范式,但更需要思考和创新,从他者的成功之处汲取经验将使地方史编修更加蓬勃向上。
(一)正视差异,厘清趋势
在地方史的编修上,过去往往是从整体入手,先研判一个地方的整体风格、面貌,甚至会提炼一些“城市精神”,后在该框架内填充资料。而塞登施蒂格却以其对日本文化的渊博知识和深刻理解,自出机杼,由细微处入手,最终将无数细节汇成宏大整体,仿佛大画师从脚画起,勾勒出满壁风动的巨像。而要如此梳理地方史,就不能回避所书写“地方”之间的差异。即如《东京百年史》所记,早在江户时代,下町和山之手地区就存在风貌、习俗、认知上的差异,随着东京都的扩大,新并入的地域和原地区更存在巨大的不同,进而形成居民对其他地区的“看法”,这是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都存在的现象。要如何在正视差异的基础上,记录下生动活泼市井风貌、众生百态的同时,又体现出多元统一的趋势,《东京百年史》给予一个好的示范。
一方面要尊重历史的原貌,不虚美、不隐恶。山之手作为传统贵族和武士聚居区域,对普通市民所住的下町存在“鄙视链”毋庸讳言,“日本桥作为古老的商业中心则习气太重”①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96页。。而国内在地方史编修中也不能回避此种现象,例如三十年前上海浦西对浦东的看法,福州鼓楼居民对台江居民的俚语表达,近些年城市化加速中老城区对新城区的观感,这些显得“不够正确”的记述所体现的局限性正是时代发展的一条刻线,生动地展示经济社会发展在居民思想感情上的冲击,做好对当时现实情况和居民真情实感的系统归纳,会使得编修成的地方史与读者产生共鸣,其可读性和可信度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从而让“更多人感受地方文化和精神”的目的真正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要做好地方统一体的表述。就如同认识人体每个脏器间的不同,并不是要将它们拎出来“独立”,而是要弄清它们之间互相支持而形成的整体。新宿曾是访客到东京的一个驿站,从名字即可见东京人原本对其的疏离,现在却已成为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江东区本是垃圾填埋场之一,受到其他各区的鄙视,但随着垃圾无害化的处理和基础设施的提升,不到十年,就成为极优美的城区。所以沿着时间的轨迹进行记录,就如延时拍摄种子萌芽到参天大树的过程,既能看到每个局部的美轮美奂,又能见到整体的生机勃勃,唯有如此,方能说一部地方史是成功的。
(二)混合记述,主线明确
地方史不着意于方志体的区分门类,也不是纪事本末体般完整讲述事件,而是综合记述地理、文化、风俗、政治、经济等,形成多个地方历史场景的断面。《东京百年史》很成功地从居民生活的细琐小事中折射出时代进步的景象,如“涩谷是奥运会过后变化最大的……成为集娱乐、购物于一体的热闹地带……原宿族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②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61—562页。,将奥运会、城市发展、新生活方式出现熔于一炉,浑然天成。这种将城市方方面面搭建为一个整体的做法,能够让人切实感受到地方的生活气息,进而被此种氛围所感染,如同置身于可知可感的历史生活中。
在多层次混合记述中,也不能缺失述史脉络的主线,缺乏主线将使所有场景成为散落的碎片,无法构成揭示时代演进的光影剧目。每一种地方史的书写都受到篇幅和资料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为统筹全书,就需选取能够反映时代的主线。《东京百年史》在地理记述上对每个时代的日本桥和浅草都给予关注,产业发展上聚焦百货业,交通设施中紧紧围绕着地铁建设,风俗娱乐中棒球、相扑、歌舞伎贯穿始终,都形成重要的题眼,让读者能够相对准确地把握住一些具象事物的变迁过程,从而感受到地方发展的历史脉动。因此,选取好能够清晰标识时代的主线事物,对地方史编修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既根植于城市个性,又关乎时代特点,要求编者需要对地方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对资料有广泛的掌握,对居民生活有真实的体验,如此方能有足够的史“识”,来发挥史“才”之长。
(三)重要节点,做好对照
一个地方的发展很少是匀速而行,往往都是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有着加速或减速。《东京百年史》最醒目的两个节点就是关东大地震和东京奥运会,关于前者“全城差不多3/4的建筑物不是被毁灭就是严重受损”①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4页。,幕府将军的江户实际上不复存在,从废墟中拔地而起的就是今日东京的雏形。在饮食习惯、妇女就业、摊贩经济、建筑特点上,均较为明确地以大地震为界形成鲜明“变”的记述。关于“奥运会”的论述中,“全世界都承认,东京乃至整个日本举办了一届超级棒的奥运会”②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47页。,不仅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有质的提升,而且家庭结构、政治传统、娱乐文化都以此为界标发生巨大转变。所以,选择突出的节点可以让“转变”这个主题鲜明且印记深远。
在国内的地方史编修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选择相关的节点,如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如开天辟地的冲锋号;对于重庆,成为直辖市是地方史中的重要节点;对于汶川北川等地,“512”大地震既是无情肆虐的可怕天灾,也见证当地人民自力更生、全国人民休戚与共的伟大重建精神。每个地方都有发展路上重要的几个节点,选好关键节点,做好前后对比,记述经济、社会、文化、习俗上的各种变化,就能够让地方史充满生机,在林林总总的史籍中别具一格、熠熠生辉。
(四)借助他者,多重视角
“河边是一派令人着迷的景象。在宽阔的河道上,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密密麻麻的各式小船和游乐驳船。”③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48页。“千千万万只船只密密麻麻地挤在差不多一英里的河道里。”④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49页。这分别是莫尔斯和惠特尼笔下的隅田川开川仪式,自从“文明开化”,东京就十分在意外国人的评述,收集很多旅日人士对日本方方面面的记载和评论。在《东京百年史》中运用不少这样的资料,既有对东京法治程度、基础设施、文明礼仪的正面褒奖,也有对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建筑衣着的猎奇窥探,还有对垃圾围城、污水直排的嘲讽吐槽。从不同的文明观对东京的发展进行片段的描绘,尽管有着强烈的主观痕迹,却也是感受东京城市发展的不同视角,而且综合各层面的评价进行判断,能中和部分主观臆断,得出相对客观中肯的地方时代形象。
以百年为视域,在我国留下过的他者观察中也不乏佳品。自五口通商后,外国人的足迹自沿海向内陆推进,有山水古迹的探险者,有民情风俗的观察者,有经济资源、军事地理的窥视者,他们所记述的社会面貌、祭祀礼俗、经济状况,对于地方史的编修来说是一笔宝贵的来自他者视角的财富。对于部分地方而言,那些外来的笔录可能是方志之外记载社会面貌的生动文字,将这些资料做好整理和分析,择其佳处运用于地方史中,既增加多重视角、检验互证的可信度,又能够使行文增加可读性和趣味性,提升地方史的传播能力。
(五)诗史互证,别开生面
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阐述“诗史互融”的史料价值,而《东京百年史》暗合这种方法,在记述中以诗为证,描写社会百态。“耳畔汽笛声响起,越过河便是佃岛,岸边闪着大都会酒店的灯光”①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51页。,木下杢太郎的小调抒发对筑地原先风格的怀念,而全诗所记载的风物,如彩色的玻璃、酒店塔楼的鸣钟、西式的餐饮,正是关东大地震之前筑地建筑和风貌的明确佐证;“夜晚的风暴,黎明到来,一无所剩,花的梦境”②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72页。,原田绢的绝命俳句看似一场清冷的白描,却可以看出明治时代日本歌舞伎的风俗规则、妇女地位、刑罚执行等各种细节,是当时东京社会边缘人群的速写;“春梦正浓满街樱云,秋信先通两行灯影”③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85页。,福地原一郎的汉诗不仅是日本节日庆典仪式和吉原游廓繁荣的生动写照,又说明维新时代,传统的文化形式在社会上仍有深厚的根基,用汉诗装点的大门依然是最具日本意象的文化氛围;“近来尽是,久疏问候,年末岁终”④爱德华·塞登施蒂格:《东京百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428页。,德川梦声的三行诗一方面是浅草区域发展后旧时风貌的离散重整,另一方面也反映曲艺表演艺术在面临电影、话剧等西方艺术时所产生的危机意识,以及在新时代中求变、求发展的自我调整。
诗文所载的民情风是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其折射的文化尊崇暗合社会思想的走向,作者撰文时的背景可能反映某些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试图做好诗史的交融,一方面要做到资料的大规模掌握,大城市、大地域要掌握名家和主要乡土作者的作品,县乡以下则应以全部囊括为目标,尽可能多地掌握诗文,以便在地方史编修中游刃有余、从容运用。另一方面,选取诗文时不能完全按照文学价值为标准,而应更关注其载史价值,“豚蹄操祝过东阡,箫鼓喧阗夜不眠”(《里社赛神词》)⑤民国《永泰县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13年点校本,第465页。是较为普通的唱酬诗,但是它所记载的永泰县里社节日赛神的史料却极有价值。
此外,融通文史不仅可以扩充地方史的史料范围,更让地方史兼具文学感化人心的力量,从而更好地促进地方史的传播和运用。
三、结 语
地方史作为一个区域的历史记录,既可以是篇幅厚重、考证精严的地方全史,也可以是独特标识、目标集中的专门记述,甚至部分记史内容较多的游记、散文、乡土故事集都可以作为地方史的组成部分。从《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早期的游历笔记中就能看出区域记史的特点,其不少内容成为该地千年后考古论史的唯一佐证。在东亚文化圈内,日本的地方史传统也源远流长,《东京百年史》的作者,作为长居日本的外来者创设不少新方式来表达其对东京历史的体验感悟,融合东西方的叙述为这部地方史平添不少魅力。《东京百年史》通过都市扩张中日本桥、浅草、新宿的地域功能不断转变,经济社会在快速膨胀中城街面貌的飞快刷新,居民衣食住行上的日新月异,文学艺术中对往昔岁月的咏叹和今朝发展的思索,从点滴细节中反映东京的城市体验和由之汇聚而成的城市精神。
社会文化史中佐以富有启迪的插曲花絮,为地方史提供更为宽广的背景语境。评价修史的标准也并非单一。有些证据如山、不可迁移,是定论一个时代的柱石之作;有些下笔温润、感人至深,是触摸往昔温情的精致小品;有些鞭辟入里、发人深省,是揭示异化问题的思维风暴;有些平淡清冷、深沉自抑,是勾勒地域剪影的素色白描。只有全面了解这些体裁对地方史的多元构建,才能以更多的方式来编修不同品类的地方史,满足不同人群对地方史的需求,逐步搭建起更完整、更丰富、更加引人入胜的地方史体系,让地方史文献走进更多人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