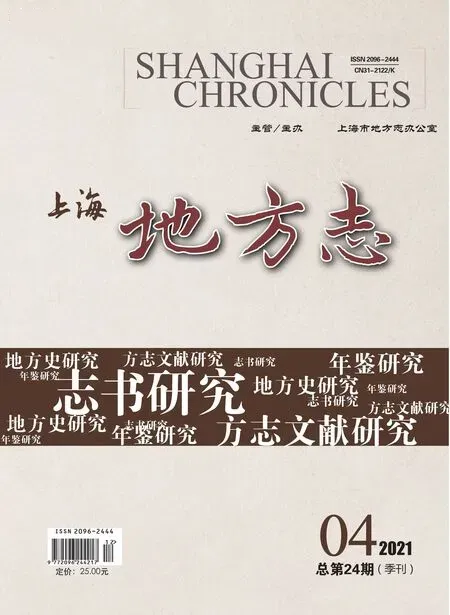社会变革中的利益冲突
——以清末民初南汇县的三次动乱为例
2021-01-31杨铭钰
杨铭钰
一、川沙余温——渔民与渔业公司
(一)经过概述
1911年2月,江苏川沙厅议员在长人乡俞公庙召开议事会议。不久,“素党”①清末川沙、南汇地区民间结社组织,首领为丁费氏。在川沙暴动中,素党是反对新政的主要势力。首领丁费氏率百余名信徒前来闹事,砸毁自治公所的招牌。俞公庙本是公产,后被“素党”占据,成为其宗教活动的场所。川沙厅实行自治时,议将此庙作为自治公所,引起了丁费氏的不满。于是便有丁费氏砸毁自治公所的一幕。不久,该地同知成安逮捕丁费氏,但后来丁费氏贿赂官吏逃脱出狱,并到各处召集人马意图报复,包括跨境前去毗邻川沙厅的南汇县召集人员。此事越闹越大,最后造成清末的著名事件——川沙暴动。②有关川沙暴动的具体细节研究,请见黄东兰的《国家、地方社会与地方自治——清末川沙自治个案研究》,收录于唐力行:《“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2-140页。瞿俊的《清末新政在地方推行之困境——以地方自治风潮为中心》中对于清末新政推行过程中的民变进行了一个较全面的论述,其中也有川沙暴动的相关记载。详见:瞿俊《清末新政在地方推行之困境——以地方自治风潮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川沙暴动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川沙县境内,但其余波影响到周围县城——南汇县,以致当时报纸报道第一次南汇风潮时都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副标题。③《南汇之闹事风潮》,《时报》1911年3月27日,第5版。
1911年3月的一天,南汇无赖张某对当地渔户说:“汝等如欲拆去渔业公司之竹帘,能出重谢,我愿为首。”各渔户遂与之约定在3月24日行动。3月24日午后,南汇六灶镇沙涂庙的渔业公司附近突然有数十人聚集,张某“首执一小旗指挥一切”“另有三人鸣锣集众”④《南汇之闹事风潮》,《时报》1911年3月27日,第5版。。后“聚众四百余人,蜂至镇西持正学堂附设之蓄鱼公司,捣毁一空”①《南汇之闹事风潮续》,《时报》1911年3月28日,第5版。。民众们将该公司在河道中所设小港两侧的竹帘拆除,“并将在该处巡查之警察船及渔业公司添立之铁链鱼帘与商团备用之洋枪等件或捣毁、或则用火焚烧”。为首的张某与各渔户还声称“渔业公司压断渔利,与公司内合设之学堂无涉,不可惊动”②《南汇之闹事风潮》,《时报》1911年3月27日,第5版。。然其事未止步于此。事后众人前往附近的沙涂庙内商议此次事件,有人说“事已至此,终必追究”。于是张某便顺势而下,提出“现在势成骑虎,若再畏首畏尾,适授官绅欺压良儒之柄。不若效法川沙风潮,既大则办不胜办,官绅必将就过去”。众人决议再将学堂拆毁,“以慑官绅之胆”③《南汇之闹事风潮》,《时报》1911年3月27日,第5版。。
当晚十点左右,张某带领闹事者回到渔业公司所设的持正学堂,将持正学堂与自治公所的房屋拆毁并焚烧,“光烛四野,远近惊惧”,又高声扬言“一不做二不休,明日再打莲笔花桥及陈家桥、陈家行各学堂”。最初因渔利而起的闹事,已经转变为指向学堂和自治公所的反抗风潮。
周边乡镇亦遭波及。六灶渔业公司附近的陈家桥、沙陀庙等处“所设之小学堂台桌一切亦遭焚毁”。不远的周浦镇五乡二十五图内渔业公司“亦已被拆毁”“虽经区董请兵弹压,无如人多势众,不免酿成绝大风潮”④《南汇乡民闹事情形三志》,《新闻报》1911年3月29日,第14版。。
闹事者行径十分嚣张。3月27日下午一时左右,汤家巷渔业公司的经理汤庆楼到县府“警告并诉详情,云当匪众于二十六午后拆毁公司时,向之求免,该匪徒则谓‘不拆毁公司,即拆毁汝屋,速自择毋多言’”。即使附近周浦镇的防兵前来弹压,站于桥畔“放空枪数排,匪知枪无子弹,不惧,一拥过桥”,使得防兵不得不退保教堂和学堂。3月27日午后,闹事乡民又前去张江棚镇西乡廿八图内的渔业公司,“将水笆渔具拆除烧毁,又将河中家鱼肆行捕略”,甚至以刀枪棍棒与当地防兵发生冲突。直至苏抚不断派兵弹压,3月27日飞划营管带沈保义带兵前来力行镇压,南汇风潮方才归于平静。
(二)第一次风潮爆发的原因分析
川沙暴动和南汇风潮同样将矛头指向新政的代表:自治公所、学堂和绅董家宅,但出发点有所不同。川沙暴动中,民众将自治公所和学堂作为攻击对象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为:地方精英积极推行自治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从而导致地方的书吏、宗教领袖等对自治公所和推行自治的绅董进行报复⑤黄东兰:《国家、地方社会与地方自治——清末川沙自治个案研究》,唐力行:《“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9—140页。。而南汇风潮中,民众攻击自治公所和学堂的暴力行为更多地为了“慑官绅之胆”的恐吓,阴差阳错地走上和官府对抗的道路。为首的张某⑥南汇地方的讼棍,南汇第一次风潮中的组织者。的一句“不若效法川沙风潮,既大则办不胜办,官绅必将就过去”,酿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南汇风潮。
张某的一己之言之所以奏效,除闹事民众的盲从之外,外部环境的因素也需要考虑。在清末自治的环境下,地方士绅的权力得到伸张,“获得了较以前更大的活动空间”⑦黄东兰:《国家、地方社会与地方自治——清末川沙自治个案研究》,《“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论文集》,第139页。。南汇风潮中,《时报》的报道中记载,“二月初五清晨,县自治筹备所接得匿名揭帖一件,痛诋办事各董及破坏禁烟赌自治学堂”⑧《南汇风潮日记》,《时报》1911年4月4日,第6版。。可见南汇绅董的权力在地方自治中也获得较大的扩展,加之劣绅的存在,本就违法的闹事民众担心渔业公司报复也就事出有据了。
在此次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六灶镇渔业公司其实早与地方渔民有利益冲突,早在3月10日,六灶乡事务所和渔业公司的牌匾曾被揭去,并有一封匿名揭帖,书有“约期拆毁学堂兼打某宅”①《南汇风潮日记》,《时报》1911年4月4日,第6版。。事后苏州府程中丞在批评南汇县令赖葆臣的禀文中也提及,“且渔业公司结怨渔户当非一日,岂竟毫无闻见……该公司章程如占据河道等情,本有未妥,尽可商令酌改。何以听其任意执行……惟近来民气嚣张,地方官办理固多未善,而被毁各绅董亦当思所以自反”②《程中丞洞见南汇官绅之心理》,《申报》1911年5月18日,第11版。。六灶镇的渔业公司乃是绅董张仁庠集资创办,其他受到冲击的渔业公司也多由该地绅董创办。渔业公司与渔民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可以视作地方绅董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地方县令对于风潮的控制不力也是南汇风潮掀起波澜的原因之一。据《时报》的《南汇风潮日记》载:“南汇自上月初旬以来,时有匪徒广张揭帖,散布谣言。各地绅士鉴于川沙之往事,咸有戒心。谋所以保全其身家性命,故不惮跋涉奔波,赴县禀诉其情……孰知赖令别具肺肠,不一援手,以致蹂躏之处日广”③《南汇风潮日记》,《时报》1911年4月4日,第6版。。其实在事件发生以前早有绅董对地方情形予以警告,如3月12日七团乡议员便因“莠民百余人结盟,定于夜间拆毁连君等房屋之信息”,前去川沙寻找正在开会的县令赖葆臣;同日陈燮也因接到拆毁其屋的匿名揭帖而前去面禀赖葆臣,二者得到的回应或是讥笑或是置之不理。赖葆臣的不作为引起地方社会的恐慌,甚至原定在15日周浦镇陈家桥乡的选举也因谣言有人前来攻打而不敢举行。南汇县学堂的学生在17日夜晚听到屋后人声鼎沸,以为有人前来毁学,“学生从梦中惊醒,裸体而逃”,却是不远的船上有人失足落水而非拆屋,“然已饱受虚惊矣”④《南汇风潮日记》,《时报》1911年4月4日,第6版。。
即便是风潮发生的前一天,持正学堂向绅董潘锷丞急报有人即将闹事,学堂先行停课处置。赖葆臣在见到潘锷丞后,看其面露难色便讥讽到“设本县写一揭帖约期拆毁劝学所,汝其信之乎”,并嘱咐潘不必惊慌,派人“往沙涂勒令开课”。赖葆臣对待此事并不上心,而当潘锷丞回到六灶之时,“火已燎原,不可向迩矣”⑤《南汇风潮日记》,《时报》1911年4月4日,第6版。。基于后人之鉴可以认为,赖保臣对于地方早就出现的民乱先兆置之不理是诱发南汇第一次动乱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地方绅董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存在已久,赖对这些事情置之不理可以看出在原有的行政体制下官员的不作为,这也是传统中国的一大问题。新政的革新并未解决清政府在地方体制上的问题,这或许也是辛亥鼎革能够发生的一个内部原因。
地方武装力量的薄弱也是南汇风潮初期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毁坏六灶渔业公司以后,闹事者于3月27日前往张江棚镇西乡廿八图内之渔业公司,“将水笆渔具拆除烧毁,又将河中家鱼肆行捕略”,适逢附近有北蔡镇巡防队因保护教堂驻扎在该公司附近,“闻警驰至,率兵弹压”,但“匪徒见其不敢开枪,毫不畏惧”,甚至以“钢杠摆舞,进而以刀枪、挡棍、钢叉、织女梭诸兵器”,官兵“莫之敢撄”⑥《南汇风潮日记续》,《时报》1911年4月5日,第5版。。甚至县令赖葆臣在得知风潮较为严重而下乡督察时,也被围住不能逃脱。
第一次风潮发生时间并不久,且主要矛头指向渔业公司、学堂和自治公所,主要损失也集中在这三种事业之上。南汇风潮发生后,县令赖葆臣反应过于平淡,其究竟是自认不必大动干戈还是收受贿赂已不得而知,可知的是在辛亥光复局势到达南汇之后,赖葆臣被一些土匪和莠民劫持至沿海滩涂,意图与之反攻民军。除赖葆臣之外,无论是地方绅董还是苏松府令对于民乱的反应都较为迅速。适逢川沙暴动平息,参与镇压的沈保义部迅速赶来,加之苏府太守迅速派兵增援,故南汇风潮并未像川沙暴动一样掀起过大的波澜。
二、匪患生起——光复中的社会动乱
1911年春,南汇风潮在武力镇压下逐渐平复。然而渔业公司绅董与渔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未完全解决。川沙风潮结束半年多后,辛亥革命的余波迅速到达上海及附近地区,南汇出现清末民初的第二次风潮。
1911年11月7日,南汇县属接到上海国民军的两封信函,信中“乃命城中悬挂白旗,否则于数日内前来取城”。县令赖氏接到信后“并不惊慌戒备,亦不悬挂白旗”。但赖氏的实际行动则显示出他的真实想法,他“暗将官眷移避他处,并将衣箱什物陆续搬运出外”①《南汇现象记》,《新闻报》1911年11月8日,第14版。。11月9日,上海军政分府派出敢死队来到南汇,“城内巡警知民军已到,即在局内挂起白旗,大开城门。城门内商团学生五十人排队出城欢迎民军”②《南汇光复记》,《申报》1911年11月9日,第10版。,南汇县城至此初步光复。
南汇县光复,意味着新的政权即将在这个县城中建立,旧有的政权代表——县令已经失去合法的地位。南汇即将迎来的是新选举出的民、军、司法等长官,旧有的矛盾也再次出现。新选举的各项官职因军政分府尚未派人来到,故各长官均为本县绅董:顾旬侯为民政长官、顾可均为司法长官、王用霖为财政长官、张仁庠为警务长官③《续记南汇独立后之惨剧》,《新闻报》1911年11月11日,第2版。。其中张仁庠即是南汇风潮中六灶渔业公司的经理人。民军来到南汇以后,南汇的绅董们先行对县令赖葆臣进行审问,查出赖“亏欠库银一千余金,民军勒赖交出,赖无款可缴。民军即将赖拘禁习艺所中”④《南汇盐枭滋事》,《新闻报》1911年11月10日,第2版。。恰好“张与赖令素不合”,张仁庠在审讯后声明“如再不缴,于十八日四时宣布死刑”。张与赖的矛盾激化。
此外,民军在前往南汇各属乡镇进行收复之时发现“是处枭匪猖獗,肆行作乱……沪军都督府派令民军前往剿捕。该枭等任意抵抗,胆敢将是处各学堂焚毁劫掠,恣意横行”⑤《南市种种》,《申报》1911年11月10日,第18版。。南汇本就是一土匪横生之地,枭匪是主要的土匪群体之一。南汇土匪尤以沿海居多,此地“民风素悍,平日杀人放火、劫掠等事时有所闻”⑥《南汇光复后记事》,《新闻报》1911年12月7日,第5版。。辛亥鼎革,各类土匪也顺势而起。民军意图收复南汇下属各乡镇,对于匪患的控制是其与地方政府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南汇光复时利益受损的群体不仅有土匪,旧式的县衙杂役在新政权结构之下也受到冲击。就这样,渔民和绅董之间的矛盾、赖葆臣与张仁庠之间的矛盾、土匪与民军之间的矛盾、旧县衙杂役同新政权结构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南汇县的第二次风潮终于在衙役、渔民和乡下土匪的推动下爆发了。如《新闻报》记载:“十七日,衙役人等以夺其生计,纠结沙民千数人,轰至县属以拥戴县官赖令”,复有“武进士倪殿元……欲与六灶董张雏生⑦即张仁庠。寻仇……张舆论素极不洽,海民恨之入骨。且今春渔业公司结怨与各渔户,此次被选举为警务长,致犯众怒”⑧《续记南汇独立后之惨剧》,《新闻报》1911年11月11日,第2版。。后不久,军政分府派护军营帮带率领三百余兵“懈怠枪械,于昨晨由沪南制造局码头渡浦由陆路前赴南汇”⑨《派兵前赴南汇》,《申报》1911年11月12日,第19版。。终于在11月17日,由沪军营吴管带奏报军政府“南汇县境内现已安静,所有司法事宜刻经分别派员前往办理”⑩《南汇安静之报告》,《申报》1911年11月19日,第19版。。
此次冲突中,南汇县城损失较大。除县自治公所和学堂被毁以外,赖葆臣还被闹事衙役与土匪樊培生劫去,被安置在沿海角落地方①《攻剿南汇土匪》,《新闻报》1911年11月12日,第9版。据该报报道,这是因为该地居民“屡受赖令恩惠,故有如此之热心”。《松江新纪事》,《申报》1912年1月6日,第12版。。关押赖葆臣的南汇县习艺所,本为清末自治时设置用来关押罪犯的改造所,也在此次风潮中被樊培生捣毁,习艺所中关押的罪犯“亦暂解散”②严伟,秦锡田:《(民国)南汇县续志》,民国十八年刻本,第201页。。无疑,这对当地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守城的冲突中,商团留驻在南汇的队员俞志伟在土匪攻城之时拼死保护,被刀砍死③《南汇之所以然》,《时报》,1911年11月18日,第9版。俞志伟死后,商团会长李平书等为之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详见《申报》中的《商团俞志伟死难》,1911年11月12日,第20版;《商团员出殡志盛》1911年11月13日,第19版;《南市》1911年11月16日,第21版。。此外,处于矛盾中心的张仁庠在此次风潮中落水自尽,民政长顾旬侯的儿子也在此次事件中丧生。顾在此次事件的打击下无意于地方县政,南汇县的民政长官遂由“前年办理普济堂事颇得民心”④《南汇光复后记事》,《新闻报》1911年12月7日,第5版。的赵谨琪担任。幸而该县“城厢内外之各店铺,皆因各守中立,是以照常开市交易”⑤《攻剿南汇土匪》,《新闻报》1911年11月12日,第9版。。而南汇县的商团也在此事以后“人数愈少”,复又召集新班五十名,“勤加操练以资保卫而维治安”⑥《南汇光复后记事》,《新闻报》1911年11月19日,第5版。。
南汇县的第二次风潮在光复南汇县城的短暂过程中兴起又结束,该县再一次归于平静。然而辛亥鼎革的政权建设并未完成,部分矛盾仍旧存在,南汇县的风潮也并未完全结束。
三、匪声复起——南汇光复后的社会动乱
光复以后,南汇县进入了建设初期。辛亥革命以后,在新式风俗如剪发等推行的同时,市政建设中的收租也同样在进行。历经两次风潮的南汇县城,其财政“本极支绌”,而“各学堂、各押所、各自治公所等均被捣毁。目前修理及地方善后自治等费均无着落”⑦《南汇光复后记事》,《新闻报》1911年12月7日,第5版。。南汇民政长官赵谨琪虽与绅董提议借积谷生息,但此并非长久之法。同时,在南汇第二次风潮中的匪患问题并未解决,赖葆臣、樊培生与倪殿元⑧清朝武举,南汇人,清末民初时落草为寇。等反对革命者尚未被缉拿,并且樊、赖二人还游走在保守力量较强的南汇沿海,问题不容忽视。
早在1911年12月,南汇境内就已有乡民抗租、拆毁民宅的报道。《申报》在报道中称“浦东南汇县境赵家楼地方亦有乡民抗租滋事,将业主奚梅生之住宅拆毁”,得民政总长派兵才将该处事件镇压⑨《青南两县请兵》,《申报》1911年12月31日,第18版。。
无独有偶,1912年1月3日,南汇县民政长官赵谨琪致电上海民政总长谓“该邑大团等处有沿海沙民抗租滋扰,聚众千余人啰唣不休,掳人勒赎”,因该地防御力量薄弱,故请派兵前往镇压。与此同时,南汇的大团马场也因田租一事兴起风潮。该地“历议增租而佃户诚恐”。军政分府在接管该地以后,欲图整顿,派熟悉该地的郡人朱梅泉前去排查,未想“突起风潮,致被佃户围殴”,甚至其所穿之衣都被撕去⑩《南汇马厂亦闹风潮》,《新闻报》1912年1月5日,第5版。。此事以后,本就猖獗的沿海匪盗更无忌惮,甚至将“该处驻防水军枪械抢掠殆罄”⑪《攻剿南汇土匪》,《新闻报》1911年11月12日,第9版。据该报报道,这是因为该地居民“屡受赖令恩惠,故有如此之热心”。《松江新纪事》,《申报》1912年1月6日,第12版。。
赵谨琪所报告的大团沿海沙民抗租闹事,即南汇第三次风潮的兴起。此次风潮的主要推动者就是第二次风潮中的倪殿元和樊培生二人,并得到了许多土匪的响应。南汇当地的土匪张家生、倪四金、孙镜清等人获悉大团起事,适逢上海方面所派的调查员王柳生到达南汇,张家生便散播谣言,谓“此系派来剪发者。凡属清民,岂甘为彼党中人乎”,并诱导民众,“况大团已起事,若代清廷报仇,欲发大财正在此时”。张家生又与樊培生里应外合,从城内将城门打开,樊培生等随即入城进行抢劫。城内多家店铺受到劫掠,甚至一黄姓的福建店主还被匪徒刀伤数处。
樊培生入城前,民政总长派去的调查员王柳生会同南汇县民政长赵谨琪与樊培生谈判,樊培生顺势提出三项要求,即:1.交出董事顾静侯;2.不准剪辫;3.赶发积谷。但王、赵二人未答应,樊等便聚众进入县城,毁坏自治公所、劝学所和商务分会等处。从中可见,在南汇县第三次风潮中,主要起事者——土匪将剪发这一反清行为作为攻击对象,并砸毁代表新政权的自治公所等处,其维护旧秩序的心理暴露无余。究其原因,倪殿元和樊培生二人均为前清武举,他们无论在清末新政还是辛亥鼎革中都未能获取利益,其身份反而因政权变革一落千丈。这种身份落差加深其对于新生政权的愤恨,使其走上落草为寇的道路,于是在两次风潮中二者均对代表着绅董的自治公所、劝学所等处进行焚毁。
地方政府有了前两次教训,反应更为迅速。上海民政总长立即选派沪军营、盐捕营等武装力量前往镇压。盐捕营统领沈保义等在樊培生为其弟与抢来的女子大办婚礼时,袭击樊培生的驻点,击毙匪徒十余人,击伤七八十人。这让樊培生失去活动的据点①《南汇土匪闹事四志》,《新闻报》1912年1月9日,第5版。。事后沈保义派300余兵丁驻扎南汇及沿海要口,沪军各营士兵一律撤回②《南汇闹事后之详情》,《时报》1912年1月16日,第9版。,南汇第三次风潮告一段落。
第三次风潮的主事者仍旧是第二次风潮的余匪樊培生等人。他们代表着民国初年的清朝维护者,在新政权建立之初伺机而动。然而樊培生等人的挑拨只是一个表面原因,或者说是导火索。第三次风潮的深层原因在于民初的制度和思想变革并未解决地方政府的资金短缺问题,而恢复地方秩序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因资金短缺需征收捐税和平民生活需要保证之间的矛盾。其时共和民主的观念尚未深入影响基层,一般平民仍旧会有旧思想,这也是第三次风潮中有关“剪辫”“发财”“清民”观念大有市场的原因。对比抗战胜利后浦东同乡会和一些南汇旅沪商人对于南汇的重建工作,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资源动员较为松散,并且地方新式精英(或者说是“绅商”)的社会意识尚未建立,主要还是一些基于传统士绅的观念在其中发挥作用。辛亥革命以后的地方稳定,需要一套相对健全的民主制度予以保护。
四、结 语
总结三次风潮中闹事民众的行为,其共同之处在于对自治公所、学堂、绅董房屋方面的毁坏,并且普通民众仅对其进行毁坏而不抢夺,可见在民众眼中这些东西仅是造成此种困境的一大诱因。南汇的三次风潮表明:新生的政权建立之时,若仅注重维护自身利益,甚至利用资源进行利益扩张,势必会引起利益受损方的反抗。清末民初的政局动荡,此当为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