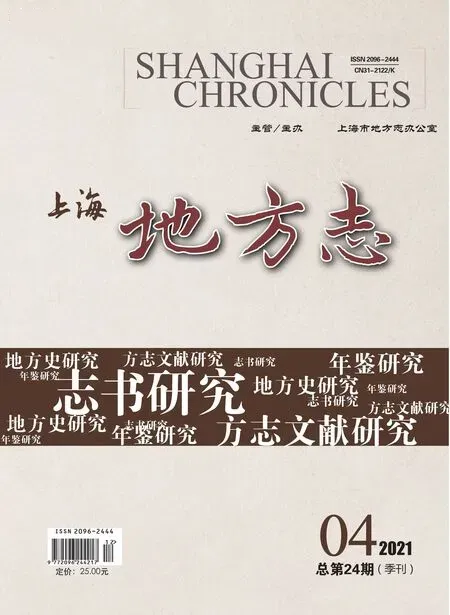晚清朱正元与《江浙闽沿海图说》*
2021-01-31白斌夏攀黄佳仪
白斌 夏攀 黄佳仪
中国地图测绘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的变革过程。与传统地方志书和官方文献对海洋地理的描绘相比,朱正元所编纂《江浙闽沿海图说》在使用传统描述语言的同时,采用西方测绘方式统计出来的数据,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正是这一变革的产物。晚清地图测绘事业中,以朱正元为代表的沿海测量和地图编纂者尽管并未超越西方测绘的已有成果,但其利用西方测绘的科学方法、结合本国需求进行大量实测和考证,为维护海疆安全做出巨大贡献,也成为中国以科学方法进行自主测绘的先驱,使得晚清成为中国海洋测绘和海图编制由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阶段。目前学术界涉及朱正元的研究主要有两篇,分别是汪家君的《19世纪浙江海区历史海图初考》①汪家君:《19世纪浙江海区历史海图初考》,(《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6卷第2期,第214—219页。和伍伶飞的《朱正元与<御览图>:晚清地图史的视角》②伍伶飞:《朱正元与<御览图>:晚清地图史的视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33卷第1辑,第152—158页。。前者通过论述《盛京七省洋图与七省沿海全图》《英版实测航海图》《八省沿海全图》《御览江浙闽沿海图》等历史海图的历史沿革、时空分布、基本特征和初步评估等,指出《御览江浙闽沿海图》试图摆脱英版图的影响,力求自成体系,自立规范,比同一世纪的其他历史海图高出一筹,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创新,堪称19世纪我国编纂的一部海图集佳作。后者在考查《御览江浙闽沿海图》及《江浙闽沿海图说》产生背景和经过后认为,正是在西方测绘技术的进步和清政府面临海上威胁背景下,洋务运动中兴起的西学教育培养了朱正元等测绘人才。而朱正元基于英版海图测绘和编纂的《御览江浙闽沿海图》融科学性和实用性于一体,是晚清作为中国海图由传统转向近代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朱正元《江浙闽沿海图说》系统研究的成果出现。因此,本文将从该书的作者背景、志书内容、编撰体例、志书特征和文献价值五个方面来展示该书的学术意义。
一、作者生平与写作背景
朱正元,字吉臣,号镜湖钓徒,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大约出生于1867年(同治六年)。1879年(光绪五年),12岁被选入广方言馆就读。1888年6月,因成绩优异被派往总理衙门考取一体乡试。同年9月,通过总理衙门的考核,并随后参加顺天乡试,相关经历登记在案。1890年,因清政府重修《大清会典》需要对所有舆图地志重加修订,朱正元辑出《海道图说》中的相关资料。1891—1894年,在格致书院学习,成绩较为优异,所作《俄国西伯利亚造铁路道里经费时日论》一文获得格致书院山长王韬的高度认可,并在《申报》头版发表。1897年,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考核,投入到江浙两省测绘事业当中。1899年夏秋完成《浙江沿海图说》(附海岛表)、《江苏沿海图说》(附海岛表),1900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经总理衙门呈送江浙两省沿海图说。又经过两年左右完成对福建沿海的实际测量和地图绘制。此后,大约在1902年到1903年冬春之际,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支持下,从事山东、直隶和奉天三省的沿海测绘工作。1905年病故于天津。
从朱正元的生平来看,他刚好经历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阶段。一方面,作为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代表,朱正元自幼接收传统私塾教育,少年时期进入与传统科举体系截然不同的广方言馆中学习英法语言及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其知识体系为后来洞察时事、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中国沿海沿江开展航道测量工作,并出版更新海图,更为科学和标准化的航线测量和海图制作方法逐渐被中国所接受和应用。以上的求学经历和技术发展方向成为朱正元决定重新测绘中国沿海航道的重要基础。在主持沿海测绘前,朱正元已经完成《周髀经与西法平弧三角相近说》《西法测量绘图即晋裴秀制图六体解》等论著。同时,在对测绘知识的系统学习和相关实践中,朱正元逐渐意识到,中国需要有中国人以科学方法自主测绘且符合本国需求的地图,以此维护海疆安全。此外,朱正元是在晚清洋务运动和外患严重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沿海的生活与学习,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经历,使得他更为关心中国的海防事业。在他撰写的《江浙闽沿海图说》中,对光绪年间沿海各区域的海战路线与炮台分布,均有详细的记录。
二、志书内容与编撰体例
朱正元的《江浙闽沿海图说》是对19世纪末期中国江苏、浙江和福建三省沿海的总体描述,由于朱正元曾编纂有《御览江浙闽沿海图》,该书应为《御览江浙闽沿海图》的文字说明。全书分为《江苏沿海图说》《浙江沿海图说》《福建沿海图说》三卷,并单独排印出版,每卷由正文和附表组成,其中正文中每省则按照沿海行政边界、海防卫所、岛屿与港口等做进一步划分。如《江苏沿海图说》正文部分分为:吴淞、上海、宝山(附小沙背)、狮子林、崇明、川沙(附南汇)、金山卫(附柘林、奉贤)、海门(附塘芦港)、吕四、掘港(附东凌港、河北汀、环港)、新洋港口(附斗龙港)、射阳湖口、老黄河口、灌河口、高公岛、墟沟(附西墅)、青口、朱篷口、刘河(一下系长江)、白茆口、浒浦、福山、通州、江阴(附靖江)、圌山关、镇江(附象山、瓜洲)、十二圩、金陵及海岛表等29个区域。《浙江沿海图说》正文部分分为乍浦、澉浦、蟹浦、镇海、宁波、三山浦、穿山、象山港、舟山、沈家门、爵溪所、石浦、健跳所、海门卫、松门卫、玉环、靴锹埠、温州、飞云江、大渔口、南北关(附沙埕港)、岱山、长涂、衢山及海岛表等25个区域。《福建沿海图说》正文部分分为长门(附馆头)、闽安、马尾、崖石、梅花江、连江(附东岱)、北菱(附黄岐、定海、小埕)、东冲(附可门)、三都、松山口、三沙、秦屿、沙埕港、松下口、镇东、海坛、万安、三江口(附江口)、南日、平海、湄洲、崇武、永宁、深沪、围头、金门、厦门、陆鳌(附将军澳、镇海)、铜山(附古雷头)、宫口、南澳及海岛表等32个区域。
江浙闽各省沿海区域的编写分成15个部分,分别是:1)冲要:将每个沿海区域的海防重要性分为“极冲、次冲、又次冲”三等,如福建长门为“极冲”;浙江穿山为“次冲”;江苏掘港为“又次冲”。2)钤辖:记录该区域海防属于那支部队管辖,如江苏金山卫“属松江府金山华亭两县提标金山营管辖,水路归外海水师六营轮巡”。3)里距:指距离周围城镇的水路和陆路距离,如福建三江口“北距涵头镇陆路五里;西距府治二十五里,水路较纡;东距江口镇二十里;东北距省会约二百里;东南距南日岛水路六十余里;东距海坛岛平潭厅治水路一百五十里;东北距长门水路二百八十里”。4)水道:记录区域航线的深浅(为大潮退后的数据)、宽窄及可以通行的船只种类,其中大号船吃水超过二丈,中号吃水超过一丈,小号船吃水为一丈内。计量单位为拓,每拓合六尺。如浙江象山港“港长约九十里,宽五六里至十余里不等,深约四拓,入内深七八拓至十拓不等;港内南岸蛤蚆嘴有通象山县小河,北岸有通大嵩城小河,西面有通宁海县小河”。5)潮汐:记录区域朔望日大潮上涨时间及高度。如江苏墟沟“朔望日潮涨于六点一刻钟,大潮高一丈四尺”。6)沙礁:记录区域航道上的浅沙滩和礁石。如浙江镇海“口外北面一片浅沙,东与游山相连,虽民船亦不敢于虎蹲、游山外直向北行。又,虎蹲西北有虎尾石(潮半即隐,上有黑色铁杆)。大游山东有夏太老婆礁(宜昌轮船坏于此处,上有红色木杆)。笠山炮台前有游山江礁(朔望潮落时,礁上水深七尺七寸,礁东面水深六拓处设有红黑色浮筒,筒上有黑色圆球)”。7)岛屿:记录区域不同方向的岛屿分布,可以与书后附海岛表相互佐证。如福建马尾“东面有罗星塔,其东北面与之相连者,曰‘青洲’,有村二,民居颇盛。东北面洋屿前有大屿、小屿(两屿均有孤树,最易识别)”。8)城镇:指区域沿海城镇,如江苏崇明“县城因海岸逐年崩坍,西南隅距海仅四十余丈,全城岌岌可危,近经筑堤障护,赖以无恙”。9)形势:指区域地形、交通在军事上的防御。“大凡地势,有前路必有后路,有正路必有旁路。由前路入犯者十一,袭后路者十九。由正路入犯者十一,抄旁路者十九。盖前路、正路必有坚台重兵扼其冲,后路、旁路则随处乘虚可入。道光二十二年,英人之犯乍浦,也不于天后宫前,而于东面金家湾之花鱼嘴;其犯镇海,也不于招宝山,而于南面之钳口斗。”如浙江蟹浦“镇海西北一带,浅沙至蟹浦而尽。由此登岸,可从海塘大道直扑县治,是为镇防。北面间道,密迩口门,须防抄袭”。10)船只:记录往来商船和渔船数量及活动,为大致估算。如福建围头“大渔船八号,小渔船八九十号;东石商船十号,余小船二十余号;安海水道,浅船只寥寥”。11)炮台:记录区域炮台位置、建立与改建时间、安装火炮数量和炮兵人数。如江苏灌河口“光绪二十一年办防。蛏架港筑土炮台二所,置土炮六尊;响水口东面老庄湖口土炮台一所,置土炮二尊;复林庄土炮台一所,置土炮二尊;响水口东街土炮台二所,置土炮八尊”。12)勇营:晚清时期的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本书中记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办理海防时期的沿海勇营数量和分布。如浙江舟山勇营“光绪二十一年办防,兵力较薄,不敷分布。十年,法防共八营二旗又小队一哨,分驻镇鳌山、东港浦、西溪岭、东岳宫、长春岭、大校场、西管庙、小竹山、獭山、虹桥、乌石庙等处”。13)绿营:清政府建国初期的军事单位,晚清逐渐被勇营所取代。如福建海坛“额设副将一员,左营都司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外委六员,兵裁存三百零五名;右营都司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外委六员,兵裁存二百四十五名。每营船两号”。14)异名:指“一地数名者”。如浙江石浦“南辉山或名‘东门山’,西南面西图名‘三门湾’”。15)杂识:指区域一些情形没有列出的。如江苏吴淞杂识记录的有,“道光二十二年,英人由浙洋移寇吴淞,攻西炮台破之,遂进犯上海;光绪二十四年,患他族之逼,处议自辟西岸为通商场,任各国聚居,新旧两炮台皆划入界内,于是议弃旧而留新,以新台能兼顾长江口门也,然既重门洞启则指顾环台尽属市廛,岂尚用武之地;崇、宝、沙因介崇明、宝山两县之间得名,近年西面渐坍,民皆徙避,海关因设检疫所于此,凡船自疫处来者,须停泊候验,以免传染内地;大小石头及鸭窝诸沙各有居民数百,而以再东之横沙为尤盛,有小市可得鱼蔬”。
除正文外,各卷书末尾还附有海岛表,用于记录江苏、浙江和福建沿海各岛屿的情况。江苏的海岛表格有2个,分别是长江口附近海岛表(自崇明东南角起计)、海州附近海岛表(自青口起计)。浙江的海岛表格有16个,分别是舟山东面附近海岛表(自舟山本岛起计算)、舟山北面附近海岛表(自舟山本岛起计算)、岱山附近海岛表(自岱山本岛起计)、长涂附近海岛表(自长涂本岛起计)、衢山附近海岛表(自衢山本岛起计)、乍浦附近海岛表(自天后宫起计)、澉浦附近海岛表(自长墙山起计)、象山港内外海岛表(自港口裹门山起计)、爵溪附近海岛表(自爵溪城起计)、石浦附近海岛表(自石浦城起计)、健跳附近海岛表(自健跳东面山角起计)、海门附近海岛表(自海门卫起计)、松门附近海岛表(自松门东面山角起计)、玉环附近海岛表(自玉环本岛起计)、温州附近海岛表(自黄华关起计)、南北关附近海岛表(自镇下关东面山角起计)。福建的海岛表格有23个,分别是长门附近海岛表(自长门炮台起计)、东冲口附近海岛表(自东冲角起计)、三都附近海岛表(自三都本岛起计)、松山口附近海岛表(自松山起计)、秦屿附近海岛表(自本处起计)、海坛西面附近海岛表(自海坛本岛起计)、海坛东面附近海岛表(自海坛本岛起计)、海坛北面附近海岛表(自海坛本岛起计)、海坛内港各岛表(自平潭大王庙炮台起计)、万安附近海岛表(自万安城起计)、三江口附近海岛表(自江口塔子山起计)、南日附近海岛表(自南日本岛起计)、湄洲附近海岛表(自湄洲本岛起计)、崇武附近海岛表(自崇武城起计)、永宁附近海岛表(自永宁城起计)、金门附近海岛表(自金门本岛起计)、厦门西面附近海岛表(自厦门本岛起计)、厦门南面附近海岛表(自厦门本岛起计)、厦门东面附近海岛表(自厦门本岛起计)、厦门北面附近海岛表(自厦门本岛起计)、古雷头附近海岛表(自古雷头南面山角起计)、铜山附近海岛表(自铜山本岛起计)、南澳附近海岛表(自南澳本岛起计)。各表格中又分为岛名、偏度、直距、长、阔、居民、船只、锚地、土产、异名、译名等11个类别。如温州附近海岛表中的一条,岛名“黄大奥”,偏度“东”,直距“二十里”,长“十九里半”,阔“九里半”,居民“千余户”,船只“百余号”,锚地“南面”,土产“山芋”,异名“大门山”,译名“何到岛”,基本涵盖三省沿海岛屿的基本数据。
三、志书特征与文献价值
(一)志书特征
《江浙闽沿海图说》成书于晚清末期,其文本受中西方地图编撰体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字。本书用繁体排版,但书中有个别文字已经采用简体印刷。此外。在对专有名字的使用当中,很多火炮名称翻译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大量岸防火炮名字“阿姆斯脱郎前膛炮”即“阿姆斯特朗前膛炮”“瓦瓦司前膛炮”为“Josiah Vavasseur”的音译,“克虏卜后膛炮”即“克虏伯后膛炮”①成书较晚的《福建沿海图说》中闽安炮台记录中已将“阜物士后膛炮”改为“克虏卜后膛炮”,即今天翻译的“克虏伯后膛炮”。。这种对早期外来语言的音译一直到20世纪初期都大量存在。同样,汉字的简化20世纪初期开始逐渐被知识分子所提倡,以降低汉字的学习难度。
2.计量单位。本书中的计量单位既有传统的丈、尺、寸等,也有比较西化的点、磅、拓②“拓”是英文Fathom的中文翻译,也译作“英寻”,为英制水深单位。1拓=2码=6英尺=1.8288米。见喻沧,廖克编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2010年版,第329页。等。具体表现在对水道、潮汐、船只、炮台等表述内容的描述中。如《浙江沿海图说》中,“沈家门港,宽约半里,深三四拓至五六拓不等”“朔望日潮涨于十点钟,大潮高一丈四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中西混杂的计量方式,与朱正元当时的求学经历有关。晚清时期,中国一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体系仍在维持运转,中西合璧的表现方式在晚清时期的大量文献中都存在。
3.内容。在本书正文中,不少内容有中西对比的论述。如《浙江沿海图说》乍浦“异名”条目中,“西图则以水道可通杭州,也名杭州湾”;石浦“异名”条目中,“南辉山或名‘东门山’,西南面西图名‘三门湾’”;玉环“沙礁”条目中,“行过大青约三四里,当路有一暗礁,潮退尚没水下二三尺,西图未载”;健跳所“水道”条目中,“大狗头与陆岸间,曰‘靖虹门’。西图作浅沙,并无水道,实则中小轮尽可出入”。这种表述在之前的志书编纂中基本没有,从中可以看出朱正元对西方国家在中国所测地图的熟悉。
4.译名。本书所附海岛表中在各岛屿的描述中有“译名”条目,即该岛屿的外文翻译名称。如《福建沿海图说》长门附近海岛表中熨斗山的译名为“划介”,川石山的译名为“尖峰岛”,五虎山的译名为“五指岛”,虎囚山的译名为“条纹岛”,东犬的译名为“东沙”。“译名”条目在近代以前的方志文献中基本是不存在的。到晚清时期,中国沿海海图大多为外国人绘制,以外文标注。因此,在本书中出现中外对照的译名。
(二)文献价值
作为一部沿海区域的实地测绘资料集成,朱正元的《江浙闽沿海图说》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本书完成后,朱正元获得清政府的赞赏,并在其后继续主持山东及其他北方沿海区域的测绘工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本书的文献价值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丰富的海防文献是本书最重要的价值
《江浙闽沿海图说》书中有许多对于海防和沿海防御等方面的记载,集中在“形势”“炮台”“勇营”和“绿营”条目中,此外“杂识”等条目也涉及海防的内容。这些关于海防活动的记载,对于研究晚清海防力量及海防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朱正元在凡例中对“形势”的解释具有明显的海防倾向。《福建沿海图说》中,连江“在闽江之北,自县城至馆头不过十余里,议者防其在东岱等处偷登,越馆头岭而南抄长门各炮台后路;或沿连江而西,由汤岭直犯省垣,建台置戍,亦具有深谋。惟此江虽宽而浅,进口处即小船亦须乘潮出入,防务似较梅花江稍松。”《浙江沿海图说》中,海门“为台州全郡门户,口门牛头颈与小圆山隔岸对峙,天然关键。今于南岸之外沙牛头颈,北岸之沙湾小圆山,分建炮台四所,颇得地势。能更置新炮,辅以防营,足以自固。惟遍地伏莽,须防乘发。”《江苏沿海图说》中,川沙“左江右海为松沪之外屏,由白龙港一带登岸,西至浦滨皆数十里而遥。从前建台置成防其抄袭固属过虑,然所筑炮台正对南水道来路,若能排列巨炮迎头截击,亦足淞防之先声也。”从具体内容可以体会到朱正元应对海上军事战略有过深入的调查与思考,有自身对海上攻防的思考,继而做出评论,印证撰者对本书军事性作用的希望。
而在“炮台”“勇营”和“绿营”条目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海防设施与防御重点的考虑。江苏、浙江和福建沿海炮台建立时间、数量和形制均有详细的记载,这些都成为当代了解近代海防区域分布和历史变迁的重要文献。《江苏沿海图说》中,崇明“当沙头港西岸砖炮台一所,康熙三年建,历次办防均加修筑,见置土炮六尊又土炮台一所,光绪十年建,已圮”。《福建沿海图说》中,闽安“北岸暗炮台系旧设,光绪十年为法船所毁,十二年重修,置八十磅弹阿姆司脱郎后膛炮一尊,一百二十磅弹阿姆司脱郎前膛炮二尊,十二生的克虏卜后膛炮二尊,二十年复于东面添建一所,置二十一生的克虏卜后膛炮一尊,铜铁土炮共十五尊”。《浙江沿海图说》中,飞云江“北岸东山埠炮台系旧设,置土炮七尊,兵五十名,光绪二十一年办防;南岸亦筑一台,与北台相望,台成而事平,未及置炮。”
此外,该书在个别地方的“杂识”中也有当地相关战事记载。如《江苏沿海图说》吴淞“杂识”条目:“道光二十二年,英人由浙洋移寇吴淞,攻西炮台破之,遂进犯上海”;《浙江沿海图说》舟山“杂识”条目:“道光二十年,英人在广东战,不利,率兵船来犯,陷之。明年,又来犯,又陷之。又明年,江宁和议成,各处解严。惟泊定海。英兵船逗留至二十五年,始扬帆去。自是定之民,晏然无西人之扰者十余年。咸丰十年,英法两国兵船,自天津败归,复入踞。未几,寻自去。”如此丰富的战争细节记载有利于还原当年战争的真实面貌。
2.沿海经济与地理文献的价值不可忽视
该书虽然并不是一本专门介绍沿海社会经济的文献,但书中“城镇”“船只”条目中记录的内容展示近代江苏、浙江和福建沿海城市与海上活动的历史风貌。“城镇”条目内容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十九世纪末期东南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为晚清经济的相关研究提供例证。如在《江苏沿海图说》中,上海“城镇”条目描述为“自通商以来,城北一隅之地各国于此驻领事、设洋行,南北船货如水归壑,地方繁盛,甲于各省,骎骎乎与香港并驾齐驱矣”。此外,在“船只”条目中从商船、渔船数量也可推知当地海上贸易、渔业经济发展状况。如在《浙江沿海图说》中,宁波“船只”条目数量记录为“商船数百号,各村落大小渔船约多至四千号”,而对比《江苏沿海图说》上海“船只”条目数量记录“本处沙船三十余号,渔船一百余号,杂船四百十号,此外中西船之停泊者轮帆蔽江不可数计”。船只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地航运需求和商业往来的实物表现,本书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此外,“船只”条目中对于了解近代东南沿海渔业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数据价值,其各区域渔船数量分布及不同时间渔船的跨区域流动是了解近代沿海渔业捕捞的重要文献支撑,其他同时期的文献鲜有如此完整而准确的数据。
本书中“水道”“潮汐”和“沙礁”及所附海岛表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完整性,为海洋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数据。水道使“何等船只可到与否不待言而自现”,潮汐配合水道信息,沙礁则“详晰注载俾知趋避”。《福建沿海图说》所附海岛表中,有某岛形为“布袋澳”“遇飓风时泊民船最稳”的相关记载。就当时而言,这些关于水道、潮汐、沙礁和相关地形的信息为船只往来航行提供了很大便利。此外,在该书所附海岛表有利于对岛屿开发的研究。海岛表居民信息充实,对岛屿的居民数量做明确的定量调查,并且对其中多个海岛的开发经历记载详细,如表中对福建海岛古浪屿的描述为“古浪屿与厦门隔岸相望,木石清奇,为诸国所绝称。厦门通商,举丸领事公署洋商住宅以及旅馆学堂医院等皆分建于此,遍山洋楼,华民则缩处西北一隅”。简短的华民偏安一隅的描述便已经展露我国人民当时生活之艰辛,但就描述中鼓浪屿数量众多的房屋和功能齐全的设施来看,当时鼓浪屿的开发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而在居民信息之外,船只的记录也能够看出当时人民对岛屿的开发利用程度。如浙江省所附海岛表中对于朱家尖的描述为“居民数千户,船只百数号”。
四、结 语
朱正元的《江浙闽沿海图说》是晚清时期中国海洋文献的代表作。与传统海洋文献专门志书所不同的是,本书是在运用西方测绘方法通过数年实地测绘和走访调研基础上撰写的文本,在近代地图史和方志编撰史上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地图史沿革来看,尽管自明代开始中国的地图编绘受到西方制图方法的影响,但从事地图测绘的人员并没有接受系统的相关科学知识学习。而到了晚清时期,以朱正元为代表的一批学子,在国门洞开和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在少年时期就接受较为系统的西方语言和科学知识的学习与训练,熟知西方地图测绘与编纂方法。这些成长与知识背景都在《江浙闽沿海图说》的编撰中得以体现。同时,中国制图的优秀传统仍得以保留下来,这就是图、文分开的绘制方式。这种绘制地图的方式在中国古代已经非常成熟,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元和郡县图志》和《乾道四明图经》。从地图测绘来看,本书即为《御览江浙闽沿海图》的文字说明与补充。另一方面,在方志编纂领域,本书是近代少有的描述中国东南海防与沿海区域的专门志书,尽管全书为地图的说明,但保留了大量的海洋地理、海防、沿海城市与贸易活动等第一手的文献数据。总体而言,本书作为《御览江浙闽沿海图》的文字说明和补充,在研究近代地图测绘和海洋地理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