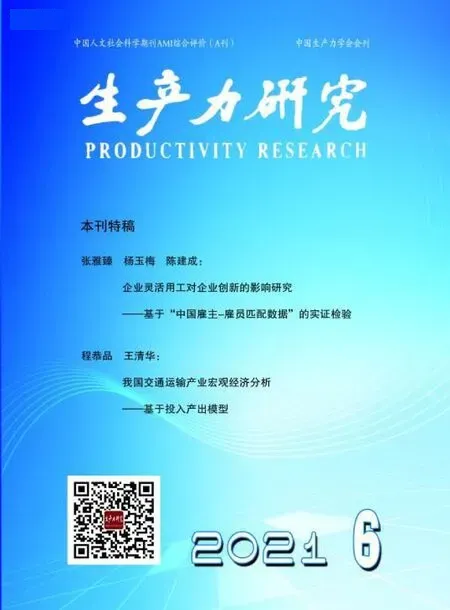从“互助”到“共赢”:打破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限制
——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2021-01-30陈哲
陈 哲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邻里之间、留守老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合作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1]。目前,农村地区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开始凸显。由于农村养老设施不完善、孝道观念的削弱、养老服务资源和投入不足等问题,传统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甚微。《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大力支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发挥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入手,积极动员各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服务中”。
近年来,以社区为地缘平台的互助养老模式开始兴起。“互助养老”模式融合了传统家庭养老和现代社会养老的特点,但与传统血缘互助养老不同,现代社会的互助养老更多利用地缘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的纽带,利用社区力量和邻里老人之间能力的互补性满足养老需要。目前,该模式在国外较为盛行,类似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时间银行”“村庄运动”和“劳务储蓄”等。而我国互助养老的实践还未有效地适应国情。因此,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还存在一些限制性问题。我国农村老年人需要从经济、精神和日常生活进行相互帮衬,要实现互助养老模式的长久运行,就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资源支撑,打破局限,实现农村养老服务从“互助”到利益“共赢”的转变。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互助养老的契合
(一)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
与互助养老这种基于信任和互惠的模式高度契合,社会资本理论也是在信任关系和通过非正式规范来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的。最早由布迪厄在20 世纪60 年代从社会空间的一些研究中逐渐开始发展[2],他定义社会资本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与熟识的关系网络有关,具体来说,与一个集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资源和关系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帮助……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3],这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集体行动的广泛合作。在布迪厄的研究中,“场域”和“惯习”是以最为核心的概念,“场域”可以理解为多种多样的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合作形成一个社会网络,这个网络联结了社会中的不同资源。“惯习”是客观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的一种社会化的主观性。它与场域之间相互协作,相互制约[4]。
随后,普特南重新定义其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不一样,“其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5]。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资本体现出了公共价值的层面,在基于信任和非正式规范形成的社会资本上,信任、规范和网络就成了社会资本的关键词。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能够提升农村互助养老中互助者之间的行动能力,通过影响和延伸农村老年人的资本要素,来构建起完整的农村互助养老体系。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互助养老的契合逻辑
中国传统的养老伦理就是建立在相互信任、非正式规范和互惠合作关系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农村留守老人的互助养老模式与社会资本理论不谋而合。换句话说,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他们社会资本的扩展程度。互助养老依靠相互协助资源来支撑,也属于集体组织共同行动的一种方式。奥尔森认为在每个人理性的选择下最终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但是,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够使农村社区的互助有效实施,打破集体行动中不信任的困境。
有学者认为可以将老年人社会资本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微观上老年人所拥有的信任、亲情与参与等;二是中观层面社区互助养老组织的关系网络和资源整合的能力;三是宏观层面上互助养老的顶层设计,包括法律、制度和理念等[6]。以上已经提到本文更适用于普特南的定义来构建互助养老模式。首先,构建相互信任的基层社会机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越紧密,信任就越重要,构成资本延伸网络需要以信任为前提。其次,规范是社会资本互助养老的一个前提条件,用于限制互助者双方的行动准则,确保合作形式良好地展开。最后,构建社会网络是实现互助形式的“舞台”,它连接着各个互助主体,也为各互助养老老人形成了一个渠道,便于互助双方相互团结,这也是能够有效培养公民精神的一种网络。
三、目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互助养老的实践
在我国,互助互济的思想根深蒂固,比如唐朝时期农村互助组织“农社”以及北宋时期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义庄”的主要功能有提供祭祀活动的经费、帮助宗族孩童上学、稳定地权、兴办公益事业和赡养等。其中养老责任就归属于赡养之中,主要是开展家族互济[7]。
回顾现代,起初部分省份探索农村幸福院,以农村家庭和社区养老院联合的形式,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随后,各政策文件纷纷下达要构建和完善农村互助养老问题,其中《“十三五”国家老龄失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事业。以幸福院为例,秉承“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原则,以村集体名义主办,没有配备专门的养老照料专业人员,是附近老人共同生活相互帮助的模式。并且,幸福院不提供住宿,在管理上坚持自主和自愿的原则。另外,有些农村地区发展了协会式的互助养老形式。比如,福建老年协会的互助模式,与幸福院不同,该模式有领导人员,多由该协会有知识和威望较强的退休回乡干部担任。协会专门的活动场所建立在村附近,活动内容包括阅读报纸、棋牌、观影、唱歌等内容。其活动经费多来源于政府补贴和成员入会会费。该协会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固定的娱乐场所,让老年人老有所乐,也为附近的年轻人提供了去处,年轻人还可以帮助照顾老年人。
我国农村目前的互助养老模式只是开始了一个初步的探索,但实施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部分农村幸福院在实践过程中成为了一个空壳,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的模式选择。
四、农村互助养老社会资本缺失的现实困境
(一)农村老年人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
老年人自身的社会资本和家庭的社会资本共同构成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其中,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农村老年人自身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老年人个人对信任和合作的思想观念、与邻里交往、文化水平等因素。由于农村老年人经济较弱、思想观念传统、文化水平和与邻里交往的频率较差,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社会网络较窄。另外,农村老年人难以对家人以外的邻里产生信任,与周边群体和社区的人际交往频率更低,身体限制和观念限制弱化了他们个体的社会资本。
从家庭的社会资本来看,如果儿女常年在外务工,就会产生地域上的阻碍,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减少。另外,传统农村老人观念中带有养老应由儿子来承担,女儿嫁出去就不属于家庭成员的陈旧观念,而外出务工的子女会选择将家庭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向后代的教育,忽视了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多固守着“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的期望,但子女又面临市场竞争的生存压力,两者之间形成了矛盾,导致家庭社会资本分散。
(二)农村老年人团体层面社会资本的匮乏
在农村地区“熟人社会”较为盛行,传统农村社区之间要么有着血缘关系,要么就因为地域的聚集熟悉程度较高。比如,最为典型的有以血缘或者姓氏为个体的行政村,这种行政村内的成员大多都为亲戚关系,具有信任感优势。但是老年人体弱多病,若身上有慢性病会长期依赖家庭,青年人员流动性较大,社区团体发展不顺利等因素,传统熟人社会在现代农村中特征较弱。邻里之间仅仅是见面打招呼的关系,社区团体资本就得不到衍生。并且,农村社区团体社会资本的存量短缺,幸福院的模式即使为老年人提供了日间照料的场所,但是对于部分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来说,实际操作上存在局限性,由于个体资本的局限性导致了老年人人际关系网络资源的稀缺。
另外,社会资本中的规范指社会团体、志愿者以及组织等规范性团体,旨在解决组织中成员所面临的集体困境,而这种团体基本在执行过程中有正式或者非正式规范的制度。从农村地区来看,尽管老年人个人的资本延伸意识不足,但社会团体可以对邻里老人之间的互惠互助产生引导和支持作用,不过农村地区社会团体资源较为匮乏,这也是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社会资本缺失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老年人国家层面社会资本的薄弱
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政府自上而下对于农村老年人社会资本的构建推动,指向政府对互助养老的顶层设计推动,包括立法、制度和理念等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没有法律体系规制。部分制度仅仅是建立在互助养老初步探索基础上,而且实行自愿原则,没有明确互助养老管理模式和实施细则。二是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政策构建不健全,比如,2013 年民政部出台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中,没有将农村社区互助型养老模式算入其中,使得社区互助养老场所管理不当,存在部分安全隐患和权责问题无法解决。三是养老保障并没有良好地体现老年人的需求,无法为互助养老的社会资本托底,提供社会保障资源。由于农村公共养老服务体系不发达,因此出现了新兴的养老模式做补充。不过当下我国互助养老体系的建立还在探索之中,因此良好的社会保障是拓展互助养老社会资本的最优选择,然而,农村养老保险和津贴问题还需进一步完善。
五、以“互助”实现“共赢”:构建社会资本的路径
(一)提升农村老年人的个体资源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前提是信任,根据帕特南的定义,公民应积极参与共同事务,形成公民共同体,包含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以及社团活动等内容。而农村互助养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公民共同体”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邻里关系、家庭关系和社区朋友之间的信任关系。由于农村行政村之间邻里较为聚集,可以构建“互助网”,即将可实行互助范围内的老年人聚集起来,创建联系方式和列明需要互助的内容,消除邻里之间的陌生感,创建辐射范围内的熟人社会。
在家庭资本方面,应鼓励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比如自愿参与幸福院的互助照料,自主管理,可以激发老年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通过自主交流的形式拓展个体资本。传统家庭观念主要是以“孝”为先,大部分农村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没有时间来顾及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乡村街道宣传栏上应在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挖掘新的阐释,提倡子孙共享天伦之乐的生活方式,倡导子女常回家。子女也应与周围邻里形成更紧密的联系,为扩展农村老年人家庭资本打下基础。
(二)培育和构建农村各类团体社会资本
社区组织是农村居民相互交往的载体,可以表达农村老年人的诉求和需要。社会资本也需要一定的嵌入性,具体来说就是需要社会组织的引导才能发挥社会网络的作用。农村社区组织主要包括社区机构、老年协会、青年团、农村妇联和各类民间互助组织,尽管这些组织不直接承担养老责任,但是可将他们与互助养老结合起来,培养农村青年群体的志愿精神。另外,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观念较为固化,需要年轻的社会组织发挥其指导作用,比如社工介入,开展互助小组活动,一方面是引领和指导老年人怎么相互帮助,可以在哪些日常生活中相互协作,另一方面是要通过社工小组展开活动卸下她们防备的心理,能够对邻里相互之间敞开心扉去信任他人。对于村内有固定互助养老的场所,应协调各类组织定期定点的协助,及时了解农村养老群体的需求向政府部门反映需要改进的地方。从群体理论中,我们可以得知社区互助养老自组织培育的过程包括养老需求评估、选举组织管理人员、发现社区资源、形成雏形、培育养老计划、逐步组织化、互助组织公益化、互助组织逐渐成长并最终成熟的过程。一旦社区互助组织培育建立,农村老年群体的互助养老网络就得以扩展。
(三)完善农村互助养老外部环境
政府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力量,应该完善我国互助养老服务的顶层设计,推动现有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完善,从立法、制度、理念宣传上为其提供资源,保障农村互助养老的实施。首先,针对现有法律,应构建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对农村互助固定场所的管理和约束,确保老年人有一个合理合法的娱乐互助环境;农村固定场所的缺乏是阻碍老年人互助养老实施的根本条件。各村委应紧跟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为每村构建起养老的基本服务设施。同时,还要加强对养老互助协会和志愿性团体的管理,为其提供资金来源,运用适当的慈善和志愿服务法律和文件来规范社区组织资本的有效性。其次,就政策出台方面,由于城市和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存在差异性,各地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出台有关当地互助养老模式构建的政策。最主要的是该模式下的资金来源,当地政府应该积极开拓多元长效的互助养老资金筹集渠道,适当给予养老津贴和补助,从用地建设和投资方面为互助养老提供政策优惠,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保证国家层面社会资本得到有效发挥。
六、结论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增强,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探索创新有效的养老模式,也是推动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目标之一。相比城市,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更容易被忽视,受经济发展、养老服务设施和子女外出打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发展邻里之间的互助,使得邻里范围内的老年人都实现“合作共赢”,达到老有所养的目的。社会资本理论正是基于改变这一难点的基础上,通过发挥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融合能力来提升互助养老服务。鉴于农村老年人还有丰富的社会资本没有得到良好的开发,因此,从个体、社会组织和国家三个层面构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使其形成社会互助网络,维护互助养老模式的长效实施,对解决目前养老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