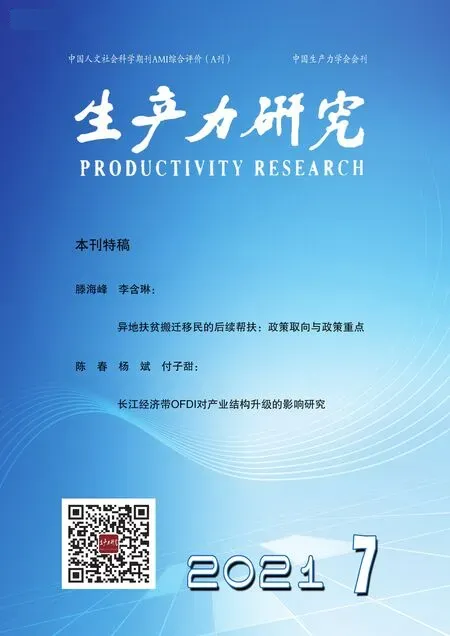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后续帮扶:政策取向与政策重点
2021-01-30滕海峰李含琳
滕海峰,李含琳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the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has completed the“spatial migration”of part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under the limited time and material resources,and made this part of the population star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ith the goal of“human development”in the new environment.The new environment refers to two kinds of situations:rural resettlement area and urban resettlement area.For the former,there have been clear policy attention,that is,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however,at present,the national policies for the latter are relatively few,an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re more prominent,so new policy attention is more necessary.The practice shows that“spatial migration”has brought many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 migrants who move to cities and towns,but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For new changes and new challenges,we need a lot of policy innovation in optimizing the urban space structure,promoting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allocating scientifically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 of market and supplying public education resourc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term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immigrants and the towns to which they moved in the areas of space,development,power,soci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so as to achiev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加强扶贫项目资金资产管理和监督,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五个一批”之一,面临着政策红利持续发挥及后续帮扶工作政策支持的现实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自实施以来,其搬迁安置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向条件较好的其他农村地区转移性就业,目标是农村安置区;另一种是向城镇地区转移性定居和生活,变成城镇经济的一部分。总体来讲,因安置区域和安置方式的不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政策重点理应不同,有所区别。对于农村安置区的搬迁移民,主要应以农村居住和从事现代农业生产为特征,其政策转型方向是“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1]。目前已有中央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关注与相对成熟的政策体系,各地都在积极贯彻落实。对于城镇(以下简称“迁入城镇”)安置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以下简称“搬迁移民”),主要应以城镇居住和从事非农产业为主要特征,其政策转型路径和着力点是促进搬迁移民与迁入城镇融合发展,政策目标是提升搬迁移民城镇化质量和迁入城镇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和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今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转型和政策关照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主题。
一、“空间迁移”引起的搬迁移民变化及挑战
易地扶贫搬迁,自200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专项资金在全国范围内陆续组织开展以来,已经快20 年了。截至2015 年底,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已累计搬迁1 200 万人以上。截至2020 年3 月7 日,“‘十三五’规划的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有930 万贫困人口乔迁新居,走出了大山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1]。其中,小城镇或工业园区集中安置的搬迁移民约263 万人①根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十三五”时期,集中安置点安置的搬迁人口搬迁总人口的76.4%,其中,行政村内就近安置占39%,建设移民新村安置的占15%;小城镇或工业园区安置的占37%,乡村旅游区安置的占5%,其他的集中安置占4%。即小城镇或工业园区安置的搬迁移民占总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26.27%,由此推算,“十三五”时期,小城镇或工业园区集中安置搬迁移民约263 万人。,占28.27%。若以此比例计算,2001—2020 年期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进入城镇安置的搬迁移民约为600 万人。实践表明,这部分搬迁移民,是在以“脱贫”为直接目标导向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支持和社会各界帮助下,搬迁移民在有限时间与有限财力物力支持下,完成了从“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的地方向城镇的“空间迁移”与“空间安置”,短期内实现了“空间”上的城镇化,也在客观上“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空间生产和享用的非正义现象,把社会主义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镌刻在祖国大地上”(胡潇,2018)[2]。但由于时间短、底子薄,搬迁移民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空间迁移”引起的搬迁移民的变化
客观实践表明,由于“空间迁移”,搬迁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占有和使用的生产资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伴随性地引起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方面的变化也是根本性的。一是占有和使用的生产资料变更。搬迁移民在迁出区,实际占有和使用承包地,从事小农生产和产品自主消费和少量的商品交换,更多的属自然经济形态,相对封闭和独立;搬迁移民在城镇,失去了原先承包地的占有与使用,不能再从事熟悉的农业生产。搬迁移民的生产资料由土地变成了“完全自由”的劳动力。二是劳动力商品化及其价值生产方式的变化。政府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方式,帮助城镇移民提高非农就业技能、助推融入城镇就业市场和融入现代市场体系,共享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红利。三是搬迁移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指居住环境的变化引起家居方式、能源方式、取暖方式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农村生活转变为城市生活,而且熟人社会变成了相对陌生人社会、群体性活动变成了相对独立性活动。四是搬迁移民融入现代城市社会方式变化。搬迁移民进入城镇被动或主动从事非农产业,以自己独立自由的劳动力参与劳动市场分工,通过市场化的劳动资料与自主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市场化的产品和商品,并在社会分配和市场交换中获得自身劳动价值体现,近距离进入现代文明体系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二)“空间迁移”引起的搬迁移民面临的挑战
由于这些显著变化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而且也是被动完成的,在时间上、心理上和适应性上都相对仓促,搬迁移民要实现自身发展及其与城镇的融合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一是搬迁移民大都来自偏远山区,思维方式相对封闭、现代知识相对欠缺、非农技能相对薄弱、现代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等,接受和融入现代城镇生产生活体系还存在不少现实困难;二是政府帮助下参与的技能培训、劳务输出和非农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诸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对于习惯了农村平稳生活状态的搬迁移民而言,由于城镇生产和收入来源的不可预期性和不稳定性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三是搬迁移民原有的承包地,尽管保留了承包权,但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水平较低,且各地差异性大,以承包地为依托的财产性收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四是部分安置区为搬迁移民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商铺,但商铺分配是市场化、股权化,收益取决于市场行情,因而这方面的收入很难保障。因此,搬迁移民在城镇能否“稳得住、能致富”和实现安居乐业,还需要相应的政策关照和支持。
二、“空间迁移”引起的迁入城镇变化与挑战
农村贫困人口的“空间迁移”不仅仅给搬迁移民带来了诸多根本性变化,也由于搬迁移民的空间介入,城镇空间结构、人口构成、社会环境、发展要素等发生诸多根本性变化,也面临相应的挑战。
(一)“空间迁移”引起的城镇发展变化
对迁入城镇而言,搬迁移民不是单纯地“硬性”与“单向”介入城镇空间,不是单纯地占据城镇空间与城镇资源,也不是单纯地分享城镇设施与公共产品,而是为城镇发展带来了诸多方面的新的发展变化。一是搬迁移民客观上增加了城镇人口规模,尽管是外来人口,但仍是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策推动下的城镇机械增长人口,搬迁移民客观上改变了城镇原有的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的知识结构、文化结构、就业机构、社会结构等;二是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的急速改变,意味着城镇医疗、教育、娱乐、文化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将伴随性地发生变化,同时,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消费结构的变化,城镇产业结构以及市场运行也将发生变化;三是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要求用地规模、空间结构以及水、电、气、信息等基础设施的供给与需求将伴随性地发生变化。根据人均建设用地100m2/人匡算,在“十三五”时期,全国因安置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而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约2.63 万公顷。
(二)“空间迁移”引起的城镇发展挑战
政策实施中客观产生与客观存在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给城镇规划、城镇建设与城镇管理带来诸多挑战。一是空间结构优化并不会伴随城镇移民安置区的建设自发产生,因为空间结构的优化,不仅仅是居住小区、楼堂馆所建设,更核心地在于整个城镇的功能分区与结构优化,如果处理不好安置区与整个城镇空间结构的关系,有可能割裂安置区与原有城镇的关系,甚至有可能使得安置区成为在城镇的“农民集聚区”。二是搬迁移民的迁入,并不会伴随性地成为城镇人口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城镇人口规模的成长,并不单纯是人口规模的“数字相加”,更在于人口结构的优化与质量提升以及相应的文化与社会融合。如果处理不好搬迁移民的“城镇化质量”提升问题,搬迁移民始终是在城镇居住的“农民”或“贫困户”,城镇发展的质量更是难以提升。三是搬迁移民要长期的安居乐业,根本在于“乐业”,但“乐业”之关键的就业岗位并不会伴随性地产生、搬迁移民与就业岗位也不会伴随性地自发匹配,这些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发展,甚至会因为无业可就而产生游民引致的社会问题。
三、“空间迁移”的本质与“融合发展”的现实选择
(一)“空间迁移”的本质
易地扶贫搬迁是搬迁移民放弃原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的过程,是“破”的过程,也是一种“否定”的过程,目前这种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今后需要做的就是“立”的过程和“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提升过程。因为“破”不仅仅是为了“破”,是要在更高层次上的“立”;“否定”也不仅仅是“否定”,要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再建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否定的否定”讲得很清楚,“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的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方式,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3]。搬迁移民融入城镇,就是“破-立”与“否定的否定”的发展过程。尽管近期搬迁移民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城镇就业与居住,但与真正城镇化的要求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目前的从业方式及其长远发展的可持续上来讲,还有诸多有待提升的地方。“历史表明,城市化与物质劳动、精神劳动的深度分工相联系,源自生产方式的变革。”(胡潇,2013)[4]这个过程对于城镇和搬迁移民来说,当前还远远没有完成。
(二)当前“空间迁移”存在的问题
为了搬迁移民在思想观念、经济收入、城镇生活方面的顺利过渡,也是为了实现搬迁移民“稳得住”,各地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针对搬迁移民能在城镇“稳得住”的实际需求和困难,采取了诸多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技能培训;二是提供就业机会;三是提供产业发展支持;四是提供金融贷款支持;五是提供社会保障;六是提供商铺共享机会等。在众多的举措中,政府提供就业机会能够显著起到政策设定的“稳得住”的目标,其他举措相对不显著(吕建兴等,2019)[5]。为什么会如此?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搬迁过程中产生的不安全感,即原有的安全条件被破坏后并没有或不易建立替代的安全条件(毛丹和王燕锋,2006)[6];二是被动城镇化群体的身体素质、教育程度、社会资源可用能力等显著影响着他们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吴大远和施运华,2014)[7],由此影响搬迁移民的融入过程和发展程度;三是从政策逻辑和现实条件角度看,当前易地扶贫搬迁的城镇集中模式面临着极大的局限性(马流辉和曹锦清,2017)[8],比如,由于整村搬迁与集中安置,一般位于城镇郊区或边缘,村集体成员集中,但与城镇原有居民联系相对较弱;搬迁移民的家迁入到了城镇,但由于在本地不好就业仍需外出务工;配套建设了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及给排水、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但由于是新建设、新运营、新管理等因素,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与老城区的优质资源相比,还有一定距离,特别是群众最为关心的教育资源;四是从“从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角度看,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这应该是稳定搬迁的必要组成部分。”(檀学文,2019)[9]针对这些主观与客观问题,搬迁移民在城镇的生计与发展是一个需要政策长期关注的现实问题。
(三)“融合发展”是弥补不足的现实选择
搬迁移民与迁入城镇是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客观存在的、具有空间同存性的特点,推动两者融合发展,是弥补不足、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现实选择与逻辑使然。主要缘由:一是搬迁移民事实上已居住生活在城镇,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城镇产品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与原有居民、企业、政府等各类主体产生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关系,从而“才能展开对包括空间在内的整个生存世界的能动作用,才能在对空间的社会性形塑中建构、确认并拥有自己的生命空间”(胡潇,2013),在城镇新的环境中逐步营建自身社会空间的同时,对城镇空间与城镇发展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即搬迁移民唯有在新的环境以新的生产方式参与产品生产与财富创造,才能发挥自身价值并在城镇持续生存。二是伴随搬迁移民进入城镇的,还有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劳动力、社会需求、空间拓展、多元文化等,若能将其科学合理地纳入城镇整体空间布局及其相应的功能分工,不仅能避免人为的“城中村”的出现,更能推动城镇产业形态多元化、组织多元化、分工社会化、发展链条化,更会促进城市空间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这是一次重组、融合、提升的发展机遇。所以,推动搬迁移民与迁入城镇融合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导下的城镇规划和资源配置中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转向(袁蓓,2020)[10]、避免“空间非正义”(胡潇,2018)的现实选择,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四、“融合发展”的政策取向和愿景目标
(一)“融合发展”的政策取向
一是政策对象从搬迁移民转向全体市民,从特殊政策转向普惠政策;二是政策任务从搬迁移民的“空间迁移”转向融合发展,要将移民及其居住小区纳入城镇、将城镇纳入区域空间总体谋划、整体推进;三是政策目标从“搬得出、稳定住、能致富”的短期目标转向搬迁移民与迁入城镇融合发展的长期目标,从单纯的以发展空间为载体的、个人物质追求转向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终极价值(叶汝贤,2006)[11];四是政策过程由政府推动向政府与市场相结合转变,即政府职能从搬迁工作的谋划者、推动者、实施者、监管者向城镇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者与维护者、优质文化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与维护者、公平市场环境与发展环境的营造着与维护者转变,重在做好基础工作,旨在引导和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主体作用。
(二)“融合发展”的愿景目标
近期目标主要有,一是搬迁移民能够以劳动力自愿、平等、公平地参与城镇生产分工、财富生产与分配;二是逐渐适应社区化的群众组织、社区治理及城市生活;三是在平等共享城镇优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城镇生活适应、市民身份确认、城镇文化共振及未来发展预期;四是能够促进国家关于“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的实现,巩固精准脱贫的效果,降低返贫的概率。
远期目标主要有,一是搬迁移民及其居住小区成为城镇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全方位、多层面深度融合发展并实现城镇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及社会结构日趋合理、充满活力;二是搬迁移民文化素质、技能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在“拔穷根”中与“贫困”“移民”等称号根本脱离;三是全体市民,包括原有居民、搬迁移民以及新进入的城镇居民,在城镇共振共享发展中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五、“融合发展”的政策重点
(一)优化城镇空间结构,构筑空间融合机制
有研究表明,“不同的城市空间发展形态,影响着城市未来的经济质量、发展潜力与健康状态”。(高新才和滕海峰,2011)[12]由于搬迁移民的空间介入及随之而来的全方位介入,必将引发迁入城镇空间结构的改变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跟随性变化。为了积极应对发展变化,促进搬迁移民与迁入城镇的空间融合,需要立足全局,着眼未来,科学谋划城镇空间结构与发展格局。一是将城镇移民及其安置区纳入城镇范畴宏观考虑、统筹谋划与科学配置,不仅仅是按照规范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要将其作为城镇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二是包括安置小区在内的整个城镇,在政府引导与市场规律相互作用中形成空间结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体系与内在机制;三是在功能分区与空间结构优化中,结合原有城镇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将安置小区列入原有功能区或根据产业、区位、人员等情况确定的相适宜的功能区性质。若搬迁人数超过五万人,可在中心城区周边建设移民小镇或卫星城;四是根据功能区性质,进行片区规划、产业选育、设施配套等相关工作;五是与安置小区相配套,统筹谋划产业园,推动新建产业和企业入园发展,营建市场空间和市场氛围;六是将城镇总体空间规划作为今后城镇建设、格局优化、空间治理、社会治理的行动纲领和法律依据,要持续坚持,久久为功。
(二)优化富民产业发展环境,构筑发展融合机制
搬迁移民进入城镇后,政府帮助开展技能培训后,其就业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在本地扶贫车间、生产性企业、服务性公司就业;二是通过劳务输转到外地务工。相对于本地转型就业,外出务工的经济成本与非经济成本都很高。所以,促进搬迁移民与迁入城镇在经济生产方面的融合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搬迁移民能够本地就业,其直接途经和现实路径是培育和发展富民产业。在“富民”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上,要明确:一是富民产业,不仅仅是“富民”,更是“产业”,只有经得住市场考验的产业才能真正起到“富民”与“强市”的作用;二是富民产业,首要的是追求与城镇发展条件相匹配、并能够提供较多就业岗位的产业类型;三是富民产业,不一定是“高、精、尖”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一定就是弱势产业、夕阳产业,根据市场需求创新发展,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成为优势产业与“强市”“强县”产业。在富民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上,离不开实体经济及各类企业的健康成长。一是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都要将打造地方实体企业当作日常工作和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头等大事,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政府服务;二是在扶贫车间、扶贫企业中注重培养本土企业;三是依托扶贫企业发展和业务拓展,主动和积极培育扶贫产业及辅助产业体系,培育和发展多种多样的本土企业;四是鼓励和推动相关公务员积极参与扶贫企业筹建、生产、管理、营销等全过程,在参与过程中锻造市场意识,增强企业认同感、市场认同感,提升为企业服务的质量,也为国资委投资、市场运营等培育市场人才;五是企业就业过程中,注重培养劳动者的企业文化认同感、市场认同感,既要注重培养合格员工,更要注重培养未来的本土企业家。企业家毕竟都是从企业中走出来的。
(三)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构筑动力融合机制
空间迁移,不仅仅是搬迁移民进城,伴随性地还有农村资源与发展要素进城。优化城乡资源科学配置,推动农村资源向城镇资源转化、农业资源向非农产业转化,切实把原来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动力转化成城镇经济发展动力,促进搬迁移民与迁入城镇在发展动力上的深度融合。一是结合城镇空间布局和结构优化,高效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增加城镇建设有效土地供给,减缓土地价格上涨,增创城镇发展的“土地红利”。二是结合城镇富民产业发展,有效盘活搬迁移民劳动力。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使迁入城镇在短期内增加了一定数量的、以从事简单重复性劳动为主的体力型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形成了富民强县强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口红利”。三是结合各类技能培训,挖掘搬迁移民中的能工巧匠,助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将城镇人才与农村人才的开发和培训同步考虑。四是结合创新发展,将农村原有的技术要素与安置区的技术要素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技术创新要素的融合发展。五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搬迁移民配建各类公共产品、引导建立物美价廉的市场产品营销体系,既为搬迁移民提供便捷舒适的消费生活环境,也通过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四)优化城镇市场环境,构筑社会融合机制
空间迁移,表面上是搬迁移民空间介入城镇,根本上是搬迁移民参与城镇各类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中形成各种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深度融合。较为理想的状态是搬迁移民通过自身诚实劳动、参与社会分工、生产社会产品,获得工资性收入,公平公正、低成本、有尊严、有预期地从事经济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活动的融合促进社会关系的融合。一是营建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开透明、公正司法的社会环境,没有或较少的欺骗、欺压、欺诈,对于本就弱势的搬迁移民来说,在融入城镇的过程中,相信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获取劳动价值与发展空间,这是融合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内在要求。二是招商引资,不仅仅要引资本,更要引进先进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市场氛围,通过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改善社会环境。三是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营造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给企业、创业者、务工者营造一个宽松且充满活力的发展空间,通过营建亲清政商关系、倡导为民务实的作风,为搬迁移民社会融入和安居乐业构筑社会机制。
(五)优化公共教育产品供给,构筑文化融合机制
“空间迁移”客观上改变了搬迁移民外在环境,但内在素质并不会随之自动提升。外因的内化作用,是一个缓慢的演化过程,离不开自身对外在环境的认知与自身素质能力的提升,其关键环节和根本途径是教育。目前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重在技能提升与非农就业,但在文化自信、文化提升、文化认同等方面还存在众多不足。一是从长久计,高度重视幼儿园、中小学等基础教育公共产品的充足与高质量供给,这是帮助搬迁移民教育和培育子女、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关键环节、基本因素与根本举措;二是针对搬迁移民的各类学校,不能仅仅定位为移民学校或者安置区学校,而要与城镇原有各类学校同等定位、同等对待、同等要求,特别是在教育质量与教育目标上要高标准、严要求;三是师资队伍由新聘年轻教师与全市优秀教师共同构成,建立年轻教师成长的“传帮带”机制;四是全市优秀教师动态支援安置区义务教育体系建立和高质量发展;五是将迁出区优秀的文化要素也全部转移到安置区,与当地的优秀的文化资源进行融合,肯定能够达到互补提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