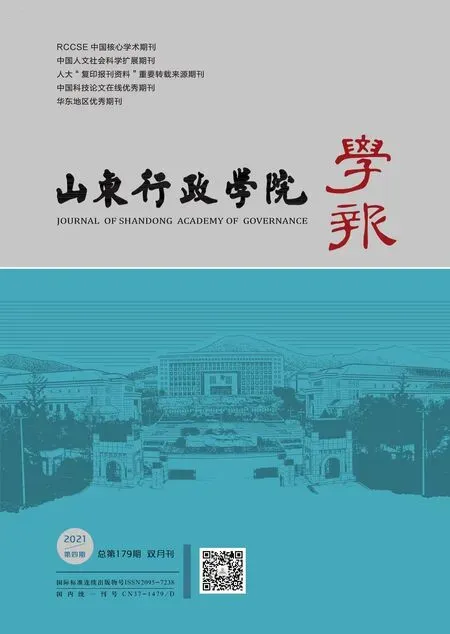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与麦卡锡主义的遭遇
——以太平洋关系学会“亲共案”为例
2021-01-29董嫱嫱路克利
董嫱嫱,路克利
(枣庄学院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枣庄277160;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1951年初,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式开始调查民间智库太平洋关系学会(I.P.R.)“共产党渗透”案。当时,在美国政界流行一种“共产党阴谋论”: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是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等国际共产党蓄谋已久的“阴谋”,“阴谋”实施的机构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共产党通过太平洋关系学会骨干影响美国国务院,操纵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策,最终导致国民党溃逃台湾,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美国失去了所谓的“可靠盟友”。美国右翼政客从反对“共产主义扩张”、反共产党“阴谋”的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国民党的溃败。太平洋关系学会和美国国务院成为美国反共主义攻击的主要目标。1952年7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委员会主席麦卡兰(Pat McCarran)在公布对太平洋关系学会调查报告时的发言中认为:“如果不是太平洋关系学会活动,中国可能还在国民党手里。”(1)Pat McCarran,Speech,John Fairbank papers,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box 5.p.3.报告认定太平洋关系学会成为共产党阴谋的工具。这份报告充满争议,其中的焦点问题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到底是不是被共产党用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工具。从有关档案材料看,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确对中国共产党作了多方面的解读,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一、共产党、“亲共”知识分子等左翼人士长期担任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骨干
太平洋关系学会创立伊始,左翼力量逐渐成其骨干。1925年,一批知名商界、学界、宗教界人士高举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和领导者的威尔逊主义旗帜,在夏威夷成立了太平洋关系学会,旨在交流研讨有关远东国家和地区(北太平洋周边)问题,促进有关国家间相互理解。1934年,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总部迁到美国纽约。该学会发展很快,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中国、苏联等十几个国家建立了分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资金主要是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其会员众多,仅美国分会会员就有1100多人。多位国会议员是太平洋关系学会会员,“二战”名将、曾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马歇尔(Geroge Marshall)将军、曾任副总统的华莱士(Henry A. Wallace)等知名人士都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理事。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主要领导人有多位左翼人士,如主要创立者卡特(Edward Carter)、骨干霍兰德(William Holland)等。卡特190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知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创立太平洋关系学会前曾在基督教青年会印度分会和法国分会工作,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Earl Browder)等人关系密切,长期被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1928年作为卡特的秘书进入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菲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是左翼作家,出身于范德堡家族,由于他本人的左派言行被称为“红色百万富翁”。菲尔德与美国共产党关系密切。1937年,他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任职,同时创办了《美亚》(Amerasia)杂志。该杂志曾发表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John Service)等人在延安对毛泽东的访谈、在延安的见闻等。左翼社会活动家霍兰德,1929年曾在中国担任学会会员、著名左翼经济史专家托尼(R.H.Tawney)的研究助理,共同研究中国土地和劳动问题。1945年,托尼在重庆见过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霍兰德还曾担任美国战时情报局中国处的负责人,战后担任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总干事。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士曾积极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1934年,维金斯基(Grigori Naumovich Voitinsky)等成为太平洋关系学会苏联分会的主要领导。维金斯基早在192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曾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美国国会在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维金斯基这一背景。1952年7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经过18个月的调查,认为有分属于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46名共产党渗透进了学会,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希斯(Alger Hiss)、菲尔德等被指控为共产党员。太平洋关系学会随即发表声明否认,这些人也大都发表声明否认,随着后来的有关档案的逐渐解密,可以确认一些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的共产党员身份。如中共党员冀朝鼎、钱端升、陈瀚笙等是学会骨干会员,曾受学会资助从事研究工作并出版著作。陈瀚笙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为共产国际工作。1935—1939年,陈瀚笙任太平洋关系学会研究员。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瀚笙1925年加入共产党,并开始为共产国际工作。1931年,陈瀚笙在美国加州开始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1938—1941年,冀朝鼎任太平洋关系学会研究员。冀朝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为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委员。《太平洋事务》副主编、知名记者毕恩来(T. A. Bisson)被维诺那档案指控为苏联间谍。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多位骨干曾和中共领导人接触交流。1937年6月,时任太平洋关系学会季刊《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的拉铁摩尔与《美亚》杂志主编贾非(Philip Jaffe)、艾格尼斯(Agnes Jaffe)、毕恩来等通过斯诺(Edgar Snow)等人牵线,到达延安访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热情接待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拉铁摩尔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听了朱德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还在朱德主持下,向延安两千多革命干部和群众发表了演讲。延安之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拉铁摩尔等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贾非和毕恩来都和太平洋关系学会有密切联系。
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政治立场多元,左翼人士发挥了主导作用。以19世纪30年代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分会为例,它囊括了从共产主义者到极端保守派的持各种政见的人士。一些右翼学者后来在国会对同为会员的左翼学者拉铁摩尔、费正清(John Fairbank)等作了不利指控和攻击。如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戴德华(George Taylor)、厄特利(Freda Utley)在国会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听证会上攻击拉铁摩尔,他们的依据就是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拉铁摩尔的一些政治观点,如他在《太平洋事务》的发文认为莫斯科大审判是民主化的先兆,再如他对中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分析。魏特夫(又名魏复古)本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世纪30年代曾受太平洋关系学会资助来中国主持研究“中国王朝史”项目,后来叛党,成为积极反共者。戴德华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通,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战后任华盛顿大学教授,他也是知名的反共右翼学者。厄特利本是英国共产党员,后来积极反共。由于立场和观点不同,太平洋关系学会中的左翼和右翼人士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19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支持者、美国商人柯尔伯(Alfred Kohlberg)退出学会,发起反对所谓“太平洋关系学会被共产党渗透”的运动。柯尔伯等人认为太平洋关系学会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化高度一致:1939年苏德条约之后,二者都反对蒋介石,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后,二者都支持蒋介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前,二者都转为攻击蒋介石;柯尔伯等人在美国组织挺蒋反共的“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成立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American China Policy Association)等多家机构,创办期刊,出版专著,专门从事反共活动,攻击太平洋关系学会以及拉铁摩尔等中国通实施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认为这些人应该为美国“失去中国”负责。
二、太平洋关系学会发表了大量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论述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宣传,影响了美国政界和社会公众的中共观。太平洋关系学会曾召开11次国际学术会议,主办《太平洋事务》《远东季刊》(美国分会主办)等知名专业刊物,出版了数千种太平洋关系领域的书籍、宣传手册等,并长期组织有关远东的研究项目工程,出版了28卷有关成果。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和出版物,包含大量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论述。左翼知识分子拉铁摩尔长期担任《太平洋事务》的主编(1934—1941),该杂志发表了大量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情支持的文章。知名左翼记者斯诺、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曾在该刊发表解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太平洋关系学会也曾积极介绍这些左翼记者作家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成果。拉铁摩尔曾大力推荐知名记者斯坦因(Gunther Stein)的著作《红色中国的挑战》(Challenge of Red China),这本书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而斯坦因被认为是共产国际左尔格间谍网的成员。通过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宣传,西方社会许多人开始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美国右翼政论家维尔瑞克(Peter Viereck)认为,“太平洋关系学会是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机器,学会以宣传所谓农业主义的谎言欺骗美国,在造成美中关系的悲剧中发挥了作用”(2)Peter Viereck,“Breath of Stalin”,How It Blew Through China Policy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New York Herald Tribune,April 18,1952.。耶鲁大学教授饶大卫(David N. Rowe)在麦卡兰委员会攻击拉铁摩尔是“美国远东专家中斯大林主义的代理人”,戴德华和魏特夫攻击太平洋关系学会走的是“共产党路线”(3)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Committee,Hearings o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p. 1043.。
太平洋关系学会在西方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农民改革家”的观点。1929—1930年期间,拉铁摩尔在中国东北考察9个月后写成的《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一书中,“认为中共只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起义在20世纪的表现形式”(4)Owen Lattimore,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Macmillan,1932;rev. ed. 1935.。这是拉铁摩尔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时的初步印象。太平洋关系学会在1944年出版的宣传册,介绍了知名记者斯图尔特(Maxwell Stewart)的专著《战时中国》(Wartime China),其中赞赏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维护大众利益的“农民改革家”,否认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宣传册把“中国红色分子(Chinese Reds)”即中国共产党描述为相当于美国的草根民粹主义者,并且得到很多进步人士和爱国的中国人的支持。1952年1月31日,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辩护者范宣德(John Vincent)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作证时承认,这些小册子有亲共倾向。“这些小册子使美国公众更加相信中国红色力量放弃了极端方式,走的是改良主义而非革命的路线。”(5)Peter Viereck,“Breath of Stalin”,How It Blew Through China Policy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New York Herald Tribune,April 18,1952.右翼分子认为,这是在迷惑美国政界和公众,博取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但由于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是自由主义,政客和普通民众对共产主义、共产党难以理解,往往有抵触情绪。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共产党执政的苏联同属反法西斯联盟,反共主义在美国社会影响很大。另有一些中国通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中国性”,和苏联的共产党有很大的区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抗战力量,主张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援助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在戴维斯、谢伟思等积极要求下,美军向延安派驻了观察组。
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费正清等中国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毛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以此为自豪。他们和苏联的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一致。但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6)John Fairbank,“Our Chances in China”,Atlantic Monthly,September,1946,p.38.。费正清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性,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也是真正的中国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主义”。1951年,费正清指导的史华慈的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即提出了“毛主义”概念,这是费正清观点的体现。费正清等中国通强调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性和独立自主等特点,实际上是在批评当时美国政界和学界流传的阴谋论。这种阴谋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傀儡,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国际共产党长期阴谋操纵的结果。这种阴谋论在政界的代表是右翼政客、威斯康星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人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以及负责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联邦参议员、民主党人麦卡兰。在学界的代表人物是魏特夫、戴德华等人。费正清与他们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发生了长期的争论。
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戴维斯(John Davies)等中国通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中国老百姓更希望“毛泽东的民主”,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广大农民的支持。1944年11月7日,戴维斯在报告中分析,“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而非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7)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U.S. Govt. Print. ,1949,pp.573,572,567.戴维斯建议,美国政府应当与国民党保持距离,要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防止苏联在中国扩张,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1944年12月9日的报告中,戴维斯预测,“中国内战中,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国民党一定会失败,美国政府不可能给蒋介石提供足够多的帮助以打败共产党。”(8)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U.S. Govt. Print. ,1949,pp.573,572,567.1945年1月4日,戴维斯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比欧洲任何革命力量强大。”(9)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U.S. Govt. Print. ,1949,pp.573,572,567.以戴维斯为代表的中国通较早预测了国共两党斗争的未来趋势,他们看好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合作的重要目的是防止战后中国被苏联操控。
关于在美国宣扬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拉铁摩尔、谢伟思等中国通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国民党必败。因此,他们主张说服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政策主张的支持者、实施者有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骨干。赫尔利大使、马歇尔上将先后来华调停国共矛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赫尔利曾在中国推动国共和谈、建立联合政府但归于失败。马歇尔促使国共建立联合政府的调停也很快归于失败。美国右翼分子指责马歇尔受到亲共分子的蛊惑,片面推动建立联合政府,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喘息机会,局势向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转变。
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严厉批评国民政府,要求其改革。太平洋关系学会多位骨干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预测到国民党将来会败给中国共产党。拉铁摩尔在1943年被罗斯福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起初,他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抗战的希望。但不久后,他对国民政府大失所望。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思、费正清等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国务院工作的中国通普遍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他们写给总统和国务院的报告中以及在美国发表的评论中都严厉批评国民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国民党的看法。1943年以前,美国还有相当多的公众援助抗日,此后,得知国民党腐败无能后,很多人失去了援华抗日热情。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骨干曾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1951年7月25日,曾担任太平洋关系学会总干事16年的卡特在国会作证时承认,1938年,时任学会会刊《太平洋事务》主编拉铁摩尔写给他的一封信的内容是真实的。在这封信中,拉铁摩尔谈到:“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立场对各国有所区别。对中国,应当站在中国共产党身后适当距离,既不要太近,免得被称为共党,也不要太远,要走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前面。对苏联,要支持苏联的国际政策,但不要用他们的宣传话语,避免造成服从苏联的印象。我认为你把太平洋关系学会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交给亚提斯(Asiatious)、陈瀚笙、冀朝鼎等是谨慎的,他们一定会作出有进步意义的研究。”(10)Peter Viereck,“Breath of Stalin”,How It Blew Through China Policy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New York Herald Tribune,April 18,1952.而亚提斯、陈瀚笙、冀朝鼎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亚提斯是指穆勒(Hans Mueller),是德国医生,长期在中国工作。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员立场观点多种多样。左翼成员对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支持理解的论述,右翼成员积极反共,大多数成员和中国、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分会主办的杂志《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在国务院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后,随即发表了三篇评论文章。罗森杰(Lawrance K. Rosingger)概括了国务院的立场,费正清从国民党的批判者的角度批评了国务院,林柏格(Paul M. A.Linebarger)则站在支持国民党的立场上批评了国务院。太平洋关系学会右翼成员积极反共。一些右翼成员如魏特夫、戴德华等,经常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国际共产党的阴谋,他们还攻击学会左翼中国通的观点。1951年9月,魏特夫在给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费正清同事和连襟史莱辛格(Archur Schlesinger Jr.)的回信中认为,“费正清在中国问题上是幼稚的,拉铁摩尔在苏联和中国问题上都是幼稚的。”(11)Karl August Wittfogel,“Letter to Arthur Schlesinger Jr”,John Fairbank Papers,HUG(FP),12.30.box 4,p.2.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左右翼成员之间,在“毛主义原创性”等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问题上,发生了长期的争论。
三、太平洋关系学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关系学会多位左翼骨干会员成为政府重要职员。由于当时美国严重缺乏有关具备远东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专业知识的人才,太平洋关系学会成为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智库和人才库,成为中国研究和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国际智库。很多会员在美国政府和其他成员国政府担任要职。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骨干如拉铁摩尔、戴维斯、范宣德、杰赛普(Philip C.Jessup)、费正清等,在美国国务院、战略情报局担任要职。拉铁摩尔是知名的中国通,长期在太平洋关系学会担任重要工作,担任学会会刊《太平洋事务》主编。他被反共参议员麦卡锡指控为“头号间谍、共产党”。右翼势力认为在国务院等政府部门工作的这些中国通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已被共产主义洗脑。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国务院官员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1944年,太平洋关系学会两个骨干成员、国务院官员范宣德和拉铁摩尔随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在这两个亲共随员的影响下,华莱士中国之行实际上对共产党有利。1944年6月18日至7月2日,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受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委派,途径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先后访问了中国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昆明、桂林、成都、兰州6座城市,这是抗战时期到访中国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在任领导人。华莱士正式向蒋介石提出美方准备派遣军事观察组到延安,美方有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蒋介石在压力之下,不得不表示同意。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开始工作。谢伟思等观察组主要成员在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着广泛深入地交流。中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察组给国务院发回大量报告,多次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印象。1945年2 月中旬,谢伟思在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准备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仿效英国首相丘吉尔,根据一切党派在对德作战中的表现,而不是以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决定是否提供援助;并希望美国政府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从自身角度考虑,反对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等。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国务院官员要求国民党改革,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中国通在给国务院和白宫的报告中提出,由于国民政府丧失人心,必须改革。美国要想保住国民政府,必须要求其改革,与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美国政府先后派遣赫尔利、马歇尔等来华调停,其主要目标就是催促国民政府改革,建立联合政府。由于国民政府改革不力,热衷发动内战,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中国通要求美国政府限制对国民党的援助,甚至制裁国民政府,一度实行武器禁运。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中国通参与了《与中国关系白皮书》的起草。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认为国民政府应为失去中国负责,主要是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了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份白皮书的主要起草者杰赛普(Philip C Jessup)、卡斯(Everett Case)等人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骨干。杰赛普1939—1942年期间担任太平洋学会美国分会主席。《与中国关系白皮书》被美国右翼分子、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等势力抨击为是在为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开脱责任,标志着美国政府一度放弃了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这成为国会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列出的一大罪状。《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严重打击了蒋介石军队的士气。
太平洋关系学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中高级官员如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思、杰赛普等人都和太平洋关系学会有比较多的联系。其中,杰赛普曾长期担任太平洋关系学会骨干,曾担任美国分会总干事。这些中国通早在1943年起,就开始看好中国共产党、批评国民党。他们给国务院和白宫写了大量有关国民党、共产党的报告,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绝不是少数几个所谓的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专家能够左右的,更不可能靠一些所谓的国务院、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共产党人阴谋小集团的活动来造就。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主要靠党的坚强领导、人民的衷心拥护。
四、太平洋关系学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解读和态度被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攻击
太平洋关系学会成为美国反共主义的主要目标。美国右翼保守势力长期反共反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右翼保守势力的煽动下,美国社会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大恐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右翼势力拉开冷战帷幕,对共产主义的第二次大恐慌产生,引发了新一轮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夺取国家政权,对西方右翼势力是极大刺激。美国政界、学界、媒体爆发了“失去了中国”的争论,右翼政客抓住这一问题大搞政治攻击。1950年初,反共参议员、共和党人麦卡锡公开攻击美国国务院和太平洋关系学会,声称大批共产党渗透进美国政府机构,认为“失去中国”是国际共产党的阴谋。共和党右翼政客攻击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其反共立场使然;另一方面,是要借此攻击民主党政府。麦卡锡写作出版了《马歇尔的故事》(The Story of George Marshall),对曾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国防部长的“二战”名将马歇尔大肆攻击。马歇尔曾来华调停国共冲突,也曾是太平洋关系学会重要会员。太平洋关系学会成为右翼势力反共的重要目标,也成为了美国政党政治斗争的替罪羊。
美国第82届国会的调查报告认定太平洋关系学会是“共产阴谋的工具”。1951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得到了太平洋关系学会前总干事卡特保存在其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小城李市家中谷仓的有关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大量档案材料。右翼分子如获至宝,开始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1948年,右翼反共众议员尼克松在参加非美委员会调查“希斯共产党间谍案”时获得“南瓜文件”(文件被发现藏在南瓜里),直接导致希斯被判有罪,尼克松成为当时的“反共英雄”,博得大名,成为政治名人。参议员麦卡锡、麦卡兰等右翼投机政客以为这次获得的“谷仓文件”是重大发现。1951年成立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之下的国内安全委员会负责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在美国远东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及其受共产党渗透情况。对太平洋关系学会遭受共产党渗透的指控,主要由参议员、共和党人麦卡锡发起。麦卡锡、麦卡兰都是积极反共的右翼政客。美国第82届国会司法委员会调查报告认为,太平洋关系学会是共产党用来转变美国远东政策以达成共产目标的工具,该学会支配了美国国务院远东政策达15年之久,不仅影响了国务院对远东方面人事的安排,而且伪造报告攻击“蒋委员长”,宣传毛泽东不是共产党而是土地改革者。报告认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是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而由各种基金支持的太平洋关系学会责任最大。
太平洋关系学会对麦卡锡主义的进攻进行了坚决反击,但最终不得不宣告解散。太平洋关系学会发布了对国会调查报告的公开驳斥。太平洋关系学会认为,麦卡兰报告调查程序违背了公平原则,调查方法存在严重错误,调查结论违背事实。太平洋关系学会认为麦卡兰委员会扩大了共产党员和亲共分子的概念,国会委员会错误地把一些在《美亚》杂志发表文章的作者也归入太平洋关系学会。1945年,联邦调查局突袭调查了《美亚》编辑部,以涉嫌“占有发表政府机密文件”逮捕了该刊主编贾菲、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人。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美亚》案”。《美亚》杂志和太平洋关系学会及其会刊《太平洋事务》在纽约的同一栋楼办公,《美亚》杂志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员。但该学会认为,《美亚》杂志和太平洋关系学会并没有隶属关系。太平洋关系学会认为,报告夸大了其对美国政府有关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决策的影响。麦卡兰委员会报告指控,1945年间,范宣德和拉铁摩尔在美国对华政策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改变发挥了影响作用,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范宣德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身处国务院的一个支点(fulcrum)。即便如此,太平洋关系学会认为,这并不能表明美国政府对共产党态度的根本性改变。美国当时寻求中国共产党合作,甚至提出援助中国共产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务实选择。当时美国在国际上和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是反法西斯盟友。日本帝国主义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敌人,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麦卡兰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司法部起诉追究拉铁摩尔和戴维斯的伪证罪,但二人最终胜诉。国会议员建议国家税务局取消太平洋关系学会作为非盈利独立学术组织的免税资格。太平洋关系学会有关免税资格的诉讼也最终胜诉。但从遭受国会正式调查的1951年起,由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社会声誉受到极大损害,其主要经济来源——社会捐助大幅下降。今后的几年又持续下降,难以为继。1960年,太平洋关系学会不得不解散。太平洋关系学会后期主要负责人霍兰德离开美国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其主要刊物《远东事务》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出刊。
国际社会对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评价褒贬不一。在遭受右翼反共势力攻击的同时,国际左翼力量则多表达对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同情和支持。1952年6月,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学者汤恩比致信赞扬太平洋关系学会,认为“太平洋关系学会是客观讨论有关中国、日本等亚洲问题重要平台,是我了解时事的主要来源”(12)Arnold Joseph Toynbee,Commentary on the McCarran Report on the IPR,New York,1953,p.38.。与此同时,太平洋关系学会在苏联受到了批评。一些苏联媒体把太平洋关系学会批评为“华尔街帝国主义的喉舌”“海盗和强盗的组织”(13)William Holland,Facts and fiction,John Fairbank papers,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HUG(FP),12.30,box 3,p.18.。由于太平洋关系学会对中国共产党作了多种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由此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太平洋关系学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遭遇了麦卡锡主义的攻击迫害。由此可见,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也是一个政治敏感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