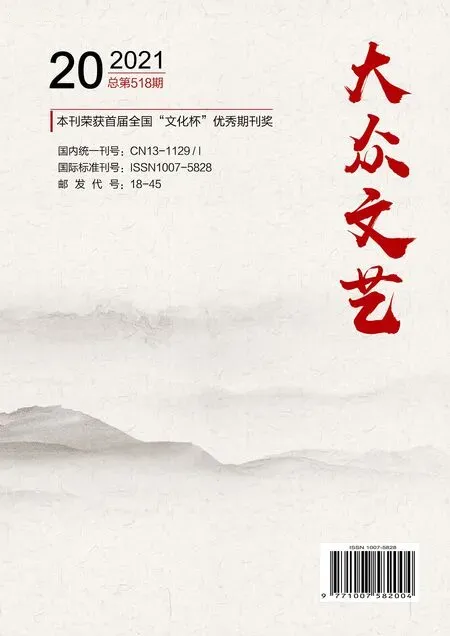试析甘肃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丝路文化”书写价值*
2021-01-28
(陇东学院 文学院,甘肃庆阳 745000)
早在1950年赵燕翼、金吉泰等甘肃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中就流露出浓厚的“丝路文化”特色;接着汪晓军、许维等一大批作家在其作品中关注敦煌壁画和石窟雕刻等“丝路文化”艺术,在奇异的佛教故事中叙说敦煌飞天在西域的弘法说佛,展现宝窟画魂和敦煌传说在童话创作中的炫丽故事,使甘肃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焕发出“丝路文化”的艺术魅力;还有藏族作家益希卓玛以及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儿童小说中将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和民族融合结合起来,实现了甘肃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多面绽放,这种创作使甘肃当代儿童文学彰显出明显“丝路文化”色彩。
一、西部自然景物和历史文化遗址彰显“丝路文化”的人文景观价值
甘肃当代儿童作家,他们大多生活在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的节点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相关的历史传说作为载体,创作出丝绸之路沿途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内容揽扩丝绸之路的浩瀚草原、祁连雪山、大漠驼队等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使甘肃当代儿童文学从独特的地域文化中获得了深厚的“丝路文化”价值。
赵燕翼的《新草原传奇》、金吉泰的《埋在沙漠里的童话》以及刘虎的《白鹿》《心在旷野》等作品都极具西部人文景观价值,特别是在赵燕翼的《驼铃和鹰笛》一书中,作品重点描写了河西走廊之间和新疆阿尔泰山地区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他的作品这样叙写西部自然景色:“有遍地的茅草和灌木,灌木草丛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花朵,有鞭麻花、血节花、蜜管花、喇叭花、香柴花、野菊花,淙淙地流着的小溪,被暖烘烘的太阳蒸晒的茂草野花……”[1]还向我们展示了草原上的黄金一般的秋天,哈萨克族牧民赶着牛羊马匹骆驼,走出天山深处集聚到伊犁河畔,欢腾的冬布拉伴奏着嘹亮的牧歌在草原上飘荡。
“童话在本质上是儿童与大自然的对话,在对话中儿童感知了自然的广袤无垠,感知了自然中千姿百态的事物之间的联系。”[2]童话之所以能影响儿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符合儿童形象思维的规律,将五彩缤纷的自然世界和奇异的故事结合起来,引导儿童追寻奇幻的童话世界。
甘肃当代儿童作家身处丝绸之路的沿途,将自然景观蕴含于人文景观之中,以优美抒情的笔调在细腻而又深刻的叙述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自然景物和浓厚的丝路文化氛围,给儿童文学作品中融进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意蕴。“使我们格外深切地意识到童话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一种精神式的宝贵和重要。”[3]而这种精神载体便是在浩瀚草原、古道驿站和大漠驼队所蕴显出来丝路文化,它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在西部开拓过程中的文化遗产和遗留的历史见证,沉淀着中华民族在西部的各种文化根源,引领着我们不断向这条神圣的道路上进发,让少年儿童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神奇。
二、敦煌情结与丝路情缘的结合显现“丝路文化”的历史审美价值
敦煌童话就是以壁画中的故事为题材,然后加上作者神奇的想象力,用现代想象为少年儿童量身定做的新童话。甘肃当代作家立足于敦煌文化,叙说着丝绸之路留下的飞天漫舞和九色鹿母等众多的题材渊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情趣,使甘肃当代儿童文学在吸收敦煌文化中立于世界之林。“古丝绸之路在漫长宏阔的时空中,留下了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丰富遗产,也开启了艺术地表达多样文化和沟通人类情感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当代价值。”[4]丝路文化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记忆,可以在儿童的心底埋下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事关儿童全面发展与民族未来。
甘肃儿童代表作家汪晓军编辑的《敦煌童话》中很多题材来源于敦煌壁画故事中的佛教故事,他编辑的《敦煌童话》中的《五百壮士建王城》,故事原型出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其情节是依据《大般涅槃经梵行品》而构思的。《五百强盗成佛》中故事的虽然讲的是五百个饥民不堪承受苛政赋税揭竿直到最后受戒皈依佛门,他们洗心革面修成正果成为五百罗汉,深深彰显着丝路文化的佛教情缘。从故事的创新之处看汪晓军在童话中去除了宗教文化的糟粕,吸取了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之精华,使童话在敦煌壁画故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还有王家达在《莫高窟精神》中以敦煌壁画和石窟艺术为描写主题,在奇异的佛教故事中展开情节,细说敦煌飞天在西域的弘法说佛,展现的沙月遗恨、三危灵光、宝窟画魂等敦煌传说。除此之外,金吉泰的《莫高窟纤夫》和冯玉雷《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以及许维《飞天》等“敦煌系列”文学,将飞天的文学内涵融入童话故事中,展现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为原型的敦煌佛教文化,获得了壁画佛教故事与现代童话的精神契合,展示了甘肃当代敦煌童话的新魅力,使丝绸之路童话给当代甘肃留下的不仅仅是物质遗产,更多的还是文化和艺术的创新之源。
三、黄河文化中的神灵崇拜表现出“丝路文化”的生命寻根价值
丝路文化起源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文化,而黄河渡口正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黄河水流湍急,在黄河两岸的羊皮筏子、雄壮的男人、汹涌的河水和祭祀河神仪式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丝路文化的重要意向。甘肃当代作家王家达从小在黄河边长大,水车、羊皮筏子和河神祭祀是他成长中的重要印记,许多关于河神神秘莫测的故事在他的脑海回荡,于是赞美黄河和敬畏黄河在王家达的心中根植出神秘莫测的传说。
在《血河》中写道“年轻的水手羊报在黄河汛期之际,他的身后拖着深深的血迹,那血便融入黄色的浪涛,这条大河便变成了一条血河。”[5]接下来四月八日迎河神,筏子客们用麦草扎成高大无比的河神爷,由众人抬着在冰桥上前进,羊报穿着宽大的法衣,大声唱着祝福歌,在火边载歌载舞,时而尖叫一声,直仰仰地躺在地上,这就叫作“走魂”。“驱使人去崇拜某个对象的那种感情,显然是一这个观念为前提:即人认为对象并不是对这种崇拜无动于衷的,它有感情,它有一颗心,而且又一颗感知人类事物的心。”[6]因此,古代黄河人民去祭祀和崇拜黄河河神,也成为一种特有的丝路文化情结。不难看出,黄河贯穿于河边两岸人民的血脉之中,而河神也正是黄河两岸人民的心灵寄托,羊报祭祀河神,这也就说明河神不单单是掌握黄河两岸风调雨顺的神秘力量,同时也更加趋向于“老天爷”的角色,调控人民的愿望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得到河神保佑的原型彰显。
而在《清凌凌的黄河水》中,尕奶奶与二哥子因为羊皮筏子而结缘,但由于村里人的不理解,尕奶奶与二哥子在逃亡中失水淹死,最后年老的二哥子孤零零地守着尕奶奶的坟墓而与黄河结缘,这也正是河神文化深入骨髓的影响。通过王家达等西北地区作家的努力,让人们能够更加地了解黄河流域独特的风土人情和黄河两岸人民旺盛的生命力,而这正是王家达在《清凌凌的黄河水》中肆意追求生命崇拜的精神支柱。
四、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丝绸文化”的精神融合价值
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裕固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之间多姿多彩的文化风俗是彰显丝路文化的重要内容。裕固族作家铁穆尔主要以草原游牧文化的独特书写深受人们追捧,为保护和传承古老优秀的民族文化,他在《山那边有个地方叫友爱》中这样写道“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迁徙鸟和大雁排着队,在秋季草原上掠过,带走了游牧人的思念。”[7]铁穆尔真切地书写了裕固族人民在人迹罕至的辽阔大草原崇拜自然,遵守自己民族文化密码的生命轨迹。他所呼唤的不仅仅是游牧民族对草原生活的怀念和向往,更是对游牧民族历史和生活的记录以及对游牧民族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
藏族作家益希卓玛在长篇儿童小说《清晨》中,以藏族儿童为形象概括着藏民族的整体性格。“他赤裸着腿脚,黝黑粗壮的身躯上,斜挎着一件褴褛的没面子的皮袄,裸露的右臂突出结实的筋肉。在他那一头蓬乱的卷发下,两只大眼睛紧盯着难驯的青马。”[8]从这里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勤劳英勇刚毅坚强的藏族人民的天生性格,他们养成了藏族人民一往无前,不畏艰险的民族气质。藏族在丝绸之路沿线生存了数千年,始终热爱着丝绸之路上的山山水水,这些自信的民族情感无疑在藏族文化环境中展现出来。
“丝路文化”不仅体现丝绸之路沿途各个民族的文化性格,更强调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精神遗产的融合,以及少数民族在西部开拓与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遗产和人文精神,对民族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益希卓玛在《清晨》一文中叙写被压迫孩子巴丹为了学习汉语和精通汉藏翻译,历尽千辛万苦地去北京学习的故事,说明了民族融合带来的文明进步,更是汉藏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果。丝绸之路作为一座文化桥梁对沿线各民族的交流融合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丝绸之路各种文明的接触与交流互为表里的关系,使丝路之路上的各种文化加深联系,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向前的发展进程。
综上所述,甘肃当代儿童作家们利用“丝路文化”题材创作儿童文学,加深了甘肃当代儿本土化进程,使童话彰显着的西部情怀,增添了童话人物形象的历史厚重之感,增强了具有传承历史文化使命的丝路情缘。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丝路文化”是古代东西方文化汇聚的十字路口,沉淀着各种神秘色彩,“丝路文化”从自然人文景观到主体意识的审美契合,渗透着浓厚的历史传承和深层的文化融合色彩,这便是当代甘肃儿童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丝路文化”价值。